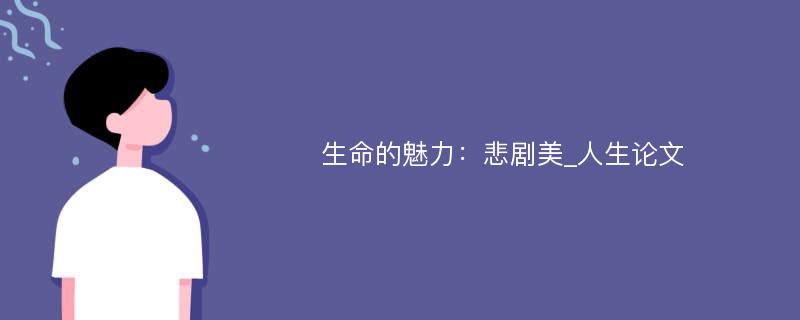
《人生》的魅力:悲剧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魅力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1-0076-05
路遥的《人生》是新时期文学中少有的持续拥有大量读者的小说作品之一。当然,路遥小说的读者有一大部分是青年。也许获得这一特殊的阅读群体,可能会削弱路遥小说的艺术普遍性和思想深度,因为青年群体阅世经验的不足和情感反应的直接化,可以反射出作家的艺术创造对于期待视野的迁就,而这种迁就会导致作家有意摈弃时代的一部分最有探险性的思想资源,也无意提高艺术创新的难度。《人生》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变革时代,但它没有被归入当时最有冲击力的新潮文学当中,多少反映了路遥艺术选择的局限性。但从另一方面看,路遥独立不倚,不赶潮流,完全从自我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满怀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虔诚,深情地讲述发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人生故事,正表明了他对占有了小说创作成功的最重要的元素(人的命运与人生纠葛)的自信。事实上,路遥的小说用真实的力量证明了写实型文学的美学价值。二十几年过去了,文学潮起潮落,但《人生》没有被读者遗忘,而水落石出般地从不同的文学思潮中凸现出来,以典型形象的悲剧美继续征服着今天的读者。
《人生》着力塑造,并达到“典型”这一艺术高度的,是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作者路遥怀着复杂的心情,刻画了他的性格并展现了他的人生轨迹。与这一人物密切相关,且同样富有典型意义的小说主人公,是农村女青年刘巧珍。路遥在这部小说里展开人生思考的创作主旨,并不是想通过这一人物的性格命运来体现的,但这一形象的成功描绘,给小说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作者的本意可能是借这个人物的爱情追求的不幸,对造成她人生不幸的人进行道德谴责,以表达自己对人生价值实现的原则①的理解。然而,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对乡村青年女性的性情、心理和人生追求有深透的了解,并进行了逼真的描绘,巧珍因此成了《人生》世界里的又一个主角。整个《人生》故事,就是以她和高加林的戏剧性情爱纠葛展开情节,并以各自人生理想的破灭产生悲剧效果的。
有抱负有才华的回乡知青高加林,与外貌和心灵都异常美好的乡村女子巧珍,一个追求事业,一个追求爱情,是那样地专注与炽烈,然而在一个并不能由他们自己把握的历史命运的左右下,他们的理想追求都遭到挫败,他俩都成为悲剧的承受者。所不同的是,高加林自己参与了对他的人生悲剧的制造,他的悲剧结局,给人以咎由自取的意味,而巧珍却好像是无辜的,她的悲剧就更让人同情、怜悯和惋惜,也就是说,在读者的心灵里,巧珍的不幸更能引发悲剧的美感。《人生》正是通过这两个主人公,写了两类悲剧,一类是在高加林身上体现的人生奋斗的悲剧,一类是巧珍身上体现的爱情悲剧。两者都带有宿命色彩,但前者更带有社会性,而后者更富有人情味,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出身农民的作家路遥对于生活的悲剧感,同时满足了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或有底层生活经验的读者对悲情艺术的期待。
先看高加林的悲剧。高加林的悲剧是农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奋斗的悲剧,确切地说,是当代中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村青年才俊的人生悲剧。高加林生在农村,父母是老实巴交、胆小怕事、认命吃苦的农民,但他自己不甘于走父母的路,而一心逃离农村,逃离祖祖辈辈的农民身份和务农生涯。高加林背弃乡村与父辈,是因为他有了比窝在农村当农民要好得多的人生目标,那就是做一个城里人,靠知识来谋取生存的位置,实现人生的价值。高加林从农村考进县城念书,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安心父辈的生存方式。进城和读书,让他看到了跟农村完全不同的世界和跟当农民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落后而贫困的乡村,与现代化的城市,劳苦而贫穷的农村人,与快活而富足的城里人,对比是如此强烈,差别是如此之大,更何况现代教育为高加林拓开的视野,哪里仅仅局限于一座县城,而是寰球世界!(用他的话说,“我联合国都想去!”)精神的高加林,不仅不是他父亲那样的农民,甚至不是一般的城市市民,由于有读书写作的爱好和拥有人文和科学知识,高加林是比普通市民甚至某些国家干部合格得多的城市人。高加林不仅知道应该而且有能力到城市里去发展自己,而不是屈居于闭塞落后的乡村,从事极为原始的劳动,浪费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受制于愚昧,看不到前途,忍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对城市的向往,其实是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所以,出身于农民而拥有现代知识的高加林,“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就很正常,“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②也完全合理。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角度看,成长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高加林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性格。这正是路遥对这一人物进行塑造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地方,也是作者对主人公的人生追求予以肯定的理由。但是,在小说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高加林的正当追求以失败而告终,他的人生抱负和理想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的挫折。
高加林的失败,在于他的人生追求是一种超越了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个人奋斗行为。横亘在他奋斗路途上的是政治权力和社会体制,这注定了他的人生之路艰难而孤苦,除非出现偶然性,不然他的挫败就是必然。被高考制度抛回农村的高加林,本来已获得了逃脱当农民的机会:他凭县中的学历当上了民办老师,取得了文化人的身份,继续努力的前景就是转为公办老师,彻底成为一个“工作人”。有天分,有学识,本人又努力,高加林不愧为一名称职的乡村学校老师。可是,大队书记高明楼,为了自己从学校毕业回村的儿子,竟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教育干事勾结,悍然下掉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把他抛进了人生的深渊。高加林遭遇的是权力对知识的轻易的剥夺。它虽然只是国家政治权力在其神经末梢上的一次轻微的颤动,但一位满怀理想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前程顷刻就被断送了。在政治权力面前,知识和它的主体,原来如此脆弱。虽然陷入了愤怒和痛苦的高加林,因为落难而意外地得到了纯洁爱情的舔舐,但是被爱情抚慰减轻的伤痛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强加给他的农民身份,破灭了的理想仍时时碎玻璃片似的刺激着他,直到幸运再一次对他垂青。
如果说,高加林在乡村里遭到权力的挤兑,被生生夺走适合于他并为他所钟爱的教师职业,他的愤恨还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土皇帝、大队书记高明楼——的话,那么,他第二次遭到更严重的褫夺、更惨重的人生打击,作为受害者的他以及所有惋惜、同情于他的人,就连想都没有想过造成农村知青人生悲剧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其实那是一种看不见的无形力量,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体制,高加林和他的同时代人不加质疑也无法质疑地接受了它。因叔父从部队转业到地区当劳动局局长,经媚权者操作,高加林一夜之间由农民身份变成了国家干部,彻底脱离了农村,进了梦寐以求的城市,走上了既光荣又能发挥他的才智的工作岗位——担任县委通讯干事。有知识、有能力、有进取心的高加林很快在这个岗位上施展出了他的才华,显得那样称职。县城的文化生活也让他如鱼得水。以记者身份频频出现于会场,以潇洒的青春姿态活跃于周末的球场,他俨然“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城市给了他发挥生命潜能的最好舞台,在这里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另一种爱情也热切地光顾,更美好的人生前景在远方向这个本来就不安分的灵魂亲切地招手……可是,这一切又转瞬间化为泡影!高加林靠“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被人告发,一夜间,从城市户口到国家干部身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城市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以不正当程序钻进来的农村青年踢了回去。飞得越高,跌得越惨。与前一次的打击相比,这一次对于人格尊严和人生理想的摧残是毁灭性的。试想一个一心求上进的青年人,正当他在城市舞台上表演得最为精彩的时候,突然被粗暴地呵斥、驱赶了下去,这是多么尴尬而黯然的人生一幕!始料未及的残酷打击,使沉浸在前途畅想中的青年高加林“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当听完对他的处理意见,他“脑子一下子变成了一片空白”,“麻木地立在脚地当中,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一个钟头以后,他的脑子才恢复了正常”。与前一次被剥夺民办教师资格,他立即做出激烈反应相比,这次的迟钝反而表明遭受的打击程度要严重得多,其悲剧性也强烈得多,它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朝阳般的青春生命突然堕入无边黑暗时的人生剧痛。“他一直向往的理想生活,本来已经就要实现,可现在一下子就又破灭了。他感到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赶忙用拳头抵住”。悲剧感就来自这种谁都害怕经受的巨大的人生失落。
高加林的人生奋斗悲剧是谁造成的呢?表面看起来,是高加林人生得意后,抛弃了一个字也不识、没有文化的农村恋人巧珍,与老同学黄亚萍旧情复萌,从已经确定恋爱关系的张克南与黄亚萍之间横刀夺爱,因而激怒了张克南的母亲,这个本来就鄙视农村人的“国家干部”,以“维护党的纪律”为理由,给地纪委写信检举揭发高加林,致使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问题,被地纪委和县纪委迅速查清落实予以处置——立即坚决地把他退回了农村,这样,高加林的人生挫折也就似乎主要是他自己私生活不道德造成的。连高加林自己也这样认为:“这一切怨谁呢?想来想去,他现在谁也不怨了,反而恨起了自己: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也就是他自己的人生失误导致了这场悲剧。高加林为此悔恨自责,小说描写也明显地把高加林的人生奋斗与失败引向道德领域。这不能不说作家在透视决定人物命运的时代生活时,眼光还不够深邃,小说在叙事上的分裂由此造成,无怪李美皆说“《人生》中存在着是两个路遥”[1]。不过,即使把人生受挫的原因归咎于高加林本人,故事的悲剧力量也是强大的,因为由判断与选择失误导致自毁前程正是人生莫大的恨事,它正是面对茫然人生的人类所恐惧的。高加林的悲剧,引起的就是这样的恐惧,它的悲剧效应在道德检省层面上照样会发生。
但是,高加林的悲剧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它引起的是另一种悲剧感。高加林即使没有移情别恋并开罪于人,他进城后的人生之路也不见得会一帆风顺。对于突然由农村人一跃而为城里人,高加林在喜极之余不是没有隐忧。“高加林进县城以后,情绪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他高兴得如狂似醉,但又有点惴惴不安。”说明在潜意识里他已认同了对自己的农村出身不可随意僭越。在终于被“组织”从身上扒走突然得来的一切,变得“像个一无所有的叫花子一般”,“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靠店”之后,高加林“甚至觉得眼前这个结局很自然;反正今天不发生,明天就可能发生。他有预感,但思想上又一直有意回避考虑。前一个时期,他也明知道他眼前升起的是一道虹,但他宁愿让自己把它看做是桥!”也说明胸怀远大但出身卑贱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不是没有意识到理想的实现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存在多么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希望的那种‘桥’本来就不存在;虹是出现了,而且色彩斑斓,但也很快消失了。”这就是他不能不接受的现实。高加林纵有超群的才能,但他的命运被一种冥冥中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所控制,在他渴望成功的心灵里,似乎埋伏着一种原罪感,只要他的人生稍稍得意,惩罚就会随即而至。
其实,对这种笼罩在他头上的无形力量,连他的父辈都早有感应。在他赤手空拳离开县委大院的前夜,他让同村开拖拉机的三星事先将他的铺盖卷捎了回去,对于儿子的被逐,他的父母竟没有感到意外和伤痛,“玉德老两口倒平静地接受了三星捎回来的铺盖卷,也平静地接受了儿子的这个命运。他们一辈子不相信别的,只相信命运;他们认为人在命运面前是没什么可说的。”被农业社会的历史固置在土地上的老一代农民,不敢奢望他们的后代有更好的命运,自然也不具备怀疑现实合理性的思想能力。然而在城乡交叉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获得了另一种人生参照的农村新人高加林,同样不能理性地知解左右他们人生奋斗成败的社会历史真相,可见当代中国形成的社会体制的惯性力量和它对于底层人的精神奴役作用有多么强大。打击高加林的无形力量,就是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提及的城乡分治社会体制。③这一体制造成的城乡差别把中国人分成差别极大的不同的两大等级,不知使多少出身农村的“英俊”,蒙受人生的屈辱(如高加林到城里淘粪受到张克南母亲的无理责难),失去人生进取的机会,甚至不得不承受遭到人生重创后的痛苦。路遥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通过高加林这一形象写出了在城乡二元社会里的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悲剧,这种悲剧近似于英雄悲剧,因为它的主人公所要抗争的是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以他引发的就是带有崇高意味的悲剧美感。路遥在审美创造时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小说一开头用写景(大雷雨)烘托气氛,表现高加林遭遇不测,无端失掉民办教师资格产生的家庭灾难和精神痛苦,就是悲剧艺术常用的处理手法。高加林乐极生悲,从省城学习还没回来就被县委常委会撤掉了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变得一无所有,不得不离开这个给过他光荣和梦想更给了他打击和耻辱的城市,向着他的来路逆行,“他走在庄稼地中间的简易公路上,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难受”,回想已经走过的短暂而曲折的生活道路,后悔失去了巧珍“火一样热烈和水一样温柔的爱”,“他忍不住一下子站在路上,痛不欲生地张开嘴,想大声嘶叫,又叫不出声来!他两只手疯狂地揪扯着自己的胸脯,外衣上的纽扣‘崩崩’地一颗颗飞掉了。”这是压抑后的爆发,多么痛苦,又多么苦涩。小说结尾,他扑倒在慷慨而宽容地再一次收留了他的故乡土地上,发出那一声包含着无比的痛悔也包含着无限的委屈的沉痛的呻吟。这些,都在强化人物命运的悲剧氛围,它在处位低下,心有不平之气的读者中,尤其能够引起共鸣,产生“净化”心灵的悲剧审美效果。
再看巧珍的悲剧。巧珍的悲剧是爱情悲剧。这样的悲剧古往今来不知在人间多少次重演,也不知在多少艺术作品里得到过千姿百态的表现。但《人生》里的巧珍的爱情悲剧还是那么独特那么动人。尽管这个人物并不是作家路遥作为诠释人生道理的主要对象来加以塑造,而是作为男主人公的陪衬来刻画的,但是这个美好的乡村女子的爱情悲剧却给人以更深刻的感动和更强烈的美感。巧珍是高家村“二能人”刘立本的第二个女儿,“漂亮得像花朵一样”,“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是“川道里的头梢子”,被誉为“盖满川”。唯一的缺憾是,她的有钱的父亲没有让她念书,害得她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但这个没读过书的美丽的乡村女子,精神世界却让人想象不到地丰富。就像她“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一样,她对爱情的追求也有超越世俗的标准,而且一旦有爱便无比热烈、执著。更可贵的是,她有一颗无比美好而又善良的心。外表美和心灵美,是那么完美地统一在她的身上。在《人生》里,巧珍是作为美的化身存在的,作者让她像一面纯洁无瑕的镜子一样,照出主人公高加林的人生失误和道德缺陷,的确起到了加强主人公人生选择的悲剧性,产生悲剧感染力的作用。但是,刘巧珍自身的人生悲剧,因凸显了汉民族民间精神的丰富性,而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巧珍美丽而没有文化,但正因为有缺憾才显出她的美,就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没有文化,是生活世界里的巧珍爱情不幸的根源。但是在艺术世界里,因为没有文化,巧珍在爱情追求中才绽放出她青春生命的全部美艳。“刘立本这个漂亮得像花朵一样的二女子,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的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村前庄后的庄稼人只看见她外表的美,而不能理解她那绚丽的精神光彩。可惜她自己又没文化,无法接近她认为‘更有意思’的人。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她常在心里怨她父亲不供她上学。等她明白过来时,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为了这个无法弥补的不幸,她不知暗暗哭过多少回鼻子。”没有读过书的人,一样有文化认同,一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样有超越自我的愿望,这正是巧珍这一个性给我们的文化启示,是文学的属人本性带来的生活发现。与高加林一心走出农村,在事业追求中证明自己不同,意识到自己一辈子只能呆在农村的巧珍,能够实现她的人生价值的只有爱情。“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而对于山村就是她的全部世界的刘巧珍来说,高加林就是这样的男人——
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加林。她爱他的潇洒的风度,漂亮的体形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她认为男人就应该像个男人;她最讨厌男人身上的女人气。她想,她如果跟了加林这样的男人,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她同时也非常喜欢他的那一身本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哩!再说,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得干干净净,浑身的香皂味!
她曾在心里无数次梦想她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情景: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拉着,在春天的田野里,在夏天的花丛中,在秋天的果林里,在冬天的雪地上,走呀,跑呀,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让他把她抱住,亲她……
这是多情女子对于可心男人的一往情深的爱恋,对于迷人爱情的想象。巧珍暗恋上了同村的读书郎高加林,爱得那样深那样专一。由于人类在历史进化过程中给男女赋予了不同的使命,社会把所谓事业更多地交给了男人,也因此只有女性才能把全副的身心都交给爱。刘巧珍爱高加林就是传统社会遗传下来的女性特性的充分体现。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怀疑乡村女子刘巧珍对爱的炽热与真诚。但她的爱既不盲目也不功利,而是明智的选择。“就她的漂亮来说,要找个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是很容易的;而且给她介绍这方面对象的媒人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但她统统拒绝了。”她要找的是真正“合她心的男人”。在她眼光所及的世界里,只有高加林是这样的人。谁也不知道,高加林是她的心上人,“多年来,她内心里一直都在为这个人发狂发痴”。可以看出,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含有文化崇拜的成分,它出自人格认同的需要。正因为这样,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情,就近似于一种宗教情感。这种情感是人类对高于自我存在的对象的最圣洁的情感,其极端就是牺牲精神。小说介绍刘巧珍,“如果真正有合她心的男人,她就是做出任何牺牲也心甘情愿。她就是这样的人!”应该不是一种夸张,不是作家出于男性自我证明需要的一厢情愿。
文化崇拜,来源于文化上的差距。高加林还在城里读高中时,巧珍就偷偷地喜爱上了他:“每当加林星期天回来的时候,她便找借口不出山,坐在她家院子的硷畔上,偷偷地望对面加林家的院子。加林要是到村子前面的水潭去游泳,她就赶忙提个猪草篮子到水潭附近的地里去打猪草。星期天下年,她目送着加林出了村子。上县城去了,她便忍不住眼泪汪汪,感到他再也不回高家村了。”这是一种无望的爱,因为巧珍知道,读书的加林迟早要远走高飞,她不可能得到他。痴情的巧珍就这样被梦想和无望折磨着,但爱却是不可改变的。文化上的差距也使巧珍在所爱的人面前产生自卑感。自卑感一旦沉入潜意识,又成为寻求人格认同的能量,致使爱的欲求更加强烈,所以尽管“她的自卑感使她连走近他的勇气都没有”,“她的心思和眼睛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他”。就像城乡有别是高加林实现人生梦想的鸿沟一样,文化差距是刘巧珍实现爱情梦想的障碍。这一差距注定了她的爱情是一场悲剧,并且爱得越真挚越深沉,悲剧的色彩就越浓烈。
《人生》不是爱情小说,但它花了那么多笔墨来写巧珍的爱情,目的是为了说明巧珍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谁得到她谁就拥有人生最大的幸福,谁不懂得珍惜就是人生最大的失误。高加林得到了她却又轻易将她抛弃,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照作者和小说中的乡亲们(首推乡村哲学家德顺老汉)看来,高加林丢掉了城里的工作,不是他最大的人生悲剧,因为农村也照样可以活人。高加林更大的人生悲剧,是鬼迷心窍移情别恋抛弃了巧珍,等于自己丢掉了到手的金子,且不可复得。为了突出这样的悲剧,小说就要不惜笔墨来渲染巧珍的美好、善良和对爱的执著,特别是要把她的富有牺牲精神的爱写得无与伦比,因为只有这样,巧珍的失恋才是美的毁灭而高加林失去巧珍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读者自然会跟着迭声叹息。“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2]巧珍是少见的好人,但她却遭受了不应遭受的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的魅力,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巧珍爱情的悲剧性。
巧珍爱情的悲剧性首先在于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带有太强的主观性。巧珍明知他俩存在文化上的差距,但她以为靠自己的俊和对对方的爱,就可以赢得从高处跌下来的加林。殊不知作为有抱负的男性,高加林的精神世界是任什么样的是爱情也填不满的,再美好的异性之爱,也不能抹去他的功名欲和功利心。高加林在沉沦中被巧珍大胆表白的爱情所感动,在不幸的时候得到了幸福,但他很快又产生“懊悔的情绪”,“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其实他内心里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熄灭。他现在虽然满身黄尘当了农民,但总不相信他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他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有时间等待转机。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他是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接受了巧珍的爱情,亲了巧珍的。他俩的爱缺乏基础,是不对等的。这样的爱,并不稳固。所以,进城之后,高加林与更有魅力的知识女性黄亚萍发生恋情就是正常的。他俩从高中同学时就相互欣赏,有共同的志趣和语言,性情相投,都喜欢浪漫,现在又不存在城乡差隔,更何况黄亚萍还能帮助加林实现进入大城市的梦想,因此,从思想与感情基础,到功利要求的满足,黄亚萍都比到了城里只知对爱人讲母猪下了几只小猪的刘巧珍更适合于改变身份后的高加林。在功名欲的驱使下,本来就狠心的高加林,在道德与功利之间,毅然地选择了后者,完成了巧珍被抛弃的命运。这样看来,巧珍的爱情悲剧,是他俩共同制造的。
巧珍爱情的悲剧性还在于巧珍是爱情的牺牲品。没有读过书的巧珍,她的精神世界尽管丰富,但其主要内容是爱的梦想,也就是一心找个中意的人,把爱献给他,用她的美貌和她的心灵。与其说是想爱别人,不如说只想被别人爱。这是一种没有自我的失去主体性的爱,是一种先爱人之忧而忧,后爱人之乐而乐的以彻底奉献为目的的爱情。巧珍为高加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讨得他的喜欢,连穿着打扮也只为取悦于所爱的人,与旧时代的“女为悦己者容”没有区别。在两人的关系中,巧珍从来把自己置于依附性的地位,对于未来的婚姻生活,她最高的设计也无非是“将来你要是出去了,我就在家里给咱种自留地、抚养娃娃;你有空了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就和娃娃一搭里来和你住在一起……”只要能和加林“一搭里过”,她就实现了全部的人生愿望。以爱情为人生目的的巧珍,与以事业为人生目标的高加林,距离只能越来越远,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危机,于是巧珍只能用加倍的奉献去克服这样的危机,这是中国农村妇女失去自我主体性的悲哀。由于在爱情追求里包含有狭隘的自我认同的目的,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就没有任何回头的余地,就像箭射出去以后,箭弓可以转移到别的手里,而箭头只能朝着原来的目标飞去。高加林进城后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可以背叛她,而她只能为爱而牺牲自己。高加林找到新的恋人后,她忍痛把自己的身体嫁给了她并不爱的马拴,而把心仍然留在了高加林那里。当高加林再一次遭到人生的重创,落魄还乡,她为心爱的昔日恋人的不幸而彻心彻肺地疼痛。为了加林,身为人妇的她特地赶回娘家,不仅跪求姐姐不要伤害加林,还央求姐姐一起去找姐姐的公公高明楼,并在他的面前哭求,让他安排加林再去学校教书。在巧珍的生命里,只有对加林的爱,而没有自己甚至别的亲人。她把自己的北方女子的美丽的身心当作祭品,供在了能够证明她的美好的爱情祭坛上。《人生》饱蘸笔墨,真切而细致地刻画了这样的美和美的自虐,用它触动读者的爱美之心和怜悯之情,产生了感人至深的悲剧美。
收稿日期:2008-10-28
注释:
①路遥在作品《人生》里称之为“生活的原则”。
②引自路遥《人生》,《路遥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以下引文未注出处的皆同。
③日本学者安本·实在他的研究路遥的论文里就提到:“……中国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中国革命‘在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之后农村所处地位。更直接地说,就是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他们的自由被限制了。”——参见[日]安本·实《一个外国人眼里的路遥文学——路遥“交叉地带”的发现》,收入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再解读——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