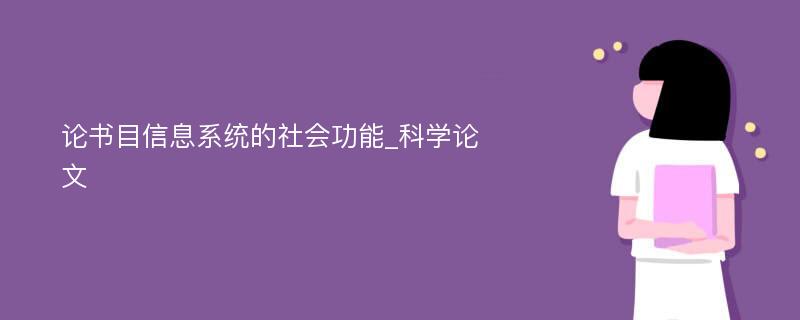
论书目情报系统的社会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目论文,情报论文,功能论文,社会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目情报系统是以知识的传递和利用,满足社会文献信息需求为目的,将书目情报系统从情报源传递给用户,由人员、过程、设备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综合体。研究书目情报系统的社会功能,应当明确书目情报系统是处于一定层次的系统之中,它既是第一层次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又是第二层次知识系统的一个部分。它作为浓缩的知识信息系统在文献信息交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书目情报系统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从文化、科学、知识各个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
一、文化积累功能
关于文化,有物质的、精神的、抽象的、具体的各种阐释。20世纪的文化讨论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文化学,经过历史的条理、哲学的思辨和心理的透视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视野,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界定,由于把握了文化的内在特质而得到广泛接受,书目情报系统正是与这一意义的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
书目情报系统的产生是文献增长和社会需要的结果,但这还只是表层次的认识,实质是文化的需要。书目情报系统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因为,人类在创造文化后就需要创造文化的记录。金克木运用符号学原理解说文化:“社会文化现象中可以把物、事、书三样当作指示意义的符号……书中的文字是符号,文字联贯成语言仍是符号,语言所说的事件还是符号,因为其中意义都是不可直观见闻的,是借文字语言而传达的。”(注:金克木:《文化的解说》,三联书店1988年版。)这与交流意义上的文化甚至与“我们的文化是纸张文化,是建立在印满了符号的纸张上的文化”(注:Shera J H.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Colorado:Libraries Unlimited,inc.1976.)是一致的。把文化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而书目情报作为文献信息交流的中介,是关于文化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书目情报系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正如章学诚所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从观念形态的角度看,书目情报系统代表着一种文化,它在物质的、制度的和心理的三个层面组成的文化结构中属于制度的层面,这个层面有两个体系:“书目——文献——知识”以及“书目情报服务——文献需求——知识需求”(注:柯平:《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
书目情报系统的文化功能首先在于文献的文化性质,一方面,文献是文化的结晶,没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不可能形成文献;另一方面,文化物化于文献,没有充分的文献就没有发达的文化。这是因为:“文化的使命就是充当自然与社会相互联系的尺度”,社会机体“自我保存”的“‘社会智力’(сопиум)世界作为一种特殊的机体,它不仅是‘自然的’的,而且也是‘历史的’,这就使它的生命活动方式,它的形式、速度和节奏,有别于其他自然”(注: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文化—人—哲学:关于整体化和发展问题》。见:冯利、覃光广编《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文献正是这种社会智力世界的影像与转化。
人类不能没有文化的记录,也不能没有文化的积累,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文化的繁盛与贫乏取决于积累的程度。人脑可以作文化的积累,但它的积累存在着局限性。这样文字及其他记录方式就成为文化积累的最佳选择。书目情报系统历来所承担的是与物质的文献积累相匹配的文献信息积累,是一种文化积累,它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有意义的,正如谢拉所说:“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字记载和保存文字记载的方式,便没有持续的文化。”(注:谢拉:《图书馆学基本原理》,见袁咏秋等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谢拉的“社会认识论”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社会知识和信仰的总和,由物质设备、学术成就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维持继续着。书目情报系统就是文化积累的社会组织之一,《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我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来新夏总结说“古典目录学领域,在长期的进程中,由于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参与,曾编制了大量的各类型目录,使中国文化载籍得到比较系统的按类记录,增厚了中国文化的积累。并在长期实践工作中探讨了不同的分类体系,提出了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宝库,也为世界文化史增添了光辉。”(注: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只有记录和积累才能够记忆,文化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越来越感到人类不能失去文化记忆,正如人失去记忆会影响其存在一样,社会失去记忆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哲学家波普所作的假设机器、工具毁坏或主观知识一起毁坏这两个思想实验恰恰作了这样的想象。事实是, 人类正在面临着失去记忆的危险, 知识和信息量愈大, “Memory Losses”就愈难以避免。 美国国会图书馆制定的“美洲记忆”规划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害怕失去记忆的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正在采取积极的行动保存文化记忆。
书目情报系统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呢?按照巴特勒的思想,“所谓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social mechanism),图书馆是为把它移入活着的个人的意识的一种社会机构(social apparatus)”(注: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而书目情报系统既把许多个人的思想移入脑外载体,又把全社会集中的思想移入个人的意识,它即使不具有意识,也进行与个人的知识过程大致相似的记忆机能活动,这种社会记忆能力被巴特勒称为“社会拟作精神”(social pseudmind)。
传播知识和信息的存贮系统是文化延续的一种保证,对于这种存贮系统, 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有的人称为“社会遗传”(socialheritage),也有人称为“社会副本”(social transcript )或是“文化图书”(cultural books)。“这是对比现代参考咨询工作中的情报存贮、索引编制及情报内容而得出的生动比喻,这种比喻还可进一步扩展为‘团体记忆’(corporate memory)”,但这种团体记忆会导致知识分布的不均匀,部分成员因大量存取记忆形成超越他人的权力,甚至于弱小文化被强大的文化所吸收吞并,也就是“毁掉了一个文化的团体记忆”(注:McGarry K J.The changing context of information:an introduction analysis.London:Clive Bingley,1981。)。 国外有人把图书馆的目录也称为一种团体记忆(注:韩扬云译:《图书馆目录——情报检索的工具》,《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4年第3期。), 它的存在正是与图书馆所起的社会记忆作用是一致的。
90 年代以来, 人们把国家书目上升到“民族记忆”(nationalmemory)的高度来认识。在IFLA1991年大会上,书目组专门讨论了国家书目的文化功能。法国M·Beaudiquez 在《国家书目是民族记忆的见证》(注:Beaudiqnez M.National bibliography as witness of national memory.IFLA Journal,1992(2):119~123。)中指出,文献目录不能等同于文献本身,而是作为它们存在的见证,而民族记忆依靠这种目录,技术发展将使国家书目成为民族记忆的较好见证。 美国B· Bell 在《今日国家书目是明天的民族记忆:问题与建议》(注:Bell B. National bibliography today as national memory tommorrow:problems and proposals.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and Bibliographic Control,1992(1):10—12。)中强调国家书目遭受失去记忆的困难并提出恢复这种记忆的战略,建议在巴黎大会的20周年即1997年召开第二次国家书目国际会议。这一主题在1992年IFLA大会上得到继续讨论,R·Holley 的《国家书目作为民族记忆:大众文化被遗忘了吗?》(注:Holley R.National bibliography as national memory:is popular culture
forgotten?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and Bibliographic Control,1993(1):13~17。)强调大众文化资料应得到记录,以便提供更全面的民族记忆。
归纳起来,书目情报系统具有文化积累的功能,表现为文化的反映或见证。虽然埃德夫图书馆藏书不复存在,但存在的书目保存了文化“片断”。可以肯定地说,书目情报系统是一种文化记忆器。
二、科学导向功能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科学能够发展,得力于科学研究的不断继承和创新。书目情报系统的科学功能首先在于它能够并且善于提供“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的资料,为这种继承与创新提供情报保证。
书目情报系统对于科学研究的这种作用早已被人们所认识。美国物理学家C·赫林认为:30年代, 科学家研究课题的文献和科学家阅读的文献相差很小,到60年代,科学家研究课题的文献增长了5至10倍, 科学家阅读的文献只是研究课题的一小部分。经济学博士海因曼指出:“为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所必需的信息量在急剧增加,信息整理和掌握是越来越复杂和消耗大量劳动的任务。”(注:海因曼著、王金存等译:《科学技术革命的今天和明天》,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科学家无法获取全部文献并无法阅读全部的文献这种紧迫的形势使研究越来越依赖于书目情报系统。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科研时间与经费。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凯斯工学院基金会以及日本国家统计局所作的统计表明,一个科研人员用于查找和阅读情报资料的时间占完成某研究课题时间的50.9 %, 瑞士M ·Eliane认为科学情报过程费用占科学研究工作总费用的10%,科学情报时间占研究人员科研总时间的20%,这些数字没有把情报过程中查找文献与阅读文献分开。里坡以芬兰技术研究中心为对象,对940个项目100多位项目带头人统计调查,得出一个人在一个项目中时间利用的分配:情报搜集96.75小时,占9%,折合工时费45000芬兰马克;而阅读120.50小时,占12%,折合工时费60000芬兰马克。(注:李自新:《情报的经济和价值问题:国外研究概要》,《情报学报》1993年第3期。 )把查找和阅读区别开来的意义在于说明书目情报系统不仅是查找文献所依赖的工具,而且是阅读文献所依赖的工具。进一步,根据马克思关于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书目情报系统节约科研人员的时间使研究过程缩短并节约研究经费,更具有生产力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1991—2000年规划中要建立“文献情报检索和报导体系”,把科研人员获取文献时间由目前占全部工作时间的30%降到15%以下(注:白国应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发展战略》,《图书情报工作》1992年第1期。),这是有科学意义的。
深刻地认识书目情报系统的科学功能,必须把它放在科学活动的全过程,作为科学活动的组成部分探讨它的重要性。
从科学能力看,科学能力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它包括五个要素:科学家队伍的集团研究能力、实验技术装备的质量,“图书情报”网络系统的效率、科学劳动社会结构的最佳程度以及现代科学教育水平,最终归纳为人(科学家)和物(科学劳动资料)。科学学专家认为:图书情报系统与实验技术装备的“二次仪器”系统是科学劳动的两翼,“现代化的‘图书——情报’网络系统的建立,基本上结束了科学家与世隔绝的个体劳动方式,结束了科学研究同图书情报分离的状态,它使科学家们的科学劳动建立在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基础上,使科研、图书、情报在更高一级水平重新建立起来”,从而解决了“现代化科学劳动的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注:冯之俊、赵红洲:《现代化与科学化》,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作为科学交流正式过程的书目情报系统是现代化科学劳动的重要标志。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从1987年起,根据美国四大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SC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LSTP)、 《工程索引》(EI)和《科学评论索引》进行统计分析,显示检索系统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及其在世界的排名:1991年11783篇,排列第15位;1992年15466篇,跃居第12位;1996年27569篇,跃居第11位;1997年35311篇,在世界排名第9位。由此说明我国科研实力逐渐增强的发展趋势, 这是书目情报系统科学功能的最好见证。
从科学预测看,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的密切联系证明:书目情报系统是总结科学发展规律、预测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洛特卡定律和普赖斯定律描述了科学生产率的分布。书目情报系统反映科学文献的发展使之兼有科学史的功能,它对于科学书目情报的测度又使之兼有科学预测的功能,例如美国《SCI》的创办者加菲尔德从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种刊物、100万著者的8000多篇论文中,统计了1982 年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献50篇,其中30多篇来自生命科学,预测生命科学是科学前沿的带头学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胡世禄以中国人民大学《全国报刊资料索引(1986——1988)》为依据,分析我国社会科学在理论层次和经验层次上的结构及其变化情况,结合社会科学的元学科排序,用9级制的加权法, 预测了我国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结构和未来排序: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教育科学;政治学、哲学、艺术学;文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传播学;体育科学、地理学;情报与文献学;宗教学;语言学。(注:胡世禄:《我国社会科学的结构现状和未来排序》,《社会科学报》1990年第3期。)
从科学创造看,创造过程存在着一个以社会知识形态记录在文献载体上联系客体和主体的“中介”,书目情报系统就是这种中介,它在调研阶段把文献信息的“中介世界”变成科学家头脑中的“中介世界”,在创造阶段把这种中介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创造新的“中介”成果,而在交流阶段把这种个人创造变为社会的“中介”财富。科学家正是站在书目情报系统的“肩膀”上进行科学创造的。
从科学组织看,科学组织就是确定研究方向,合理利用人财物,取得最大的效益。书目情报系统及其查新服务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为科研选题提供科学依据,避免科学研究的“新哥伦布”现象,特别是通过书目情报系统掌握科研动态并激发研究灵感,具有为科学研究指引方向的作用。
通过这些分析,科学可以用S=HW(人件)+PW(物质件)+IW (情报件)+OW(组织件)这一公式表达。“科学总是通过信息密集型的方法检验的,这是由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注:霍尔茨纳著,傅正元、蒋琦译:《知识社会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书目情报系统作为科学的情报件(Inforware), 其科学导向功能在今天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重要。齐门说:“现代的科技发展如果要成功必须注重科际间复杂的协调程序。在信息还原科学的发展中可以预见另一项结论。即若电脑能够储存大量知识并以程式来处理以便自动还原之应用,如此才能充分运用所有收存之知识。这一门崭新的辅助性科学仍未超过起步阶段。目前可以说是一个信息危机的时代,许多重复的研究在所难免。”(注:齐门:《科学与人类文明》,见迈尔一莱布尼茨等著《人·科学·技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赫林说:“现代的情报危机,从性质上说,不同于过去经历过的那种情形,它可能导致科学发展的明显延缓。”(注:米哈依洛夫等著,徐新民等译:《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而书目情报系统总是在分担科学家的情报吸收负担,消除这种可能的危险性,因此它始终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加速器。
三、知识控制功能
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得到科学史的证明。早在1944年,美国美以美大学赖德发现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藏书量平均每16年翻一番。之后,普赖斯把这一发现推广到科学知识的全部领域,用W=ae[Bt]表达了科学知识量的指数增长律, 说明科学发展与知识增长有关,而知识增长与文献信息增长有关。
关于文献信息的增长,统计数字是最好的证明。70年代以前,每年发行的图书50万册,期刊超过6万种,科技论文报告100万种,专利报告30万件以上。70年代以后,世界每年出版书籍80万种,期刊约15万种,发表论文超过450万篇。就出版信息总量而言,60年代年72万亿字符, 70年代年232万亿字符,80年代超过500万亿字符。(注:丘峰:《情报检索与主题词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文献信息增长率与科学知识增长率是对应的。比较之一,据西方专家估计,从1750年至1900年150年间,人类知识总量仅增加一倍, 1900至1950年的50年间也增加一倍,而1950年至1960年10年间又增加一倍。(注:顾敏:《图书馆学探讨》。(台湾)枫城出版社1981年版。)而15世纪自印刷术在欧洲和其他地区推广后,世界图书种数几乎每个世纪都比上一世纪增加三四倍。比较之二,据估计,本世纪60年代以来的科技发明创造成果比过去历史上两千年的总和还多,而世界图书累计种数自7世纪至19世纪末约1133万种,至1949年约2183 万种, 至1986 年达3883万种,至本世纪末将增长到5000万种。(注:林穗芳:《世界各时期出版图书数量初步统计与分析》,见陆本瑞主编《世界出版概观》,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60年代以来的文献量是过去1200年的总和。比较之三,据Unesco的“UNISIST”统计,科学知识年增长率60 年代以来已从9.5%增长到10.6%,到1980年已达12.5%。至今,学科2000 种,科技队伍人数每15年翻一番,科研论文年总量500万篇,每10 年翻一番,科技期刊每10—15年翻一番,知识总量每7—10年翻一番。 这些足以说明,文献增长与知识增长是相应的,它们都需要记录和控制,书目情报系统正是这样的一种控制装置。
另一方面,随着知识量的激增,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和满足比“知识量”更大的“知识需要量”。书目情报系统开发和利用知识比记录和控制知识增长更有意义,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目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顾敏从知识现象出发,阐述目录控制与知识体系的关系,认为知识成长、知识管理、知识运用是三个相关的因子,在整个知识演化的领域中此三个因子之间维持着相互支援、甚至相互交替的平衡状态,而维系这种知识现象平衡状态的主要因素就是目录控制。(注:顾敏:《图书馆学探讨》。(台湾)枫城出版社1981年版。)因为他所谓的目录控制是指一种目录系统,所以书目情报系统与知识体系的关系应是一种控制关系。
书目情报系统对知识增长的控制是通过对文献增长的控制表现出来的,其中包括在知识表达过程中文本书目情报的知识控制作用,这种控制首先是在数量方面,它容纳足够的知识量支持知识交流,知识交流的范围和程度与书目情报系统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一种控制,这些都是书目情报系统最基本的任务。
易于忽视的是在知识增长过程中知识质的提高,数量的扩大增加了质量提高的机会,质量的提高又蓄集了数量扩大的能力。然而,由于知识生产的社会复杂性以及量与质的矛盾关系,知识生产既有知识的创造,也有知识的复述和加工,而大量新知识的产生意味着某些知识的老化,以致于知识质的增加淹没于知识“海洋”之中。要使知识质的提高表现出来,必须对知识量进行提炼、浓缩,这比容纳知识量更为重要,而书目情报系统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过滤器。
作为知识过滤器,书目情报系统对文献信息的加工处理充分考虑到读者的知识需求和社会知识需要量的增大。读者的知识需求常常表现为对文献信息的需要,通过获取文献阅读并吸取知识营养的过程是一种消费,这种消费比物质消费有更大的能量,“知识就是力量”体现在这种消费中,知识消费和知识生产这两种活动是相互交替、相互刺激和相互循环的,知识交流把它们连结起来。
在知识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作用中,书目情报系统的知识过滤显得特别重要。第一,知识过滤能够刺激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的数量。读者从书目情报系统获得一定的文献信息和知识量,知识消费量的多与寡,可以扬起或抑制生产的数量,某一学科文献信息被利用的程度与该学科的成果成正比;反之,生产量也可以扬起或抑制消费量,系统中揭示的文献愈多,被提取利用的机会愈多。第二,知识过滤加快知识生产和消费的速度,书目情报系统对文献信息的加工愈科学,读者获取文献就愈容易,从而促进生产和消费。第三,知识过滤一方面是替代读者的文献信息处理过程,促进知识营养的吸收和转化,另一方面保证有用的知识不被遗漏,文献信息的开发和知识揭示愈全面深入,读者接收文献信息时,知识的流失量就愈小。
通过以上的讨论,书目情报系统在社会文化、科学、知识三个方面都表现出其独特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是相互联系的。知识的功能是书目情报系统直接作用于社会的,相比之下,文化的功能则是间接作用于社会的。如果将书目情报系统的功能区分为若干层次,那么,知识的功能属于表层次,文化的功能属于深层次,科学的功能则介于两者之间。通过这三种社会功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证明书目情报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于书目情报系统的建设及其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