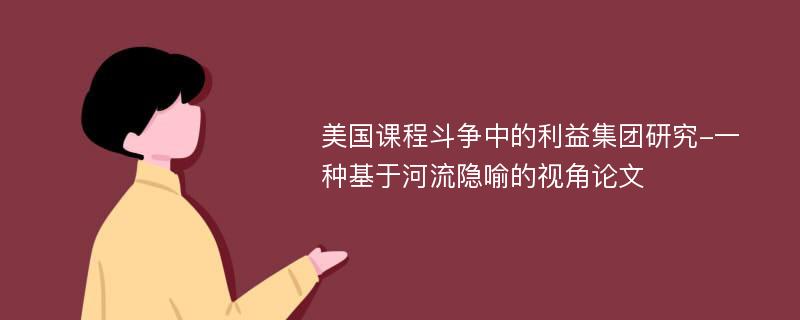
·比较教育·
美国课程斗争中的利益集团研究
——一种基于河流隐喻的视角
韩江雪
摘 要: 美国课程史学者赫伯特·M·克里巴德在《美国课程斗争(1893-1958)》一书中,基于一种河流隐喻的视角将抽象的课程历史进程和寓于其中的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及背后主导的四大利益集团予以形象化阐释,揭示出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课程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层关系,是从社会史视域把握课程脉搏的一次伟大尝试。作为一种新的课程研究范式,它通过洞悉四大利益集团势力的持续与消长来表征美国的现代课程变迁形态,其内蕴的课程史观摆脱了陈腐的二元对立思想而尊重了课程史本身的混重性、模糊性、复杂性,将课程重新放回了它所在的社会历史场域,得以为一些课程历史的神话祛魅。
关键词: 人文主义;社会效能;发展主义;社会改良
赫伯特·M·克里巴德(Herbert M. Kliebard)是美国著名课程史学者,他的代表作《美国课程斗争( 1893-1958) 》(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93-1958) 是美国课程史研究的里程碑式经典。该著作超越前人之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河流隐喻思想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自19世纪9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半个多世纪的课程史变迁,并运用一种“利益集团”的方法论视角,将角逐课程舞台的四大利益集团隐喻为课程河流的主流(mainstream)与支流(stream),还运用了潮流(tide)、潜流(undercurrent)、漂变(swift)、上升流(a rising tide)、涨潮(flood tide)等术语来隐喻不同时期课程主导势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其主次关系不是绝对化和固定不变的,而是恰如河流流势受到诸如天气、降水、植被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每一课程利益集团也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借助不同的社会氛围、公众态度、世界局势、经济水平等在美国课程舞台上擅一时之风流。与此同时,其他的“暗流”也没有在绝对意义上干涸,而是成为汩汩的“地下河”,条件成熟后再次伺机成为一股干流。
水稻移栽之后,要重点做好大田稻瘟病、白叶枯病的防治工作。水稻稻瘟病,在苗期到抽穗期都可发生,其中水稻分蘖期到拔节期、孕穗期到始穗期是该种疾病防治的关键时期。一般每亩使用75%的三环唑可湿性粉剂40 g,或40%的遛环唑悬浮剂250 mL兑水60 kg,田间喷雾。白叶枯病在发病初期,每亩选择使用70%的叶枯唑悬浮剂150 g或25%的叶枯宁可湿性粉剂100 g或50%的氯溴异氢尿酸水溶性粉剂30 g,兑水60 kg,田间喷雾。
关于以河流的隐喻来澄清四大利益集团在半个多世纪课程角逐中的势力消长,克里巴德提出两种假设:首先,隐喻的方法可以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工具,而不仅仅是书写和语言上的文学美化装饰。隐喻法作为超越刻板逻辑理性思维的一种感性内蕴的解释方法,将复杂、抽象、难理解的事物阐释为日常生活中容易感知、理解的事物,甚至是我们经历过的真实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组织思维和理解事物的一般概念范畴的视角。其次,隐喻不仅是我们了解事物的一种认知和感受的工具,也是一种争论形式——当我们使用隐喻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是孤立地表达彼此特异范畴内两两相对的事物之间的切近特征,以此将它们联系起来,而是致力于挖掘探索隐喻所指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这两种假设,课程隐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课程利益集团关系的语言或解释,形成理解课程理论的基本概念性框架。[1]34-35
国内关于西方课程史的研究主要以西方课程史的研究取向、研究范式、分析路径、历史演进脉络等为主,以及对课程史领域的领军人物及其著作的相关理论展开研究,以期从西方课程史研究中挖掘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并对课程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批判、反思。其不足在于,针对作为课程史研究重要方法之一的隐喻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通常仅仅将其作为技术理性的对立面提及其质性分析的性质,而忽略了隐喻法本身的神秘性、想象性、丰富性和对思维的启蒙意义。克里巴德正是巧妙地运用了隐喻的透视才得以将美国课程中纷乱的斗争力量及其动态辩证的复杂关系予以揭示。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克里巴德在美国课程斗争中的隐喻内涵,以利益团体的课程争斗解释课程史,批判课程改革的“钟摆效应”观点而重构课程史观,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为从隐喻视角研究课程史提出了新思路。
要想提高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先要了解大棚蔬菜种植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我国大棚蔬菜种植问题由多方面因素综合引发的,所以需要多方的配合与协调,才能提升大棚蔬菜种植效率,实现绿色生产、高效生产。
一、四股水流的历史发端与原始形态
克里巴德认为,美国社会的四个利益集团分别是人文主义者( humanistists) 、发展主义者( developmentalist) 、社会效能派( social efficiency educator) 和社会改良派( social meliorist)。当考虑到任何社会的不同阶层都会强调不同形式的知识对社会最有价值时,一个社会所珍视的知识与其融入课程之间的路径就会变得无比曲折。对于一种文化中的哪些资源是最有价值的,人们很少有普遍的共识。如,捕猎动物的实际知识必须与部落神话的知识相协调;拉丁语的变体知识必须与该文化固有的语言能力和文学传统进行权衡;性教育必须在道德和宗教价值观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因此,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行使绝对霸权。相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时间,会根据当地和一般社会条件争夺课程的主导地位,实现某种程度的控制。因此,这些利益集团中的每一个都代表着一股力量,促使人们从文化中汲取不同的知识和价值观,从而为不同的课程进行游说。
(一)人文主义者
19 世纪末期,鼓吹学术性科目的恒久价值并带有强烈的学院精英色彩的人文主义流派以心智训练说(mental discipline)为武器,主张对所有受教育者实施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博雅教育(或译通识教育、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代表人物是查尔斯·W·艾略特(Charles W. Eliot)和威廉·托里·哈里斯(William Tory Harris)。其主要观点有:第一,重视培养人的理性与心智。如艾略特所言,“对权威原则的依赖太多,对理性的渐进和持久诉求的依赖太少”,他坚持黑格尔主义学校教育哲学“将发展人的理性作为第一要务,而教育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2]第二,以培养符合人文主义理想、具有理性能力、审美敏感性和高尚品德的各阶层公民为教育目标。“教育的目标在于通过人类的知识,即人类长期积累的人文财富和文明遗产的学习,培养一个在他所生活的文明社会里行使真正自由的有理性的人。”[1]37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艾略特没有强调教育有直接性社会改革目的,但他仍然对人类的能力持乐观态度。“我们美国人习惯性地低估了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每一个教育阶段的能力”,但“不能学习几何、代数和外语的文法学校学生的比例将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小得多。”[3]10第三,通过学术课程来控制、引导人的自然天性。哈里斯认为自我活动作为一种自发性存在于每一个新生的灵魂中,是一种行为的无限可能性,但有好有坏。课程的功能是激发学生追求真理的兴趣,以及在对美的热爱和行善的习惯中发展自我活动。哈里斯认为课程中的每一个学习分支都能为人们更充分地理解西方社会和知识传统开辟道路,由此他提出五扇“心灵之窗”(windows of the soul)[3]15,包括数学、地理、历史、语法、文学和艺术。对他来说,这五扇窗户代表了引导孩子进行自我活动的最佳方式,这种自我活动将引导他们掌握西方文明资源。
(二)发展主义者
经过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是60%,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是96%,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对比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
发展主义阵营普遍同意:学校把孩子当作被动的接受者,并向他们提供与他们的自然倾向和偏爱背道而驰的学习项目,从而阻碍了孩子对活动的基本需求。但霍尔有一个更别致的视角——文化纪元理论(culture-epochs theory)。虽然该理论披着科学的外衣,但是其内核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和神秘的,它揭示了个人发展与人类历史进化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儿童在他的个人发展过程中再现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孩子在他的行为中重温了种族的历史,就像他身体里的许多原始器官讲述了种族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故事……主导一切的,当然主要是无意识的,孩子的意志是复演过去,就像他的早期祖先在他的意志和身体里挣扎,使他们的影响被感觉到,他们的声音被听到。[4]443
霍尔还是遗传决定论的坚定信仰者,他提倡根据儿童的禀赋进行差异化教学,甚至敦促在小学阶段为智障儿童设立单独的学校。以性别为例,霍尔认为性别隔离应该在青春期萌芽时就开始,因为性别间的显著差异是在青春期早期开始的。霍尔让我们警惕性别逐渐趋同的现象:虽然女孩十岁以前就树立与自身性别切合的理想,但研究表明十岁后的女孩开始采用男性理想。霍尔引用一个作家的言论表示他的担忧,“女性性别以后将会失去女性特征”[4]448。同样地,在一个男孩应该充满“硬汉气质”的时期,课程应该适合青春期男孩的天性,比如男孩子对内容的偏爱和对形式的弱视,但现实是学校里的男生发展受到了“女性化进程”的威胁。此外,霍尔还强调了身体养护的至高地位,他坚持以促进儿童“健康”发展作为学校教育的目的,从正面反对了哈里斯的智性教育主张。
本文首先总结了沥青路面坑槽病害的成因与一般修补技术,然后在某高速公路中使用冷补沥青修补料进行坑槽病害修补,并对其养护维修效果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冷补沥青修补料能有效修复路面坑槽病害,修补路面的抗滑性能可满足行车安全要求,同时具有较好的抗渗性能,能有效减缓路面水损害现象,对提高道路的使用寿命具有积极意义。
(三)社会效能派
1892年成立的全国赫尔巴特协会也对人文主义者发动过猛烈抨击,其主席德加莫与哈里斯针对赫尔巴特的两个关键术语“相关”和“集中”的含义展开过辩论,尤其是1895年的克利夫兰会议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争辩的内容,更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标志着为争夺美国课程控制权而战的力量开始重新集结,更带有旧秩序的消亡和新秩序的诞生的意味。[15]
社会效能派还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控制色彩。爱德华·罗斯(Edward A. Ross)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美国的个人主义必须得到遏制,他提出一种社会控制思想:他不会告诉招聘人员、街头阿拉伯人或埃尔米拉监狱的囚犯他是如何管理的;他将向管理社会道德资本的教师、牧师、编辑、立法人员和法官发表演说,这些人掌握着控制的工具。[6]
上周(8月13日-8月17日),出口市场预收订单充裕,价格高位企稳,局部涨跌互现。8月20日中国磷酸二铵批发价格指数(CPPI)为 2847.73点,环比下跌2.66点,跌幅为0.09%;同比上涨221.74点,涨幅为8.44%;比基期下跌374.04点,跌幅为11.61%。
社会效能派借用工业生产的隐喻致力于消除社会浪费。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主张,作为消除教育效率低下的动力的一部分,课程应谨慎地适应每个阶层的个人,不应该教给人们他们永远不会用到的东西。为了减少浪费,教育工作者必须进行科学的测量,以预测一个人未来在生活中的作用,这一预测将成为差异化课程的基础。在这一新理论的框架下,“按需教育”只是“按预期的社会和职业角色教育”的另一种说法。例如,在诸如职业、娱乐和公民身份等方面,不同的男孩与女孩也要接受不同的课程,用同样的方式训练他们是没有效率的。博比特在他的理论背景下对“原材料”(raw material)的关注[7],与其说是对个人幸福的关注,不如说是为了消除课程中的浪费,进而消除社会秩序中的普遍浪费。社会效率理论为科学地使课程适应新工业社会的要求提供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
(四)社会改良派
社会改良派的思想最初发端于19世纪末莱斯特·沃德(Lester Frank Ward)反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中。沃德在《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中提出,人的天赋在社会阶层和性别中是平等分布的,社会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社会遗产分配不均的产物。“贫民窟的居民在心理因素方面并不比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差……罪犯是贫民窟的天才。”[8]
罗斯认为,教育是社会武库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特别是考虑到其他社会控制方式的衰落。在当时混杂的制度之下,几乎全世界都在从宗教转向教育,将其作为间接的社会约束手段。不幸的是,美国的学校被灌输了一种智力偏见,这种偏见导致美国的学校与其说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不如说是帮助个人成功的工具。与社会控制思想相适应,社会效能派还强调一种分型的课程。基于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罗斯呼吁学校采取更为直接和明确的社会目标,课程设置应与未来公民将要履行的命定的角色有关,因此需要根据科学的心理测量系统提供的对学生能力的评定来制定分化型的课程[3]92。
沃德出于人道主义立场阐发的文明遗产公平分配和政府积极干预的思想酝酿了半个世纪后才焕发生机。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出版的《第二十六期年鉴》(The 26th Yearbook)呈现了美国课程改革领域又一股领导力量——社会改良派,旨在改善美国社会中贫穷、不平等、失业等社会问题,以及经济的大萧条、低迷的社会状态。[3]152
首先是批判教育为特权阶层服务。康茨(George S. Counts)是教育界领袖中最早反映出对美国社会结构感到不安,并将这种不安直接指向批评美国学校考试的人之一。他最早的主要著作的主题是,美国教育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只服务于相当狭窄的特权阶层。通过对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以及纽约的弗农山的调研发现,“不幸和幸运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9],学生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取决于其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格拉索恩( Allan A. Glatthorn)在《课程领导》(Curriculum Leadership) 一书中,也赞成使用河流的隐喻来分析课程史。如格拉索恩所言: “用持续流动的河来谈论它时而丰沛、时而微弱、时而分流、时而汇聚,或许更为适切。”[11]数股支流的隐喻很贴切地描绘了课程是如何运动的,支流穿过系统,时而涨潮,然后积聚力量且在动态的汇流处合流在一起。这一隐喻似乎比钟摆的陈腔滥调更有帮助,后者意指一种简单的来回运动,而河流隐喻意指在课程史中的任何特定时间,数股支流在流动着。在过去的一个时间点,某股支流的影响力是微弱的,而后,它集聚了力量且变得强而有力。有时,这些支流广泛地分离,在其他时候,它们合流在一起。而且,某股特定支流的力量显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复杂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影响。
二、干流与支流的相互转化和此消彼长
20世纪到来时,决定美国新课程方向的四股主要力量已经出现。在20世纪的舞台上,关于什么是最值得教授的知识和学校的核心功能被反复提出和讨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能获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的进程中,社会和经济的一般趋势、集团间的联盟、民族情绪、地方条件和集团领导者个性等因素影响了这些集团把控学校的能力。最终,主导美国课程的并非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任何一个集团,而是一种松散的、没有明确表述的、并不十分清晰的集团间妥协和杂烩,因而形成了一股混重的合流。
其次是批判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康茨称社会效能派大肆鼓吹的效率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效率,是一种机械的效率,致使整个国家都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机器文化的影响。1932年2月在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第十二届年会上,康茨发表了《进步教育是否进步?》(Dare Progressive Education Be Progressive?)的讲话。他认为,进步教育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没有阐述任何社会福利理论,是无政府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的。当然,所谓无政府主义,康茨并不是说这些成员与政治无政府主义者结盟,而是谴责那些成员没有深厚而持久的忠诚,没有愿意为之做出牺牲的信念,没有日常物质享受就难以生活,对社会不公麻木不仁,只愿意在人类历史剧中扮演旁观者的角色,拒绝以清醒的姿态看待现实。[10]
(一)集团内部的异质与分歧
以人文主义者为例,《十人委员会报告》是美国课程历史上推动美国课程改革进程的重要报告。艾略特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人文主义者的课程思想在当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妥协现象也已经在集团内部发生了,这种隐隐的裂痕为后来人文主义的逐渐式微埋下了伏笔。首先,艾略特选择设置四门不同的高中必修课程,而不是选修课。[3]10这是学校管理者一直在寻求的高中课程统一性的衡量标准,预计大学将接受这四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作为录取依据。艾略特认为应该根据学生的需要调整部分课程,如中学课程应该减少算术、拉丁文、希腊文等晦涩难懂的部分,因为这些部分对将来升入大学的学生来说更有用,而对其他以后进入职业领域的高中毕业生来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实际关联。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人群的需要,应提供分化的课程来满足学生高中毕业后的不同去向。“他预见到分化的课程可能会影响学生未来的职业”,由此反映出,艾略特课程改革的价值观体现出对学生个体能力差异性的关注。但十人委员会的各分会否定了艾略特“课程分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美国的中学里,学生修习的每一门课程的教学时间、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都应一致,每门课程都应以同样的方式教授给每一个选择这门课程的学生,无论学生中学毕业后的去向如何。[12]其次,尽管哈里斯曾经是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还是煞费苦心地把自己与心智训练说划清界限。[3]4最后,人文主义者倡导的课程与人们通常认为的古典文科课程并非绝对吻合,他们倡导希腊文的学习仅限于古典课程,年限从传统的三年减少到两年,四门课程中有两门是现代语言和英语,也没有学习拉丁语的要求。而且十人委员会表示,古典和拉丁科学课程在某种意义上优于现代语言和英语,但这是因为前两种课程发展得更好,有更多经验丰富的教师,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更好。[3]14这些主张与传统的古典人文课程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流露出人文主义者们作为一个集团其内部思想的某种异质和分裂的信号。
莱斯本是一个与霍尔思想切近的赫尔巴特协会成员,最初同意发展主义者的观点——关于儿童的科学研究数据是制定合理课程的关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莱斯从义愤填膺的人道主义者转变为通过应用科学管理技术来消除课程中的浪费的狂热分子,几乎违背了他的初衷。莱斯成为第三个主要课程利益团体的主要先驱,这个团体出现在世纪之交之前,即社会效能派。这说明不同的利益集团也许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壁垒分明、决然对立,而是如同众多涓涓细流一般分流互渗,不断地在冲撞中聚合,又在合流中渐渐分叉,彼此之间暗暗地吸收着来自对方的力量。
以社会效能派为例,博比特、查特斯(Werrett Wallace Charters)和斯内登(David Snedden )呼吁取消传统学科,而选择本身就是生活领域的公民身份和休闲课程。然而,斯内登的门徒金斯利(Clarence Kingsley)试图不废除历史和英语,只是要求对它们重新定位以实现《中等教育基本原则》七大目标中的至少一个,最好是几个。斯内登继而谴责委员会“主要致力于青年的通识教育”[13],有人文主义者的嫌疑。20世纪30年代的要素主义者可能是导致传统人文主义和社会效能派之间的既定界限变得彻底难以界定的一个例子,这说明即使是与时俱进的社会效能派也没有完全脱离古希腊文化遗产的精神源头。
(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攻讦
当一个利益集团处于河流干流的地位时,其他的支流往往伺机而动,他们作为地下暗流在积蓄着力量,以单一形态或以组合联手的方式向主导势力发出非难。比如前文提及的霍尔对十人委员会议案的三大抨击。霍尔旨在根据不同儿童的天赋素养进行分化培养的理念在艾略特看来是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相悖逆的,“美国公众打算让他们的孩子在十几岁之前就被划分为职员、制表师、平版印刷工、电报操作员、泥瓦匠、卡车司机、农场工人等等,并根据这些对他们适当的人生职业的预言,在学校里受到不同的对待。谁来作这些预言呢?”[14]进入20世纪,人文主义者源自古希腊遥远又灿烂的梦想最终在学校的残酷现实中干涸了,因为事实证明,并非所有中学生都能掌握为大学做准备的严格的学术性课程。
社会效能主义的先行者约瑟夫·梅耶·莱斯(Joseph Mayer Rice)在对美国学校的走访与调查中发现众多管理者均由政治任命,缺乏教育学知识,导致美国学校教育质量堪忧。莱斯在 1912年的著作中提出“一个科学的教育管理体系会从根本上要求测量结果基于一个固定的标准”[5],表达出强烈的社会效能取向。从此,精准测量、统一标准、目标导向成为社会效能者的主要诉求。
1)提供具备层次性差异的医疗保险服务,以公共医疗单位为主,鼓励民间医疗机构加入,建立好商业医疗保险等补充性保障制度,拓宽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共同构建完善的乡村医疗体系。探索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模式,促进两者的并轨与衔接。
(三)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渗透
全国教育研究协会《第二十六期年鉴》的两卷都专门讨论课程问题。芝加哥大学的康茨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拉格(Harold O. Rugg)被推选为编纂这些书的委员会主席。他们代表了与科学课程制定者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者的不同观点。随着康茨、拉格的出现,第三次课程运动开始了。半个世纪之前沃德也曾主张将教育作为改善社会的工具。美国课程改革这一地下潮流的重新出现,似乎是由于这些思想本身与有利于它们生存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此次改革的核心推动力恰是来自于对美国经济和社会体系的不满。在这场课程运动中,“长长的失业队伍和救济棚挫伤了早先盛行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关乎资本主义的未来,还关乎有关孩子在学校自然发展的浪漫主义思想。”[3]157因此,个人本位的,无论是侧重让每一个人都在社会阶层中找到他应有地位的社会效能派思想,还是遵从儿童自然天赋、个性自由、身体养护的发展主义派思想都不能迎合当时社会危机,渐渐失去了水源的补给,而社会改良派开始成为河流的干流,课程被视为纠正社会不公、纠正资本主义罪恶的工具。
其次是发展主义者对人文主义者的渗透。1908年,艾略特面对传统学校学科不保的危机,抛弃他一贯的立场,转而宣布“小学老师应该根据学生可能的命运对他们进行分类”[3]105。在提到手工培训的问题时,艾略特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且是课程中非常有用的一项内容——“应该增加贸易学校,为熟练的体力劳动生活做准备”[3]105。然而仅仅就在三年前,艾略特及其委员会还拒斥了发展主义者霍尔的“课程设置应与学生可能的命运挂钩”的言论,但是现在他比霍尔走得更远,甚至试图让分化课程延伸到小学阶段。这个人文主义者并非向发展主义阵营投敌,而是为了捍卫自身的精英立场:如果他所珍视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不能播散给所有的学生,那么这些价值观至少可以被保留在那个注定要上大学的群体中。如果没有这种妥协,至少在20世纪头十年的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可能完全从美国学校课程中被铲除。
再次,随着教育变革浪潮的冲击,人文主义者似乎还与社会效率教育者达成了一种不宣而就的和解。他们保留了传统的学术课程,但这些传统课程只与一部分特定的学生——大学预备生有关。1926年,康茨在《高中课程》(The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中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7],学校中的传统科目又开始捍卫自己了,打着健康、家庭生活、工业生产、公民身份和休闲娱乐几个社会效能派的大旗,实则是在以《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中的七大目标重新定位自己——尽管教学材料还是没有变化。1918年《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的出台基本上宣告了人文主义者被迫退守的姿态,可是他们依旧在社会效能派这里找到了继续存在的可能。
儿童研究运动的领导者倾向于将他们的祖先追溯到科米纽斯(Comenius)、弗洛贝尔(Froebel)、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和卢梭(Rousseau),但直到19世纪后半叶,儿童研究是课程设置的关键所在的观点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视。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认为,儿童的自然发展顺序是决定课程应该教什么的最重要和站得住脚的科学基础,因此他特别批判了人文主义者起草的《十人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en),主要指控以下三个观点:一是所有的学生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同等程度的教育,而不管他们可能的目的地是哪里。霍尔认为学生的天资不齐,尤其是低能儿童无法消化正常水平的课程。二是如果教得同样好,所有科目都具有同等的教育价值。霍尔反对“心智训练”中科目的形式可以传达训练价值,反对把学习内容作为“家具”的基本假设。三是适合上大学和适合生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霍尔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恶作剧。十人委员会认为,适应生活就像适应大学一样,然而,对霍尔来说,这只是大学控制主导高中课程的一种策略。[3]12
最后,社会效能派渗透了发展主义的思想。博比特在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第二十六期年鉴》中否定了他早期的中心观点——教育代表着为成人生活做准备。相反,他宣称:“教育主要不是为未来某一时刻的生活做准备。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高举当前的生活……生活是无法准备的,它只能生活着。”[18]杜威对儿童当下经验和生长本身的重视也寓于其中。
四大主导的利益集团时而分流,时而互渗,有时是主动吸收对方以充实自己的思想,有时甚至是无意识地受到对方的暗示。又或者,四大集团在课程立场上的分歧并非像他们的政治分歧一样绝对和明显,在其基本立场初步形成的时候就各自调和了众多并非异质的理念,而这些理念有着同一套思想源流。
(四)社会历史的总体驱动
以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改良派的崛起为例,可以清晰洞察课程主导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1926年美国失业率开始显著上升,众多行业,如煤矿、纺织业以及农业等都陷入了困境,随着股市投资者继续疯狂购买股票和债券,公共和私人债务都在迅速增长。于1929年上任的美国总统胡佛曾受过工程师的训练,以高效的行政管理而闻名。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他是新一代管理者的象征,一个凌驾于喧嚣的现实政治之上的人,并且当时乐观、繁荣和快乐是我们对“疯狂的二十年代”的一贯印象,但在这种乐观、繁荣和快乐的表象之下,似乎有一股强烈的不满情绪正蓄势待发。[3]1511929年10月24日,股市持续暴跌,一望无际的繁荣景象突然消失了。1931年,大萧条的影响冲击了欧洲,一场全球性危机变得越来越明显。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和雷克斯福德·图格韦尔(Rexford Tugwell)等美国左翼领导人呼吁采取激烈行动,包括对企业实施更大程度的控制和制定更多的政府规划。
杜威和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一起,对他们所认为的充满社会不公的体系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看法,“彬彬有礼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信条,和经济成功的权利和义务,使他继续信奉‘繁荣’这一虚伪的宗教。”[19]当这种不和谐的潜流(undercurrent)浮出水面时,它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课程改革的进程,但在20世纪20年代,课程改革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为改善员工作业环境,方圆生产总厂还对电解车间净化劳保进行了调整,将防毒口罩全部更换为以防护砷化氢为重点的1#滤毒盒防毒口罩,发挥出了较为优越的保护效果,受到了员工的认可和好评。
首先是人文主义者对社会效能派的渗透。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能力持理想乐观的态度,如艾略特认为“不可救药的人”的实际数量在学校人口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这因此成为对全民实施自由教育的前提条件。这种信念随后也在社会改良派的沃德那里生根发芽。沃德认为:(1)人的天赋在社会阶层和性别中是平等分布的。(2)文明的实现不是让宇宙的自然力量顺其自然,而是通过人的明智的行动将事情变得更好。“如果道德的进步不是由宇宙法则的世俗影响带来的,那么它一定是人类本性的力量向人类利益的渠道所引导的智力结果。”[16](3)借用一个遗产继承的隐喻,他进一步认为,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合理和公平分配的教育体系,因为无论在人类中可以观察到什么差异,它们都可以直接归因于这种教育的分配不均。在对人人天资平等,均有享受公平教育权利这一方面,沃德不仅仅与艾略特和哈里斯合流,更是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对人的主体尊严与自由高扬的理想。
但是时代在变化,社会改良派同样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驱动。一旦世界冲突的危机逼近,对美国社会状况的批评不再流行,社会改良主义作为一种推动课程改革的力量就让位给更符合时代潮流的课程思潮。随着美国即将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的批评逐渐失宠,取而代之的是由外部侵略威胁引发的爱国主义浪潮。而二战结束后,为经济的急剧变化做出了最具体的调整,并为可能成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满的社会提供了稳定的措施,这正是社会效能派重新崛起的缘由。
三、混重化与课程史观的重构
诚如克里巴德所言,“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改革之后,今天的美国课程是一种‘混合物’(patchwork)”,“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许多课程改革与其说是一种立场对另一种立场的胜利,不如说是曾经独特而容易辨认的课程立场的融合”。[12]大约在社会重建主义者在美国课程改革的斗争中发起攻势的同时,另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正在影响美国课程改革的进程。与其说它是一个新出现的利益集团,不如说它是曾经众多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与课程改革新融合的产物,它是所有竞争者有时有意识、有时无意识的思想大杂烩(potpourri)。
(2)减少独董可兼职的企业,将独董可兼职公司由五家减少为两家。保证独董的精力与时间,同时避免因兼任公司过多而引起混乱等情况的发生,增加独董对企业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提高其对企业的归属感。
比如,《第二十六期年鉴》宣布的目的是就新课程的组成达成一致意见。从进入20世纪开始,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动力推动取代一种通常被认为不适合新工业时代和大量刚进入中小学的新学生的课程。但是,这种变化的性质却一点也不清晰,从1924年开始,年鉴委员会在拉格的指导下,齐心协力地为混乱的改革带来某种连贯性,但最终敲定的“综合声明”与其说是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课程改革的重建或重新制定,不如说是对课程应然走向的深刻差异的掩盖。
又如,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八年研究”(又称“三十校实验”)试图解决的正是同时期出现的大学对高中的控制造成中等教育改革步伐缓慢的问题,大学与中学的关系思考又一次在半个世纪后提上日程。一些中学不用再学习大学为他们规定的课程,这些科目也不再成为进入大学的必须“关卡”。其基本思想是将实验中学从大学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然后证明这些不受束缚的学校的毕业生与完成传统的大学入学科目的学生是平等的,甚至更为出色。关键的测试是看实验组的学生和对照组的学生在大学里的成绩如何。最终29所高中大约3600名配对的学生被纳入样本。实验中学的新课程关注人文主义者呼吁的博雅通识和全面发展,发展主义者强调的个性自由和经验活动,社会效能派的目标导向和科学效率,同时也有社会改良派侧重的人与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学校为社会进步做出的努力。社会对青年的需要和期望正变得与青年本身的需要难以区分。混重化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所谓的核心课程——最持久的八年研究的成果之一,是一个混合体(hybrid)[3]183——学习者个体发展与社会整体效益,将珍视已有的经验与为将来做好准备的信念,将个体天赋素质和社会积极干预统统汇聚,凝成一股混重化的汤汤水流。
如前所述,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项改革背后的理由是因改革者而异的,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改革者可能暂时围绕特定的教育改革目的结成联盟,但是这种思想含混与暧昧的结盟一开始就是松散的、开放的、不稳定的。手工培训作为一项教育改革内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围绕着这一特定的课程改革,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改革者,他们认为手工训练有着截然不同的优点。卡尔文·伍德沃德(Calvin Woodward)认为这是一种维护学校项目工作尊严的方式;斯内登和弗兰克·莱维特(Frank Leavitt)对在没有高度差异化的课程安排的情况下接纳新入学的学生感到绝望;杜威认为手工训练是一个可以消除传统学术研究和校外世界之间人为障碍的机会。[3]282在手工训练课程改革中所拥有的就是一种联盟,他们在其中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使持反对立场的人聚在一起支持一项改革。这说明主流运动并非由单一的意识形态立场所驱动,其间的改革甚至还有逆流出现。因此钟摆现象实际上模糊了课程斗争的复杂性,流露出一种简单化的消极情绪,不是一种合理的课程史观。克里巴德以河流作为课程史斗争的隐喻,实际上正是批判了传统的二元循环的课程史观,即“在教育事务上,从改革到保守主义的摇摆不定的班轮运动和钟摆现象确实在20世纪成为一种持久的、几乎神秘的现象。”[3]75比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课程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学生牢固掌握以学术性学科为主的扎实的学科结构,有的观点认为这是导向人文主义者对传统学科的光复。但其实时代早已不同,面对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和苏联卫星上天的巨大压力,社会呼吁着科技人才的横空出世。这种现象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能解释的,而是融合了社会历史进程、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立场、西方文化遗产累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发展、阶级关系等众多因素作用形成的混重化现象。教育意识形态的钟摆现象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一历史时期并非由单一意识形态完全主宰。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课程理念的不断融合,半个世纪以来塑造了美国课程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至少在纯粹形式上是如此。比如,1945年哈佛委员会的报告《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1945)有一种温和的语调,“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既成为某一特定职业或技术上的专家,同时也成为自由人和公民”[3]206。红皮书虽然承认了一种时代呼唤的分化课程,但同时对于那些“思想水平较低”的人,也建议他们接受包括“世界、人类社会生活、想象力和理想领域”在内的通识教育。该红皮书充满了对学术学科的宽容,同时符合社会效能的要求。尽管哈佛委员会的报告与著名的哈佛前校长艾略特1893年的报告在学术建议上相去甚远,但它确实代表了对传统人文主义理想的谨慎和几乎胆怯的重申。以二元钟摆的课程史观解释这种人文主义的复辟是用历史退步论和宿命论的立场来看待课程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等于对半个多世纪的课程发展视若无睹。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致使整个欧洲都陷入了虚无,在那样一个神经过敏性焦虑增长的时代,就连那些相信自然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人,也开始思索人的存在和现代性的课题。以社会效能派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斗士一直在筹划剥去自然的精神意义,剥去人的精神投射到其上的全部象征性形象。这场把人剥得“赤身裸体”的奋斗在20世纪达到了高潮[20],引向两次大战后人类的总“崩溃”。欧美人站在那些精心制造的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上,对上帝、对提供物质必需品的庞大社会机构来说都是陌生人——而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预测、导向成功结果的世界竟然如此脆弱!无处可逃的绝望情绪引领美国的课程又一次向人与自然尚未撕裂的古典时代寻求慰藉和反思。
大哥,救救我吧!我实在是没劲了,再漂一夜,我怕熬不住了。听声音,跟男人年龄差不了多少。不中!这小木排,禁不动三个人。能禁动。大哥,你就行行好吧!苏楠看见水里面有个黑影撑着木排想朝上爬。
笔者经过多年在该领域的教学发现,没有合适的教材是大多数院校未能讲授这部分内容的主要原因。客观来说,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优秀著作并非没有,如上海交通大学刘延柱教授、洪嘉振教授编著的《多体系统动力学》《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高等动力学》《多刚体系统动力学》等,天津大学刘又午教授编著的《多体系统动力学》,吉林大学陆佑方教授编著的《柔性多体系统动力学》,北京理工大学袁士杰教授编著的《多刚体系统动力学》,大连理工大学齐朝晖教授编著的《多体系统动力学》等。
就四大主要集团而言,不同课程集团成为历史上的主导势力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前后继替的关系,而是作为不同势力的水流在无法明确划定时间的历史场中存在的,非主导力量即使受到时代和人民的压倒性批判时也没有绝对干涸,而是隐隐地融入其他的势力中,或者对自身的立场稍作改变,或者在保留原立场的基础上兼容了其他的思想流派,或者对自身观点做出符合时代特色的新的阐释,他们作为地下暗河留存了再次焕发生命力的可能性。
可以理解的是,一股新生的力量在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是很难为人所知所容的,甚至他自身也尚不具有将自己与其他力量完全区分开来的成熟的体系性和明晰性,因而具有某种混重的性质。但是它的发展经历了从混重—明晰—混重的过程,其中经历的一切是不容抹杀的。而且,课程学家也是人,他们既塑造集体的心理,也渗入彼时彼地集体的心理。课程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和政治、宗教、艺术、科学一样都是人借以存在的样式,认识课程史不是一蹴而就和断章取义的,更无法是非此即彼、抽空历史的。克里巴德认为课程走向混重的观点表明人的某种能力的局限性,也隐隐约约地暗示了自然可能归根到底是混沌的。认识课程史就要求人必须认识存在于所有人的存在借以表达的全部样式之内或者之后的统一性,即使它可能是混重的。
参考文献:
[1]魏小梅.赫伯特·M·克里巴德课程史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8.
[2]Kenneth Zimmerman,William Torry Harris.Forgotten Man in American Education[J]. Journal of Thought,1985(20):76-89.
[3]Herbert M.Kliebard.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M].New York:Routledge Falme,2004.
[4] Hall,G.S.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anthropology,sociology,sex,crime,religion and education,Vol.1[M].New York:D. Appleton,(1904a):8.
[5]Rice,J.M.Scientific managementin education[M].New York:Hinds,Noble & Elredge,xiv,1912.
[6]Ross,E.A.Social control: A survey of the foundations of order[M].New York: Macmillan,1901:441.
[7]Bobbitt, F.The elimination of waste in education[J].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1912(12):269.
[8]Ward, L. F.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M]. Boston:Ginn,1893:290.
[9]Counts,G.S.The selective character of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2:148.
[10]Counts, G.S.Dare progressive education be progressive[J].Progressive Education, 1932(4):258.
[11] Allan A.Glatthorn.Curriculum Leadership[M].Glenview,Illinois:Scott,Foresman and Company,1987: 89.
[12]李倩雯.克里巴德课程研究的河流隐喻及其历史意涵——基于《美国课程斗争(1893-1958)》的文本解读[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8(1):125-135.
[13]Snedden,D.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M]. School and Society, 1919:9, 526.
[14]Eliot,C.W.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in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en (1893)[J]. Educational Review,1905(30): 330-331.
[15]Drost, W.H.That immortal day in Cleveland——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Fifteen[J]. Educational Theory,1967(17): 178.
[16]Ward, L. F.Dynamic sociology, or applied social science as based upon statical sociology and the less complex sciences,Vol.2[M].New York: D. Appleton.1883:216.
[17]Counts,G.S.The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6:146.
[18]Bobbitt,F.The ori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maker[M]//Harold O. Rugg.The Twenty-Six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Bloomington, IL: Public School Publishing,1926:43.
[19]Dewey,J.Why I am for Smith[J]. New Republic, 1928(56):321.
[20]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5.
A Study of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Curriculum Struggle——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iver Metaphor
HAN Jiangxue
Abstract: American curriculum historian Herbert M. Kliebard vividly reveale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urriculum from 1893 to 1985 in American Curriculum Struggle(1898-1958)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iver metaphor, so as to uncover the complex ideological struggle and the dominant 4 interest group behind it. Kliebard explained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and the whole society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t is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that provide a new angle of view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urriculum. As a new paradigm of curriculum research, it represents the changing form of modern curricu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insight into the power of the four interest groups. Its inherent conception of curriculum history gets rid of the stale dualism and respects the mixture, ambiguity and complexity of curriculum history itself. It puts the curriculum back into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fi eld and disenchantments the myths of curriculum history.
Key Words: humanistist; social ef fi ciency; developmentalist; social meliorist
中图分类号: G5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19)05-0068-10
收稿日期: 2019-08-07
作者简介: 韩江雪(1995-),女,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 于小艳)
标签:人文主义论文; 社会效能论文; 发展主义论文; 社会改良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