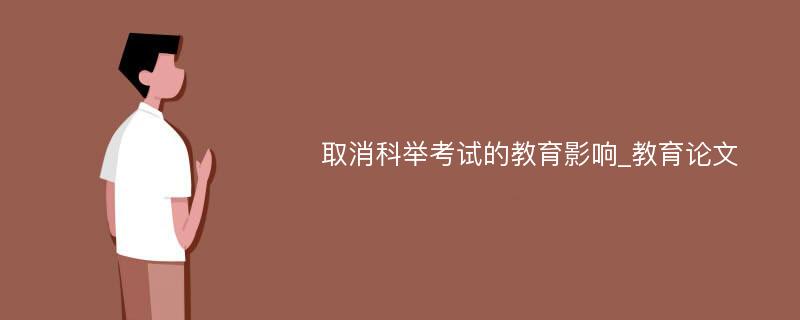
废科举的教育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以考促学”的国家考试制度,对教育的影响不言而喻,从这一意义上亦可视之为一种教育体制。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亦传入中国。近代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洋务派都将民族图强的希望寄托在新式西方教育上,并将教育症结归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束缚,极力主张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因而,科举的废除与教育是直接相关的。而废科举后的教育在获得大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困境,可谓是利弊兼得,且在很多方面是利弊相依的。
从利的方面看,由于废科举的直接目的与理由便是给新式教育开路,对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学者认为,虽然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即已兴起了新式高等教育,但在科举废止前,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步伐一直十分缓慢。这是由于科举不仅是传统高等教育的重心所在,而且还极大地制约着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因此,科举改革事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变革之全局,科举存废成为新旧高等教育转化的关键所在。废除科举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学制迅速推广,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留学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发生巨大变化。[1]
废科举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利的方面是女学的兴起。作为社会的“半边天”,女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女性接受教育则是反映其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虽然我国早在古代即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但受“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女性一直被拒于正规学校教育门外,女子学校教育因此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教育史上的空白。直到近代,这一空白才得以填补。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会”在宁波设立阿尔特塞女子学校,虽然该校进行的只是初等教育,目的也是培养虔诚的女信徒和未来的教牧人员,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可谓是一大创举。[2]此后,女性教育又开辟了通过留学教育这一途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教会女校和女子留学教育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中的进步人士,也开始创设女学堂。1907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的颁布为女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学从此更蓬勃地开展起来,且层次不断提升。
可见,我国近代女学虽然发轫于教会学校,但真正兴起却得益于学堂的兴盛。而学堂的兴盛正是废科举的最主要产物。据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1905年为8,277所,1906年为19,830所,1907年为35,913所,1908年为43,088所,1909年则已高达52,348所;学生总数也逐年递增,1905年以前最多不过258,873人(不含军事、教会学堂),1907年达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8,844人,1912年跃升为2,933,387人,几乎是1905年的12倍。[3]学堂和学生数的增长中便有女学的贡献。截至1907年,全国共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6人(据《光绪三十三年分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4]到1909年,全国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5]
从弊的方面看,废科举使得教育的普及失去了制度的推动与保障。在科举官僚体制下,由于读书应举基本上是士子们进入仕途和享受荣华富贵的唯一途径,正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企求功名富贵亦成为多数士子学习的根本动机。而以才学为录取依据则利诱着士子们刻苦学习,形成了促使人们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传统,和“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浓厚学习风气。[6]邓嗣禹即认为,科举考试制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儿童的向学之早之勤:“启蒙以后,家资虽贫,必茹苦含辛,送子学成:天资虽鲁,父师必严厉挞责,谆谆告诫,俾成可造之材。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纨绔公子,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倘肄业之时,一曝十寒,遇大比之年,名落孙山,则不拘富贫,皆垂首丧气,无面见人。非若现今学校,毕业与否,不甚紧要也。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7]事实上,由于科举具有“光宗耀祖”之功,儿童向学不仅受家庭父母而且也受宗族或家族的推动。宗族都设有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就读本族的宗族学校接受教育。再者,科举吸引着几乎天下所有可读书之人,但中第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落第者滞留在社会下层,他们为生计而设馆授徒,发挥着普及教育和传播文化的作用。即使是那些高中为官者,在仕途不得志或离职后,也大多回到乡间从事教育。而他们的科场经验,对热衷科举的学子们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无形中也增强了他们在普及教育和文化中的作用。
此外,和以身份等级为基础的结构封闭性的社会相比,科举时代由于精英层以及上下层之间均存在一个流动机制,使其文化知识与教育的覆盖面明显高于前者。萧功秦认为,隋唐以前,在九品中正制这种封闭性的人才选拔制度下,功名的获得所依据的条件,是世袭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努力与知识积聚的水平。文化知识的传播范围,往往局限在少数具有贵族血统或较高的世袭身份等级的阶层中。整个社会缺乏强大的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而在科举制下,功名、地位与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获取,是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这个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的,这就使社会的文化教育覆盖面达到近代以前最为广泛的普及与提高。而且,“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各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费用)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8]因此,国家和政府无需支付巨额的教育费用,科举亦得以避免其他“官学”因国家经费窘困而面临的发展瓶颈问题。正是这种全民向学和促学的浓厚风气,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到了清末,更是读书人数骤增,以致在外国人眼里,中国的读书人简直是世界第一,“就男性人口而言,世界上已知的国家内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有中国那样广泛。在这里,文学被置于一个最尊崇的位置,文学知识成为通往国家高官之阶的敲门砖……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知识置于财富、高贵门第之上。”[9]
科举被废后,虽然新式教育大兴,学堂数和学生数猛增,但其普及教育之功非但远不及科举,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还严重阻碍了教育的普及。首先,学堂的接纳能力与需求量严重不对称。1905年后,学堂的绝对数量虽有惊人增长,但对于当时有着4亿人口的中国,仍是杯水车薪。据估计,1906年,中国应受学之人约1亿,其中学龄儿童至少5,000万,而实际就学率仅为6%。适龄儿童就学率最高的北京城也不过42%。在兴学成绩斐然的直隶,1903年至1908年,学生数从6,000人增加到18万余人,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长,但相对于570万学龄儿童,1908年直隶的就学率仍只有3.2%!直隶尚且如此,其他不及之省份,其就学缺口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更有甚者,是学堂的办学效率低下,学务严重名不副实。例如,1906年,河南密县29所公立小学共有学生131人,平均每堂不到5人[10];顺天府的情况更令人怵目惊心,“各州县连一个真正的学堂都没有。某县立有蒙学堂十余处,其中的学生多半是花钱雇了来的小工,教习大概也都开过学房铺。在城内立有高等小学堂一所,学生共有四五人。前几天南路厅下乡查办事件,要到学堂里头去参观,赶紧连司事的全扮作了学生,对付着凑了十来个人,敷衍了敷衍。”[10]由于学堂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教育的普及,甚至可以说,科举被废后的教育普及状况比废前更恶化了。据罗斯基的研究,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从1895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却一直在下降(直到30年代,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至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11]
其次,是学堂对教育的促力远不及科举。邓嗣禹在对科举罢废前后的向学之风进行对照后认为,“自罢科举后,中大学毕业,无瞰饭之所,于是纨绔子弟,终日逸游,贫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义务学校,免费供膳,犹辞不入。强迫教育之今日盛,反不若科举时代能使人力争向上也。”[7]促学力的下降,盖因科举功名观念影响的余力尚大,使新学堂的毕业生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还远不能和科举功名获得者相比。清末学堂在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并未随之提升,反而因前者而出现质量的失控。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12]虽人人竞言开学堂,但开学堂所需的人才和物质基础并不具备,以致造成新学堂培养了不少“新人物”,但未必养成多少“新学人”的尴尬境地。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清政府在财政窘困的情况下,屡屡削减教育经费,亦严重制约了质量的改善——这些问题在具有民间办学性质的科举体制下都不存在。再者,科举的苛严竞争已深入民心,对传统教育深为迷恋的时人自然对清末处于混乱状态的新式学堂嗤之以鼻。因而,在废止科举前后,清廷为促进学堂的发展,不得不出台了一些甚为奇怪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依学生等级高下和程度优劣,分别实行科举虚拟和职官实授的双重褒奖,直到宣统三年(1911),各学堂实官奖励政策才被停罢。这种以科举功名和出身奖励学堂毕业生的做法,其实质是新式学堂教育与传统科举教育之间的一种妥协,同时也说明在科举被废之初,其对教育的促力仍远大于已然蓬勃发展的学堂,亦反衬出废科举对教育普及的消极影响。
废科举给教育所带来的另一个弊端是教育机会的上浮,进而造成新式教育的贵族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科举时代所形成的教育平等性。众所周知,科举制给天下士子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舞台,科举教育因此亦深具平等性。正是这种平等竞争机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也促进了教育机会的扩大与下移,并使得“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观念在科举时代深入人心。不只如此,科举制度还注重各地区教育机会的均衡,实行分区定额取中办法,以优待照顾边疆和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士子,促进当地人文教育水平的提升。[13]
科举即废,其原有的教育平等保障机制亦随之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全新的近代学堂教育体系。这种新教育体系不仅带来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管理体制、经费及教育结构重心等诸多改变,而且带来受教育机会的变化,后者主要由前者某些方面引起。以教育结构和教育经费的改变为例。虽然废科举带来了学堂的迅猛发展,但由于清末教育投资的重点在中学堂以上的高级教育中,致使为数众多且成为教育普及基本单位的初等教育学堂因资金紧缺而发展乏力。再者,从各级学堂的设址看,京师大学堂和其他各类高等、专门、实业和师范学堂都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学堂也基本上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显然,学堂的如是布局基本上将农村排挤出去了。[14]教育层次结构的严重失衡,带来的后果便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学校教育的割裂,以及如陶行知所谓的“让农村人往城里跑,让自利者变为食利者,(学校教育)只针对有钱达官贵人,而百姓子弟仍无受教育机会”。[15]
再从教育经费的支出看,学堂(初等小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除外)实行收费上学,且学费昂贵,加之书本笔墨和膳宿等开支,不像昔日科举教育的主要开支仅周期性的赶考费一项。据张謇对江苏南通地区的估算,在20世纪初,一个家庭要送一个孩子上初等小学,每年需花35-50元的总学费(而传统私塾的学费不过是几元)。当时,一个普通农民每年平均收入仅12-15元,而在张謇工厂的工人每年也只有50-100元的收入。而湖南西路学堂每学期的膳宿及杂费就高达50多元,一年即要100多元。[14]清末京曹何刚德在比较科举和学堂的教育费用支出时曾说:“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火,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金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收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所以入学者寥寥无几。[15]对科举痛加批判的民国时期教育家黄炎培,也不得不承认科举导致教育机会下移这一点。他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公家教育,最初是偏于贵族方面的。由贵族教育,移到平民教育身上,靠什么东西,做他们过渡的舟子呢?倒是科举。宋赵汝愚评王安石时代的政治,说‘自科举罢后,寒畯之士,进取无途。’(《续通典·选举略》)自然,任何问题,见到九百九十九分的坏处,总不要忘掉中间也有一份好处。科举也是这样。等到后来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带多少贵族教育的意味,这倒是科举时代料想不到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废科举给教育带来的影响总体上弊似乎要大于利。民国初年的政论家杜亚泉认为,如果在最初考虑改革科举制度的具体办法时,不是简单的废止科举制度,而是“稍稍改其课士之程式,简(选)稍通时事之儒臣,典试各省,依今日之教科门类,列为试题,以定取弃”,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单单废除科举而建学堂的效果更好。[8]历史不能假设,亦无法重来。且不论杜亚泉的观点正缪与否,但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科举影响的新思路。笔者以为,废科举于其时的教育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但历史的脚步无人能阻,且废科举在开辟现代教育之路这一点上的积极意义至为深远。随着这条路越走越宽阔,其积极意义将越来越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