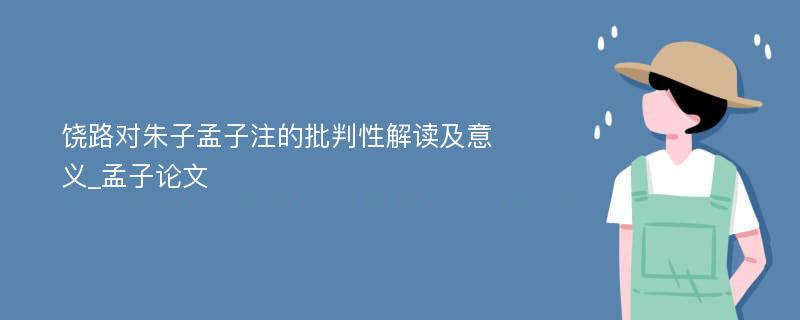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集注论文,批判性论文,意义论文,朱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1-0126-10 饶鲁,字伯舆,一字仲元,又字师鲁,号双峰,江西余干人,大致活动于南宋理宗、度宗朝。饶鲁师从朱子高弟黄榦、李燔,不事科举,专意圣贤之学,以其深厚的理学造诣,屡被各地礼聘讲学,同时创办书院,教化学者,声望甚隆。饶鲁著作甚多,惜乎皆不传,后人辑录为《饶双峰讲义》16卷,基本为饶氏《四书》论述。学界对饶氏思想研究极少。事实上,饶氏是对宋元之交理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宋元学案》所立《双峰学案》,认为他上接黄榦、下开吴澄,其思想尤以不同于朱子为特色。饶氏据自身为学工夫,在《四书》诠释上提出了新的诠解,对朱子学展开了诸多批判修正,流露出“心学”痕迹,显示出朱子后学思想的创造性。本文拟论述饶氏在《孟子》诠释中就理气、性、心、工夫、仁政诸论题中提出的颇富新意的看法,并剖析饶氏多异于《集注》的原因及其影响,以见“后朱子学”演变轨迹之一斑。 一、理气 饶氏以理气说为枢纽阐释《孟子》,其对“浩然之气”章的阐释更是围绕理气展开,提出了不少新颖之见。 首先,在理气关系上,提出理主气辅说。饶氏认为“自反而缩”的“缩”指理,“不惴、吾往”指气,理对气具有直接主导作用,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辅。理能决定气,故理直则气壮,理屈则气馁。“缩不缩,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气言。理者,气之主。理直则气壮,理屈则气馁。”①他主张理先气后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浩然之气全靠道义为主宰,无道义则气软弱无力。原因在于有是理而后有是气,理在气先,为气之主宰。理气关系好比太极与阴阳之关系,二气所以常在,盖有太极作主。《孟子集注》以“合而有助”解“配义与道”之“配”,理气不离,很好地揭示了气以理为主、理以气为辅的关系。饶氏说: 浩然之气全靠道义在里面做骨子,无这道义,气便软弱。盖缘有是理而后有是气,理是气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气,以有太极在底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集注》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于彼者。盖理气不相离,气以理为主,理以气为辅。② 其次,以体用解释道义,认为道体义用,体用不离。故养气工夫仅说集义这一道之用而不言道之体。浩气自身亦有体有用,其体、用分别与道、义相配,体用一源,言用即体在。此处仅言义上工夫,盖体上无法用功也。“道是体,义是用。浩然之气有体有用,其体配道,其用配义。故曰‘配义与道’,其体用一也。言用则体在其中,体上无做工夫处,故只说集义。”③ 再次,以理事解释道义,主张道义相当于理事,道是理,义是事。古往今来只有一个道,道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稳定性,义则表现为把握事物的变化,在变动之中应对合宜,具有权变的意味。理有正邪之分,事有当否之别,故道义、理事皆从两面言之。就理事关系言,一时合宜之事往往存在与古道不合之处,故对事情的判断应两面兼顾,既要从义之用上看,还要从道之体上看,二者缺一不可。汉儒“反经合道”之说仅仅顾及一时之用而忽视不变之体。饶氏说: 孟子说道必说义,如配义与道,皆是先义。亘古穷今只是这一个道,义是随时处事之权。要两下看……义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之,则得其宜;以理言之,则得其正,然后为尽善,故两言之。今处事有合一时之宜,及揆之以古道,则有不合处。道是体,义是用。既就用上看,又须就体上看方得。汉儒反经合道之说,便离了个体。④ 复次,把理气运用于政治领域,提出理德气势说。《离娄》“天下有道”章言:“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⑤《集注》把“天”释为“理势之当然”,兼顾理、势两面。饶氏指出,《集注》以理势解说本章,“德贤”就理言,“大小、强弱”就势言。决定天下的因素在于理和气,二者相依不离,有理必有气,气在事上的表现就是势。因此,理气关系就呈现为理势关系。一方面,决定事情走向的是势,势的发展有其不可避免的规律性,即“势之当然处”,事情发展至“势之当然处”,则非人力可回,也即是天了。如郑、卫、齐与南蛮之楚作战而大败,乃是势不如楚。可见势对事情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孟子》所谓“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即强调势在起决定作用。但饶氏又指出,大德之贤人在面对不利之势时,通过其强大的才德,可以做到以德胜势,以德回天,使大势小德者为我所用,文王即是如此。此即《孟子》所谓“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之义,此说极大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突出“德”对事情发展的决定性,它可以使命运始终牢牢把握在主体之中。饶氏说: 《集注》将理势二字来说。小德大德、小贤大贤以理言,小役大、弱役强以势言。盖天下有理有气,就事上说气便是势。如郑卫齐楚之役,亦势之当然也。才到势之当然处,便非人之所能为,即是天了。 贤兼才徳,以政事言也。虽曰时势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胜了这势,孟子所以不说尧舜而说文王者,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为纣所役,此可以见德足以胜时势处。⑥ 最后,批评程朱“孟子论理不论气”说。饶氏在“生之谓性”章指出:“人说孟子论理不论气,若以此章观之,何尝不论气也?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觉运动,为是个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禀得天地之生气,所以有这活底在里面。告子是见得这气,不曾见得这理。盖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觉运动者,属乎气。其所得于天,以为仁义礼智之性者,则属乎理。”⑦他认为程朱所言“孟子论理不论气”说不对,孟子其实亦论气。本章孟子明显论及理气两面。人在有生之初禀得天地生气,此生气给予人知觉运动的活动能力。告子仅仅识得此气而不见及理,“认气为性”,故有“生之谓性”说。人的精神魂魄之所以能运行,亦是属于气而非理。理是天所降生人所禀赋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理、气其实内在一体,密不可分。 二、性 饶氏把“性、天理、仁义”贯通起来解释“性”之名义,据《中庸》“天命之谓性”说指出性是人所禀之天理,人性来源于天理,同时又是天理的内在体现。人性的内容是以仁义为首的五常。因为仁义为人性所固有,故照仁义去做就是顺应人性之自然,反之则是戕贼人性。“然不知性者,人所禀之天理。这天理即是仁义,是顺此性做去,便是自然,不是矫揉。”⑧ 饶氏继承程子说,考察了性与气的不即不离关系。人生之前不可说性,既生之后才可说性,但此已是落在气质中之性了,此气质之性有善与不善。其性之本然,则是纯善无恶,即天地之性也。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必须分成两个说,否则性、气糊涂无别。但亦不可把性、气过于分开,当合作一性说,否则会认作两个外在的东西。二者关系可谓不即不离,一而二,二而一也。他说: 人未生以前不唤做性,既生以后,方唤做性。才唤做性,便衮在气质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气质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气质中指那本然者说,是则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两个性说,则性之与气,鹘突无分晓。若不合做一个性说,认做两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则不是”。⑨ 饶氏批评了《孟子集注》有关性的论述。《滕文公》“滕文公为世子”章提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集注》认为先言“道性善”、后言“称尧舜”,是以尧舜这一典型来证实性善的真实可信,使学者知仁义内在,圣人可学。“故孟子与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欲其知仁义不假外求,圣人可学而至……”⑩饶氏的理解恰与《集注》相反。他认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目的不在性善,而在称尧舜,希望世子以尧舜为楷模,效法学习之,但因担心其学尧舜有畏难情绪,故先道性善,其意在于使世子知学尧舜不难,性善为人人所固有。《集注》此处对“性”的解释是:“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11)并以“性善”解释《孟子》的“道一而已”说。饶氏批评《集注》此处对“性”的阐发偏重,指出性以所禀言,是上天赋予的普遍之理,人皆同有;道以所由言,是现实状态中人对于性的实现,具有工夫实践意义,“性一”与“道一”具有本原与效用之别。当世子与孟子再相见时,已经相信性善说,只是怀疑尧舜难以效仿企及,孟子“道一而已”乃是劝勉世子以尧舜为榜样,“道一”是就典型事实说而非就性上说。下文孟子紧接着引用成覵、颜子、公明仪三贤说,目的皆在于以事实证明圣贤可学。《四书管窥》引饶氏说: 饶氏谓:“道一而已矣”与“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禀言,道以所由言。《集注》此处说得“性”字稍重。 [史伯璿按]但饶氏自上节说性善尧舜处,已与《集注》不同。此节又是承上节所说之意而言耳。其于上节,则曰:“孟子之意不在性善,只在称尧舜,欲世子凡事学尧舜。又恐其以尧舜为难及,所以先道个性善。”惟其上节如此说,故于此节则曰:“世子再见孟子,已信孟子性善之说了,但疑尧舜非人所及,孟子说‘道一而已矣’是就尧舜上说,不是就性上说”云云……饶氏又谓:“当以孟子所举成覵、颜子、公明仪之说推之,可知其意。”(12) 《孟子集注》“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取程子说,认为“此章专为智而发”。饶氏直接批评了“专为智发”说,主张本章主旨是“性”而非“智”。他把全章分为三节,起首“天下之言性也”云云说“性”,中间“所恶于智者”云云说“智”,最后“苟求其故”云云说“故”。若本章仅仅是言“智”,则仅中间一节足矣,又何必起首言性、末尾言故?“这一章本是说性,不是说智,若把做智说,则首尾不类。初说性,中间又说智,后又说故。若曰说智,则中间足矣,又何必兼首尾说?”(13)饶氏的性、智、故三节说影响颇大,连向来对饶氏颇无好感的陈栎,其《四书发明》亦称:“每读此章,不能无疑于程氏之说。得饶氏此说,以读此章,意豁然矣。”(14)其弟子倪士毅所著《四书辑释》亦“备载饶说”。 饶氏对仁义亦有新说。《孟子集注》“仁之实”章解为:“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15)《四书管窥》所引饶氏说对此表达不同看法:“饶氏谓仁义有以性言者,有以德言者,有以道言者。此章尝(按应为‘当’字)作道说,《集注》‘仁主于爱,义主于敬’八字,恐非本文之意。若曰‘仁之道主于爱,义之道主于敬’可也。”(16)饶氏指出:仁义可从性、德、道三个层面讲,本章从道的角度切入较好,《集注》仅从爱亲师兄的道德事实层面解释仁义,不合本文之意,加一“道”字保持作为体的仁与作为用的爱的距离。有人认为,管仲责备楚国苞茅不入昭王不复是假仁。饶氏指出,仁居五常之首,可含摄仁义礼智信五常。管仲虽然是假义,但孟子不说假义而说假仁,是因为仁包五常,故言仁则义在。“孟子不说假义,却说假仁,盖仁包五常,言仁则义在其中。”(17)饶氏进一步认为,仁甚至亦可包含乐。如《诗经》言自乐非仁、同乐是仁,与民同乐即是仁之体现,是天理之发露。“自乐便不是仁,同乐便是仁。如文王未尝无灵台灵沼,然与民同乐,便是天理。”(18) 饶氏对“浩然之气”章提出新解,认为整章的中心在于“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两句,“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长”是集义,“正而助长”是义袭。不做集义工夫者为不耘苗者,以义袭为心而预期其效为揠苗者;浩气为集义所生,故直养之,勿忘之;非义袭而取,故无害之,勿助长之。他说:“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长,是集义工夫。正而助长,是要义袭而取。集义、义袭两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义为无益而忘之者,不耘苖者也;以义袭为心,预期其效而助长,揠苖者也。又谓‘是集义所生者’,故当以直养;‘非义袭而取之也’,故当无害。惟其是集义所生者,故当心勿忘;惟其非义袭而取之,故当勿助长。”(19) 三、心 饶氏对心的认识亦是在批判《集注》的过程中展开,侧重仁与心的一体,流露出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如他指出《孟子集注》“至诚不动”章“明善又为思诚之本”说过于分析支离,造成思诚在明善之外的印象,而孟子之意,则强调明善即是思诚,二者一体不分。“《集注》‘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似明善之外又有个思诚,恐非本文之意。盖明善即是思诚。”(20)《集注》把“君子所以异于人”章“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解释为:“以仁礼存心,言以是存于心而不忘也。”(21)饶氏指出:《集注》对孟子的以仁礼存心说添一“于”字,变成“以是存于心”,便与本文意义有很大差别。孟子意在用仁礼存心,心之所主在仁礼,要求把心安顿在仁礼上,即心主于仁礼,不至于放纵邪僻,无有片刻之离。心安于仁,即居天下之广居;安于礼,即立天下之正位。此时心为仁、心为礼也,显示了君子存心高明之处。《集注》加“以”“于”二字,便好似把仁、礼当作物体一般置于心中,变成仁礼主于心,与《孟子》义正好相反。孟子强调的是仁、礼作为道德原则对于心的主导性,《集注》“以是存于心”说则更突出了仁、礼对于心的依附性,彰显了心对于仁礼的包容与统领,正与朱子所秉持的“心是性之郛郭”的心为性之载体说相合,饶氏之说则更近于心学的仁即心说。《四书管窥》说: 饶氏谓孟子只言“以仁存心,以礼存心”。《集注》乃云:“以是存于心。”添个“于”字,便与本文不同。孟子之意,是把仁礼来存我个心,我之所主在于仁礼上,我个心安顿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广居。我个心安顿在礼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饶氏又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此心常在仁礼上,无顷刻之或离。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耳,他人便不能以仁礼存心。”(22) 饶氏对“牛山之木”章的解释同样强调了仁义之心的一贯性,批评《集注》的知觉之心说。他认为孟子前文“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指仁义之心言,后文所引孔子“操存舍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之心亦应指仁义之心,《集注》解后者为神明不测的知觉之心,违背了孟子之义。饶氏之意,心是性与知觉之合,含仁义与知觉两面。孟子所引孔子说从表面看来似乎言心之知觉,其实质是强调操存此心,若是知觉之心,何须操存?操存本就是为了守住仁义之心。《集注》仅主张专言知觉之心而未言仁义之心,不确。他说:“孟子说‘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则后面所引心之出入,亦只指仁义之心而言。《集注》云‘神明不测’,似又专说向知觉上去,恐非孟子之意。盖心者,性与知觉之合。”(23)史伯璿认为:仁义之心与知觉之心不可分离,处于仁义之心状态时知觉之心同样存在,即强调仁义之心并无须否认知觉之心,而饶氏的特点是将二者相对立,以突出仁义之心。“双峰每以仁义之心对知觉之心而言。”(24) 在“仁人心也”章的理解中,朱子的门人黄榦、再传弟子饶鲁就心的属性提出与朱子的不同看法。孟子本章首言“仁人心,义人路”,末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集注》对此“心”分别从义理与知觉的角度做了区别,认为“仁人心”突出仁是心的本质,决定了心的根本走向,正如谷种的本性在于生生不已,生决定了其所以为谷之种的生长这一根本属性一样,仁则显示了人心具有义理这一根本属性。但朱子接下来的论述重心迅即转向了“心”而非仁,他认为“人心”说正显示出心作为身之所主的应接、统领功能。“求放心”的“心”是知觉之心,“放心”具有“昏昧放逸”的特点,与之相应的“不放之心”则具有气上清明、理上昭著的性质,突出了心如镜般的“明、照”性。他说: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谓之仁,则人不知其切于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则可以见其为此身酬酢万变之主,而不可须臾失矣。 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25) 饶氏则认为,孟子“仁人心”之“心”指义理之心,“求放心”之“心”同样是义理之心。《集注》视后者为知觉之心,与前文不相应。放的心是什么心呢?如果是知觉之心,则知觉之心随时皆在,不存在放不放、求不求,故当求的应是放去的仁义之心。若把“求放心”当作收摄精神,使其保持惺惺不昧的工夫,则是专就心的知觉而论了,与本文“仁人心”强调仁义之心显有不符。饶氏说:“孟子上面说‘仁,人心也’,是把这心做义理之心;若把求放心做收摄精神,不令昏昧放逸,则又只说从知觉上去。恐与上面‘仁,人心也’不相接了。”(26)饶氏之说又得到陈栎、倪士毅的认同,史伯璿指出:饶氏“此说盖为破《集注》志气清明与昏昧放逸数语而发”(27)。其思路与“牛山之木”章相同,皆是强调心的义理属性而反对《集注》的知觉说。其实《集注》“虽说从知觉上去,却于义理放逸之意两无所妨”。 《四书大全·孟子集注大全》卷十一引饶氏说,并加入了其师勉斋之说: 双峰饶氏曰:“曩以此质之勉斋,勉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学问之道,非止一端,如讲习讨论、玩索涵养、持守践行、扩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过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学问之道也。三个‘心’字,脉络联贯,皆是指仁而言。今读者不以仁言心,非矣。”(28) 黄氏认为:“仁人心”指仁是人之心,“求放心”是学问之道,其途径有多种,但皆以求仁为根据,故求放心即是求仁,此乃学问根本之道。仁人心、放其心、求放心三个“心”脉络相连,皆是指仁,读者当始终铭记言心当从仁入手方是为学正途。朱子与黄榦、饶鲁看法相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此从不同层面立论。朱子着眼于“放心”的性质,放心表现出来就是知觉上的昏沉暗昧,遮蔽了心所固有的虚灵、神明之性;意念上的放纵散漫,毫无收束主宰。饶鲁追问的则是“求放心”,所求的只能是仁心而非昏昧放逸的知觉心,“放心”作为一专有概念并非所求之物,“求放心”当理解为心已经散失了,故当求之,所求的是散失之前的心,而非散失状态的心。黄榦则有所折衷,提出学问之道有多端,涉及讲学讨论、玩索涵养等,但其根本是求仁,求心即求仁。心即仁也。 四、存养扩充 饶氏《孟子》的诠释还分析了儒学的“反之之道”。程子提出“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有学者提出:若未反之时,此性在否?饶氏认为未反之前,此性亦在,性与理一般,永恒存在,并不因人之反不反而产生变化。只是因为人有气质、物欲之累,导致不能常存此性。必须通过反之工夫以存性之本体,具体包括涵养、体认、克治、充扩四方面。但孟子对工夫之论述,言及涵养夜气,体认扩充四端,惟独对克治工夫有所遗漏,应补充之。 问:“‘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时,此性亦未尝无……但人有气质、物欲之累,则此性不能常存。须于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问:“反之工夫如何?”曰:“涵养、体认、克治、充广,皆是反之之道……孟子说夜气,便是要使人涵养,说四端及扩充,便是要体认充广,独有克治一边,却不曾说。”(29) 饶氏特别重视存心、推扩工夫,指出“牛山之木”章“紧要在三个‘存’字上”。该章首言此心本来存乎人,次言夜气是说众人不能存,最后言操则存,是教导人用力于此。仁之扩充次序是亲亲仁民爱物,以达到普爱民物之境地;义之扩充次序是就一事之宜推于事事合宜,礼智皆是如此扩充之。“自亲亲而仁民而爱物,推至于无一民一物之不爱,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于无一事之不得宜,是充义之量。礼智皆然。”(30)他还认为,四端虽然人皆有之,但并非人皆能扩充之,惟有君子能扩充四端而众人不能扩充之,此即君子与众人的同异所在。扩充之关键在于“知、皆”二字,既应知如何加以扩充之法,又能对四端皆能切实扩充,若能如此,则为君子人也。 问:“四端众人皆有,若扩充似非众人所能。”曰:“‘知皆扩而充之’,其紧要在‘知’字、‘皆’字。众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扩而充之,又于四者皆能扩而充之,则便是人中之君子。”(31) 饶氏批评《集注》把孟子立其思的工夫改变为敬以修身工夫。《告子》“心之官则思”章言“此天之所与我者”,《集注》谓:“此三者,皆天之所以与我者,而心为大。若能有以立之,则事无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夺之矣,此所以为大人也。”(32)饶氏指出:此处无须耳目心三者合说,只须强调天降生赋予此心于我,使我以此心去思考,便能做到驾驭身心各处,此即为立其大者。但《集注》并未指出“立其大者”是把“思”立起来,却说“立之则事无不思”,立后才思,把工夫转移到“立”上来,所谓“立”又变为以敬立身,把工夫要领转移到敬上去。朱子此番诠释脱离了《孟子》本章突出“思”的本意,将其主旨转换为了他所推崇的主敬说。《孟子》此处显然并无敬意,《集注》所引范浚《心箴》“克念克敬”说乃范氏之意而并非孟子意。《四书管窥》引饶氏说: 饶氏谓不须合三者说,只说天把这心与我,教我去思,便能御众体。此即立其大者。 饶氏又谓《集注》不曾把思做“立其大者”,却谓“有以立之,则事无不思”,如此则又先要做立底工夫,又做敬上去了。然此章在思而不在敬,箴中敬字是范氏意,非孟子意。(33) 饶氏就知言养气提出了不同于朱子的新看法。他首先区分了境界与工夫,认为孟子自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不是修德工夫而是成德境界,“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才是养气工夫,进而结合《中庸》之说,指出“浩气”即三达德(知仁勇)之勇,不动心是勇者不惧,知言是智者不惑,并强调浩然之气特别凸显了“勇”这一德目。“孟子之言善养气是以成德言,非是说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说养气做工夫处。浩然之气即达德中之勇,不动心即是勇者不惧,添一个知言即是知者不惑。”(34)饶氏明确肯定孟子“知言”即是知道,“知言”乃是孟子不欲以知道自居的谦虚表述。“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谓,所以只说知言。”(35)他还就诐、淫、邪、遁四病做出细致分析,从阴阳的角度分为两面:诐、淫属阳,邪、遁属阴;前者尚有部分道理,后者则纯是违理。除去四病的关键在于去蔽,人受蒙蔽的源流不同,大概有四种:或气禀,或物欲,或学术,或习俗。据夫子关于言蔽的论述,去蔽的方法在于“好圣贤之学”。盖非圣贤之学者皆易误导人心,只有专意圣人之学方可摒除四病。 虽是四件,却只是两件,诐与淫属阳,邪与遁属阴,盖诐尚有一边是道理,邪则并这一边亦离了……欲去蔽陷离穷之病,在先去其蔽。无所蔽便无下面三件。蔽之源有四:有为气禀所蔽,有为物欲所蔽,有为学术所蔽,有为习俗所蔽。问:“去蔽之道当如何?”曰:“孔子尝谓六言六蔽皆基于不好学,欲去蔽者,当自好圣贤之学始。”(36) 五、仁政 饶氏还就《孟子》所涉及的仁政、征讨、王道等政治问题提出与《集注》的相异之解。他认为仁政首要确立的是封建制度,但孟子却从不言及封建,原因在于孟子之时,诸侯之间大小强弱相并,封建制度主体已经残坏,仅残存其迹而已。再则,封建之事乃王者所专行,孟子所论说对象皆为诸侯,故不及封建。《四书管窥》云:“饶氏仁政第一是封建云云。或问:孟子不十分说封建,何耶?曰:当时大并小、强并弱,封建虽坏,其迹尚存。兼之封建,王者之事。孟子当时只为诸侯言之,所以不及此。”(37)饶氏指出,《集注》释“夫子当路于齐”章“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节的“大行”为“教化大行”不妥。此处上文有“文王之德”的“德”字,却无“教化”字,据上下呼应关系,所谓“大行”亦应指“德”之大行而非“教化大行”。因天下在文王时尚有一分未被其德,尚未平治天下,经武王拥有天下,周公推行礼乐之后,连殷之顽劣之徒亦受其德化,天下皆归于文王之德,故至此方可谓大行天下。“本文无‘教化’字,恐只当接上文‘德’字说。盖文王之时三分有二,尚有一分未被其德,所以犹云‘未洽于天下’。至武王有天下之后,周公制礼作乐而殷顽亦率德改行,然后无一人不归是‘德’之中,是谓大行。”(38) 关于诸侯征讨,涉及齐王是否可以讨伐燕国的问题。《集注》引杨氏说,主张“燕固可伐矣”,认为若齐王能诛其君而吊其民,则“何不可之有”。饶氏则据《孟子》惟天吏可罚有罪之国说,推出诸侯间不能互相擅自征伐。沈同仅知燕国可伐但不知齐国不可去伐,因为齐国不具备天吏之身份。“饶氏曰:惟天吏可以伐有罪之国。诸侯如何擅相征伐?沈同但知其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39)此解适与《集注》有别。饶氏更注重讨伐者身份的正当性、合法性,朱子则更关注齐王伐燕行为本身的正义性而不在乎其身份的合法性。二说各有所据,但就孟子本意而论,恐《集注》说更胜。史伯璿就认为《集注》之说活,饶氏之说死。 关于王道。饶氏认为《离娄》“得志行乎中国”章所举舜与文王分别为东夷、西夷之人,二圣所处时代、地域差别甚大,但皆得志于中国,其志行好比剖判符节之相合,批评《集注》解“得志”为“得行其道于天下”不妥,把“道”字说得太早。因此时尚处于“得志”时期,尚未推进到“行道”阶段,下文“先圣后圣其揆一”方才说及“道”。 饶氏谓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皆得志于中国,便如符节两处来相合一般。《集注》解“得志”做“得行其道”,说得“道”字太早。“得志”是得遂其志,留得个“揆”字在后面说,“揆”正是说道。(40) “其揆一”的“其”指大舜、文王,“揆”是说道,“揆”好比符节,此符节非人力所能为,而是上天赐予的,是天命之道。《集注》“度之而无不同”说已经涉及人为,似乎还需要作者用意度量方能如此,与“道”已经隔了一层,没有把“道”的普遍性、同一性彰显出来,忽视了对“其”的理解。 其揆一也。饶氏谓“其”字指舜、文而言,“揆”便是符。这一个“揆”是天与之,此“揆”不是人做得。《集注》言“度之而道无不同”,又隔一皮了,不曾解得“其”字。(41) 《集注》解《离娄》“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章为:“民已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道已至矣,而望之犹若未见。”(42)饶氏则认为,“伤”应为用刀伤害之义,突出文王对百姓关切之深,对百姓处境之不安充满恻隐愧疚之情。此处上下文意皆论及治理天下之问题,似乎与道并无多大关系,故“道”恐为“治”义。饶氏之解,自可备一说。“饶氏谓平日视民,便如我著刀伤相似,望道或以为望治。”(43)《集注》“孟子去齐”章引孔氏说,认为公孙丑欲以“仕而不受禄”之一端来裁定孟子出处。饶氏认为礼有经义有权,如命召不俟驾和不召之臣即是,公孙丑之意并非是以一端裁孟子,而是在问礼之权变,故孔氏断语不够稳妥。他说:“礼则有常,义则有权,如君命召不俟驾,礼也;有不召之臣便是义。孔氏谓‘仕而受禄,礼也;不受齐禄,义也’,说得自好。但言公孙丑欲以一端裁之,下得却未稳。”(44) 饶氏亦就有关古代制度礼法的问题提出与朱子的不同之解。如饶氏认为《朱子语类》把“滕文公问为国”章的“彻”当作与贡、助并行之法不妥。孟子之“彻”不过是不分公私、普遍通行之义。周人彻法之行,仅是助法的补充。“朱子之意,只把彻做法了,孟子之意不然。彻则无分公私,但周人是因助之田而行彻之法。然周虽用彻法,有用助处,毕竟优于乡遂。”(45)《集注》对“人皆谓我毁明堂”章的“耕者九一”从赋税角度解释,“八家各受私田百亩,而同养公田,是九分而税其一也”(46)。饶氏认为“耕者九一”不是赋税,而是所得,即九成得一,若赋税则采用十一制,且下文世禄亦是就所得言。“饶氏谓耕者九一是以民之所得者言,谓九百亩中得百亩,非说赋税。若说赋税,则是什一,下文世禄亦是指士之所得言。”(47)此外,饶氏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孟子,对其井田制、“治国不得罪于巨室”、“三月无君则吊”诸说提出批评性看法。如认为井田制在中原平整之地可行,但山区地势则无法推行,孟子对井田制的理解恐为臆度之言而不符合事实;“不得罪于巨室”说与孔子堕三都说矛盾;“三月无君则吊”说当就祭祀之礼来理解,吊是吊其不得祭而不是不得君。 六、饶鲁与“后朱子学” 上述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解读,可略窥饶氏思想之一斑。就思想史而论,饶鲁并非重要人物,但亦非可以完全轻视之人物,尤其在朱子学的发展历程中,饶鲁是有其特殊贡献与地位的。在朱子去世之后,以黄榦为首的朱门弟子全力护持、发扬朱子学,饶鲁作为黄榦器重之高足,“亦勉斋之一支”,与同出于黄氏的“北山学派”首领何基分传朱子学于江西、浙江,对宋末元初江西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培育了朱公迁等一批朱子学者。但学界或囿于资料,或限于省情,对“北山学派”的研究与对“双峰学派”的研究相差甚远。我们认为,对思想上具有独创性的“双峰学派”的思想亟需加强研究,尤其是在朱陆异同、理心合流这一影响元代理学大局的论题上,“下开吴澄”的双峰学所体现的某些近乎心学的特质值得挖掘。 耐人寻味的是,饶鲁虽为朱学正宗,其思想却以“多不同于朱子”(48)而著称于“后朱子学”界,引发了元代朱子学者的高度关注与热议,后朱子学界对其可谓“爱恨交加”而“欲罢不能”。学者对其思想多所“发明”之处普遍加以肯定、吸收,并常以之纠正《集注》之说,此为其“可爱”之处;同时,就其偏离朱子之学、“破《集注》说”之论述亦予以猛烈批判,甚至有就其人格、气质加以批驳者,此为其“可恨”之处。尽管学者普遍能正视饶氏思想之得失,但在爱恨之间仍表现出某种偏向。以下以元代数位知名朱子学者对饶鲁的看法为例,以显示其对元代朱子学的深刻影响。 婺源胡炳文集50年功力纂成《四书通》一书。该书以删、辨诸家谬误,会通朱子之意为宗旨,对朝鲜理学亦影响颇深。他在凡例中特别交代双峰之说对朱子大有发明,其中亦有个别地方偏离朱子,则须加以辨析。“双峰饶氏之说于朱子,大有发明,其间有不相似者,辄辨一二,以俟后之君子择焉。”(49)该书对双峰思想的吸取远大于辨析,尤其是选择其关于《中庸》的章句划分而不取朱子说,至为明显(50)。另一同时期婺源学者程复心的《四书章图纂释》以750余图对《四书集注》加以图解,并引用诸家说对之加以纂释,该书在朝鲜理学界具有特别意义。程复心于此书中数次引用双峰说以矫正《集注》之解,显示出对双峰说的倚重(51)。此二位对双峰可谓“爱多于恨者”。 史伯璿著有《四书管窥》,专门矫正朱子后学对朱子思想之偏离,饶鲁当仁不让地成为该书批判的中心人物。因为该书以“驳”为主,故其大量引述了饶氏之说,保留了有关饶氏思想的珍贵资料。史伯璿认为饶氏“《四书》中所见不同于朱子者,十居其九”(52),分析饶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欲摆脱朱子学的束缚而自立门户,不肯亦步亦趋于朱子之后,期望与朱子并驾齐驱。再加上饶氏弟子逢迎饶氏意图,往往寻求《集注》瑕疵加以讨论,引导饶氏提出异于朱子之说,导致饶氏处于骑虎难下之境地。故无论自家之说是否有理,皆要千方百计提出不同于《集注》之说,以此表明自己高于朱子,能发《集注》所未发。尽管饶氏之内心未见得有如此高之自信,但为了博得弟子对自身之推崇,不得不强为己说。而门人又无是非辨别能力,凡饶氏之说皆辑录而传之,此实造成圣贤经传之厄害。史氏说: 不过双峰平日务欲自立门户,不肯为朱子下。故其门人承其风旨,往往皆逢其师之私心,以求《集注》之瑕疵,以启双峰之立异,双峰亦是骑虎之势,不肯默然自谓无说。所以虽无可说处,亦千方百计寻一异说,以高于朱子。其意亦未必自谓可以取信于来世,不过但得门人一时尊己过于朱子足矣。但其门人率皆无见,不能辨别。惟有翕然尊信,辑而录之,以传于后,遂为圣经贤传无穷之窒碍。(53) 史氏之评自然不乏情感成分,但仍然透露了某些事实,如饶氏对自身学术有着相当的自信,这种自信达到了近乎狂妄的地步。元代另一大儒陈栎言饶鲁晚年以圣人自居,并从心理上讽刺饶氏此种自我标榜已陷入精神失常。“晚年自号饶圣人,真心恙矣。”(54)其实,对自我加以高度肯定标榜,在心学学者中甚为普遍,此属于孟子所言“狂者气象”,不足为奇。而朱子学者气象多近于“狷者气象”,与之不契亦属正常。即此亦见出饶氏气质确有近乎心学之处。尽管史、陈二位对饶氏可谓“恨多于爱”(陈氏《四书发明》亦不乏取双峰说处),但饶氏在当时学界享有很高威望,受到弟子普遍推崇,则是可以肯定的。饶氏门人后学则对其发自内心的尊崇,如朱公迁《四书通旨》凡引饶氏说皆径称“饶子曰”。 史氏认为双峰《四书》与朱子相异者九,相同者一。就事实而言,饶氏对朱子还是以继承为主,诸多相异于朱子的想法,亦是顺朱子思想而做的进一步发挥。不过,在整个朱子学历史上,从义理上对《集注》提出大量反驳,以“破《集注》之说”为特色的朱门后学,饶鲁恐怕是首屈一指了。饶鲁对《集注》提出异议,并非出于妄自尊大之私心,而是根据自身为学工夫之受用、文本原意之理解两方面而做出的新的理解。他对《大学》“至善、格物、诚意”的诠释,对此有所表白。“鲁自少读朱子《大学》之书,于前三者反之于身,自觉未有亲切要约受用处。”(55)当然,对饶氏这样一位“欲成一家之言”的学者来说,他对《集注》的理解多据自身思想而发,并不以准确解释《集注》之说为目的,此亦是饶氏《四书》诠释不同于其他朱子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如他认为宰我所谓“夫子贤于尧舜”未见其所指,不可理会。故程子从事功的角度来论之,《集注》引程子事功说亦微含不满宰我之义。饶氏此说不确,其实,朱子《中庸章句序》还是特意采用宰我的夫子贤于尧舜说。饶氏之所以忽视《章句序》说,盖欲以程朱证成己说也。饶氏对《集注》批评,似乎愈到晚年愈加增多,这与当时朱子弟子相继去世,缺乏权威的学术状况不无关系。另外,对《集注》批评不满而欲矫其蔽的做法,饶鲁之师朱子之婿黄榦已开其端,饶鲁则进一步发扬、张大之(56)。总之,尽管饶鲁之著述未有专门流传至今者,但其思想在当时显然已甚为流行,其关于《四书》的论说大量被元明清学者采录于相关的《四书》著作中(亦见于明代科考范本《四书大全》),反映出饶氏思想持久之生命力。正如全祖望所言,双峰思想以“多不同于朱子”而引人注目。此不足为饶氏之短,恰恰显示出“后朱子学”理解、阐释朱子思想所体现的创造性与独特性,不可仅将之视为谨守门户的朱子附庸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