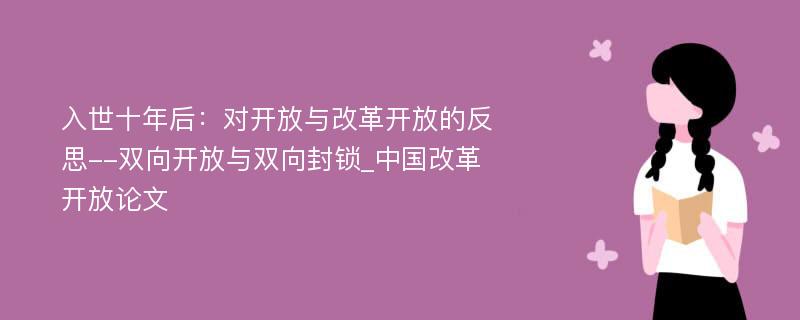
“入世”十年:再思开放与改革——双向开放,或者双向封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
这是对外部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在此前漫长的近现代历史中,中国通常是被坚船利炮轰开大门。
时间倒溯208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四,试图与中国从事贸易、制订贸易规则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乾隆避暑的热河,最终争论的焦点变成是否要行三跪九叩礼。至于国际贸易,是热衷于探讨朝觐的天朝人从未理解的概念。
2011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10年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4~5倍,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通过发展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实现了大范围的脱贫,完成了中低端制造业产业链条布局,对外开放成为大势所趋,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但在入世10周年时,从国际角度看,贸易摩擦并未减少,国内对于是否应加入WTO的争议未曾平息;从国内角度看,经济艰难转型,与对外开放并行的是在资源等领域的“国进民退”,中国未能在对外开放时积极稳健地推进面向民资、致力于建设市场化基础的对内开放。
激进而成功的对外开放
中国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从1978年以来,以开放促改革,以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发展从未动摇。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入世10年后,2011年1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上,商务部长陈德铭表示,中国将以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曾评价中国为世界贸易领域内“大象”的WTO总干事拉米,2006年在中国入世5周年之际,对中国入世后的作用给予了“A+”的打分。2011年,在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拉米再次给出“A+”的高分。
中国对外开放是激进而成功的,这说明对外开放不会摧毁中国经济,反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鲶鱼,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如在电信设备领域的华为与中兴通讯,如IT领域内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
国外商品拥入我国,加上我国逐步开放的服务市场,使本土经济面临着强烈的竞争,中国人了解了更多的国外品牌,创建了一大批本土品牌,洋品牌的溢价逐渐消失。但国外的一些品牌,如大宗消费品,如哈根达斯等,在中国仍作为高端品牌享受溢价,正是中国开放不足的反映。
对外资开放已经深入核心的金融资本领域。从2006年至今,外资银行在中国资产从0增长至超过1.3万亿元。
外资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对金融人才的激烈争夺,使金融行业的薪资增长了数十倍。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林清德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尤其是2006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之后,银行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更多的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新的外资银行来到中国,你会发现行业的发展速度已超出各机构人才的供应储备。因此,对渣打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在某地开设分行,在最早进入的时候,需要确保了解当地的经济情况,会招收当地的人才,因此,高管需要的是本地人,需要很了解当地政府、监管部门和当地社区的情况。
各种争论仍在继续,中外贸易博弈日趋激烈,正是中国开放之后的表现,中国正在学会运用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竞争。
为加入WTO,有关部门对当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政策措施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最全面、最彻底的一次清理。入世10年来,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工作从未间断,个别清理始终进行,相继废止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修改了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
从规则制订到经济分工,中国都在进入对外开放的深水区,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迟缓而痛苦的对内开放
然而,对内开放从未能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
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是正确的。对草根市场经济的歧视,导致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根基不稳,从而激发出广泛的民粹主义情绪。
在重要的资源性行业,对内资开放徒有其名,直到目前,在煤炭等领域驱逐民资的“国进民退”仍未受到清理,在石油等行业通过进口权、排产权等限制弱化民资地位。在入世之后,本应先对内开放的市场却先对外国投资敞开了大门,给外商的“国民待遇”大大优于民营企业,以致人们形象地称民营企业为“非国民待遇”。
此外,在重要的税收方面直接歧视内资。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此前外资所得税税率是15%,而内资企业的税率高达33%。吸引外资作为政绩之一,外资买单将难言坏账一盖了之等好处,让地方官员对外资趋之若鹜。
中国的金融机构成为对外开放而对内封锁的典型行业。2007年的数据显示,境外投资者通过低价入股国有银行狂赚1万亿,加上在香港低价上市的垄断型公司的利润,远超1万亿。
有一种自欺欺人的可笑观点:既然内部市场资源无法激活金融市场,外资又不是活雷锋,它们进来既获得了收益,使中国银行业开始了真正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改革,也使中国银行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更高的估值,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其实中国金融业从未真正向内部开放,例如村镇银行升级,民间机构必须让出大股东位置;再如小额贷款公司被严厉禁止吸储,最终以高利贷的畸形方式获得赢利权,因此在政策上与道德上受到双重打压。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起步,竭力争取在境外开疆拓土,设立或者通过并购的方式建立分支机构,也设立了理财中心为国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服务……但市场化并不只是并购游戏,也不是股权激励,其实质是一种竞争体制,所有的组织架构都围绕竞争而来,而体制内的银行恰恰缺乏对于竞争的本质理解,它们是天然的蓝筹股,可以获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它们在资本市场降生伊始就是股市的定海神针,可以理直气壮地首批获得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编者注)资格。
市场改革绝非一蹴而就,许多人都清楚的事实是,许多国有银行的董事会仍缺乏人事支配权,银行内部建立以业务为条线的事业部制等体制如一团乱麻。银行的改革路径在验证一条以开放促改革的路线能否成功,现在看来问题极大,只有对外开放而缺乏对内开放,无法改造内部的行政土壤,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环境,无法改变漠视境内投资者利益的不良文化。
另一个典型行业是资源行业。由于对民企的步步紧逼,民企在石油等行业步步撤退。1998年以前,民营企业在石油流通领域占到了85%,每年上缴利润高达人民币1000多亿元,就业总人数134万人。民营企业进入中国成品油分销领域的各个环节,不仅企业数量多,而且分布区域广。而到了2007年,中国民营石油批发企业由1998年的3340多家锐减到663家,民营加油站有2/5处于死亡边缘。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国内石油零售市场在2004年对外开放,国内石油批发市场在2007年对外开放。而从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八部门的“38号文”明确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的批发企业经营,其他企业、单位不得批发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重申两大集团的成品油批发专营权,并进一步赋予其零售专营权。2007年1月出台的《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3月的《成品油经营企业指导手册》,设立过高的门槛,实质上是在驱逐民营石油企业。
大型企业可以与国际石油巨头建立合资企业,康菲石油在渤海溢油事故后态度傲慢,可我们的民营油企至今仍在追问,生存还是死亡?
正因为民营企业生存艰难,要求给予民企生存空间的文件才层出不穷。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大对内开放,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提出“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结合起来”。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出台“非公经济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核心是给予民企国民待遇。让人遗憾的是,老36条未见效,只能推“新36条”,5年后,国务院再次颁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非公有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被形容为“将已经透明的玻璃窗擦得更亮”。有传闻称,细则将在2011年底出台。
中国存在“王爷经济”,官方垄断企业拥有天然优势;还存在“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本应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被各种费用等层层分割,国内市场物流费用甚至比远洋出口更高昂。
中国的市场化只完成了一小半,重要的资源行业、金融行业均未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根基,也未在用工制度上建立市场雇佣机制,更没有在资源配置上响应市场召唤。中国的市场化是表层的浮浅的市场化,从根本上不接内部市场化的地气。最接近民间市场化的温州草根经济,目前也处于生死关头。
对外开放而对内封锁,加上权贵经济推波助澜,使得国内民粹主义泛滥。
对西方经济的解读只剩下两个字:“阴谋”。甚至在中国本土也亟须的知识产权方面,也认为是西方对中国封锁技术的阴谋。这显然是受虐心态的表现,虐待之源来自内部的不平等。在不平等待遇下,民营企业家既痛恨权贵的不公,也痛恨外资的跋扈,由于无法向权贵发作,只能向外资开火。从2005年开始抨击外资并购,到近期抨击金融战——对内不开放,引发的民粹必然导致民粹对外资的痛恨,对外开放难以持久。
1978年,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允许草根市场存在,但2011年,仍然在探讨“国退民进”。1861年到1894年,中国开始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可以视为上一轮的国企参与世界竞争,最终,退回到民粹主义的彻底闭关锁国。
没有内部的市场经济,以偷懒的对外开放取代内部的艰难市场建设,必得市场软骨症。
洋务运动经历半个世纪,以血腥的战争方式失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空前的饥荒悲剧;而现在,是回到洋务时代,还是进入新一轮的市场草莽建设期,以真正的市场建设立下中国发展的百年根基?
希望不是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