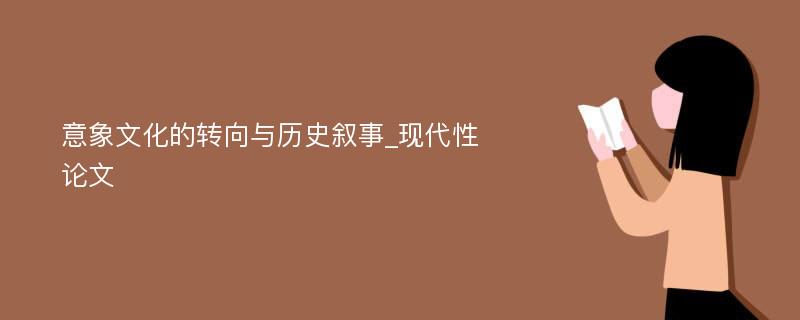
图像文化的转向与历史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像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图像、视觉文化与历史 本文意在探讨历史叙事中的图像使用,而海德格尔关于“图像”与“现代之本质”的预言式论断——《世界图像的时代》值得关注: 倘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是在追问世界图像。通过与中世纪的和古代的世界图像相区别,我们描绘出现代的世界图像。但是为什么在阐释一个历史性的时代之际,我们要来追问世界图像呢?莫非历史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图像,并且是这样,即每个时代都尽力谋求它的世界图像呢?或者,世界图像的追问就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并且仅仅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吗……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毋宁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①对海德格尔而言,世界图像“这一名称并不局限于宇宙、自然。历史也属于世界”②。换言之,世界图像与对历史沉思之关系,其核心重点在于“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同时“并且仅仅是现代的表象方式”。而这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用本文所关心的视角语言而言,亦即这一种可能的理解(世界)历史之认知模式,是现代之所以是现代的决定性“本质”。 那么,以图像来把握世界对理解世界是一种何等特色的认知景况? 说到图像一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关于某物的画像。据此,世界图像大约就是关于存有者整体的一幅画像了。但实际上,世界图像的意思要多得多。我们用世界图像一词意指世界本身,即存在者整体,恰如它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约束性的那样。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这个习语中可以听出的东西。这个习语要说的是:事情本身就像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去了解某物”意味着:把存在者本身如其所处情形那样摆在自身面前来,并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存有者。但是,对于图像的本质,我们还没有个决定性的规定。“我们对某事了如指掌”不仅意味着存有者根本上被摆到我们面前,还意味着存有者——在所有它所包含和它之中并存的一切东西中——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③因之,对于海德格尔所言:“倘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是在追问世界图像”,就可被解译为:沉思现代,就是以“对某事了如指掌”的方式来思考。但所谓对某事了如指掌,并不是指图像是外在经验世界的直接指涉符号,亦即“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换言之,图像符号并不是以“相似性”的认知概念被使用来当作一种认知、理解或沉思的媒材(媒介材料)。相反的,图像是一种媒介符号,亦即一种媒材,依海德格尔的观念而言,使用这种媒材“去了解某物”,是指挂戴着一种“对某事了如指掌”的认知态度来理解世界,但这种了如指掌态度是这样一种理解视角:“不仅意味着存有者根本上被摆到我们面前,还意味着存有者——在所有它所包含和它之中并存的一切东西中——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换言之,透过图像媒材而所要去被认识、理解的标的,是“一个系统”。用一种简单的说法,图像媒材应该指涉直观经验表征之外具有更丰富意义的内容,亦即图像媒材是以一种“表征模式/再现模式”的认知思维架构来被使用。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开头引述的海德格尔提问:“或者,世界图像的追问就是现代的表像方式,并且仅仅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吗?”是的,如果对图像的理解思维架构是以表征/再现模式来定位,而不是以一般常识概念中的“相似性模式”/“摹本”来定位使用图像媒材的理解模式,那么我们就更能清楚地理解海德格尔对自己提问的解答:“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然而,对本文而言,一个更重要追问是:为何以表征/再现模式的图像解读方式来理解世界,“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表征/再现模式的图像解读模式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就海德格尔而言,这具有“现代性”的解释作用。 海德格尔说道:“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④亦即以表征/再现/表象模式的图像解读模式来理解世界和人成为主体是种一体两面的关系,“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有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⑤。这要如何来理解呢?对海德尔格而言,理解的重心在于什么是表征/再现/表象?那就是“摆置到自身面前和向着自身而来的摆置”⑥。对图像而言,这是指对图像内容进行“摆置到自身面前和向着自身而来的摆置”,“摆置”意味着图像的内容不再被重视为是否是对外在经验世界对象的逼真摹本,换言之相似性概念不再成为内容形构的主导性考虑。相反如何“摆置”成为内容如何组构的思考主线,亦即表征/再现/表象是形构内容的主导视角。此刻,我们要再对前引“追问世界图像”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追问世界图像”,是指“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般的认知态度“去了解某物”,即“把存在者本身如其所处情形那样摆在自身面前来,并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存有者”。这种了解有两种特色:(一)“存在者如其所处情形那样”,(二)“如此这般被摆置”。但所谓的“存在者如其所处情形那样”的“如其所处”,并不是以相似性/摹本式的概念来决定是否为“如其所处”,而是指“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换言之,“为我们所了解”意指为创作者/接受者的主体性视角决定了什么是世界的“如其所处”。正是从人的主体性视角出发,“摆置”才能扮演图像内容形构过程重要的角色,也因之表征/再现/表象模式才能成为图像创作/接受的主导性理解视角。正是从人的主体性的视角出发,那么创作者/接受者的思维态度、认知架构或者说——请原谅作者在词穷状况下所选用这一充满争议的术语——意识形态,就必然对如何摆置具有影响力,因之被摆置而形就的图像就必然的沾染上了某种从主体意识形态出发的“系统性”。这正是前引海德格尔对于他所提出的图像式理解所下的“决定性规定”:“‘我们对某事了如指掌’不仅意味着存有者根本上被摆到我们面前,还意味着存有者——在所有它所包含和它之中并存的一切东西中——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 如果说,以“摆置”这种“方法论”上的特色来形构/理解图像是“标志着现代之本质”,那么对海德格尔而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人”也正是以“摆置”的方法论来形构世界、理解世界。这一现代性的过程: 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本身特别地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种地位当作被他采取的地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一种可能的发挥的基础。根本上,唯现在才有了诸如人的地位之类的东西。人把他必须如何对作为对象的存有者采取立场的方式递给到自身那里。于是开始了那种人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占据着人类能力的领域,把这个领域当作一个尺度区域和实行区域,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存有者整体的支配。回头来看,由这种事件所决定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新时代,而毋宁说,这个时代设立它自身,特别地把自己设立为新时代。成为新的,这乃是已经成为图像的世界所固有的特点。⑦因之,人对图像的摆置与人对世界的摆置,原来是相同的,都是从表征/再现/表象的认知立场出发,此即意味着“从自身而来把某物摆置到面前来,并把被摆置者确证为某个被摆置者。这种确证必然是一种计算,因为只有可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持续地是确定的。”⑧换言之,表征/再现/表象即是“对……的把捉和掌握”⑨;在这一过程中,“存有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表象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表象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由此,表象把万物纠集于如此这般的对象的统一体中。表象乃是心灵活动”⑩。 “表象”,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心灵活动,海德格尔追溯到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sum)中,cogitare就是在这一本质的和新的意义上被理解的”(11);“最早是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存有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了”(12)。职是之故,海德格尔强调:“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这里,‘图像’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在这种制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他能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有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有者”(13)。换言之,所谓世界图像的时代之所以可能是在这样的前提上:“只要存在者没有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解释,那么,世界也就不能进入图像中,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像。”(14)因之,前引海德格尔文中的一句关键性话:“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句话并不是一般所谓“视觉文化的转向”此种当代文化转型的某种哲学式的预见。所谓视觉文化转向此种文化转型可被描述为:“一个可以经验到的发展趋势是,当代文化的各个层面越来越倾向于高度的可视化。可视性和视觉理解及其解释已成为当化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活动的重要维度。”(15)或是“视像和控制技术时代,电子再生产时代,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开发了视觉类像和幻象的新形式”(16)。同时,前述海德格尔的那句引言,也不是在有关图像与文字这两种媒材的长期战争中,“图像压倒了文字”的某种哲学式脚注(17)。对海德格尔而言,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是一种阐释性的策略,意在表达我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时,存有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有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有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有者整体的本质的决断。存有者的存有是在存有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18)。对海德格尔而言,存有者以表象方式被看待的地方,不只是在图像中,历史亦然。 二、表象状态与历史“叙事” 表象状态,亦即以表征/再现/表象的认知活动立场来看待世界,这种认知活动的目的“是把每个存有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能够对存有者感到确实,也即确定”(19)。这才是现代的本质。对海德格尔而言,图像只是这种现代性本质的一种呈现,科学、企业活动以及历史同样以现代性本质进行运作,亦即以表象的方式来做出说明,以表象当作“证明的方法”(20)。 在现代性的概念下,海德格尔对于历史,有着一段相当长的论证说明: 但是,现代的研究实验不光是一种在程度上和规模上更为准确的观察,而是在一种精确的自然筹划范围和职能内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规律证明的方法。在历史学精神科学中与自然研究中的实验相当的是史料批判。“史料批判”这个名称在这里标志着整个史料发掘、清理、证实、评价、保存和阐释等工作。尽管以史料批判为根据的历史学说明并没有把事实归结为规律和法则。但它也没有局限于一种对事实的单纯报道。在历史学科学中同在自然科学一样,方法的目标乃是把持存因素表象出来,使历史成为对象。但历史只有当它已经过去时才可能是对象性的。过去之物中的持存因素,即历史学说明据以清算历史的东西,是可以比较的东西。在对所有一切东西的不断比较过程中,人们清算出明白易解的东西,并把它当作历史的基本轮廓证实和固定下来。历史学说明只能达到这一步,这乃是历史学研究所能触及的区域。独一无二的东西、离奇的东西、单纯的东西,质言之,历史中伟大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始终是不可说明的。历史学研究并没有否认历史中的伟大之物,而是把它说明为例外。在这种说明中,伟大之物是以惯常和平均之物为衡量尺度的。只要说明意味着:回溯到明白易解的东西,并且只要历史始终是研究,亦即是一种说明,那么,就不存在另一种历史学说明。因为作为研究的历史学是在一种可以说明和忽略的效果联系意义上来筹划过去,并且使之对象化,所以历史学要求史料批判作为它的对象化的工具。(21) 在这样的论说视角下,历史之所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等同于科学,在于“史料批判”等同于“科学实验”。对海德格尔而言,史料批判与科学实验的相提并论并不在于这两种方法于观察及规律证明的精准度上是等同的,而是在于和“自然科学一样,方法的目标乃是把持存因素表象出来,使历史成为对象”。因之,海德格尔对二者之间的等同性之所以可能的论述进而补充说道:“可以说,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在历史学的事后计算中,历史受到了摆置。自然和历史便成了说明性表象的对象。这种说明性表象计算着自然,估算着历史。”(22) 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性”的“表象状态”之所以得以成立需要两种条件,亦即海德格尔所言的“决定性规定”:(一)文本创作者是以“人成为主体”的地位,亦即“人本身特别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23),来“摆置”对象。(二)对象被摆置得是以“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换言之,对象的被摆置并非是任意性的,而是在某种“系统”约制下的摆置呈现,亦即对象的摆置是具有“体系性”的。“体系并不是指被给予之物的人工的、外在的编分和编排,而是在被表象之物本身中结构统一体”(24)。因之,“在世界成为图像之处,就有体系起着支配作用,而且不只是在思想中起支配作用”(25)。如果现代性历史作品,如海德格尔所言,是一种表象状态的文本,“目标乃是把持存因素表象出来,使历史成为对象”;那么现代性历史作品的写作过程:(一)创作者是以“人为主体”的地位来摆置历史对象,(二)对历史对象的摆置是“体系性的”而非“任意性的”。 以“人为主体”的作者,亦即作者“获得对存有者整体的支配”(26)之地位而写出的历史作品,如用文学/文本理论的术语来谈,那么这种历史作品是在“作者‘无所不知的’叙述情境(第三人称全知)”之下而被完成的(27)。这亦是巴赫金文本分类概念下的“独白型文本”:“其中的一切,都是在作者的包罗万象、全知全能的视野中观察到的,描绘出来的”(28);“主人公在作者的构思中是作为客体、作为对象出现的”(29)。这一文本模式中的作者是“无所不知、无法不能的处于神地位上的作者”(30),“一切都从服于他的唯我独‘存’”(31)。换言之,现代性表象状态的历史文品是“独白型文本”性格的文本。然而,独白型文本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历史作品,例如巴赫金的独白/对话文本理论是对小说的研究中而提出的,那么决定独白型作品中的“历史性”,亦即决定独白型作品中何者可以被定为历史作品,就有赖于海德格尔所言的第二项“决定性规定”:“体系性”。 “体系性”约束着“摆置”,换言之,“人为主体”的作者,在对经过“史料批判”后的史料对象进行“摆置”,这摆置过程并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在某种体系约束之内运作。正如同打篮球一样,看似球员自由意志下的满场跑,但却是在篮球规则的约束之内。换一个角度来说,篮球运动之所以是篮球运动,在于篮球规则这一“体系”,而不是那个篮球以及球员等这些“内容”。同样那个篮球及那些球员,如果不在篮球规则体系的约束下“打球”,就不是“一场篮球”。因之,一位球员,即一场篮球赛的“持存因素”,是以“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如用篮球为例来比喻,历史作品之所以是历史作品而不是其他作品,即一场球赛是篮球而不是排球,除了作品内容对象要是经过“史料批判”的历史“持存因素”之外,亦即球要是“篮球”、球员要是“篮球选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作品写作是在“叙事”这种“体系”约束之下进行的,亦即篮球赛是在篮球规则这种体系内运作的一样。在此,就本文的论述脉络而言,历史作品将被理解为作者处于“第三人称全知”状态下,在“叙事”、“体系”约束中,对经过“史料批判”的历史对象进行“摆置”过程的“独白型文本”作品。对于探讨历史写作与图像使用之间的关系而言,“叙事”这种“体系”在历史写作中到底发挥着什么的“约束力”影响了对“图像的摆置”,则是无法被回避的重点。 正如同篮球和排球不同的体系规则会决定球员如何来“摆置”“球”,“叙事文本”中体系规则同样会影响了如何摆置图像这种内容/写作元素以形构成叙事作品。在此,就要借助于文学/文本/叙事理论中对“叙事文本特质”的探讨,进一步论述历史写作中的图像使用。正如同保罗·利科(Paul Ricceur)在《历史与真理》中引述泰弗纳兹所言:“事实上,是事件本身把历史变成现实,支撑历史的合理性,给予历史其意义。”(32)换言之,历史之所以可以形成意义或是“有意义”的重要条件,在于事件的安排;亦即历史“叙事”“作为构成的统一,它把赌注压在与事件连接在一起的整体秩序上”(33)。对阿瑟·丹图(Arthur C.Danto)而言,对事件的“叙述描述”与“理论描述”更是区分了历史与科学,因之其在《叙述与认识》说道:“对于任何事件都有无数的描述,只有在某些描述下,事件才是对科学解释来说有效的事件,它们将描述与解释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与科学相关的描述与那些对史学来说重要的描述将是不一样的,因而,一个事件不可能是特定的描述下被规律所覆盖,在同样的描述之下它又被历史叙述所覆盖。”(34) 那么,对事件的叙述与历史作品的关系,换言之,历史作品的事件叙述是否有着特殊的思维框架来影响着一部叙事作品会被当作是历史作品,而不是其他文类作品。这思维框架有两个面向:(一)对“事件”进行“史料批判”,这自不待言。(二)如从一般而言的现代叙事理论而言,是对作品中“叙事时间”这一面向的强调。周建漳在《历史的哲学解释与逻辑分析》一文中言:“在形而上层面上,历史之为存在恰恰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历史存在的这一关系性特征称之为它的‘两间性’”,而“历史存在的两间性在语言中表现就是丹图所称的叙述句(Narrative sentences)”(35)。的确丹图强调“叙述句子”,“它们最一般的特征是,它们提及至少两个在时间上分开的事件”(36)。但赋予事件排列的“时间性”却仍必须面临“编年”与“历史”的差别,除非我们认为编年等同于历史。但显然丹图并不如此认为:“事实上,即便我们可能给出一个完美的描述,它也仍然不过是编年而已……因此,最好的编年史仍然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有的东西却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即便它告诉我们的细节远逊于完美的描述。真正的历史视编年为其热身活动,它自己的认知却是专注于赋予据信由编年史给出的史实以意义,或是分办出包合在其中的意义。”(37)对此,丹图将编年史称之为“朴直叙述”,而真正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叙述”(38)。从“有意义的叙述”这一角度而言,丹图说道:“在历史学家通过叙述手段描述过去所发生事情的意义上,由于叙述本身是一种组织事情的方式,从而‘跨越’了给定的事实,他们就涉足了某种可以称为‘给出阐释’的事情。”(39)那么所谓“有意义叙述”下的事件安排,如何可能的“给出阐释”?丹图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待解释项并不单单描述事件——所发生了的事情——而且还有变化”。他解释道: 例如,简单地将一辆车描述成带凹痕的已经隐含地涉及同一辆车早先尚未凹陷的状态。对于故事,我们要求其有开头,有中间,还有结尾。这样,解释就在于在变化的两个时间端点之间填进内容……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说明,我应该说就是一个解释,关于由开始到结束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解释,而开头与结尾都是待解释项的组成部分。(40)换言之,历史的叙事是对事件组织的方式在于针对某一主题相关的各种事件上进行具有“开始到结束”上变化的排列。这亦是后现代史学历史所认同的,例如海澄·怀特(Hayden White)即说道:“就编年纪事中众事件予以进一步编排,使之成为某一‘景象’或历程之分子,并藉众分子结构一首尾分明之过程,于是故事生焉。”(41)因之历史文本若要能有解释的发生,亦即意义阐释的给出,有一根本性的基本前提:事件的排列必须是具有时间维度的,亦即“两间性”。历史作品创作者的最重要的写作技艺就在于创造事件安排上的“时间性”,这时间性赋予了历史作品本身具有“给出阐释”的基本文本特质;因之,历史作品如有优劣之分,正在于作者如何拿捏各种事件“两间性”之间的处置/摆置,亦即作者透过事件的安排以形就“时间性”上的创造性。 在上述的理解之下,历史作品的叙事特色必须是:(一)“历时性”的,因为事件的安排必须具有开始至结束的“时间性”的维度,意义的阐释才能给出。这里对历史作品历时性的强调在于与“共时性”这一概念对比,因为图像的意义给出是“共时性的”,后文将详论。(二)历史性作品是作者对事件进行摆置从而在作品中开拓出意义可被给出的时间性维度,“在丹图看来,编年与历史的真正区别……前者属于当事人视野下的当下描述,而后者则是将当下事件的未来后果包括在自己视野中的叙述”(42)。“在自己视野中的叙述”,这正是前文所谈巴赫金文本理论概念下的“独白型文本”。因之,“有意义的”历史作品是在编年朴直叙事的限制之下,以“历时性”的手法对事件进行“摆置”的“独白型”作品。“独白型”这一概念在此处的强调,乃在于独白型文本的意义给出过程,其意义给出的模式在于“它进入我们的话语意识,是紧密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方只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43)。这种整体性的、宏大叙述性的、大写的、同一性的、中心性的意义给出模式,正是所谓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史学”批判上的火力弹着点;而所谓的后现代史学所追求的历史叙事,所强调的另一种说故事的方法,并不是挑战传统史学的编年朴直性与历史性,而是在反问:是否有一种具有编年朴直性与历时性的“非独白型”历史作品,如同凯特·詹京斯所言:“一种会产生跟纪事/编年史非常不一样意义的叙事”?(44)换言之,如依后现代“叙事转向”史学取径的另一问法是(45):放弃第三人称全称写作叙事情境下而写出的“有意义的”历史作品,将会是一种何等的文本风貌? 在如上的铺陈之后,历史叙事与图像使用之间的关系,其所紧扣之处就在于共时性意义给出模式的图像与历时性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非独白型”历史作品在图像使用上所可能开出的新视野。 三、共时性图像媒材与历史叙事 图像是“视觉事物”,从晚近“视觉研究”这一学术场域而言,图像“它们用视觉语言转述世界。但转述本身绝非毫无心计。影像从来就不是观看世界的透明窗户”(46)。本文对这一认知立场是肯定的,因之认同约翰·博格(John Berger)在《观看之道》一书中所言:“我们不只看一个东西:我们总是在看东西和我们的关系。”(47)这正如同本文是引用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的时代》之讨论为开始,图像对本文的论述核心意义而言,“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这个习语中可以听出的东西”。亦即图像是以表征/再现/表象的意义呈现模式,“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以表征/再现/表象为意义的呈现模式,亦即“摹本”不是最重要的图像创作依据,那么创作者对图像的内容对象“摆置”就成为重要的图像文本形成环节。当然,创作者对图像内容对象的摆置亦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某种“系统性”的约束之下,换言之是在某种文本结构体系下才能形成的意义给出。对历史作品而言,如果这体系性是“时间性的”、是“历时性”,那么对图像作品而言,这体系性是“空间性的”、是“共时性的”。 就我们对图像观看的切身经验而言,面对图像,我们往往是对图像内容物的摆置位置,亦即空间关系进行理解而给出对图像的意义,此即“空间性”,而这一种理解是当下整体成形的,而非是在一种“首-尾”式的时间运作中而有的意义给出,因之是“共时性的”。正如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言,绘画是一种空间聚敛,“图像是与感觉相关的可感形式……感觉就是直接传达的东西,它回避讲故事的迂回和乏味”(48)。因之,当要去论及历史写作与图像使用的关系,就本质而言其实是涉及了时间/历史性体系与空间/共时性体系两者之间的安排关系。就传统有意义的历史叙事而言,如果说事件在时间维度上而形成的变化是历史意义被给出的基础,那“历时性”就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因之在一旦在历史叙事中必须动用到图像这种媒材,那图像就不得不被视之为“以文字描绘的事件”的“替代物”或是“补充物”。换言之,传统历史中的事件如果是以纯文本描绘出来,那么一旦图像在手,在历史叙事的过程,图像就会成为文字的补充者,此即一般常见的“插图式”的图文表现,透过图像让文字事件有更多的细节。另一种更为极端的图像使用,是以“单纯图像”来代替文字事件,这即是纪录片/电影式的历史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影像式的文本若要有“历史性”,那么影片中的图像变动,即画面的变动,也必须创作出在相同主题下的具有“首-尾”式时间维度的变化。图像与历史写作之间的关系一旦被如此确定,再来的问题只是图像的(一)“史料批判”,(二)“共时性”诠释。 图像的史料批判,正文同传统文字的史料批判一般,是有关“真伪考定”的问题,在一般历史学科的训练上这是强项,在此不再深论。对本文的论述取径有更大影响者,在于“共时性”诠释。图像的“共时性”诠释是指:如果对图像的理解是一种对内容整体性的感觉,而“感觉的特点就是包含层面的构成性差异和构成性领域的多元性……因此就有了感觉的不可简约的综合性”(49)。那么,对图像的“共时性理解”往往是“更多于”图像可视对象的内容。如果我们以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有意味的形式”之概念来谈的话,“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看作艺术家、宗教、哲学,甚至个文明的‘文献’”(50)。换言之,一件图像作品,如果透过适当的理论框架来解读,例如卡西尔的解读框架是“有意味的形式”,那么对图像的“感觉式理解/共时性理解”就可以透显出更丰富的意义阐释。 当然,卡西卡的所谈的“图像”是指高级绘画“艺术作品”,但在后现代/文本/视觉学科的理论推演之下,可以具有“文献”性的图像,已由“美学”概念下的“艺术作品”扩展到“视觉文化”概念下的“文化物品”(51)。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可视物”,从“广告形象到影视节目,从印刷物图像到服饰、美容、建筑、城市形象……X光透视、CT、核磁共振图像”等等(52),都进入了在学术研究操作上文献/文本的视野之内。这一“图像史料”范围的扩展,是相应于解读图像理论框架的推陈出新,而图像解读框架的快速变化,则是来自于所谓的后现代/解构叙事理论的推展。正如同Currie所言:“叙事学研究范围的大规模拓展和研究对象的日益包罗万象,的确是该领域新变化的显著要点。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引用叙事例证有电影、广告、电视和报纸新闻、神话、绘画、唱歌、喜剧性连环画、逸闻、笑话、假日里的小故事、逸闻趣事,等等”(53)。同时Currie强调:“解构主义这个术语可以当作一把伞,在它的庇护之下,叙事学中很多最重要的变化都可以描述,尤其是便于描述那些脱离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化轨迹的新变化”(54)。而解构主义对于一般而言科学化的结构主义所带来最大的冲击和改变则在于:“解构主义允许将历史观再次引入叙事学,此举为叙事学走向更为政治化的批评起到了桥梁作用。”(55) 如果说,形式/结构主义下的文学/文本理论,强调的是作品/文本内部独立自主的规律,“排除了文学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56),从而与作品外部的社会、历史环境划清了界线,那么历史学科与之保持一定学术距离是在可解理的范围之内。相反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解读架构,则对历史学产生了影响。Mccallum说道:“大多数历史学史家仍然觉得这门学科大体上还是经验性和实用性的,完全不信任抽象和理论……然而,受到刺激的历史理论家正着手抵制由于一些历史学家不愿辩护自己的研究方法而造成的历史边缘化。最近的历史著述理论化的重点有三:叙事策略、修辞技能与理论依据,其中,叙事策略显然与后现代小说及其理论的关注点有共同之处”(57)。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应是很好的例子。怀特在受访时面对提问:“从《元史学》到《形式的内容》,你有什么演变吗?可以看到其中有大的变化。”他的回答是:“我积极地应对后结构主义。”(58) 一般而言,历史学科往往会将解构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怀疑史料,怀疑语言,怀疑叙述,怀疑史学家的真诚”(59),认为“这一认识,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如果历史学家能对史料作随意的解释,那么历史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60)本文无意于此深究“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目的论”关系(61),本文可以确定的是后现代文本解释框架能够“解放”史料的范围:“诸如建筑、艺术、电视、电影、时尚、流行音乐、休闲、消费、娱乐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都是脱离正统之后,真正能够了解文化原质的素材”(62)。当然,后现代解放史料的威力也扩及到了“图像”或是“可视文化物品”,各式各样和后现代/解构主义有着亲、疏学术血脉关系的图像解读框架不断涌现,企图解读出图像在直观/感觉的背后所隐藏的更多意义,或是引申出图像所含摄的社会性、历史性解读。 于是可以看到各式图像或视觉文化的导读类书籍,介绍各种图像/视觉文化物的解读框架就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Howells的《视觉文化》一书就分为二大部分:理论,媒介。而理论部分就有:图像学、形式、艺术史、意识形态、符号学、解释学,每一个章节就是一种图像的解读框架。Howells说道:“与简单的看法相反,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思考我们是如何观看以及我们是否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观看,进入图像世界,我们需要带上结构性的知识、方法以及明确的自我意识。”(63)Rose的《视觉研究导论》,则从内容分析一路推进为:符号学、精神分析、论述分析I、论述分析II、其他方法、综合方法(64)。以上述两书为例的话,可以看到的是图像研究的视角重心的转移是从主题/内容、形式/结构到政治/意识形态。这一研究图像转向,“应该清楚的是,它不是回归到天真的模仿、拷贝或是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反倒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65)。对历史学科而言,可以说是从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图像学研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艺术的故事》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词与物》。此亦即是从帕诺夫斯基的“从百合花象征着玛利亚的纯洁”、贡布里希的“追求新思想的进程”(66),到福柯所谈的委拉斯开兹的名画《宫中侍女》。福柯“认为表象只是一种相似性的人也消失了”(67)。 然而一旦拉回到有意义的历史叙事这一面向,那么共时性意义呈现模式的图像在透过的“理论框架”的解读之后,容或许可以带出对图像“感觉”之外更丰富的意含,甚至这些意含可以具有强烈社会、历史、政治、意义形态上的面向,但是有更多意含的图像终究必须被放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中,因为只有在历时性的叙事结构下,文本才会具有“历史性”,才会成为有意义的历史作品。在历时性/时间性的体系约束之下,事件要能有“首-尾”两间性上的安排,才能从事件的变化中解读出“历史意义”。因之,在历史写件中使用图像,那么被当作事件材料/史料使用的图像必须要能有时间维度上变化,换言之必须是有相同主题关系上的至少二张图像,同时二张图像必须是在视觉观看上有变化的并有着“首-尾”式的安排,如此图像才能在历史叙事的文本中体系中成为“可用”的材料,不管这图像是用上何种框架来解读的。 从实际的历史写作过程而言,要收集到具有相同主题关联性,同时又有时间维度上视觉观看面向而言产生变化的二张以上图像,并不容易。因之,可以看到就构成历史叙事的“事件元素”而言,一般说来在写作过程终究是使用文字的描述变化来构成具有两间性的事件变化,换言之是用文字来构成“事件”,图像只是文字的配角,是“插图”。不管图像可以诠释出什么,就“正规”的、“有意义的”历史作品而言,图像终究必须附搭于文字,图像必须要依靠文字才能转化成可进入历史叙事而被“摆置”的事件。虽然,各式图像理论可以让图像所附搭的文字去形成更具有意识形态解码上的意义丰富度,但构成史叙事的“媒材”终究是文字,而不是图像。图像的这种下场,是“目前正规”历史叙事体系下的必然结局,这是历史文本的结构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叙事文本体系下,唯一打破图像附庸于文字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影像史学,靠着影像在时间运动中的变化产生历史意义,但此时,文字则成为图像的搭附媒材了。那么,图像与历史的关系,还能有什么样的文本想象吗? 四、对话式历史作品与图像 有一本研究“小说”的书,书名《历史话语的挑战者》,副标题是“库切四部开放性与对话性的小说研究”。库切(Johm Maxwell Coetzee)是南非作家,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奖。书的作者段枫强调,库切当然清楚小说不是历史,“小说话语的虚构性质使得故事就是故事,不是历史”,但是小说家库切写出的文学作品为何是要对“历史话语”挑战呢?对库切而言,所谓的历史话语/历史作品只是一种书写模式的象征性说法,历史话语代表着一种“封闭式、独白式的书写模式”。库切的小说所要挑战的足所谓“历史附庸者”式的小说,亦即是遵循传统现实主义再现观的小说,“他希望创作的是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再现手法的另外一种小说形式,一种具有自身独特发展规则、能够揭示出历史书写独白式的小说形式”。“库切在考察历史独白性书写模式的同时,也一直尝试在写作实践中,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和形式结构发展出小说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则,用开放性、对话性的小说话语对抗历史话语独白式的封闭结构”(68)。换言之,库切要挑战“历史话语”,其所要挑战者是某种文本写作模式,这种写作模式一般而言是“历史作品”的写作模式所代表者,是独白的、独调的、封闭的写作模式,而库切恰恰是要用开放的、对话的写作模式来与之对抗。 借由库切对“历史话语”的批评,要反问的是:一种开放性、对话性的历史作品是有可能的吗?如果前文对于独白式V.S.对话式所谈的种种,是关注于文本“形式”的问题,而不是“内容”的问题,那么只要把小说的“虚构内容”以经过史料批判过的“历史内容”来置换,那么就理论而论,如果有着开放性、对话性的小说,就理应能形成开放性、对话性的历史作品。要往下追问的是:什么是“独白性”写作模式,而什么又是“对话性”写作模式?而不同的写作模式对于图像这种媒材是否有不同的摆置思考?在文学/文本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独白性对比于对话性小说文本模式的提出,是巴赫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亦是库切如何挑战历史话语的理论解析之依据;本文亦依巴赫金的对话性/复调性文本理论来探究对话性历史作品的可能,以及此种作品与图像间的写作关系。 对巴赫金而言,独白型小说“是从荷马开始的写作方法,即由作者描绘他笔下的人物:‘他是谁’?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外貌、出身门第、脾气秉性,是由作者独白,在人物语言的引号外面来描写的”(69)。“独白型小说取决于作者意识对描写对象的单方面规定。这里只有一个声音,即作者在说话,一切主人公的语言、心理和行为都被纳入作者的意识,都在作者全能全知的观点中得到外来说明”(70)。正如巴赫金以托尔斯泰小说《主人与帮工》为例分析道:“托尔斯泰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独白世界,主人公的议论被嵌入作者描绘他的语言的牢固框架内。连主人公的最终见解,也是以他人(即作者)议论作为外壳表现出来的。”(71)但如果以叙事理论中的作者及叙事者有所分野的角度来看待叙事作品(72),上述概念下的独白型叙事还可以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文学理论来看,真实作者是不同于叙事者,两者不可“混为一谈”(73)。“真实作者是创作或写作叙事作品的人,叙述者则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高老头》中的叙述者是巴尔扎克虚构出来的对‘伏盖公寓’和高老头的家世十分了解的人,绝不等于巴尔扎克”(74)。上述论说的作者、叙事者两者分野的概念一旦引用到上文第一、二节所论述的历史叙事作品特质,那么历史作品即是作者等同于叙事者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情境下的作品,换言之,经过“史料批判”的历史事件以“两间性”的方式被摆置从而创造出可被解读的“历史意义”,是在作者等同于叙事者这种“全知的零视角”的叙事角度来完成。 那么,对“历史话语”的挑战过程中,“作者等同于叙事者的第三全知叙述视角”就是值得发动攻击的防线。段枫在库切的研究中指出,为了“放弃独调叙述的声音,为小说除掉历史的外衣”,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是库切前、中期曾大量使用的写作策略,“发掘第一人称叙述除逼真性假象之外的其他优势”。然而,库切在其小说写作的后期,写作的策略又回到了第三人称叙事手法。如果从一般叙事而言,在强调所谓作品客观真实的不可靠性时,往往局限于第一人称叙事作品的研究,那么对历史话语进行挑战的库切选用第一人称的写作策略是可理解的;但为何在其写作后期他又转往第三人称的写作策略呢?库切放弃或改变了对历史话语的挑战立场了吗?非也!在后期第三人称的写作策略中,库切的小说发展出透过巴赫金理论可以观察出来的“复调性、对话性”小说形式,“并以此向历史话语独白式、封闭式的书写模式提出了挑战”(75)。从上述库切的挑战历程来看,对目前的历史学科而言,如果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是难以被认同为历史作品的写作策略,那么以第三人称写作策略下的复调式、对话式文本形式历史作品,就会是在相同于历史作品第三人称写作策略下,从“文本形式”的面向上对“正规”历史文本进行挑战。 巴赫金的“复调”、“对话”文学理论是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研究中发展而成,其理论发展是从“作者与主人公”这一视角出发(76),这大约是相同于现代叙事理论下从“作者与叙事者”的角度进行探讨。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对话概念在于确认了一种“哥白尼式”的关于描绘主人公的文本呈现形式(77)。在复调小说中,“主人公议论具有特殊独立性;它似乎与作者议论平起平坐……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复调’(多声法)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存在方式’”(78)。巴赫金谈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恰似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他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声的奴隶(如宙斯的创造),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比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见。”(79)自由的主人公这一观点往往易于引起误解,如董小英所举例的,“好像神笔马良画了一个大力士,他从墙上跑下来,把马良的神笔夺走了”(80)。 对巴赫金而言,主人公是由作者写出来的没有争议,但主人公的自由又是如何可能呢?这即是“复调”这种文本形式的“厉害之处”,亦即透过复调/对话式的形式展现来表达“主人公的自由”。复调原理,“是靠作品的结构使每一个人物的故事成为不同的声音,构成相互对立、互为补充的复调形式”(81);同时“这些声音都是具有平等的权利”(82)。巴赫金谈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的主要之点,恰恰在于不同意识之间发生的事,也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因之,“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透过这种形式,作者把“自由”给了主人公,“主人公的议论并不会从作者的构思中消逝,而仅仅是从独白型作者的视野中消失。而打破这种视野,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意所在”。复调/对话文本“结构的原则各处同是一个……他要表现的,恰恰是一个主题如何通过许多不同声音来展示;这可以称作主题的根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多声部和不协调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重要的,也正是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83)。 在此,我们看到了“配置”这一概念,这关系到文章一开头所引海德格尔借由世界图像所谈及的“摆置”概念。然而,巴赫金的“配置”和海德格尔的“摆置”却是两种异质性的概念。摆置对海德格尔而言意味着“从自身而来把某物摆置到面前来,并把被摆置者确证为某个被摆置者。这种确证必然是一种计算,因为只有可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持续地是确定的”(84)。在这过程,“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他能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有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有者”(85)。从这种人的地位出发,“在历史学的事后计算中,历史受到了摆置。自然和历史便成了说明性表象的对象。这种说明性表象计算着自然,估算着历史”(86)。从这种人的地位出发来写作历史,正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这样的历史作品也正是不折不扣的是独白型历史文本。然而,巴赫金的“配置”概念,却可以是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下,创造出一种复调性、对话性“相互关系”的文本,打破“独白型作者的视野”。在这种巴赫金式的配置中,意义的呈现模式是“一个主题如何通过许多不同声音来展示”,这些声音也处于“地位平等的意识”状态。这种配置关系,巴赫金强调是一种“对话性”的关系,“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一重特殊形式”(87)。 然而,文本中对话性配置关系下所形成复调式文本为何就能打破“独白型”的文本呢?对巴赫金而言,独白型话语是一种“专制的话语”,“它是完整结束了的话语,是没有歧解的话语;它的涵义用它的字面已足以表达,这涵义变得凝滞而无发展。专制的话语要求我们无条件地接受,绝不可以随意地掌握,不可把它与自己的话语同化”(88)。这种对意义防卫严整式的话语,要如何破解呢?巴赫金谈道: 独白语境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遭到削弱或破坏:两种同样直接指述事物的表述,汇合到了一起。两种同样直接指述事物的语言,如果并列一起,出现在同一个语境之中,相互间不可能不产生对话关系,不管它们是互相印证,互相补充,还是反之互相矛盾,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对话关系(如问答关系)。针对同一主题而发的两种平等的话语,只要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应对。两个已经表现出来的意思,不会像两件东西一样各自单独放着,两者一定会有内在的接触,也就是说会发生意义上的联系。(89)换言之,破解的“招数”在于“针对同一主题而发的两种平等的话语”汇合到了一起。这正是对话性的意义展现形态,也正是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所以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90)。 那么陀氏的复论型小说形式,有可能成为一种历史作品的形式吗?从叙事文本理论而言,陀氏小说和有意义的历史作品在形式面向上基本是相同的,都是对事件进行两间性的描绘,但描绘事件的方法在根本概念上是不同的,杜氏小说是以“配置”的方法来形构事件,而历史作品一般而言都是以海德格尔“摆置”的方法来形构事件。就理论而言,如果以陀氏作品配置概念来形构两间性事件,而事件内容都是经过“史料批判”的,那么有意义的复调历史作品就是可能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再一个问题是,历史学科有可能接受充满“对话”性格的历史作品吗?这是历史学科“职业化/专业化”自我定位/设限的问题,而不是历史意义非得要以特定文本形式来被呈现的问题。 对话式意义呈现模式当然不同于独白式的如此为“紧密而不可分割的整体”(91),相反的对话式的意义呈现模式,“它的意义结构是开放而没有完成的”(92)。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话式的意义模式是“后现代性”的,亦即“思想在文本中循环、流动、打漩、汇集、跳跃……作品的‘完整性’也变成海市蜃楼”(93),而是正如同维根斯坦所揭示的,“被我们称之为涵意的东西只有在语言符号的使用场景中才能得到解释,而这样的场景是多元的”(94)。因之,巴赫金强调对话性的涵义展现是“辩证的”,是“一种辩证的综合”(95)下“积极的理解”(96),正如同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所言,把散布在一个时间序列或空间场内的诸因素“综合”起来(97)。 如果对话式的历史作品是一种“可思议”的历史文本,那么图像与历史写作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另一种可能。如前所述,在传统的历史文本结构下,事件要能有“首-尾”两间性上的安排,才能从事件的变化中解读出“历史意义”,但对事件的描绘往往是以某一媒材为主导。如果是以文字为主导,那图像则沦为插图的辅助性角色;如果是影视史学,则文字只是帮衬。但若从对话性文本的角度而言,意义的产生模式是:“针对同一主题而发的两种平等的话语,只要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应对”。换言之,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可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遇在一起,从而产生相互应对的对话式意义呈现模式;此亦即对事件的描绘除了以文为主导或以图为主导外,图文平等关系下的并置,是另一种可以描绘事作的可能写作形式。至少就理论上的推演是如此。 事实上,图文平等关系下的写作模式一直是有被探讨的,这种写作模式被称之为“多重形构(multimodality)”(98)。Kress和Leeuwen就图、文关系指出:“图不是只当作文字内容的插图,也不只是‘创意雕琢’;这些图是‘多重模式化’所构成内容的一部分,是各个模式间的符号语言交互作用,其中文字与视觉扮演了定义明确且同样重要的角色。”(99)而多重形构文本所扮演的多重性,Kree和Leeuwen谈道:“多重形构不论是在教育界、语言学理论或是一般人的共识上一直被严重忽略。在现今这个‘多媒体’时代,顿时被再次察觉。”(100)Leeuwen为强调这种写作形式的重要性,在Visual Studies期刊中还特别以“新写作形式”来称呼之(101)。 然而,多重形构文本事实上并没有如此的被忽略,只是一直未被“高雅的”知识圈所认可为“合法的”知识呈现形式。例如在儿童图画书领域,这种文本形式一直是被关注的主题重心。正如同Lewis于Reading contemporary picturebooks一书中所言:图像与文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distinct media)在图画书中交织在一起而创造出单一文体(single text),而不是以文字为主再佐以图像为插画(102)。另一种我们熟悉的多重形构文本则是漫画书。要能理解漫画的内容,必须同时依靠文字及图像二种媒材“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互文性,解读内容才有可能(103);文字与图像二者并没有那一样是占据着“优势主导”的地位。换言之,图、文以平等关系来构成对话/复调式叙事文本,就历史学科而言,并没有文本理论上的障碍,也并非没有具体存在的文本可供参考。事实上,唯一的障碍恐怕是历史学科是否可以认同:“看起来像是”儿童图画书或是漫画书的历史作品,也可以是“正规的”、“严肃的”甚至是“学术的”历史作品。历史学科能否跨越这一学术领域的障碍,影响着在数字时代中历史叙事是否能对“数字文本”进行使用;这是因为“只有当文字和图像位居同等重要的位置时,互联网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力量”(104)。 收稿日期:2014-02-20 注释: ①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76-78页。 ②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6页。 ③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6-77页。 ④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0页。 ⑤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0页。 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0页。 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9-80页。 ⑧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95页。 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95页。 ⑩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95页。 (11)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95页。 (12)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5页。 (13)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2页。 (14)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7页。 (15)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6)Mitchell,W.J.T.:《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7)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第8页。 (18)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7页。 (1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5页。 (20)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1页。 (21)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1页。 (22)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4页。 (23)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9页。 (24)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7-88页。 (25)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8页。 (26)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0页。 (27)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28)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29)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5页。 (30)北冈诚思:《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31)北冈诚思:《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第57页。 (32)保罗·利科(Paul Ricceur):《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33)保罗·利科(Paul Ricceur):《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第24页。 (34)阿瑟·丹图(Arthur C.Danto):《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xii页。 (35)周建漳:《历史的哲学理解与逻辑分析》,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译者序,第3页。 (36)阿瑟·丹图(Artbur C.Danto):《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第143页。 (37)阿瑟·丹图(Arthur C.Danto):《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第147页。 (38)阿瑟·丹图(Arthur C.Danto):《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第147页。 (39)阿瑟·丹图(Arthur C.Danto):《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第175页。 (40)阿瑟·丹图(Arthur C.Danto):《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第290页。 (41)海澄·怀特(Hayden White):《史元》(上),刘世安译,台北:麦田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7页。 (42)周建漳:《历史的哲学理解与逻辑分析》,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译者序,第5页。 (43)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44)詹京斯(Keith Jenkins):《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41页。 (45)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9年,第199页。 (46)Rose,G.:《视觉研究导论》,王国强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7页。 (47)Berger,J.,Ways of Seeing,London:British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and Penguin,1972,p.47. (48)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绘画与感觉》,陈永国译,陈永国主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49)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绘画与感觉》,陈永国译,陈永国主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第227页。 (50)曹意强:《图像与语言的转向——后形式主义、图像学与符号学》,曹意强主编:《艺术史的视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424页。 (51)Winters,E.:《美学与视觉文化》,李本正译,C.Eck & E.Winters主编:《视觉的探讨》,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 (52)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第6页 (53)Currie,M.:《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54)Currie,M.:《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第4页。 (55)Currie,M.:《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第6页。 (56)Currie,M.:《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第9页。 (57)Mccallum,p.:《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蓝仁哲、韩启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58)Domanska,E.:《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59)杨耕、张立:《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总序)》,R.M.Burns & H.R.Pickard主编:《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张羽佳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序页第16页。 (60)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25页。 (61)Eagleton,T.:《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周宪、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5页。 (62)林载爵:《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叙述方式——后殖民论述与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张玉法、林能士主编:《近代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1997年,第11页。 (63)Howells,R.:《视觉文化》,葛红兵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64)Rose,G.:《视觉研究导论》,王国强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65)Mitchell,W.J.T.:《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第7页。 (66)Howells,R.:《视觉文化》,葛红兵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67)福柯(Michel Foucault):《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1页。 (68)段枫:《历史话语的挑战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0、22、16页。 (69)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4页。 (70)张杰:《编选者序》,张杰主编:《巴赫金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8页。 (71)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72页。 (72)Bal,M.:《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73)巴特(Roland Barthes):《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张寅德主编:《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74)胡亚敏:《叙事学》,第36-37页。 (75)段枫:《历史话语的挑战者》,第104、105、106页。 (76)Hirschkop,K.,Mikhail Bakhtin:An Aesthetic for Democra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0-108. (77)北冈诚思:《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第54页。 (78)北冈诚思:《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第62页。 (79)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4页。 (80)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5页。 (81)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第185页。 (82)Vice,S.,Introducing Bakhti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112. (83)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47-48页、第4、85、354页。 (84)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95页。 (85)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82页。 (86)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孙周兴译,第74页。 (87)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961年笔记》,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 (88)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127页。 (89)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246页。 (90)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5页。 (91)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127页。 (92)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130页。 (93)Wellmer,A.:《论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4页。 (94)Wellmer,A.:《论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第89页。 (95)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华昶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96)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59页。 (97)怀特(Hayden White):《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98)Kress,G.,& Leeuwen,T.V.:《解读影像: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原理》,桑尼译,台北:亚太图书公司,1999年。 (99)Kress,G.,& Leeuwen,T.V.:《解读影像: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原理》,桑尼译,第160页。 (100)Kress,G.,& Leeuwen,T.V.:《解读影像:视觉传达设计的基本原理》,桑尼译,第60页。 (101)Leeuwen,T.V.,"New Forms of Writing,New Visual Competence",Visual Studies,Vol.23,No.2,2008,pp.130-135. (102)Lewis,D.,Reading Contemporary Picturebooks:Picturing Text,London:Routledge,2001,p.3. (103)Groensteen,T.,The System of Comics,Mississippi: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7. (104)Lester,P.M.:《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霍文利等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