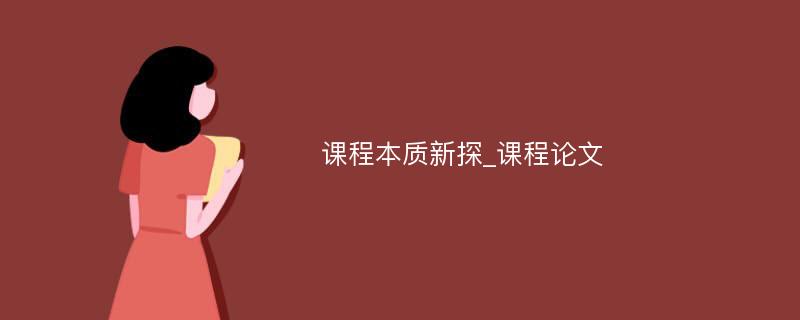
课程本质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翻开教育史,“课程本质”的理论探讨发端于19世纪末。在那以前,人们世代相因的唯一观念或理论为:教材就是课程,教科书就是课程。[1]这可以称为课程本质的“教材说”。进步教育萌动之初,一些人激昂地对传统教育的这种课程观进行了严厉批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儿童中心课程”,从而引发了进步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就课程本质的一场激烈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端。在这样的背景里,杜威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写出了课程论史上的开山之作《儿童与课程》。他在分析批判了争论双方的偏颇之后指出:儿童和课程仅仅是表明一个过程的两端,教学是从儿童目前的经验进展到有组织体系的真理,即我们称之为学科所代表的经验,因而课程的实质就是经验[2]。这可以称为课程本质的“经验说”。
课程本质的“经验说”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辉煌之后,伴随着进步教育运动的衰落而被欧美教育理论界所质疑。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课程本质进行了探讨,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据彼得·奥利瓦的考察,对课程本质的阐释,典型说法有13种之多:给课程下的定义,有代表性的就有9种之多[3]。最近出版《国际课程百科全书》也列出了学者们对课程下的9种不同定义[4]。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不应该深入地去探讨课程定义问题呢?美国学者蔡斯的回答是否定性的,他格外看重多种定义并存的必然性,认为:“寻求某种正确的课程定义并不是很有创造性的事业,学者们可更多地化时间去处理学校现实情境中课程编制的实际问题。”[5]我国有些学者十分赞同蔡斯的这一看法和态度。笔者的回答则与之相反。课程定义问题实际就是课程本质问题,多种定义并存表明人们对课程本质的认识尚比较肤浅,还有待深化。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界也一直在不断地研究“课程是什么”的问题[6];目前我国课程改革的日益深入,则客观地迫切地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课程是什么”的问题,以求进一步地揭示课程的本质,从而满足课程实践和课程理论发展的需要。
决定课程本质的客观基础是课程内容的特性,而课程内容无疑又是来源于文化,要深刻地探明课程的本质,就必须深入地探明课程内容的特性和文化的内核。因此,本文拟从分析文化、课程内容入手,对课程本质作一番新的探讨。
二、文化的内核凝结着人类能力
目前人们比较普遍一致的看法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7]或文化是“人在其历史经验中创造的观念和事物的复杂总和。”[8]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便获得了自身客观存在的规定性,从而反过来成为人生存和活动的一种外在条件。因而,从人自身的角度看,文化便是人生存和活动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对培育新生一代掌握已有的人类知识和经验并在能力上获得发展具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功能。为什么文化具有这样的育人功能?
人类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了和创新着文化的。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特性是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具体体现为:在人的认识活动或实践活动过程的范型中,第一个阶段总是“提出假说阶段”或“计划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开始行动之前,先在头脑里设计出自己将要进行的认识活动或实践活动的预想结果,形成活动结果的“图象”;然后,通过行动,使预想结果变为现实,即将头脑内的“图象”外化为认识结果或实践结果。这样的认识结果和实践结果,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无疑地,人是利用已掌握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感性的和理性的知识和经验在头脑中形成活动结果的“图象”的。不过,人之所以能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是因为他具有人类特有的“人类情感”、“人类技能”和“人类能力”。很明显,人在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活动结果的“图象”,表面地是人掌握的一定知识和经验产生作用的结果,实质地则是人的一定情感、技能和能力结晶。因此,随着人们的认识或实践行动,随着人脑中已有的预想结果的“图象”外化为认识结果或实践结果,人所具有的有关的情感、技能和能力便外化到客体或对象之中,即外化到认识结果或实践结果之中。
前苏联的列昂节夫认为,观念作为具体的客体物化的过程(劳动过程)实质上是“人的能力的客体化过程”[9]。日本的大木规和夫进一步指出:人“预先在头脑中描绘的图像(观念)是被固着于工具、机械之类的物质事物和语言、科学之类的观念现象之中”[10]。这就阐明了,人在活动(劳动)过程中的观念外化,不仅有观念性的物质化,还有精神性的对象化。所以,归根结蒂,人是凭籍着特有的“人类能力”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了和创新着文化;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和创新着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实质是人类能力客体化和对象化的结果。故而,文化的内核凝结着人类能力。
19世纪,文化时期说在欧洲诞生了,在吸取了达尔文进化论所概括出的自然自己复演自己的原理之后,它便发展为复演说。赫尔巴特及其弟子齐勒把这种理论用于教育,提出个人知识的发生,无论就其模式上还是排列上,都要符合人类历史中知识发生的进程[11]。很显然,他们探索的目光停留在了文化的知识层面而没有深入下去。深入一步的问题是:隐藏在个人知识发生复演人类历史知识发生下的底蕴是什么呢?
恩格斯在考察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流行的复演说之后精辟地指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约一些罢了。”[12],这就揭示出了,隐藏在个人知识发生复演人类历史知识发生下的实质为,新生一代的能力发展是人类能力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人类能力发展的历史积淀是怎样实现到个体能力发展的进程之中的呢?
在已有的整个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类能力历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成果凝结在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中;这样,人类通过各种活动和劳动将自身能力客体化和对象化为文化而保留和积淀下来。新生一代在发育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活动继承和掌握一定的传统文化,同时便将凝结在文化内核中的祖辈在历史上形成的能力内化为自身的东西,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人类能力发展到什么样的高度,个体能力就能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
正是由于文化的内核凝结着人类的能力,而文化又是作为人活动的必然环境,所以伴随着活动,个体将凝结在文化中的人类能力内化为自身的东西,从而实现着自身的发展。
三、课程内容是教育化的文化
文化的内核凝结着人类能力,同时,文化又是庞杂的,一种质地和一定水平的人类能力凝结在大量的、多种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样式里。这是因为,人类能力的发展具有同一性,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人群的活动却具有多样性和重复性,具有同一能力和同一能力水平的不同的人创造着大量的、多种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样式。
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各部落或公社在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创造出的文化在量上是有限的。各个部落或公社的成员及其新生一代能够自然地占有全部文化并其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部落与部落之间文化开始交流,同时新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使文化的总量不断地增长。当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文化积累到了事实上的足够的量后,一个绝对的矛盾出现了:人类个体和一定的群体就不能自然地占有凝结了人类已有的能力种类及已达到的能力水平的全部人类文化并将其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客观上又要求个体和一定的群体占有凝结了人类已有的能力种类及已达到的能力水平的文化并将其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一对矛盾,就必须给予新生一代更多的专门时间以使其能够占有更多的文化,同时必须对已有的全部人类文化进行选择和重新组织以便使新生一代占有表征着人类发展程度的文化精华。这样的任务便历史地赋予了从社会活动中相对地独立出来的教育活动以及继而从教育活动中相对地独立出来的学校教育活动。
在教育情景中,经过选择和重新组织的文化便是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尽管来源于文化,但它是被选择和重新组织的过程中,又获得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新的客观规定性。在文化中的一部分被选择出来进行重新组织而成为课程内容的过程中,作为选择者和组织者的人将其特有目的性客体化和对象化到课程内容之中了。很显然,选择者和组织者的根本目的就是教育人,就是培养新一代儿童青少年,就是为学生提供一种特殊而优化的文化环境,从而使学生能够在教育活动中,通过自身的学习活动掌握已有的人类文化的精华,同时将凝结在课程内容中的人类已有的一定能力及其一定水平内化为自身内在的东西,得到尽可能充分的、自由的和和谐的发展。
人类创造文化和创新文化的根本目的则不在于此,而在于满足人类的生存和享受的需要。不可否认,人类创造和创新出来的文化也渗透着人类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目的,也内在地具有促进人发展的功能,也客观上具有育人性。但是,文化具有的促进人发展的功能和育人的性质,不是文化的直接的、专门的和根本的功能和性质,而仅仅是其间接的、附属的和派生的功能和性质。然而,正是有了文化原本就具有的这种间接的、附属的和派生的功能和性质作为一种客观基础,才使人们有可能从文化中选择出一部分作为课程内容,并使之具有直接的、专门的和根本的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和育人的性质。
这样,我们就认识到了,课程内容实质上是一种教育化了的文化。课程内容作为教育化的文化,具有如下特性。
一是再生性。文化在进入教育活动的入口处,必须要经受教育者的选择。这种选择就是教育者以文化为客体和对象,以通过促进学生尽可能充分的、自由的和和谐的发展来满足社会对一定人才的需要为目的,从而进行活动来形成课程内容。所以,课程内容尽管来源于文化,却已不是人类创造出来时的原生性文化,而是一种再生性文化。
二是简洁性。文化表现为精神化和物质化的知识和经验,其内核又凝结着人类的能力。知识经验和人类能力,均是人类进行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的产物。知识经验的积累和人类能力的发展,均依赖于人类活动的深化。知识经验要素大体可分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及应用知识改造世界的活动方式;活动方式的实际经验,包括重复性活动经验和创造性活动经验;关于世界及人类相互关系的态度标准。这些要素纵横交错,构成了庞杂的知识经验体系,大体分为自然科学体系、社会科学体系、思维科学体系和人文科学体系。人类能力大体包括:语文能力;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人类能力见诸于客观对象,便集中表现为创造能力,并凝结在知识和经验的内核之中。
知识经验总是特异性的,人类有什么样的实际活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特殊知识经验,从而使知识经验在量上急剧膨胀。而人类能力则总是一般性的,人类无论进行什么样的实际活动,能力的发展总是表现为水平的上升和品质的改善,能力自身几乎不表现出量的扩充。因而,知识经验和人类能力便构成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一般性的人类能力重复性地凝结在庞杂的特异性的知识经验体系中。这就决定了,一定量的而不是全部量的知识经验就全面地涵括了一般性的人类能力。
因此,对文化的选择而生成的课程内容,客观上被要求同时也可能具有人类能力的“全息性”即少而精的一定量的课程内容的内核凝结了已有人类能力的种类和各种水平。所以,课程内容既不是原生性的庞杂而大量的文化,也不是从庞杂而大量的原生性文化中割取出的一部分,而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的精华部分,是再生性、简洁性的文化。
四、课程是预期教育结果的重新结构化序列
尽管古今中外对课程这一术语的基本含义的理解是相同的,“即课程是指学校教学的科目及其进程。”[13]然而学者们对课程的定义则各持己见。不过,透过历史上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出对课程认识的发展轨迹:这就是就课程的含义引伸到课程的外在和内在联系、从简单到复杂、从表面到深入、从外部到内部、从现象到本质。值得重视的是罗伯特·加涅采取的一种全新的方法,他定义课程是把教材(内容)、结果(最终目的)陈述、内容顺序和对学生开始学习时需要的起点技能的评估编织在一起[14]。基于这种方法,小莫里兹·约翰逊把课程定义为“一种预期学习结果的结构化序列。”[15]他的定义对我们深入认识课程的本质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在教育进程中,通过师生双方以课程为客体开展活动,学生最终便掌握了课程内容表征的一定的人类知识和经验,同时将课程内容凝结的一定的人类能力内化为自身的东西,从而实现了发展。这也就是教育结果。这种教育结果,是教育者在教育活动进程的“计划阶段”就进行了设计并于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图象”的。这种“图象”外显出来,在抽象和简捷层面上的表达就是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正是有了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作为依据,人们才从文化中择其精华作为课程内容并将其重新组织,从而将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具体化到课程之中。因而,从教育活动所特有的育人目的性的角度看,作为教育结果的学生发展的进程,就是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以及课程的实现过程。所以,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实质上就是一种抽象的预期教育结果,而课程实质上就是一种具体化的预期教育结果。
从文化中选择出的课程内容,还带着始生性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结构,这种结构的逻辑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形成的特有的学问研究的逻辑。而课程内容要达到有效地内化为学生自身的东西,其结构就必须符合学生发展的心理逻辑和实现学问逻辑与心理逻辑的有机统一。这就客观地要求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新组织,使之形成既符合学问逻辑又符合心理逻辑的新的有机结构。这一任务是由对课程内容的重新组织环节来完成的,产生出来的便是课程。所以,课程是重新结构化了的。
人类能力的历史积淀实现到个人能力的发展进程之中,就客观地要求科学逻辑与心理逻辑的有机统一,还必须包括在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新组织时使课程内容纵向结构形成与学生心理发展进程中从低到高的各级水平相适应的结构序列,也就是在课程中实现课程内容各种要素的安排序列与学生心理发展序列统一。因此,课程还是课程内容的一种结构化序列。
这样,对课程本质的深入分析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课程定义:“课程是一种预期教育结果的重新结构化序列。”[16]
注释:
[1]、[5]、[11]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98-99、258、107页。
[2]《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1页。
[3]See Peter F.Oliva:Deceloping the Curriculu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2,P.5-7。
[4]See Arieh Lewy(ed):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urriculum,Oxford,Pernamon Press,1991,P.15。
[6]See Arieh M.B.Brimfield,Curriculuml What's Curriculum?T-he Educational Forum,Vol.56,No.4,Summer 1992.
[7]《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
[8]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International Edition)(Vol.8),Grolier Incorporated,1985,P.315.
[9][10]《现代教学论发展》,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6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13]黄甫全:《关于教学、课程等几个术语含义的中外比较辨析》,《课程·教材·教法》,1993年第7期。
[14]See Robert Gagne:Curriculum Research and 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AERA Monograph Series on Evaluation:Perspectives of Curriculum Evaluaaion,no:1(Chicago Rand McNally,1967),P.21.
[15]Mauriaz Johnson,Ju.,Definitions and Models in Curricu-lum Theory,Educational Theory 17,no:2(April 1967):P.130.
[16]这一定义最早发表于拙文《课程难度刍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当时因文题及篇幅所限,论述未及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