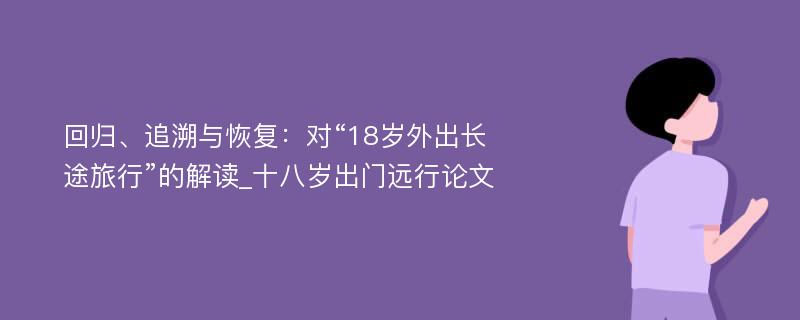
回归、追溯、还原——《十八岁出门远行》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八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0年,在宁波,一个十多人住的屋子里一个靠近窗子的上铺,名不见经传的20岁的余华第一次读到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发现了一种比伤痕文学那种控诉更有力量的小说表达方式。
1986年,小有名气的26岁青年作家余华得到了一本《卡夫卡小说选》,突然发现写小说可以这么自由。
同年,被卡夫卡震撼的余华在一张小报的夹缝里看到嵊县一辆运苹果的车被抢的负面新闻,就是这件事,使他写出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
其后至今,余华关于这篇小说留下了不少回忆和评价。难能可贵的是,二十多年来,他的这些创作谈,自始至终基本上是统一的。这相对稳定的自我回味与评价,就给我们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分析研究依据。
一、川端康成与卡夫卡、基础与解放——为什么会有《十八岁出门远行》
从文学的操作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小说,有着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两个渊源。
虽然余华自己说看了卡夫卡以后知道自己“终于可以摆脱”川端康成了,但其实后来余华自己也说过:“我现在回头去看,川端康成对我的帮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时间里,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感受,这非常重要,这样的方式会使细部异常丰厚。川端康成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作家。就像是练书法先练正楷一样,那个五六年的时间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写作基础,就是对细部的关注。现在不管我小说的节奏有多快,我都不会忘了细部。所以,……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写作的基本方法。”[1]
的确,《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这种细腻的个人感受俯拾即是:“我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然后我对着自己哈哈大笑,但是我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我立刻不笑。”“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竞在这里。”从中我们分明可以清晰地看到川端康成作品中那种用感受的方式去面对细部、表现微妙情感的细腻而丰厚的基本写作方法。
而正如余华所说,卡夫卡对他来说是“思想的解放”。以前,他“觉得自己还仅仅是个‘小偷’,所有的技术只能满足于‘小偷小摸’,充其量,也就是能做到不留痕迹。但是,读了卡夫卡之后,才明白人家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汪洋大盗’,什么都能写,没有任何拘束。所以,从那以后,我找到了那种无所羁绊的叙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找到了那种‘大盗’的精彩感觉”。[2]在余华看来,这无异于一种“拯救”:“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都极为严谨的作家,而在叙述上又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于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与川端不一样,卡夫卡教会我的不是描述的方式,而是写作的方式。”[3]
卡夫卡对他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上,而是整个世界观的改变。从根本上说,卡夫卡给他“带来了自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写作的自由”,“可以不用去考虑刊物怎么想,读者怎么想,只要它能够调动我个人的激情”,“就是最好的方法”。所以,读了卡夫卡之后,“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祖先》等一大批作品,都是一种自由写作的产物”。[4]可以说,对卡夫卡的顿悟成就了26岁的余华的未来,而《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余华为卡夫卡式写作唱出的第一个音符。
二、诚实与直接、强硬与强烈——《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什么如此残酷
很多人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直接表现一个少年面对充满欺骗、恐惧、虚伪的世界的人性恶,十分残酷。多年之后,余华和洪治纲有这样一些对话,似乎道出了他当时的潜意识:
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才真正知道一个道理,就是你用一种最诚实的方式去写小说是最困难的。但是,也就是这种最诚实的写作,才造就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拥有那些伟大的作家,他们几乎都写下了优秀的小说。
诚实就是“写小说不要绕”。
文学的力量往往就是在这种正面推进中哗哗地展示出来。
每部作品都有很多敏感的部位,它们决定了整个小说的内在力量。有些作家没有意识到,所以就扯开了;有些作家没有信心来写,所以就绕开了,或者轻描淡写一下了事。但是,好作家绝不是这样,他会一步步地推过去,用最诚实的叙述将它全面地展示出来。作家写小说,说到底就是拼性格,拼力量。你行或者不行,其实就是看你在那些广泛的敏感区域中,有没有能力去直着写。因为直着写比绕着写要难得多。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强硬的叙述者,或者说是像“暴君”一样的叙述者。我认为人物都是符号,人物都是我手里的棋子。我在下围棋的时候,哪怕我输了,但我的意愿是要我输的,我就这样下。我赢了,也是因为我的意愿要我这样下的。[5]
很明显,不管1986年底的余华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已经在以一种“暴君”般的强硬,“直接”写那些别人出于种种原因“绕行”的内容,这大概出于他骨子里的那种“力量”吧。苏童曾经说过:余华喜爱的是很强烈的东西。对此,余华非常认同:“我确实喜欢比较强烈的东西,……我喜欢的作家,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福克纳,都是很强烈的作家。”对“诚实”的追逐、对“直接”的推重、对“强硬”的享受、对“强烈”的喜爱,当然,再加上之前我们探讨过的对卡夫卡的崇尚,恐怕还有26岁这个年纪的血气方刚,《十八岁出门远行》展现得如此残酷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真实与想象、先锋与朴素——《十八岁出门远行》对余华意味着什么
尽管《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确有生活原型,但我们知道,余华不是在写新闻报道。从很多细节的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出,余华是在追求“作家眼中的真实”。
其实,我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和我的生活有关。因为我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历,它还有想象,有欲望,有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都组成了我的生活。
在1986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6]
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7]
为了表达自己心目中的真实,余华就转向了更为丰富的、更具有变化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而对于人们普遍将先锋文学视为80年代的一次文学形式革命的看法,余华则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仅仅只是使文学在形式上变得丰富一些而已。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余华在中国被不少人看做学习西方文学的先锋派作家,而当他的作品被介绍到西方时,他们的反应却是余华与文学流派无关。比这个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国内,《十八岁出门远行》刚刚诞生之际,余华受到的肯定也不是“先锋”,而是“朴素”。那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林斤澜、副主编李陀看完以后都非常喜欢。林老说:哎,写得真好。李陀评价《十八岁出门远行》时用了一个词,说写得这么“朴素”,真好。
余华自己认为,真正确定他后来风格的小说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他说过:“我自己愿意把它看成我的处女作,因为我不愿意让我很不成熟的作品展现给读者。”[8]以此篇小说作为自己创作成熟的标志,可见作者对它的喜爱之深。
余华发现,几乎所有的20世纪的大作家,刚开始都是先锋,慢慢地都变得朴素,经历了一种复杂以后,又变得简单了。或者可以说,余华是80年代文坛一个具有朴素本质的先锋人物,他从一开始就以朴素而深得赞许。
在1986年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余华自己都感到意外:“我隐约预感到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即将确立。我曾和老师李陀讨论过叙述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李陀说:‘首先出现的是叙述语言,然后引出思维方式。’”余华说:“我的个人写作经历证实了李陀的话。当我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我从叙述语言里开始感受到自己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往前行走,使我写出了《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等作品。”[9]
也就是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对余华,意味着一种文学真实的实践,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和一种全新写作态度的确立。
卡夫卡式的思想自由成就了余华选材的大胆,川端康成式的细部描述成就了余华手法的细腻,嵊县的负面新闻给余华提供了放开手脚的载体,对文学真实的追求使余华敢于正面推进,与朴素的天然联系使得余华从一开始就具有成为小说名家的素质,前辈的指点提携更构筑了余华日渐巩固的文坛地位,而以上一切,都承载于这一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