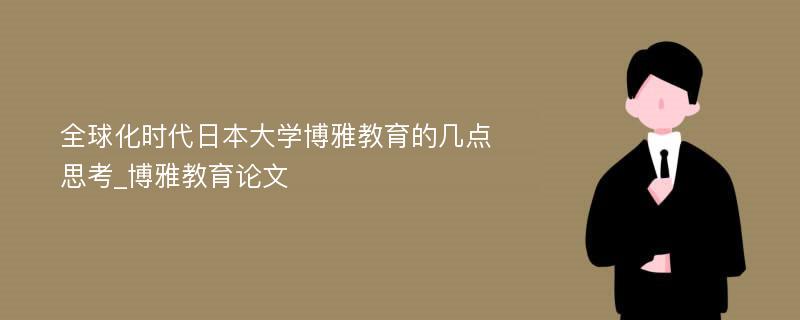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对日本大学博雅教育的若干思考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雅论文,日本论文,时代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9)01-0001-06
不同的人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但差别并不显著。即便如此,仍很难对“全球化”做出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只能把握其某些明显特征,如普通市民也加入到广泛传播的网络化的市场中,国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适者生存”和“市场主导”的发展趋势逐渐增强。全球化主要指各国经济融入世界一体化经济的过程,但也涉及到其他方面,如权力、文化和环境等,有些人已经注意到这些方面。
当前的全球化时代,不仅经济面临着各种挑战与变革,而且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其他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与变革。与全球化相关的教育概念频繁出现,举几个例子,如“自由化”、“私有化”、“公司化”和“分权化”。全球化的三个共同特征似乎引起了特别关注:(1)放开对货币和物资的管制,实行自由化;(2)信息通讯技术(ICT)创新;(3)采用所谓的“世界标准”。“全球化”表达了竞争社会中全新的多方位变革,作为形成人类智慧的核心——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应该如何在日本以及全世界的大学进行呢?本文追溯了日本博雅教育的简史,重点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相关改革与发展,以探索博雅教育的发展前景。
1.二战前日本高等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缺陷
在二战前的教育体系下,学生在进入帝国大学[1]以前,要在旧制高中接受3年正规的人文教育与博雅教育。一进入大学,学生就被要求在毕业前接受3年的专门化(specialized)或专业化(professional)教育。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一些比较有名的私立大学和像东京商科学校(the Tokyo College of Commerce)等之类的公立学大学提供3年的预科课程,以为接下来的正规的专门化或职业化课程提供充分的准备。
一般来说,这些在二战前旧的教育体系中形成的日本大学都受到欧洲大陆大学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德国大学的影响,其典型特征是专业研究与教育相结合。于是,专业研究活动比单纯的教学受到更多关注。所谓的人文教育与自由教育则在旧制高中或大学预科进行,为进入大学做准备。
为了与西方国家竞争并取得成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建立起现代军事体系,同时鼓励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以提高经济实力。帝国大学最初作为国家机关而建立,要求通过教育与研究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这种国家主义的大学目标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大学渐渐地纳入到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系中,天皇至高无上。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前日本大学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某些特定领域(或学科)的研究和教育。历史证明这种方式最终导致了惨重的损失。
有一件事详细地解释了二战前大学教育的弊端。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南京,东京帝国大学作为当时全日本最好的大学,举行了一个仪式以庆祝这次胜利。那时该校的许多学生是第一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在第一高等学校接受了博雅教育。特别是许多优秀的精英在第一高等学校教学,如新渡户稻造和内村鉴三等,他们是当时的自由基督徒与学术界的代表。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智慧,丰富情感,养成相互理解的同情心和宽容的态度,深入思考人类的价值与尊严,并形成推动这种价值与尊严的人文观。然而,不管是在优秀精英的教导下还是在一定的博雅教育培养下,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们都不能准确判断局势——日本即将爆发战争,也无法预想在南京发生了什么。连日本“最优秀的”大学都显露出这样的缺陷,大家不难想象当时日本其他学校的境况了。
2.二战后的新大学体系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二战后的1947年,为了实现教育体系的民主与平等,日本改组、整顿了高等教育体系和整个旧的教育体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将二战前复杂的双轨制变革为单轨制。这种新的民主化体系最终促使更多高中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当然也推进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教育内容改革(或课程改革)伴随着体制层面的改革同时进行。基于对上述过去的错误与不善管理的反思,日本开始进行教育改革。
在讨论大学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一些观察者试着界定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并明确其重要性。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东京商科大学校长上原専禄(Senroku Uehara)指出,二战前大学教育的缺点在于不仅“伪自由教育(pseudo-liberal education)中缺乏专业教育意识”,而且“伪专业教育(pseudo-specialized education)中缺乏自由教育意识”。[2]上原校长认为,“大学教育人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克服之前的缺陷,自由教育旨在培养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智慧,并期待人类智慧与能力的多样发展”。[3]同时,上原校长强烈批判在完成自由教育之后才提供专业教育的教育结构,认为这是违背自由教育理念的悖论。另一著名学者、原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Shigeru Nanbara)也重申在大学教育中实现人文理念的重要性。他认为,二战前大学教育使学生形成了低层次的学习态度并使他们趋向权力与实用。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他强调大学应该培养“人文理念”,大学的新使命是“不仅培养智力,而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们性格与深刻而丰富情感的养成”。[4]
这些学者的观点都受到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的影响。报告书的第六章有一段相关论述提到:“在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中,我们认为提供通识教育的机会太少,专业教育过早且领域狭窄,并过于强调其职业性。应该培养更广博的人文态度,为自由的思想和良好的专业训练基础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这将丰富学生今后的生活,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职业与人类社会的整个图景是相契合的。我们认为,通识教育应该整合到学生的常规课程中,这样学生就可以得到全部的学分,而不必把它作为额外课程单独学习,不仅通识教育课程如此,专业课程也需要增加设置的灵活性。”[5]
这正是二战后日本大学中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理想原型。值得注意的是,使节团报告书中使用的是“通识教育”,而不是“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
1950年,日本大学基准协会(The Japan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准备了一份报告——《大学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勾勒了战后高等教育标准的基本框架。报告指出,“自由教育”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但却始终体现着强烈的贵族气息。报告进一步强调,自由的、人的教育应该摒弃贵族气质,而发展为“通识教育”。委员会认为这种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优秀市民,使其成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原动力”。[6]
基于此种观点,所有大学都设置了通识教育课程(一般教育),包含三个领域(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每个领域的通识教育分配相同的学分(即12学分的人文科学、12学分的社会科学和12学分的自然科学)。外语学习最初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但很快就从中独立出来。每所大学都提供通识教育中的各类课程,在大学的前两年每个学生都要学习这些课程,后两年则学习专业学科。因此,通识教育有时被当作进入专业学习的预备阶段,有时被当作成熟学科的入门课程。
“通识教育”在初期阶段存在很多矛盾。该术语本身就与自由(博雅)教育相混淆。而自由教育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本问题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的区别尚未进行过彻底的讨论。结果,通识教育最终被认为是不实用的(或许,根本无用的)知识,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甚或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1956年文部省颁布的《大学设置基准》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基础教育学科”。《大学设置基准》是所有高校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条例,规定36学分的通识教育中最高可以有8学分专业基础课程。这种变化回应了产业部门的要求,产业部门对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下滑表示不满。
实施通识教育的组织结构仍存在问题。二战后的教育改革中,通识教育观念虽被接受,但大学中应由谁或哪个部门负责这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在早期并未得到澄清。1963年《国立学校设置法》(The National School Establishment Law)修订后规定,建立一个特殊的部门即教养部,负责为所有在校生提供通识教育课程。到1968年有32所国立大学建立了教养部管理通识教育。[7]“教养部”这个名字可以直译为“博雅教育部门”,而不是“通识教育部门”。在二战后新的教育体系形成之初,前者即博雅教育是可以接受的。然而术语的混淆使用表明其中有着某种矛盾,而且拨给通识教育课程部门研究员的年度研究预算通常低于其他部门负责专业教育的研究员。从史实来看,许多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二战前不是大学教授而是旧制高中的教师,在二战后的教育改革中才提升为大学教员。通识教育部门的教员水平较低可能也来自这种历史背景,这限定了教员的事业发展和专业资格。
3.所谓“博雅”教养(kyoyo)的若干思考
日本用语“教养”指“文化”和“人文学科”,而且仅指人性的培养。此外,人文学科的概念在西方语言的演变中包含自然科学,因为它源自七艺。七艺由前三艺(即文法、修辞和逻辑)和后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构成。在西方的概念中,人文学科指除职业和技术以外的学术学科,似乎包括基础学科、通识学科和专业学科。然而,人文学科在日语中的内涵不包括专业学科。
在任何一个社会,所谓的主流文化都是上层社会的文化。主流文化通常将经典作为他们的核心,并获得共享这种文化的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支持。明治维新之前,汉学(或对中国经典的学习)是武士或武士阶层流行的文化。在那时,武士阶层形成了社会的主导力量,武士文化和中国经典也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知识在封建教育机构传承下来,如塾、藩校和昌平黌等教育机构。
然而,自明治维新以来,武士阶层解体了,他们以中国经典为基础的悠久文化也在现代学校中消失,于是传统文化最终消亡。谁(或者什么)将来填充这块文化真空呢?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从中国经典到西方经典的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在内的日本知识分子尝试采取某种行动,用西方的经典来弥补失落的文化。受这种文化观影响,二战前的教育体系要求高等学校教授哲学、西方人性和人文课程。然而,毕竟这些学科与知识是舶来品,显得非常片面与零碎,看起来并不能成功地形成自我包含式的、全面的文化。而且这些课程被当作大学的基础预备课程,为进行专业学习做准备。因此,可以说在二战前的日本,不管是在学校或是任何社会阶层和群体中都没有成型的文化形象。从西方文明舶来的文化基础对高等学校和大学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马克思主义曾经一度风靡于年轻的知识分子中间,也无法弥补我们自身文化基础的真空,文化无根的状态一直持续至今。持续增长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科学技术优于人文知识的现象又激励了文化的发展。
除了文化本身,日本对博雅教育的理解并不清晰,但显然不同于美国。日本有2个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和崎玉大学)和5个私立大学(东北学院大学、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基督教大学、东海大学和大塚山大学)建立了教养学部(Faculties of Liberal Arts)。其中只有2所,即东京大学和国际基督教大学建立了少数几个人文学院,还没有美国学校中那么广泛多样的学院。
4.20世纪9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改革与“自由教育”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继明治维新后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和二战后的第二次教育改革,开始了历史上第三次重要的教育改革。改革最初开始于1984年,教育改革特别委员会在首相中曾根康弘的领导下成立。二战后40年来积聚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教育改革特别委员会的目的就是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教育改革特别委员会的推荐下,大学审议会(The University Council)于1987年成立。审议会多次积极地提交大学改革报告,其中1991年6月提交的报告具有划时代意义,提出了大学教育的质量改进与振兴以及个性化问题。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一就是,放宽《大学设置基准》(The Standard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ies)。文部省将《大学设置基准》简单化、灵活化,因此,各高校都予以更多的考虑。新修定的《大学设置基准》第19条款规定校长组织课程管理,即将通识教育作为“广博而影响深远的教育,培养人的一般判断力和丰富人生品质的教育”。与1991年之前相比,日本现在的高校不再受学分的限制,只要修满至少124学分就可以毕业,以前的学分均分给通识教育的三个领域和专业教育。[8]
随着1991年《大学设置基准》的放宽,许多大学开始进行课程改革。1994年,即法案修正后的第3年,552所大学(73所国立大学、33所市立大学和223所私立大学)中有329所(59.6%)在全校实施课程改革。此外,46所大学在有限的几个学院里实施课程改革。因此,总共375所学校(67.9%)开始实施各类课程改革,其中,362所学校(78所国立、28所市立和256所私立)进行了通识教育的具体改革,已经有194所学校取消对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割裂。[9]关于通识教育教学的组织,105所学校(19.0%)经历了结构变革,因此,139所学校里的特殊部门只用于从事通识教育教学,32所学校中属于该特殊部门的教师负责教授通识课程。在140所学校中,教授通识课程的教师分散在各个学院,在104所学校中,每个单独的学院都负责通识教育。[10]然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都逐渐削弱,几乎所有的大学已经取缔了教养部,该部门在改革后的5年内专门负责通识教育,许多大学将其重组成新的专门学院,如“人文环境学部”(Faculty of Human Environment)、“综合文化学部”(Faculty of Integrated Culture)、“综合科学学部”(Faculty of Integrated Sciences)等。
对通识教育轻易地取消与重组表明,在过去的几年中它已经不为人重视,开始走下坡路。另外,在其走下坡路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趋势,即再评价普通自由教育(general liberal education),并探讨对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的保护。日本组织各种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讨论这一问题。而且,奥姆真理教(The Ohm Sinrikyo)的罪行(1995年,奥姆真理教教徒在地铁内释放沙林毒气,致使许多无辜市民伤残乃至死亡)成为再度审视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重要性的直接推动力,特别是后来发现奥姆真理教的教徒许多是一流大学科学领域的毕业生。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他们犯罪的原因:这些罪犯在学校生涯中缺乏人性的培养,尤其是在大学阶段。
5.21世纪初日本的博雅教育
2000年,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11](The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University Evaluation,简称NIAD-UE)以95所国立大学为对象,对自由教育进行评价。作为其功能的一部分,该机构从第三方视角客观地评价大学中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随后出台了一份报告,名为《国立大学自由教育成果现状》。报告强调了《大学设置基准》修订后10年内大学发生的细微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术语的使用中,术语“通识教育”代之以“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
报告指出,“据调查发现,自由教育的理解仍然因校而异”。[12]然而,随着负责通识教育的教养部的解体,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不仅由之前的教养部担负起来,大学中的其他部门也担负起来。许多大学建立了新的组织或部门,负责协调全校的博雅教育并将博雅课程分配给每位教员。报告将各种各样的博雅教育课程分为9类:(1)激发新生使其适应大学教育的课程;(2)狭义的博雅教育课程(过去定义为通识教育课程);(3)跨学科综合课程;(4)外语课程;(5)信息处理课程;(6)健康与运动课程;(7)专业基础课程;(8)补偿教育课程,弥补高中教育的缺失;(9)国际学生的日语课程与日本面面观课程。教学方法是多样化的,如讲座、小组研讨、辩论、集体作业、实习或现场培训等。从广义上讲,不仅一、二年级学生学习这些博雅课程(早期的通识教育也是如此),而且三、四年级的学生也与专业课程一同学习。95所国立大学中有58所(61.6%)在4年中提供这些课程,15所(15.8%)仅提供给一至三年级学生,13所(13.7%)仅提供给一、二年级的学生。[13]
下面以广岛大学(Hiroshima University)的课程改革作为博雅教育改革的一个实例。和其他日本大学一样,广岛大学在改革后用“自由教育”取代“通识教育”,一直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自由教育的目标是:(1)通过参加大学或社会活动组织的学术研究,提高学生的智力;(2)帮助学生获得专业学习所必需的基础知识;(3)发现人类要面对的问题,提高学生的跨学科综合思维能力;(4)提高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与合作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广岛大学的自由教育课程现在由6部分组成:(1)小组研讨会,掌握大学的学习方式;(2)提高外语能力的课程(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和韩语);(3)信息处理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课程;(4)了解各种不同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课程(如“广岛”研究、左翼与右翼的本质、智慧碰撞、东方思想、教育与人性、认知与学习、大脑与行为、哲学、生物世界、天文、科学实验方法等);(5)专业学习的入门课程(如微观经济学、基础物理学、普通化学、地质实验等);(6)体育运动课程。
理论上,这些课程的教学工作由大学全体教师共同承担,从初级到高级可以在4年内的任何时间为学生提供。然而,除非课程集中于前两年学习,否则不可能按标准完成4年的学业。而且,一些技能性课程,如外语、计算机课程、专业入门课程也同跨学科课程一样同时出现在课程设置中,这些课程的设置需要合理化(事实上,学生们对新的博雅教育课程评价不高)。[14]学生对新改革课程并不积极的评价似乎没有影响广岛大学改革的进行。
每所大学都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实施博雅教育的挑战,但尚未找到最终明确的答案。正如NIAD-UE报告所言,许多大学的课程改革都有机地将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联系。关于这种联系,我们或许该回顾一下阿什比(Sir Eric Ashby)在他的《技术与学术》(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中所说的,“为了适应技术专业化时代,大学必须把专业研究作为自由教育的手段”。[15]他说:“假定学生决定学习酿酒课程,他获得普通文化的途径不是听建筑、社会历史及伦理学等受欢迎的讲座,而是学习酿酒这门核心课程。……这是学习生物学、微观生物学和化学的必经之路。……随着他的学习获得动力,再让他有兴趣地研究啤酒销售经济学、酒吧及其设计、建筑,或者在社会历史中研究啤酒的历史,或者在宗教与伦理学中研究饮酒过度的不良道德影响。”[16]
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提出了与阿什比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在《美国智慧的结束》中强调博雅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回归西方文明主要是回归古希腊经典。[17]同样,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著名的《大对话》(The Great Conversation)(或《西方世界巨著》,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中第一卷就包含了54册,我们可以看到长长的西方经典巨著名单。
日本人仅参考这些书是不够的。我们是否应该将自己的知识纳入到自由教育中,如日本文化、亚洲文化或者世界文化?然而,如果我们寻找自己的东西,可能会过度迷失于自己的文化中,难道最后不会导致文明的冲突吗?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日本人用无根的生活方式反倒有很多优势。当代著名思想家加藤周一(Shuichi Kato)曾将日本文化定义为“杂种文化”(hybrid culture),认为日本文化由外来的多方面要素构成,否定坚实基础的存在。[18]人类学家青木保(Tamotsu Aoki)断言,我们有必要进入“健忘”[19]的状态,以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构建全球化时代完整的人类文化体系。
笔者很难在这么短的篇幅内阐述未来博雅教育发展的具体细节。然而,基于上述提出的观点和观察到过去几年内日益加速的变化与发展,可以看出日本人很好地遵循了阿什比的思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日本人更愿意积极地用我们“无根”(或混杂)的身份构建全新的博雅教育体系,无需刻意坚持我们自身的文化基础。
注释:
①本文是大塚丰教授在北京第三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的发言稿,作者同意翻译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