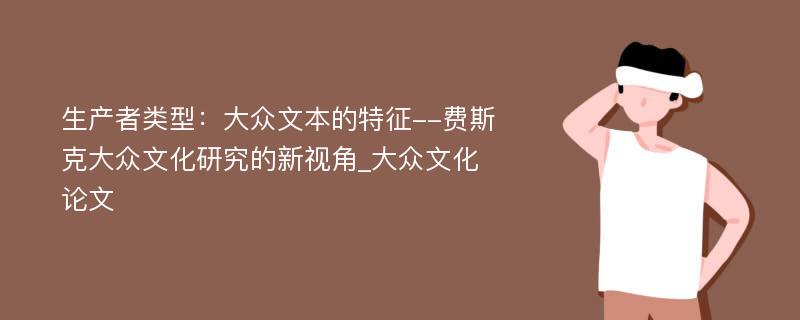
生产者式:大众文本的特征——费斯克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生产者论文,斯克论文,新视野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8)02-0037-06
费斯克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并无所谓“本真的”(authentic)民间文化。在商品经济的天罗地网中,所有文化资源都是一种产业化的资源,除了极少数和极边缘的例外,大众无法、也未曾生产自己的物质商品或文化商品。大众文化是大众在使用资本主义文本资源的过程中、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工业产品消费的交接部位创造的。“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与其说在于商品的生产,不如说在于对工业产品的生产性使用。”[1](P34)但是,大众能够“权且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本资源,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对资本主义提供的所有文化商品都无辨识地照单全收。众多的事实表明,大众的利益与文化工业的利益并不一致。在追求利润动机的驱使之下,文化工业当然十分注重如何贴近或取悦于大众。然而,它更像单相思的追求者,只能够希望其产品被大众选中,却从来无法保证能否被选中,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选中或不被选中。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常常让数量浩繁的电影、唱片或其他产品变成一种昂贵的“失败”。这就提出了大众选择的标准问题:是什么决定文本被大众选中或抛弃?费斯克回答说:“大众对文化工业产品加以辨识,筛选其中一部分而淘汰另一部分。这种辨识行为往往出乎文化工业本身的意料之外,因为它既取决于文本的特征,也同样取决于大众的社会状况。”[1](P154)在这里,费斯克事实上提出了大众筛选文本的两个标准:“文本的特性”和“大众的社会状况”。按照他的说法,大众文化的文本特性应该是“生产者式的”(producerly),大众的社会状况就是“相关性”(relevance)和“大众辨识力”(popular discrimination)。本文拟着重讨论费斯克大众“生产者式文本”的特征。
费斯克否定那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分析方式,认为大众文化批评分析者的角色和作用,不是去揭示文本真正的或潜藏的意义,甚至也不是去追溯大众所做出的种种解读,而是“要追溯权力在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即追溯一场所有文本牵连其中、大众文化总是处于从属者一边的权力游戏的踪迹”[1](P5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文本”在大众文化形成中的作用,他所否定的仅仅是那种对文本的本质主义的分析取向。费斯克既承认文本是大众可以“权且利用”的资源,同时又不相信所有的文本都能成为大众可以“权且利用”的资源。在他看来,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的,就应当具备某些特征,“如果该文本不具备这些特征,那么,它就几乎没有被使用的可能性”[1](P222)。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本,就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力量的机会,即由从臣属式的但不是完全被剥夺权力的位置出发,反抗或规避宰制性力量的那一类机会。人们不可能选择任何只服务于支配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商品,大众文本只有通过使自己成为权力和抵制、守纪律和无纪律、秩序和混乱持续不断的斗争中“令人向往的地带才能确保自己的流行”[2](P6)。
费斯克承认大众文本往往具有浅白、表面等特征,不是那种有深度的、同时也会使大众对其敬而远之的精心制作的文本。如果说“精心制作的文本”意味着把文化产品经典化、高雅化,包括学科化、艺术化、学术化等,以适应于所谓“高雅趣味”,那么大众文本则意味着文化产品的资源化,以适应大众“权且利用”的需要。经典化常常是神圣化的同义语,它使文化参与者与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大众文化资源的使用者与其资源之间却不允许存在这种距离或隔阂。费斯克说:“资产阶级趣味和大众趣味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对距离和绝对性的看重,也在于它缺乏嬉戏(fun)和某种共同体的感觉。”[1](P167)没有距离也就无所谓敬意,因此,即使当经典成为大众文化的对象时,往往也会遭遇亵渎和贬损,而大众文本则常常被一些批评家贬斥为是缺乏趣味的、庸俗的。费斯克认为,对大众文化的这类贬斥,往往包含着一种利益的表达。因为趣味就是社会控制,是作为一种天生更优雅的鉴赏力而掩盖起来的阶级利益。大众文本也充满着双关语,其意义成倍地增加,并避开了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淹没了其规范,双关语的泛滥为戏拟、颠覆或逆转提供了机会;大众文本常常关涉于身体及其知觉而不是头脑及其意识,“因为身体的快乐提供了狂欢式的、规避性的、解放性的实践——他们形成了一片大众地带,在这里霸权的影响最弱,这也许是一片霸权触及不到的区域”[2](P6)。
总而言之,大众文本是在封闭(或支配)力量和开放(或流行)力量之间的紧张状态下建构的。大众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和原子化的群众。这些从属者群体积极地对文本进行解读,以便从中生产与他们的社会体验相关的意义。正因如此,大众文本必须具备多义性与灵活性的特征,才可能受到普遍欢迎,从而得以流行。电视文本就是大众文本的一种范例,“电视文本的一个特征,就是闭合力与开放力之间的矛盾。前者力图关闭各种潜在的意义,从而提倡电视的倾向性意义,而后者则使各类观众能从文本中生产出适当的意义”[3](P84)。大众文本是意义的潜在体,可以由不同的大众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关注,进行解读。因此,费斯克以肯定的语调说,“大众文本应该是‘生产者式的’(producerly)”[1](P127)。
在考察费斯克的“生产者式文本”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他的“文本”(text)概念。费斯克的文本是一个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意义上的概念。在《澳洲神话》(Myths of OZ)导言中,费斯克指出,“我们采用的方法称为符号学方法,源自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符号系统的研究。符号学的一些方法是简单的同时又是强而有力的”[4](P4)。按照符号学,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可以被看做文本。一种文化产品也许实际上不能被书写,但它依然由符号组成,无论是视觉的、听觉的甚至是触觉的(如雕塑,可被触摸)符号,都可以被“阅读”或解释。
费斯克认为,任何文本都不只是能指,“文本是意义的载体,它使能指与意义相连,而不只是给意义提供适当的所指。它们识别并限制可能发现意义的舞台”[3](P84)。从这一角度看,“文本”是一个具有广泛概念的含义。他认为,文化工业经常被看做是生产诸如电影、音乐、电视、出版物之类产品的工业,但从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所有工业都是文化工业,一条牛仔裤或一件家具就像一张流行音乐唱片一样都是一种文化文本。“文化工业,我指的是所有工业,必须生产出全套产品以供人们从中选择。”[2](P5)在理论的意义上,可以将晚期资本主义的商品区分为物质-功能意义上的资源,如食物、衣服、交通工具等,以及符号-文化意义上的资源,如媒体、教育、语言等。但为了避免误解,费斯克同时又声明,如果说两种资源之间存在差异,也仅仅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起见,因为任何一种物质-功能性资源,都与符号-文化性的资源相交叠。“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也是一种言语行为;烹调也不仅仅是为了提供食物,它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援引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表述,我们可以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所有商品都是‘会言谈的物品’(goods t0speak with)。”[1](P34)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的所有商品都是“会言谈的物品”,因而便都是意义的载体,是识别并限制可能发现意义的舞台,从而也就都可以被视为“文本”。
费斯克的“生产者式文本”这一概念与埃科(Umberto Eco)的“开放式、作者式文本”(open,writerly text)、巴尔特(Roland barthes)“读者式”(readerly)文本与“作者式”(writerly)文本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了理解前者,有必要对后者加以分析和考察。
费斯克认为,在一个由拥有不同利益的多样社会群体组成的社会中,文本如果能够流行,就必须如埃科(Umberto Eco)所说的那样是“开放式的”(open)。按照埃科的观点,文本既可能是开放的,也可能是封闭的(close)。封闭式文本(close text)往往注重叙述结构和叙述风格,多少有些直露地告诉读者如何去理解人物、主题和环境,从而控制读者的解释;封闭式的文本往往只允许一种解读,其倾向性解读明显超过其他解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一个开放式的文本则叙述清晰,力图释放出多种多样的联系和解释,允许多种解读同时并举,以使其全部的“丰富内涵”和“文本肌理”都得到赏识。开放式文本并未试图传达一种单一的信息从而关闭其他可能的意义,也未将自身的重点集中在一个唾手可得的意义上,从而把不同的读者都限定在同一种理解之中,它允许在其中进行各种不同的、复杂的解读,因为解读永远不可能是单一的。开放式文本拒斥封闭(closure),无论这种封闭是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其话语结构来进行的,还是作者通过其自身的权威性施加给读者的。费斯克相信封闭式与开放式文本的概念,是相当有用的,“尤其是当我们把它们与意义之争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电视文本描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各样观众之间斗争的场所。前者力图封闭其所提供的抵抗性解读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一个封闭式的文本,而如果后者想让文本流行开来,就要不断努力使文本具有开放性,以适应对它们的各种不同的解读”[3](P94)。
与埃科关于封闭式文本与开放式文本的区分相类似,巴尔特区分了“读者式”(readerly)文本与“作者式”(writerly)文本,并考察了两种文本所引发的不同阅读实践。[1](P127)“读者式文本”设定了一个固定实体的存在,同时假定自身是对这一实体的描述,它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把文本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读者式文本”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本,只倡导单一的意义,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作者式文本”,它并不提供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邀请人们去生产无数的实体,它不断地鼓励读者重新书写文本,并从中创造出意义。“作者式文本”是丰富的、多义的,充满矛盾的,它反对一致性与统一性。它的代码中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也不承认话语的等级结构,它是开放的。“作者式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constructedness),它邀请读者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意旨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费斯克认为,巴尔特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埃科尤其是巴尔特的概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费斯克的“生产者式文本”这个范畴,“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对这样的文本进行‘作者式’解读,不一定困难,它并未敦促读者从文本中挖掘意义,也不以它和其他文本或日常生活间的惊人差异,来困扰读者。它并不将文本本身的建构法则强加于读者身上,以至于读者只能依据该文本本身才能进行解读,而不能有自己的选择”⑴(P128)。按照费斯克的说法,“生产者式文本”把“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与“读者式文本”易于理解的特性结合了起来。它像巴尔特的“读者式文本”一样通俗易懂,而且从理论上说,即使是那些已经充分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读者,也可以轻松地阅读这种“生产者式文本”。费斯克举例说,如果这类读者存在的话,石油大亨或许也会观看《豪门恩怨》吧?同时,与封闭的“读者式文本”相比,“生产者式文本”又具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与“读者式文本”不同的是,“先锋派的作者-艺术家会使读者惊讶地认识到文本的话语结构,会要求读者学会理解新话语的技能,以便使他们能够以作者式的方式参与意义与快感的生产”[3](P95),而“生产者式文本”并不要求那种“作者式”的主动行为,也不设定规则来控制它,它所依赖的只是读者早已掌握的话语技能,仅仅要求他们以对自己有利的、生产者式的方式来使用它。“毋宁说,生产者式文本为大众创造提供了可能,且无论是多么的不情愿,它还是暴露了它的倾向性意义的种种脆弱性、限制性和弱点;它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倾向性意义相悖的声音,尽管它试图压抑它们;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确确超出了自身的控制。”[1](P128)
先锋派的作者-艺术家往往会追求作者式、先锋派文本的“陌生化”(unfamiliarity)效果。“陌生化”是相对于“自动化”(automation)的习惯、经验和无意识而言的,它产生于变形和扭曲,产生于差异和独特。陌生化正是要不断破坏人们的“常备反应”,使人们从所谓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重新调整心理定势,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从而重新唤起人们感知艺术的原创性。而费斯克认为,“生产者式文本”“并不像作者式文本般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它们的不受规训,是日常生活的不受规训,这是人们相当熟悉的,因为这是具备权力结构的等级社会中的大众体验所具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要素。而且,这些大众文本并不要求这种‘作者性’,因为要求它就意味着规训它(先锋文本的‘作者式’读者,是一个被规训的读者);但是这些文本允许‘作者性’,因为它们无法阻止它”⑴(P128)。与先锋文本所拥有的特殊文本力量(competence)和陌生化效果形成对照,大众生产者式文本鼓励大众进行不受文本控制的自由的社会体验,寻找文本与社会关系的交接处,并且驱动大众从中生产出自己的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
“葛兰西式”的文化研究,既关注结构又关注能动性,既关注文本又关注解读,既关注自上而下的宰制性力量又关注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根据斯道雷的表述,“在一个霸权的形势下,从属集团看起来好像是积极地支持和同意统治集团的价值观、理想、目标等,企图把他们自己也整合进权力的主流结构以及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之中。然而,正如威廉斯所指出的,‘霸权并不是以一种统治的形式而被动地存在的。它是被不断地更新、重新改造、维护和修正的,同时也被不断地抵抗、限制、改变和挑战的’。所以,尽管霸权以高度的共识为特征,但它绝不是没有冲突的,而总是充满了抵抗的”[7](P53)。在费斯克关于大众生产者式文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中,“葛兰西式”文化研究的这种兴趣点也有充分的体现。
费斯克相信大众文化内部充满着矛盾:既关乎宰制,也关乎臣服;既关乎权力,也关乎抵抗。它充分地显示,宰制性力量的运作,并不是单向的、纯粹自上而下的,大众文化并不是如一些理论家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被统治阶级操纵并且用以灌输和麻醉群众的“鸦片”或“白日梦”。“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这些意义是有利于从属者的”。[2](P2)大众的抵抗和权力的运作之间总是充满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诚然,大众文化是由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所创造的,大众文化的创造与支配行为的结构有关。但是,只有当人们选择工业商品作为大众文化创造的“权且利用”的资源时,工业生产的经济需求才可能得以满足;只有当大众选择和阅读那些体现着霸权的文本并予以抵抗、逃避或中伤的时候,霸权的机器才可能得以开动。自上而下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时才可能开始运作。费斯克说:“任何发挥着作用,以求镇压或限制被支配者的中介行为得以运作的空间的那些社会力量的路线,都会抵牾于力图扩大这一空间的那些横穿着的对抗式路线。”[2](P213)正是从大众的抵抗和权力运作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费斯克观察到了对“生产者式文本”的“生产者式”解读所发挥的功能:“大众文化充满了对抗的因素,而‘措辞’(diction)的对抗(contra)力量则来自它(不情愿的)‘生产者式文本’的‘生产者式’阅读。”[1](P129)正因如此,分析大众文本的特征,也就顺理自然地成为理解大众文化内部矛盾特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丹尼·卡瓦拉罗指出,对阅读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是批判及文化理论在语言和阐明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阅读日益被看做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不单单指我们细读书面文本时所投入的一项活动。事实上,一旦我们置身于这个世界,并试图去理解或解读周围的符号,阅读便成为我们自始至终参与其间的一个过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是我们的社会存在枢纽上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7](P53)对“生产者式文本”的“生产者式”阅读的重视,显然是与批判及文化理论注重“阅读”的研究倾向同条共贯的。费斯克认为,阅读既关乎文本,又与阅读者生活的世界具有相关性。而他首先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生产者式文本”特征召唤了大众的生产者式阅读倾向?文本中吸引大众认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对考察对象进行双重的聚焦,是费斯克一以贯之的思路。他常常提醒大众文化的研究者不仅要聚焦于金融经济,而且更要聚焦于文化经济;不仅要聚焦于自上而下的权力,更要聚焦于自下而上的抵抗;不仅要聚焦于意识形态的压制力量,更要聚焦于大众如何与之相对抗。对大众文本的分析,他同样提醒人们必须进行双重的聚焦,即不仅要关注文本的深层结构;而且更要探究大众如何应付这个体制,如何阅读体制提供的文本,以及如何从体制的资源中创造大众文化。费斯克首先肯定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结构学和符号学等方法对深层结构研究的有效性和敏锐性。他认为,这些研究方法揭示了,对于所有父权制消费式资本主义的产品,意识形态的宰制性力量都在顽强而内在地发生作用。费斯克说:“如果把这些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将十分清楚地发现,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必要条件决定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日常生活又反作用于它们。”[1](p129)但是,费斯克同时又强调,如果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这里,就可能会忽视同样重要的资本主义文化领域,而且最终将会困囿在悲观主义的状态中,从而丧失判断力。“对大众文本深层结构的研究,或许能够合理地解释我们对这个体制的厌恶,但它无法提供在这个体制内部进步的希望,它所能提供的仅仅是经由激进革命改变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的信念。”[1](PP129-130)
费斯克更关注和强调的是另一种聚焦,也即分析文本如何逃脱控制的意义,如何召唤读者进行“生产者式”阅读的倾向,文本中吸引大众认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大众如何应付宰制性体制,如何阅读体制提供的文本,以及如何从体制的资源中创造大众文化。费斯克相信这种聚焦可以提供一种补充性的视角,从而弥补以往大众文化研究的不足。费斯克注意到,传统的学院分析和专业分析很少以这种方式研究大众文本。无论是学院中人还是专业的批评家,都苛求学科的完美。他们往往因大众文本具有浅白、过度、煽情等不同于所谓高雅文本的特征,就对之加以贬斥或藐视。费斯克认为,这或多或少隐含着一种阶级阶层利益的诉求。正如布尔迪厄所阐明的,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生活的基础,既提供了人们相互理解、交往、参与社会实践的空间,同时也是社会支配的源头活水。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文化实践和符号交流,都或多或少地表达或泄露了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身份和等级。鉴赏者在区隔对象的同时也往往区隔了自身,文化从来都不可能断绝与社会支配权力之间的姻亲关系。布尔迪厄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个“经济”的世界里,最“反经济”和最明显的“无私”的行为,也可能是有私的,这些行为具有一个经济合理化的形式(即使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而且决不把它们的创造者从期待与经济规律相一致的“经济”利益中排除出去。在这里,仍然存在有积累符号资本的空间。“对于作者、评论者、艺术经销商、出版商和剧院经理来说,唯一合法的积累存在于为自己命名、命一个著名的并被认可了的名字之中,存在于获得一种暗含了使物(与特征或姿态一起)或人(通过出版、展览等方式)神圣化的能力的‘神化’资本,并从中体现价值、获得利润之中。”[8]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费斯克指出,那些苛求学科的完美的人恰恰泄露了他们的传统身份、传统利益正在遭受大众生产力和辨识力威胁的秘密。因此,对大众文本的分析,当然不能站在这些传统批评家的立场上。恰恰相反,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大众文化分析的起点之一,是探究传统批评在大众文本中忽略或痛诋的是什么,并且关注那些完全被传统批评所忽略,或者,只是遭受传统批评斥责的文本”[1](p130)。也就是说,在费斯克看来,对大众文本的分析,应当从传统批评家所忽略或诟病的东西出发,从文本中寻找那些被“斥责的”、被视为“粗俗”的东西,从而发现“文本中吸引大众认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