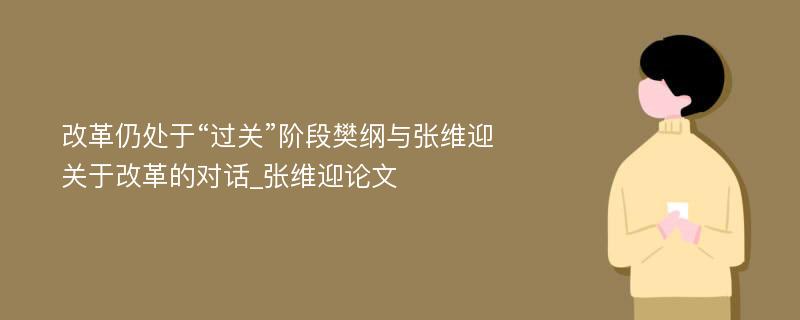
改革,仍处在“过大关”的阶段——樊纲、张维迎论说改革对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关论文,阶段论文,张维论文,樊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任重道远
樊纲:中国的改革改的不仅仅是1949年之后的30年里形成的东西,那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同样存在的转轨问题和体制问题。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那就是成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形成的东西——民主法治传统稀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难题。
转轨问题和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写文章、做报告、出书,都是为了缩短这个过程,为了政府能够更加理性、科学,企业家和老百姓头脑更加清楚、思想更加解放。
不做这些事情,中国要建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经济,恐怕需要100年,做了这些事情、做到最好,也还得30年甚至50年,我们这代人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这就是客观规律。但改革不是为了一代人,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张维迎:30年计划经济,时间虽然不像前苏联那么长,但30年交织了几代人,形成了从最基本的产权制度到文化道德观等一整套体系,借用王蒙的话,是一锅“坚硬的稀粥”。
为什么要建立计划体制,是为了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赶超。当时的人们相信以国家出面,用政府主导的形式,把所有的资源、甚至人的思想都集中起来,能够最快地实现工业化变革。
实践证明,它破坏了对个人的激励原则。当民众没有创业的积极性、社会因为缺乏竞争而死气沉沉时,政府由上而下推动工业化就无法持续。事实上,计划体制不但没有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反而为转型带来了更多的障碍。
回顾最近20多年走过的路,可以说改革的方向一直在探索之中。改革初期我们的想法只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一点市场条件,所有制问题就更没有提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咱们的体制没问题,只不过让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给耽误了,只要把能人放到计委,再引入计算机设备分析投入产出,计划经济就能运转。回头看去,当时最激进的改革派也没能把改革方向看得很清楚。
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先声
樊纲:建立市场经济的概念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有,但直到现在,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认识仍未统一,因为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我们可以看到,资源配置还在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向某些企业倾斜,产权改革在很多地方还是步履维艰,明明企业再不卖掉就一钱不值了,但由于一些人坚持,有些地方仍不敢轻举妄动。
张维迎:对企业家而言,如果旧观念仍居主导地位,个人财产的合法性就仍然成问题,对个人产权的保护也仍然成问题。在这种预期下,人们的行为就会扭曲、就容易短期化、就会考虑用金钱换取权力来保证安全。
樊纲: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了“两个凡是”;第二次突破了“姓社姓资”;1997年十五大前后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它仍在进行中。1997年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改善了不少,宪法也作了一些修改,但是思想还远没有彻底解放,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改革。
张维迎: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了太多的枷锁,并且对它们顶礼膜拜。好在改革以来每隔几年枷锁就要被砍掉几条,人们的思想随之解放一次。许多东西,我们觉得是创新、是理论上的飞跃,在国外学者看来都是常识。
改革的大方向不可逆转
樊纲: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不是探索怎么走,而是往哪儿走。方向不明确是中国改革的一大问题或者说是一大特点。
一方面,方向不明确总比明确一个错误的方向好;另一方面,这么多年的摸索,死胡同一个一个地走完后,南墙一堵一堵地撞遍后,改革方向正在逐步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产权改革,比如发展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致的,不可能人为创造出另外一套东西。
我是相信经济规律的,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中国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走。10年前,经济学家们关于产权改革的讨论根本没有人听,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与此同时,经济没有死、社会也没有乱嘛!
对未来,我一直比较乐观,因为我相信在见了黄河、撞了南墙之后,我们的政策会做出调整。只要大家不想中国垮掉、真心地希望国富民强,中国就会按经济规律办事,虽然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成本可能比较高。
张维迎:中国未来的走势已经比较明朗了,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前进的速度正在加快。我认为中国陷入动荡或者印度那样的制度性腐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非理性的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约束的封闭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像企业与企业一样,国与国之间也面临着竞争。国家和企业一样,面对竞争压力,要想生存就得讲效率,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激发民众积极性的体制。
竞争是改革的动力,它会使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入正确的轨道。没有竞争,无效率的体制就会一直锁定下去。
其实观念问题不简单是你信什么不信什么,可怕的是,观念可以变成斗争的工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这个企业应当卖掉,虽然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我依然会借此把你赶下台。所以,一个无效率制度的最可怕之处不在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它会创造出维护这一制度的人。这样就使这个制度改起来非常难。
没有份额的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改革
樊纲:历来如此,不仅中国。这不能只用经济学,而要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改革难就难在有人的处境会因此而变坏。尽管全社会总的利益增加后我们可以给那些受损失者补偿,使他们的利益从绝对量上不致下降。但在相对量上,权力失去了、地位失去下、相对的高薪失去了,而在一些人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但你改变不了既成的利益格局。官员就是不愿失去权力,国企职工就是不愿意下岗。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模式。
张维迎:旧的既得利益是确定的,变革带来的潜在利益可能非常大,但是它的受益者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旧利益格局的力量就要比追求新体制的力量强。因此,改革就一定要对既得利益进行“赎买”。
樊纲: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定的,就是一部分人可能会相对较少地从新体制受益。比如岁数较大的人,已经退休的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职工。
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由于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50岁以上的人生活水平比起过去仍然提高了一大截。而年轻人是认同改革、认同收入差距、认同市场的,因为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光明的前途。这也正是中国稳定的原因之一。
张维迎: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绝对水平,一个是相对水平。在效用函数中,我的效用不仅来源于我的收入,还来源于你的收入。
即使整体而言蛋糕变大了,每个人分得的那一块也变大了,但分配比例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打个比方,原来一共有100元钱,我拿90元,你拿10元;现在有1000元钱,我拿400元,你拿600元,对我来讲,收入是增加了几倍,但在感觉上会觉得还不如原来拿90元。
樊纲:所以,对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补偿,相对水平必然要下降。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把收入分配办法改变过来。
在传统体制下,只要是国有的,就能享受到优惠和特权。国企职工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是“铁饭碗”,厂长经理们无论企业盈亏都可以升迁,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变成按效率来配置资源、分配收入,能者多得、勤者多得。一切在过去不劳而得、少劳多得的人,一切自身效率低下、靠体制保护为生的企业和部门,都将是这场变革的受损者。如果还是我拿900元,你拿100元,那么改革就还没有完成。
张维迎:没有份额的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改革。补偿是另一回事,补偿实际上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如果补偿的结果是你的状况比以前变得更坏,那你肯定不会接受,这是交易成立的前提。
现在,我们的社会资源被大量浪费了,如果把资源交还民间,就会创造出更多财富。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对既得利益者进行补偿,以换取他们不至过多地反对把社会资源交出来。这就像俩口子离婚,一方不同意,另一方提出房子可以留给你,每月再给你若干生活费,这样婚就可以离成了。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改变了他们实现利益的方法,这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麻烦在于补偿标准怎么定,有权力的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强,此外还可以通过寻租自我补偿,普通职工就缺乏谈判能力,只能由上面来定,因此交易的公平性就成了问题。
樊纲:这就是我刚才没讲完的那层道理。我们这个制度所能做到的补偿,就是使你的绝对收入不下降。改革的难点,就是它不能使人人受益,这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两回事。生活水平大家都提高,即使下岗工人,生活水平也比20多年前好,这是绝对收入。但是,相对收入他们肯定大大下降了。因此,进行补偿可以减小改革阻力,但是无法消除阻力,因为你不可能在相对量上也作出补偿。
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
张维迎:权力的资本化、货币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旧体制下,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改革就是把这个金字塔型的单一利益结构变成利益主体多元化、选择多元化的多元利益结构。虽然我不当官,只要我富有,你能享受到的我都可以拥有。
但在现实中,一些有权的人总能通过操纵改革进程补偿自己,权力货币化后,他们获得的东西甚至比以前更多了。比如官商现象,官员寻租设租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能力范畴了。
你原来获得的利益有没有合法性,这一点暂且不论,我们讲改革,就一定要尊重既得利益。剧烈的变革,结果往往不如意。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历史没有飞跃,单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就需要很长时间。
樊纲:在现阶段,我们看到的官商又挣钱、又舍不得权,利用权力经商、利用经商谋权,挣钱归自己、亏损给国家。这就是典型的转轨期腐败。经济学家张五常多次提醒说,中国不能掉进“印度陷阱”,所谓“印度陷阱”,就是旧体制不变的同时又利用新体制牟利。改革理论越是不彻底,越是有观念上的障碍,越容易形成制度化的腐败。因此,本次思想解放最基本的是,先把产权关系理顺。
张维迎:如果产权改革能够完成,就不用担心制度化腐败了。否则,像印度那样,私人可以办企业,但举手投足都要政府官员批准,东西是你的,干什么得听我的,这不等于你有了财产权。
这种权力本来就不该他所有。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审批制的合法性。创业是人们天生的权利,就像说话一样。你能想象每说一句话都要经人审批的情形吗?如果把审批统统废除了,腐败至少减少50%,GDP至少增长30%。
现在政府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看来,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政府的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越过这一点,政府想有所作为,副作用就很难避免。
樊纲:政府行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已经取代国企改革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这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社会稳定最大的破坏因素,这一点是必须提出警告的。政府不在大小,而在于干什么。如果今后还是把精力放在抓经济管企业上,那一定会导致低效,导致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激化社会矛盾。
1993年,我写过一篇《市场中的政府》的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七八次,但是我仍然愿意在这里重复其中的主要观点,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提供法治、产权保护、市场秩序和基础设施。
(樊纲:1953生于北京,曾先后在河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哈佛大学等学校求学深造,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改革基金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吴堡,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Iees,199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