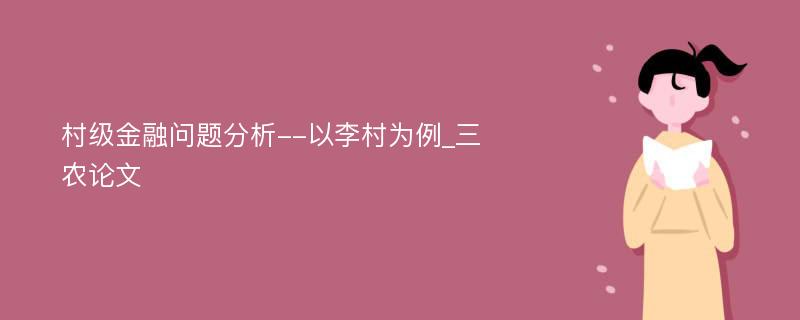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村论文,个案论文,村级论文,财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和调查情况
李村位于安徽省L县南端,D乡政府所在地,居民419户,人口1875人,面积947亩,下辖17个村民组。1999年有3个村民组划归D乡街道,因而实际人口为1538人,土地762亩,人均收入千元以下。改革开放为李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宏观制度背景,1983年李村的村民自治开始启动和运作。1998年11月4日。中央正式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明文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规定实行“村务公开”,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李村于1998年11月25日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选出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组(二者合一,成员由五人组成)。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的查询。”虽然改革开放和村民自治促进了这几年村里收人的大大增加,但村民并未从中得到多少实惠,村里也没有什么村办企业,村民负担并未减轻。因此村民一致要求民主理财组对1990年以后的村账进行清查,本着“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的思想,理财组成员接受了这一任务,于1998年12月30日至1999年2月1日对村里财务账目进行检查,结果发现问题颇多。从李村来看,村级财务管理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1.利用假票据,谎报支出,现金管理失控。如利用村民组修路,谎报3 500元;利用两个村民组外出旅游制造假票据一千多元。加上打白条、领借款未经批准的共达152807.00元。从1994—1997年村干部以假票据支出总计达79189.00元。这一数据,后经县农经委清查证实。现金管理失控最明显的就是,1997年村支书M卖了村部加工厂、彩印厂共10万多元,当时召开全村党员和队长会,订立了制度,决定将钱专款专用,但到年底,这笔钱却不知去向。
2.重复票据,账物不符。从上访材料中发现,仅1997年的票据中就含有从1989—1995年七年的票据款共6700多元。同时,还有村民建房费、计生罚款、公粮退库、救灾救济款等未入账,计164 848.00元。而村民意见最大的是修TH公路的土地补偿费和乡政府征收土地费却始终未能查清关于钱的收入、支出以及最终的去向。李村村民认为至少有20多万元未入账。但由于缺乏原始材料,土地补偿费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3.非生产性开支大。主要是各种不合理开支,尤其是每年的招待费村民反响很强烈。从调查的资料来看,李村从1992—1998年11月份就吃掉240 562.51元,其中1997年一年的招待费竟达70 000多元,超过了当年全村的村提留(65 625.00元,内含公积金、公益金)。不仅招待费额高,招待次数也频繁,一日多餐已是常见现象,1999年甚至有时一日五餐。根据理财组清查的结果,总共不正当开支达494188.34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1991-1998年李村财务收支情况表 单位:元
内容
年份 总收入 总收出 其中伙食费借款费 车费
1991 58695.5672419.32 2613.84 1926.90
1992 226086.48
204284.2736432.06 1817.00 1905.00
1993 112756.20
107601.1218041.50 3060.68 1850.00
1994至1996
633698.34
608860.3274803.58 6889.54 9313.00
1997 339726.76
441173.6568244.83 9401.19 5627.90
1998(到11
618620.65
5563396.07
43040.54 12737.591580.00
月20日止)
注:资料来源于李村民主理财组清查数据
4.私分公共物品问题突出。除了私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之外,村干部还私分救济款、土地占用款。根据村民代表反映,县农经委查出,从1995—1998年村干部私分财物共有七笔,私分烟酒、衣服、茶叶、购鱼款,共12 800元。根据D乡人民政府文件(1999年8月8日)精神,要求村委会将4 200元救济款及时发放到困难户手中,但事实上并没有兑现(根据当事人的证明)。显然,钱已被挪作他用。
5.私自加重农民负担(主要指私自提高税费),关于村民上缴的农业税的比例,根据国务院条例的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农民纯收入总额的5%;本年的标准则控制在上年度农民纯收入的3%以内;其中,村提留掌握在上年度农民纯收入的2%以内,乡统筹掌握在上年度农民人均收入的1%以内。但根据李村1997—1998年农户承担乡村税费集资提留汇总以及乡村送发给村民《1997—1998年度负担的决定》,全村两年人均多收94.88元。也就是说,事实上“农业税的征收制度,地方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乡村两级政权采取变通行为来决定上缴多少以及使用什么经费充当上缴税务。比如,在李村,既可以使用卖地款,也可以用其他费用来充当税费,以此代为缴税,并不问纳税人的个人责任。然而,集体结算并没有给村民带来实际利益,村民负担的税费反而因此增加,因为他们要负担村干部以高利贷形式垫付的税费。
6.村务不公开,操作不规范。据村民代表反映,自从1998年11月25日实行村务公开后,李村从未召开过村民代表会(仅仅为电话费、伙食费开过一次),也未订立任何规章制度,更未建立财务明细账,虽经监督组多次催促,村干部却置之不理,村公开栏形同虚设,列出的数字村民多不相信。
二、村级财务问题成因分析
第一,制度性失范是产生村级财务问题的根源。李村的财务问题,表面上屑于经济问题,实际上根源于农村现行的制度土壤。从我国宪法的规定来看,村民委员会是以村民为主体的自治组织,它不是国家一级基层政权。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并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是指导、帮助与被指导、被帮助的关系。但在现实的农村政治运作中,村委会扮演的实际上是双重角色。一方面,在法律层面上,村委会是自治组织,有权自主地管理本村的内外部事务;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运作实践中,村委会又是乡政府的派出机构,肩负着乡政府所委托的任务。有学者认为,村干部的地位类似胥吏,他们的任务就是“催粮、要钱、要命(计划生育)”。从治理结构看,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设计成相互监督的关系,乡村两级政权互补与支持,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形成乡村干部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从监督机制来看,民主理财小组并不具备真正的批准、查账和处理权力。从财税制度来看,集体结算、以支定收已成为乡村默认的变通行为。以李村为例,为抓好合同规定,该村规定各包片村干部按照农户合同上缴的95%交付,5%归村干各人。在1994—1997年村干部虚列支出的79189元中,其中村干5%包干奖励款59510元。税费收缴程序限制的缺乏,为乡村干部的违规操作提供了空间。从现行的土地制度来看,国家虽然明文规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制止土地租用权的频繁变更。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发包权掌握在村集体组织手中,作为个体农民没有资源的拥有权,只有集体才能征用土地和调整土地。实行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机制后,大多数村庄采取自行调整土地的办法,强化所有权,弱化承包权,从中渔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失去了原有意义上的资源合理配置功能。
第二,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产生不规范操作的内源动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利益导向为核心的社会动力系统。“物质利益至上”逐渐得到社会默认。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的确定,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利益分配作为一种动机在驱动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各领域地位和作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使农村社会各阶层经济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并促使他们寻求各自的经济利益的保护机制。农村社会交换的基本原则不再主要是传统乡土社会的人情原则,而变为经济原则。同时,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国家权力逐渐从农村收缩,乡村的权力结构发生着深刻的转换,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制度性空隙,为村委会的权力扩张留下了自由空间,也为他们利益的获得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村的权力精英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从而产生“寻租行为”。尤其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缺乏有效的监控情况下,权力精英的违法也往往更“合法”、更隐蔽和更有效率。
第三,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利益格局的分化,使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和基本准则逐渐变得不确定,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现实行为选择失去了合理的价值观依托。在确认市场价值的重要性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法的价值、行政伦理的价值,道德失范行为由此增生。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探讨
村级财务问题出现后,多数乡村采取村财乡监、村财乡管的新机制,目的是能使村级财务运行纳入规范的轨道。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村干部的违规行为,但实际上造成了国家与社区组织的功能错位。不论是从自身的性质还是从法律的规定来看,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只有拥有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承担村自治功能,为农村社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经济实体。实行村财乡管,必然会削弱村级经济的能力,那么村民自治就只是一纸空文。村财乡监实际上是把问题留到乡级层面,造成单方面的上级监督,而乡干部的经济行为却无人监督。实行了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虽然得到了减轻,但并不意味村级财务管理状况的相应好转。税费改革后,相比较县乡收入,村级收入减少,村组织作为经济实体的能力减弱,由此村民自治也难以获得正常的运转。因此,不论是实行村财乡管、还是费改税都不至于从根本上解决村级财务问题,关键在于要完善乡村制度、法德治村和加强监督。
第一,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和土地制度。从目前村民自治现状来看,制度设置上存在着责、权、利的分离。由于村委会具有行政化色彩,村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享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权力。村级政权通过控制村民的土地承包和调整的权力来实施自己的管理,并通过权力符号化抑制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村委会实际上已由村民的“代理人”转变为“承包人”。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理顺乡村两级各自权限,明确它们之间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还村委会以真正的社区面目和自治功能,形成政府力量与社区力量互动、功能互补、合作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良性运作机制。而这就需要“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制度的垄断”。同时,必须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流转体制应在严格按照法律的框架下进行,防止变通行为的发生,真正发挥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第二,法德治村。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乡村政治的现代化。完善对村级财务的管理、促进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必须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国家政策正是通过他们得以在基层贯彻执行的。乡村干部作为国家政策的直接推动者,其思想政治素质往往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实际成效,因此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他们的道德自律,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乡村民主政治也是乡村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道德自律应与法律他律相结合。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能仅靠精神的道德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这就是以法律来规范和约束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不仅要加强乡村的普法知识教育,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等深入广大人民群众,还要使乡政府依法行政和村庄依法自治同时并举,把它们的一切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
第三,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这是制度防腐的重点所在。“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多少关于民间监督渠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涉及公共领域的行政案件。因此,完善权力监督机制,首先要扩大民主监督渠道。除了加强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之外,还要发挥其它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监督的监督力量,尤其要充分发挥村民的监督作用,赋予村民以真正的监督权力,使监督权行之有效。从民主政治的本质内涵来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治政治,也就是说,权力的来源、授予、运作、更替、监督以及归宿都应落实到人民的意志上。从李村实践中可以看出,村民们不再停留在过去拥护政策和要求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层面,而是主动扮演了监督政府是否执行政策的角色,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