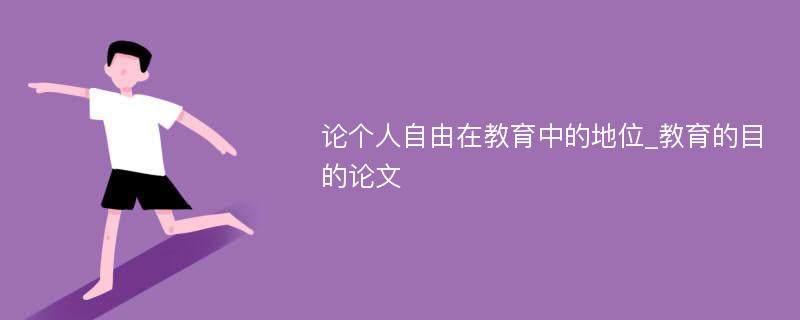
论个人自由在教化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2)11-0001-05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到,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冲突已成为我们时代理智上甚至道德上最主要的问题。(注:参照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M].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关于理性主义的衰微的论述还可参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有关思想,如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M],还可参照陈振明著《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我们在面对理性危机、批判理性主义教育时,隐含着一种抛弃“理性”的危险,这使得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怎么都行”的去价值的生存。我们的时代需要理性吗?如果我们的社会需要培育人的理性精神,需要培养理性的人,那么,教育将无法僭越运用理性于实践的个人自由。
一、教化成就理性
康德曾经说过,启蒙就是通过人们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而摆脱蒙昧和被监护的状态。这种蒙昧和被监护的状态一部分来自于人们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和决断。[1]尽管启蒙运动主张的普遍理性在今日受到深刻的反思,但是理性的运用是摆脱蒙昧和愚弄的方式是无法否认的。理性的自由、公开的运用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更是社会的理性精神的确立。正是理性的公开运用是个人摆脱愚弄和奴役、发展整体的人性的方式,所以社会如何平等地保障理性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社会在制度和社会治理上把社会成员当作理性的思想者和行动者的时候,当一个人作为一个理性的、自治的存在而不是隶属于任何精神监护权威的时候,人才能获得自主性,社会的理性精神才能真正地得到张扬,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才能实现伦理上的健康。
理性精神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任何形式的行动中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反思我们的动机和经验,提升我们实践的道德与智慧,使我们的行动合乎理性、合乎价值。理性促使个人有能力批判和质疑任何相遇的东西,使他能够反思自己的生活。我们通过理性获得一种经验的穿透力以及判断、质疑的勇气,从而可以克服任何的盲信和盲从,克服冲动和盲动,既制服外在的权力和暴力,又形成内在的自制和自治。
事实上,我们处在相信和沉迷于感觉的时代,理性成为一个在一定意义上的贬义词。(注:现代人和后现代人对理性的批判其实恰恰意味着对理性的把握的需要。理性的模糊其实意味着现代人缺乏把握理性的理性。这不能不说是理性的危机。人的存在的实践目的意味着理性依然是人们珍视的价值。理性的问题是我们存在的问题。理性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指导。它使实践真正成为价值目的的实现。)尽管如此,理性使生活的目的成为人对自身的生命承诺,它为人生提供一种约束性目的,构成我们正当行为的能力。理性是我们避免暴力威胁和权力压制的方式,因为理性的运用意味着理智和谦卑,意味着寻求合作和和谐,意味着负责和承当,也意味着平等和妥协。理性的人采取的是通过公开的讨论和辩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不能也不会用权势、暴力、恫吓和诱惑制服他人,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和观点,相反,理性的态度意味着一种平等交换意见和乐意向他人学习的态度,一种向他人承诺自己的道德责任的态度,一种承认不完美但寻求改进的态度。这些都是理性的运用所追求和所能实现的。理性主导着造福个人和造福社会的人生的实践。这难道不是教化所追求的吗?
因此,培养理性是教化的使命。教化通过创造理性得以发展自由和机会,培育个人的理性精神,教化因此意味着理性的启蒙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而发展理性精神。
现代教育把理性等同于工具性的认知智能,其结果就是训练人的工具职能,为现代技术化的社会制造“一个聪明的机器人”,人被当作技术社会的手段而训练,这样就扼杀了理性精神发展的机会。从根本上讲,教育着力于训练人对社会的适应性,怀疑、批判和创造的理性精神不再关注,因此,现代教育是反理性的。
教育对人的工具化其实意味着人之为人的精神特性的失去。运用理性的自由一旦被遏制,这必然地伴随着人类的道德智慧和精神品质的衰落,也伴随着人面对自然而惊奇地认识品质的蜕变。人越来越成为隶属于某种大机器上的无关紧要的小部件,我们并不能理性地分析我们的行动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我们失去了改造世界和自我改造的价值理性,也失去了洞察实践的合理性的精神动力,我们只是随波逐流,我们不再运用启蒙最骄傲的批判传统对生活实践进行反思,(注:福柯说:“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见福柯.什么是启蒙,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M].三联书店,1998.433~444.)我们最终失去了理性赋予我们的责任,从而也使社会公共生活失去了理性。也许,我们的理性的衰退,恰恰是造成精神理想和生活价值不可追问和失落的原因。
今天我们对教育重新提出理性的培养的任务,重新把教化看作是为了理性,其实是为了重新理解和解释人类一直所珍视的价值,在反思和批判中重新确立文化的理想,重新确立教育的崇高理想——引导人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
教育培育理性精神,目的在于让理性在人类事务中自由地发挥作用,这是社会公共生活健康和繁荣的关键。[2]
二、教化成就自我
教化在尊重个人理性的基础上促使人的精神的成长,它包含着精神培育的意蕴。在这个意义上,教化是成就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消除那些加之于个人的阻碍自我的反理性的东西,让人的自我充分地展现自我。
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变化”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新的存在。人的“变化”意味着人永远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事实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不断超越的过程——向着价值生存的意义超越。人总是走在成为人的路途上,他无法实现完善,但永远期待完善。
因此,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物”,不能被当作“物”来处理。把人当作“物”来处理,人就失去人之为人的自然(nature),人就是非人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种教育把人作为“物”来处理,它就彻底地否定了人的自我,因此必然会表现出型塑的权力意志,它可以违背学生的意志任意地对他们进行算度、驯服,它可以以某种理由对学生进行残酷的惩罚,它也可以以独断的权威和虚假的知识窒息人的理性。总之,它可以任意地像处置一件“物”一样地处置人。在我们的教育中,人是否正在成为非人?如果教育伴随着对学生自我的强制和压迫,伴随着痛苦和恐惧,伴随着体罚和叱责,伴随着灌输和愚弄,教育就是非人的。
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形成驾御自己和创造自己的能力,这本身就是存在的伦理性。我们作为自主性的创造者,处在社会场域中。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就是现实的自己,虽然我们感受到种种局限,但是我们试图追求自我的创造,这意味着在社会场域中我们试图达到自我的关注和自我的看管。这是人的理性精神对生活进行治理的表现。自我的看管是一种道德生活的反省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是一种对自我的构成。在这种反省实践中,我们运用自己的自由空间形成看管自我、创造自我的实践能力。所以,作为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我们的人生实践是以积极的方式构成自我的过程。
教化面对的是人的自由条件下的自我创造。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基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而改造我们的教育,我们必须建立和创造有利于个人自我创造的教育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必须成为一种帮助人实现自我创造的实践活动的艺术。只有成为这样一种技术或者艺术,教化培育理性的理想才能渗透在教育的每一项活动中。应该说,现代教育越来越让位于纯粹的工具性人格的固定的再生产模式,越来越让位于那些排斥自我创造的规训技术,教育的崇高的理念越来越排斥人的自我管理的伦理技术,结果是,具体的教育活动为权力控制的微观技术所把持,教育对工具人的生产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标准化,教育失去了教化的价值。
三、教化成就人的自由
尽管人生活在历史与文化的社群中,生活在社会场域中,但是,他的可能性是无法预定的,他的成长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可限量的,同时,人的自我的生成也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他是自主和自律的(autonomy)。每个人都是自我决断和选择的主体(humanagency)。因此,任何人为力量对人的干预和压制都是不正义的。
人具有两种自由: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在追求和享有消极的自由中,人的自我的创造免受任何外部人为强加的干预和约束,(注:伯林提出两种自由的概念,他支持对自由的否定性的规定,他认为,自由是免受他人强加的约束。)任何外在于个人的条件性因素,不论是政治治理,还是社会管理,不论是制定的法律,还是道德伦理规范,不论是教育机构,还是个人,都不能为了任何的原因强制、奴役、干预个人的自由,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自由有促进人性丰富和社会繁荣的价值,而且是为了自由之故,把任何的限制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这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只能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一是他人也能够享有平等的自由,二是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伤害他人。
消极的自由其实向教育提出了两个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应该受到什么合理的限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怎样保证学生个人自由?消极的自由同时也向个人的理性提出了问题:我的自由在怎样的条件下存在?我的自由的空间有多大?消极的自由向个人提出了理性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向个人承诺和保证了最大的发展和选择的空间。
在追求消极自由的同时,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的理想和人生的意义,这就是个人作为一个自主的能动者的主体的自由,也就是积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把个人在生活中的终极意义的追求和价值的自我实现交给了个人,只有他个人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而消极的自由为他的发展的自由的空间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保证,同时也把自由约束在自由的责任之内,既避免个人没有对生活的价值追求的愿望和想象力,缺乏个人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技术,又避免放任的我行我素,既减少任何外在的强制和干预,又实现责任的自治和合作的共存。
教育过程的存在意味着人的生成的历史性。教育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学会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的重要过程,这意味着教育过程是一个获得自由的过程。积极的自由说明,只有当一个人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积极、自主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时,他才是自由的,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去实现自我,他就是不自由的。[3]
因此,自由包含着实现自由的能力,包含着发展个性的能力。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而且也是现实的生活艺术、技术。毫无疑问,自由这种生活的艺术是在自由生活的历程中获得的,是在教化和自我教化中获得的。自由因而不仅仅是向个人的外在的条件提出的价值诉求,也是向自我提出了实现自由的内在能力的要求。自由意味着既要去除外在的阻碍自我实现的东西,又要驱除内在的障碍。自我的欺骗、自甘情愿的奴化、自我认识的欠缺、自我控制的缺乏都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的障碍。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存在有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变化过程。自由是人的生活的根本的诉求,也是教化根本的诉求。在去除外在和内在的阻碍中学会自由,实现自由,这是教化和自我教化的价值承当。
教化能够帮助人们形成追求自由的勇气和能力,帮助人在自我的价值实现中进行自由的实践并获得实践自由的能力。一个人在生活的复杂的历程中,可能有种种的外在和内在的原因使他缺乏自我价值实现的动力,可能存在甘愿的自我放弃,可能发生自我蒙蔽和自我麻痹的情况,教化不就是在帮助人的自我超越中去除这些东西吗?假如一种教育以某种方式误导人、愚弄人,使人产生自我的蒙蔽;假如一种教育以某种方式摧毁人的自尊,使人自觉地放弃自己;假如一种教育以某种方式强制人对生活和道德价值的追求,使人不能自治;假如一种教育仅仅为了满足一个人当下或未来的欲望,使人不能自我控制;假如一种教育阻碍人的选择的判断;假如一种教育限制人的表达的权利;假如一种教育灌输着既定的东西,取消了独立的思考,那么,这种教育就会毁灭人的内在的实现自由的能力以及在自由的实践中学习自由、实现自由的机会。
教化帮助人发展自由的能力,其实包含着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限制和破坏人的消极自由,也就是不能以不自由的方式对待人,如限制人的表达权利,进行全景的监督,要求绝对的服从等等。我们的教育其实倾向于一种对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控制,这种控制为人指定了一种给定的目标和方向,也给人限定了特定的行动和特定的言说。这种观念下的教育设定了一种虚妄的想法,那就是:生活的理想和价值应该是统一的,每个人都应该服从统一的目标、统一的领导。我们的教育不正是在这种观念中控制我们的儿童吗?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被限制了表达的权利,如果我们没有确定自己的生活目的和目标的自主,如果我们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我们可能只是在被控制、被训练中被动地活着。在这种生活状态中,我们很难学会判断,很难学会自由,因而也就没有实践自由的机会,我们就不会获得自由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形成丰富多样的个性。
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人是生活在社会群体中,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了社会的目的而强制人、奴役人,剥夺人的自由,让人成为机构和群体的隶属。如果一种机构或者社会以某种理由强制人们按照某种规定好的统一的目标行动,强制人们接受某种划定范围的知识,这种社会就是一种由少数人把持思想权力的社会,就是排斥人们独立运用理性的权利,排斥人们的批判和反思的自由,限制人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其实,这样的社会必须依靠教育改变人们的意识,使人们相信那种统一的目标的唯一正确性。因此,教育可能通过灌输和规训塑造社会成员的思想的“一体化”和精神的“一致性”。为此,就要限制个人的选择,修剪人们个性的多样性,树立一种统一的模式。在这种教育中,服从高于自主,听话高于思想,接受高于创造,一致高于独立。显而易见,这种教育不关怀个人的自我实现。
自由的意义可能向我们的教育提出了一种关怀的要求,即关怀个人的重要目的的自我实现。尽管现实中的教育不一定如此,但这是教育存在的首要的理由。对于教育中的人而言,自由就是能够自主地选择和实现自己的重要的生活目标。在成长和生活中,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和选择,能够由我们自己本身来决定。我们每个人希望成为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在的逼迫和诱惑,也不是出自内在的蒙蔽和盲动。每个人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的人。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绝对条件。[4]
如果教育中的人去失了获得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自由,他们没有锻炼自己的理性选择的机会,他们就不可能形成运用自由的能力,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对自己负责,也就不可能对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负责,也不可能与他人形成一种社会共同生活的道德责任的共契。他有可能把他之外的一切都看作是与他对立的东西,处处与他相异的、压制他的东西。因此,教育中的人的自主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他们的自由的重要的需要,也是理性精神得以发展的需要。成长和发展需要自由,如若没有自由,发展就是被纳入了特定的框架中的,就是排斥了人的理性的他治的过程。
倘若教育认为,处在发展中的人理性的不成熟和自制能力的缺乏无法使他们把握真正的目标,无法理解“真实”的自我,无法做出真正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教育和学校可以为他们设定真理性的目标,可以为他们做出走向幸福的正确选择,并且为了使他们能够追随认定的“真理”和“幸福”,教育可以强迫他们,监视他们,那么教育可能是以“真理”和“幸福”的名义行使着为着他种目的的霸权,可能为教育中的专制主义留下了后路。尽管教育把这样做看作是获得“自由”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教育却使自由面临着威胁。
如果不承认我们每个人在教育中具有自我实现和发展的自由,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任何形式的自由,也就不可能学会运用自由,也就不知道我们的自由具有什么样的界限。同时我们也将不可能要求教育成为我们运用自由的必要的环境和条件。教育成为一种人们运用自由、学会自由的必要的条件的前提就是我们每个人具有的自我发展的自由。
教育对每个人的自我发展的关怀其实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教化,一种对自由的实践和操作,因此教育与自由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理念中,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实践中,也就是在自由中培养我们运用自由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才能摆脱强制的塑造,成为我们运用自由、学会自由的必要的环境。这意味着教育作为具体的自由实践的形式,它必须成为我们实践自由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实践自由的“操作”,它不仅仅免除外在的强制和压抑,同时也关怀我们的价值的自我实现,在其中,我们不仅仅学会能做什么的自由,而且也学会不能做什么的自由。
教育作为具体的学习自由、实践自由的机会,本身应该是自由的保障条件。自由联系于一种追求自由的具体的教育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自由是教育的具体的活动所建构的,也就是借助于教育的制度的安排,把权利归于每一个学生。自由不是教师的馈赠,也不是教育的恩赐,而是教育必须保障的权利,是必须实现的一种教育状态。我们强调自由,是因为自由不仅是通过政治社会而保障的权利,而且是必须通过教育而实现的每个人的一种存在状态,是教育所追求、所实现的每个人发展的状态。在这里,自由是一种教育价值,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一种排除了支配、依附和控制的教育方式。教育是人的发展的条件,只有在教育保障和形成了人的自由状态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教育保障自由,是因为教育只有排除了干预、控制和奴役状态,人才能获得个性的自由发展。这就意味着自由不是一种单纯的天赋的自然权利,而是一个人走向可能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义务,也就是人之为人的责任。奴役状态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受制于外在于他自己的任何独断的意志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缺乏任何受到保护的自由身份。如在我们的教育中,人是一个被塑造者,或者是被改造者,他的行为受到学校或者教师等教育权利关系的全程监督,他不是作为自由身份的人生活在教育中,他随时可能受到监视、训责、干预和惩罚。这就会使本来稚嫩的孩子处于一种无法受到正常保护的脆弱状态,可能在强势之下只能顺从、畏惧和屈服,这样个人只能处于一种他治的状态。
对于教育而言,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不仅在教育制度上确定教育者的自由身份,同时必须要实现权利的平等,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享有平等的发展的权利,才能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不受他人的歧视和任意处置的自由。所以,教育必须要创造权利平等的条件,也就是创造自由得以实现的教育条件,比如丰富的教育机会、资源和目标可以保障每个儿童在成长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支持性的资源,可以具有自治的目标,从而避免在竞争机会和资源中的失败,可以寻求自我价值得以展示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也是教育必须创造的人的发展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