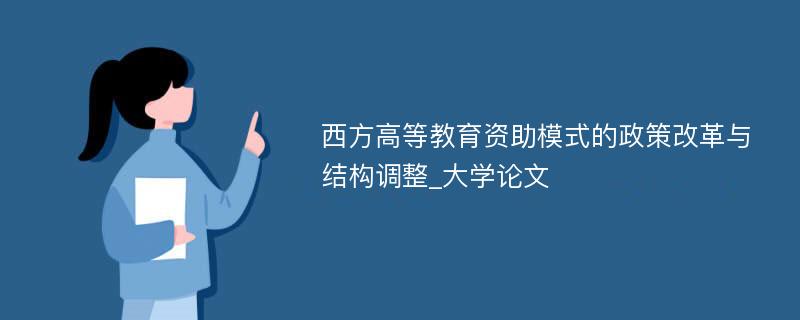
西方高等教育的政策变革与经费模式的结构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经费论文,模式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2)05-0091-05
一、政策变革:西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表现
政策往往是一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集体选择和公共决策的结果,因此政策的内容及其价值倾向能有效地折射出各方利益群体的政治主张及其力量对比,也能准确地反映出被决策事务的发展趋向和变革可能。从政策的角度研究西方高等教育,既有助于把握西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状况,更有益于深入认识西方社会转型对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冲击。
在西方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体系中,“效率”、“责任”逐渐成为其核心追求,“绩效指标”、“战略规划”、“使命”、“质量控制”、“效率”等逐渐成为其工作的重要手段[1]。这种价值偏好集中表现在院校关系的调整以及大学与工业、政府之间关系的变革中。
1.引进院校竞争机制
引进院校竞争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仍然存在不良的“马太效应”:拥有较大自治、自由权力的高等教育系统顶层部分在资源、声望和地位分配方面多能锦上添花,而对于一般性大学和学院来说,甚少雪中送炭。这种状况,既造成了院校待遇上的不公平,也不利于在普通大学与尖子大学之间开展有益的竞争[2]。
强调院校竞争机制的国家主要有两类:一为实行“双重制”高等教育体制的国家,如英、澳等;二为传统中重政府集权、轻市场竞争的国家,如法、德等。就英国而言,虽然在建立“双重制”时承认多科技术学院在社会地位、教师工资、资源分配,特别是学位授予权力等方面与大学平等,但事实上的结果是,大学和学院之间的等级区分制度日益严重,尖子与普通之间的等级樊篱日益明显。于是澳大利亚和英国先后在1988年、1991年宣布废弃“双重制”,并在此后的改革中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市场机制的偏好[3]。这在希拉·斯洛特等人看来,“就是一种通过允许声誉较低的多科技术学院与大学之间展开公开竞争,从而降低大学太高成本的做法。借助于院校之间的竞争,中学后教育部门就能够在降低、削减而不是提高大学的丰富资源基础、而又不为多科技术学院提供与大学一样多资源的情况下,为教育系统的扩张提供财政支持、满足日益增长的入学要求。”[4]在原联邦德国,象征着引进院校竞争机制的重大事件是,《明镜》杂志社和西德比勒菲尔德大学民意测验研究所首次模仿美、英,联合发布一份调查报告,对大学和学科进行了必将引发激烈竞争的“名次”排序。
2.强化大学与工业的关系
为了强化大学的“责任”思想,西方高等教育主要做出了两种政策变革。一是大力鼓励大学—工业之间的体制化联系,积极构建多种多样的组织机构和合作制度。在美国,建立了多种研究、咨询和政策建议机构,如商业-高等教育论坛,大学-工业研究圆桌会议,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等。通过这些机构,大学从工业界及其他非官方机构所取得的资助已从80/81学年的42亿美元增加到88/89学年的89亿美元。因此有人评论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教育改革旗手如果说是康南特、里可佛等军政界人物的话,在80年代则是企业界的巨子和大型基金会。西欧仿效北美模式,于1988年建立了欧洲大学—企业论坛。在英国,由于撒切尔政府的支持,拥有深厚传统的学术专业文化和院校自治理念遭遇了不断强劲的创业文化的冲击,朱里特委员会更是强化了这种理念;此外,在工商业界的推动下,还建立了工业与高等教育理事会,并创办了其政策性刊物《走向合作》[5]。
其次是加大立法力度,规范、支持大学—工业的合作关系。以英国为例。1987年白皮书、1988年教育法都对上述举动给予了合法化肯定。改革前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全部17名委员中,来自实业界的仅2人,但新成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UFC)15名委员中,却有实业家5人[6]。人数比例的如此变化,特别引人注目。
美国自1980年起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鼓励大学与工业间的技术转让活动。较有影响的有:1980年的史蒂文森—韦德勒技术创新法案和彭—德勒法案、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1984年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防拨款法案、技术再投资法案,等等[7]。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彭—德勒法案。受其鼓励,美国研究经费排名前100名的大学所获专利数,在1979-1984年间、1984-1989年间各翻了一番;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的各会员大学,通过转让专利所获得的收入自1991年的18.3亿美元增长到了1994年的31.8亿美元[8]。由此可见通过立法推进大学—工业合作关系的强大功效。
3.改革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实行财政紧缩、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包揽是西方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调整的首要政策。在80年代的改革之前,政府是大学的最大赞助者,英国大学90%以上的经费由政府提供。这种状况在财政危机时期给政府以难以承受之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西方政府开始转变角色,由经费上的无偿赞助者转变为大学的顾客之一。斯坎内尔发现,纽约州在1982-1992年间,用于监管犯人的费用上涨了270%,但用于高等教育开支的费用却下降了8%[9]。“在1979年撒切尔上台的三天内,大学预算在一夜之间就被削减了1亿英磅。在1980-1984年间,政府划拨给UGC的经费又锐减了17%。”[10]对此,有观点认为它与其说是教育财政开支的简单紧缩,倒不如说是对教育经费资源的重新分配,分配的方式有专业重组、战略规划以及不断增加兼职教师等,其结果是在专业设置、学额分配、师资建设等方面不断强化了市场化和实用主义倾向[11]。
扩大公立大学的自主权和自由度、提高大学的市场适应能力是西方高等教育政策变革的突出特征。政府财政资助缩减所造成的大学收入“真空”迫使大学通过与工业的创业性接触来弥补,为此需要政府的放权。这在日本表现为,国立大学正在全力推行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国立大学的性质,并由国家办学转向法人办学,使大学自主管理和有效运营其内部事务[12]。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瑞典公立大学恰尔默斯早在1994年就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退出”国家控制的高等教育体系,凭借它同教育部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改制成为一所独立的“基金制”大学,由大学自身组建的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从而以一种近乎私立的姿态,享有着非常大的自由权限[13]。
加强政府的监控力度、贯彻政府的质量意图是高等教育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监控方式有:(1)立法。撒切尔政府根据克罗哈姆报告的建议,以《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为蓝图,推动制订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首开用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调整大学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先例。(2)运用经济杠杆。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构建准市场机制,并影响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模式。(3)改组高等教育的管理机构。在英国,UGC于1989年被改造为UFC,不久,UFC又演变为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对此,彼德士评价道,“新成立的机构并不如同前者一样是大学同政府之间关系的中间缓冲器,它更有可能利用合同契约关系对大学进行拨款。”斯科特则认为,这种变化将产生两种影响,“首先,大学在接受政府拨款时将受到更为严密的指挥和绩效评价,其次,大学将发挥更为巨大的首创精神以竞标那些分别指定用途的政府资助。”[14](4)强调国家质量标准。一份对OECD国家教育评价的分析指出,政府的质量评价指标已由简单地关注教育成本、入学人数等扩充到教学组织形式、教育决策和政策分析、教育成就以及青年人就业等诸多内容,从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从教育背景到教育教学过程再到教育结果”的完整评价体系和质量监控标准。[15]
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种“由产业牵头、政府主持、大学提供服务的产-官-学合作关系”[16]——这种新型三角互动关系被西方学者称为“三重螺旋”[17],从而标志着大学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已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表明西方高等教育的政策重点由注重民主、平等向崇拜效率、责任的全新转移。
二、经费模式的结构性调整:西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产物
高等教育政策的总体性变革,引起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层次主体(从院校机构到教师个体)各类型行为(从教学到科研、乃至社会服务)的持续改革和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于并集中地表现在高等教育经费模式的结构性调整上。具体而言,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不但导致了高等教育系统经费来源结构的改组,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的经费支出模式。以下仅就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模式的变化进行概要性探索。
伯顿·克拉克认为,当今西方高等教育的经费模式已演化成由三种渠道所构成的复合型模式,它们分别是:来自政府的大学资助和高等教育预算,来自各种研究委员会的科研补助和合同经费,以及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经费——统称为“第三渠道”[18]。值得注意的是,不但第三渠道经费作为一种新现象在公立大学中首次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原有的第一、二渠道经费在划拨模式和性质定位上也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政府教育拨款模式的变革
变革之一是拨款日益以大学的运作绩效为依据。传统的预算拨款模式有二,一为累进式拨款,政府根据前一年的开支情况,对大学的日常经费进行预算;二是按公式拨款,即政府根据大学的招生人数、毕业率和按时获得学位的人数等分配公共资源。上述二种都属于以需要为基础的拨款方式。与此有着本质性差别的是第三种预算、拨款方式,它以绩效为基础。这种方式往往根据大学过去在某些方面的突出表现而划拨特别款项,并指定其专门用途。在按需拨款方式之外增加以绩效为基础的拨款方式,其实是政府日益关注大学经费的使用效率、关心大学的尽责状况的逻辑结果,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趋势与高等教育公共预算有限等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19]
变革之二是政府拨款机制日益注重以竞争为原则。英国的大学基金委员会曾提出这样的设想:首先由成本核算中心计算出每一个全日制学生所需教学费用的最高价格,然后要求各大学副校长根据指导价格进行报价。大学基金委员会希望各大学的报价既是“经济的”,同时相对于其他大学而言又是“竞争性的”。尽管这种指导价格公式的拨款模式因遭到多方人士的怀疑、责难和批评而没有得到彻底推行,但它的提出在较大程度上冲击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拨款理念,为此后的改革打下了必要的基础。[20]
第三,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对拨款与贷款之间的比例分配出现了逆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联邦学生资助对拨款、贷款比例的分配分别为76%、20%,10年之后却变成了29%、67%。这种逆转随后又得到了《1992年高等教育法》的认可[21]。当这种转变与院校收费日益攀升、家庭收入停滞不前等情况交织在一起时,列维斯认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及其家庭将日益艰难[22]。
2.政府研究经费划拨模式的变化
首先,大学争取研究经费的竞争性日益增强,准市场机制日益完善。研究经费的多少、研究能力的强弱与院校、与学术人员本身在学术系统中的等级地位、荣誉、声望等直接挂钩。改革之前的大学研究经费主要集中在居于高等教育系统顶层的少数尖子大学之中,使用效益很难评价。英国政府自1991年起,改变科研拨款的双重资助制度,抛弃大学可以从大学基金委员会、各类科学研究委员会得到双重资助而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只能从科学研究委员会中竞争科研经费的不公平做法,按照“多元性、竞争性、选择性、责任性”等原则构建科研拨款的新结构。也正是这种竞争性分配方式的出现,才使得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学院在与大学合并之后能有机会与大学同时进入竞争研究经费的行列之中。
第二,研究经费的划拨、管理倾向于以合同契约为纽带。早在1975年,法国高教司司长盖尔莫纳就提出了大学经费分配的合同制设想,可惜因政府改组而无果;1983年教育部改变了科研经费的发放制度,由一年一拨改为4年一个合同;真正大型的改革发生在1988年。再次上台的社会党决心全面推行以合同形式分配经费的制度,合同政策“建立在二个原则之上,赋予学校自治以真实内容;促进全国高等教育力量的协调一致。”合同制虽然在90年代中叶曾一度受挫,但随着1988年的经济复苏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下,这项政策尝试达到了新的高潮。故被人称为“没有改革的革新”——恰好与以往那些“没有革新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照[23]。
第三,积极淡化由政府研究经费资助所得科研成果的公共性质,加快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进程。政府鼓励某些由公共经费资助的科研成果有条件地投放到市场中去。美国1980年通过的彭—德勒法案,就允许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受联邦财政资助的研究机构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专利,并将专利的特许使用权转让给私营企业等非政府团体。法案在三个方面为这种技术转让活动、为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便利:直接免除以前那种必须通过与联邦政府的冗长谈判才能进行技术转让的麻烦;支持大学与工业之间谈判转让专利使用权的活动;对于未获得专利权的将限制其商业化应用。因此这个法案不但使美国大学的“赢利”权力合法化,而且还允许大学和小企业拥有保留由联邦研究发展经费资助的科研成果的使用权。[24]
3.第三渠道经费的拓展
伯顿·克拉克认为,“第三渠道”经费由三种资金构成:一是来源于其他政府部门的资金,既包括其他相同级别的部门(如农业部、林业部、科技部等)资金,也包括其他层次政府部门(如地区、市级政府部门等)的资金;二是来源于私人组织的资金,这些私人组织包括:其他产业部门所属的各种公司、鼓励开展继续教育的行业协会以及提供各种专项资金和无偿援助的慈善基金会等;三是来源于大学自身的创收,包括基金和投资的收入、大学校园服务机构(如医院、书店等)所得、学生的学费和生活开支、校友筹款、大学和教职工共享的知识产权专利税等[25]。
近30年来,欧美等国大学第三渠道收入得到了持续地增加。比如,英国的沃里克大学、荷兰的特文特大学、苏格兰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瑞典的恰尔默斯大学、芬兰的约恩苏大学等在1995年通过第三渠道所得到的创收性收入竟分别占其大学总收入的47%、21%、51%、20%、27%[26]。
第三渠道经费是高等教育经费模式市场化的集中表现,表明了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的多元化倾向。除了少部分规定了特殊用途的份额之外,这笔经费中的大部分可供大学自由使用于改善教学设施、添置科研设备,甚至还可以用于大学的经常费开支。而且,这笔经费常常得到了官方的保护。在德国,即使是大学通过一些显而易见的直接市场行为所获得的收入,比如“由出租房屋,使用运动场和语音室及科学文献收取的费用,由为第三者服务(如使用学校的车间、照相室、图书装订车间、印刷厂、复印车间、出售大学所有的出版物),在规定要收取费用的进修班交纳的学费以及大学人员从事副业而得到的收入,都应该不加减少地流入大学。”[27]第三渠道经费在大学经费构成中的大幅上升及其可供灵活处理的属性,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学术人员的行为方式——这就是资源依赖理论所提出的“10%法则”即在不破坏社会地位和声望系统的情况下,处于边缘性地位的一小部分金钱会很大地改变教师的行为[28]。
诚然,上述改革和发展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传统生存方式和专业性文化理念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冲击,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些改革和发展使得西方的大学在政府拨款锐减、社会要求大学尽责的呼声日益强烈的情况下,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甚至还使某些大学得到了不断发展、日益繁荣的可能。所有这一切,值得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感谢导师王承绪先生在本文写作、修改过程中所给予的不倦教诲和细心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