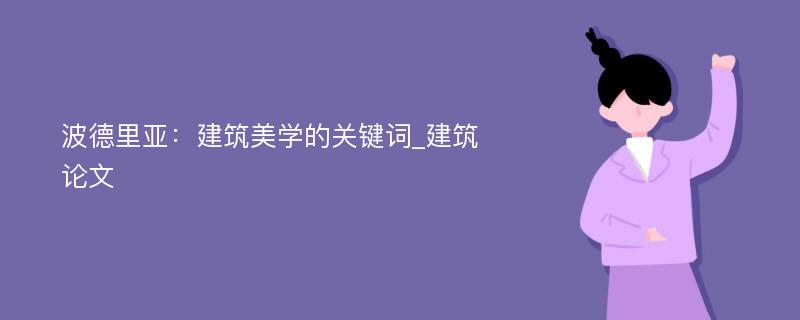
鲍德里亚:建筑美学关键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美学论文,关键词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2-0033-07
鲍德里亚的建筑(或城市空间)美学思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通过大量论文(和著作)①直接地深入地介入了建筑美学问题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体系与我们将要论及的这些建筑美学关键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唯有理解了这些关键的概念,才能对他的思想获得深刻而全面的把握。比如他最重要的仿真理论、诱惑理论等,如果单纯从论述这些理论的专著本身入手,要想进入鲍德里亚理论的堂奥,是相当困难的。
鲍德里亚创立的建筑美学概念多而且杂,对有些概念,鲍德里亚自己也语焉不详,这里只能撮其要者,略加申论。
空间与本源性
鲍德里亚所谓的空间,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当他从实存论的视角谈论空间的时候,空间就是作为建筑和城市的第一现场的空间。鲍德里亚在同法国著名建筑师诺维尔对话时,曾提议:“让我们从空间开始,这毕竟是建筑的第一现场;让我们从空间的本源性(radicality)开始,即从空无(void)开始。”②但是,当他提议要从空间的本源性考量空间的时候,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空间还原到了最原初的自然性,还原到一种“空无”空间(empty),“虚空的空间”(void),“什么都没有的空白”(nothingness)空间。
如果说空间的本源性就是空间的原始自然性,或宇宙的未被触动的状态,未被人类搅动的状态,那么,在鲍德里亚这里,建筑的本源性则是建筑的初始性,或者说原始性,即劳吉尔所还原的最原始的建筑原型——有点类似于树屋的棚屋原型。
鲍德里亚的本源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在回归到建筑最原始的现场的同时,回归到前建筑理论和前艺术理论状态,也就是说铲除我们所执着的一切建筑的和艺术的甚至美学的历史的观念,进入一种绝对的、无任何理论框框限制的“自动写作”,或“反建筑”(反现存的平庸建筑观)写作,使建筑真正回到鲍德里亚所称许的那种“无意识的本源性”——那种并非刻意让人凝视而是只为着自身的生活或生存而自在地建造的“自发性”。鲍德里亚说:
有一种建筑历经千年,至今犹存,却并无任何“建筑的”概念。人们自发地、随心所欲地设计并营造其居住环境,他们以这种方式创造空间,全然不是为了被人凝视。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建筑学价值,甚至更准确地说,也没有任何美学价值可言。甚至当下,我喜欢的一些城市,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城市就包含这样一些因素:你在这些城市转来转去,却绝不会考虑任何有关建筑理论的问题。你来这里就如同在沙漠里旅游一样,你不会沉迷于任何关于艺术和艺术史、美学和建筑这类精雅的观念之中。应该承认,这些建筑是为了多种目的而建造的,但是,当我们与它们邂逅时,它们就像是一些纯粹的事件和纯粹的物体:它们使我们重新回到了空间的原初现场。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些反建筑的建筑……③
鲍德里亚的话语通常包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修辞风格。要么是明确的对照,如真实与虚假的对照;要么是隐晦的比较,言在此而意在彼,声东击西。当鲍德里亚在强调空间和建筑的原初性和本源性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当今这种没有足够的“空”和“无”的拥挤的城市空间的讽刺,和对城市缺乏“消失”感的炫耀性的“垂直秀”建筑的批判。
鲍德里亚对美国圣巴巴拉城市空间的评价,可以作为他固执地要把我们拉回到空间的原初现场的注脚:
在圣巴巴拉芳香四溢的山坡上,所有别墅都像殡仪馆。在栀子花和桉树之间,在植物的多样性和人种的单一性之间,是乌托邦之梦成为现实的悲剧……所有的住宅都具有坟墓的特征,但是,在这里,伪造的宁静是彻底的。绿色植物可耻地四处蔓延,像极了死亡的纠缠。落地窗玻璃看起来就像白雪公主的玻璃棺材,苍白矮小的花丛像得了硬化症似的延伸开来,房屋里面、下面、四周是数不胜数的科技小物件,如同急救室成簇的输液管,电视机、立体音响、录像机保障了与外界的交流、小汽车(或多辆小汽车)保障了与殡仪馆式的购物中心,即超市的连接,最后还有妻子和孩子,表征着辉煌和成功……这里的一切证明,死亡最终找到了它的理想家园。④
这里的空间、建筑、环境,包括室内布局,一切看上去都很美,但是,在鲍德里亚看来,却已经完全失去了空间和建筑应有的本真性和原初性。
其结果就是,城市空间变成了一种富有反讽性和悲剧性的矛盾空间:居住空间变成了死亡空间,而死亡空间反而成了最理想的居住和生活空间。
鲍德里亚就曾不无反讽地评价欧美现代城市说:
如果说墓地不存在了,那是因为现代城市在整体上承担着墓地的功能:现代城市是死亡之城,死人之城。如果说实用性大都市是全部文化的完成形式,那么很简单,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死亡的文化。⑤
又说:
目前的低租金住房看上去很像墓地,而墓地则很正常地呈现出住房的形式(尼斯等地)。反过来,令人感叹的是,在美国的都市,有时也在法国的都市,传统的墓地构成城市贫民窟中惟一的绿地和空地。死人的空间成为城市中惟一的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意味深长地说明了现代城市公墓的价值颠倒。在芝加哥,孩子在公墓玩耍,自行车手在公墓骑车,情人在公墓拥抱。哪个建筑师敢从目前城市布局的这一真理中获取灵感来根据墓地、空地和“被诅咒”的空间设计一座城市呢?这将真的成为建筑学的死亡。⑥
鲍德里亚借用并发挥了巴塔耶的“过剩”观念,认为当代城市的人造空间已经过剩,而且从个体建筑物来说,尺度也大都过于夸张,大大超越了正常的需求。正是由于这种过度,城市空间走向了人类的反面。
与此同时,在虚拟的和心理的意义上,鲍德里亚又定义了另外两种空间:一是代码空间,一是错觉空间。这两种空间也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化了实体空间所存在的问题。
代码空间是另一种过剩,是信息的过剩。在这样一种过剩之中,我们进入了所谓数字化的符号(代码)空间。在代码空间,一方面我们利用符号——差异的符号来操作,一方面我们又被这些符号——差异的符号所操纵。这里有的是“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⑦,有的是虚拟,仿真,和过量的符号增值。
在看似先进的数字技术时代,在看似美妙高效的代码空间中,我们却遭遇了技术对人类自身的反讽。在无数被编码了的预定选择中,我们却被剥夺了选择权;在海量的真实信息中,我们却无法筛选出需要的信息。即使像全民公决这样严肃而重大的事件,在当代整个交流系统都从语言的复杂句法结构过渡到了问/答这种简单的二元信号系统和不断测试的系统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了仿真的完美形式:答案是从问题中归纳出来的,它事先就被设计好了。因此,“全民公决从来都只是最后通牒:这是单向性问题,它恰巧不再是发问,而是立即强加一种意义,循环在这里一下子就完成了。每个信息都是一种裁决,例如来自民意调查统计的信息”。⑧也就是说,在仿真的时代,或者说,在仿真的境遇中,测试和全民公决只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狡猾的民主骗局和政治表演,它其实只是装着向测试者发问,因为它已经预先设计和安排好了答案。它需要的是一种程序——即经常用作民主遁词的所谓程序公正——通过这种程序来加强这一政治策略的完满性和意义。⑨
代码空间在另一种意义上,在科技和智能意义上,把人类和真实的生活隔绝开来。代码空间使人类进入了“信息越来越多,而真实越来越少”的尴尬境遇。
在这里,鲍德里亚证实了意义过剩、技术过剩是如何将人类推进了仿真的深渊。
而在论及错觉空间时,鲍德里亚看到的却不再是一种过剩,而是一种不足,一种“不及”,一种缺乏——人们在城市空间中所感到的一种诗意的缺乏,一种审美心理体验的缺失。当代城市给人的印象不是壅塞,就是满溢。因此鲍德里亚希望城市建设更多地使用减法,甚至缺损法,消失法,错视法。城市和建筑设计要更多些空灵,唯有运用空灵,城市空间才会富有诗意,才能兑现诱惑效能。关于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论述,此处不赘。
秘密与诱惑
鲍德里亚认为,真实的有品味的空间或建筑,是那种潜藏着秘密的空间或建筑。因为有秘密才能诱惑。诱惑是空间或建筑的本质效能。
秘密是空间或建筑的深度模式,是建筑师在空间中嵌入的谜。这个谜往往在动与静、虚与实、即与离的变幻之中,发散出奇异的吸引力。
空间(建筑)必须保持其秘密,而要保持秘密,就不能一味地强调其示现功能,甚至眩惑或炫耀功能。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种做派,只能算是单纯体现“秀”(show)和“注意”(attention)的动作,是一种粗野的广告效能,与城市美学无关。
那些炫耀性的所谓“注意性”建筑之所以被视为令人厌恶的空间暴力,是因为它粗野地挤占了城市应有的审美空间,而且是以直挺挺的、沉默的、僵硬的冷面,傲慢地拒绝并且连根拔除了观者对话的冲动。
鲍德里亚说:
我是在审美化意义上讲到文化问题,我反对这种审美化,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损失:目标的丧失,秘密的丧失。秘密是艺术作品和创新性成果所蕴含的东西,是比美学还要重要的东西。秘密不能以审美的方式被揭破。⑩
因此,赤裸裸的表现,透明的展示,甚至卖弄,都是与秘密——从而也是与诱惑——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秘密不能被完全遮蔽,完全遮蔽的秘密是已死的硬化的秘密、无法激活的秘密。秘密也不能被完全揭破或解密。唯有处于半透明之中的秘密,是真正具有审美杀伤力的秘密,有艺术诱惑性的秘密。
秘密需要有同谋;要有同谋,就必须使秘密始终处于一种似揭破非揭破的模糊或悬疑状态。在设计者、空间设计(或建筑设计)作品与观者三者之间,必须建立一种有待开发的潜在的同谋关系。当然,只有高明的设计者可能并且有能力坚守他和观者之间微妙的同谋关系。
但是,同谋并不意味着审美主体和客体的齐心协力与和谐一致。诱惑空间就其本质而言,根本就不是一种和谐的、统一的或一致的(consensus)空间。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竞争性的“双极空间,它必须把一个对象置于与现实的秩序——即包围它的可见秩序——相对抗的境遇。如果这种双极性不存在,如果双方没有发生交互性,没有这种境遇,诱惑就不可能发生。在此意义上,成功的建筑体存在于自己的现实之外,它是一个创造了双极关系的对象,这种双极关系,不仅要借助于(视觉)偏移、矛盾和运动方式,而且还要将所谓真实的世界和它基本的幻觉直接对立起来,才能实现。”(11)
另一方面,建筑或空间的秘密必须处于一种激活的状态。只有处于一种激活状态,它才能充分发挥诱惑的审美效能。
鲍德里亚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建筑或空间作品就必须表演同时出现和消失的游戏,同时在场和缺席的游戏。
鲍德里亚说:
随着虚拟维度的到来,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同时展示可见性和不可见性的建筑,也没有了那种既玩弄物体的重量和引力的游戏,又玩弄其消失的游戏的象征形式。(12)
因此必须恢复已经失去的这种审美游戏,必须展示维里利奥所说的那种“消失的美学”(13)。鲍德里亚说:
诱惑不是简单的呈现,也不是纯粹的缺席,而是一种遮蔽的在场。它的唯一的策略就是同时出现/缺席,从而生成一种忽隐忽现的闪烁……在这里,缺席引诱出现……(14)
单纯的消失和单纯的出现一样,都是对诱惑的一种毁灭。只有在显与隐、即与离的交互运动之中,即在秘密的优雅的闪烁之中,或者说,在所谓“之间(between)”之中,诱惑才会有所依傍,并可获得充分展现。同时,建筑客体和审美主体、建筑客体和环境,才能在巧妙的运动中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对话关系。
鲍德里亚认为,完美的建筑,就是那种遮蔽了自己的痕迹、其空间就是思想本身的建筑。(15)所谓“遮蔽痕迹”,其实就是体现鲍德里亚的所谓“消失(disappearance)美学”的建筑,也就是能够“同时展示自己的可见性和不可见性”的建筑:一方面,建筑融入自身的环境——消失、缺席或被遮蔽、不可见(一种收敛性);一方面,建筑呈现于环境,在场,展示可见性(也是一种竞争性)。正因为它能消失,所以它就能够引诱。
这就是鲍德里亚关于建筑的美学逻辑:在缺席中在场;在消失中呈现;在时隐时现中挑逗、诱惑。
但是,鲍德里亚的诱惑美学,在当代这个广告泛滥的媒体时代具有相当大的空想性,甚至可以说,这是他构拟的又一个美学乌托邦。
因为多数建筑师、开发商甚至城市管理者所考虑、所追求的,恰恰是一种固执的,甚至是粗暴的、非消失的注意美学,或者说广告美学。
鲍德里亚的诱惑美学思想形成于1980年(De la séduction)至2000年(Les Objets Singuliers:Architecture & Philosophie)之间。而在他出版《论诱惑》时,欧美已经开始进入媒体时代,建筑师也正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如何在媒体的喧嚣中突出(而绝不是消失)自我的妙法。
曾经邀请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参与巴黎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的著名解构主义建筑师埃森曼在1980年代后期就曾表示:“一切都在向我们证实,现实已经媒体化了。现在,人们甚至不再愿意花一分钟时间来观看商品广告了……一分钟之内,你就可以看四个广告。这就是凝聚(condensation)(16),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术语。强大的凝结力,使一个广告只需15秒即可播完。”(17)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属于强的形式的建筑,现在就变成弱的形式的,被铺天盖地的广告所遮蔽。如何从广告的包围中突围,就成为摆在建筑师面前的一大难题。
所以,建筑师屈米等人提出,要通过建筑创造“事件”(Event)(18),同时创造本雅明所说的“震惊(shock)效果”(19)。这可以部分解释形体狂怪的建构主义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突然兴盛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当今东方国家热衷于创造世界最高楼的原因。
建筑不仅要在实体空间中与户外广告争奇斗艳,而且要在虚拟世界——媒体世界——与广告一决雌雄。因为,像埃森曼一样,建筑师们相信,现实中不再存在看客,只有电视观众。对电视观众来说,实体的建筑是虚假的,不可靠的;虚拟的建筑,或者是被媒体化的建筑,才是真实的。而要被媒体化,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事件:或建造最高或最怪楼之类,或者创造破碎或狂怪的形体。
所以鲍德里亚不免有些失望地感叹:
(当今)建筑最狂野的冲动不是别的,就是建造怪物;不是确证城市的完整性,而是分裂性;不是确证城市的有机自然性,而是非生态性。它们没有赋予城市和城市的更新以应有的节奏;它们只是一些从莫名的太空灾难中掉落的碎片……它们的吸引力不过是那种使观光客惊异的方式……(20)
建筑师的出位冲动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挑战鲍德里亚的诱惑美学。这在消解鲍德里亚的美学的同时,似乎刚好从一个特定角度确证了鲍德里亚这种美学长久的真理价值。
错觉与诗意(poetic)
错觉,在鲍德里亚这里,是诱惑的一个要件,也是诗意的一个要件。
鲍德里亚对“仿真”和“内爆”怀有很强的戒心,为了不使读者在他所褒扬的错觉和所鄙弃的虚拟现实之间产生相似的“错觉”,他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说:
错觉与虚拟现实不同。虚拟现实,在我看来,是超度现实(hyper-reality)的同谋,即,是一种强制的,透明的可见性,是一种屏幕空间,心理空间(21)……错觉是意指其他东西的符号。在我看来,你(指设计卡地亚基金会大楼的建筑师诺维尔——引者)所设计的最好的东西,就是那种可以透过玻璃屏幕欣赏的建筑(也是能够产生错觉的建筑——引者)。正是因为你创造了这个有点像颠倒的宇宙的东西,你就必须彻底摧毁这种完满感,充分的视觉感和你所强加于建筑之上的意义超载。(22)
错觉其实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前提,就是空间设计上的空灵或不足或策略性的缺失。因此,错觉是实觉的美学分泌物,是空间“留白”的剩余价值。在主体方面而言,就是可以从建筑客体中接收到似乎比实觉更多的信息,也就是建筑师诺维尔所说的那种“有点难懂的、并非一览无余的空间,那种可以拓展我们的视觉心理空间的作品。”(23)
错觉也可理解为在话语的战术性停滞(或中断、沉吟)之后听者对言说者话语的创造性的误读或误解。
虚拟现实却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它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仿真。它一方面比错觉显得更真实更细腻,一方面更虚假更具有欺骗性。在建筑中,虚拟现实往往意味着虚假的美学许诺。一个屏幕里的美轮美奂的虚拟建筑,往往就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但是它通常被用作绑架业主的美丽借口。正因为此,鲍德里亚警告说,随着建筑的虚拟时代的到来,建筑的危险也显现出来了——“这个危险是,建筑不再存在,根本不再会有建筑这东西。”(24)
鲍德里亚通过将虚拟现实和哲学进行类比,总结道:
将现实置于视角中是一种哲学的直觉,因而没有任何“否定主义”的味道。至于虚拟,在对现实的技术性清除举动中,它才是真正的否定主义。(25)
也就是说,虚拟是真实的死敌。因为它以真实的许诺的形式——无法兑现的美丽的许诺方式终结了真实。
如果说虚拟现实只是代表一种暗含否定性的真实的许诺或愿景,那么,Trompe lóeil,即错视画,就是一种暗含戏谑性的逼真的假象。古希腊画家宙克西斯的葡萄和神话中塞壬女王的歌声一样,都属于一种妖法,而且是要命的妖法。宙克西斯的葡萄差点要了因贪嘴而上当的鸟儿的命(26),塞壬女王则不知要过多少贪耳的“音乐听众”的命。不过,错视画玩的是视觉或审美心理的游戏,它主要是以模仿战胜或替代现实或真实的方式,确证艺术创造的潜力——极限的潜力。但错视画只能诱惑眼睛,却无法征服精神。塞壬女王玩的却是政治学游戏,她用音乐打造了一座温柔而至美的陷阱,所有寻美者最终都无法逃脱她恶的圈套。
错觉,建筑或城市空间中的错觉,如果说有什么承诺,那只能是审美的承诺。它不以取代实觉或真实为目的,而只是在实体空间中循环并且作为实体空间的美学拓展,或用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的说法:作为空间的“氛围”和烘托,增加空间的灵动感和诗性。
鲍德里亚说:
错觉(illusion)是一个世界特性,它通过物质的二律背反结构,保留着消除能量和使能量非物质返回的可能性。错觉是那种通过强制回复……保留化为乌有的及超越“物质”客观的可能性的意识的特点……(27)
这里的二律背反,在视觉和心理上的表现,显然就是出现与消失的互动。所谓“消除能量”就是对象在空间中的消失;“能量的非物质返回”,就是对象在空间中的“再现”(reappearance)。
消失与出现的替换形式,就是错觉与真实(实觉)的对话。一般而言,在空间中,真实睡眠之际,也就是错觉出现之时。但错觉不是对真实的遮蔽,而是对真实的修辞、升华和诗意的转换。
因此,错觉是空间诱惑力的主要来源,或者,是空间诱惑产生的原因。而“诗意”,则是诱惑的结果。
鲍德里亚说:
……我们可以相信,由于建筑也从场所精神出发,从场所的愉悦出发,并且考虑到通常会出现的偶然因素,我们可以创造另外一些策略和独特的戏剧效果。我们可以相信,面对这种对人类、场所和建筑的普遍的克隆,面对这种普遍的虚拟现实的侵入,我们依然可以实现我所说的环境的诗性转换,或转换的诗性环境,走向一种诗性(poetic)建筑,一种戏剧性建筑,一种文学建筑,一种本源性的建筑,当然,这是我们所有人仍然怀有梦想的那种建筑。(28)
很显然,所谓诗性或诗意建筑,不过是对消失美学和引诱建筑的一种补充或升级罢了。诗性建筑最本质的东西,依然是消失/出现,设谜/解谜,融合/示现……这样的双级并置或交替的游戏。
但是,鲍德里亚诗意的转换或诗意的操作,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在空间设计中对“空白”(nothingness)的妙用。鲍德里亚说:
要让一座建筑物有一个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它不会勾起破坏它的欲望,即使是想象中的欲望,它必须自身懂得赋予空白的直觉,以及一种有别于玻璃的透明的直觉。(29)
这里,鲍德里亚强调了两个关键点:一是坚决反对满盈的空间设计,倡导类似于中国画的“留白”、计白当黑——因为空白是想象力、也即错觉的源头活水。二是要创造一种有别于玻璃的透明的直觉——要透明,但不要玻璃式的透明;这里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对现代或后现代建筑的玻璃幕墙的反感和拒绝。玻璃的空白依然是一种虚假的空白,正如错视画中的屋中窗户,只是僵硬的墙体的一种掩饰或遁词而已。鲍德里亚需要的是真正的透明,真正的属于“无物之阵”的空无。所以鲍德里亚要强调,“诗意的操作就是使空白(nothingness)从符号的权力下升起”(30),因为只有在空无之中,缪斯的猫头鹰才会起飞。
鲍德里亚在考察美国城市洛杉矶后感慨道:
在这个国家中,城市与村庄并不是抵御沙漠的避难所,而是给沙漠提供了保护地。它们并不筑起堡垒来抵御沙漠,而是把沙漠纳入房屋的网格中,或纳入房屋庭园中,那里有着同样的沙尘,在一片片夯实的土地上,骆驼、驴子、孩子和女人们自由地来来往往。空间从未被分配给住宅。任何建筑物难道不应该从空隙中汲取灵感,并使空隙以这种方式循环起来,而不是把空隙驱逐到一片今后被占领的城市空间里?我们不需要去穿越空间,而是空间应该穿越我们,就像庄子的刀穿越躯体的所有空隙那样。(31)
人造空间应该积极地拥抱自然空间,回归自然,让自然来穿越我们,而不是让城市或人类以空间(人造空间)屏蔽自然。这就是鲍德里亚的空间辩证法。
鲍德里亚对沙漠表现出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恋,他甚至有一种死也要死在沙漠中的执着。他说:
无法想象在寂静的沙漠以外的地方死去。尤其不要消失在嘈杂和狂热中。重新找回唯一的自由,即空间的和空白的自由。(32)
从这里,我们看到,鲍德里亚的思想又回到了他思想的原点。因为消失—错觉—诱惑—诗意,这样的逻辑思路,还是基于对现代文明的反自然性的反思和批判。而沙漠本身不仅是空白的标本,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对照和反讽。
鲍德里亚说:
自然界的沙漠将我从符号的沙漠中解放了出来。它们教我们同时去解读表面和运动,地质和静止。它们创造了一种被根除了其余一切——城市,关系,事件,媒体——的视野。它们诱发了一种将符号及人类沙漠化的令人兴奋的视野。它们构成了精神的边界,在这边界上,文明的所有举动都遭搁浅。它们处于欲望的领域及其周边之外。我们总是需要呼唤沙漠来抵御意义的过剩,抵御文化意图和追求的过剩。它们是我们神秘的操盘手。(33)
当代城市空间疯狂的蔓延——水平的和垂直的蔓延——其实就是典型的“意义的过剩”,“文化意图和追求的过剩”,当然也是文明的过剩。而沙漠,在这里,则成了现代文明的解药或阻隔器。
鲍德里亚的美学价值取向显然偏向于原始主义和精英主义。他对当代城市与空间的诊断,是空间过于满盈(所以人造空间过剩),技术过于追新(文明过剩,所以有仿真和代码过剩),空灵的诱惑空间或错觉空间却严重匮乏。所以他主张摒弃一切理论,回到空间的本源性,回到建筑的本源性,回到总体的原始性(颇类席勒所描绘的素朴状态),以挽救因追求过满而堕落的空间的命运,创造富有诗意的错觉空间和诱惑空间,重建城市的和谐与灵动、丰富与生机。
注释:
①如《独异的建筑体》(英文版2002)、《大众、认同、建筑》(英文版2003)、《模仿与仿真》(英文版)、《艺术的阴谋》(英文版2005),《冷记忆》(英文版1990)和《美国》(英文版1988)等。
②Fransceco Proto(edited),Mass Identity Architecture,Willey-academy,2003,p.125.
③Fransceco Proto(edited),Mass Identity Architecture,Willey-academy,2003,p.131.
④Ibid,p.41.
⑤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⑥同上,第196页注释。
⑦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⑧同上,第89页。
⑨参见拙文《空间的衰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
⑩Baudrillard,Jean.The Singular Objects of Architecture,Minnesota,2002,p.19.
(11)Fransceco Proto(edited),Mass Identity Architecture,Willey-academy,2003,p.25.
(12)Ibid,p.135.
(13)鲍德里亚在此只有借用了维里利奥的这个概念。
(14)Seduction.Trans.Singer,Brain.Montreal:New World Perspectives & Theory Books,2001,p.85.
(15)Fransceco Proto(edited),Mass Identity Architecture,Willey-academy,2003,p.131.
(16)即凝结作用(condensation):是指在同一个梦境中多个或多种心理欲望往往被综合地组织在一起。
(17)Peter Eisenman,Strong form.Weak Form.Archticture in Transition:Between Deconstruction and New Modernism.Edited by Peter Noever,Prestel,Munich,1991,p.37.
(18)Bernard Tschumi,Event Architecture,Archticture in Transition:Between Deconstruction and New Modernism,Edited by Peter Noever,Prestel,Munich,1991,p.37.
(19)这也正是鲍德里亚说的那种危险的“挑逗性诱惑”。
(20)Fransceco Proto(edited),Mass Identity Architecture,Willey-academy,2003,p.75.
(21)鲍德里亚称虚拟现实为心理空间,显然也混淆了错觉的概念——引者。
(22)Fransceco Proto(edited),Mass Identity Architecture,Willey-academy,2003,p.26.
(23)Ibid,p.23.
(24)Fransceco Proto(edited),Mass Identity Architecture,Willey-academy,2003,p.23.
(25)鲍德里亚:《冷记忆5》,张新木、姜海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26)悖谬之处在于,宙克西斯的拿葡萄串的小孩却不能吓跑鸟儿,这成为宙克西斯拟真功夫不够的证据。帕尔哈奥斯遮盖画布的绘画却迷惑住了宙克西斯本人,正如三国画家曹不兴的苍蝇迷惑住孙权一样。
(27)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1页。同时参见Jean Baudrillard,Le Crime Parfait,Galiée,1995,p.95.
(28)Fransceco Proto(edited),Mass Identity Architecture,Willey-academy,2003,p.137.
(29)鲍德里亚:《冷记忆5》,张新木、姜海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30)Jean Baudrillard,The Conspiracy of Art,MIT Press,2005,p.28.
(31)参见鲍德里亚:《冷记忆5》,张新木、姜海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48页。
(32)同上,第67页。
(33)鲍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