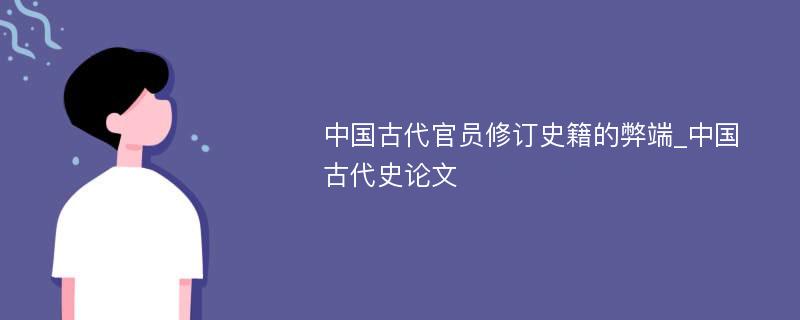
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弊论文,史书论文,中国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史馆开创的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学业绩,其所涉史籍之浩翰、理论之精到以及制度之完备,确实堪称天下第一。然而,几千年的官修制度为后代留下的遗憾,也同样为世上各国所不及。
宰相监修国史 历史蒙上尘埃
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监修国史制度,在初创时期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实行的一人独断修史事务,却使历史的真伪蒙上了尘埃。
浏览一下历代史馆监修所为,有以下几点特别令人深思:
第一,附庸风雅,假充内行。这是不称职的史馆监修的通病。史馆监修虽然不是一个肥缺,但在文人圈内却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荣誉位子。做监修的史官不一定能做宰相,但宰相有了史馆监修的头衔便会受到天下文人的认同,名声大振。所以自唐初开创宰相任史馆监修先例后,历代宰相无不以兼任史馆监修为仕途之幸事。这种官修史书制却是一场灾难,馆内正常修史秩序被打乱了:
其一,胸无点墨(指史学)的宰相可能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但在纷杂的历史现象面前却一筹莫展,往往是“每欲记一事、载一事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不知从何下笔。其二,即便有过一点舞文弄墨经历的宰相,挂上史馆监修的头衔后,极易忘了自己的根底。原先时政记一类的国史资料都是由一般史官编写的,中唐之后宰相戴了监修的桂冠,以为自己真的亦具备书写乾坤的本事了,独揽了此类史书的修撰。纵览封建官场,大凡以官秩博学术名声者,忠君思想固然牢固,专业知识却往往低下,所以唐以后监修编的此类国史资料的资信程度很低,要么由于不通文法,连皇帝这关都过不了;要么竭尽吹捧之能事,捧得连皇帝也不敢看。国史达到如此境界,功当首推这些帮闲监修。其三,史馆大权在握的那些假内行,虽然才识有限,但决断欲望却很强,热衷于用自己臆想出来的“条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馆外的高官都可以凭自己的官品盛气凌人地批评修史,指责史官。当然,如果监修们真能在修史事务中为史官提出些指导性的意见来,偶而独断一回也算不了什么,问题恰恰在于这些监修既无点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力。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书了。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笔,“一国三公”的干扰已提前到来了,从而使史馆修史主体的史官没有了自己的头脑。对史馆内外行领导内行的错位现象及其产生的后果,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大为不满,称其是“首白可期,而汉青无日”。
第二,忠君为上,政治取士。平心而论,唐初史馆取士还是颇具史学眼光的。这恐怕与唐太宗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胸怀有关。所以唐初要求史官不但要有政治和史学的素养,“言论慷慨,冠乎终古”,而且还要“文藻宏丽,独步当时”,具备文学家的功底。这时那些渴望用自己的才智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史馆可谓是一座通达彼岸的桥梁。
当时精通儒术成了史官入馆的首选标准。这自然是由于精通儒术者一般个人素养较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具有政治头脑,忠君思想牢固。依靠这种人修史至少可以杜绝与统治者利益离德的现象。况且,每每改朝换代,社会上便涌动着一批企图寻求自己新的位子和依附的读书人,他们到处吟唱:“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达何由达明主?”史馆藉此收罗一批专业子弟兵何乐而不为呢?
及至后代,所谓的“慎选儒臣,以任分修”几乎成了封建政治的代名词了。史馆选士看重的不再是个人的素养,而是其政治的信仰了。诸如五代那种虽才智一般,但“议论刚强”,能够在修史中以“圣朝功德”为本的读书人,或者像明朝那样“论及政事,洋洋千言”,“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于人君鉴戒”的儒生都是有希望入主史馆的。
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因素,如家世、出身也成了史馆监修们选士的必需条件。唐初的姚思廉,因其父亲是隋朝太子舍人、秘书丞,有过编书修史的经历,他遂以家学渊源初选入馆。宋元之后,家学也被人看轻了,史馆更注重的是那些有权势的官宦或贵族出身的人,比如元朝的脱脱、阿鲁图并无多少史学才能,可因其祖上是豪门世家,便被纳为史馆监修。显然,统治者需要的是有忠君思想的卫道士,而不是史家臆想中的直笔良史。
这对那些阿谀奉承之士或许是一个机会,但对那些直笔良史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当时之史馆已非唐初所能比,秉笔直书、不隐善恶被人称为“务于华而忘其实,弱于词而弃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则被视为有偏激情绪,专论“朝廷得失”。连那些由科举入主翰林史职的人,如明朝的焦肱竟因“性复悚直”,将对朝廷的不满付之于言论被解除了史职。而像明朝谈迁那样,苦心积虑几十年编成一书又非常人所能忍受。读书人几乎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百般无奈之中只有放弃文人的清高和史家的独立去依附政治了。
“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
从史学发展来看,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受到人们的赞誉。唐后,正史为各代史馆专修,这种赞美之声却不多见了。原因很简单:史馆所修的正史已成了只说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样文章了。这种做法虽然与司马迁的本意大相径庭,但却因能体现君主思想和监修意图而被历代史馆奉为信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唯上统治了史馆的所有修史领域。
第一,限定修史范围。史馆修史任务中以国史修撰最为责任重大,而国史的主要史料来源就是起居注和时政记。这类史册原本为史官专事记录,待皇帝死后再编为国史。史官的这种特权是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的。但自史馆建立之后,史官的特权却受到了帝王和史馆的双重干预。无论唐太宗、明太祖还是其他帝王,表面上都赞成史官“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可是,一旦史官真的秉笔直书了,帝王们又心虚得很,再三提醒史官要“不书吾恶,记朕功业”,并直言要史官改删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而史馆监修则索性以防史料外泄为由,把起居注等编撰权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史官刚一提笔,就有如此众多的提醒,又如何以个性驰骋于史学天地?
第二,裁决史料取舍。史料取舍原是史官修史的一项基本功,但自从监修们在史馆内提倡忠君为上以及以政治取士的思想后,史料取舍变变成了气味很浓的政治活动了。例如唐修晋史时社会上尚有18家晋书的本子,但到了《晋书》修成时,民间已见不到这些本子了。清修《四库全书》征书12000余种,但到修成时约近万种书籍被悄悄处理了。被毁掉的史书当然是因为“毁誉任意,传闻异辞”,与史馆的一切唯上有“抵触之处”。这其中有些消失可能属于史家正常消化史料。宋朝司马光修成《通鉴》时竟销化了整两书屋的史料。但这种正常消失里还是包含了必然的非正常消失史料的因素,试想司马光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抵毁封建政治秩序的史料塞入专供皇上看的《资治通鉴》中吗?显然不能。可见所谓的裁决史料的取舍,同样是为一切唯上式的修史服务的。
第三,划一史书体裁。唐初史馆撰修《晋书》后,曾为《晋书》的笔法和体裁着实兴奋过一阵。作为官修第一部正史,既语言华丽,又师法两汉书体例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如果浏览一下唐之后史馆所编写的正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体例、笔法都与《晋书》大同小异,毫无时代特征和史家特色。同样的划一体裁也表现在史馆所修的典志体、会要体史书上。作为首创者五代史馆的王溥确实功不可没,他在唐人苏冕的基础上推出了以帝王、礼、乐、学校、民政、食物、外国等15个门类的新会要体史书。但遗憾的是,他的创新仅仅唤来了一批因循仿效者,这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秦会要》都没有跳出他的窠臼。可见,对于制造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奇观——千人一面的廿四史,划一史书体裁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划一体裁的作法,使中国史学失去了许多向西方史学靠拢和接触的机会。
第四,规范修史准则。如前所述,史馆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如果史馆在修史中不能提高本朝威望,强化传统理论,史馆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所以,以规范修史思想为名,把史学挤向政治,实在是史馆求得自己生存的一个交换条件。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史馆之修史准则,统治者还是从中获益的,比如,能得到史馆美饰的身后名——实录,开明的君主或许还能从历史上得到维护统治的经验等。但对史学而言,这规范的思想无疑是一个紧锢咒,它给中国史学带来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数以千万集的史料被销毁、被榨干、被过滤,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最后成了一本干瘪瘪的帝王家族史,人才济济一堂的史馆也由古代修史的最高权力机构沦为一架破旧的编撰机器。对史官来说,所谓规范的修史思想又是一帖麻醉剂。史官不必竭耗精力发掘史料、推敲文辞,也不用担心没有个性和创见为时代所抛弃,更不用担心编书不成断了生计。只要以统治者一家之言为纲,哪怕它永远“汗青无日”也无妨,因为这已经成为社会相延成习的规矩了。
不难看出,官修史书的流弊对后世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从体制上讲,这种大锅饭式的制度消磨了史官的锐气,助长了不思进取的懒汉史学和奉承史学思潮的发展,并极度挫伤了知识分子修史的积极性,说史馆利用制度扼人才并不为过。而从史学上讲,其流弊更值得我们深思: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了一种思想、一种笔法和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并使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统统陷入史馆所设计的思维规范之中,这究竟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悲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