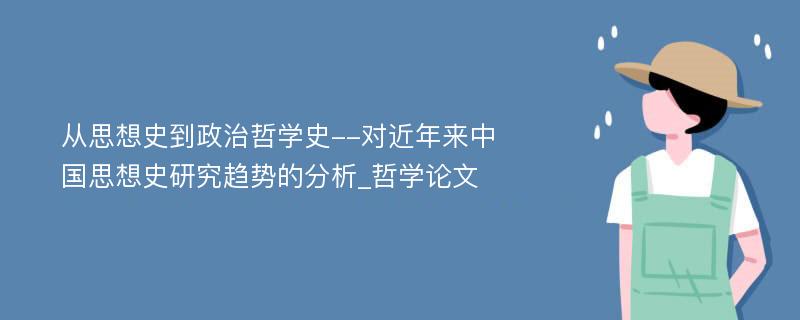
从思想史到政治哲学——关于近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趋势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想史论文,史研究论文,哲学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哲学史写作的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哲学之终结”论述的异域回响;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学术史热和国学热以来,关于思想史写作讨论的日趋兴盛,也总是关涉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构成了这一问题出现的近因。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写作范式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写作最初问世之际便已经出现。时人多从陈寅恪与金岳霖关于冯友兰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读出“微言大义”般的审思顾虑,这些顾虑多集中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素材和范围与西方哲学的理想性规范之间,是否会出现削足适履、圆凿方枘之问题上。因此,思想史与哲学史两种范式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恰当处理中国思想传统及其历史实际的问题,也涉及到中国学术现代性中哲学与史学之间的分际问题。
思想史写作中成为稳定范式并影响及于今天的,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一的侯外庐思想史学,二是由钱穆发其端、余英时及其后学在港台衍其流的思想史学。所谓思想史学,不仅是哲学思想的历史,更是结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对历史中思想的整体性分析,而这种整体性分析的旨趣还表现为将思想视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而必然结合着对作为其下部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因此,侯外庐思想史学内在关联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学而成为一种总体历史学。
余英时曾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关于思想史“内在理路”的研究,意在区别于与社会史结合的思想史和着重于道德形上学体系架构的熊牟系新儒家。一方面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所侧重的外部社会结构分析而强调思想传统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则将思想传统的内在逻辑区别于形上学系统的观念逻辑。
90年代以来思想史范式的回热与90年代蔚为显学的新社会史研究有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九十年代的思想史研究是另一种形式的与社会史结合的思想史学。其不同于侯外庐思想史之处,恰恰可以从人类学取向的新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宏观社会经济史研究之间的差别中看到。葛兆光将自己的思想史学称之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探究在长时段历史中作为“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的”“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尽管他将这种关注主体背后结构性依据和假设的思想史写作,区别于仅仅关注“小传统”中所谓民众思想的思想史,但其意图则在于通过思想史与新社会史的结合,来克服新社会史的缺陷。这种态度虽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但在着重于结构而不是主体的取向上,却如出一辙。此外,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则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基本上把思想作为一种历史中的话语,通过话语的历史分析来展现历史变化,致力于通过话语的思想史研究来揭显中国现代历史演变。
学术史上“中国哲学”问题的出现,严格说来是以观念史上“真理”观念的发生为先导的。研究哲学需要“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是从”。对真理的探讨是超越于一时一地之利益,故而所探讨之真理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而且王国维明确认为,在中国是存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哲学”的。中国“哲学”之需要一种理性的形式系统来加以重组,正是蔡元培期待于留洋归来受西方哲学之系统训练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之处。因此,研究整理中国的哲学问题,其实都已经内在地具有了一种“比较哲学”的视域。这种“比较哲学”视域的内在化,使得中国哲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哲学问题出发对中国思想传统的重组和重构,或者说是对中国精神传统的哲学性表述。
基于这样一种“中国哲学”观而展开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从开始便具有着双重张力,亦即作为中国哲学的专门史叙述如何呈现中国思想传统乃至中国历史的整全性问题,以及作为中国哲学的历史叙述如何成就“中国哲学”的哲学性意义问题。这种张力其实正是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正视这种张力结构,正面利用并转换这种张力,或许正是赢来中国哲学创造力的动力所在,也是实现中国学术现代性转换的关键。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张力并加以转化呢?
一种转化这种张力的方式,是由历史研究提供的。围绕宋代思想史叙述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历史态度。继承陈寅恪关于宋代思想学术的整体性论断,邓广铭、漆侠师徒以宋学取代宋明理学的叙述视角的选择,虽然丰富了哲学史叙述,但不足之处是反而有忽视理学在宋学中之核心地位的倾向。对理学的忽视而不是在历史处境的客观描述中真实再现理学历史作用的态度,反映了史学方式如何展现精神价值的方法论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内部也出现了修正以冯友兰和侯外庐宋明理学诠释理路的宋代思想研究,如余敦康和卢国龙的研究。他们着重于宋代思想的政治性,以及政治性与形上学性格之间的关联,贯彻了一种从历史实际出发,如其本来地呈现思想真实的态度。90年代中期,余敦康发表了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正如卢国龙先生所言,余敦康先生的易学研究,“一直在执着地借附于易学,探讨某种比‘两派六宗’之易学史更具根本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勾勒同时也是重塑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虽然该书是以易学为主轴,但却是对北宋新儒学思想史的整体把握。通过易学来把握北宋新儒学,并非取决于研究视角的方便选择,而是作者认为易学“明体达用”的精神旨趣最能体现北宋新儒学进而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即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因此,余敦康通过易学重新整理宋学叙述,代表了一条从易学来突破并完善宋明理学史叙述的思路。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强调了明体与达用之间的内在有机性,这意味着原来从形上学出发着意关注的内圣心性之学,仅仅着重于明体而忽视了达用的环节。这正是熊牟系新儒家道德形上学的问题所在。这种忽视并非可以用关注重心的偏向来解释,而是意味着一种对宋学乃至中国文化精神把握上的缺失。具有哲学意味的内圣心性之学与达于外王之用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说天道与人道的关联,或者说哲学与政治、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是一种精神传统成其为精神传统的充分而又必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精神传统之不同,恰恰在于对哲学与政治或思想与实践或天道与人道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故而,通过历史性视野展示的宋学精神,不仅让我们明了哲学的政治运用的历史限制,同时也让我们对一种精神传统如何发挥其新的历史作用有了更为冷静的认知。
余先生通过“明体达用”这一范畴,分析了北宋思想史上关于明体与达用之间的不同离合关系,并将这种历史性分析最终逻辑地归结到洛学的兴起上。同时,余先生对“明体达用”这一核心范畴的运用,旨在揭示宋学,特别是其中理学的完整精神意义,因而其对宋学实践性的强调,更多的是从理论上意义上展开的强调,并没有直接从这些实践内容的实际落实上来讨论其政治性的实践意味,余先生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宋学的政治哲学可能性,却并未直接从政治哲学的实践视野出发来重述宋学。这一点或许与易学的形式化特征有关,而选择易学作为切入宋学的突破口,或许也与余先生对“体”的形而上性格的理解有关,这种理解又与作者对“哲学”的固有理解相关。为了呈现了宋学复杂多元的政治性格,不仅需要易学之外的路径作补充,还需要一种哲学观念的更新。
卢国龙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余先生自然顺接的一个“转语”。《宋儒微言》一书的副题《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提示了该书的研究思路在于直接从政治哲学出发来探究宋学内涵。又如该书绪论之标题“政治变革中的北宋儒学复兴”所示,其对宋学的重述,是基于北宋政治变革这一时代历史性课题而展开的。从宋学的历史性课题出发,来把握宋学的完整精神,并将这种宋学的完整精神归结为政治哲学,卢国龙的研究可以说实现了儒学诠释理路转向所具有的意义转换的目的。他把天道与人道的关联方式作为基本分析范畴,来梳理围绕天道与人道关系的种种说法,进而拈出王道的概念,将北宋思想界关于天道与人道关系的不同表述,整理为如何为北宋政治寻求政治宪纲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运动。所谓政治宪纲,亦即“人君之学”,而“从儒家经典中探求古代圣君之用心、治理国家之要道,也就是建立一个高于君主个人情感和意志的宪纲,它对政治的最高决策发挥作用。”北宋儒学的实质便在于“将此‘人君之学’拓展为公共学术”。根据天道与人道之间不同关系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梳理,作者认为王道的理想型模式,还是由强调天道与人道落实贯通的洛学来表述的。所谓“政治哲学”,主要是意指一种政治和哲学或人道(治术)与天道的关联性:哲学在为政治提供形上根据的同时,也制约政治的格局;政治则是哲学理念的实际体现及其目的所在,并以此来规定这种哲学的性质。因此只有具有形上意味的政治哲学才具有政治宪纲的意义。
关于宋代儒学中《春秋》学与礼学的研究,是儒学诠释理路的思想史转向中必然涉及的领域,也是由思想史研究开展出一种恰当的儒家政治哲学视野所必然纳入的资源。《春秋》学的“王道”“正统”理念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政治以及历史原理的核心,中唐至北宋的《春秋》学复兴又与这一时期新天观运动的萌发相互激发,为从唐至宋的文化转型的一大关节。而这一转型的立足点又在礼教秩序的重建上。因此,从《春秋》学与礼学两方面来全面观照宋明儒学,将会对中国文化的原理、内容及价值理想有更为充分的了解。关于北宋《春秋》学的研究,早年牟润孙先生曾撰文专门论及,日本户崎哲彦等学者亦对中唐至北宋《春秋》学多所关注,而蒙文通先生通过对先秦儒学传统的三系划分及其不同旨趣的揭示,指出西汉公羊学政治理念针对西汉政治的理想性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从思想的历史研究中恰当地分析出思想的理想性来的极有启发性的例证。而蒙文通先生亦是最早向我们提示中唐大历学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起承转合意义的,他从经学、史学、文学和观念等方面揭示了大历学术的新气象,其中对中唐《春秋》学的研究,指示了一条如何从《春秋》学出发整理从中唐至北宋文化转型的思路。关于宋明儒学中礼学的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颇可借鉴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毅的研究。以“礼教之渗透”为基本观察点,他认为朱学和王学的对立仅只是用礼以渗透社会的方法上的不同,而并非如从近代启蒙思想出发诠释王学之进步意义的论者那样,将王学从其所内在的思想传统和时代问题中剥离出来加以重构。对于朱学和王学整体性格的把握,涉及到对主导近代中国思想史及哲学史叙述模式的启蒙思想的反思检讨,已不在本文所论范围之内,但是值得我们思索的是,我们究竟该如何从一种关于历史的目的论叙述及其背后的话语权力关系中彻底抽身而出的问题,因为如何如其本来地叙述历史,不仅是历史学的意义所在,更重要的在于如实的叙述可以带来认识乃至观念的解放,并且进而可以为一种恰当的哲学探讨提供切实的平台和保证。因此,避免从某种哲学观念出发对历史和思想的任意诠释,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哲学探讨必要的条件。
从思想的历史实际来把握思想和历史整体面貌的目的,并不意味着以一种史学叙述模式简单代替哲学的叙述模式,而是试图通过史学对历史和思想如其实际的把握,恰如其分地厘清思想的历史性与超越性的关联,以便建立起历史与思想之间的分析性关系。通过历史明确哲学之限度,是为了更加适宜地运用哲学寻找空间;而我们对哲学自主意义领域的确立,同时便意味着赢得了历史学运用的内在约束性尺度。将这样一种史学与哲学的辨证用之于中国哲学史领域,一方面可以将中国哲学史所具有的张力,以史学的方式加以转化,恢复思想与历史之间更为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对这种张力的转化,拯救出其中所蕴涵的创造性来,从而为哲学的体系性创造正名,恢复中国“哲学”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为实现这一点,恰恰需要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哲学观念的出现。这种新的史学观念便是一种具有现象学旨趣的对历史实际的如其本来的呈现,关注于处于意义与结构之间的主体自我形成及其与历史运动的关系,姑且以思想史名之;与此配合的哲学观念,则是对形上学理念及其实践性同时关注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不再把超越层面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唯一问题意识,而是将超越层面的问题与更为广泛的人间实践结合起来,将一种精神传统可能有的理念意义作为哲学创造的内容,姑且名之为“政治哲学”。一种处理精神传统的完整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史”视野的打开,为政治哲学的建构开辟了可能性。这正是我们期待于今后中国哲学研究之处。
标签:哲学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