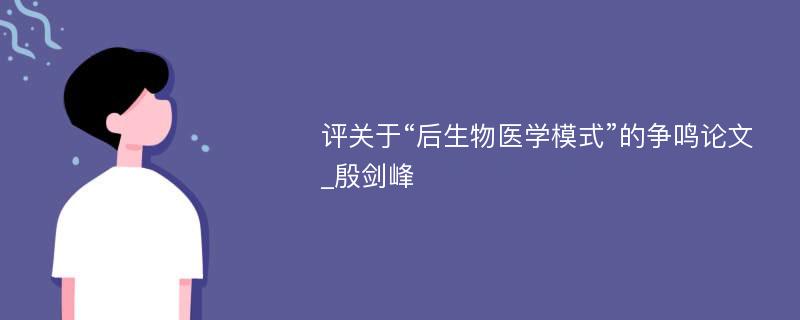
殷剑峰 (江苏省扬州市中医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文章重新审视了医学模式的定义,提出了“后生物医学模式”的概念,并对近年来医学模式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后生物医学模式的各种概念中共识程度最高的,但也存在不少分歧——研究者们纷纷提出了各自“理想”的医学模式,如“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协同医学模式”、“大生态医学模式”、“四维空间医学模式”、“环生物医学模式”、“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等,并对这些医学模式一一进行了评价。此外,作者还对医学模式研究中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滥用“医学模式”概念及对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盲目自恋现象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 医学;医学模式;后生物医学模式
[ 中图分类号 ] R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医学模式(模型),从字面上看,是指医学自身形态及人类医药活动的行为方式。由于医学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所以医学模式也就包括医学认知模型(medical model)和医学行为模式(medical pattern)。前者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医学自身的认识,即医学认识论;后者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医药实践活动的行为范式,即医学方法论。医学模式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概念,常用语言文字或图像表示。医学模式一经形成,便会成为医学实践的指导。
由于医学模式是人们对医学实践的抽象概括,因此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会提出不同的医学模式概念。例如关于古代医学模式就有多种表述:经验医学模式、神灵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僧侣医学模式、弥散医学模式、古代朴素的整体医学模式等等;关于现代医学模式更是争论不休,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环境生态医学模式、整体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多元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大小宇宙相应模式、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等等。
通过对医学模式研究成果的整理,不难发现关于近代生物医学模式的共识程度是最高的,几乎没有争议,而古代医学模式和现代医学模式则是争论较激烈的两个领域。至于对古代医学模式的提炼,属于历史学范畴,其价值主要在于认识历史的真实;而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其价值不仅在于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被动的认识,而且还要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主动的设计和定位,使之更加真实、更加合理,从而引导医学实践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两者比较,后者意义重要重大。所以,本文将对学术界关于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再现现代医学模式研究概况,以便形成对现代医学模式的更高程度的共识。
事实上,在诸多关于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中,研究者并不只局限于“现代”这一时间概念,而是在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概括的同时竭力设计人类医学的理想模式,而这一理想模式已远远超出“现代”这一时间范畴,更多的是对未来医学模式的设想。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表述这一历史阶段的医学模式,我将其统称为“后生物医学模式”。后生物医学模式(post-biomedical model),就是指生物医学模式以后的医学模式。它不仅包括现代医学模式,而且包括未来理想的医学模式。
1、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的共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在人们一致检讨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时,一种更为合理的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medicine)实现了对生物医学模式的超越。最早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是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George L. Engel),他1977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的论文,对生物医学模式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The dominant model of disease today is biomedical……It leaves no room within its framework for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s of illness”.[1](P130)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disease and arriving at rational treatments and patterns of health care,a medical model mus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atient,the social contest in which he lives,and the complementary system devised by society to deal with the disruptive effects of illness,that is,the physician role and the health care system.This requires a biopsychosocial model.” [1](P132)
关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这一认识最早是在1981年的第一次全国医学辩证法讨论会上被介绍到中国,[2](P4)引起了国内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关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凭着比生物医学模式更科学的内涵,很快赢得了多数人对它的认同。如今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把“现代医学模式”等同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至于多数关于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合理性做进一步诠释,也有不少学者只是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作了探讨,而很少有人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是否存在缺陷产生过怀疑。例如崔俊杰的论文《现代医学模式的哲学理论基础新探》(《锦州医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李霁、张怀承的论文《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存在合理性的伦理学分析》(《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薛瑞华、孙道盛等的论文《现代医学模式的文化取向》(《卫生软科学》1994年第8期),何国平、邱琳枝等的论文《现代医学模式与思维模式》(《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分别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哲学理论基础、伦理学依据、文化取向、思维形式等方面对其合理性做了进一步解释。又如徐任霞、胡怀明等的论文《试论医学模式的转变与重新设计和培养21世纪医学人才》(《预防医学文献信息》1997年第2期),王国富、梁振洲等的论文《医院转变医学模式的十点建议》(《医学与哲学》1997年第7期),段钟平、刘青的论文《运用现代医学模式指导生物人工肝的临床应用》(《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11期),王小燕的论文《医学模式的转变促进健康观念的更新》(《医学与社会》1999年第5期),王慧、林汉等的论文《浅析新医学模式下的职业道德建没》(《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分别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医学教育、医院管理、临床医疗、健康观念、医学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做了探讨。上述研究成果或偏重于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进行理论阐释,或偏重于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医药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其前提都是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全然接受。
通过“中国期刊网(清华同方医学院镜像——医药)”检索(2005年2月28日),自1997年以来关于“医学模式”的研究论文共有236篇,其中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合理性做进一步说明的28篇,占总数的11.8%,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173篇,占总数的73.3%,两者合计为85.1%。这表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是后生物医学模式的争论中的最强音。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后生物医学模式的争论中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共识程度是最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声音。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一些学者在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作深入研究的同时,也揭露了它的许多缺陷,并各自提出了自认为更合理的医学模式,从而形成了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的争鸣景象。
2、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的分歧:诸多医学模式的争鸣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是以人类的疾病谱以及健康观念的变化为依据的。这一模式认为导致人类疾病的不只是生物因素,而且还有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治疗方法除了传统的生物学方法以外,还应当包括社会科学法和心理学方法。认真分析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被提出的思维方法,我们不难发现依然是西方传统医学所奉行的“分析、还原”方法。它考虑到致病因素并不只是生物因素,但却没有考虑到所有致病因素;它考虑到了治病方法不只有生物学方法,但却没有考虑到所有的方法。由于没有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难免也存在一些缺陷。
一些研究者认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考虑的致病因素和治疗原则不够全面,因而提出了“更加全面”的医学模式。如卢焯明、陈诗慧等提出了“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张守诚、梁兆科等提出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日本的池见酉次郎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等。卢焯明、陈诗慧指出:“尽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的趋势已成必然,但在内容上仍有不完整的地方。为此,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3](P18-20)他还对这五个因素与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做了详细论述。认为“基因与人类疾病的关系异常密切,尤其对于今天的人类疾病谱,基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它生物因素”,因而强调在医学模式中增加基因因素。梁兆科指出:“目前倍受推崇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按照前述医学模式的两层含义来理解,仍存在很大缺陷。笔者认为,能全面和深刻反映现代医学实践和认识的医学模式就为‘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4](p368)他认为这一模式既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本质,反映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因素,也能全面概括当代医学实践领域,并能给健康下一个较完美的定义。日本学者池见酉次郎1980年通过对25名患者的致病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生物心理社会伦理致病2名(8%)”[2](P11),于是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
事实上,上述研究者虽然指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缺陷并予以“纠正”,但其思维模式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分析、还原”模式。如果思维方式不变,即使罗列N个影响人类疾病与健康的因素,在“医学模式”前加上N个修饰语,也不可能穷尽影响人类疾病与健康的所有因素,这样的医学模式仍然存在缺陷。他们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批评难免会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而且他们所提出的所谓补充“因素”,事实上已包括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内。例如“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中的“基因”、“自然”因素和“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的“自然”因素已包括在“生物”因素之内。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主要在于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而过分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而自然属性固然包括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体内的各种自然组成部分(包括基因)。同样,“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中的“伦理”因素也应当属于“社会”因素的范畴,“伦理”的实质就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以,上述几种医学模式并没有超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反还没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表述那么简练。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看到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存在缺陷的根源——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线性思维方式,他们在以“整体性、联系性”为特征的系统思维方法指导下提出了有别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医学模式概念。如顾跃忠、汪开提出了“协同医学模式”,陶功定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谢宇峰提出了“四维空间医学模式”,孟宪武提出了“环生物医学模式”,匡调元提出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李恩昌、会德全提出了“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等。下面分别叙述:
“协同医学模式”。顾跃忠、汪开利用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哈肯(H. Haken)的“协同学”和普里高津(L.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对人类的存在和进化做了深入分析,指出“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复杂、高度有序的非线性协同态。医学的本质和目的就是要维持或促进或恢复我们人类的最佳协同态或最佳健康态。”并利用协同理论对健康和疾病作了全新的解释:“健康是指人体在一定协同度范围内的存在状态;疾病是指低于协同度的存在状态。”他们还提出了“协同医学模式”下的医学体系:“协同基础医学”、“协同应用医学”、“协同医学工程”。[5](P108-109)
“大生态医学模式”。陶功定把人类置于一个大生态系统之中,认为人作为大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要与其他系统发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和谐是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志。他指出:“健康是人的身体和精神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优化人类生存环境是医学最广义的、也是最首要的任务”,“医学应当是以改善人类生存状态为根本目的的综合科学和实践体系,是关于优化人类生存的学问”。[6](P1-4)与陶功定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刘典恩、杨瑞贞等,他们指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被生态医学模式所取代,生态医学模式或许是后SARS时代医学发展的必然选择。[7](P27-29)
“四维空间医学模式”。谢宇峰指出:“一个较为完善的医学模式,应当建立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对健康和疾病产生影响的一切相关因素,如:自然因素、社会、心理、体质、时间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为此,引入现代物理学相对论的‘四维空间’概念,提出四维空间医学模式。”[8](P18-19)孟宪武也提出了与“四维空时医学模式”相对应的医学学科体系——“环生物医学模式”。他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医学学科体系角度入手,对医学模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环生物医学模式是指由各种医学相关学科动态地环绕生物医学主体所构成四维时空的医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医学相关学科,除了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还有医学伦理学、医学环境学、卫生经济学、卫生生态学、医学哲学、医学统计学、医学教育学、医学法学等若干学科,它们对生物医学的作用与社会、心理学科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些学科中,“生物医学不能不占有主体地位,其它学科,其它因素在模式中永远不能与其并列平行,更不能取代其地位。”“环生物医学模式用一个‘环’字,既代表了各相应学科的内容,也表现了它们各自的地位与构成关系,比较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医学观的概貌。”[9](P447-448)
“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匡调元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论的启示下利用系统论的观点探讨了人、天与人、地与人、食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超越“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他指出“人类疾病的根源在于人与天、与地、与他人相互关系的紊乱以及人体内部机能、结构、代谢的紊乱,‘整体制约论’为其发病机理”。[10](P1-4)
“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李恩昌认为:“医学必须将人放在整个自然社会以及时间、空间最广泛的背景下,研究生命现象及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2](P1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曹文秀、陈小明,他们利用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解释了健康与疾病现象,指出“一个人如果从主观意识和情感上能够顺应社会变革发展,驾驭各种矛盾,把握自身的心理平衡,与社会之间产生良好的全息共振效应,则心情愉快、事业昌顺、无病自强;反之则心情郁闷、疾病丛生。因此,人的精神心理活动能否与社会与周围环境产生良好的全息共振效应,作为社会全息元的人来说是强身健体的重要因素。”[11](P56-62)
一切物质都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的,因此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事物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Bedalanffy,L.V.)正是从有关生物和人的“生命问题”出发提出了一般系统论,这表明生命形式或生命过程是最能体“物质的系统存在”这一特性的。既然如此,那么以“人”为研究和服务对象的医学就应当充分体现人以及人的生命现象的系统特性。因此,医学模式的研究也就不能摒弃系统论这一根本方法。上述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的探讨,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运用了系统论的方法。相对于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而言,更具合理性。
论文作者:殷剑峰
论文发表刊物:《健康文摘》2015年1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6/4/28
标签:模式论文; 医学论文; 社会论文; 生物论文; 心理论文; 提出了论文; 生物医学论文; 《健康文摘》2015年11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