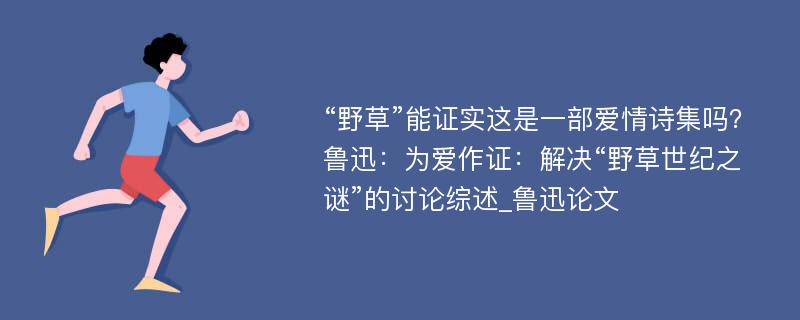
《野草》能确证是爱情散文诗集吗?——《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野草论文,鲁迅论文,确证论文,诗集论文,之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无疑可称得上是新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因此也无可置疑地得到了生前身后最多的评论;《野草》,是学术界中公认的复杂难懂的散文诗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当代前沿问题研究》的课堂上,李今老师选取了2000年以来最新出版的几本《野草》研究专著:孙玉石著《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加拿大学者李天明著《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以及胡尹强著《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以下简称《为爱情作证》),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了《野草》集的深入探讨。
其中,胡尹强完全从爱情的角度来解读《野草》,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老师和同学就其论述内容、行文方式与叙事手法、以往《野草》的学术研究的反思以及自身对《野草》的看法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得出了一些颇为新鲜的认识。
一、“为爱情作证”与伟大有关
陈丹青先生有一篇在鲁迅纪念馆的演讲,题目叫《笑谈大先生》。他“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说到“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这是有别于我们以前看到的严肃和带点尖刻的“睚眦必报”的鲁迅先生的形象,“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模式里,我来插一脚,又是不好玩。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我以为也是中肯的话。”这样,就把鲁迅先生从万民景仰的神坛拉回到了人间,让普通人有了与“先生”对话的可能。
《为爱情作证》就俨然是一部与鲁迅的“人间对话录”,起初同学们大多以为,“为爱情作证”的题目是为了吸引眼球,追求轰动效应,不乏商业出版的噱头,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发现胡尹强自己是很用心的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滴水不漏的论证来经营(实际效果如何姑且不论)。大多数同学认为本书写得最精彩的部分是引论,也以此触动了同学们心中想过也许没有机会表达出来的疑惑,为《野草》的研究透入一股清新自由的空气。作者在引论中就作出了很多有力的追问,比如作者在举出《新青年》团体从“酝酿”散掉到最后的解散期间鲁迅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后说道:“事实有力地说明,《新青年》团体酝酿‘散掉’的时候,鲁迅没有彷徨、苦闷,《新青年》团体完成分化、散掉的全过程,鲁迅也没有彷徨、苦闷,反而更坚定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至少小说创作反而更多更好了。而现在——进入1924年了,分化、散掉的事实已经过去三四年了,鲁迅反而因此彷徨、苦闷起来,这就不大合乎情理了。”这种追问是有力的,它让我们重新思索鲁迅对自己创作《野草》的解释——“《新青年》团体散掉而生的苦闷在创作上的表现”。不仅如此,作者还继续追问:“要弄清楚《彷徨》时期,鲁迅到底为什么彷徨、苦闷,先要弄清楚,《彷徨》时期,鲁迅的彷徨、苦闷表现在哪里?”作者以此出发,找到的依据是爱情,由爱情而生的苦闷促成了鲁迅创作《野草》。一直到这里,我们都很惊叹作者这种打破成规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作者说:“为什么鲁迅灵魂的这段苦闷、彷徨的感情湍流,只发生在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而没有发生在其他年月?”
李今老师在总结中也肯定了《为爱情作证》的启发性意义:《〈野草〉英文译本序》中鲁迅谈“《野草》大抵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大家应该注意“那时”二字,说明现在可以直说了,那么是什么事情呢,和许广平由暗到明的爱联系起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鲁迅创作《野草》中的第一篇作品《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而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是1925年3月11日,也就是鲁迅创作了《野草》中的11篇,几近一半的作品之后才收到许广平传达爱的信息的信,而且这封信并未将俩人之间的窗户纸捅破。如果鲁迅在此之前就已感觉到了许广平的爱,并引起一系列的情感和创作活动,那就只能归于爱的神秘第六感觉了。这样说,也并不是要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许广平敢于在信中激烈地表白:“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恐怕只有取得特殊的身份才可能无时、地的界限)甚至大声疾呼:“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决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从这里,一个“刚率”的许广平亟待鲁迅接受她的爱的心情,不是昭然若揭吗?更说明问题的是,这两段话在《两地书》出版时,前者被修改,后者全部删掉,岂不是欲盖弥彰吗?由此可见,虽然是第一封信,但他们之间的感情恐怕应在写信前就已存在。胡尹强给我的启发有一点很重要,鲁迅过去对生活有一种设想,而且作为作家,已将其公布于众:“我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到光明的地方去”,下定决心要孤独一辈子,和朱安挂名夫妻一辈子,从道德上讲,是很伟大的。但是他和许广平好了以后要推翻自己过去的一切,他又是公众人物、偶像,心中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经过多么艰难的挣扎。就这一点,不读胡尹强的书,我是想不到的。所以这本书读了以后,对我很有启发,我赞同他的某些解读是因为和我的某些感觉是一样的。比如说《腊叶》是鲁迅唯一承认“为爱的”,但就是此篇,我读不出爱来,那么胡的解释联系上下文就比较妥贴了,鲁迅因为大病,很怀疑他和许广平的爱情关系能够保持下去;《一觉》说是对青年人的赞美,但读来有的地方感情却太激烈了,不像是对一般青年人的赞美:“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而胡解释成鲁迅写作时洋溢着对许广平的爱就好理解了。(李天明也许也有提到)
而王莹同学在讨论中所强调的是,对鲁迅解释的丰富性不会损伤鲁迅的伟大,反而是作为人的“丰富的痛苦”能够维持一种伟大感。可以肯定《野草》是鲁迅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感情体验与生命体验,虽然不一定是爱情。她说:“我有一个希望,如果能将《野草》作为爱情散文诗来诠释,对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不降反而更趋完美,一个‘伟大’的作家并非一生战斗,如果一个作家所有的文学都是战斗的,那么他的写作还不完整,抒写爱情是必要且必需的衡量标准。我也希望大家能在评论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鲁迅自己的文字中会有对身体、衰老的担心,如果考虑到他与许广平的相爱,爱情中包含着情爱,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从《两地书》的删节也可以清楚看到,王得后小心翼翼的分析其实辅证了胡尹强的观点,既然鲁迅能写出那些轻松、戏谑的文字,那么《野草》也有机会被看成是鲁迅个人内心情感的一次挖掘,并且不是做给许广平看的,而是做给自己的。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份真切的爱,会越惧怕失去对方,会把两个人的未来在美好憧憬中也极端的从反面去想。鲁迅在《野草》中流露的心态与口吻就很有这种矛盾感。
但是如果仅仅把《野草》理解为“为爱情作证”,大多数同学都表示不能认同。刘秀明和谢贵军同学都抓住了章衣萍的回忆——鲁迅曾经十分明白地告诉别人:“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如果把《野草》所有的篇章都解释为是在为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作证,那鲁迅对章衣萍说的话就是说他的所有人生哲学便都包含在与许广平的恋爱之中了,从这一点反推,《为爱情作证》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野草》内涵的丰富必然是和作者的经历的复杂相关。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也曾经提醒我们注意:《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由此可见《野草》绝非仅能狭隘地被认为是爱情之作,即使有爱情的显现,也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点,而绝不是它的全部。
二、小说家笔法与影响的焦虑
在行文方式与叙事手法的问题上,虽然也有同学表示赞同:“胡尹强对《野草》每篇的论述都可以自圆其说,每一篇都可以独立成章,同时每一篇又同上下篇前后联系。从《秋夜》到《题辞》,胡尹强认为鲁迅完成了对许广平的爱情旅程,同时,胡尹强也认为鲁迅完成了从迷茫、困惑到坦然、欣然的肯定。首先,他分析了各篇章的创作时间,同时用鲁迅和许广平感情的发展阶段来加以印证;其次,胡尹强参阅了许多鲁迅亲友的回忆录,并结合研究界对篇章的相关论述,加以辩证的分析解剖;最后得出自己的论点,从文中撷取富有代表性的词语,并加以引申,得出鲁迅隐藏在《野草》后面的爱情篇章。”但是批评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同学们举出大量的例子,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全知叙述与“小说家笔法”
以往学术界敢于触碰《野草》的著作大家其实耳熟能详,像孙玉石、王得后、钱理群、汪晖、王晓明对《野草》的解读,都有精彩的地方,但是确乎不够丰富,很多情况下是将不能处理的部分搁置,比如对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这一阶段《野草》的酝酿期不能给予很好的解释,像鲁迅这种可以即时作杂文的人不会还因为几年前新青年的解体一事而苦闷写作。而胡尹强从“爱情”角度入手,在他之前只有长春师范学院的一位老师和胡尹强自己提到的李天明,并且像他这样卖力气的力图把《野草》的所有篇章、段句都解释清楚的,仅此一人。但是如果你一直读下去,会产生阅读疲劳,这也许是大家都觉得引论精彩的一个原因,完全不像讨论爱情的文字,开始的时候还愿意和他一起动脑思考事情的原委,但随着他行文中将材料与揣测混在一块,读者会丧失兴趣与信任感。细节上有些地方阐释不够有力,比如书中第46页对《秋夜》中“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解释,李天明把枣树理解为朱安确乎有不妥当之处,但是他自己却将其解释为“眼前的景物实际看到的就是这样,”“诗人只是用重复的修辞手段,强调一下,不一定字字句句都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也许实际情况真如他所说,但是他用揣测的结论也不可能将“两棵枣树”的公案解释得特别明白,对学术研究没有贡献。
但是此书最为人所诟病的,一是在行文中,胡先生从不限定视角,常常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出现,甚至替鲁迅代言,替鲁迅思考。二是小说家笔法,以揣测当证据,混淆了真实与虚构应有的距离。
例一,在论及《狗的驳诘》时,胡先生认为狗的四个“不知道”后面的省略号的意思“只能是‘新和旧’”。更令人惊讶的是,胡先生多处极为细致地描绘鲁迅和许广平交往的细节,仿佛他就在鲁迅身边,目睹了一切的发生,甚至洞察了鲁迅的内心。在论述过程中,“合理的想象”可以弥合材料之间的缝隙,但是“过分的虚构”出现在一本学术著作中却显得很不适宜。在书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字眼:“我猜想”、“我以为”、“我猜测”……这样的措辞告诉我们,胡先生的推论是揣测性的,但是在这个推测之后,胡先生的笔锋一转,出现“只能是”、“当然是”、“毫无疑问地”等字眼。既然是建立在推测之上,又怎么能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论断呢?
例二,谈谈支撑本书的论证的一个重大方面——鲁迅《野草》写作与发表的时间差问题。作者在分析《秋夜》的时候这样说道:“鲁迅写着这段文字的时候,脑海里肯定幻出在教务处全体女学生包围他、维护他、挽留他的永生难忘的一幕。她们卫护、挽留鲁迅,是出于对光辉的向往和敬仰。小青虫的向光性和扑向灯光,当然也暗示对异性的性爱的追求,不要忘记,诗人是学医的。”首先,作者所讲9月14日女师大学生挽留鲁迅辞去职务是自己猜测的,其次在作出猜测以后作者不能再度用“肯定幻出”“永生难忘的一幕”这样的词句,因为作者并没有在下文中说明自己是如何作出这种猜测的,是在鲁迅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呢,还是在其他人回忆鲁迅这段生活时这样说过呢?这样的猜测在本书中俯拾皆是。
例三,作者在解读《希望》时有这样的话语:“察看《鲁迅日记》。22日本来是应该去女师大讲课的日子,然而,《鲁迅日记》却记道:‘晴。休假。’不知道为什么休假?总之,没有去女师大讲课,自然也没有见到她。一星期后的29日,诗人才去女师大讲课。这时已经是新年临近了,而诗人好像也已经两个星期——从16日到29日没有见到她了,现在见到她了,当然期望在新年到来之际,对一直悬挂在有与无之间的爱情,她会有进一步的热烈的表示。诗人以为,她毕竟年轻,因袭的负担轻,没有婚姻的羁绊,她是自由的,遇事又果断、坚决,诗人期待着她能够更主动、更积极地向他发出进一步的爱情信息。”这就是以一种现代人的心理去揣摩一个出生在清末的鲁迅的“妄测”的表现了,似乎在写作《野草》这部爱情散文诗(姑且这么认为)时,在鲁迅的生活中没有其他,只有许广平和爱情了。
(二)对散文诗(艺术作品)性质的误解
在胡先生对《影的告别》这一篇的解析中,他说:“读者最想知道的,例如《影的告别》里形和影分别暗示谁,《过客》里女孩暗示谁,‘布片’暗示什么——鲁迅却故意避而不谈。”我认为,并不是鲁迅故意避而不谈,而是没有谈的必要。我们知道,《野草》是散文诗,而不是自传之类的纪实的作品,我们不能把作品里的一切意象来据《两地书》和《鲁迅日记》加以佐证,我们不能据此就认定《野草》就是鲁迅当时生活情形的对应。这样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一种对作品的误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两地书》、《鲁迅日记》与《野草》对照着读,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两地书》作为我们理解《野草》的资料,以便我们更能接近和理解写作时的鲁迅,了解作品的内涵。
(三)强势话语与影响的焦虑
细心的李子衿同学受西方批评家布鲁姆理论的提示,考察了胡尹强在书中时时流露出“影响的焦虑”:“爱情说”,即《野草》中存在描写爱情的篇章,在学术界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以加拿大学者李天明的博士论文《难以直说的苦衷》和又央的《〈野草〉:一个特殊的序列》为代表。作者也在书中多次提到他们的观点,但是往往用这样的词句:“李天明认为……我难以苟同”或者说“不敢苟同”来破除别人的观点。从作者沿用李天明的“私典说”和在破除李天明的某些观点时用词的激烈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此书时的某种焦虑:有人提出过爱情说了,我又来提出似乎有点重复?这种焦虑也体现在作者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的破除上,这里就不举例子了。此外,作者的这种焦虑还体现在材料引用上。本书共引用了十三种资料:
1.《鲁迅全集》(卷1、2、3、4、6、7、8、10、11、12、13、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李天明:《难以言说的苦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12日版;
3.又央:《〈野草〉:一个特殊的序列》,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5期;
4.《许广平文集》(卷一)(卷二),江苏文艺出版社(没有注明年代——注者);
5.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
7.胡尹强:《爱情的湍流,灵魂的地狱》,《社会战线》2000年第5期;
8.李何林:《鲁迅〈野草〉注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和1978年修订本;
9.朱正:《鲁迅传略》(未标出版社——注者);
10.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11.胡尹强:《破毁铁屋子的希望》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
13.恩思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在这些资料中,其观点作为破除或支持对象的就有第2、3、6、7和11五种,而第12、13种是作为工具书使用的。子衿最后反问道:为论证本书所持观点不能提供给读者更多更新的资料,作者就只能在破除或支持别人观点上下工夫?
黄剑敏同学也说:《为爱情作证》特别不能让我同意的一点就是将《野草》的每一篇文章都解读成“为爱情作证”。《野草》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很多篇章、段落是鲁迅潜意识的书写,即便令鲁迅重生,他也无法一一解开“野草之谜”。《野草》的神秘和“难懂”也正是《野草》的魅力所在,读者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解读。然而,胡先生告诉我们,他已经“破解了”《野草》的“世纪之谜”,光书名就透露出令人惊讶的狂妄(或许书名的设计未必完全是胡先生的原意)。在具体行文中,胡先生不断引述前人对《野草》的解读,但是他的态度是这样的:鲁迅的《野草》就是为爱情作证的,别的对《野草》的解读都是“误读”,都是不能进入《野草》的艺术世界的。当《野草》——“为爱情作证”成为胡先生在整本书要做的唯一的证明题,就出现了“预设”结论的危险。胡先生认为“为了守护恋爱的秘密,鲁迅还必须‘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这是理解野草的“障碍”。当无法证明、无法自圆其说时,胡先生就拿出他的“法宝”:这是鲁迅的“障眼法”。这种做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四)对《野草》的影响、传播、接受的盲视
王莹同学认为作者在自能圆洽的同时,也封闭了这个文本,读罢此书会冒出一个想法,如果《野草》在当时能被人解读出此意并出版流传,可能会影响几代人的爱情观。历代研究者都认为《野草》的象征意味浓,但仍然在看到“死”、“生”、“过客”、“大欢喜”等这些富有深意的概念时将其坐实;而胡尹强没有注意到文本的接受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倾向于《野草》是战斗的、痛苦的这样的解释,而且也是作为这样的意义来传播的,他也没有明确《野草》的散文诗的性质,将“诗”谈得如此日常生活化,这都是很遗憾的。如果说,后人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存在阅读者的主体参与,那么只要作品确实存在所解读的一切,即使作家写作时并未意识到的也是合理的。只是,如果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其他,则有失客观和完整;如果只注意到“形而下”的简单的事实,而忽视“形而上”的伟大深邃的精神和思想,就会导致对作品价值的贬低,这或许就是《为爱情作证》一书的缺陷吧。
三、对于“鲁学”界:胡尹强——需要直面的现实
(一)《野草》研究:需要新鲜空气
要认识一位作家,需要从各个方面入手,既包括作家的生活经历,生活的时代环境,社会环境,甚至家庭环境,也包括作家的个性,气质,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等。而人的经历必是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爱情经历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对鲁迅《野草》的研究,人们多从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大文豪,大思想家,革命家和民族英雄的身份进行阐述,却很少有人重点从鲁迅的爱情经历入手。似乎人们忘记了鲁迅其实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去除其头顶上的光环,他也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追求普通人追求的一切的意愿的人。这无形之中,人们将鲁迅进行了神化,使其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精神的代表和象征,失去了凡人的血肉,而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丰富的,让人感觉真实可信的人。在这一点上,胡尹强的写作,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应该说具有一种反拨和矫正的作用。
(二)胡尹强——需要直面的现实
在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栗军芬同学向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信息:胡尹强,1937年生,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关于《野草》是爱情散文诗集的观念形成于其教学阶段,早在退休前他于浙江师范大学执教期间,便不断地向学生讲述自己的观点,后逐渐地将之体系化,其《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一书初稿完成于2001年,定稿于2004年。也就是说,此书完成于胡尹强65岁之后……
当听到胡尹强先生已经年近七十时,我们曾经的不屑与对这种写作是不是一种为求出名的“功利性写作”的猜测变得轻如鸿毛,而突然意识到我们在做一件怎样的工作,有点类似于法国批评家与作者的关系,毫不认识,没有任何先设的,如果有也只是时而对鲁迅研究学术惯例的遵从或小小叛逆。不由想到刘心武先生与胡先生都是小说家,他们的研究是两个个案,如何对待这些研究成果,原本并不相及的两个学术圈子(红学、鲁学),瞬间要面临同样的问题。
胡尹强的论述语气与方式显得有些焦虑与焦躁,并自觉与专家学者对立划分,不客气地指出孙玉石怎样讲过,李何林怎样讲过,他手中掌握的材料并不比别人多,但是对内在理路有独特的认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读到这样的文字而有些不舒服呢?在我看来,他的不沉着正反映了我们的学术体制与惯例对新事物的态度,这让我想起了红学家批评刘心武的研究,他们的反应那样相似。在中国,研究鲁迅、《红楼梦》都象征着一种学术权力,形成了丰富和强大的传统,大家在一个共识下各说各话,相安无事,若有人敢在无新材料的前提下以一己之力来直面鲁迅“难以直说的苦衷”,最初受到阻力或不认同是正常的,但在学术风气渐开之日,此说法慢慢被接受也是必然的。最可怕的事情并非新观点受批判,而是学术界对这种并非毫无道理的论说持漠视的态度。胡尹强写作的内容是一方面,而这本书放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支持,《为爱情作证》一书,而且,我们十分期待学术界能为此产生争鸣,不回避现实。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李今老师开设的《现当代前沿问题研究》课程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讨论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我们由一本书间接地走进了曾经被视为神圣的鲁迅及《野草》研究,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处理的问题与最终采取的态度,都将对我们的学术修习产生深远影响。
王莹整理
王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83
标签:鲁迅论文; 野草论文; 许广平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爱情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日记论文; 新青年论文; 两地书论文; 秋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