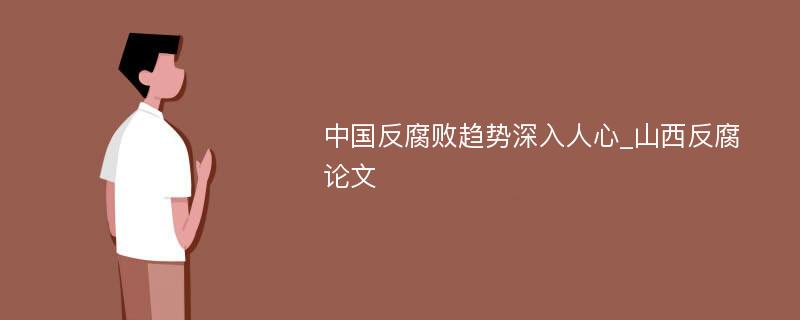
中国反腐走向纵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纵深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腐篇:腐败愈演愈烈了吗?
腐败是一种罪恶,一种世界流行病,一种社会破坏现象。长久以来,人们莫不这样认为。
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里,腐败已俨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一部分。鲁帕塔·莱在长时期游历了印度之后,就惊奇道:“那里贪污非但是道义上允许的一种行为,而且还是人们所向往的期待的东西。”
鲁帕塔的慨叹和流传于中国民间的腐败的“臭豆腐”理论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暗合。然而这种浮于表面的观察结论并未成为主流。反腐败国际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虽然不同的国家可能对能够接受的行为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认为,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牺牲公民的最高利益,与商业承包人签订非法协定,让自己变得富有的行为是正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清明廉洁”的政治,始终不懈地在与腐败进行着斗争:
192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内第一份反腐败文件。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规定:贪污500元,处死刑。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市委书记张子善因为贪污腐化被处以极刑。
1980年,中国改革刚刚起步,陈云即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尔后,针对党内滋生的腐败现象,邓小平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尖锐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
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腐败现象久除不尽、甚至愈演愈烈的新问题,十五大明确要求:力争在五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五年来,全党、全国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加大。查办的大案要案逐年增多成为重要标志之一:
199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2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3970人,地(厅)级干部292人,省(部)级以上干部12人。
199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3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17人。
而200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数已达174633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6076人,地(厅)级干部496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6人(次)。
再回头对照十五大的要求,枯燥的数字似乎在暗示着我们又步入了腐败现象久除不尽、愈演愈烈的怪圈。打击腐败固然“成效明显”,遏制腐败却远未得到民众的认可。媒体对腐败大要案的频频曝光更加深了群众对“腐败越反越严重”的认识。
然而我们从腐败的根源入手,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五年来的反腐已然使腐败的蔓延得到有效的控制,只是鉴于腐败的发生和被查处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单纯从数字我们尚不能感受到腐败被遏制的成效。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来源于两个方面。
其一,腐败蔓延与体制、机制和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十五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廉政法律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正在逐步减少。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这在反腐败领域同样得到了印证。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的蔓延,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漏洞为腐败留下了空间。例如,上世纪80年代,国家推行价格体制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大量寻租性腐败机会也由此而产生。其时,通过“走后门”、“批条子”而争相“寻租”的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和“官倒”等腐败行为一度猖獗起来。90年代以后,随着价格双轨制的逐步取消,与此相联系的腐败现象也跟着消退下去。再如,1992年至1996年间,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向深层次推进。由于缺少监督制约方面的制度和机制,以贷款谋私利,以贿赂手段求“上市”,贪污或挪用公款从事炒房、炒地、炒股、搞期货交易等十分严重。十五大以后,党和政府大力整顿金融、证券、股票、房地产市场,使这些领域的市场行为逐步得到规范,相应的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也逐渐趋于缓解。可以预测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制度性腐败的机会在逐渐丧失,为人们所诟病的腐败必将进一步得到控制。
其二,对腐败蔓延的遏制与惩腐力度息息相关。十五大以来,被媒体曝光的桩桩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背后,实则都来源于反腐部门具体的惩腐工作。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有效地震摄了腐败分子。
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腐败现象蔓延的状况还取决于惩腐力度。十五大以来,各级党委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以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着重查办了金融、证券、建筑、海关、人事、司法等领域的案件,贪污贿赂、徇私枉法、买官卖官、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特别是查处了一批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这些案件的查处,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对广大党员干部也起到了有效的警示作用。在不久前,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10个省(区、市)进行了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02年,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69%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事实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
防腐篇:阳光下的苛条密制
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防治腐败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严刑峻法使之不敢腐,苛条密制使之不能腐,高薪清誉使之不愿腐。如果说在防腐战略中“严刑峻法”是保障,“高薪清誉”是前提,“苛条密制”则无疑是三者之中的关键。
“通过深化改革,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这一要求,经过五年的努力,全国的反腐工作已由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新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年来,我们在“苛条密制”的成效上比之查处的反腐大案并不逊色,虽然在群众眼中,这些措施并不如茶余饭后就报章披露的腐败案例来番怒骂痛责更让人痛快。但这些制度和措施却切切实实在遏制腐败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98年7月,党中央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所办的经营性企业一律彻底脱钩。
199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中央党政机关必须在1998年年底前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完全脱钩,不再直接管理企业。1999年,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也开始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
1998年,中央决定首先对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等四部门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随后,其他执收执罚部门也都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
五年中,对防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措施还有:
推出政府对国企管理方式、缉私体制、金融体制等三项重大体制改革。向国有大型企业派驻稽察特派员、建立国家缉私警察队伍、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等重大举措的施行,改变了旧有的体制,堵塞了漏洞。
建立健全有形建筑市场,加强对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建立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工程发包承包制度。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市)级以上城市建立了有形建筑市场。按规定应实行公开招标投标的工程项目,大都纳入了有形建筑市场进行招标投标。较早实行此项改革的苏州市,1998年这一领域新发生案件比1996年下降了85.7%,1999年建设工程项目的报建率和招投标率继续保持了两个百分之百。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及推荐责任制等做法,在各地各部门逐步推广。不久前出台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使这方面的改革走上快车道,对根治用人上的腐败行为将发挥巨大作用。
另外,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会计委派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及领导干部用车、住房等福利待遇货币化试点,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至2000年,中央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廉政建设的党纪政纪条规达20多个,内容涉及党员领导干部行为的多个方面。
实践表明,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强化管理,从源头上防止权力不正当运用,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如果说查办好似“扬汤止沸”,那么体制改革就是“釜底抽薪”。
展望篇:向反腐资源的整合要效率
英国爵士百里渠,在提请成立廉政公署(ICAC)的一份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贪污就像一辆快车,你可以登上去,那么你将变成富翁,你也可以在它的旁边走,知道它的存在但不告发它,那么你会相安无事;但你要是选择站在它面前,那么你肯定会被碾得粉身碎骨。也许,只有像何海生一样曾经勇敢地站在了这辆“贪污快车”前面的人,才会读出百里渠话中的沉重。
腐败这辆“快车”是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它是渺小的,也许当它从你身边驶过时,你通常都会忽略它的存在;但它又是如此庞大,大到足以轻易摧毁一个工厂、一个城镇、一个政党,乃至所有的国家机器。而站在这辆“快车”前面的人需要以多大的勇气、历经多少磨难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又有多少人身处困厄,四面楚歌而最终湮没于岁月。
作为“官方资源”,直接面对腐败这辆“快车”的是各级纪检和各级检察机关。纪检是为保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为政清廉而组建的系统内监督机构。检察机关是由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这两大机关无疑都为中国的反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成绩背后,却隐藏着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现象。
为解决这一弊端,整合官方反腐资源,建立统一的反腐机构,并保证其依法独立行使反腐败案件的查处工作已日渐显得重要。
而在官方反腐资源的整合之外,“民间反腐资源”的利用和整合也应予以重视。因多次上访惨遭割舌的山西岚县青年李绿松,不懈举报终将湖南第一贪蒋艳萍送上法庭的陈荣杰,海南“反腐狂人”何海生等,这些来自民间的反腐英雄和数不胜数的举报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正努力推动着中国反腐事业的进程。“民间资源”与“官方资源”应如何以更科学、更合理的配置以求提高“成本收益率”,已然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现阶段,我们必须为“民间反腐力量”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支持和保护举报人。近年来,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屡见报端。
只因为调查并举报了省政府秘书长情妇的假干部身份问题,使得这位已摇身化为“部长”的三陪女怒火中烧。举报人朱继岚被雇佣的凶手连刺5刀。
山西灵石县英武乡岑泊村村民联名向乡党委、乡政府告发村民委员会主任马计斌种种违纪违法行为,正因为他们的举报,挨打的挨打,有的还遭到绑架……
“不怕人头落地就随你们的便。”在中国正大步走向法治的道路上,出自被举报人的这句话显得格外地震耳,然而我们更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力量使得这句话竟能如此随意地冲破法制的封堵脱口而出?
除了对反腐英雄们的举报予以依法查处外,“官方反腐机构”应理直气壮地支持举报人的行为。国家法律也应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保障做出具体的规定,让英雄莫再流血又流泪。
其二,建立举报补偿制度。当群众为反腐(例如向专门机关举报线索、提供有力证据等)作出了贡献并支付了成本后,政府应及时给予认定和补偿。报载,尽管近年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加大了对举报有功人员的奖励力度,但前往领取奖金的只有寥寥数人,近九成举报人放弃了奖励。举报人的拒领奖励并不意味着建立举报补偿制度的不必要。相反,为了维持群众个人反腐败的积极性,包括反腐官方机构在内的“有关部门”应更多地努力改善举报环境,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援,在法律知识、方法、技巧等方面向群众提供指导。唯其如此,民间反腐资源才能被更好地纳入整个反腐资源配置的序列之中,从而使民间反腐力量成为一种“可再生资源”,以形成良性循环。
也唯其如此,多年后,我们再一次面对何海生这个名字时,才可以了无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