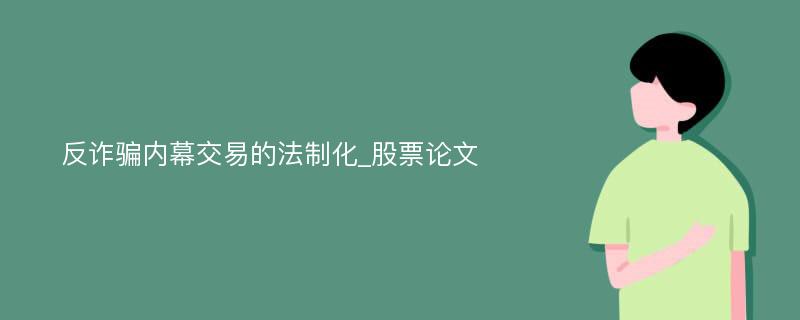
反欺诈型内幕交易之合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证券内幕交易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均已被非法化,实证研究也揭示了在实践中禁止内幕交易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①一国是否实现了这一点已经成为了衡量该国金融法制水平的重要指标。但至少有一种内幕交易应当予以合法化,即反欺诈型内幕交易。
所谓反欺诈型内幕交易,指的是公司内部人或知情人在知晓公司正从事会计、财务方面的欺诈造假行为时,所进行的交易操作。由于欺诈行为曝光后,公司股价必然下跌。所以在没有买空机制时,此类操作一般都是出售而非购入公司股票。这种交易行为因为涉及未公开的、重要的、和公司股价密切相关的信息,且当事人由于职务便利或其他因素而得以提前知晓此类信息并进行了证券操作,是完全符合传统的内幕交易定义的。事实上,至今为止,其在各国也几乎都是同样被禁止的,如我国《证券法》第76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并未豁免任何例外。不过,这样一种内幕交易虽然谈不上高尚,但却有情有可原之处,同时在促进真实股价形成、提早揭露公司欺诈行为、减少投资者和公司雇员的损失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贡献。因此对并未实际参与相关欺诈的知情人的此类交易,可以予以合法化。其不仅有利于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也并无太多不公平之处。
一、反欺诈型内幕交易可以存在的一个前提:举报与揭露方式的低效
按照一般的观念,当公司欺诈行为发生时,知情人所应当做的似乎该是积极举报、揭露此类行为,而非利用这种信息去买卖股票。在美国这样的已通过法律安排保障了公司欺诈举报者之权益的国家尤其如此。但事实上,知情人的举报并非是一种有效揭露、遏制公司欺诈行为的办法,相关成功案例极少。
这是因为:首先,公司欺诈行为的知情人往往是公司的员工或者客户,与公司有着紧密的利益关联。即使他们没有涉入这些欺诈活动,也会由于碍于情面,觉得此事不直接损害自己利益,或担心被打击报复、投鼠忌器等而心存观望,②而不愿意“撕破脸皮”进行举报。③实践中,举报公司欺诈行为的往往是在提拔、薪酬等方面和公司有争议的,甚至已被辞退的人,这往往实质性地降低了他们举报的可靠性(见第二部分的分析)。
其次,大型的公司欺诈行为往往比较隐密谨慎,甚至可以长达数年而不被发现。非直接卷入欺诈活动的公司员工或者客户可能最多只会发现公司行为异常,而不一定能有确凿证据来支撑其举报,故也会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在法治不发达,政府可能会对企业进行无理调查、“敲竹杠”,市场可能会做出非理性反应的国家,心存善意的知情人更是不会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轻易举报。
第三,监管机关未必会认真对待相关举报。公司欺诈行为的直接后果一般是股价的虚高,而股价虚高的公司往往是市场中的所谓明星企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论是美国的安然、世通,还是中国的银广夏、蓝田,在东窗事发前都是炙手可热的名角。监管者本来就是风险规避型的,④他们往往不愿意在证据不确凿时贸然调查此类企业。等到监管者真的进行查处时,大都已经是欺诈行为到了拆东墙补西墙也于事无补,受害者损失惨重、无法弥补之际了。
例如,从1999年开始,一位当过货币经理的投资调查家就开始向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举报马道夫(Madoff)在从事大型财务欺诈,但因为“缺乏确定的证据”而被置之不理。故尽管马道夫的经营有很多明显不合常理之处,SEC在二十多年内一直无所作为,⑤直到2008年12月马道夫的骗局在金融危机压力下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再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著名的Dirks v.SEC案中,⑥一位公司员工向SEC和两个州的证监机构举报本公司造假,但没有获得关注,故他告诉了证券分析师Dirks这一信息,Dirks在验证后,多方帮着举报,也没有得到有效响应。
在中国,由于法治尚不健全,且很多造假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要通过举报来解决上市公司欺诈尤为困难。如1998年大庆联谊公司职工向证监会举报内部职工股发行中的问题,尽管“材料非常详实”,经调查也发现“问题基本属实”,证监会仍然以“查处力量”有限为由,而让“事情一时搁了起来”,直到举报者上访到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处才有了转机。⑦1999年后,农业部内部有人士逐级反映该部应该对其持股的蓝田股份公司上市造假问题承担责任,但一直无果。2001年4月,中国蓝田总公司的原职工向国家工商总局举报公司虚假注资。可同年8月,该举报信由蓝田公司总经理亲手返还给举报人。⑧同年末,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对蓝田公司的质疑所造成的风波更是生动展示了举报在中国是多么不容易甚至危险的一件事情。
2001年10月刘姝威在《金融内参》发表《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短文,认为该公司财务报表不真实。本来,刘姝威应处于一个相对于传统举报者更有利的地位:她依据的是自己对蓝田公司多年财务报表的专业解读能力,而非道听途说,比起大多数举报人所提供的线索要有力得多。作为资深学界人士,刘姝威与蓝田公司无涉,也不必担心打击报复。可事实上,刘姝威被蓝田公司起诉,接到恐吓要杀她的电话和邮件,《金融内参》声明“刘文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在金融界,一些与刘相交甚欢的朋友在面对刘的求助时开始变得躲躲闪闪”,⑨蓝田公司看到了机密刊物《金融内参》上的文章,并请动当地法院和公安局领导亲自进京给刘姝威送传票,⑩都令刘备受压力,直到2002年1月蓝田股份主要高管忽然被刑事拘传。
其他专家出手揭露却不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2001年3月,《证券市场周刊》和《财经时报》就开始有分析师长文对银广夏公司的高速增长及丰厚利润提出9点质疑,但该公司直到8月才泡沫破灭。2006年,长征电器公司监事李杰斌和著名证券律师严义明联手举报长征电器业绩造假,但未被证监会认可,(11)严义明还被指责和起诉。(12)
二、反欺诈型内幕交易合法化的积极理由
综上,举报和揭露方式并不太容易得到监管者认真和迅速的对待,不是很有效率,往往还反而给举报揭露者自身带来不小的麻烦。而这并不能被简单归咎于监管者的官僚主义,故也不能指望通过改善公共治理来改变这一状况。说到底,这是由于举报揭露机制本身缺乏内在可靠的机制所致,相比之下,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反欺诈型内幕交易则在遏制公司欺诈行为方面就相对显得颇有效率和可靠。
(一)反欺诈型内幕交易者切实承担了错指公司欺诈的风险
通常的举报揭露往往得不到监管者重视的一个原因是其本身的可信度问题,即举报揭露者多是“空口说话”、仅给个线索甚至只是方向(可以拿出一堆有力文件来暴露问题的终是少数),本身投入不多,缺乏对其所作陈述之可信性的风险共担机制。
而且,在这些举报者中,基于对职场挫折而报复性举报的相当常见。(13)如四川长虹公司前干部范德均十年来一直举报长虹财务造假、偷税等,四川证监局和绵阳市国税局多次调查均认为无问题。而他本人曾因职务侵占而被判7年徒刑。(14)再如举报长征电器的前监事李杰斌是在其本人及其好友的职务被长征电器解除后开始举报的。(15)虽说这并不必然降低他们举报的真实性,但其中的私人恩怨显然也是不宜忽视的。
其他的举报动机还可能包括获得政府高额奖励的企图和对公司行为的误解。(16)而且,如前所述,对公司的举报还存在着一个逆向淘汰的问题,即动机纯正的举报者往往会三思而行,而动机不纯的报复型举报者反而较少顾忌而出手大胆,这使得公司举报总体质量不高。故而很多中立的观察者都认为举报不一定是出于道德因素,未必具有正义性,而是富于争议性甚至可能是破坏性的。(17)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如果举报都是正当的话,诚实的公司经营者可以通过设立举报奖励制度来表明自己问心无愧,树立形象,可实际上几乎没有公司自愿奖励举报的。(18)一些研究机构如美国公共管理协会也主张建立良好的上下沟通和内部争议处理渠道,以免雇员必须诉诸对外举报来解决问题。(19)
因此,当被举报的对象是一个至少在外人看来信誉良好的大公司时,监管者不重视这些来自被解雇的前员工之类人士的举报,未必是值得指责的。毕竟,监管者如果一一核实各种举报,对自己和调查对象都会带来很高的成本,而收益则值得怀疑。长虹被范德均公开举报后,公司增设了24小时热线回答股东的提问。四川证监局也抽调了“十几个人,两个月内基本上取消了节假日,来专门从事搜集”相关资料,(20)但并无什么收获。
在美国,举报者不需要对举报承担太多证明责任,法律又对举报者进行了保护,故公司不太敢惩戒进行不实举报的员工,加大了举报不可信的问题。(21)有鉴于此,针对安然、世通等重大公司欺诈事件而制定的美国萨班斯(Sarbanes-Oxley)法在规定了较为详细的举报受理机制和举报人保护机制的同时,也规定在受理投诉时需要严格注意投诉与人事争议的关系,以防止遭受不利的人事决定的雇员滥诉。(22)
总之,举报者如果举报错了的话,受损失的主要是公司和监管资源,自己受到的损失较小。相比之下,反欺诈型内幕交易不存在明显的误指公司欺诈的风险,可谓“盈亏自负”。交易者必须仔细考量自己是否真实明确地感知到了公司欺诈行为的存在,是否能断定公司前景注定暗淡。如果他冒昧行事、错卖了不该卖的股票的话,受损失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公司和其他股东。
换言之,反欺诈型内幕交易者虽然在判断正确(如提前卖出涉案公司股票)时可以有效减少损失,但在判断错误(如在不必卖出时而仓皇卖出)时,同样也将遭受损失。对并非公司欺诈参与人的普通知情人来说,这种判断错误的风险并不算太小。他们在这种内幕交易中得到的,并不是在多数普通内幕交易(如在公司宣布利好信息的前夜购入)中可以轻松得到的暴利,而是有着相当大的风险相伴的普通收益。
(二)反欺诈型内幕交易能更有效地产生真实股价、暴露欺诈、减少投资者损失
举报往往不能及时开启监管调查程序,其真正能打动监管者时,通常已经是问题很严重了。所以这往往带来股价的急剧下跌,令刚购买股票的投资者损失极其惨重。而反欺诈型内幕交易者不需要有足够的信息、技巧和勇气去说服监管者,不需要开启庞大而反应迟缓的官僚机器。只消通过一个或几个了解公司真实内情的人的操作,就能使难以让人启齿的信息被输入公司股价,令后者向真正的供求方向移动。公司欺诈行为越重,就会有越多的知情人感知问题的存在并卖出其股票。
如果允许进行反欺诈型内幕交易,就意味着允许内部人快速变现自己获得的内部信息的租值(rent)。所以内部人会更有积极性去投入时间、精力,追寻、调查公司中存在欺诈活动的蛛丝马迹,掌握更多的关于公司的真实信息(否则,他们可能会消极等待,安于现状)。
而市场对内部信息的反应很快。(23)内部人和其他知情人对有欺诈活动的公司股票的抛售必然会被市场感知,(24)股价会早早地得到一种有力的渐进矫正。尽管这种矫正未必是根本性,不一定能从根本上抵消欺诈活动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但比起那种神话破灭时的雪崩式股灾,对无辜投资者的伤害显然更小。(25)美国著名证券法学者Henry G.Manne教授甚至认为,如果允许内幕交易的话,安然一类的大型公司欺诈丑闻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有很多人会知道内情,他们必将去从事内幕交易,这样问题在数月前就会被发现。(26)
中介机构判断股价可靠性的主观能力之不足,尤其凸显了这种内幕交易在反映真实股价方面的意义。即使在美国的成熟资本市场中,本应该帮着发现欺诈和股价虚高问题的中介机构也往往不仅不能配合举报者,有时候还会打压之。如Equity Funding公司案中,直到该公司被交易所停牌,分析师、州监管者、公司审计师、财经记者都没有对有关线索予以重视,而且上述各方的按兵不动还给了其他方不采取行动的理由。(27)最后Dirks在多方帮着举报无效的情况下,(28)索性自己让客户抛售该公司股票了事,才令公司的真实面被市场发现。
在会计机构频频参与造假和机构投资者缺乏识别不实的价格之能力的中国市场中,通过反欺诈型内幕交易来实打实地降低股价水分更为必要。例如,银广夏造假案事发前,是机构投资者重仓持有的对象。虽然名义上他们也对银广夏做过各种调查,但实际情况表明这大多流于形式,如有的基金在银广夏长达7年的造假中,先后十余次的考察未能发现任何端倪。有的基金人士甚至称其之所以打消对银广夏年报漂亮数字的疑虑,只是因为被它一家分厂“盛大的剪彩仪式感染”了。(29)
三、反欺诈型内幕交易合法化的消极理由
可靠的揭示欺诈和促进真实股价产生可谓是反欺诈型内幕交易的正面价值。而此处的几点理由未必能凸现此种交易的功能,但却说明了法律为何不应当否定之。
(一)此类交易者并未窃取公司合法财产
禁止内幕交易的基本法理依据不是这些交易会造成不同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公平。如果穷尽追究一切根据信息优势而进行交易的行为,只是为执法者提出了难以完成的任务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在证券法最为发达的美国,反而原则上不存在一般性的规则来禁止任何拥有内幕信息的人进行交易,(30)而是以交易者另外违反了特定的义务为追究法律责任的前提。这些义务通常是交易者对信息源公司所负的受信(fiduciary)义务,或者是由于采用了非法手段盗用了信息而产生了责任。
换言之,如果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未被侵犯,内幕交易不应当被视为违法。例如一家投资银行如果受客户的委托,对收购要约的潜在目标公司进行调查,并在谈判中获得了未公布的重要信息。后来客户放弃了拟议的收购计划,那即使投资银行利用此等秘密信息去买卖目标公司的股票,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31)进一步的,即使规制机构制定规则,在特定情形下限制一切主体的交易行为,那这样的规则也是值得审视的。例如,美国证交会规则14e-3禁止一切主体在要约收购中根据内幕信息进行交易。(32)但该规则本身的法理依据受到了学者批评,认为其是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著名判例Chiarella案的反动,(33)是利益集团如公司管理层施加向证交会压力的结果。(34)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也一度推翻之,认为规则14e-3不要求事先存在受信义务的这部分规定已超越证交会规则制定权限,不具法律效力。(35)
禁止特定的内幕交易的行为的正当的深层次理由应当是:尚未公开的重大信息属于公司的财产,(36)故内部人不能利用公司财产去损害公司利益,如在知道公司将收购其他公司时,去预先购入目标公司的股票,待价而沽。之所以内部人成为法律规制的突出点,是因为这些特定主体更容易基于职位、委托或信任而独享重要和有价值的信息,故法律对其施加了特殊的、外部主体所不需承担的受信义务,(37)禁止其使用此类信息为自己谋利。或者说,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公司也会事先与内部人约定,令其不得从事此类交易。
进一步的把这种受信义务从公司特定职位拥有者扩展到信息获得者和信息来源之间的关系上,就构成了盗用理论,即任何主体都不能利用从具有信任关系的信息源处获得的信息,进行违背信息提供者本意的交易。(38)例如,公司有权要求为公司服务的各类内外部人保守“公司将有分配股利的计划”这个秘密,不得擅自据之进行内幕交易,直到该信息被公开。
尽管应当被保守的内幕信息这一公司财产的范围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任何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都首先应当是合法的,信息也不例外。而“公司正在从事欺诈活动”这一信息,显然不是公司的合法财产。公司无权要求知情人为其保守这个秘密。(39)所以,知情人“擅自”利用这个信息,既然并未侵害公司的合法财产,也就谈不上违法了。内幕交易和法律所提倡的举报一样,是使得这种关于违法活动的信息不被保密、从而被揭露的一个过程。(40)Dirks案判决的一个要旨是:分析师并不是在某个内部人在违反受信义务后参与分享信息的,(41)所以不需要禁绝使用他获得的内幕信息。而本文的论点略为推进了一步,即对于公司在从事欺诈活动这样的特定信息而言,知情人自身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交易,甚至为了私利向他人提供此种信息,也无不可。(42)因为这并不是公司有权合法保守的秘密,不是公司的合法财产,使用、泄露信息者也不存在违反受信义务的问题。
(二)不存在对其他投资者的不公平
交易相对方不是内幕行为的受害者。即使通过匿名的股票交易成交撮合系统,某人购买了内幕交易者实际卖出的那些股票,也不能说前者的买卖决定是由后者的报价所致。与虚假陈述、操纵市场中的情形不同,这里真实的景象是:交易者已经做出了交易决定后,恰逢内幕交易者做出了方向相反的交易决定(43)而且,在交易相对人购买该公司股票之愿望既定的情况下,内幕交易者的出售还提供给了他一个稍低的股价,多少减少了这些购买方在日后的实际损失。(44)
与反欺诈型内幕交易人同向的交易者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内幕交易者的价格竞争,而可能因此遭受了一定损失。但这并不是否定反欺诈型内幕交易的理由。
这是因为:内幕交易本身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害通常很小,(45)交易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值得怀疑甚至可谓不存在的,(46)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Dirks案中指出的:“在许多情况下,在内幕交易行为和外部投资者的损失之间可能不存在因果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市场价格波动以及投资者们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不完全、不正确的信息行事,市场上总有输家和赢家”,(47)故其在后来的O'Hagan案中索性不提内幕交易是否给投资者造成了实际损失,而是谈论内幕交易对公众信心、市场效率、流动性等可能造成的外部成本。(48)
理性的证券投资者追求的应当是预期回报最大化,而不是在每一次交易中都有回报(payoff),如果一项制度安排在总体上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其就不会在意由此在单个交易中产生的风险。(49)换言之,对投资者来说,在事前(ex ante)实现投资价值最大化才是真正的公平(fairness)。(50)
而反欺诈型内幕交易正是在总体上能促进证券市场总体利益的一种制度,其带来的更准确的股票定价也是公司的管理层和股东的共同利益所在,(51)并由此增加了公司欺诈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提前了其被发现的时间,更好地威慑了潜在的欺诈行为,使其发生机率降低,在整体上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故可谓是帕累托(Pareto)最优的体现:一方的利益增加了,而其他各方的合法利益都没被减损。
所以,即使知情人可以因反欺诈型内幕交易而获利,甚至是在没有付出更多的劳动、没有投入更多的资本的情况下获利,也不能说是对其他投资者不公平、而应被禁止的。正如哈佛大学教授Louis Kaplow和Steven Shavell所指出的,法律政策分析应当以个人福利(well-being of individuals)为指导,法律规则不应该以单纯的公平概念为指导,除非这种公平概念对个人福利有影响。(52)理性的投资者会“一致同意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法律规则,而不看收益是如何分配的”。(53)
退一步说,即使某些公司认为应该确保每一个投资者在每一场交易中得到公平对待,禁止此类交易的决定权也应当交给各个公司,而不是由法律统一禁止。(54)
(三)公司无辜内部人减少损失的客观必要性更强
通过反欺诈型内幕交易,公司内部人固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外部人无法获得的利益,这种“特殊利益”之所以应当被接受,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承担着一种“特殊不利”。对并不该对欺诈行为负责的无辜公司内部人来说,他们很可能是因为公司欺诈行为而受损最重的人。通常,在公司欺诈丑闻曝光后,涉案公司经营会陷入困顿,甚至倒闭。与欺诈活动无关的公司广大普通员工也很可能会因此失业,为这个公司投入的特定人力和物质资本(如对这个公司的运作机制的了解、积累的人脉、与工作配套的住房、配偶工作安排及机会成本等)会急剧贬值,在寻求再就业时也会因为履历上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公司而遭受歧视。此外,在安然等案例中,员工大量的将退休金投入本公司股票,这进一步地加大了他们职位、储蓄两空的危机。所以,即使是所谓举报安然问题的女英雄、该公司高级职员Watkins也事实上从事了抛售安然股票的内幕交易行为。(55)在当代诸多上市公司实行了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制度的背景下,这点十分值得关注。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虽然允许内部人利用其知道公司从事欺诈的信息来获利有所不公,但这种不平等是符合罗尔斯(Rawls)(56)关于“让条件最不利的人获得最大利益”的原则的。(57)何况,这种行为产生的财富分配效应还受到了两个重要的限制:
一是在很多情况下,如在中国没有买空机制的背景下,这些内部人也不过是消极的减少损失,而非积极的增加收入。
二是现代公司法对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这些人往往是更重要的知情者和持股更多的人)出售股票有严格的限制,他们所能减少的损失极为有限。如我国《公司法》第142条规定,这些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章程可以对这些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四)强于知情人通过交易对手公司的股票来规避风险
主张一般性的内幕交易都可以合法化的学者曾指出:担心公司管理者如果能内幕交易,就会故意弄低公司股价,从卖空公司股票中获利的看法是没道理的。原因之一就是管理者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58)他可以购买一个竞争对手公司(如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股票。这样他一方面可以弄坏本公司的经营,另一方面通过持有对手公司的股票而牟利。(59)这不仅是合法的(除非公司明文禁止这种行为),甚至可能比交易本公司的股票更有利可图。(60)
类似的,知情人在察觉公司的欺诈行为时,即使不被允许利用此种信息卖出公司股票,也仍然可以购入对手公司的股票,堤内损失堤外补。据信息经济学的原理,拥有额外信息的人总是可以找到实现信息租值的办法,区别只是在于通过何种方式来合法的实现。相比之下,反欺诈型内幕交易能较早地让本公司股票恢复到正常水平,避免股价有一个剧烈的“跳水”,公司及其他股东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这种信息租值。而信息持有人如果通过购入对手公司股票来减少风险,则意味着租值被消散到了其他公司,而对本公司毫无裨益。
(五)不存在普通内幕交易中可能存在的弊端
一般性地主张公司内部人可以从事内幕交易的学者也承认内幕交易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如诱使内部人通过释放信息、增强股价波动性来盈利,甚至主动制造坏消息等。(61)这也可谓是寻常内幕交易应当被禁止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问题显然不存在于反欺诈型内幕交易中,特别是在本文明确反对把从事欺诈活动的主体归入此种内幕交易的适格主体的前提下。
四、反欺诈型内幕交易合法化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一)适用范围上的限制
反欺诈型内幕交易的适格主体不包括欺诈行为本身的参与者。只有无辜但知情的人才能从事此类内幕交易活动。
虽然欺诈行为的参与者如果从事此类内幕交易的话,也能在客观上产生使股价趋于真实等效应。但根据“任何人无权从恶行中受益”的基本法理,他们从事内幕交易的行为不应获得豁免。毕竟,他们只不过是在减弱自己参与的一个恶行的后果罢了。他们对于这种信息(公司正在从事欺诈活动)的获得并非是经过“诚实的努力”所致(尽管可以说他们在实体层面上生产出了这些信息),故没有合法的财产权和由之而来的处置权。(62)允许他们进行此类内幕交易,还会增加他们进行欺诈活动的激励。(63)
(二)不会过分延迟欺诈事实被揭露的时点
有人认为,如果内幕交易可以合法化的话,知情人可能会先进行内幕交易操作,然后再考虑揭露欺诈,从而造成一定的延误。(64)这一指责并不成立,原因在于:
首先,即使是就一般的内幕交易而言,其存在对信息披露造成的延迟影响也没有得到实证检验支持。(65)
其次,根据市场有效性理论,可以认为内幕交易向市场注入了信息,通过对股价及时与正确的调整,就已实现了“实质上”(virtual)的信息披露,另外的举报几乎是多余的。(66)
再次,有很多欺诈行为本来就是不会被揭露或举报的,或者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被有效揭露的。相比之下,反欺诈型内幕交易使信息更快、更可靠地获得了揭露。(67)
第四,对一个至公无私的知情人来说,其能否从事反欺诈型内幕交易,都不会影响他在什么时刻进行举报或揭露。而一个优先考虑自己利益的知情人不会在公司状况还不错的情况下贸然去举报,以免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如职位、工资等。其会等到问题很严重、危及自己将来更大的利益(如公司产生垮台的风险)时才会去举报。这时候即使赋予其从事内幕交易的权利,也只不过是令其增加了一个要安排在前面的动作而已,对举报的时点的影响甚微。
第五,当反欺诈型内幕交易者卖出股票后,其未必会愿意看到公司股价继续处于虚假的高位,可能反而会有动因去告诉监管者或媒体公司欺诈行为的存在。倘若卖空机制可以存在,他们更是会积极去披露所掌握的欺诈行为存在的信息,推动股价的下跌。而如果不允许他们从事内幕交易,他们倒反而乐见公司股价继续保持虚假繁荣。
注释:
①参见Utpal Bhattacharya & Hazem Daouk,The World Price of Insider Trading,57 J.Fin.75(2002)。
②安然、世通、Adelphia等美国公司倒台后,很多由此受害的无辜员工、小型供应商、当地社区和依赖这些公司的捐赠的慈善组织把当初举报的人单独拿出来指责,认为是他们制造了麻烦。见Jonathan Macey,Corporate Governance,Promise Kept,Promise Brok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166。
③如安然公司倒台后被追捧的所谓举报女英雄Watkins只不过是努力说服过公司首席执行官采取私下自我纠正的措施,免得从外部招来大麻烦。而且她的动机是防止自己的前途随公司一起破灭。参见Jonathan Macey,同上注,pp.170-172。Dan Ackman,Sherron Watkins Had Whistle,but Blew It,Forbes.com,Feb.14,2002,http://www.forbes.com/2002/02/14/0214watkin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8月30日。
④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80。
⑤F.N.Baldwin,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RICO)and the Mafia Must Now Welcome Organizational Crime,17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 404(2010),409-412.
⑥Dirks v.SEC,463 U.S.646(1983).
⑦“大庆联谊:内部职工股的泛滥”,载《国际金融报》2010年12月16日。
⑧“四司局官员出演‘蓝田神话’历数孙鹤龄几大罪”,载《新京报》2005年9月27日。
⑨庞义成:“恶梦何时了结?学者写文章炮轰蓝田遭追杀”,载《南方周末》2002年1月18日。
⑩张念庆:“刘姝威对阵蓝田谜局何日能解”,载《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11日。原洪湖市委副书记、市长也曾从蓝田处受贿。
(11)参见“证监会答复:长征电器‘三宗罪’不成立”,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8月28日。
(12)严义明:“举报长征电器与利益集团无关”,载《东方早报》2006年9月4日。傅光云:“上市公司起诉律师第一案 长征电器索赔300万”,载《证券时报》2006年9月8日。
(13)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70,196。
(14)骆海涛:“长虹范德均十年战未休”,载《南方周末》2010年6月3日。
(15)“长征电器监事李杰斌自述:‘深喉’背后的‘深深喉’”,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月19日。“长征电器称‘深喉’涉嫌经济犯罪”,载《中国证券报》2006年5月8日。
(16)如美国《反欺骗政府法》(False Claims Act)规定对任何联邦政府资金使用中的虚假申报(false claim)进行举报者,都有权获得高比例的经济奖励。有研究指出:这催生了很多跟内幕交易者一样,只是出于逐利动机而行事的举报者,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p.168-170。又如,业界对2010年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对举报的高额奖金规定的一个重要疑虑也在于有些心怀不满的公司员工可能做出不实举报。见Incentives to Spark Surge in Tip-Offs,Financial Times,2010-8-9,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995/ce。国内一个可以对照的例子是多个城市都试行过有奖举报交通违章的做法,但在付出数百万元奖金后,违章有增无减,职业举报者倒应运而生。见“武汉将继广州深圳后取消有奖举报交通违章”,载《华西都市报》2010年10月7日。
(17)参见Gerald Vinten ed.,Whistle Blowing:Subversion or Corporate Citizenship? London,Paul Chapman,1994。
(18)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p.195-197。
(19)参见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Position Statement on Whistle Blowing,http://ethics.iit.edu/indexOfCodes-2.php?key=12_97_419,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8月30日。
(20)骆海涛,见前注(14)。
(21)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86。
(22)参见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97。不过,也有人认为举报和奖励举报都是有意义的,只不过萨班斯法等的具体规定值得改进,见Terry Morehead Dworkin,SOX and Whistleblowing,105 Michigan Law Review 1757(2007)。
(23)Plott & Sunder,Efficiency of Experimental Security Markets with Insider Information:An Application of Rational-Expectations Models,90 J.Pol.Econ.663(1982).
(24)现代证券法往往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申报和公告股份持有状况(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第3.1.7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所持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动的,应当及时向公司报告并由公司公告),这些人的交易行为将释放更强的信号。
(25)在普通法下,对内幕交易是一般性允许、例外性禁止,而一个区分标准就是对股价的影响,Dennis W.Carlton & Daniel R.Fischel,The Regulation of Insider Trading,35 Stan.L.Rev.857,pp.860,883-884。内幕交易对股价和买卖者的影响之分析,还可见Haddock and Macey,A Coasian Model of Insider Trading,80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449,1452-1455。
(26)Larry Elder,Commentary,Legalize Insider Trading?,Wash.Times,June 15,2003,http://www.washtimes.com/commentary/20030615-112306-2790r.htm,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8月30日。更多理论陈述可见Henry G.Manne,Insider Trading and the Stock Market,New York,Free Press,1966。Manne教授系一位主张所有内幕交易都可合法化的重要学者。
(27)参见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p.178-179。
(28)认为Dirks违法的Blackmun等少数派大法官也承认,在这个案子中,要求当事人不交易而是去披露信息,客观上有困难,证交会的工作需要改进。
(29)“银广夏造假案追踪:理财专家缘何踏入‘陷阱’”,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10月1日。
(30)Robert 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West Group 1996,法律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p.433.判例可参见Santa Fe Industries,Inc.v.Green,430 U.S.462,474-477(1977)。不过这一点不乏支持者,如Chiarella v.United States案中,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的上诉法院意见和最高法院少数派意见认为任何人利用其他人不能获得的重要信息都构成欺诈。
(31)参见Walton v.Morgan Stanley & Co.,623 F.2d 796(CA2 1980)。
(32)17 C.F.R.§240.14e-3(1982),该规则得到了一些判例的支持,如U.S v.Chestman,2d Cir.1991。
(33)Chiarella v.United States,445 U.S.222(1980).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披露或戒绝义务根源于业已存在的信任关系(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confidence),对内幕信息源公司没有受信义务的主体不会违反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则10b-5。
(34)参见Haddock and Macey,A Private Interest Model,with an Application to Insider Trading Regulation,30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1,1987,pp.316-317。对该规则的评述还可参见Robert Clark,Corporate Law,Little Brown,1986,p.354。
(35)United States v.O'Hagan,521 U.S.642.但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第八巡回法院的判决,并简略地指出,考虑到该规则所针对事项的特殊性和适用的有限性,该规则并未超越证交会的权限。最高法院的这一结论似乎是出于一个公共政策考量,而不是法理演绎。
(36)参见Janet Dine,Company Law,4th edition,Palgrave MacMillan 2001,法律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p.258。
(37)参见Chiarella v.United States,445 U.S.232-233,Dirks v.SEC,464 U.S.646(1983)。对美国法上一些重要判例的介绍,可见杨亮:《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91-132。张建伟等:“美国内幕交易执法理论演进”,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廖凡:“美国证券内幕交易经典案例评介”,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gid=335566358&db=art,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8月30日。
(38)参见United States v.Newma,664 F.2d 12(2d Cir 1981),cert.denied,464 U.S.863(1983).United States v.O'Hagan,U.S.,117 S.Ct.2199(1997).
(39)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82。
(40)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p.183-185。
(41)Dirks v.SEC,463 U.S.646(1983),p.667.
(42)Fischel指出,最高法院Dirks案判决有一个问题,即只关注内部人向Dirks披露公司欺诈是合法的,而忽视了这会导致股价大跌,股东受损。但他也指出,从事前(ex ante)观点看,披露欺诈能减少欺诈,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所以披露还是符合受信义务的。由此,内部人为了好处而披露欺诈,也能在事前提升公司价值、最大化股东利益,故并无不可。最高法院把Dirks的信息源是否直接或间接获取利益和Dirks的行为合法性挂钩的观点存在偏差(例如,难道内部人无偿向路人散布内幕信息,就是合法的么)。Daniel R.Fischel,Insider Trading and Investment Analysts:An Economic Analysis of Dirks v.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13 Hofstra L.Rev.127(1984),138-140.笔者完全同意此看法。
(43)当然,这个理由可以推广适用于所有的内幕交易,相关论述可见Langevoort & Gulati,The Muddled Duty to Disclose under Rule 10b-5,57 Vand.Law Review 1639(2004),1676。J.D.Cox,Insider Trading and Contracting:A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 "Chicago School",1986 Duke L.J.628,635.Frank H.Easterbrook,Insider Trading,Secret Agents,Evidentiary Privileges,and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1981 Sup.Ct.Rev.309(1981),311,324.William Carny,Signaling and Causation in Inside Trading,36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863(1986-1987),890.
(44)参见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p.192-193。Henry G.Manne,ed.,The Economics of Legal Relationships: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West Publishing Co,1975.
(45)Elkind v.Liggett & Myers,Inc.635 F.2d 156(2d Cir 1980).
(46)参见Manne,见前注(26),p.91。Michael P.Dooley,Enforcement of Insider Trading Restrictions,66 Virginal Law Review 1(1980),33.耿利航:“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功能质疑”,《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页79-81。
(47)Dirks v.SEC,463 U.S.646(1983),p.666.
(48)参见Thomas Lee Hazen,Treaties o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6th ed.,West Publishing,2009,p.357。Robert Thompson,Insider Trading,Investor Harm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50 Case West.Res.L.Rev.291(1999-2000),299-300.耿利航,见前注(46),页91。
(49)Frank Easterbrook & Daniel R.Fischel,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61.该书中译本可见《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0)同上注,p.110。对不平等和更高回报之间的权衡,见chapter 5。
(51)参见Henry G.Manne,The Case for Insider Trading,Wall St.J.,Mar.17,2003,at A14.http://online.wsj.com/article/0,,SB104786934891514900,0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8月30日。
(52)Louis Kaplow & Steven Shavell,Fairness Versus Welfa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7.
(53)Id.,at 124.事实上,说内幕交易能通过激励机制“把饼做大”,一直是主张其应当合法化的学者强调的一点,Carlton and Fischel,见前注(25),p.881。
(54)参见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91。如何有效率的在公司和国家间分配内幕交易禁止权,见Carlton and Fischel,见前注(25),pp.894-895;Easterbrook & Fischel,见前注(49),pp.262-264。
(55)参见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p.176-177,189-190.
(56)参见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83(1971),中文版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又可见Daniel Markovits,How Much Redistribution Should There Be?,112 Yale L.J.2291,2326-29(2003).
(57)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90.
(58)其他原因包括管理者系集体工作,单个人较难暗地使坏;弄坏公司会影响其自身作为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价值等。
(59)Carlton and Fischel,见前注(25),pp.873-875.也可见Easterbrook & Fischel,见前注(49),p.268.Ian Ayres & Joe Bankman,Substitutes for Insider Trading,54 Stan.L.Rev.235(2001).
(60)Heather Tookes,Information,Trading and Product Market Interactions:Cross-Sectional Implications of Insider Trading,The Journal of Finance,Volume 63,Issue 1,379-413,February 2008.
(61)参见Easterbrook & Fischel,见前注(49),p.260。
(62)参见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bk.Ⅱ,ch.V,at 285-302(Peter Laslett ed.,3d ed.,Cambridge Univ.Press 1988)(1690)。中译本见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17-32。
(63)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87。
(64)参见Mendelson,Book Review,117 U.Pa.L.Rev.470,p.489。该文是对Henry G.Manne,Insider Trading and the Stock Market(1966)的评论。Schotland,Unsafe at Any Price:A Reply to Manne,Insider Trading and the Stock Market,53 Va.L.Rev.1425,1440-42.
(65)Michael P.Dooley,见前注(46)。
(66)Manne,见前注(51)。该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内幕交易合法化的话,各种举报、披露要求和监管都将是多余的。披露制度也只不过是为了事后证明价格的变动是合理的。
(67)Jonathan Macey,见前注②,p.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