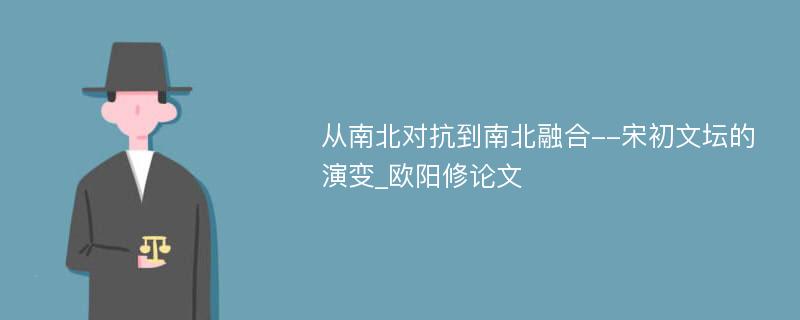
从南北对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坛演变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宋初文坛基本上沿袭了唐朝故态,自天圣以后至庆历期间古文运动的全面展开,文坛始现新变,这时距宋代建国已近百年之久了。在此期间,文坛所呈现的从南北对峙到南北融合的艰难历程,为我们认识宋初为何以近百年的时间才实现从沿袭到新变的转折,提供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本文将从南北文坛的差异与对峙、南文北移与南北交汇、南北文坛的冲突与融合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南北文坛的差异与对峙
以韩愈古文为旗帜,以柳开为先驱,中经穆修等人的努力,后由欧阳修的大力倡导,文坛桴鼓相应,文风丕变,古文终于战胜了偶俪时文。北宋古文运动所经历的这一历程,已成为学界的常识,然而,对于欧阳修与柳开等人在倡导韩愈古文时的不同路径,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韩愈古文成为他们的宗尚对象,原因不仅在于有别于时文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文以载道”的内涵。吴曾指出:“程正叔云:‘韩退之晚年所为文,所得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是倒学了,因学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吴子经耳。子经《法语》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①,程颐所说的“有所得”,就是指“文以载道”。但韩愈在文道的顺序上却先文后道;欧阳修也因学文而及道,与韩愈一样经历了因文及道的“倒学”之路;柳开推崇韩愈也以文章为前提,但“以古道发明之”②,因好道而及文,其路径与欧阳修不尽相同。扩而言之,欧阳修为江南庐陵人,柳开生于北方大名,他们因文及道与因道及文的不同路径,是否代表了南北士人在文道关系上的两种不同取向?
柳开为开宝六年(973)进士。他“以古道发明”古文,变革“卑弱”的“五代体”③,目的在于师经探道,明道垂教。柳开主张的“道”与“文”,即其《应责》所谓“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④;而“文章为道之筌,筌可妄作乎?……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⑤。这一观念决定了他对韩愈古文的态度。柳开在24岁时说:“读先生(韩愈)之文,自年十七至今凡七年”⑥;三年后却指出:“幼之时所以名者,在于好尚韩之文,故欲肩矣。逮乎长而成所以志者,在乎执用先师之道也,故亦将有所易矣。”⑦究其原因,不外有二。首先,韩愈毕竟是极具才藻的文学家,他虽以古文传导“先师之道”,走的却是因文及道的“倒学”之路,难免“辞之华于理”之“恶”;其次,柳开于道不是习而得之,而是生而知之,用他的话来说;“我之所得,不从于师,不自于学,生而好古,长而勤道”⑧。并认为“圣人之文章,《诗》、《书》、《礼》、《乐》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学焉。”但“韩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则从于俗矣”。因此,他晚年自称“曾学文章,爱扬雄、孟轲之述作”⑨,干脆将韩愈古文拒之门外。事实表明,柳开对“五代体”有所反拨,但因片面强调道的作用,忽视了文章自身的特性,无法获取韩愈古文的精髓。据载,柳开临终时,“语门人张景曰:‘吾十年著—书,可行于世。’景为名之曰《默书》。辞义稍隐,读者难遽晓也”⑩。《默书》是柳开晚年之作,张景赞誉“其言渊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窥其极”(11)。但正因为这种过于“渊深”简古的风格,导致了“辞义稍隐,读者难遽晓”,故柳开古文“卒不能振”(12),也在必然之中了。
然而,文学史上却将柳开置于十分重要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范仲淹所说的:“懿、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13)。这使柳开的文名得以张扬,尤其是张景《柳公行状》所宣传的“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14),对后世评价柳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昭示了作为北方传播古文的一支重要队伍,柳开及其门人师经探道的盛况,以及北方文坛的基本取向。在宋初北方,柳开及其门人和以陈抟、种放为首、以孙复、石介为首的三支队伍在传播古文中,取向一致,声息相通,融合成了北方文坛的主力军;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员生长在黄河流域,尤以洛阳与齐鲁两地为多。宋人以为:“大河自积石行万里出砥柱,旁缘太行,至大伾斗而东,下走大海。长冈巨阜,纡余盘屈,以相拱揖抱负。小则绵一州,大则连数郡,其气象如此。而土风浑厚,人性质朴,则慷慨之士,固宜出于其中。”(15)这虽不乏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但环境影响人的成长不可小觑。据载,洛阳张齐贤“常作诗自警,兼遗子孙,虽词语质朴,而事理切当,足为规诫。其诗曰:“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无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个如端的,天应降吉祥”(16)。史称“洛邑为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旧族”(17)。所谓“衣冠旧族”,就是像张齐贤这样的家族。以这种家族为文化支架的洛阳地区,决定了其“民性安舒”、“人性质朴”区域人文性格;齐鲁士人也“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18),同样是尚质重道,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往往因好道而及文。柳开一支证明了这一点,其余两支也概莫能外。
关于陈抟、种放一支的师承谱系,晁说之《传易堂记》有清晰的记载:“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19)可见维系这一师承谱系的主要是六经中的《易》学。陈抟门人种放“与母隐终南山豹林谷,结草茅为庐,日以讲习为业,后生多从之学问,得其束修以自给。著书十卷,人多传写之”(20),因而在北方又拥有众多弟子。在种放的弟子中,提倡古文最有力的当推穆修,其突出表现就是整理韩愈与柳宗元的文集,使韩柳古文广为传播。邵伯温说:“时学者方从事声律,未知为古文。伯长首为之倡,其后尹源子渐、洙师鲁兄弟,始从之学古文,又传其《春秋》学。”(21)但无论穆修抑或尹氏兄弟,他们学作古文,并非为文而作文。穆修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专雄诗歌,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才“大吐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其“辞严义密,制述如经”,古文始兴,道统始明(22)。说明了他整理韩柳文集,注重的首先是“如经”一般的传道“制述”,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古文。至于尹洙古文,欧阳修欣赏其“简而有法”(23)的同时,又“意犹有所未足”(24)。因为“尹洙抗志希古,糠秕六代,唐人舍韩柳外,亦视同桧下”(25)。他虽不像柳开那样片面强调道的作用,但在尚质重道与因道及文中,继承了柳开以来过于简古的创作风格。
以孙复、石介为首的一支均为专经之士,史称“东学派”。“‘东学’之倡,自孙、石二先生始。……鲁人既素重此二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莫不嗟叹。祖无择、姜潜、龚鼎臣、张洞、刘牧、李缊,皆其门人”;贾同、刘颜、士建中为同调。孙复主研《春秋》,著有《尊王发微》,“齐鲁学者多宗之”,富弼、范仲淹等“荐其道德经术宜在朝廷”,广为“世法”(26)。在文学上,孙复反对当时“率以砥砺辞赋,唏觇科第为事”,以及南朝“沈、谢、徐、庾妖艳邪哆之言杂乎其中”的“无一言及于教化”之文,认为“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27)。石介也竭力主张“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28)。同时又十分推崇柳开,他早年所作
《过魏东郊》诗谓柳开“六经皆自晓,不看注与疏。述作慕仲淹,文章肩韩愈。下唐二百年,先生固独步”(29)。后又认为“唐去今百余年,独崇仪克嗣吏部声烈,张景仅传崇仪模象,王黄州、孙汉公亦未能全至。崇仪、贾公踈、刘子望又零丁羁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视于唐差劣”(30)。在石介的心目中,柳开的古文成就超过了王禹偁;进而宣称:能发扬韩愈古文的仅五人,其中功绩最大的是柳开,次为张景、贾同、刘颜、士建中(31)。
石介与欧阳修同为天圣八年(1030)进士。天圣八年至庆历年间,是南北对峙、文道交争,也是融合南北、化合文道的关键时刻。交争双方以石介与欧阳修为代表。石介视文为道德经术的附庸,极端推崇柳开,目的在于清除西昆作家“专事声律”的偶俪时文。欧阳修同样以“先师之道”相号召,却不以杨、刘时文为非,早年又“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32)。这与他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欧阳修生活在南方文学世家,其父欧阳观“本庐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进士第者六七人。观少有辞学,应数举,屡阶魁荐。咸平三年登第”(33)。其母郑氏“世为江南名族”,欧阳修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於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34);并“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为欧阳修后来“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35)的文学成就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换言之,欧阳修因文及道,众体兼备,各极其工,终成古文运动的领袖,与他早年的文学熏陶及其文学功底是密不可分的。
其实,研习声律,崇尚文艺是五代以来江南人文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事不断,文艺人才日趋凋零。叶梦得说:“唐自懿、僖后,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谓之空国无人可也。”(36)而“于稽其世,唐末诗人如罗隐、韦庄、韩偓辈,往往流落江南、吴越、荆楚诸国”(37)。因为江南相对安定,江南诸国国主又崇尚文艺,礼贤下士。如南唐“以文艺自好”的李昇专门“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延见士类,谈宴赋诗,必尽欢而罢,了无上下贵贱之隔”,李璟、李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李昪以来三世,“天下瓜裂,中国衣冠,多依齐台,以故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38),营造了尚文重艺的人文环境,为宋初江南文学人才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晁说之指出:“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以词章进,刁衎、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欧阳少师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39)他们就是从尚文重艺的江南走向北方,并在因文及道中,为朝廷建立“纪纲法度”的。其中广陵徐铉、建州杨亿、抚州晏殊、庐陵欧阳修前后四代,又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杨亿“夙昔师范徐骑省(铉)为文”(40);而晏殊“幼能文,李虚己知滁州,一见奇之,许妻以女,因荐于杨大年,大年以闻,年十三。真宗面试诗赋,疑其宿成,明日再试,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书省正字,令于龙图阁读书,师陈彭年。彭年亦抚州人”(41)。李虚己、陈彭年也是习声律、尚文艺之士。李虚己与杨亿同乡,“少从江南先达学作诗”,后与南丰曾致尧唱和,并将其诗法授晏殊(42)。陈彭年为徐铉弟子,在徐铉去世的次年,即编其文集并为之序,晏殊则于23年后又复为徐集作序。晏殊与其前辈杨亿均以神童举荐入朝,故李虚己将晏殊纳为乘龙快婿后,荐于杨亿;杨亿《晏殊奉礼归宁》云:“垂髫婉娈便能文,冀子兰筋迥不群。南国生刍人比玉,梁园修竹赋凌云”(43)。对晏殊关爱有加,赞美之至;当晏殊知贡举时,又将门下士、南国能文者欧阳修擢为第一。这种代代相惜的一个重要纽带,就是南士尚文重艺、因文及道的共同取向。
作为太宗至仁宗年间南国士人的代表,徐铉、杨亿、晏殊、欧阳修既前后传承,又各为文坛盟主,与北方柳开、种放、石介一系相并而行,在因文及道与因道及文的不同路径上,构成了宋初文坛南北对峙的两大阵营;造成对峙的原因在于南北不同的人文环境与性格。治平元年,欧阳修与司马光的争论,从更为广泛的层面揭示了这一点。司马光有感于西北诸路举子因不善文学而进士及第者少的历史,指责“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的“用人之法”,有违孔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说,希望逐路取人(44)。欧阳修却指出:“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应“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若逐路取人,必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有违以艺取人的祖宗之法(45)。南人好文重艺,北人尚质重道的差异,导致了南北士人在科举上的对峙与争论,文坛上出现南北对峙的两大阵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南文北移与南北交汇
诚如郑方坤所说:“五代中原多故,风流歇绝,固不若割据诸邦犹能以文学显。”(46)五代北方无文的历史在赵宋开国之初并没有完全终结,类如京兆人杨砺“为文无师法,诏诰迂怪”(47)的现象,在北士中屡有所见。因此,赵宋王朝要建设适应新政权的文化事业,仅靠北人是不够的,还需要擅长文学的南士加盟其中。太宗统一南北后,大量南方文士北上为官,并占据了朝廷许多文官之位。如“太平兴国元年,汤率更悦、徐骑省铉直学士院,王梓州克政、张侍郎洎直舍人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48)。士北上,参与新朝的文化建设,从事文学创作,对改变五代北方士人长期不文的局面,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加上“国初每岁放牓,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49),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全面实施,加快了南文北移的进程,也推进了北士对南方文学的认同与南北文坛的交汇。
在太宗朝的南文北移中,徐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铉自南唐入宋,“得为王臣,中朝人士皆倾慕其风采”(50);其“儒笔履素,为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佑与之交款;李至、苏易简咸师资之”(51)。陈彭年又指出:“唐氏隽义为多,比百王而虽盛;文章所尚,方三古而终殊。于是韩吏部独正其非,柳柳州辅成其事。……其有道冠人伦,才为世表,令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复见之徐公(铉)矣。”(52)在多数宋人那里,柳开是宋代倡导韩柳古文的先驱,陈彭年却视徐铉为韩柳的继承者。这就是说,在柳开之前,徐铉就已学韩柳了。不过,柳开倡导韩柳,旨在张扬“古道”;徐铉崇尚韩柳,则主要体现在诰命辞章。徐铉在南唐与宋初都曾掌翰林之职,其辞章为世所重。“太平兴国初,李昉独直翰林,铉直学士院,从征太原,军中书诏填委,铉援笔无滞,辞理精当,时论能之”(53),于此可见一斑;同时也开启了宋初辞章取径韩柳的风气。杨亿称扬李沆的文学成就时说:“公之书命也,启迪前训,润色鸿业,善为辞令,长于著书,考三代之质文,取两汉之标格,使国朝谟训,与元和、长庆同风者。”(54)所谓“元和、长庆”就是指韩柳元白的文风。李沆诰命辞章的取径便始于徐铉。而徐铉的弟子入宋以后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郑文宝“水暖凫鹭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之诗,时人谓“不减王维、杜甫”(55);又其“杜曲花香浓似酒,灞陵春色老于人”诗句,“亦为时人所传诵”(56)。诚然,以徐铉为首的第一批贰臣的创作与李煜入宋以后的词一样属于五代南方文学的余波,但对南文北移不乏推进之功。
需要指出的是,在太宗时期出仕新朝的南方文士,绝大多数属于归降之士或伪官之后。他们面对新的政权,存有无法稀释的避嫌心理,即便是徐铉也不能例外。譬如:“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57)。既要存旧主之义,又要不得罪新主,可谓前恐跋胡、后恐疐尾。徐铉如此,其他南方文士的心境,也就不难想见了。南士的避嫌心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太祖与太宗。据载,“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58)。后又盛传太祖所定“不用南人为相”的“国是”,宣称太祖御笔“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并“刻石政事堂上”(59)。实际上,太祖、太宗对南人的防范,当戒南方未真正臣服或意有专指,与其说是“国是”,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猜忌。二是北士。他们以大国胜利者的心态,视南方为“下国”、南方文化为“非正统”(60);认为“南人轻巧”,“南人误国”,“不宜冠多士”(61)。在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中,这种观念常为北士用来攻击南人的重要依据。神宗以后,南人的地位已固若金汤,难以撼动。在宋初,尽管徐铉等第一批贰臣为新朝所用,接着又有大批读书人入仕,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高于北人,渐渐对北方士人构成了威胁,但羽毛未丰,地位未固,所以顾忌重重,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成就。太宗时期,南士笔下没有创作出具有杰出成就的作品,就是被称为文坛“大手笔”的徐铉,在其《骑省集》后十卷的入宋之作中,多数是用于酬唱或点缀新王朝的升平,很少有发自内心的声音。
徐铉等人的这种避嫌心理延续到了第二代的南方文士身上。真宗咸平五年,陈恕知贡举,“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6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真宗时期,南文北移却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如果说太宗时期以徐铉为首的南士北上,揭开了南文北移的序幕,那么真宗时期以杨亿为领袖的西昆作家群的形成,则在官方完成了南文北移的任务。
真宗景德二年(1005),杨亿受诏修《历代君臣事迹》(即《册府元龟》)。修书之余,杨亿在部分修书者和朝臣之间发起了一场著名的诗歌酬唱活动,酬唱的作品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结集,名为《西崑酬唱集》。集中所收共17人,除任随占籍难以确定,杨亿、钱惟演、钱惟济、丁谓、刁衎、舒雅、崔尊度、薛映、刘骘、张秉等十人来自南国,张咏、晁迥、李维、李宗谔、刘筠、陈越等六人产自北方。这表明从事唱酬的主体是南人。在南人中,钱惟演、钱惟济为吴越王之后,舒雅、刁衎、张秉之父与杨亿之祖仕于南唐,薛映之父仕于西蜀,丁谓之祖仕于吴越,均为被猜忌的伪官之后。令他们欣喜的是,这场酬唱活动得到了北士的认同与配合。
在参与酬唱活动的六位北人中,年龄最小的是刘筠、陈越。刘筠是在杨亿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咸平二年(999)三月,“命吏部侍郎陈恕、知制诰杨亿同试诗、论各一首于银台司,第其优劣,得前大名府馆陶尉刘筠”等六人,刘筠为第一(63);事后陈恕又对杨亿说,得刘筠“不愧于知人”(64),表明了这两位南方主考官对刘筠的赏识。六年后,刘筠参与杨亿发起的酬唱活动,追随座主创作实践,也就势在必然了。陈越也经杨亿奖拔而闻于世,是杨亿的追随者。(65)在其余四人中,张咏与王禹偁齐名,长杨亿28岁,“秉笔为文,落落有三代风”(66)。晁迥是两宋文化史上具有显著地位的晁氏家族中显名于政坛的第一人,长杨亿23岁,其主要著作《法藏碎金录》与《道院要集》类属释、道,但他欣赏白居易诗(67),对文学不无爱好之情。李维乃宰相李沆之弟,长杨亿13岁,他在“雍熙中,以文雄于场屋”(68)。李宗谔为李昉之子,出身相门,成名较早,长杨亿9岁,其文“雅而理明白,气和且清,真可贵也”(69),也为好文之士。他们以长者的身份加入以杨亿为首、以南人为主体的酬唱活动,显然是对杨亿文学才能与文学追求的认同,以及对南士北上与南文北移的配合。这种认同与配合是建立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需求之上的。
淳化三年三月,“赐太常寺郎杨亿进士及第”,“亿时年十二(按当为十五),读书秘阁,拟《文选·两京赋》,作《东、西京赋》二道以进。太宗宠而嘉之,诏学士院试《舒州进甘露颂》,即时而就,帝益赏其俊才。故有此命”(70)。杨亿的《舒州进甘露颂》已散佚,在现存其《武夷新集》中却多雅颂之作。在杨亿看来,“皇宋二叶,车书混同;端拱穆清,详延俊义;皋夔稷卨,日奉吁俞;枚马严徐,并在左右。礼乐追于三代,文物迈于两汉”,正是需要恢复“雅颂”之道的时代;而“雅颂之隆替,本教化之盛衰:傥王泽之下流,必作者之间出。君臣唱和,赓载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赋而为礼,废之久矣,行之实难。非多士之盈廷,将斯文之坠地”(71)。因此,颂扬当朝盛世成了杨亿一生创作的主旋律,也使其诗文呈现出一派雍容典雅的气象。这一方面改变了在乱世中形成的“气格摧弱,沦于鄙俚”的五代文风,(72)故史称“自唐大中后,词气衰滥,国朝稍革其浮,至亿乃振起风采,与古之作者方驾矣”(73);另一方面,对当时最高统治者和以北人为主体的赵宋政权来说,也需要士人予以赞美与歌颂,杨亿正以南人特有的敏捷文思与华丽辞彩,适应了这个时代需求,即吕中所说,“国家创造之初,则其大体必本于忠风俗;涵养之久,则其大势必趋于文”,而杨亿“文章格力,足以润色王猷,黼黻云汉”(74)。西崑酬唱以及由此形成的崑体,就是其中的具体表现。刘克庄说:“崑体若少理致,然东封西祀,粉饰太平之典,恐非穆修、柳开所长”(75),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评价崑体的价值与意义的。以上两点,当为北士认同并参与杨亿主持的酬唱活动的主要原因。
不过,就具体的文学主张而言,杨亿与张咏等北人并非完全相同。张咏曾期待杨亿能臻“长世之期”(文章永恒),为“瑞时之表”(文坛盟主);但前提是在运用智慧以避祸的基础上,补察时政,揭露时弊,做到“超然独到,邈与道俱”(76)。这与杨亿以“雅颂”实现教化的创作主张适成对比;而补察时政,揭露时弊,也体现在张咏、王禹偁等北人的创作中。如王禹偁“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羣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77)。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审美趋向,但任何一个作家的个性与审美趋向的形成,与他的生活境遇密不可分。在宋初,北士以文章、言论至台辅者不乏其人,其中李沆、寇准等人,在历史上又评价甚高。常遭猜忌的南士,或像张洎那样与寇准“同秉大事,奉事准愈谨,政事一决于准,洎无所参预,专修《时政记》,甘言谀词以媚上”(78);或如前文所述,陈恕知贡举时,为了避嫌,不惜牺牲南士的利益;或如徐铉、杨亿那样,安于文臣地位,以博学广闻与文学才藻立于朝。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南士,都很难像王禹偁、张咏那样臧否人物,揭露时弊,因为他们在仕途上的待遇远不如北士来得优越,心中的顾忌也要比北士多得多。尽管如此,杨亿“以斯文为己任,由是东封西祀之仪,修史修书之局,皆归大手,为皇家之盛典。当时台阁英游,盖多出于师门矣”(79),终成文坛盟主,以他为主导的崑体也成了官方的主流话语体系。因此,宋人往往将杨亿与王禹偁相提并论。周必大说:“一代文章必有宗。……若稽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业,文治兴斯文。一传为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焉;再传为真宗,杨文公大年出焉。”(80)胡卫还认为:“朝廷之上号大手笔如杨亿、王元之,虽尚拘崑体,而场屋间王曾试《有物混成赋》,识者即以公辅期之。”(81)其依据固然在于王禹偁、杨亿具有共同摆脱五代文风的理想与实绩,但将王禹偁归入崑体的行列,属于误判抑或另有所指?
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与南人王世则、姚铉、罗处约、曾致尧同中进士第,所交也多江南文士,其中在23岁时结交的柳宜,尝携文“叫阍上书,且请以文笔自试”(82),王禹偁自称在这位江南闻人那里,常得到“厚于我”、“善于我”的关怀(83);王禹偁提携的文学后进,同样多江南文士,其中孙何、丁谓就是他在“天下举人”中奖拨出来的“杰出群萃”的“韩柳之徒”(84)。王禹偁也十分赏识杨亿,赞誉杨亿“才名官职过欧阳”,“笔削留惇史,囊装贮赐金”(85)。王、杨均以修史名世,而古人所谓文学卓异者,往往包括了史笔。当然,王禹偁的主要成就在于“笔下追还三代风,祛尽浇漓成古道”(86)的诗文革新上,但他不以“古道”的继往开来者自居,而是在“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中,“以文章负天下之望”(87)。他倡导古文,却厌弃“其句昧然,难见其义”的“好大而不同俗”之作;并认为“诗三百篇,皆俪其句,谐其音”(88),创作了一些平易的偶俪之文。他主张“风骚”诗道(89),讽刺现实,补察时政,但不反对“雅颂”,以为“形容于盛德”的“虞歌鲁颂”,可“见王化之兴隆”,也是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90)。凡此种种,表明了王禹偁的诗文革新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昭示了在宋初南文北移的过程中,王禹偁是北士认同南文,熔铸南北的杰出代表。因此将他与杨亿相提并论,甚至将其诗文归诸崑体,就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了。
与王禹偁一样,张咏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也是相当开放的。他要求杨亿补察时政,揭露时弊,却也作有《甘露贺表》之类的颂体文;同时指出:“君臣父子,非文言无以定其分;朝会揖让,非文言无以格其体;政以正之,非文言无以导其化;乐以和之,非文言无以节其变;咸迹于行事,播为文章。……纷纶众制,六籍悉备焉。周汉已降,代不乏贤。视文之否臧,见德之高下。若以偶语之作,参古正之辞,辞得异而道不可异也。故谓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荡,非文也”(91)。在主张远师六经中,既强调文章在载负道德经术上的多重性功能,又倡导文章在表现功能时的多样性形式。在他看来,以声律偶语为形式的今文能表达这些功能,未尝不是好文;若“好古以戾”即王禹偁所说的那种“好大而不同俗”之文,即便是古文,也属“非文”,因为“其句昧然,难见其义”,损害了文章应有的功能。可见张咏与王禹偁一样注重文学的自身特性,同样强调各种文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仅此而言,他加盟文学后进杨亿发起的西崑酬唱活动,也在情理之中。
三 南北文坛的冲突与整合
杨亿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去世,崑体的主要作手钱惟演、刘筠却仍然活跃在文坛;与此同时,杨亿的众多门人在仁宗初期也相继走上文坛,其中晏殊“以文章为天下所宗”(92),且“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93),人们熟知的就有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王琪、张先、宋庠、宋祁、石介等。晏殊成了杨亿与欧阳修之间的又一文坛盟主;在晏殊时代,崑体依然作为官方的主流话语体系而畅行其道。不过,从晏殊到欧阳修,既是宋初南文北移在民间继续进行,又是引发南北文坛冲突与整合的一个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的南文北移,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仁宗天圣末年以文学为纽带的洛阳文人集团的形成。该集团的主人是留守钱惟演,主盟者为通判谢绛,骨干有推官欧阳修、掌书记尹洙、主簿梅尧臣等,又有大批国子学秀才为羽翼。关于这一集团的形成及其创作活动,王水照先生有详尽的论述(94)。需要补充的是,其主要成员除尹洙外,钱惟演、谢绛,梅尧臣、欧阳修均为南人,因而不妨说,他们在洛阳的创作是南人在北方民间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学传播活动,众所周知,作为唐代的东都,洛阳具有深厚的文学与文化积淀,但在五代近一个世纪的文坛上,却患了严重的“失语症”;再如前文所述,以张齐贤这样的家族为文化支架下的洛阳,也只能培育出官僚而不会是文学家,宋太祖以来,洛阳在文学史上毫无地位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以南人为主体的文人集团的到来,洛阳才开启异代接武,旧事重演的历程,重现了原有的文学光芒,成了宋初民间南文北移的一次成功的运作,在北宋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嘉祐三年,梅尧臣在回忆洛阳时期的创作时说:“谢公(绛)主盟文变古”(95)。欧阳修也自称:“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96)。洛阳文人集团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正是他们在洛阳吹响了仁宗时期古文运动的号角。然而,钱惟演为崑体作手,谢绛被杨亿誉为“文中虎”(97),也以偶俪之文称著于世,欧阳修在官洛阳前一直创作时文,梅尧臣则同样“是在西崑诗人培养之下进行创作的”(98),他们在洛阳为何弃时文而作古文?
天圣七年,朝廷颁布《庚申诏书》,首次以政令的形式对杨亿以来的时文发起了攻击:“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荟萃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礼部其申饬学者,务明先圣之道,以称朕意焉”(99)。以杨亿为首的崑体作家以“雅颂”实现教化的主张,固然出诸国家统一、皇权重建后政治文化的诉求,但真宗去世以后,各种社会弊端日益显露,有识之士也开始从原来的盛世光晕中走了出来,审视危机四伏的现实,在士林逐渐形成了革新政治的思潮。天圣三年,范仲淹上万言书,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仁宗借科举之机,抨击“浮夸靡蔓”的时文,倡导“先圣之道”,正是这一思潮的具体产物,并在取士行为及士人的观念中得到了迅速的反映。次年,欧阳修应举,被晏殊列为第一,但在殿试时,北人王拱辰却为状元,这显然是《庚申诏书》作用的结果;石介则即时盛赞王文“渊深粹纯,雄壮高拔,格如唐柳宗元、刘禹锡,意若到韩退之吏部、柳仲涂崇仪”;又说,“状元力排贬斥淫辞哇声,独以正音鼓唱乎群盲众迷,将廓然开明乎天下耳目,而早以文章得状元于天子”,将来“主盟斯文,非状元而谁”(100)。其中虽不乏追捧之嫌,但《庚申诏书》的确冲击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也对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欧阳修在洛阳改习古文或“谢公主盟文变古”的一个直接的动因,便在于此;同时为主张恢复“古道”的北士掌握文坛的话语权,首次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在太宗与真宗两朝,北方柳开、种放等倡导“古道”的群体,一直活动于民间,他们用于明道垂教的古文也不合皇权运作的时宜,始终未能介入官方的主流话语体系,古文与时文虽处于对峙状态,却很少有正面冲突。随着天圣年间政治文化的变化,古文逐渐从民间转向了官方,从非主流转向了主流,时文与古文之间的冲突也就无可避免地摆在了士人的面前。
在冲突中,“东学”之士扮演了急先锋,尤其是石介,他在《怪说》三篇中,将杨亿等人的崑体与佛道两家相提并论,认为造成“文之本日坏”,“轻薄之流,得斯自骋,故雕巧纂组之辞遍满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诡诞之说肆行天地间而人不御也”的根源(101),在于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目的就是“使天下人目盲,不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102);这是因为杨亿“性识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争胜,独驱海内,谓古文之雄有仲涂、黄州、汉公、谓之辈,度己终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为,远袭唐李义山之体,作为新制”(103)。毋庸赘言,石介的这种批判,未免太过偏激,甚至在无中生有中,夹杂着对杨亿的无端攻击,难怪田况有“岂至是耶”之叹(104);石介同调孙复却相与唱和,认为“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只有石介知晓“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105)。所谓“揭而行之者”,便包括了对杨亿与时文的抨击。为了对抗杨亿以来的偶俪时文,石介、孙复等人又创立了怪癖生涩的“太学体”,即苏辙所谓“文律颓毁,奇邪谲怪”,“剽剥珠贝,缀饰耳鼻。调和椒姜,毒病唇齿。咀嚼荆棘,斥弃羹胾。号兹古文”(106)。就是这种“古文”,曾在太学与科场尘嚣一时,从中不难看出孙、石等专经之士反击时文的影响力。
孙复、石介等专经之士以偏激的舆论与怪癖的实践形态反击时文,虽不能引起所有北方士人的首肯,却在文坛导致了不小的震荡,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北士的观念。如穆修斥责“浮轨滥辙”的声律偶丽之文为浅浮糜靡(107)。尹洙则唯“简而有法”的《春秋》文法是瞻,不仅全盘否定杨亿以来的偶俪时文,而且对于韩柳只肯定其恢复“古文”的功绩,于放笔挥洒、极尽情态、文采斐然的作品,也是排斥不容的,所以他加盟洛阳文人集团,从事古文创作,与文道并重的欧阳修等南士难免有不协调的音符,在他去世后,其家人便将这种不协调演变为与欧阳修的正面冲突,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108)。对于北人的这种观念与言行,南士作了公开的应对。梅尧臣甚至以“山东腐儒漫侧目,洛阳才子争归趋”(109)之语相轻诋。欧阳修读了《怪说》后,则严肃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110);又竭力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的盲目崇古,对“太学体”的文化与文学取向“痛排抑之”(111)。不过,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并没有停留于此,面对冲突,如何整合南北、融合文道,重构文坛,则是他所要完成的任务。
在北宋,造成南北冲突的原因,既有士人政治利益的驱使,又有尚文重艺与尚质重道的不同人文性格。但这种冲突并不总是公开的、简单化的,而往往是隐蔽的,复杂的,属于隐性文化链上的行为,当涉及南北士人的利益时,矛盾便会激化,尤其是北士,有时还以“南方下国”、“南人误国”之语相攻击;或受到某种因素的激发,冲突就会趋向公开化,上述因天圣以后政治变革引发的南北文坛的冲突,即为显例。但随着大一统政权的不断巩固与深入,地域政治的色彩不断淡化,至天圣年间,南士纷纷进入了权力中心(112),欧阳修自言“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113),又昭示了天圣以后南方文士议论时事、揭露时弊的主体精神已全面形成,南北士人在参政主体上呈现出平等的局面,意识形态中的文与道势必随之趋向融合,南人在尚文的同时也像北士一样注重“先圣之道”。这为欧阳修整合南北,化合文道,重构文坛创造了条件。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欧阳修继承了王禹偁、张咏等人熔铸南北的文学主张与精神,体现了兼容并蓄南北名家优秀成果的开阔胸怀与思想境界。
首先,继承了杨亿以来南方作家文学创作的成果及其审美理想,明确提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114)。所以宋人有欧阳修与尹洙“始倡为古文,以变西崑体”,后又与苏轼“复主杨大年”之说(115)。需要说明的是,欧阳修在倡导古文的过程中,并未否定偶俪文体及其辞采。事实上,对于杨亿、刘筠的诗文,欧阳修始终怀有敬慕之情,他在给蔡襄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表示了对杨、刘文采的“倾想”(116);并充分肯定杨亿、钱惟演、刘筠“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无施而不可”(117)的学力与艺术素养。这出于欧阳修自身的体验,也合乎宋代文学以学力见长的主体特征与审美趣向,为后来的文士在创作主体上树立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标杆。有基于此,欧阳修对“后崐体”作家晏殊的诗文作了高度的评价,(118)对被视为“小人”的曾致尧、梅询等南方文士的偶俪之文与诗歌成就也予以充分肯定(119)。在创作上,欧阳修虽自言进士及第后不复作骈俪之文(120),当代学界也往往认为“欧阳修是以韩文作为学习的楷模来扭转崑体的骈俪之习的代表人物”(121),但欧阳修在应举前深染骈俪之习,进士及第后也不乏偶丽之作,现存《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均作于入仕后,其中如《上随州钱相公书》、《谢校勘启》等不少作品,都是言情叙事俱佳的精品。这些作品正如清代骈文史家孙梅所说:“宋初诸公骈体,精致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122)。在继承杨、刘“精致工切”的文风基础上,融入古文的“古雅”格调,为骈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
其实,作为一种文体,骈文自有其功能与价值。对此,同样是张扬“古道”、创作古文的范仲淹也持有清醒的认识,并付诸自身的创作实践。其《岳阳楼记》就是一篇在结构形式与语体风格上源白杨亿《涵虚阁记》的骈俪之作,无论写景抑或抒情,都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为历代读者所称颂;尤其是对杨亿“独步当世”的“应用之才”,范仲淹更是敬重不已(123)。所谓“应用之才”,就是指杨亿骈文创作的才能与成就。宋祁将文章分为“论著、应用二体”,认为古文适用于论著体,骈文适合于应用体,各有所需,各行其道(124)。因此,欧阳修在以韩愈古文作为学习楷模的同时,对骈俪文体在理论上予以肯定,在自身的创作中,则以古文格调融入其中,发扬了杨亿以来骈文创作的成果,将宋代骈俪之文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谢伋说:欧阳修“制作浑成”的四六骈文问世后,“学之者益以众多。况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而知”(125)。便总结了欧阳修骈文创作的历史地位,也指出了骈文在两宋的盛况及其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继承了自柳开以来北士尊韩的传统、特别是石介倡导韩愈的思想成果,为古文创作注入了灵魂。石介早年就“有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126),是仁宗时期尊韩思潮中的急先锋式的人物。他将韩愈视为孔子、孟轲、扬雄以来一脉相传的道统正流,主要是因为韩愈的道统观和排佛思想。欧阳修在年轻时对韩愈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主要为韩愈浑浩流转的古文所吸引,对于韩愈所谈之道,并没有多少亲切的体会(127)。他在庆历初所作的《本论》中,推崇的是孟轲、董仲舒而不及韩愈。天圣至庆历初,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锐意改革的士人群体,石介与欧阳修均为中坚力量。为了给政治变革寻找理论基础,建立一种能为士林群体普遍接受的学术思想,欧阳修与石介携手共建,其中就包括了对石介辟佛兴儒思想的吸收,这从庆历三年所作《读张李二先生文赠石先生》(128)一诗中可见一斑。庆历六七年,欧阳修先后作《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对石介在这方面的业绩作了很高的评介:“宦学三十年,六经老研摩。问胡所专心,仁义丘与轲。扬雄韩愈氏,此外岂知他。尤勇攻佛老,奋笔如挥戈。不量敌众寡,胆大身幺么”(129)。并称石介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者,未尝一日不诵于口”(130)。在赞扬石介始终不渝的传道精神的同时,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欧阳修的认同。庆历八年,欧阳修乃充分肯定了韩愈在传道中的成就。(131)
苏轼指出:“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又说,“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132)。韩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唐宋新儒学的先驱。将欧阳修视为宋代的韩愈,也是就儒学与古文两个方面而言的。但欧阳修“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是与他吸收北方士人尊韩的思想成果是分不开的。只是柳开、种放、穆修、尹洙、孙复、石介等北士在因道及文中,注重的是韩愈所倡之道而忽视了韩文在文学上的自身特征。欧阳修在因文及道中,文道并重,既倡导了韩愈在新儒学上的“道术”,又发扬了韩愈在文学意义上的古文。陈善说:“韩文重于今世,盖自欧公始倡之。”(133)孙弈又具体分析了欧阳修倡导韩文的实绩:“以文章独步当世,而于昌黎不无所得。观其词语丰润,意绪婉曲,俯仰揖逊,步骤驰骋,皆得韩子之体。故《本论》似《原道》,《上范司谏》似《谏臣论》,《书梅尧臣诗稿》似《送孟东野序》,《纵囚论》、《怪竹辩》断句皆如《原人》。盖其横翔捷出,不减韩作,而平淡详赡过之。”(134)通过具体篇目的比照,指出了欧阳修在文意、文势、构思乃至句法上学韩的表现,以及学中思变,自成格调的风范与成就。又刘敞“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135)在“公取者粗可数”以下,刘敞所举的论证均为诗歌。韩愈诗歌为宋诗风格、尤其是在“以文为诗”上导夫先路,是学界的共识,欧阳修是宋代倡导韩诗的先驱,也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
事实充分表明,欧阳修主持古文运动,进行诗文革新,光大了王禹偁、张咏等人熔铸南北的精神和多元化的文学主张,对杨亿以来的南方文学在改造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对柳开以来北士倡导韩愈古文的思想成果在修补中吸纳,在吸纳中发扬,于儒学与文学两个方面,完成了韩愈的未竟之业,从中整合了南北,化合了文道,“故天下翕然师尊之”,使文坛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为熙宁至元祐时期文学高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余论
史称“尹洙与修俱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才不逮,修文遂行于世,文体为之一变。庶几乎西汉之甚盛者,由修发之(136)”。将倡率古文的成功归诸欧阳修的才力,并停留在文体的新变之上;而当今学界又往往将古文与时文对立起来,认为欧阳修变革文体的主要对象是崑体作家的偶俪时文。诚然,经欧阳修的大力倡导,古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文坛为之一新,但欧阳修并没有停留在文体的新变上,在倡导古文的同时,又继承了杨、刘的创作成果,将偶俪之文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既然如此,如何看待这场古文运动?
欧阳修“以古文倡率学者”,是文学界的一场运动,更是士林阶层的一场思想运动,其最终目的在于重构适应新儒学运行的新的实践主体。欧阳修指出:“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137)视古道为价值的源泉,文章为升华那些价值的载体;其间的中介是“履之以身,施之于事”的实践主体。欧阳修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原因在于“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138);而道能否“无不之”,则取决于主体能否得道之意和得意以后的定心:“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毅”(139)。惟其如此,才能“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140)。这些表述很容易使人理解为以道制文,取消了文的独立价值。实际上,欧阳修所强调的是学道之人在道与文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精神境界,它基于实践主体屏除功利后的道德自律,以及在自律中形成的坚毅而鲜活的个性,在宋代文学史和思想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欧阳修将纯理性化的先王之道转向入世,转入“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毅”的具体活动中,重构适应新儒学运行的实践主体,成了范仲淹在政治变革中倡导“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新精神的重要内涵。庆历年间的政治变革虽然失败了,这一新精神却普遍被融注到了参政主体与文学创作主体之中。所以苏轼在总结欧阳的古文成就后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141)揭示了欧阳修倡导古文的最终目的及其所完成的最终任务。
注释:
①《能改斋漫录》卷八“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4页。
②(12)韩琦《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全宋文》,第4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第80页。
③《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同),第13003页。
④《全宋文》,第6册,第367页。
⑤《上王学士第三书》,《全宋文》,第6册,第284页。
⑥《昌黎集后序》,《全宋文》,第6册,第355页。
⑦《答梁拾遗改名书》,《全宋文》,第6册,第900页。
⑧《答臧丙第三书》,《全宋文》,第6册,第298页。
⑨《知邠州上陈情表》,《全宋文》,第6册,第267页。
⑩王称《东都事略》卷三八《柳开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下同),第382册,第251页上。
(11)《柳公行状》,《全宋文》,第13册,第359页。
(13)《尹师鲁〈河南集〉序》,《全宋文》,第18册,第392页。
(14)《全宋文》,13册,第354页。
(15)李邦直《韩太保惟忠墓表》,引自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61页。
(16)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17)《宋史》卷八五《地理志》,第2117页。
(18)《宋史》卷八五《地理志》,第2112页。
(19)《全宋文》,第130册,第263页。
(20)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四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4册,第370页上。
(21)《易学辨惑》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册,第404页下。
(22)《唐柳先生集后序》,《全宋文》,第16册,第31页。
(23)《尹师鲁墓志铭》,《全宋文》,第35册,第308页。
(24)邵博《邵博闻见后录》卷一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页。
(25)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9页。
(26)刘荀《明本释》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3册,第169下—170页上。
(27)《答张洞书》,《全宋文》,第19册,第293-294页。
(28)《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三《上蔡副枢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同),第143-144页。
(29)《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过魏东郊》,第20页。
(30)《徂徕集》卷十五《与君贶学士书》,第180页。
(31)《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上蔡副枢书》,第145页。
(32)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全宋文》,第33册,第57页。
(33)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六,中华书局1961年版(下同),第157页。
(34)欧阳修《泷冈阡表》,《全宋文》第35册,第273页。
(35)欧阳发《先公事迹》,《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五。中国书店1986年版(下同),第1370页。
(36)《避暑录话》卷上,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37)邱仰文《五代诗话·序》,《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8)旧题史虚白撰《钓矶立谈》,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856册,第15页。
(39)引自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7页。
(4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四引《谈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41)司马光《涑水记闻》附录二《温公日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8页。
(4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页。
(43)《全宋诗》,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以后陆续出版(下同),第1388页。
(44)《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全宋文》,第55册,第3-4页。
(45)《论逐路取人劄子》,《全宋文》32册,第292页。
(46)《五代诗话·例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47)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七《杨砺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8册,第245页上。
(48)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49)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第24页。
(50)欧阳修《徐铉双溪院记跋》,《全宋文》,第34册,第333页。
(51)《儒林公议》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93册,第35页。
(52)《故散骑常侍东海徐公集序》,《全宋文》,第9册,第227页。
(53)《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第13045页。
(54)《李公墓志铭》,《全宋文》,第15册,第64页。
(55)欧阳修《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下同),第13页。
(56)司马光《续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5页。
(57)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页。
(58)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第53页。
(59)详见《道山清话》(百川学海本)、《邵氏闻见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60)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载,雍熙年间,馆臣校勘木版九经,馆中藏有南朝宋、梁时期所校《左传》,雍丘孔维便上书指出南朝政权为非正统,南人所校《左传》“不可案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7册,第262页)。类似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北人中相当流行。尹洙《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又从史学的角度竭力宣扬北方才是唯一的正统(《全宋文》,第28册,第19-21页)。
(61)《江邻几杂志》(广陵书社《笔记小说大观》第七辑):“莱公(寇准)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当作状元,莱公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时为枢密使。”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有详细的记载(中华书局2004年版,下同,页1920)。又真宗赐晏殊同进士出身,北人寇准阻之,理由是“殊,江外人”(《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第10195页)。
(62)《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第9202页。
(63)《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二,中华书局影1997年影印本(下同),第3册,第2231页上。
(64)陈师道《后山丛谈》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54册,第32页。
(65)杨亿《杨文公谈苑》(宛委山堂本)称陈越为“雍熙以来文士诗”中的“后来之著声者”。
(66)王禹偁《送张咏序》,《全宋文》,第7册,第422页。
(67)晁迥《法藏碎金录》卷五:“予观白氏诗,凡有惬心之理者,每好依据而沿革之,往往得新意而自规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52册,第508页下)。按晁迥清丰(今属河南)人,后徙彭门(今属四川)。
(68)杨亿《送集贤李学士员外知歙州序》,《全宋文》,第14册,第370页。
(69)柳开《与李宗谔秀才书》,《全宋文》,第6册,第338页。
(70)《宋会要辑稿·选举》九之一,第5册,第4397页。
(71)《广平公唱和集序》,《全宋文》,第14册,第384页。
(72)苏颂《小畜外集序》,《全宋文》,第61册,第348页。
(7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第4册,第2227页。
(74)《宋大事记讲义》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6册,第248页下。
(75)《平湖集序》,《全宋文》,第329册,第163页。按粉饰太平是《西崑酬唱集》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杨亿、刘筠同题唱和的《受诏修书述怀三十韵》,即为一例。
(76)《儒林公议》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93册,第14页。
(77)《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第9799页。
(78)《太宗皇帝实录》卷八○,四部丛刊本。
(79)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全宋文》,第19册,第6页。
(80)《初寮先生前后集序》,《全宋文》,第230册,第105页。
(81)《宋会要辑稿·选举志》六之四○,第5册,第4349页下。
(82)王禹偁《送柳宜通判全州序》,《全宋文》,7册,第435页。
(83)王禹偁《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全宋文》,第8册,第186页。
(84)详王禹偁《答郑褒书》、《送孙何序》,《全宋文》7册,第393、424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孙何丁谓举进士第,未有名。翰林学士王禹偁见其文,大赏之,赠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二人由此名大振。”(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页。)
(85)《送史馆学士杨亿闽中迎侍》,《送正言杨学士亿之任缙云》,《全宋诗》,第2册,第745、775页。
(86)王禹偁《酬安秘丞见赠长歌》,《全宋诗》,2册,第785页。
(87)《答郑褒书》,《全宋文》,第7册,第393页。
(88)《答张扶书》,《全宋文》,第7册,第395页。
(89)《还扬州许书记家集》,“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全宋诗》,第2册,第781页)
(90)《中书试诏臣僚和御制雪诗序》,《全宋文》,8册,第15页。
(91)《答友生问文书》,《全宋文》,第6册,第120页。
(92)欧阳修《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全宋文》,35册,第245页。
(93)欧阳修《六一诗话》,第13页。
(94)详见《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73页。
(95)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八《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9页。
(96)《记旧本韩文后》,《全宋文》,第34册,第860页。
(97)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98)朱东润《梅尧臣作诗的主张》,《中国文学论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2页。
(9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天圣七年五月己未”条,第2512页。
(100)《徂徕石先生集》卷一五《与君贶学士书》,第180-81页。
(101)《徂徕石先生集》卷一六《与裴员外书》,第191页。
(102)《徂徕石先生集》卷五《怪说中》,第63页。
(103)《徂徕石先生集》卷一九《祥符诏书记》,第220页。
(104)《儒林公议》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93册,第2页。
(105)《寄范天章书一》,《全宋文》,第19册,第290页。
(106)《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六《祭欧阳少师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1页。
(107)详《答乔适书》,《全宋文》,第16册,第20页。
(108)详见王水照《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467页。
(109)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一《四月二十七日与王正仲饮》,第561页。
(110)《与石推官第一书》,《全宋文》,第33册,第72页。
(111)《欧阳修全集》附录《四朝国史本传》,第13672页。
(112)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劄子》:“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全宋文》,第222册,第198页。
(113)《镇阳读书》,《全宋诗》第6册,第3600页。
(114)《书尹师鲁墓志》,《全宋文》,第34册,第82页。
(115)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十《吕氏家塾记》,四部丛刊本。
(116)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117)《六一诗话》,第13页。
(118)详《晏公神道碑铭》,《全宋文》第35册,第244-248页。
(119)详《曾公神道碑铭》,《梅公墓誌铭》,《全宋文》,第35册,第226-228、289-291页。
(120)《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全宋文》第35册,第52-53页。
(121)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页。
(122)《四六丛话》卷三三,《续四库全书》,第1715册,第602页上。
(123)《尹师鲁河南集序》,《全宋文》,第18册,第392页。
(124)王正德《余师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616册,第8页。
(125)谢伋《〈四六谈尘〉自序》,《全宋文》,第190册,第335页。
(126)《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赠张绩禹功》,第17页。
(127)详《记旧本韩文后》,《全宋文》第34册,第860页。
(128)详《全宋诗》第6册,第3594-3595页。
(129)《读徂徕集》,《全宋诗》,第6册,第3604页。
(130)《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全宋文》,第35册,第368页。
(131)见《青松赠林子国华》,《全宋诗》,第6册,第3619页。
(132)《苏轼文集》卷一○《六一居士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第316页。
(133)《扪虱新话》上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0册,第6页。
(134)《履斋示儿编》卷七“祖述文意”条,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5册,第62页。
(135)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八,第140页。
(136)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28册,第490页上。
(137)《与张秀才第二书》,《全宋文》,第33册,第69页。
(138)《答吴充秀才书》,《全宋文》,第33册,第58页。
(139)《答祖择之书》,《全宋文》,第33册,第99页。
(140)《与乐秀才第一书》,《全宋文》,第33册,第112页。
(141)《苏轼文集》卷一○《六一居士集叙》,第316页。
标签:欧阳修论文; 王禹偁论文; 晏殊论文; 古文论文; 南方与北方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宋朝论文; 韩愈论文; 徐铉论文; 杨亿论文; 柳开论文; 刘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