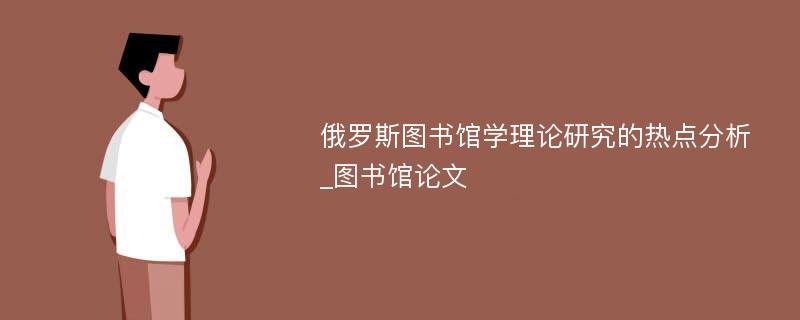
俄罗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热点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热点论文,俄罗斯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CLASS NUMBER G250
鼎盛时期的苏联图书馆学在世界图书馆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理论思维与思想曾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家。但自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各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以俄罗斯图书馆学为例,它与前苏联图书馆学有何异同?其研究热点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和图书馆工作者感兴趣的问题。本文正是从分析近年来俄罗斯图书馆学期刊所刊载的论文入手来解答这些问题的。
1 概述
俄罗斯公开出版的图书馆学期刊远没有中国这一领域的期刊多,在为数不多的专业期刊中,《图书馆学》是最具权威性的一种。1992年之前,《图书馆学》名为《苏联图书馆学》,1993年正式改为现名并专门刊登了启事,声明期刊的性质由原来注重纯研究转变为理论与实践并重。该期刊改名时曾有多篇论文回顾和评价了苏联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观点,并将一些观点与当时图书馆学面临的形势做了比较。这些论文指出,苏联时期各级苏维埃政权创建了36万个图书馆和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系统。它们在苏联文化、科学和教育发展中起到了卓著的作用,其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但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原先的许多理论观点已无法简单地套用。随着《苏联图书馆学》改名为《图书馆学》,《苏联图书馆员》和《苏联科技图书馆》也分别改名为《图书馆》和《科技图书馆》,这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时期图书馆学的外在变化[1]。
进一步分析俄罗斯图书馆学期刊论文的内容,可以发现,近年来每期甚至每页都会有新的名词、术语或概念,而这些名词、术语或概念在原先的图书馆学教科书和图书情报学词典中都从未出现过。常见的术语如“图书馆记忆功能”、“图书馆营销”等。在俄罗斯图书馆学现行刊物上,目前对这些名词、术语或概念也大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有些解释还不尽完善和准确,或正在争议之中。这些新的术语和概念的出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俄罗斯图书馆学学科的发展需求,反映了俄罗斯图书馆学的内在变化,同时也代表着当今俄罗斯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潮流。
2 图书馆事业哲学
图书馆事业哲学实际指的是图书馆学学科或图书馆知识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这是多数人的认识。除此之外,波罗申认为,图书馆事业哲学是“关于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和世界观的科学[2], 但他没有展开自己的观点。其他一些图书馆学家则认为,图书馆事业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是揭示图书馆的社会任务(社会使命),即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设置对社会所应发挥的作用。譬如,道夫金娜就认为,十月革命前的图书馆事业哲学是启蒙哲学,当时俄罗斯国民教育的先驱人物(如鲁巴金等)的著作中已包涵了图书馆启蒙哲学的原则和价值体系,正是凭借着这种哲学和价值体系,才形成了当时图书馆员的理想境界,而这种启蒙思想在新的图书馆观念体系中理应得到重新确认[3]。 卡拍捷列娃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她认为,俄罗斯图书馆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从(藏书的)殿堂到启迪民众进而促进居民普遍教育的机构的转变;第二次是从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到传播意识形态的社会设置的转变。目前,俄罗斯图书馆的信息、文化、休闲、消遣等功能成份都明显地增强了[4]。
图书馆事业哲学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其主要问题是什么?其实质和社会意义何在?俄罗斯图书馆学者对此尚未取得共识。由于研究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同,学者们对图书馆事业哲学的认识也各有特色,这些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归纳为3个大的流派,即文化学派、 营销学派和情报学派。
文化学派从维护人文主义理想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出发,认为图书馆学应从文化角度考察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图书馆应建设成为人类知识和文化的神圣而宏伟的殿堂,而不应将其变为集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十月革命前俄国图书馆的人文主义思想实质及其对当今图书馆事业的通用性,提出要重新弘扬这种思想精神。譬如,克里马科夫认为,从彼得大帝时起一直到十月革命前乃至现在,图书馆都有着类似的目的,即“收集和保存人类文明和精神成就,促进人类对世界历史文化和世界当代文明的互相利用”[5]; 波罗申则高度评价了革命前俄国图书馆作为人民大众精神和文化源泉对整个民族精神和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在俄国,有两个殿堂,一个是教堂,另一个就是图书馆”。沙保斯尼科夫也是文化学派的成员,他将图书馆主要社会使命归结为实现“社会教育”功能,而俄罗斯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的实现经历了宗教精神阶段(11~18世纪)、启蒙教育阶段(18世纪~1918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阶段(苏联时期)和文化复兴阶段(20世纪90年代),等[6]。文化学派还从理论上重新论证了图书馆的“记忆功能”。
营销学派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产物,其代表人物有秋琳娜、奥西波娃、宾捷尔斯基等。秋琳娜认为,只有运用营销学方法,尤其是在用户服务和图书馆管理领域中运用营销方法,图书馆才有能力巩固和确立自己作为一种社会设置的地位。奥西波娃认为,营销方法能够使图书馆以现代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种社会设置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并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7]。 宾捷尔斯基则把营销学作为图书馆学的“新思维”加以论证[8]。但是, 营销学派的观点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马林诺娃就曾提醒人们警惕将营销学这一“手段”变为“目的”。她指出,这样做将动摇图书馆学赖以存在的信念并将抽掉其精髓,因为图书馆的目的是保存人类的知识记忆并促进其社会利用,而营销学不过是一种商业手段,对其过分热衷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9]。
情报学派则运用情报学观点解释图书馆的社会使命。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向每一位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提供情报保障。譬如,德奥尔金娜认为,追求情报的通畅性是图书馆工作的基础,为此,图书馆事业新的哲学应该是“研究情报提供的有序性、通畅性的哲学”[10]。
除上述三大流派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如波贝列娃认为,确定图书馆学哲学概念的意义在于确定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体系,而不是图书馆学实质和图书馆目的,她主张通过历史的、哲学的、技术的、组织原理的等几种概念的互相过渡、转化与补充,形成统一的图书馆学的具体概念[11]。总之,俄罗斯学者对图书馆事业哲学的探讨还远不成熟,图书馆事业哲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它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还是模糊的,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3 图书馆事业与意识形态
“图书馆事业与意识形态”是当前俄罗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又一热点,对此学者们也尚未形成共识。如德沃金娜在《从意识形态到图书馆事业哲学》一文中将意识形态和图书馆事业哲学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意识形态是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图书馆事业哲学的任务正在于促进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确立[12]。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想或观念体系,那么意识形态必然有其特定的哲学基础;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图书馆事业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必然要与意识形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图书馆事业是否应从属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俄罗斯学者们倾向于图书馆事业不应从属于某一政党、某种政治、某种意识形态。1994 年12 月颁行的《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第12条第2款即指出, 全部或部分由联邦预算拨款提供资金保障的图书馆,应该在图书馆活动中反映社会多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13]。俄罗斯图书馆法所反映的观点实质上淡化了图书馆与执政党及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关联。
然而,淡化意识形态的观点也遭到了部分图书馆学家的质疑。伏诺托夫认为,图书馆提出非意识形态的命题只是原则上的正确,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命题所涉及和面对的是某些政党的政治主张时才是正确的,假若它涉及和面对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则可能会变为经不起推敲的理论,因为“任何国家的图书馆都是依照相应国家特定的意识形态并以相应的形式来保存、开发全人类的文化财富的”。以美国为例,其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思想也对应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为了美国的民主理想、美国的生活方式理想和发挥美国在全世界的主导作用,使图书馆要更加接近于人民,接近于世界”[14]。梅瑞斯也认为图书馆事业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他在《图书馆意识形态发展前景》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将自己的目的确定为积极宣传民主思想、民主价值和自由,并以此为基础帮助读者明晰自己的思维和世界观,这就是图书馆事业的意识形态倾向[15]。
“图书馆事业与意识形态”的争论反映了俄罗斯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之后图书馆学界的混乱情形,在此,历史出现了中断,一些图书馆学家不得不回到十月革命前鲁巴金等人的著作中寻找论据,而更多的学者是无所适从。缺乏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支持正是俄罗斯图书馆学区别于前苏联图书馆学的最大特点。深入地分析,伏诺托夫等人虽指出了美国图书馆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及其图书馆事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倾向,但他们却看不到俄罗斯图书馆究竟按照何种意识形态发展,用什么作为理想的努力方向。瓦涅耶夫指出,如果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体系,那么图书馆还是应该选择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建立应以图书馆事业新的哲学为支撑点,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前提[16]。这或许才是更为合理的观点。
4 图书馆学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研究是苏联图书馆学的优势,俄罗斯图书馆学继承了这个传统。德奥尔金娜等人试图将哲学方法与方法论结合起来,以探讨意识形态与图书馆哲学的同一性。她们认为,虽然方法论概念在哲学和科学中已经具备,但在俄罗斯图书馆学中至今尚无明确的图书馆学方法论概念。方法论是图书馆学以及其它任何学科所固有的三位一体结构的组成环节:理论—历史—方法论[17]。对图书馆科学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重新认识,势必将俄罗斯图书馆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方法论问题。譬如,鲁卡绍夫就重新分析了“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方法论是关于结构、逻辑组织、活动方法和手段的系统学问,是科学原理、科学认识形态和方法的复杂学说,它实际上包容了图书馆事业的所有问题[18]。
在苏联时期,党性原则是最主要的方法论原则,但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图书馆学刊物上,这些原则不断遭到猛烈的批评。起初的表象似乎表明了俄罗斯图书馆学由意识形态化向非意识形态化的转变[19]。但是随着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现象更多的显露出俄罗斯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化倾向。因为俄罗斯图书馆学家在批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在企图找到一种论据充分的等价物来代替原有的意识形态理论,以避免形成图书馆学方法论上的真空。瓦涅耶夫就明确表示,图书馆学应该建立自己可依靠的方法论原则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事实进行选择和评价的历史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瓦涅耶夫还指出,图书馆学家们以往在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时就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是以共产主义党性原则为基础的。在此,瓦涅耶夫又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困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也许只有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条件下才能实现[20]。
在讨论如何构建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问题时,俄罗斯图书馆学家还在寻求一种主导的方法,他们认为学科的独立性是以其科学方法的独立性为基础的。持各种观点的学者们曾各自将图书馆学的主导方法分别归结为藏书研究的计量方法、书目方法和社会学方法,以及书目引证的统计学方法等。克雷坚科则声称,夸大某种一般科学方法或专用方法的认识作用,把它作为唯一的和“全能的”方法而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这是一种错误[21]。然而在具体研究中却可以选出某种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与图书馆学某种专用方法的应用不是相互隔离或平行的,而是处于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的统一之中,它们在相互作用与相互补充的同时加强了各自的长处,并抵消了各自的某种局限性,从而有助于推进多方面的研究。
结合图书馆事业哲学范畴的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不仅要兼顾一般与个别、部分与整体、简单与复杂、原因与结果等传统的哲学范畴,而且要运用专门的科学方法,提出像要素、层次、结构、功能等具有哲学意义的新范畴[22]。
苏联图书馆学曾经在方法论研究方面为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俄罗斯图书馆学虽然继承了方法论研究的传统,但由于社会体制转换之际出现的意识形态的“真空”现象,其方法论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无序状态。可见,无论是图书馆哲学还是图书馆学方法论,都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约束。苏联时期过分强调党性原则固然不尽合理,可能给图书馆学研究造成了某些限制。但苏联解体后对党性原则的全盘否定则有可能使图书馆学的发展无所适从。
5 图书馆学的范式
在俄罗斯,关于图书馆学范式的讨论起因于对图书馆转型的思考。列昂诺夫在《关于图书馆学新范式》一文中提出了图书馆学的两种范式:一种是“现存的范式”,一种称之为“新的或正在形成中的范式”。他认为,图书馆学理论观点的转变,最终可归结为范式的更替,即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以突变的形式完成的,它是随着理论的发展,从旧的范式中逐渐产生新范式的萌芽,最后形成新的范式。需要指出,图书馆学新范式并不是为了否定和抛弃过去,而是为了论证和勾画出一种新的研究观点和理论框架。列昂诺夫认为,俄罗斯现存的范式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理论上则形成于丘巴梁60年代的教科书《普通图书馆学》,其后又集中体现在1988年集体编撰的《图书馆学普通教程》中。就现存的图书馆学范式而言,其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明显,理论研究对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诸问题的预测长期存在着软弱性和片片性等特点,大部分研究方法具有经验主义成份,研究资料和选题的重复性及研究结果的雷同性也不容忽视,所以,在现存范式的框架原则范围内不可能产生出克服图书馆学危机的新观点。有鉴于此,列昂诺夫提出了称之为“过程范式”的图书馆学新范式,它以解释图书馆现象发生过程为基础,研究形成这一过程的内部机制、结构、实质和特性;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图书馆学,而且包括了目录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图书出版事业和图书贸易等同一过程;换言之,图书馆学属于社会交流科学[23]。
列昂诺夫的“过程范式”已超越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以至于当其它图书馆学家循着他的思路做进一步考察时,发现除了图书馆与其它邻近学科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的共性之外,几乎看不到图书馆活动的独特性,这也就意味着图书馆学丧失了作为一门学科应具有的学科独立性。其实,列昂诺夫的努力颇似我国文献信息学的产生过程,当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出版发行学等相互独立之时,它们似乎具备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独立性,但当它们整合之后形成新的学科或范式时,似乎它们各自又无本质的不同。
俄罗斯图书馆学家也从图书馆功能的角度论及图书馆学的范式。他们认为,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图书馆学传统中,图书馆最重要的功能是意识形态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和情报功能[24]。在新形势下,有必要重新认识图书馆的功能,于是,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记忆功能、休闲功能、社会系统功能、信息功能等新的认识[25]。应该说,这些讨论只是有限地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就主流而言,关于功能的讨论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图书馆学的无所适从——图书馆的功能早在70 年代IFLA大会上已有定论,上述所谓的“新功能”都未能超出IFLA讨论的范围。
6 简评
综观俄罗斯图书馆学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和理论热点,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其理论研究的无序性。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摒弃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就形成了“历史的中断”现象,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引发图书馆学乃至其它社会科学研究的混乱无序。图书馆学归根结底还主要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可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而失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支撑的俄罗斯图书馆学力图论证“图书馆事业哲学”、“图书馆事业与意识形态”、“图书馆学新范式”等等,其目的正是为了寻找理论归宿和理论依据,但由于俄罗斯一时之间还难以建立足以取代苏联时期共产主义那样的意识形态,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真空”或“多文化”现象,所以,俄罗斯图书馆学研究的无序是必然的,上述问题的探讨就是俄罗斯图书馆学为其力图摆脱无序状态而做出的努力。
比较俄罗斯与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双方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又有质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面临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新问题,俄罗斯“图书馆营销学派”的出现与我国关于“有偿服务”、“信息产业”、“信息市场”等问题的讨论在起因和结论方面都有诸多一致之处。质的区别在于俄罗斯是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其“休克式疗法”破坏了历史的连续性,造成了图书馆学研究无所适从、低水平重复乃至倒退的后果,而我国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这种建设性的改革进程保证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连续性,同时又刺激了其创新性。
俄罗斯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目前在我国也有趋热的倾向。近年来,北京大学周文骏先生一直在思索图书馆学的哲学问题,周先生的高足周庆山博士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吕斌副教授等后起之秀则发表过有关“图书馆学哲学”的论文。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宝岛,赖鼎铭先生出版了“图书馆哲学”方面的专著,其新作《论图书馆学的十大范式》将在近期的《图书情报工作》上发表。可见,图书馆学研究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需要通过图书馆哲学的突破来带动其全面发展。
无庸讳言,俄罗斯图书馆学仍然是世界图书馆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整序与发展必将能够给世界图书馆学增添新的活力,同时也能够给我国图书馆学发展以启迪和借鉴。为此,我们将随时关注俄罗斯图书馆学的发展,并将尽可能全面而及时地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每一个感兴趣的图书馆界同仁。
(来稿时间:1997.5.20。编发者:赵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