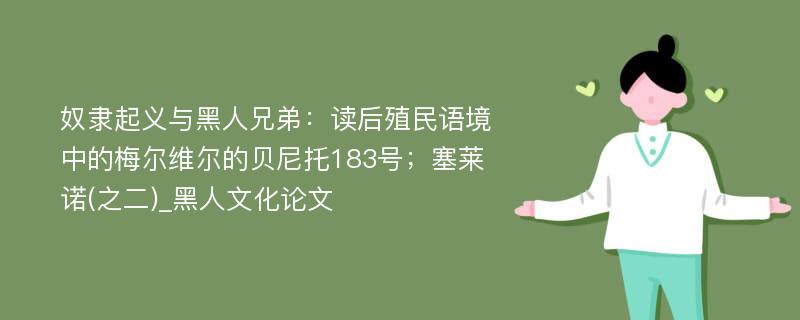
黑奴暴动和“黑修士——在后殖民语境中读麦尔维尔的《贝尼托#183;塞莱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奴论文,修士论文,暴动论文,语境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麦尔维尔的研究者都知道,《贝》的故事有个相当完整的原型。不但贩奴船起义事件的基本事实(包括地名、人名、塞莱诺的跳船),就连使用不知情的美国船长的视角、加上利马法庭调查的结构线,都不能算是麦尔维尔的创造,而是全盘取自历史上真实的德拉诺船长所著《航海记》的第18章。(注:Amasa Delano, A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Northern and Sonthern Hemispheres: Comprising Three Voyages 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a Voyage of Survey and Discovery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Oriental Islands (Boston, 1817) 318-353.该书第18章收入Runden, 76-104;以下引文均出自该版,只随文注明“原型”和页码。这是斯克德(Harold H. Scudder)在1928年发现的(Runden, v-vi; 125, n9)。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便是德拉诺船长的后人(《诺顿美国文学》Ⅰ,2148页,注1)。此外,第18章严格说分为三部分,头两页引用美国船的航海日志,写从美国大船上的观察和参与缉捕的情况,三言两语交代了全部事件,接着才是德本人叙述和法庭审理。)这么一个真实的黑奴起义事件,已经写进1817年就公开发表的书中,可是不但麦尔维尔对真实的原型秘而不宣,就连19世纪50年代主张用暴力袭击奴隶主的激烈方式推翻蓄奴制度的人士也毫无觉察,直到70年后才被发掘出来,又过70年麦尔维尔在150年前就用隐晦的方式坚持了今天看来是正确的立场才被“普遍”认识——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对当下热衷的批评意见做了微妙的注释。
麦尔维尔的创作习惯是使用“一个现成事实的骨架进行构建,使之丰满起来,脉络充盈,富有美感”,(注:转引自Feltenstein, in Runden, 126.)包括《白鲸》在内的故事都有原型;可哪个原型都无法和德拉诺的《航海记》18章相比,以今天的眼光看,《贝》简直就是大规模直接抄袭了德的第18章。尽管如此,两者的区别还是巨大的。原型中,航海日志和德的叙述至塞莱诺跳船的发生,总共才6页,也就是说,麦尔维尔将原材料拉长了至少8至9倍,(注:七十多年来,对《贝》的评论几乎都会对小说与原型进行比较。本文所作比较主要基于我本人的细读和整理,其中一部分参考了本文已经提到的诸多文章,除需特别说明的,一般不再一一列出参考资料。)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他的原创。特别是历史上的德拉诺并没有使用比喻的习惯,所以小说中的喻象结构应属于麦尔维尔。那么,麦尔维尔对原型,尤其在黑人形象和起义行为方面,做了什么样的改造呢?
从技术细节上说,《贝》将起义的时间提前了四年半,从而有效地避开了1804年海地宣布独立,成立黑人国家的历史事实,增加了德拉诺之麻木不仁的可信度;但原型中1804年起义的黑人询问附近有没有黑人国家是事出有因,而小说中的黑人问这个问题就缺乏根据了。起义的具体时间从南半球的夏季换到冬季,将实际航程拉长了一个月,(注:原型中西班牙船于1804年12月20日出发,1805年2月20日清晨在圣马利亚岛遇美国船,塞莱诺谎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漂泊4个月26天;《贝》将贩奴船出发时间提前到1799年5月20日,8月18日遇美国船,塞莱诺自述漂泊190天,即6个多月(151页)。
在原型和小说中,西班牙船实际从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出发,可能因为黑奴的主人阿兰德是阿根廷西部的门多萨人,瓦是离他最近的太平洋港口,从那里去利马,并不应该走两个月,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船先北上,黑奴起义后又掉头南下。如从大西洋沿岸的布城出发,意味着船必须绕过合恩角北上,再加上所谓的风暴、无风、败血病等等灾难,使得漂泊4个多月或6个多月获得了可信度。在几个世纪中,西班牙殖民者开通了几条贩奴路线,奴隶的集散地是加勒比海地区,那里奴隶起义很频繁。征服智利和秘鲁地区后,印第安人人数大减,使得利马副王辖区劳动力紧缺,所以又开通了从西非南下的路线;当时没有巴拿马运河,如从大西洋沿岸去利马,只能绕合恩角(这个信息由赵德明教授提供)。所以,塞莱诺的谎言听上去有真实性。)这使作品中阴霾气氛陡增,塞莱诺的“受难”过程延长。小说大大扩大了贩奴船的规模,作为起义主干力量的青壮年男子人数从原型中的十几个扩大到近百人,突出了起义者对塞莱诺的绝对控制。小说从原型的起义者中选取了巴波(Babo)作为起义领袖的名字,使其听上去更有原始意味。(注:有许多文章讨论Babo这个名字,如Babo与baboon(狒狒)在音、形上的近似。参见Sidney Kaplan, in Runden, 172, 173 n4; Allen Guttmann, in Runden, 181.)德拉诺在西班牙船上的逗留时间也大大延长,并将原型中塞莱诺主动向慌张的起义者提议欺骗美国人的情节(原型91页),改为由处惊不乱的巴波在很短的时间内设计和布置周密的应对措施(213-214页),这使巴波成为智慧超人、能量巨大的领袖。小说对“证言”的改动更是耐人寻味。
原型中,证词的篇幅几乎两倍于美国船的日志和德的叙述,(注:其中有塞、德和美国船押货员的证词、各类证人签字认可、更正、判决、执行以及事后的通信等,十分冗长,原始文件可能达80页以上。)小说只列塞莱诺的证词,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篇幅。因所叙事件中大部分是麦尔维尔的编造或创作,所以塞的证词和原型差别甚巨。作者似乎为对付自己头脑中的这个问题,特地添加了一段话:“节录证词之前,最好加一说明”;称当时法官们听了塞莱诺的作证,觉得难以置信,倾向于认为塞的脑子出了毛病,只是后来其他活着的水手一一作证,与塞自述的一些最离奇的细节相符,才使法庭有了最后判极刑的依据。“假如这些陈述没有被证实,[法庭]会认为有责任不予采信。”(207页)这段话可视为麦尔维尔借用法庭的权威为自己创造的离奇情节所做的自辩,但它也在无形中增加了法庭的“公正性”——好像保护奴隶买卖和蓄奴制的法律并不一味听信白人和奴隶主的话,他们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取得确实证据后才做裁定。
然而,最大的改造是原型中三方的形象。《航海记》所记叙事件的骨架虽在,可人物的血肉和魂魄却纯粹是麦尔维尔的再造物。改造工程使白人形象得以提升,黑人形象则大大“恶”化。
小说全面拔高了塞莱诺和德拉诺这两个白人的品格和形象,至少是剔除了他们身上猥陋的一面。在原型中,两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经济纠纷,主要因事后塞不想如约还给德任何钱物,更不愿付任何报酬。(注:原型中,报酬和补偿问题在德的叙述和证词部分中均占了相当篇幅,前后有些矛盾。德说他为鼓舞手下人攻打起义船,曾说追回船的话,“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船和货物就都归他们了。(83页)德在法庭作证却说,塞告诉他“假如他追回船,一半价值归他,另一半仍属原物主。”(96-97页)看来两人应有过某种口头协议,但据德的证词,追回起义船后,船、货连同让美国船保管的一袋金币和几袋美金等已如数交还塞。(85页)利马总督是个明白人,判塞偿付德8,000美元作为部分报酬,而且决定还强制实行了,塞则因为拖延不付,差点被投入地牢。(86页))出身名门的塞莱诺胆小怕事,不但在受到黑人控制的时候紧张得“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就是跳船也根本不为救美国人,而是出于逃命的本能;听说德要用小艇追赶黑人,吓得要死,说“那我们谁都没命了。”(原型83页)一旦上了岸他却异常活跃,反诬德拉诺是海盗,(原型85页)为赖账成了恩将仇报的小人,哪里有小说中塞莱诺那种利他主义和感受黑暗的深沉精神!原型中的德拉诺是精明的经济动物,从不隐瞒自己的经济企图。遇到西班牙船时,他已在海上漂泊一年半,收获无多,境遇不佳,连能干的水手都被骗走。(原型78页)尽管他标榜自己“纯粹出于人道动机”(原型103页)帮助了西班牙船,但他绝不白送物资,而是期待塞在利马还钱或为他重新购置物品。(原型92页)两年后,德在波士顿收到西班牙国王赐给他的金奖章,但他期望从国王处得到更大的“实质性利益”,只可惜1808年查理四世被(拿破仑)推翻,未能如愿。(原型102页)然而《贝》则开篇就交代,德拉诺指挥着一艘大型捕海豹船兼商船,“拉着一船值钱的货物”。(141页)金钱考虑在德拉诺身上虽仍有残留,不像在塞莱诺那里变得荡然无存,但一个收获丰厚的美国船长对于物质的欲望毕竟不那么迫切了。难怪麦尔维尔在创作和修改中不断降低德拉诺预期得到回报的数字。(注:原型中德鼓动船员攻打起义船时说那船的价值有10万美元;在1855年的杂志版中数字更动为“1万达布隆”,到《回廊集》中,又往下降为“1千多达布隆”(199页;达布隆是西班牙金币)。参见Runden 192页对《回廊》初版第241页18行与杂志版的异文比较。)过滤掉利益权衡后的白人形象表现出一种哲理意义上的单纯:一个曾跌入“黑暗”的深渊,“曾经沧海难为水”,另一个则被鳞遮住了眼睛,根本不懂得何为“黑暗”。(注:德拉诺终于醒悟时,小说中用了《圣经·新约》中形容保罗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时的用语: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202页)经文见《使徒行传》第9章第18节。)
小说对黑人的改造复杂得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巴波有惊人的智商、组织能力和表演才华,这些却都是原型中的起义者所不具备的。换言之,是麦尔维尔将高智力赋予了巴波。但他同时也让小说中的起义者丧失了原型中黑奴起义单纯的目的。
根据原型中利马法庭的调查记录,出身塞内加尔的青壮年黑奴为夺船和保证起义成功,先后用棍棒和匕首杀了36名白人船员中的25名,杀了奴隶主阿兰德及其随从若干(有的未刺死推下海去);但当塞莱诺提出与起义者签署协议——他保证带黑人去塞内加尔,黑人保证不再杀人,到目的地后将船货交还白人(原型91页)。黑人也签名同意之后,他们没有再杀人(直至后来两船交火)。争取自由、返回家乡的单纯目的使他们的暴力行为在那个时代变得至少可以理解。德拉诺出手制服起义船的举动似乎更是出于对叛逆行为不能姑息这个海上通则的尊重,而不是因为他对反抗奴隶制的行为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反感。事实上,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写黑人“以拼死的勇气……尽他们所能用的一切手段进行自卫,直至最后一刻。”(原型84页)塞莱诺的证词也说黑人们“自卫到最后一刻,怒不可遏地直冲向长矛的尖头。”(原型93页)德还以同情的口吻写出死伤黑人的惨状,以愤懑的语气叙述西班牙船长和船员对被俘黑人的暴力报复。(原型84页)无论德拉诺有意还是无意,他的文字载录了一次失败起义的悲壮。
到了麦尔维尔的笔下,起义者却在与塞莱诺签署协议后,继续残酷、无理性地杀人和破坏,捣毁了几乎所有的小艇,杀了大副——除塞莱诺之外唯一会开船的人。(213页)一位老年水手因企图用“绳结”暗示德拉诺,“被借故调离视线,后来给搞到货舱里做掉了。”(176、218页)起义者简直被写成施虐成性的群体,(注:如前所说,阿兰德和塞莱诺对黑人的信任造成了起义的便利条件。小说维持了原型(89页)这个说法,并没有增添细节,说明黑人的仇恨事出有因。)就连妇女也“想慢慢折磨死”西班牙人,而不是直接杀了他们。(217页)巴波更是刻意制造恐怖,从对白人的肉体与精神折磨中获得巨大的快感。他的施虐有很强的创造性和表演性,例如就地取材、叫人用滚烫的沥青浇在青年侯爵的手上(仅仅因为后者“蜷缩了一下”);(219页)以剃须为名对塞莱诺进行威胁是又一例。(186-187页)小说中大肆渲染的,最为阴森恐怖的情节,莫过于杀害阿兰德并以其尸骨制成船艏饰。原型中,起义领袖穆里通知塞莱诺,他们要杀死主人阿兰德,因为“非如此不能保证获得自由。”睡梦中的阿兰德遭到猛刺,“还没死,十分痛苦,他们把他拉到甲板上,推下海去了。”(原型90页)这是相对平实地交待事件经过。《贝》则为巴波增加了一条杀阿兰德的理由,写出他强烈的权力欲:“为了控制住船员,他要给他们准备好一个警示,”让他们明白该走哪条路。他命人用短斧行刑,阿兰德“还没有死,被砍得血肉模糊,”但是,巴波却不让将阿推入海中,而是“命令他们在甲板上当他的面将他[阿]杀死。”(210-211页)巴波给白人的“警示”于第四天拂晓时明朗化。他指给塞莱诺看替下了原先挂在船头的哥伦布像的一副骷髅,并问他,这么洁白的骷髅,难道不应是白人的吗?他将所有尚活着的白人一一叫来,不断地威胁他们说,如有“任何反抗的言语和举动,”“那你的魂与身都将追随你的头领而去。”(212页)巴波还用白垩粉在船头涂写了“追随你的头领”,用阿的“骸骨制成的死神艏饰”则为这行字“做了个白色的评注。”(203页)
巴波的行为显然已大大超出原型中起义者们为“确保获得自由”而第二次大规模杀人的需要,或者说,争取自由的目的在无尽的肉体折磨和恐怖气氛的扩散中被大大模糊化了。(注:以上对作品中的死亡、恐怖气氛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表明,麦尔维尔不大可能赞成使用恐怖、暴力手段达到起义的目的,更不会用哪怕是隐晦的手段张扬暴力起义。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内战前麦尔维尔写过类似梭罗那样的檄文,明确表明废奴主义立场。我想指出,这种态度在当时并非少数,而且根本不能说明麦尔维尔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他是个绝对信奉美国式民主的人士,但是比他的民主姿态更鲜明的惠特曼也曾斥责废奴主义者“发疯式的狂热”,却因反对蓄奴制扩张到准州的明确观点而被“布鲁克林之鹰”报解聘。见James D. Har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5[th] ed. (Oxford: Oxford UP, 1983) 821.这至少说明反对蓄奴制度的人完全可能同样反对采用极端手段解决这一体制性问题。亦参看以上注(25)。)作者所添加的大量细节不仅使黑人起义者比原型精明能干得多,更使他们变得极其凶残。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作者真的要为起义者张目,他又为何要如此毒化真实的起义黑人形象?当我们将细节和作品中的隐喻、象征联系起来时,这种“毒化”更是一目了然。
朗敦选本的文本异动对比表明,杂志版的《贝》中德拉诺提到,两个黑人因“被一个水手不小心碰了一下,便向他发出一连串可怕的诅咒,”后来还“猛然将他掷到甲板上,跳到他身上……”(注:见电子版本的《贝尼托·塞莱诺》,所涉及段落可用“jumped upon”查到。版本比较见Runden, 191(头三条)。)麦尔维尔在《回廊故事集》中降低了调子,将“诅咒”和“跳到他身上”的细节改为“用力将他推到一旁”。(169页)然而,他的修改很不彻底,在小说中仍留下两处痕迹:德拉诺将“水手被两个黑人踩踏”(trampling)的事件列为船上无纪律性的例证;(179页)塞莱诺的证词也提到,占领起义船后,一个西班牙水手用匕首刺向被绑缚的黑人,“那人曾在当日伙同另一黑人将他推下来,跳到他身上。”(220页)
不彻底的修改反而凸现出“踩踏”的细节与船艉雕饰在形象上的关联。小说开头,德船长在靠近圣多米尼克号时,只见那“大大的椭圆形盾状船艉饰雕刻着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的纹章”,在其周围的花饰顶端有“一个黝黑的戴着面具的萨梯尔,他的一只脚踏在另一物的脖项上,后者匍匐在地(prostrate),身体扭动着(writhing),也戴着面具。”(144页)(注:纹章参看注⑤。“萨梯尔”(Satyr)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神,古典时期以来的西方艺术中,萨梯尔的形象逐渐从半人半羊演化为基本具人形,但又有某种羊或其他兽类的特征(尾、角、耳、蹄等)。“匍匐”和“扭动”在英语中常与蛇(撒旦)的形象和行为相关。)此图像又与小说中巴波紧随塞莱诺跳船后的情景惊人地相像。认定巴波向自己行刺的德拉诺夺下其凶器,将攻击者“用力推倒在船底,”左手按住半倒的塞莱诺,右脚“踩住了匍匐在地的黑人”(the prostrate negro),只见巴波又拔出一把暗藏的小匕首,“从船的底部像蛇一般扭动着身子起来了(snakishly writhing up)。”(注:原型中是塞莱诺欲用暗藏的短剑行刺被俘的黑人,被德拉诺愤怒地制止;(84页)现在麦尔维尔却将这把匕首(不,两把匕首)交到了“蛇”形的巴波手中,让他来刺杀塞,而被德及时制止。此情节对原型的改造曾被Feltenstein强调指出,作为麦尔维尔将巴波“变成纯粹的恶的表现”的有力佐证(Runden, 126)。另外,卡普兰谈到萨梯尔、扑击的立狮、蛇、扭动以及下文要谈到的狼等比喻时,指出“这些大多数是麦尔维尔本人所用的直白的形象——不是德拉诺的。”(Runden, 174))当德看到巴波用刀对准塞莱诺的心脏的时候,“真相才如闪电般掠过他那长时间陷入暗夜的头脑。”(201、202页)
蒙面的践踏者与蒙面的被踏者,黑人踩踏白人,白人踩住黑人:这三幅“踩踏”的图像不断玩弄着黑白、真假的颠倒,令人眩晕。描写中关键词语的惊人相似——“匍匐”,“扭曲”,以及巴波如蛇一样盘旋起身的姿势,却几乎向读者明示,巴波是撒旦式的蛇,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邪恶的目的。“蛇”的隐喻不是暗晦的象征,其所指在清教文化中是公开的,具有很高的公众认知度,更何况出现在这样一部有关“真相”(黑人暴动)不断被“表象”(白人海盗)窜改和掩饰的作品中。圣多米尼克号从一出现在读者眼前,就是彻头彻尾蒙着盖布的。小说开始时,德拉诺不仅看到了其船艉饰,还很快注意到被“蒙蔽”的船头。(144页)虽然遮盖白骨艏饰的帆布一直到黑人的“面具被掀开”(203页)的一刻才现形,然而死亡和白骨的意象却早在他看见“泛白”的船身和到处弥漫着的破败景象时就浮现在他脑中:“船龙骨的铺放、肋骨的拼合好像都是在以西结的枯骨平原完成的,她的航行从那里出发。”(144页)(注:《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第1-2节中,先知以西结称,“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藉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部先知书指出以色列败亡的原因并预言将来的复兴。)实际上,小说中的起义者在“真相”析出的一刻全面“恶化”了:压在舷墙上的黑人好像即刻会“发生的黑色雪崩”(201页;形容词sooty有污垢、污染的意思);他们乘大船向海上逃离时,如“逃出猎禽者掌心的乌鸦呱呱乱叫”;(203页)美国船员攻上大船后,黑人“绝望地反抗着,红色的舌头如狼似的从他们黑色的嘴巴中伸出来(lolled, wolflike)”。(206页)
在小说《贝》中有着“蜂巢般精妙叵测”(223页)头脑的巴波就是蒙面的践踏塞莱诺的萨梯尔,让城堡血流遍地的立狮,白骨船艏饰的作者,磨刀霍霍的理发师。他能在两个小时内计划得如此周全,伪装得如此巧妙,对塞莱诺看管得如此严密,乃至将富有海上经验的德拉诺完全引向歧途,这也从反面衬托出笼罩在塞莱诺们周围的恐怖气氛——那种使得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说出,甚至暗示出巨大隐情的浓密深沉的黑暗,也让我们对造成塞莱诺身心俱焚、精神彻底被摧垮的状态多了一份理解。必须指出,尽管几十个白人被砍杀得鲜血淋淋,但实施屠杀的是尚武的阿散蒂人,巴波的手上滴血不沾。大恶者不犯小恶,这正是麦尔维尔笔下“天生邪恶”(Natural Depravity)的特征。他后来在《比利·巴德》中谈到克莱格特的时候说,这种玄学意义上的罪大恶极者绝非一般的绞刑架上或牢狱里所能见到的罪犯,因为他们“一成不变,都是绝对智力型的。”(注:Herman Melville, "Billy Budd," in Billy Budd and Other Tales (New York: Signet, 1979) 37.)
这不等于说,巴波——黑奴起义领袖——就是“恶”?果真如此,这篇小说还能读吗?还应该读吗?
然而问题恰恰又在于,《贝》中的“黑奴”还是不是原型中那些争取自由的起义者?麦尔维尔已然将一个原本真实的起义事件改造成一桩巨大的、几近完美的阴谋(这对德拉诺心中有关“海盗”的阴谋情结真是奇特的反讽)。当他对真实的原型进行改写的时候,他的头脑中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幻视,使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偏转?
四
我们还是要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比喻的迷宫。《贝》叙述的既然是发生在西班牙船上的事件,那么作者使用与拉丁文化有关的意象本来是不奇怪的。但为什么原型中的人名未改,可两个本来挺合适的船名却都更改了?为什么叫“历练”号的船被改造成了与西班牙古王朝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圣多米尼克”号,虽然破败却昔日气派犹存?为什么原型中“坚毅”号的德拉诺一靠近“历练号”,立即发现了满甲板的奴隶,(原型80页)而“快乐的单身汉”号的德拉诺在隔着浓雾看去时,却先将船喻比成了比利牛斯山上“被暴风雨刷白了的隐修院,”接着看到眼前“整整一船僧侣……蒙头的修士服……在修道院回廊上走动的黑修士”?(143页)为什么他刚见塞莱诺就把他比作“患疑心病的隐修院长”?(148页)为什么说塞莱诺慵懒的、不耐烦的神情活像他那位“隐退前夕的皇帝同胞查理五世”?(149页)为什么麦尔维尔最终将塞莱诺送进了安哥尼亚山上的隐修院,并让他很快结束了生命?
先从很多评论都谈到的船名讲起,它们本身就是重要的隐喻。费尔顿斯坦可能是详细评论《贝》的第一人,她指出,美国船名来自《白鲸》中的两条船:“单身汉”号(Bachelor)和“喜悦”号(Delight),前者乐天,不信恶的存在,后者悲观,认为恶无法抵挡,分别暗合德拉诺和塞莱诺的性格。(注:Feltenstein, in Runden, 127-28.该文的标题等信息参看注(20),下文对西班牙船名的分析见Runden, 127。《白鲸》中提到的两条船分别见第115、131章。)更为重要的是,她指出了小说中的“圣多米尼克”(San Dominick)与多明我修道会(the Dominicans)的关联,以及后者与各国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的关系。甚至贝尼托这个名字(Benito)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就是本笃修道会修士(Benedictine friar)。(注:Feltenstein, in Runden, 127.宗教裁判所又译作异端裁判所,由中世纪教廷交给多明我会管理。关于塞莱诺的本名,原型中先后使用Bonito(意为“漂亮”)和Benito两种拼写,费尔顿斯坦认为小说选择后者而非前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作品的线索。)多明我修士因着黑色披风而被称为“黑修士”(Black Friars),本笃会隐士的服饰据信后来亦以黑色为主,所以也有“黑僧侣”(Black Monks)之称。(注:本笃隐修会的发端比多明我会早了六七百年,努尔西亚的圣本尼狄克(约480—约547)被视为“西方隐修制度之父”。见《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2卷,第369、370页。笔者在一部小百科中发现对本笃会服饰的说明,该条目称本笃会牧服的“颜色并未在教规中作具体规定”,据猜测起先用未经染色的羊毛织物的本色,后来“黑色成为主色,由此本笃会士也被叫做‘黑僧侣’。”Funk and Magnalls New Encyclopidia (Funk & Magnalls, 1985), vol. 3, 427.本笃修士有时也称“黑修士”(Black Friars), monks和friars两个词的主要差别在于本笃会原是一种隐修会,修士是住在隐修院中的,但从12世纪开始兴起的一些修道会中,会士成为“传教的修士”(preaching friars),他们云游于世间,从事布道和教育工作,所以比在院墙内隐修的修士活跃得多。参见John R. Hinnells, ed.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Religions (New York: Penguin, 1984) 218.中文一般将friars译作“托钵修士”。)
这一阐释打开了另一扇门,我们似乎从中体会到麦尔维尔在改造西班牙船的时候,不仅将天主教文化与玄学意义上的深沉“黑暗”之间画上了某种等号,而且还对这种文化十分迷醉。值得注意的是,“黑暗”不是体现在塞莱诺、奴隶主和其他白人身上:他让黑皮肤的黑奴在这艘被改造为修道院的船上充当了能主宰一切的黑暗势力。然而,只是在笔者读到朗敦选本中另一篇被列为“原始资料”的文章后,很多疑问才得到了合理解释。这就是H.B.弗兰克林的《〈贝尼托·塞莱诺〉:苦行僧的痛苦》。(注:H. Bruce Franklin, "'Benito Cereno': The Ascetic's Agony", in Runden, 105-117.这应是他的书(In the Wake of the Gods: Melville's Mythology)的一部分,196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许多评论作综述时会一带而过提到弗兰克林,不过一般将他归入讨论新旧世界、尤其旧世界宗教、文化的陨落和颓势一类。本文的侧重面不同。)
弗兰克林发掘出了《贝》的另一个“底本”——威廉·斯特灵所著《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隐修生活》(以下简称《隐修生活》)。(注:书名为The Cloister Life of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Fifth,文章同名。我未能找到该书或该文,因此下面的所谓比对也只局限于弗兰克林文中所谈到的部分。)据他说,“该资料的重要性从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德拉诺的《航海记》”。(朗敦105页)斯特灵于1851年在《弗雷泽》杂志连发两期,后又扩充为同名的书,到1853年已经发行第三版。(105页)该书极为著名,1853、1854两年内,许多刊载对麦尔维尔作品评论的杂志都同时有对该书的评论,因此弗兰克林认为麦尔维尔不可能没有读过。按照朗敦节选的十几页内容看,《贝》对它的依赖程度之高,使我觉得必须修正自己在第三部分所说的,“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他的原创”,因为《贝》的大量细节,甚至最重要的灵感,都来自《隐修生活》。
简要说来,麦尔维尔将斯特灵所描述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与教会、修士团的关系复合在塞莱诺与巴波为首的黑人的关系上了。依照书中说法,实行政教合一的查理五世先是利用、放纵了多明我会去挞伐新教和异端(该会即“黑修士”团体,“圣多米尼克”就是该修道会的创始人),但后来皇帝完全受到教会的控制,教会成了皇帝的真正的“主子”(小说中,不愿为黑奴上镣铐的阿兰德和塞莱诺完全落到了黑奴的手中,剃须情节一再强调巴波是真正的“主子”)。皇帝晚年陆续交出世俗权力,隐退入修道院,不久就在那里死去。塞莱诺也是被迫交出权力,几个月生活在象征修道院的船上,后来真的进了修道院,这就是小说开头时“圣多米尼克”号被比作修道院(教会的地盘),黑人被当作“黑修士”的根本动因。
难怪船的规模要大大扩大,德拉诺无论远远看它,还是在船的各处游荡,还是站在上层后甲板上,他都在强调这船原有的皇家气派;难怪船艉饰和旗布都与王室有关;也难怪塞莱诺被影射为他那“隐退前的皇帝同胞”。弗兰克林说,塞莱诺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了查理五世的幽灵——既是他超自然的幽灵,也是他的象征的幽灵。”(106页)这位皇帝死后三次被开棺,移尸(110页),但是最最匪夷所思的是,他本人在死前两个月亲自导演了自己的活出丧,一条大船载着他的棺材,浮在海面上,“海面以下有复杂的装置,支撑起代表西印度群岛的岛屿”(109-110页)(查理五世将Santo Domingo,即圣多明各岛作为第一个大规模贩卖黑奴的地点,113页),而皇帝“跟随着自己的棺材,甚至可能在里面躺下了”(110页)。这个事实更使得塞莱诺的船成了皇帝的浮棺,而德拉诺也一再使用与幽灵有关的比喻传达他对西班牙船的感觉。皇帝死后,四个僧侣为他守灵;而圣多米尼克号也有四个老年的黑人捻缝工守卫,他们的“单调的低吟声”被比作了“葬礼进行曲”。(110页,小说146页;这些人物是原型中所没有的)
弗兰克林至少还罗列了几十个细节,证明“圣多米尼克”的构造、装饰、舱房设计、房内布置、外部环境,尤其上层甲板等,全都是按照斯特灵书中描写的查理五世在隐修院住处的内外环境设计的。对人物的特征和习惯的描写(包括每日按时剃须的习惯),更是处处都有皇帝的隐修生活的影子。说到剃须,弗兰克林注意到。在塞莱诺住的小舱房内,“对其中几乎所有物件的描写不是同隐修生活有关,就是同宗教裁判所有关”,例如扔着的旧绳索很像“一堆穷修士的束腰带”,沙发竟然像“宗教裁判所的拷问台”,安乐椅看上去则像“奇形怪状的刑具”等等。这种描写不只是仿照了查理五世在隐修时的住房模样,像“宽大的、奇形怪状的安乐椅”完全就是皇帝房间里十分显眼的家具。(106-107页)
小说和《隐修生活》在语词上的对应和雷同有一处值得提出来讨论。一位批评者曾注意到麦尔维尔在塞莱诺出庭作证的时候,使用了原型所没用的词:“he[appeared] in his litter……”他紧接着问,“为什么用‘litter’?麦尔维尔是想暗示废物、垃圾,还是一窝小动物?还是大概指抬伤病员的担架?‘Litter’的意义是含混的。”(注:Mark C. Anderson, "Stolen flesh, borrowed fresh: Herman Melville's Benito Cerenodeposition,"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28. 1 (1998); 61-76. 〈http://search. epnet. com/direct. asp? an=957153&db=aph〉)必须指出,litter一词在此就是“担架”,塞莱诺是用担架抬着来的,这完全符合人物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有任何歧义。该词是从拉丁文通过中古法语进入英语的,词源意思是“床”,所以“担架”是它较早就有的意思,废弃物和一窝(小猫等)的意思倒是后来的发展。如果定要这样解释,那就像“贸易风”和“奴隶贸易”的问题一样,只能为了政治立场的需要而委屈英语的语法了。其实,litter指担架的用法在18世纪的作品,尤其与法国、西班牙有关的作品里,是非常普通的用法。不过,麦尔维尔之所以选用这个词,恐怕还是因为查理五世去隐修院的路上常常就是“borne in alitter”——用担架抬着走的。
如此说来,麦尔维尔似乎既将黑奴当成用暴力争取自由的起义者,同时又把他们当成了“黑修士”,也就是控制了神圣罗马皇帝的、擅长搞阴谋诡计的天主教的修道会。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多重身份是常见的现象,后殖民批评对角色混淆的文化含义更是关切。例如,黄梅在论述17世纪英国女作家贝恩的《奥鲁诺克》时,就分析过围绕主人公所出现的“一系列的身份混淆和矛盾百出的态度。”贝恩笔下的奥鲁诺克似乎既是黑人,又是白人,既贵为王者,又沦为奴隶,既是贩奴者,又是奴隶起义领袖。(注: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2003年,第23-25页。)同样,麦尔维尔笔下的巴波也呈现复杂的身份,他既是黑人,也是白人;既是起义者,也是阴谋家、权术家;既是18世纪末期的新世界人,也是16世纪初期的旧世界人。当麦尔维尔将黑人当成起义者时,我们能体会到他对德拉诺身上种族主义态度的批评审视。当他把他们当成“黑修士”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最深沉的黑暗和恐怖的代表。这时,由德拉诺所代表的一般美国人的倾向,即乐观,看不到也不相信大恶存在的倾向,就成为麦尔维尔批评性审视的对象。就这点而言,麦尔维尔的关怀和他所写的《霍桑和他的青苔》中的“黑暗”,以及对能否有认识黑暗的“鹰眼”的关注是一致的,和书记员面对“墙”时麦尔维尔想让我们体会到的意思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