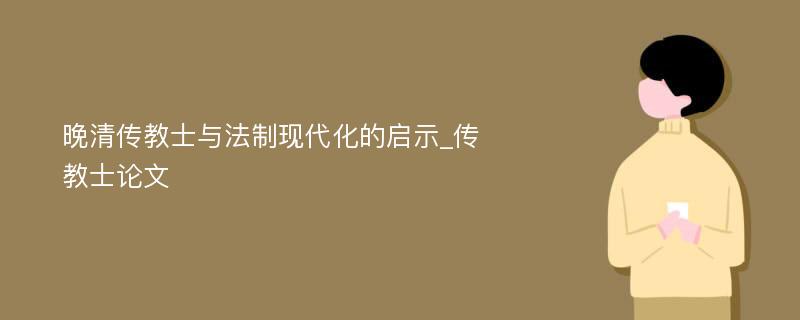
传教士与晚清法制现代化的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传教士论文,法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07)02—0043—05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法律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充当了打破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急先锋。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向古老的中国展示了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法律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潮;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向衰弱的中国灌输其法律观念和价值,导致了中西法文化的冲突。伴随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结果是封闭、排外、保守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中华法系逐渐走向了解体,而相对先进的西方法律观念和制度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中西法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并由此促进了晚清法制现代化的启蒙。
一
中西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外国传教士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继唐朝的景教和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之后,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天主教也开始进入中国传播。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这次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就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而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初西来的耶稣会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1542年他到达印度,1549年转赴日本,发现文化发达的日本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深感欲归化日本,应先到中国传教,在一个东方文明大国去填补天主教的空白。因此,1552年,方济各抵达澳门。但不幸的是碰上了中国海禁最严厉的时候,他虽曾一再想设法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均未获成功,最后只落得染疾客死于广东海面的上川岛上[1](P514),方济各虽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却起到了开路者的作用,为30年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到来打好了前站。
1582年,利玛窦抵澳。在他的带动下,一些耶稣会教士也相继来到了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适应中国习俗,结交中国士大夫,援引中国经典词句,作为传教依据,收到了一定效果。最后,利玛窦终于在1601年,以进贡为名获准觐见神宗皇帝,并允准长驻。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说,称利氏为近世西来第一人,实不为过。这些先期抵达的传教士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下了良好开端。
从方济各到利玛窦,耶稣会一开始就注重世俗学问。他们从事文化教育,用文化的手段传教。给早期的东方教会打上了人文精神印记。耶稣会在早期中国传教中,走上层传教和知识传教的路线,又为中国天主教确立了深厚的理性传统。1601年,利玛窦给中国皇帝的贡品中就有《万国图志》一册,即收有各家所绘的53种地图的世界地图集。在随后来华的耶稣会士中,艾儒略撰译了《职方外纪》,“其中各国图说至为详备”,将“四方万国地形之广狭,风俗之善恶,道术(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类之强弱,物产之怪异,具载无遗”。[2](P17—18) 文字记述部分又大大超过了利玛窦。他们不辞劳苦地译绘和增订世界地图,当然主要不在于向中国人传播最新的世界知识,而在于用它来敲开中国士大夫灵魂的大门,以传播天主教的福音。
《职方外纪》中不仅包括了有关整个世界的自然地理知识,而且也为中国人展示了一幅西方人文世界的图景。其中对欧洲法律制度就作了特别详细的介绍,称欧洲各国“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官府必设三堂:词讼大者先诉第三堂,不服,告之第二堂,又不服,告之一堂,终不服,则上之国堂。经此堂判后,人无不听于理矣。讼狱皆据实,诬告则告者与证见即以所告之罪坐之。若告者与诉者指言证见是仇,或生平无行,或尝经酒醉,即不听为证者。凡官府判事,除实犯真赃外,亦不事先加刑,必俟事明罪定,招认允服,然后刑之。官亦始终不加骂詈,即辞色略有偏向,讼者亦得执言不服,改就他官听断焉。吏胥饩廪虽亦出于词讼,但因事大小以为多寡,立有定例,刊部署前,不能多取。故官府无恃势剥夺,吏胥无舞丈诈害。”[2](P73) 《职方外纪》的编撰者显然注意到了中国刑罚的苛酷,力图以中文介绍西方的刑事制度,以此来映衬中国刑政应加以改变的必要。这些描述虽不无粉饰,但不尽虚构,它向国人传播了欧洲已将刑事诉讼规范化、制度化,建立了诸如审级制度、证据制度、刑讯制度等西方政法知识。
除此之外,1637年刻出的艾儒略的《西方问答》一书,介绍了40多个有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问题。其中也以相当篇幅介绍了欧洲的法律制度。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中记载,金尼阁随船运来的西书有七千余部[2](P7),其中介绍欧洲法律制度的书一定也有一些。
随着地理知识和文化眼界的拓展,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开始跳出“虚幻环境”,用开放的心态、平等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的短长。明末学者谢肇淛在《五杂组》一文中写道:“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已把天主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了。清初编纂的《四库全书》虽未收入《西学凡》,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承认它是一种知识,归类于子部杂家类。显见,中国士大夫已认可西学,并企图将其整合到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去。但中国传统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的封闭性,以及“内夏外夷”文化信念对人们的强大支配作用,从一开始就给迈向近代的人们设置了难以跨越的文化心理屏障,“巨大的文化遗产,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巨大包袱,它障蔽了人们的时空视野,成为文明发展的赘疣。”[3](P263) “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尚未面对来自西方的政治与军事的真正挑战,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知识和智慧的交锋。”[4](P46) 因此,这时还远未到触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到18世纪初,由于“礼仪之争”,天主教自绝于中国,来华传教士大为减少,一度出现的开放局面也遂告结束。从康熙、雍正起,清王朝一改统一中国初期的开放政策,而采取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在传教士的文化传播方面基本被堵塞了一百多年。但自康熙五十九年中国查禁天主教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5](P16—17)。随着国际经济、军事、文化交往的日益加大,中国已无法使自己置身于世界交往和国际冲突之外。在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前,那些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教士通过编印书刊等途径,捅开了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互相隔绝的封闭状态,向中国传输了大量关于西方政法的知识。
从1815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六家中文报刊和十一家外文报刊[6](P10),其主编人大多为外籍传教士。传教士办刊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宗教,这也是他们来华的主要任务,但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同时也起到了向中国介绍西方的作用。传教士郭实腊等人编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是这样一份期刊,它也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郭实腊在创刊意见中,明确提出创办这份期刊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和原则,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的途径以表明我们并非‘蛮夷’,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很多的东西。”[7](P187) 作为一种具有明显世俗化倾向的综合性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自创刊起,该刊就辟有“政治法律”一栏,举凡欧美各国政制、司法、狱政等情况,以及近代西方民主法治理论,均有所涉及,较多地介绍了有关西方政法方面的知识。因之,王健认为,“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法学的进路实以此为嚆矢。”[8] 这个论断是相当准确的。
除报刊外,这一时期传教士出版的书籍中,对西方政法知识介绍较多的当首推裨治文编纂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其简要介绍了美国的法律。该书的早期版本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和《合省国志》的编写都不同程度地参考过此书。
统观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事实上,自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近世可以说便已经开始了。”[9](P33) 虽然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政法知识还是零碎的、肤浅的,并且此时真正钻研这些知识的中国官僚和士大夫也还为数甚少,但应该说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还是起到了奏响中国法制现代化启蒙序曲的作用。
二
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成了外国传教士加紧对中国法文化渗透的阶段。1844年与1860年是两个关键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两个年份,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前者因被查禁120多年的天主教开始走向了驰禁,后者因清廷开始正式允准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0](P62)。该条约签定后不久,道光帝又批准驰禁天主教,但这时清廷对传教士来华的开放还是有限度的。中国政府明确申明,传教士“止准其在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不得擅入内地”[11](P6049)。虽然清政府对于这一禁令的实际执行并不十分严格,但其毕竟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使传教士不敢公开大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国传播西方法文化。
但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与其之前又有所不同,17—18世纪西方教会保守势力在晚清已大大削弱。较少受到神学限制的来自英美的新教传教士这时加紧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和改造,他们与中国士大夫合作,以举办文化性的活动为名,进行所谓“间接传教”、“学术传教”活动。晚清能进入清廷结交权贵的传教士,已不是耶稣会教士,而是新教传教士。
雅裨理就是这样一位新教传教士。1844年,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畲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雅裨理利用这次会晤不失时机地向徐继畲宣传基督教教义,并回答了徐继畲向他询问的许多有关中国外部世界的情况。雅裨理记叙了有关徐继畲虚心求教的情况,说:“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显而易见,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要远远比倾听各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商务关系上。相比其他国家,给予了英国、美国和法国更为详尽的考察。”[12](P169—170) 徐继畲从雅裨理处获得的有关外国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对于他此后写出《瀛环志略》是大有裨益的。为此,徐继畲在这本书中,曾先后七次提到雅裨理的名字。当然,雅裨理向徐继畲传授有关世界知识,不过是其传教的一种手段,其兴趣所在还是传播基督教。
来华传教士除言传身教外,也十分重视所谓“文字播道”工作。当然,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书报出版工作,同样是出于“使中国皈依上帝”的意图。关于这一点,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就有赤裸裸的表露,认为控制住中国出版的主要报纸和杂志,“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从这一险恶用心出发,外国传教士竞相在中国创办报刊。据统计,1860年外国教会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32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6](P19)。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我国的新闻出版业。
这一时期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1853—1856)、《六合丛谈》(1857—1858)、《中外新报》(1858—1861)等。其中,《遐迩贯珍》月刊继承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办刊思想,刊载了不少有关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历史及人物的文章,如《英国政治制度》、《花旗国政治制度》等,就介绍了英美两国的宪法。该刊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论遐迩贯珍表白事款编》称,该刊“每月以印三千本为额,其书皆在本港、省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处遍售,间亦有深入内土。”[13] 是书为时人所珍重。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将他收藏的全套《遐迩贯珍》,作为了解西学的知识读物借给他的知识界朋友[14](P146)。该刊物成了当时中国了解西学的重要参考读物。
至于《六合丛谈》,它创刊于1857年,是上海第一份中文刊物。关于办刊的宗旨,该刊主编英国伦敦会教士伟烈亚力在《六合丛谈小引》中写道:“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以中外之大,其所见所知,岂无短长优绌之分哉。若以此书而互相效学也,尤予之所深幸也夫。”[15] 希望把它办成中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阵地。虽然刊物的主编人都是随着侵略者的军旗闯进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但如同《遐迩贯珍》一样,《六合丛谈》也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法文化的交流。
最早介绍近代国际法到中国来的,也是外国传教士。1839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中英关系渐趋紧张。林则徐为制夷命下属大量收集“夷邦”的情报,发现国际法的著作有可用之处。恰在此时,美国传教士伯驾致书林则徐,认为“钦差大臣由于不了解各国的法律,不晓得他们的强大,无意识地采取了与友好国家的惯例相抵触的措施,已经程度不轻地得罪了英国”,建言“简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只需了解各个外国的特性和形势。”[16](P78) 林则徐收到伯驾的信后,便派人请伯驾翻译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中有关战争、封锁、禁运等有关规定。此后,林则徐又命袁德辉翻译了同样部分,并增译了几段。这些译文后来收录在魏源《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夷情备采部分中。
此后,因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林则徐即被撤职查办,引入国际法的工作便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但上述对西方国际法的零散翻译,还是使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国际法,激发了他们法制现代化观念的启蒙。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对英政策就明显受伯驾和袁德辉二人翻译的《国际法》影响,曾试图运用一些国际法的做法,来处理有关战争以及如何对待外国人的问题[17]。
鸦片战争后二十年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法文化影响。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不仅辑录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有关内容进行介绍,而且还给予很高的评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指责英国为“无道之虎狼”,颂扬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赞扬美国总统的选举任期制。这在中国近代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先觉的意义。在魏源之后,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也征引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有关内容,并对华盛顿极词赞叹,认为“米利坚合众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见《瀛环志略》,第9卷,“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对米利坚合众国的民主政治流露出一种向往之情,这种认识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先进的。
总之,由于鸦片战争攻破了闭关锁国的清朝封建壁障,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动荡的转型期。外国传教士越洋西来,不仅带来了上帝的旨意,而且也翻译西方书籍,介绍西方法律思想家的著作,也传播着西方近代法文化。中国封建法律思想营垒开始了初步分化,其结果导致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观念启蒙。
三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伴随着列强的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而来的。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各国传教士又正式获得了准许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从19世纪60年代到世纪末的这段时间内,传教士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内地,在中国各地凭借不平等条约,依仗本国政府的军事力量和领事裁判权宣扬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有了迅猛发展。仅以基督教徒的规模为例,就由1869年的不足6000人,发展到1890年的58000人[6](P18)。对于传教士在华势力的增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早在《天津条约》签定后不久,就公然宣称:“人们已经意识到传教士已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们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18](P1) 这些露骨的自供完全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妄图借助于传教士从精神和思想上控制中国的企图。
随着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日益频繁,西方法文化也开始大量传入中国。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于“使得中国官僚能学会半殖民地国家所应守的规矩”[19](P50) 的意图,就有意翻译一部完整的国际法著作。1864年,他在几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完成了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翻译工作,取名为《万国公法》。此书经清廷御准后刻刊出版。这是第一部以专书出版的比较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中译本。该译著出版后,清政府即发给中国各通商口岸一部,以备参考,清廷派出的外交使节,也多备有此书,在近代中国政界、外交界和法学界流布较广,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在当时中国的对外交涉中产生了效果。1864年,清政府就采用该书中有关国际法原则,处置了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中国内海扣留丹麦商船事件[20]。表明清政府已由对欧美国际法所知无多,进入到自觉运用阶段,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启蒙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与此同时,在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会中,一些有条件的教会学校开设了法律课程,教授一些国际公法知识。据《万国公报》开列的中西书院八年西学课程,其中第七年就开设万国公法[21](P8558)。清政府因洋务需要开设的少数几所洋学堂,有的也聘请了外国传教士开设有关国际法的课程。同文馆就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开设了有关国际法的课程。这些传教士开设的国际法课程,对于培养近代中国具有国际法知识的人才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清政府官办的江南制造局(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北京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和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广学会、益智书会等出版机构,为推介国际法知识也出版了一些国际法书籍。其中,傅兰雅与他人合作翻译的国际法有四部:《各国交涉之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公法总论》、《邦交公法新论》。[16](P262) 丁韪良在担任同文馆工作期间,与他人合作陆续译著出版的国际法书籍有五部:《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陆地战役新选》、《中国古代万国公法》。[16](P209) 在当时中国极端缺乏书籍的情况下,这些由传教士与人合作翻译的国际法书籍,对中国法制现代化是有一定启蒙作用的。
在外国传教士译著的书籍中,还有其他一些涉及政治法律的书籍。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及其所著的《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林乐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会议堂解》。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评介“《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而林乐知所著可能是用中文向中国人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政体、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及其理论基础——天赋人权说和自由平等说最早的一篇文章。康有为为推动变法将《泰西新史揽要》和《列国变通兴盛记》直接推荐给了光绪帝,推介此二书“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22](P195) 以致光绪帝“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23](P251)。外国传教士译著这些书籍,是出于“使中国皈依上帝”的意图,但客观上,它无异于向当时古老而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接受这些知识的大都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或上层人士,他们在得到新思想的武器后,积极推动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90年,外国教会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76家之多,比1860年增加了一倍[6](P19)。在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万国公报》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该报刊原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主办和编辑,它的前身是《教会新报》(周刊),1868年,在上海创刊。1874年,林乐知将改刊改名为《万国公报》(周刊),到1853年停刊。1889年复刊,改为每月出版,仍由林乐知担任主编,并成为成立不久的广学会的机关报,一直到1907年停刊。
《万国公报》虽为教会报纸,却大量刊载评论中国时局的政治和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知识性文章,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事刊物。李提摩太等传教士通过《万国公报》,定期地、大量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办法。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都直接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康、梁大量阅读了《万国公报》,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政论,有的就源出《万国公报》宣传过的言论。当时,就连光绪帝也阅读《万国公报》。该报刊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一部分官吏,都起过程度不等的思想启蒙作用。
总之,传教士在中国主要从事宗教传播,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注入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其中就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制的现代化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促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军旗而来的传教士,他们常常以征服者自居,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阻滞作用。
收稿日期:2006—12—06
标签:传教士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晚清论文; 海国图志论文; 法律论文; 职方外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