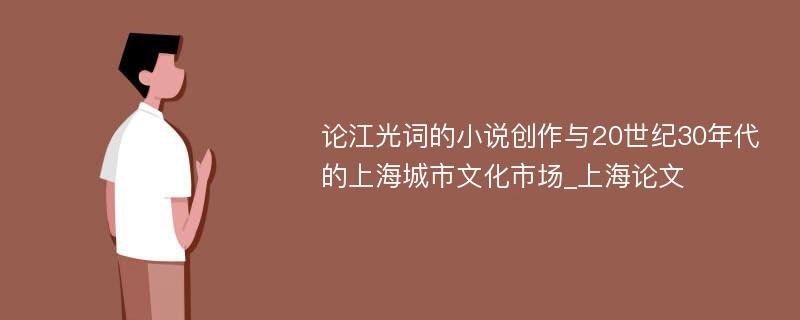
论蒋光慈小说创作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市场论文,三十年论文,上海论文,都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上海正处在都市现代化的高峰,它不仅以较发达的工商业环境为人们提供了比其他城市更多的生活需求,也以独特的政治环境、优越的经济地位和开放的文化市场为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蒋光慈的小说创作也紧紧连结着上海都市文化空间,他的创作心理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革命观念,而且具有或隐或显的文化市场意识。正是在革命意识和文化市场意识的驱动下,他才创作出迎合上海都市社会多层接受者的心理需求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展现了30年代上海都市社会文化图景。
一
郁达夫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以后,普罗文学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① 在1928年到1930年的短短一两年时间内,蒋光慈的小说掀起了畅销旋风。他的作品刚刚出版就会被迅速再版,一年之内能够重印好几次。盗版现象也十分惊人,当时甚至有专门以盗印蒋光慈作品而出名的书店。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像茅盾这样的新文学大家的作品也会被书店包装成蒋光慈的创作以出版②。不仅如此,蒋光慈小说被大量模仿,形成了“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在文坛、社会上广泛流行。一时间,蒋光慈把带有“先锋性”的普罗小说转变成畅销书和流行读物,成为上海都市文化市场的宠儿。
我们如果把蒋光慈小说“热”和蒋光慈畅销书作为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市场的独特文化现象看,那么,这个文化现象紧紧连接着作家的文化市场意识。以前我们研究蒋光慈和左翼文学,总是关注他们的革命意识、普罗理念,而没有光顾他们的文化市场意识。其实,蒋光慈及左翼作家大都具有文化市场意识的。
那么,何以见得蒋光慈具有文化市场意识呢?从哪些方面可以考察出他的文化市场意识呢?
第一,从报刊编辑看蒋光慈的文化市场意识。蒋光慈生活的30年代的上海,文化市场非常繁荣。当时的上海拥有现代中国最发达的出版机构和传播媒介,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三家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就占30年代全国所出新书的65%以上③。上海的杂志数量也占据了30年代杂志的大半江山。发达的出版系统既为上海的文学繁荣提供了物质前提,又以其商业化的运作机制改变着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作家的创作心态。当时的上海文人大多依靠文化市场来获取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办刊物、写作、翻译是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蒋光慈也不例外。蒋光慈及左翼作家,他们要创作普罗文学,要传播革命理念,首先要获得生存的条件,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才能谈得上去创作、发展革命文学。因而,蒋光慈及左翼作家们不得不以鲜明的文化市场意识,面对市场,以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和文化运作方式。这种鲜明的文化市场意识体现在他所从事的编辑文化活动之中。蒋光慈曾先后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和《拓荒者》等杂志。这个时期的杂志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杂志,明显地带上了商业化的倾向,尤其是上海的杂志,商业性更为显明。以蒋光慈编辑的《拓荒者》为例,它在凸显革命性的同时,也以商业化的倾向反映其鲜明的文化市场意识。
首先,在《拓荒者》杂志中穿插了大量有关书籍出版和杂志下期预告的广告,而这些广告与商业市场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在《拓荒者》第1卷第1期的扉页上就有蒋光慈日记《异邦与故国》的广告,曰:“这是蒋光慈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到日本养病时的日记。从这部日记里,不仅可以看到蒋光慈先生的日常生活,也能以找到蒋先生对于日本的印象,和他对于许多书籍的批评。”这就像今天的时尚杂志追踪明星的日常生活一样,是时髦读者所热心追求的。目次后第一页又有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出版广告,这一广告内容:“读者要知道白俄妇女在上海的生活吗?要了解旧俄之何以殁落新俄之何以生长吗?要读富于异国情调之作品吗?请一读蒋光慈先生的这一部长篇‘丽莎的哀怨’!”以一系列问句的方式,介绍了小说主要内容和特色,直接拨动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同时又以“风行一时”、“再版出书”强化它的发行量,彰显它的商业性。接着,在第2期和第3期中有着同样的关于《丽莎的哀怨》一书的广告,可谓轮番加强商业化炒作。当然,《拓荒者》不限于蒋光慈的书籍出版预告,其中也有其他作家作品的广告。同时,《拓荒者》还设有“国内外文坛消息”和“关于编辑室”(“编辑室消息”)栏目,这些栏目也具有广告性质。如第1期的“国内外文坛消息”中“六、中国新兴文坛杂讯”,其中有“蒋光慈君现在除创作长篇‘父与子’外,又从事于傅利采的‘艺术社会学’,及新俄名著‘碰壁’的翻译,并主编北新书局的‘中国新兴文艺丛书’”④。同时在本期“关于编辑室”栏中指出“光慈的长篇‘父与子’决定在本刊三期开始发表”⑤。这是对蒋光慈当前文化活动信息的传递,以这样的信息引起读者对蒋光慈创作和翻译的阅读与关注。
应该说,这些书籍出版预告,除了向读者及时传达了书籍出版的信息,以方便读者的阅读购买外,而更多的是通过广泛的媒体传播,扩大了作品的知名度和普及率。通过对作品富有吸引力的介绍,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刺激了读者的购买欲望。
其次,《拓荒者》中的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则具有隐性炒作的文化市场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往往借助论争吸引社会注意力,获取话语主导权,占有文学势力从而重新分配新文学资源。这里不去论及不同政治文化集团以杂志为阵地的围绕着文学属性、历史走向、功能和性质等重大问题而展开的文学论争,也不谈思潮性的、思想史的文学批评,单谈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创作倾向、审美意识、手法和风格等的批评,即文学的内部批评。作为小说家、《拓荒者》的主编蒋光慈,在20年代中、后期倡导革命文学时,就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而这种鲜明的文化批判意识很自然地带到他所主编的杂志上来了。在《拓荒者》第2期的“编辑室消息”中,他明确提出:“关于本报所刊载的创作,以及本报同人的单行本,以及其他的新兴刊物和创作,自本期起,我们已开始了自我批判的工作。无论本报同人或其他读者对于这些批判如认为有意见时,不妨尽量寄来发表。我们绝对的主张展开自我批判的工作,对内理论斗争的工作,只有这样,在指导理论和创作双方才能更进一步的得到开展”⑥。这样,在《拓荒者》2、3期和4、5期合刊中,围绕着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展开了一系列的批评和论争,主要是关于《冲出云围的月亮》和《丽莎的哀怨》。《拓荒者》第2期刊登了钱杏邨《创作月评》,他认为:《冲出云围的月亮》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的三种倾向,指出了指引现代青年的正确路线,同时也指出了三方面的缺陷。第3期冯宪章的《“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从社会政治角度和美学艺术角度高度评价了《丽莎的哀怨》,而对《冲出云围的月亮》,除了赞同钱文的赞扬的方面外,也对钱文提出的缺陷表示了不同意见,总之是对蒋光慈的创作大唱赞歌。而在4、5期合刊中,华汉则针锋相对,发表了《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对蒋光慈的这两部小说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大加批判,认为冯宪章是十足的观念论的批评。我们姑且不论蒋光慈这两部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价值究竟如何,仅从文化圈中几多人为这两部作品互相批判、互相攻击的态度,就激起了广大读者阅读作品的兴趣,想去看看究竟谁是谁非,究竟作品中什么质素引起人们的争论不休。在这里,蒋光慈已经成功地运用文学批评论争的方式调动了读者的市场期待。更令人奇怪的是,面对围绕自己的作品而产生的论争,我们在《拓荒者》杂志中,没有看到蒋光慈对这一论争的点滴态度。当事人的缺席,无疑更会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再次,《拓荒者》杂志还体现了蒋光慈强烈的读者本位意识。报纸、期刊是大众读物。任何一种报纸、期刊都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为了生存,这些报刊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一读者群的代言人。同时,读者的审美需求也反过来对作家的创作指向和杂志的办刊倾向产生影响。在4、5期合刊的“编辑室消息”中,蒋光慈们郑重申明“……‘拓荒者’始终是大众的刊物,是左翼作家所共有的杂志,要这个刊物健全,只有大家一同来努力;至于每期的缺陷,也希望大众随时给予指导,使编辑人能随时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加以克服!”⑦ 出于强烈的读者本位意识,蒋光慈及其编辑者还很注重组稿和文学通信。在组稿方面,他们常邀请读者积极参与杂志的文化建构。在文学通信方面,他们为了加强读者大众与杂志编辑的互动,开办了“文艺通信”栏。以这样的方式,达到提高宣传左翼团体也包括他自己的作品面向市场的热度。
第二,从蒋光慈与出版机构的关系看他的文化市场意识。蒋光慈的小说多生产于上海,他生活于上海而从事文学创作,就不得不依靠上海文化市场以推销自己的作品。他在上海利用同乡关系,结交了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为自己的创作开拓出版路径。他的小说主要在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现代书局、北新书局等出版。作为上海文化市场的出版机构,出版商为了赚钱,常请一些著名作家聚会,以联络感情的方式拉稿、出书。由于蒋光慈的小说畅销,因而他更是被出版社邀请的重要对象。据吴似鸿(吴与光慈1930年2月结婚)回忆:一次,现代书局和北新书局联合宴请上海的作家,地点在四马路菜馆,她陪同光慈赴宴,蒋光慈非常得意⑧。蒋光慈的“得意”,不单是有吴似鸿的陪同,更含有对自己作品销量的“得意”以及与出版机构合作的“得意”。他的小说销量大,因而抽得版税也最高,他和鲁迅的作品都是拿20%的版税,是当时上海获得版税最高的作家。蒋光慈平均每月版税收入有200元左右,他当时的生活是比较优裕的。比如,他住在沪东区广业里一幢二层楼房,还雇用一个女佣人,一个人的住房和田汉家十多个人住房面积差不多。他常在经济上接济田汉、钱杏邨,也曾汇钱到日本接济生活困难的中国留学生。他还常常带吴似鸿到四马路菜馆、法国菜馆吃饭,到南京路咖啡馆喝咖啡,到大世界、外滩公园游玩,等等⑨。可以说,蒋光慈的文化消费、消遣是上海大都市的文化市场提供的。
是的,上海文化市场需要蒋光慈,蒋光慈也需要上海文化市场,上海文化市场不仅养活了蒋光慈和一批左翼作家,而且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展。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29年9月25日,“太阳社”东京支部的成员冯宪章和森堡(任钧)来到蒋光慈的寓所。“他们俩告诉了我一件新闻:最近中国某作家写信给他的东京友人说,‘你若要出名,则必须描写恋爱加革命的线索。如此则销路广,销路广则出名矣。……名字顶好多有几个,故作疑阵,使读者疑你的某部著作,或系某重要人物之所作也。……’我的天哪,这简直是什么话!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说得出口的话吗?这是著作呢,还是投机呢?”⑩ 蒋光慈对这种机会主义行为非常愤怒,但是,实际上,他的作品刚刚出版就会迅速再版,一年之内就会被重印好几次;他的名字在那段时间里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许多出版商都非法地将他的名字用在一些仿作者的身上,例如,1930年1月,爱丽书店还将茅盾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包装成蒋光慈的创作,以《一个女性》为名出版(11)。蒋光慈的作品在市场上的成功,不仅将革命加恋爱的左翼小说转变成无尽地煽动公众欲望的商业产品,而且自己“奢侈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也变得依赖于消费量的扩大。如果没有文化市场提供给蒋光慈如此多的作品消费量,很难设想,蒋光慈能在上海立足,并以那么大的热情去从事革命文学宣传和革命文学创作。其实,依赖消费文化的何止蒋光慈一人呢?整个上海文人包括左翼作家,有谁不依赖上海文化市场而获得生存、创作的物质条件呢?
二
以上我们从报刊编辑和出版机构两方面探讨了蒋光慈小说创作与文化市场的关系,呈现的是蒋光慈小说创作的显性的文化市场意识。其实要全面审视蒋光慈小说创作与文化市场的关系,必须进一步深入审视其小说文本。当我们进入他所描绘的上海都市图景中,即可探寻出他创作的隐性的文化市场意识。所谓隐性的文化市场意识,即是他在描绘上海都市图景时,并没有带上明显地面向文化市场的炒作倾向,他是从小说家为人物活动提供生命环境出发去描绘上海都市图景的,但这些都市图景又恰恰适应了文化市场的需要,因为人们可以从这些都市图景中了解上海大都市的“现代性”进程。以《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为例,可以看出他描绘的上海都市文化图景是千姿百态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开篇就对上海繁华的夜景作了描绘:“上海是不知道夜的。夜的障幕还未来得及展开的时候,明亮而辉耀的电光已照遍全城了,人们在街道上行走着,游逛着,拥挤着,还是如在白天里一样,他们毫不感觉到夜的权威。而且在明耀的电光下,他们或者更要兴奋些,你只要一到那三大公司的门前,那野鸡会聚的场所四马路,那热闹的游戏场……那你便感觉到一种为白天里所没有的紧张的空气了。”(12) 这里紧扣上海的夜:明亮而耀眼的电光,都市漫游人,百货公司,四马路,拉客的野鸡,游戏场,写出了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特质:现代艳异、紧张热闹。《丽莎的哀怨》中的丽莎来到了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她看到:“这里充满着富丽的,无物不备的商店,这里响动着无数的电车,马车和汽车。这里有很宽敞的欧式的电影院,有异常讲究的跳舞厅和咖啡馆。”从这两部作品所描绘的上海图景中,你会感受到上海的确是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东方的巴黎”。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中,重绘了上海“现代性”进程的都市地图,这些图景包括: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生活、城市和游手好闲者。这些图景在蒋光慈及左翼作家笔下几乎也都涉笔到了。总括蒋光慈在两部小说中绘出的上海都市“现代性”图景尤其是文化娱乐、消费场所大致有四类:(1)饭店、旅馆:如一品香旅馆、东亚旅馆、远东饭店、天韵楼大东旅馆、远东旅馆等;(2)大街、公园:南京路、外白渡桥、四马路、黄浦滩公园、虹口公园、梵王渡公园等;(3)百货公司:先施公司;(4)游戏场:大世界、新世界游戏场等。这四类文化娱乐、消费场所标志着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体现出现代都市文化的消遣性、休闲性、娱乐性的特质。这是蒋光慈对现代上海大都市的现代感觉,无意中表现出对于现代工业化和物质文明的亲近和肯定。他笔下的人物在这里享受了都市文化的娱乐性,其实他本人身历其中也享受过都市物质文明带来的娱乐性。如上文所述蒋本人和吴似鸿也曾在上列有关文化消费场所游玩过、娱乐过,如到四马路菜馆、法国菜馆吃饭,到南京路咖啡馆喝咖啡,到大世界、外滩公园游玩,等等。
由于上海本身在30年代加快了“现代化”进程,随着其经济、文化的发展,生活在其中的作家们,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作家,他们只要去描绘上海这一大都市,都不会无视它的“现代性”图景。蒋光慈及左翼作家们虽然对都市的“现代性”带有焦虑和矛盾心情,但他们在客观地描绘中显露了对都市文化的肯定倾向。像茅盾,他在《子夜》的一开头就对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的都市情景作了鸟瞰式的描绘,有学者把这种描写视为昭示着“西方现代性的到来”及相伴而来的西方势力的入侵(13)。《子夜》前两章大肆铺叙了作为繁华的大都市的“现代性”的物质象征:汽车(三辆1930式的雪铁笼)、电灯和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洋房、沙发、手枪(一支勃朗宁)、雪茄、香水、高跟鞋、美容厅、回力球馆、Grafton轻绡、法兰绒套装、1930年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银烟灰缸、啤酒和苏打水,以及各种娱乐形式:跳舞(狐步和探戈),“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必诺浴,舞女,电影明星”(14)。李欧梵认为:“这些舒适的现代设施和商品并不是一个作家的想像,相反它们是茅盾试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和理解的新世界。简言之,它们象征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而像茅盾那样一代的都市作家在这种进程前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15) 其实茅盾的“焦虑和矛盾”与蒋光慈相似,他们并不排斥和否定上海大都市的“现代性”进程,在都市人们的生存领域包括作家们的生存空间,又怎么能离开这都市的现代物质生活呢!因此,从茅盾对繁华都市的“现代性”物质象征的大肆铺叙中,也潜存着对都市物质文明的肯定倾向,小说借着诗人范博文之口,说出了吴老太爷这古老社会的僵尸之所以一到上海现代大都市立即“风化”的原因,这位诗人带着浪漫激情宣称:“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风化了”。这明显地带有对古老的封建社会的诅咒,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赏。但是,同是这位诗人,他又对“都市的畸形发展”、“有钱人的死的‘舞蹈’”进行谴责,显露出他对“更加殖民地化了”的现代大都市的不满。这实际上也是茅盾以诗人范博文的激情表述,表达了他对30年代上海大都市的“现代性”进程的“矛盾”心理。
但是,作为左翼作家,蒋光慈和茅盾们对现代大都市的物质文明的亲近、肯定又是有限的,与新感觉派作家所描绘的上海“不夜城”的声光色电的图景及其对“现代化”大都市的亲近稍有不同,蒋光慈更看到灯红酒绿的都市背后所掩藏着的贫困丑陋和劳苦大众的悲苦。他描绘的弄堂、亭子间、人肉市场,又让人看到在“热闹”、紧张掩盖下的荒淫和罪恶。以他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描绘的大世界人肉市场为例,就可以看到这里的人肉“欢场”充满着上等人的淫乐与下等人的悲哀:“这又是一个巨大的人肉市场,在这里你可以照着自己的口味,去选择那胖的或瘦的姑娘。她们之中有的后边跟着一个老太婆,这表明那是贱货,那是扬州帮;有的独自往来,衣服也比较穿得漂亮,这表明她是高等的淌白,其价也较昂。有的是如妖怪一般的老太婆,有的如小鸡一般的小姑娘,有的瘦,有的胖,有的短,有的长……呵,听拣吧,只要你荷包中带着银洋”。这是一个极不公道的世界,是阶级鸿沟极为鲜明的世界,对这个世界,蒋光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态度,他对这样的人肉市场是谴责的。据吴似鸿回忆:蒋光慈有一次带着吴似鸿到大世界去游玩,他们看到了一个肥胖的白俄年轻女人,赤裸着身体,竟抱着一条公狗滚在一起。这样的场景看过后,他就对吴似鸿说:“这是资本家为了赚大钱,竟干出这种卑鄙、不人道的事”(16)。可见,他对灯红酒绿的摩登都市文明背后掩藏着的罪恶是带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去进行谴责的。与上等人在欢场寻欢作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下层人物的痛苦呻吟,黄包车夫像马一样的拼命拉车,破衣衫褴褛的乞丐哀声哀气的乞讨,被逼卖淫的小姑娘发出凄惨的“救一救我!”的声音,罢工的工人被枪杀倒在血泊里……这一类情景常常出现在蒋光慈等左翼作家的作品中。正因为蒋光慈等左翼作家带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去审视都市文明,所以他笔下的人物王曼英也以一种阶级的眼光去看待上海都市文明,她不仅与这个都市文明相对抗,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向阶级敌人(都市中的有钱阶级)复仇。当她在大世界以女学生模样的打扮去引诱复仇对象时,遇到了一个被生活所迫而沦为妓女的姑娘,这姑娘向她倾诉了求死不得的悲苦:“家中把我卖到堂子里来了,那我的身体便不是我自己的了,他们不许我死……我连死都死不掉!”“姐姐呵,世界上没有比我们这样的人再苦的了!”这位姑娘的痛苦,实际上也是曼英感受到的痛苦,“曼英因此深深地知道妓女的生活,妓女的痛苦……唉,这世界,这到底是什么世界呢?!”这个世界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一边是过着淫荡的生活,享受着别人的肉体;一边则是悲痛的供别人享用的肉体。现实生活中的蒋光慈用阶级的眼光去审视“大世界”,谴责“大世界”的不人道,而进入小说创作,他又用王曼英的眼光去审视“大世界”,让她去谴责这个世界,去发现上海大都市的严重的贫富对立。作品写王曼英“见着那无愁无虑的西装少年,花花公子,那艳装冶服的少奶奶和小姐,那翩翩的大腹贾,那坐在汽车中的傲然的帝国主义者,那一切的欢欣着的面目……她不禁感觉得自己是在被嘲笑,是在被侮辱了。他们好像在曼英的面前示威,好像得意地表示着自己的胜利,好像这繁华的南京路,这个上海,以至于这个世界,都是他们的,而曼英,而其余的穷苦的人们没有分”。这个繁华的大都市是属于资本家、帝国主义者、有钱有闲阶级的,而不属于穷苦人们的。因此,蒋光慈所描绘的上海这个号称“东方的巴黎”的大都市,其“现代化”的都市图景就明显地带上半殖民地化的特点了。这和茅盾《子夜》所彰显的带有半殖民化的都市图景是相近的。这样的都市图景适应了社会各阶层的观赏:上层人物从中得到欢乐,找到了自己的影像;下层民众看到了自己的痛苦,释放了悲苦的能量;广大市民从中满足了消遣、娱乐心理;贫富的阶级对立又能唤起人们的政治启蒙激情从而受到革命教育,而30年代的上海文化市场更需要作家们提供大都市“现代性”进程的图景,并要迅速地将上海大都市的全景推向社会,以谋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因此,多方面的功能、多方面的需要,拉近了蒋光慈与文化市场间的关系。
三
其实,蒋光慈的小说创作与上海文化市场的紧密关系,不单单表现在他所提供的上海大都市“现代性”的图景方面,而更重要的表现在他所创作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体式方面。1929年9月,蒋光慈在日本就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你若出名,则必须描写恋爱加革命的线索。”(17) 钱杏邨也说:“书坊老板会告诉你,顶好的作品,是写恋爱加上革命,小说里必须有女人,有恋爱。革命恋爱小说是风行一时,不胫而走。我们很多的作家喜欢这样干,蒋光慈当然又是代表。”(18) 蒋光慈和左翼作家创作“革命加恋爱”小说固然是为了宣传革命,但也迎合了文化市场的需要,如果钱杏邨说的话切中蒋光慈们“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心理的要害,那就可以说明蒋光慈在进行“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时,头脑中就存在着一个面向文化市场的“虚拟的读者”:充满革命浪漫谛克式的热血青年和一般市民群众。
蒋光慈及左翼作家创作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按照茅盾的评价这类小说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干革命,同时又闹恋爱;作者借这主人公的‘现身说法’,指出了‘恋爱’会妨碍‘革命’,于是归结于‘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的宗旨”。这是革命与恋爱冲突的一种类型。二是“小说里的主人公还是又干革命,又闹‘恋爱’但作者所要注重说明的,却不是‘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而是‘革命与恋爱’怎样‘相因相成’了”。这是属于“革命与恋爱相因相成”,“革命决定了恋爱”的一种类型;三是“革命产生了恋爱”的一种类型(19)。在这里,茅盾总结了“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三段式:“冲突—互惠—革命至上”(20)。以上三种类型不管是哪种类型,它们的叙事模式均离不开革命与恋爱的关系。蒋光慈在创作《少年飘泊者》时就书写了革命与恋爱,不过小说的主体是写主人公汪中由飘泊者经过人生的磨难成为革命者,大笔书写革命。作者在此篇的《自序》中明确表示要从那些沉醉于花呀月呀、哥呀妹呀的“软香巢中”跳出来“做粗暴的叫喊”,而且他看到了当时“粗暴的人们毕竟占多数”(21),做革命的力的叫喊能够为多数粗暴的人们所接受。到了《短裤党》书写革命,“粗暴的叫喊”更加有力,正像钱杏邨所评价的:《短裤党》“代表了青年的革命家表现他们最伟大的力的时期,是青年革命家的血沸腾到最高点的时候,是他勇敢向前,走上牺牲的血路的时期”(22)。再发展到《最后的微笑》、《冲出云围的月亮》,作品不仅“做粗暴的叫喊”,而且更增添了复仇尤其用肉体复仇的革命书写。尽管蒋光慈及左翼作家的革命书写存在着对革命体验不足留有概念化的毛病,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社会进步青年不甘寂寞尚思作革命之追求的时候,蒋光慈笔下的人物的“粗暴的叫喊”以及复仇的行动,无疑会引起社会热血青年的感情共鸣,使他们受到革命激情的感染和革命精神的教育。就连都市的一般青年和市民,革命书写对他们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蒋光慈作品中的革命→复仇→变态的复仇,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部分“虚拟的读者”的猎奇心理。
“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革命书写固然能吸引读者,但它毕竟是有限的,而更能吸引广大读者、更能迎合文化市场的是“恋爱”书写。蒋光慈在《野祭·书前》写道:“这本小书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著作,但在现在流行的恋爱小说中,可以说是别开生面。”(23)“别开生面”,即是指并没有落入缺乏哲理的三角恋爱的窠臼,而是从爱情的角度透视革命,以革命的选择来书写爱情。小说中的革命者陈季侠没有领受章淑君的爱情,章求爱无获从而参加工人运动。陈则与小学教员郑玉弦相恋,但郑视陈为危险人物而抛弃了他。与郑的恋爱的挫折,使陈意识到章淑君的灵魂的高洁。最后是淑君为革命牺牲,陈季侠为其举行“野祭”。这里的“恋爱”与“革命”是互动的关系,恋爱促成革命,革命又促成了恋爱,章淑君是以革命获得陈季侠的爱情。《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因革命而与柳遇秋相恋,但革命受挫,柳变节,王在堕落中用肉体向敌人复仇,后得到革命者李尚志的教育帮助,到工人群众中去重新参加了革命,获得了新生,“革命”使王曼英成了“冲出云围的月亮”,革命使王曼英获得了李尚志的爱。因此,在蒋光慈“革命加恋爱”的小说里,革命与恋爱并无冲突,革命成就了爱情。像这样由革命而恋爱,革命成就了恋爱的叙事模式在阳翰笙的《转换》和《复兴》中也有表现,小说的主人公林怀秋最初追求梦云的恋爱而不得,但当他参加革命并屡获功绩后,便成了梦云心中理想的爱人了。所以林怀秋与梦云的爱情也是由革命促成的。这类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通过革命而获得恋爱并强化了恋爱,同时在恋爱中又不忘革命。当然,左翼作家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提供的也不单单是蒋光慈式的一种模式,还有书写革命与恋爱冲突的,像丁玲的小说《韦护》中的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中的望微是在抛弃恋爱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这就显露了要革命就不得恋爱的思想倾向。而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中的素裳与施洵白的爱情,则遭到其丈夫徐大齐的破坏,徐用阴谋手段杀害了施洵白,最后素裳只身去莫斯科。这里,恋爱与革命均遭到破坏,但作为生命个体仍然坚持走革命道路。在丁玲、胡也频的“革命加恋爱”的书写里,革命成了至高无上的追求。
尽管“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叙事种类不同,在书写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时,或各有侧重,但就整体而言,恋爱书写还是胜于革命书写,而且是他们体验最深、描写最生动感人的地方。因为当时写“革命加恋爱”的作家大都比较年轻,有不少左翼作家并没有亲身参加革命运动,缺乏亲身的革命体验,多采取虚拟化的写法,故在作品中革命书写就不可能占多大篇幅,情节情感也就不大容易感动读者。恋爱书写则不同了,因为作为年轻的左翼作家,他们大都有恋爱的切身体验和对他人的恋爱的了解,像蒋光慈就有1924至1926年间与宋若瑜的爱情经历,宋于1926年11月病逝。蒋曾于1926年秋天在妻子宋若瑜的病榻前写完小说《鸭绿江上》。宋若瑜死后,蒋光慈还出版了他和宋的书信集《纪念碑》。他的“革命加恋爱”小说《野祭》也留下了个人丧偶的感哀。1930年初,蒋光慈又爱上了年轻的女学生兼演员的吴似鸿,并很快结婚(24)。这些爱情生活的体验无形中就成了他写“恋爱”的最生动的材料,因而写起来得心应手,也最容易进入作家乃至作品中的男女人物的情感境界,用这样的恋爱情感当然能吸引青年读者的心灵了。
由于“革命加恋爱”小说侧重于写爱情,而爱情本来就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古往今来的爱情小说备受世人的欢爱,何况这类小说颇似“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这就更适合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需求了。作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市民阶层,他们大都是洋场男女、公司职员、无所事事的太太小姐们,他们喜欢看电影、新旧小说、各类小报、时装杂志等,尤其是恋爱小说更是他们爱不释手的消遣“食品”。再加上这类小说不仅像“才子佳人”小说那样,它们在“恋爱”上面还加了“革命”,这样就更迎合他们的猎奇寻乐的心理需求。而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又有他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对负心人的厌弃和对忠情男女的赞赏,《野祭》中的陈季侠本来认为郑玉弦是“一个很忠实的女子,既然爱上了我,绝对不会有什么变更的”,可后来却抛弃了陈,于是郑玉弦在陈的心目中也就成了“心灵微小”的女人了。而章淑君不仅忠于爱情,而且忠于革命,因而她即使牺牲了,也成为陈季侠崇拜的爱的对象,最后他写下了一首忠情的“哀诗”。而到了《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不仅诅咒、谴责出卖灵魂背叛爱情的负心郎柳遇秋,而且还将狂热的真挚的爱送给了既忠于革命又忠于爱情的李尚志。像这样谴责负心郎、赞美忠贞的爱情的情感走向,很投合普通市民的审美心理。二是浪漫抒情的对女性的“欲望化”书写。蒋光慈写女性,《野祭》里的章淑君是“浓眉”、“大眼”、“一个圆而大的,虽白净而秀丽的面庞”,“一幅白净如玉的牙齿”,凸现女性的朴素的美。写华丽丰艳的黄女士:“高高的身材,丰腴白净的面庞,朱红似的嘴唇,一双秋水盈盈,秀丽逼人的眼睛,——就是这一双眼睛就可以令人一见销魂!”他对女性的“欲望化”书写最富有挑拨性的也只是“乳峰”和“红唇”,而没有自然主义地去写女性的“下半身”或裸体。他更多地抒写男主人公对女性的心理欲望、情感渴求,《野祭》中写陈季侠与郑玉弦互唤着“亲爱的亲爱的”进入热情的境界时,“我(陈季侠,笔者注)一把将她抱到我的怀里,和她接了很多的甜蜜的吻。这时我愉快,兴奋,欢喜到了极度,仿佛进入了仙境的乐园似的”。在他笔下常出现:男女之间的拥抱、接吻以及这种浪漫激情的抒写,很能够拨动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心灵。蒋光慈的爱情书写,到了《冲出云围的月亮》更向女性身体书写方面发展,作品中的王曼英,用肉体向敌人复仇,那女性肉体的“狂欢”展示得较为充分,这更迎合了文化消费者对于女性身体的想象需要。因此,蒋光慈的小说像《鸭绿江上》、《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等,成了出版界一印再印、包装改印、多方盗版的文化现象,这正像一位《冲出云围的月亮》的评论者所说:“为我万所料不到的,蒋光慈君的《冲出云围的月亮》,竟会在一月以后再版。还不管它每版印多少;但是究竟是我们读书界的一个好现象”(25)。是的,蒋光慈以他的文学作品开创了面向并迅速迎合上海文化市场需要的“好现象”。
注释:
① 郁达夫:《光慈的晚年》,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
②(11) 参见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第95页,第95—9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1927—1936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337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⑤⑥⑦ 《拓荒者》影印本,第416—417页,第420页,第844页,第180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
⑧⑨(16) 吴似鸿:《我与蒋光慈》第32页,第16、26页,第14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⑩(24) 吴腾凰、徐航:《蒋光慈评传》第406页,第143页,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
(12) 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文集》第2卷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
(13)(15)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5页,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茅盾:《子夜》,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8集第31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7) 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蒋光慈文集》第2卷第456页。
(18) 钱杏邨:《〈地泉〉序》,见华汉:《地泉》,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
(19) 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茅盾全集》第20卷第3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0)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第7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 蒋光慈:《蒋光慈选集》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2) 钱杏邨:《蒋光慈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作家》,泰东书局1928年版。
(23) 蒋光慈:《野祭》,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6集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5) 苏读余:《冲出云围的月亮》,《现代文学》创刊号,193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