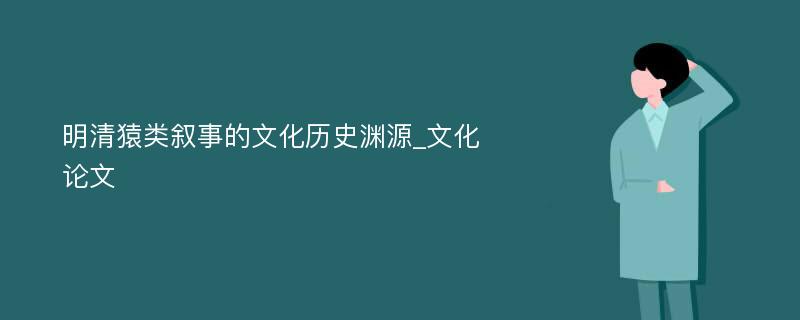
明清猿猴叙事的中外文化史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猿猴论文,文化史论文,渊源论文,明清论文,中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3~0093~06 作为地球与人并存的生物主体,野生动物中灵长类猿猴最“像”人。从生态学视野整体性考察猿猴与人的关系,当是中国农历猴年文学研究中一个意蕴丰富、饶有兴味的课题。 一、模仿表演:猢狲动物性的艺术化表现 猴子出色的表演技能,较早出现在铺陈状物的赋体文学中。例如,东汉张衡《西京赋》“猨狖超而高援”,三国魏阮籍《猕猴赋》“整衣冠而律服”、“举头吻而作态”。此后,最突出的是西晋傅玄《猿猴赋》:“扬眉蹙额,若愁若嗔。或长眠而抱勒,或嚄咋而龃断;或鄅(禺)邛而踟躇,或悲啸而呻吟。既似老公,又类胡女。或低眩而择虱,或抵掌而胡舞。”这说明猴戏拟人之特长在于进行情节剧的表演。隋代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的“麋鹿下腾依,猴猿或蹲跂”之诗句亦为猴戏的记录。唐代是猴戏的鼎盛期,宫廷大戏中有马、犀牛、大象与猴共同演出,盛行唐肃宗时的“百兽之舞”即猴戏。唐昭宗时有猴被驯服得像上朝那样行跪拜之礼,被封“供奉”赐红袍。罗隐有诗云:“二十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逢。何如学取狲供奉,一媚君王便著绯。”可见,驯猴在宫中地位相当显赫。《野人闲话》载,猴子表演引起轰动,驯化的“智慧猴”因与人类生态条件、表情行为接近,是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类人”,十分接近人类的行为特征与心理反应。蜀人杨于度养胡狲大小十余只,懂人语,可执鞭驱策,戴帽穿靴: 如弄醉人,则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狲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1](P3647)。 猴做醉态,倒地不醒,一再威吓,仍故作不理,而俯在猴耳边轻呼“侯侍中来”,装醉的猴却猛然跃起,作张惶惧怕状。当朝权臣的煊赫霸道,昭然若揭。此故事可为利用猴戏进行政治宣传之最,也是利用动物角色进行政治讽刺的一个较早范例。那么,猴通人性的信奉究属何来?魏晋以降,服食长寿的信奉,使人相信“食灵砂”可改变猢狲的动物本性,听懂人言。说明饮食是智力提升的关键一步。在这里,猴的表现能力已跨越了被利用对象角色,而成为相对独立的存在主体——人的表演搭档,它基本上能揣测人的行为内涵,这当为古人与动物相处的较高境界。 猴戏规模宏大,间或有政府行为,后随着其他戏剧活动形式的增多,猴戏渐少,乃至被挤出主流文艺演出领域,成为江湖艺人、乞丐者流赖以求生的主要方式之一。于是,猴的文化角色随着猴戏演出更加江湖化、世俗化。富察敦崇《蓝京岁时记》载:“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练广,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之沐猴而冠,殊指此也。其余扶犁、跑马,均能听人指挥。扶犁者以犬代牛,跑马者以羊易马也。”李振声《百戏竹枝词·猴戏》云:“取猴之狡黠者教之,戴面具以演剧,如人形焉。”顾禄《清嘉录》则称:“凤阳人畜猴,会其自冠带并豢犬为猴之乘,能为‘摩房’、‘三战’诸出,俗呼‘猢狲撮把戏’。”有的“艺猴”甚至还会利用自身优势记住凶手样貌特征,为曾解救过自己的恩主报仇,这在古代已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动物报仇系列。事实上,具有恩报功能的“智慧猴”已超越了动物的模仿与表演生存行为,进入人类群体的社会结构功能之中,并承担着一定的教化或伦理道德义务。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它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社会产物,亦即“人化”猢狲形象。 二、顽劣猴形象:异邦猢狲的文化引进 顽劣不羁,是猴子形象的另一面。利用猢狲的这一特性,嬉笑怒骂地惩罚、嘲弄坏女人,是印度民间具有原创性的叙事母题。例如,《故事海》描写猴子代为惩治骗子妓女:富家独子伊希婆罗婆尔曼被妓女孙陀利母女骗取五千金币,床头金尽遭驱赶,其父责备鸨母耶摩耆诃婆没把儿子教导好,于是后者训练猴子阿罗,能如数吐出事先吞下的金币。妓女孙陀利及其母见猴能吐金币,以为是一颗化作猴子的如意珠,便用全部财富来换,而伊希婆罗婆尔曼交猴后悄然离去。开始两天,孙陀利喜气洋洋,猴子每天按照她的要求吐出一千金币。而到了第三天,猴子却连一个金币都吐不出来,孙陀利怎样哄它也没有用,只好举起拳头揍它,猴子一挨揍,愤怒地跳将起来,张牙舞爪。孙陀利的母亲也来帮女儿揍猴子,猴子便抓破她俩的脸。孙陀利的母亲脸上流着血,愤怒地拿起棍棒,打死了猴子。孙陀利看到猴子死了,自己的全部财富也没有了,痛苦不堪,准备与母亲一起抛弃生命。……孙陀利和她的母亲既破财,又破相,亲友们好不容易打消了她俩轻生的念头[2](P260~265)。 猴性急躁易怒,感觉受骗的女人冲动之下恰恰忘记了不能任性,更不能用人的情感尺度、事理去衡量另一物种。猴子遭遇生命安全冲击时的变本加厉,是生命主体生存本能的必然反应,这一动物特性被人成功利用。上述故事同时蕴含着对“势利女性”阴毒本质的揭露与谴责,但有意味的是,这一母题传入中土,除了增加对底层妓女的同情,也将佛经“以恶治恶”、女人易骗易怒等要素引入,较直接地启发了清初《醒世姻缘传》中猴子向坏女人报仇的描写。 唐初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描写了巧计使猴弃宝珠事:王后将所佩真珠缨络忘在树上,猕猴持之上高树。国王使者抓住一乞儿屈打顶罪,多人受诬陷狱。大药挺身而出捕猴,他请来佩缨络的宫人,诱使猕猴模仿起舞俯身,珠堕地而大药获赏[3](P345)佛经也写了人猴私通。如姚秦时《鼻奈耶》描写一雌猕猴在比丘处屡获美食,久之共“为不净行”。值别的比丘来访,雌猕猴来,此比丘羞愧不从,猕猴便攫掣比丘使其受伤,在场众比丘这才觉察出犯戒比丘行为不端[3](P852)。故事突出了雌猕猴兽性情欲支配下的冲动与妒意。萧齐时译经《善见律毘婆沙》也写到:在禅房前游戏的雌猕猴颇肥壮可爱,一比丘以饮食引诱“共行不净法”。别的比丘来,雌猕猴见与先前那人无异:“便以欲根向诸比丘,现其淫相,举尾现示待,恐诸比丘皆有淫意,于久不见,便自作其淫行状,示诸比丘。”事遂暴露[3](P684)。又云观世音菩萨派能化为人身的猴力士努曼陀罗来雪域:“此猴到雪域吐蕃中部一个大山崖底下修定,有一岩魔女每天来到这猴子身前,显现各种不净行之爱欲情状,又现出要在猴子身前自杀的样子。……由观世音和度母加以指示后,这猴子与岩魔女结合。”[4](P80)这里与猴通婚的罗刹女代表当地土著,外来的猕猴则是以猕猴为图腾的一支氏族。据研究,今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的藏缅语族如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有以猴为始祖的传说[5],其核心情节即人与猿猴通婚,隐喻不同族群之间的通婚,这有利于人种改进。有人类学家记述说,东南亚一些传说称,当地有大量的猴子,“像大猩猩和猩猩一样,盗走妇女并把她们带到自己的森林里去”,这些半人半兽的家伙常出现在民间大众信仰中[6](P368~374)。 《北齐书》魏收本传云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诸优为猕猴与狗斗。”对此,杂技史家评曰:“这类乔妆动物戏,不但装扮外形,而且动作要求模仿动物,此类节目已形成了完整的套子和固定的形式,其典型是‘兰陵王’。”[7](P101)杂技艺人何以能够很形象地扮演动物舞蹈?这显系远古巫术的遗存,或曰人类这种“人科物种”对于与自己接近的动物关注的自然记忆。 又如钱钟书曾指出《焦氏易林·剥》“南山大玃,盗我媚妾”叙事,对后世猿猴形象特征的类型化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猿猴好人间女色,每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史者也。……西方俗说,亦谓猿猴性淫,莎士比亚剧本中詈人语‘yet as lecherousas a monkey’可征也。”[8](P546)显然,这里道出了猢狲的另一动物属性——好色,一种延续种属行为的道德评价。喜欢美色,这一人与猴族的共同趣好,或许是此类故事跨文化、超时空存在的接受基础。人猿类似,而人类正是在猿猴身上看到了人自身以及潜藏于其内心的欲望。不仅是雄性猿猴喜欢女人外在的自然属性和形式美,野女也特别喜好抢掠男人尤其是外来男人[9]。因此,上述故事作为男性社会中心的文学化显现,暗示出异类有抢掠男性的社会资源的欲望和动机,是物种间资源争夺的深层较量,也是人类种族生命力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 三、白猿形象:猢狲“类人化”行为的认知局限 与猴子相比较,猿类不仅形体巨大,智商也较高,可归入猢狲类的“智慧型”。“智慧型”猢狲具有超常能力,有不少文本曾对此加以记载,且意蕴极为丰富。 首先,唐初《补江总白猿传》被称为“将军”的白猿精,是早期神话形象的延续,也是某些人类贪欲本性膨胀的对象化展现。作品叙述西南边陲“异邦情调”的故事:梁大同末(约546年),别将欧阳纥随军南征西南至桂林、长乐。而纥妻纤白甚美,部下担心此地“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果真失妻。欧阳纥率众在深山见众妇,得知肇事者弱点,将白猿精醉缚刺杀。其实白猿也有一定的自卑感和生存危机意识,对自己的命运早怆然有预感[1](P3629~3631)。此故事充满了生命体无法掌控个体命运的悲凉,情感丰富的白猿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外研究者强调白猿故事本事的政治寓意:“作者抓住欧阳询形似猿猴和曾书《大唐宗圣观记》这两点,制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白猿故事,提醒李唐的政敌不要忘记欧阳询当年的所作所为,以侮辱欧阳询为手段来打击欧阳通,似乎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10](P280)其实白猿将军的精怪行为,更是现实生活之中作为灵长类动物一个自然状态的体现。 白猿近乎人而能力超人,其寿高逾千岁,喜“素罗衣”,有收藏宝物的癖好,且能说“华语”,爱读书,“舞双剑”,“半昼往返数千里”,甚至能依据某些征兆预见死期,且有人世间的亲情,危急时还不忘叮嘱“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巧妙地利用人的功利欲念来保全自己的骨肉。这一“智能化”的白猿形象,作为民俗传闻艺术展演,也是人性、兽性和神性的结合体,其不属于哪一物种,能力和欲望都超越了某类物种的限度,“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卢梭曾指出,欲望无限膨胀,“终于要并吞整个自然界”,还成为“使得我们要为非作恶的原因,也就这样把我们转化为奴隶,并且通过腐蚀我们而在奴役着我们”[11](P189)。白猿正因不满足于“与天地同寿”,又抢掠人间众多女子,以及无数珍奇宝物,欲望过度扩张而导致生命消逝的结局,正如其自认“此山峻绝,未尝有人至……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似乎自然界也会利用自身规律来适时调节生态平衡。其实,南朝刘宋时人刘敬叔《异苑》的精怪“牝猴”,不过是众多诱惑人类的动物精怪之一,其能量非常有限[12](卷8,P76)。但何以唐初便出现了如此神通广大的白猿精?这正是人们对于猿猴类动物体验加深、多样化的表现,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伴随文化重心南移而推进增高。 其次,与“智慧型”猿猴类动物超常的生存能力相关联的是古人对“异类”的不容受心态。如张鷟《朝野佥载》写猩猩群体面临共同的生存威胁,及其采取主动应对措施,以种群少数牺牲换取群体安全,同时对濒死者洒泪送别。此故事不仅展现出猩猩具有高级思维,能作出合乎种属安全存在的合理部署,还透露出人类对动物的选择性认同与同情,以及持不平等的物种交往规则: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帕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蓄,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13](P135)。 外国学者分析,在唐代中西(西域、中亚、南亚)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故事“可能掺杂了一些外国故事和外来传说中的成分,但猩猩就是中国境内的长臂猿,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14](P457)。但在文学作品中,山林才是猿猴的真正乐园和归宿。小猴由人抚养大、通人情,故事充满了人类中心话语下动物驯化的理念和动物观的改变。五代王仁裕蒙巴山人献小猿,起名“野宾”,强壮后非常淘气,只畏仁裕。猴还能登高树破巢掷雏,送百余里外寻归;被善弄胡狲的擒得,又颈系红绡送远处,旬日后解而纵之,后王仁裕入蜀逢巨猿下顾,红绡仿佛,呼之“野宾”还声声相应[1](P3643~3644)。与人相处日久,猴的智慧往往能够跃升,以感悟人类的情感。“逢人必啮之”的各种原因尚需考究,但淘气顽皮的确是猴的天性。当派人把它抛弃远方后,猴其实感受到了被抛弃的威胁,因此“掀扑食器,登屋掷瓦”以表示不满。再次被抛弃,猴只能无奈地回归自然,但其实仍不曾忘怀与人相处的那段时光,所以当溪水边相遇时,主人“不觉恻然”,猴子“呜咽之音”不绝于耳。其实猴与人多有相通处,尊重各自的主体性,或许才是彼此应有的相处之道。 再者,在争夺自然资源过程中,人类对猴群的征服。华夏古人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注意并利用猴性的弱点,引诱、分化、恫吓,最终发挥作为“道德代言人”的人类之优势,将同是“生态主体”的猴转化为人类食物或豢养的宠物,取消了它们的大地居民资格。《北梦琐言》描述了寺僧与猿猴接触的实况:“猕猴见僧,即必围绕,状如供养。戎泸夷僚,亦啖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禅,则必相悦而来驯扰之,逡巡众去,唯留一个,伴假僧偶坐。僧以斧击,将归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击之。然众竟不之觉。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径,仍削木棒可长一二尺者三五十条于侧边。其猴啖糟醉后,拈棒相击,脚手损折,由此并获。”[1](P3647~3648)这类擒猴叙事,体现了在共同生存空间、“资源共享”的情况下人猴之间的密切关系。僧人为了生存得更舒适,利用猴好奇的动物性行劫杀之事,违反“不杀生”佛教戒条。而猴依本性争夺人类劳动果实被人恼怒,故而予以严惩。故事中人对猴的设计捕杀,说明戒条约束不了世俗之众,反而以被戒律约束的僧人来骗猴。 人们有时依靠熟悉猴性的“弄猴人”来降服猴子。野猴祸害庄稼,引起村人招募湖北弄猴人来整治,群猴被诱入陷阱,老猴因误信误导而愧疚触壁死,弄猴人被抓伤:“待其饥疲,取一猴枭首以示,众乃大惧,各抱头俯伏,觳觫听命,一一取置笼中,得四十余头。……自此猴患乃绝。”[15](P48~49)枇杷岭作为人类和猴类共同居住地,物种之间为了生存而竞争食物本是自然存在的常态,“弄猴人”发挥强势物种特长,根据猴性设诡计将群猴一网打尽。令人深思的是,猴的社会群体颇近于人世,当老猴目睹族群遭难,负疚抱愧,居然“泪眼莹莹”地自责甚至自杀;猴群起反抗,终究被“弄猴人”采用饥饿和枭首警示降服,古代中国智慧猴的克星似乎就是人类。故事中的人猴之争,根本上还在于生态主体对生存环境、生活资源的占有与争夺。英国人类学家米歇尔·卡文纳考察非洲喀麦隆猴群,从草原迁徙到人工开垦的森林里生活:“坦忒勒斯猴在新环境区定居下来后,赢得的名声是农业的祸害。无怪农民要尽一切方法捕捉它们。1960年,正当这种猴处于灭绝关头,这一地区被划为禁猎区,它们才得以生存下来。[16](P175)故事也暗示出,在人类尚无法接受与动物平等相处的文化观念下,如果人采用更专业的捕杀方式,即使智慧猴也很难应付。此为猴类族群进化的艰难历程,也是人类重新审视生态秩序与生存模式的过程,武力压制仅仅是主体力量表现之一。 四、“智慧猴”形象:猢狲报恩的“情商”与情绪记忆 猿猴懂人性,通人情,具有“类人思维”,而且能够向人类施以救助,遵循报恩的伦理规则。据元代马纯《陶朱新录》载时人实历:某医者被执为盗,他辩解称赃物不是自己主动行窃,而是在行医时被群猴带到岩谷石室中为巨猴诊脉,“恐猴久必为患,故多与药,因欲杀之”,不料又被猴引为众猴索药,获赠银子衣物,转卖事发被拘,猴代为鸣冤,用猴语“指画若辩理者”解救医者[17](P329~330)。故事暗示出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两个生态群体间的有趣交往,猴有求于人,人却利用智慧借机欲加害生存伙伴,有些对不起报恩猴,医者薄受惩罚似乎显示了自然生态的平衡法则。有的异文则颇接近唐初白猿掠妇故事,得到医者疗救的老猿洞中“侍立数妇人,皆有姿色”[18](P254)。此与前故事具有互文性,但“猿有愧色”的人性化描写,更显示叙事者对猿类的亲和感,至少对于按照人类“知恩图报”规范行事的动物表示了认同,尽管猿窃银报恩的手段欠妥。明代李日华《六砚斋二笔》讲述了“医圣”张仲景为桐柏山老猿疗病,获赠万年古桐的故事。猿幻化为人求医,张仲景能辨出兽脉,体现了人兽和谐相处的境界[19](P364)。《都公谈纂》也称医者毛某用小柴胡汤治愈了深山老猿,获赠宝贝献给郑和获赏,郑和下西洋以此盘获海中之物吐珠,多不胜数[20](P472)。猿猴识宝物,这里的老猿也就成为可寻宝之宝,灵石吴先生也因医好白须猿翁的病疽,得到可制止汾河洪水的灵石[21](P139~140)。 早自中古汉译佛经“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而来的“人不如兽”观念,在猿猴形象中典型地体现了出来。人猿在汉文学世界里实际上并未相“揖别”,众多传闻不约而同地表明猿猴是人类与动物的过渡阶段,人类的贪婪等弱点肯定会在猿猴身上有所体现;猴所带有的淳朴,也多被作为针砭人性异化的参照。袁枚著文说,康熙年间某学士与友人同游黄山文殊院,得遇隐居的明朝周总兵,后者杀虎为群猿夺回山洞,群猿为此“每日轮班来供使令”。众猿的生活除了食用“松子、橡栗”,还有澄碧而香的“猢狲酒”,最有意味的是长髯白猿以松枝结屋而坐,手持书诵之琅琅:“不解作何语,其下千猿拜舞。”[22](P401~402)这简直就是世外隐居者的翻版。又有文说“素嗜方技”的徐纬真道经山东古庙,忽闻庙中大铁钟下有呼救声,称误伤良善,蒙谴限满,徐生如同解禁孙悟空放其出,遥见大白猿叩谢。后得年少书生赠天书谢恩,但徐生只喜欢“吐火吞刀”、“征风召雨”之术,令其深感失望,徐生果然未能用之得所,被雷火击毙[23](P226~228)。故事中的猿公已完全脱离动物本性而人化了,成了秩序与正义重构的代言人和赞助者,猿公还严守“天书不能妄用”的禁忌。 清末传闻闽中卖草扇客,途经山麓,挥扇动作为诸猿窥见,扇子被抢光,深谙“猿性”的农人告知他,作出掷扇于地的动作,“猿必效之”,一试果然。有客卖雨笠也有此经历。后来,樵夫车照来打柴,干粮被众猿窃食,他怒责后:“猿听之,若喻车意,既而同代采取,聚少成多,不逾时,已足一肩。车摇手止之,猿乃罢。次日,车多带干糇,分食众猿,猿服劳益力,日可得柴两肩,后以为常。”一次,车照被众猿拥拽至解救立崖之半的白猿,解救后仍回采樵,群猿助之如故,白猿坐视如监。有顷,白猿去而复还,以巨叶包食物令车照食。车照视之,如白蜜,未敢遽尝。猿先食,以示无毒,车照乃食。其味如桃,食尽三分之一,未食时饥甚,食后不唯充饥,更觉精神倍爽,筋骨强健,心知其异,遂留之以进双亲。双亲食之,悉弃杖而步,俨同少壮,车照大喜。 在此,山林中的白猿被描绘为具有过人的感悟能力,它与人类共同的需要是健康长寿,猿猴的上述感恩方式大有与人类追求彼此互补的意味。细心的白猿甚至还观察到恩人对白银的珍爱:“若知银为人世之急需,遂去。未几,衔一银来,置车前。”还试探更贵重的“赤金”更能博得恩人欢心,给弄来千余两。樵夫车照也常以食物酬赏群猴。在与猴群的交往中,一个普通人及家人均得到了健康长寿和富有:“车百廿余岁,犹强健如五六十岁人。车之入山食群猿也,呼哨一声,众猿立至,人咸戏以‘猴王’称之。”[24](P137~139)故事超越了众多文本结尾仅以恩报伦理解释的意蕴,展示出人们罕有言及的深远的生态意义。樵夫在这里冲破了世俗之见,人兽之隔,而与群猴一起真正回归到了同为“生态主体”的境界。猿猴如同儿童嬉笑玩耍,天真烂漫,特别是猴眼之于人的观察,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和颠覆。 猿猴何以能报恩?以其山中颇染仙隐之士的仙气,似乎在向修炼称真的路途中行进。因而,难怪也有遇仙猿得服仙草的疗病传闻。青城子《志异续编》称黄某在罗浮山采药见石壁下二老人将青草捣成丸吞吃,拾吞后他“心地清凉,头目爽利,自觉血脉和畅,骨节皆通”,喝下余浆竟不渴不饥。可是,孰料绳子被大风吹移挂住,困在岩下,夜听两位老人观天象说兵戈将起,天明土人告知说,听父亲曾讲少时常见二猿在绝壁上飞走,猜测所遇当为此[25](P11~13)。黄某病愈而战乱果然爆发。老猿成仙为人间的“智慧老人”,显示出由野兽向社会中人的转变,只不过特别类似人间的仙隐之士。董潮《东皋杂抄》说某人游黄山曾见一老者,呼名询问家事,还说与某曾祖父交好。后来还得以结识原洞主白猿,获赠木杖和舞剑术,某归家梦中得丹,九十岁仍健步如飞[26](P1~2)。老猿成仙,已同山林仙隐形象结合互动,人猿难分。 五、明清时代猢狲母题的多元取向 明清猢狲故事具有多元指向,内蕴更为复杂而趋于世俗化。如《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三回写白猿化美女获取男子元阳,还戏弄张真人,显示巫胜于道。《初刻拍案惊奇》则以弘佛反道为主题,作怪被杀的猿精原来由一个怪老道变化而来。沈会极《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第六十六回写白猿精在济宁算命,能助人考中进士,只因托人向张天师要玉印而被杀,转世托生为沈晦,成为起事首领徐鸿儒的军师。《剪灯新话》卷三《申阳洞记》写李德逢射中猴妖魁首,解救了申阳洞中三个女子。而冯梦龙《情史》卷二十一“情妖类”也收罗了猴精惑女的传闻。 即使是多情猿精,也并非只是负面形象,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伦理化、情感化社会因素。甚至猿声哀鸣的古远情绪记忆,也使其介入到凄楚哀婉的悼亡叙事中。如王猷定《汤琵琶传》写汤应曾善弹琵琶,事母甚孝,后娶邻居孀妇侍奉老母,在楚地谋生时弹《洞庭秋思》,遇一老猿哀号,抱琵琶跃水中,归省母果然母在而妇已亡,母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于是遵妇遗言,弹琵琶于其墓而祭之。哀啼的老猿,成为悼亡主体连结悼亡对象的使者,具有超越空间冥感的神秘性,烘衬出思妇的深情凄婉。 而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则把擒猴叙事作为刻画悍妇燥急性格的必要配备情节。对悍妇肆行的嘲弄,出手者竟是通人性的猴子。作品叙说素姐生日,有人推荐“傀儡偶戏”和弄猢狲游戏,素姐嫌那衣帽不鲜明,就将狄员外、狄婆子衣服拆做道具,把狄希陈衣服裁做猴子道袍夹袄,取笑木偶人是狄员外狄婆子,猢狲是狄希陈。演完戏留下那猴当作狄希陈来尽情折磨,于是猴将素姐咬得眼瞎鼻伤又逃上房[27](P1086~1087)。猴的行为体现出自然生态情况下的一种客观公正。倚云氏《升仙传》第四十八回描写剑侠运用马猴戏弄奸臣,作品叙说济小塘用法术把马猴和小石猴拘来变作两个道士,带进严世蕃衙门,公子让小塘变戏法、道士(猴)“耍飞琵琶”的提议获世蕃允许,一场戏弄奸臣的闹剧从戏弄奸臣豢养的美女开始了: 老猴听说,用手往挨挨儿茉一指,她怀中的那面琵琶滴溜溜起在空中,左舞右舞只如一个飞鸟一般。众人看着正然喝彩,小道说:“琵琶要下来,美人细看可别打着。”言未尽,唰的一声琵琶落将下来,把一个摸摸儿茉打倒在地,哀声不止。狗子大怒说:“好妖道,可害了我的美人了,小厮们快与我拿住。”小厮和捕役一齐动手。小石猴左跳右撞说:“莫要动手,还有好戏法哩。”说着就往席上指了两指,那些月琴弦子之类一齐乱飞,落将下来把赵文华、军门公子和严世蕃俱各打倒在地……几名兵士往上乱打。两个猴左右躲闪,哪里能打的着[28](P264~265)。 猴子化为道士大闹,把仙侠戏弄奸臣的喜剧推向高潮。这一幽默诙谐的场面生成,前提是人们对“猴性”的既有印象。袁枚《怪异录》卷二写在滇南采药的赖天德,得到看守沉香树黑猿的悯惜而获取沉香,还蒙黑猿护送免入虎口,可他却杀害了有恩于己的黑猿,香木宝贝亦失,可见人要相亲相安的并非只是猛兽,而“宝失金败”意旨的介入隐含了生态伦理的警示。黑猿死日,赖翁长媳生子,长大后伶俐善跳,被人呼为“黑猿子”,后作乱牵连全家遭诛,被斩前才昭明黑猿托生报仇。故事传播者感慨:“异类有恩,人类忘之,殊堪太息。至人类有恩,人亦忘之者,天焉。恐不仅赖姓一人也,不更可慨叹哉!” 在猢狲母题的文本书写中,猿猴们的人化行为,特别是驯化后的“智慧猴”已约略成为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进而引发了人与动物生态关系的深刻反思。传统文化中的人类中心意识所具有的认知局限,工具化的利用理念,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一系列话语暴力与道德挞伐,应作必要调整与改进,或许才能达至构化天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