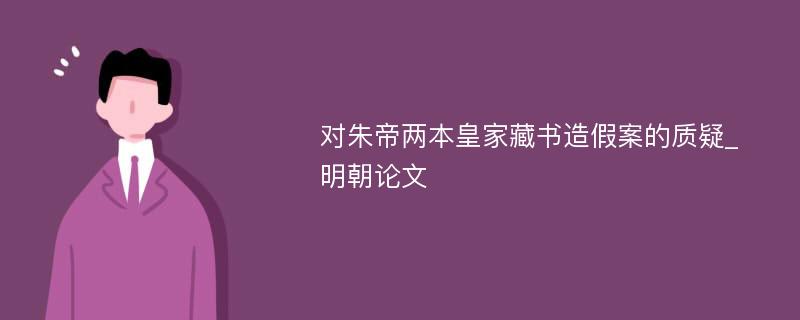
关于燕王朱棣的两篇敕书造假案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王论文,两篇论文,案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读史、著史,可谓难矣。难之所在,一是古人所记,错讹杂出,确如古人所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二是记载不实,一旦率尔著文,遽加论断,或又将贻误后人。故前人有“述而不作”之论。诚哉斯言!
本期所收二文,足证前论不虚。燕王朱棣藉靖难而登极,对史事多有篡改。这是共识,勿需赘言。然对明初史事,亦不可一概怀疑。即以《毓庆勋懿集》所载两篇敕书而论,尽管前贤已有怀疑,但是否允当,尚有待新的史料检验。就此而论,南氏所撰之文,藉其他史料,对两篇敕书重加考订,广征博引,小心印证,得出敕书并非伪造的结论。虽难说已成定论,但已将相关研究推进一步,则毫无疑问。明朝人的地理观念,虽因郑和远航而有新的认识,却尚缺乏全球的观念。尤其是对欧罗巴的认识,更是付之阙如。自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东来,才使明朝人对欧洲有了相对完整的全新认识。这是因时代变迁而使人的认知进步的典型之例。就此而论,庞氏之文,对此问题的考察,亦将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深入。
治史之要,在于“大胆”与“小心”兼备。一则敢于大胆假设。自读史之初,即抱怀疑精神,对古人之记言、记事不盲目迷信。秉此精神,则古人所说所记,疑窦丛生。问题因此而生,“献疑”由此而始。二则必须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固属不易,小心求证则更须付出艰辛。考史之难,固在多读书,然更须史识。史识的获得,无疑需要一个人的灵心,但日积月累之功亦不可或缺。人的认知,因时代而进步。明朝人对欧洲的新认识是如此,考史之得亦如此。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045-07
一、引言
明朝初年,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取了皇位。事后,明成祖为了应付当时盛行的指斥其篡位的舆论,并预防后世继续遭受非议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自己辩护,论证其得位实属合理。他组织文臣两次改写侄儿朱允坟在位时期初修的《明太祖实录》,借以伪造其善举,夸大其功绩,渲染其大得明太祖之赏识,向世人宣示,似乎明太祖在其末年已有传位于其人之心意,就是这一系列举措中的重要一条。有鉴于此,后世史家特别是民国以降,王崇武、黄彰健等大家对此多有批评和揭发。诸位先生之努力,廓清了许多历史迷雾,使真相大白于世,对于明初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笔者与许多同行都深得其益,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光耀于史学史之上。但是,其具体论证,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也难免或留下有待商榷之处。《明太祖实录》卷257载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亥(二十九日)命燕王(即明成祖,时尚为镇守北平之藩王)统率诸王备边防秋的一篇敕书,王崇武先生曾提出“疑为(《明太祖实录》)馆臣所伪造”[1]卷1,9。黄彰健先生更曾撰写专文《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2]第34本下册,将《明太祖实录》卷257所载另两篇与上述敕书相类的敕书论定为伪造史实。而近日笔者研读了一些史料,认为王、黄二先生的这一论点即应予商榷。王、黄二先生的这一论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信息,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影响甚大。对于黄先生一文,不仅黄先生本人在其所著《明太祖实录校勘记》中已加以引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出版),而且功力极深、学术价值极高的钱伯城等先生主编的《全明文》,在其第一册有关部分也予全盘照搬(199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他绍介转述者更非罕见。为了对历史真相负责,也为了更好地向王、黄等先生学习,将其研究明初史的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笔者特将关于黄先生一文中论定有关两篇敕书伪造史实的不同意见写成此文。因为王先生对这一问题只提观点,未加具体论证,故本文不再具体分析。
二、有关敕书之原文及黄先生之分析
为了便于讨论,首先将《明太祖实录》卷257所载两篇敕书原文转录于下。其中载于该卷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乙酉(九日)条的一篇为:
敕今上(这里的“今上”指时尚为燕王的明成祖)曰:迩闻塞上烽火数警,此胡虏之诈,彼欲诱我师出境,纵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堕其计中。烽起之处,人莫宜近,虽望远者亦须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虏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度其人马不下数万,岂可不为之虑!可西凉召都指挥庄德、张文杰,开平召刘真、宋晟二都督,辽东召武定侯郭英等,会兵一处。辽王以都司及护卫马军悉数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军须十五万,布阵而待。令武定侯、刘都督、宋都督翼于左,庄德、张文杰、都指挥陈用翼于右,尔与代、辽、宁、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使彼胡虏莫知端倪,则无不胜矣。兵法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尔其察之。
其中载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十二日)条的一篇为:
敕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虏远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候,余皆选拣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地屯驻隄备,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
黄先生论定以上两篇敕书之伪造史实,系根据原北平图书馆所藏《毓庆勋懿集》中收录的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及五月十三日明太祖予武定侯郭英敕书两篇。《毓庆勋懿集》一书,笔者无机会见到,据上述黄先生一文,可知为武定侯郭英的后人武定侯郭良所编,于正德中由郭良之子郭勋增辑刊行。为了便于讨论,亦需将《毓庆勋懿集》中收录的这两篇敕书原文引录出来。据上述黄先生一文,其中洪武三十一年四月的一篇原文是:
敕武定侯郭英等:迩闻塞上烽火数警,此胡虏之诈,彼欲诱我师出境,纵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堕其计中。烽起之处,人莫宜近,虽望远者亦须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虏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度其人马不下数万,岂可不为之虑!可西凉召都指挥庄德、张文杰,开平召刘真、宋晟二都督,尔等会兵一处。辽王并都司及护卫马军悉数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军须十五万,布阵而待。令武定侯、刘都督、宋都督翼于左,庄德、张文杰、都指挥陈用翼于右,代、辽、宁、谷等王居其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使彼胡虏莫知端倪,则无不胜矣。兵法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尔其察之。故谕。洪武三十一年四月。
其中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的一篇原文是:
皇帝制谕武定侯郭英:命尔挂靖海将军印,充总兵官,都督宋晟、刘真充副总兵,启辽王知道,将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官军,除开原留一百望高外,其余选拣精壮统领,跟随辽王前往开平迤北二三程地,择险要去处驻扎陡备。一切发号施令,皆尔等为之,仍听王节制。如制奉行。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黄先生在其上述一文中,对以上所述《明太祖实录》所载的两篇敕书,与《毓庆勋懿集》收录的两篇敕书进行了对勘,而后加以分析,就其异同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对比《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九日)条所载的敕书和《毓庆勋懿集》收录的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敕书,可以发现两者的重大区别有二:一为前者首句作“敕今上”,即敕燕王,后者首句作“敕武定侯郭英等”,即两者所记敕书下达的对象不同。二为前者文中之“尔与代、辽、宁、谷五王居其中”一句,将受命出师的藩王记作包括燕王在内,共有五王,后者文中相应之句作“代、辽、宁、谷等王”,未记燕王包括在受命出师的藩王之内。对于这两个区别,黄先生在文中所作分析说:“《毓庆勋懿集》所载盖据家藏原敕,所记自真实可信。太祖与郭英敕书仅言‘代、辽、宁、谷等王居中’,未言燕王,是燕王未受命出师。《实录》之作‘敕今上’,命率诸王防秋,明系据太祖与郭英敕书改窜,并伪造史实也。”
对比《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十二日)条所载给予武定侯郭英的敕书和《毓庆勋懿集》收录的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给予武定侯郭英的敕书,可以看出两者所记日期相差一天,但基本内容和行文结构等并无大区别,它们当是同一敕书,惟所记日期或有一种不慎有误,前者当为删润后者而成(两者之相互关系黄先生此文已予指出,读下文所引即可得知)。另外,也可看出,两者有一重大区别,即前者言及“悉听燕王节制”,而后者并未谈及燕王,相应句子作“仍听王节制”,联系上文阅读,此“王”当作“辽王”。对于这个区别,黄先生在文中所作分析说:“《毓庆勋懿集》所载明系原敕,而《实录》则据宫中所藏敕底删润。原敕言:‘仍听王节制’,王即辽王,《实录》改作‘悉听燕王节制’,此则永乐史臣伪造史实矣”。由这一分析出发,黄先生又进一步在文中提出辽王当是这次行动的主帅,说:“以情理言,命将出师,当设主帅,而主帅亦未有命二人为之之理。与郭英原敕仅言听辽王节制,则辽王当即是行主帅”。
黄先生上述分析的核心,是当时燕王没有受命率诸王备边防秋,而受命担当其任的实为辽王,《明太祖实录》记燕王受此命令乃属伪造史实。这一分析是在引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作出的,甚有说服力,是其在学界影响甚大的原因所在。不过,细思当时的状况,仍会使人感觉这一结论存在可疑之处,而现存的一些黄先生没有注意到或虽注意到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史料,也可使这一历史问题得出相反的结论。
三、不用兄长充当统帅之疑惑
阅读上节所引《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九日)条所载“敕今上”敕书和《毓庆勋懿集》收录的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敕武定侯郭英等”敕书,可知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明太祖下令率兵备边防秋涉及的军队,主要包括山西、北平和辽东的驻军,而当时这一地区明太祖封驻的藩王,有燕王朱棣、代王朱桂、辽王朱植、宁王朱权、谷王朱穗、晋王朱济熺凡六王。
如前所述,上引《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九日)条所载“敕今上”和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十二日)条所载“敕武定侯郭英”两篇敕书中,记载其时受命统兵参加此次备边防秋的藩王共有燕、代、辽、宁、谷五王,且由燕王负总率诸王之任,《毓庆勋懿集》所载洪武三十一年“敕武定侯郭英等”和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皇帝制谕武定侯郭英”两篇敕书中,只记代、辽、宁、谷四王参加这次行动,且令郭英等听从辽王节制,而黄先生则在其文章中据《毓庆勋懿集》所载两个敕书,主张事实应是此次行动仅代、辽、宁、谷四王参加,燕王缺席,担负主帅者为辽王其人。如果果真如黄先生所说,那么结合上表所列其时山西、北平、辽东地区明太祖所封驻诸藩王的情况,进行审视,则可发现,这次军事行动在有关藩王的统帅责任安排上,不仅根本不让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头号兄长燕王朱棣参与其事,而其余的四个兄弟代王、辽王、宁王和谷王中,也用位居其次的辽王跃居于位居其上的代王之先。这种以弟统兄、舍弃兄长不用的办法,按之当时的处事惯例,应当是不可能出现的。
孝悌即孝事父母、尊敬兄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处世准则,明太祖对此极为重视。他曾对召至京师的富民说,能够做到“尊敬父兄,和睦亲族”等规范者,“方为良民”[3]卷2,《崇教化》。曾对礼部尚书李原吉称赞虞夏商周之世,认为当时由于“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3]卷2,《厚风俗》。还曾强调“齐家莫如礼”,“居家有礼则长幼叙”[3]卷2,《议礼》。他甚至因为赞赏尊敬兄长,还可破例为有此举动者轻处罪犯。洪武二十九年九月,“民有犯死罪者,其弟诉于通政使司,愿为军以赎兄罪,辞意恳切。上(指明太祖——引者注)悯之,命同系者三十余人,皆减死戍边”[4]卷247,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丙子条。对于其儿子们的关系处理,他同样注意提倡孝事父母、尊敬兄弟、长幼有序。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为了使年幼的第二十子韩王朱松、第二十一子沈王朱模,通过“游观诸王国都,以敦友悌之情”,明太祖特别安排他们用半年的时间,前往远在北方的二兄秦王朱樉、三兄晋王朱棡、四兄燕王朱棣、五兄周王朱橚、七兄齐王朱榑所在封国,进行拜访[4]卷232,p3下-4上,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寅条。在出现儿子们共同从事某一活动而须排序时,明太祖总是将长幼有别的因素考虑进去以作安排。如在其洪武前期撰定的为儿孙规定行为规范的《祖训录》中,他明确写下:“凡亲王每岁朝觐,不许一时同至,务要一王来朝,还国无虞,信报别王,方许来朝。诸王不拘岁月,自长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亦分长幼而至。周而复始,毋得失序”[5]371。“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诸王遣使奉表称贺,谨守边藩,三年不朝,许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员入朝。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规,委任正臣,内无奸恶,三年之后,亲王仍依次来朝。”[5]375到洪武末年,明太祖根据情况的变化对《祖训录》进行了修改,改名为《皇明祖训》,以上两条又被一字不易地保留了下来[5]396、401。当出现两王及两王以上同时出征、需要确定一王担任统帅的场合,明太祖也总是毫不犹豫地以长者出任。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敕谕第七子齐王朱榑率山东都司等精锐马步军士出征,规定其要受四兄燕王朱棣的“节制”[4]卷199,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乙酉条。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敕第十三子代王朱桂“率护卫兵出塞”,规定其要受三兄晋王朱棡的“节制”[4]卷226,洪武二十六年三月辛亥条。三十年五月,命第六子楚王朱桢“率师征古州洞蛮”,以十二子湘王朱柏“副之”[4]卷253,洪武三十年五月乙卯条。大量史实说明,明太祖对于孝悌这一传统规范不仅非常重视,而且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类实际行为中,严格遵循行事。在这样的情形下,怎能想象他在洪武三十一年下令诸王统兵备边防秋的这次行事中,会完全不顾长幼之序地确定统帅人选呢!
燕王朱棣不仅在当时山西、北平、辽东地区的诸位藩王中居长,担任宗人府右宗正之职[4]卷195,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丙戌条,而且之藩最早,屡次率兵出征,多有战功,经验丰富,这些当为史家之共识。在洪武后期,其与明太祖的关系亦未见能确证有不和谐之处的记载,而其正常活动并仍受明太祖正常对待和使用的记载则俯拾即是。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九月,燕王朱棣向朝廷进献了永清左卫龙门东屯所产八棵嘉禾,表现出对当朝嘉瑞的祝贺[4]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条。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二月,明太祖令燕王选精卒壮马,“抵大宁、全宁,沿河南北,觇视胡兵所在,随宜掩击”[4]卷244,洪武二十九年二月辛亥条。洪武三十年二月,明太祖因从曾孙靖江王世子朱赞仪年幼,“欲其知亲亲之义,且令涉山川险易,以成其德器”,特命之不顾路途遥远,分别前往拜访居于各封国的十三个亲王,其中之一即为燕王[4]卷250,洪武三十年二月己亥条。同年四月,明太祖又令燕王同晋王共同“督诸王并都司、行都司,报知孳畜预战马数”[4]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条。明太祖对于行为不端的在外藩王,往往将之召回京师,严加教训。如洪武二十四年,因秦王朱樉“多过失,召还京师,令皇太子巡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翌年始命归藩[6]卷116,《诸王》。而在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布置发兵备边防秋之时,并无召燕王回京师之事[7]第四章第二节,《燕王入朝》。这当为此时燕王一如既往地正常活动并仍受明太祖正常对待和使用的有力证据。在上述情况下,当时明太祖之决定诸王率兵备边防秋,只能是毫不犹豫地安排燕王参加,并让他统帅诸王和其余参与其事的将领、士卒,而不可能作出另外的选择。
黄先生在其文章中,对于其所谓燕王此次未参与行动并任统帅的原因,作过如下一番解释:
以情理言,晋王既殁,燕王于诸王中年最长,苟命诸王出师,似当命燕王统率。于时太祖春秋高,太孙参预朝政,即心不乐燕王,亦似不宜见之行事,而使燕王难堪。《奉天靖难记》言:“燕王沉静深远,莫测其端倪”,是燕王早已蓄有异谋。意者燕王于晋王殁后,惧太孙疑忌,遂称病韬光养晦,亦未可知也。
按,所谓燕王“沉静深远,莫测其端倪”,为《奉天靖难记》中所载建文帝即位后黄子澄对齐泰所言。但“沉静深远,莫测其端倪”,仅为论其智谋多端,不易窥测,并非指为“早已蓄有异谋”,更不能由此而断定“燕王于晋王殁后,惧太孙疑忌,遂称病韬光养晦”。按之史籍,当时燕王不仅与明太祖关系正常,而且其对军事行动仍在正常参与。朝鲜史书记载: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日,“辽东被掳人金松逃来(朝鲜),告曰:‘蒙古军向辽东,燕府王率师攻击,败之,辽王领兵将行,予亦充军而行,中路逃来。’”[8]卷14,戊寅七年六月甲寅条这里所说的燕府王(即燕王)与蒙古人作战之事,当发生在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日以前一到两个月(将金松其人由辽东逃到朝鲜所需时间计算在内),而这一年有闰五月,故此事发生之时当为本年五月或闰五月,这是证明当明太祖于这年五月下令诸藩王率兵备边防秋时,燕王仍在正常参与军事活动的明确史料。既然此时燕王仍在正常参与军事行动,那么谓其“称病韬光养晦”,可知绝对不合实际。黄先生亦自知这一说法软弱无力,因而在文中加上“意者”、“亦未可知”之类表示只是姑且推想的词语。关于这一番话,黄先生在文章的下文没有作进一步申述,更没有提出任何一条可作佐证的史实。这种没有史料根据、有嫌牵强的论说,显然无法令人首肯,从而无法令人解除对所谓燕王未受命参与此次行动之说的怀疑。另外,即使退一步讲,姑且承认黄先生关于燕王因“称病韬光养晦”而未受命参与此次行动之说,其所谓辽王担任此次行动统帅的论点也不能成立,因为对于由此出现的在代王、辽王、宁王、谷王四兄弟中,舍去年长的代王不用,越次起用居于第二位的辽王,这一不合惯例的现象,仍将无法解释。
四、燕王受命率兵备边防秋之证据
由第二节的引文可知,不论《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九日)条所载“敕今上”敕书,还是《毓庆勋懿集》收录的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敕武定侯郭英等”敕书,皆称都指挥庄德在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明太祖下令备边防秋时,被确定为“翼于右”,可见庄德之受命参与其事,当属史实。而最近笔者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而黄先生却未及注意的重要史料,它既涉及庄德,也与燕王之受命率兵备边防秋有关。它就是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明太祖发出的一道圣旨。此圣旨收载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抄本《太祖皇帝钦录》之中。该书共载有明太祖敕谕诸藩王的圣旨或函件106件。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发出的这道圣旨的原文为:“说与晋王知道,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隄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9]这里的张杰,当即《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九日)条所载“敕今上”敕书中的张文杰,这里的“教陈用、张杰、庄德”“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当即《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九日)条所载“敕今上”敕书中的“(令)庄德、张文杰、都指挥陈用翼于(燕、代、辽、宁、谷五王之)右”。两者的区别仅在一用口语,一用润色过的书面语言,内容则毫无差别。由这一史料看来,燕王之于洪武末受命率兵备边防秋一事,不仅仅在《明太祖实录》有记载,而且在《太祖皇帝钦录》中也有明确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太祖皇帝钦录》中所载的这道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圣旨,其形成早于永乐十六年五月初一日修成的《明太祖实录》[10]卷200,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朔条21年之久,其所记的内容不可能为抄自《明太祖实录》的记事,这使之应被视为当之无愧的确凿可信的史料。换言之,这道圣旨透露出的关于燕王曾受命率兵备边防秋之事,应是不可轻易怀疑的。
查焦竑《国朝献征录》,其中收载有《忠节录》所撰的庄得传,传中称“庄得,洪武末为西凉都指挥,召至北平,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11]卷110。这里的“庄得”实即“庄德”①。这里所说的“为燕兵右翼”,似即指作燕王所率部队之右翼,如果这一推测不误,这一记载也为洪武三十一年四月燕王曾受命率兵备边防秋提供了一个依据。无可讳言,这条记载在单独充当上述证据上,是有嫌不足的。《忠节录》即《建文忠节录》,又称《备遗录》,为正德十一年张芹撰成。由于《忠节录》成书年代晚于《明太祖实录》,现在又无资料证明其记载并非抄自《明太祖实录》,因而不能断定其中的“为燕兵右翼”之说是否本于《明太祖实录》。另外,其“燕兵”一词也不等同于“燕王”。显然单凭此书来判定燕王当时确曾受命率兵备边防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然而,将此书与上述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圣旨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其对印证燕王当时确曾受命率兵备边防秋,当认为或有一定的作用。
由第二节引文还可知,不论《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乙酉(九日)条所载的“敕今上”敕书,还是《毓庆勋懿集》收录的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敕武定侯郭英”敕书,皆称都督宋晟在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明太祖下令备边防秋时,被确定“翼于左”,可见宋晟之受命参与此事,亦当属史实。查张廷玉等撰《明史》之卷155《宋晟传》,其中载有“(洪武)三十一年出镇北平,从燕王出塞,还城万全诸卫”之语[6]4246。这一记载,可说是为燕王在这次明太祖命令备边防秋时,受命参与其事并居于统领地位提供一个佐证。黄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及《明史》的这一记述,但以《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五月所载宋晟本传(查《明太宗实录》卷69,此传实系于永乐五年七月——笔者注)及杨士奇《东里集》卷12宋晟神道碑,“均未言是年从燕王出塞”为由,断定“《明史》书(宋晟)从燕王出塞”,乃“原本《太祖实录》,非另有确凿可信之史料以为其依据,不得据之以难本文所论也”,即仅靠《明史·宋晟传》之记载,尚不能认定燕王在其时确曾受命率诸王备边防秋。《明史》之撰写远远晚于《明太祖实录》,《明史·宋晟传》之“从燕王出塞”一语,就目前所知者,尚为既不能排除其非据《明太祖实录》写出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其据《明太祖实录》而来的可能,因而黄先生的这一意见除“原本《明太祖实录》”一语有嫌武断外,其余当是正确的。但如上所述,现在已发现了燕王曾于洪武末年受命率兵备边防秋的确凿可信之新史料,对于《明史·宋晟传》之“从燕王出塞”一语,显然就不应再断然否认其佐证燕王当时确曾受命备边防秋史实存在的作用了,起码应承认其与《忠节录》中的庄得传一样,或有一定的作用。
在明代史家黄光昇的《昭代典则》卷11(万历庚子万卷楼本)及何乔远的《名山藏》卷4《典谟记》(崇祯刻本)之中,皆记载有本文上述《明太祖实录》卷257所载“敕今上”、“敕武定侯郭英”两篇敕书。另一明代史家谈迁的《国榷》卷10(古籍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记载有本文上述《明太祖实录》卷257所载“敕今上”一篇敕书,其关于燕王于万历三十一年是否受命参与备边防秋并统帅诸王一事的记载,皆与《明太祖实录》卷257所记相合。从行文结构和用语看,他们当为抄自《明太祖实录》,在论定这一疑案时,自然不可将之当作判断是非的有力证据。但这些史书的作者皆为卓有贡献的明史大家,其之认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似不应轻易给予否定,在现在发现了可证实《明太祖实录》记载之确凿史料的情形下,更应如此。由此说来,黄光昇等三位明代史家的上述记载,也可当作论证《明太祖实录》卷257所载两篇敕书,在燕王洪武三十一年参与备边防秋并统帅诸王上并未作伪的部分佐证。
五、关于《毓庆勋懿集》所载两篇敕书之解释
以上已从惯例和史料证据两个方面,论证了《明太祖实录》两篇敕书所记燕王洪武三十一年曾受命参与率兵备边防秋并任各路军统帅史事之可信。为了论证更加完整严密,尚须解释何以《毓庆勋懿集》中的两篇敕书所载与之不同。前文已叙及,由于条件的限制,目前笔者尚未读到《毓庆勋懿集》原书,因而不能做出十分详尽的解释,只能就所看到的黄先生上述文章中对此书的介绍,提出一点大胆的推测。
据黄先生介绍:该书“所录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凡八”,除上述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及五月十三日两敕外,还有“洪武二十年七月九月,二十一年正月二月,及三十年正月三月六敕”。此六敕所记与《明太祖实录》相合,但“(洪武)三十年三月与郭英敕书,《实录》系于是年四月辛卯。恐当以《实录》为正。《毓庆勋懿集》所载此敕有讹字,如‘应有机务,条列以闻’,列字即误作例。”
黄先生在这里当非就《毓庆勋懿集》所记八个敕书的文本优劣,作全面检讨和评论,但即便如此,已可发现,其竟能在一个敕书中至少有两处错误(从“如‘应有机务,条列以闻’”之行文中用“如”字,似可推想,可能其误当更多),不仅有错字,而且连敕书的时间也搞错了。可见《毓庆勋懿集》绝非编写谨慎、校勘精良的刊本,其有关记载难免有误。
《毓庆勋懿集》既是这样一种书籍,对其记载当不可盲目相信。当其他记载与之有差异时,要仔细分辨,只有发现了另外可信的史料可与两者中的某一方相呼应和印证之时,才可将信任票投给某一方。当下遇到的这项燕王于洪武三十一年是否参与备边防秋活动及出任统帅的疑案,即应如此处理。就笔者所知,在这个疑案中,《毓庆勋懿集》否定燕王在洪武三十一年参与备边防秋活动并出任统帅的记载,得不到另外的史料的明确呼应和印证(黄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未见提出),而与之记载相反的《明太祖实录》,却得到了另外的史料的明确呼应和印证(这在上文已经叙及)。面对这种情景,结论显然应当是抛弃《毓庆勋懿集》的说法,而采信《明太祖实录》的记载。
关于这项疑案,《毓庆勋懿集》为什么发生了错误呢?笔者仔细研读其文后,有一大胆的推测:当是其在两个敕书中各脱一“燕”字,即其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敕武定侯郭英等”一篇敕书中,在“代、辽、宁、谷等王居其中”一句的开首脱一“燕”字;其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皇帝制谕武定侯郭英”一篇中,在“仍听王节制”一句的“王”字前脱一“燕”字。试将这两篇敕书各补一“燕”字,其全文读起来并无不顺,而又可与其他各书之记载不相矛盾。此种设想,岂非可备一说?
六、余话
本文否定现存《明太祖实录》中的上述两篇敕书对史实有所伪造,并非完全否定现存《明太祖实录》一书有歪曲历史真相的现象。包括王崇武、黄彰健等先生在内的诸位前贤对明成祖君臣在《明太祖实录》以及其他一些史书中歪曲、伪造历史的真相进行揭发,意义重大,功绩不可磨灭。如果笔者关于上述两篇敕书的论述确能成立,也不可因前贤的偶有一失而忽视甚至否定其作出的巨大贡献。
《明太祖实录》中所记燕王参加上述率兵备边防秋活动并担当统帅的敕书,除前面论述的两篇外,尚有另外两篇。其一为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十二日)给左军都督杨文的一篇,其中说:
敕左军都督杨文:兵法有言,贰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应敌,为将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宁三府护卫,选拣精锐马步军士,随燕王往开平隄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军悉听节制。慎毋贰心而有疑志也。[4]卷257,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条
其一为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亥(二十九日)给燕王的一篇,其中说:
敕今上(这里的“今上”指时尚为燕王的明成祖)曰: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 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等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朕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4]卷257,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亥条
这两篇敕书,皆可作为肯定洪武三十一年燕王曾受命参与率兵备边防秋活动并担任统帅的证据。黄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曾提及这两篇敕书,但以《毓庆勋懿集》所载的上述两篇敕书为依据,否定了其真实性,认为它们与上述《明太祖实录》卷257所载两篇敕书一样,为改篡伪造而成。但黄先生在此并未提出其他证据,上文对上述《明太祖实录》卷257所载“敕今上”及“敕武定侯郭英”两篇敕书真实性的论证,同时也应适用于这两篇敕书,它们的真实性不可怀疑。
世人常有思维定势的缺陷,对某事或某人先入为主地形成一种看法后,常常只看到有利于这种看法的现象,而忽视不利于这种看法的因素,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不利于这种看法的情形曲解为这种看法的新证据。《列子·说符》中所说的亡鈇者怀疑邻之子的故事,就是这种缺陷的惟妙惟肖的描述。笔者关于本文所述《明太祖实录》敕书是否伪造史实的论证,不知是否重蹈了亡鈇者的覆辙。希望不是。倘若自病不觉,确实重蹈了亡鈇者的覆辙,敬请诸位旁观之清者莫为袖手旁观。
本文所论敕书造假案一事,关乎对明太祖逝世前夕燕王朱棣政治地位及其与朝廷关系状况之了解,亦关乎对靖难之役发生背景及其当事双方责任之评估,事非小可,敬请诸位方家给予特别注意。
收稿日期:2010-12-03
注释:
①卷2元年七月甲申条、卷7三年三月辛巳条等即将“庄德”记为“庄得”。明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