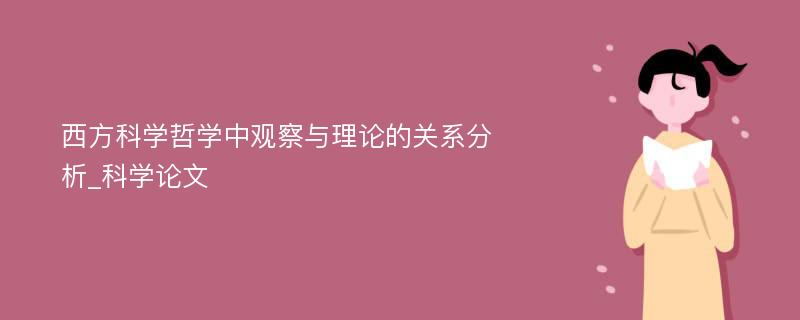
西方科学哲学中观察与理论关系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大致说来,这个问题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理论的基础是不是观察的问题;观察/理论“二分法”的问题;观察证据在理论检验中的合理性问题。本文的目的主要的不是在于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在于通过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理清该问题的逻辑展开,以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一
科学史表明,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应归功于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的应用。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功绩之一,便是倡导观察和实验,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空洞、烦琐的形而上学思辩。正如达·芬奇所指出的:“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1) 弗·培根作为“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哲学上系统地发挥了这种思想,提出了“科学始于观察”的归纳主义科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者借助于逻辑分析方法,继承和发展了弗·培根以来的经验论传统。他们试图通过揭示科学理论和感觉经验之间的逻辑关系实现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将科学概念定义或还原为感觉经验的概念;将科学理论还原为基本的观察命题。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坚定地相信:科学理论最终逻辑地建立于观察的基础之上。
波普尔首先对“科学始于观察”的传统归纳主义发起猛烈进攻。他认为:“追溯一切知识的终极观察源泉的纲领在逻辑上是不可能贯彻到底的,它导致无穷倒退。”(2) 他明确指出:观察必须带着一定的问题,带着预期的设想,没有问题就无法观察。因此,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始于观察。他认为只要坚持“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始于观察”就可以排除无穷倒退的危险,因为“如果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我们最后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3)
一般认为,波普尔的这个批判对于归纳主义来说是致命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关于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理论的基础问题,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一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涉及理论的起源问题;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涉及获得理论的方法问题;三是从逻辑学的角度,涉及理论的逻辑基础问题。这三者虽是相互联系的,但严格说来,却不是同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注意到,波普尔对归纳主义所批判的与归纳主义者自己所认为的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因为他的批判是从发生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但归纳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的真正含义却是在逻辑学的意义上,即“科学在逻辑上始于观察”,或者更准确一点说:“科学逻辑地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之上。”弗·培根的科学金字塔,实际上就是按逻辑建筑的,虽然他自己认为这也是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而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知识的基础问题,则更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4)
在发生学上,是理论在先还是观察在先的问题,就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只能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决:人类的科学是随人类本身的进化而进化的。否则都将导致无穷倒退。波普尔认为他的“科学始于问题”的模式排除了无穷倒退的困境,但事实上并没有排除,因为人类最原始的祖先是否也有天生的期望是很让人怀疑的(一般动物显然没有与人一样的天生期望,否则它们也都会有科学了)。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有着比较复杂的情况,似乎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模式。对于一个从事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的科学家来说,他的研究既可以从观察、实验开始,也可以从理论上的问题开始。这两种模式在科学史上都可以找到同样多的例证。
至于在逻辑上,科学史和实际的科学活动都告诉我们:科学的观察基础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归纳主义科学观有其坚实的自然科学上的实践基础。任何科学领域中的任何一位科学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归纳主义的科学观,正如玻恩所说的:“科学仅仅承认能够用观察和实验加以证实的依赖关系。”(5)
因此,虽然在发生学和科学研究方法论上,波普尔的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他对归纳主义的批判与归纳主义原来的问题是不大相干的。事实上,波普尔实在不应该对“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观察基础或它的归纳方法”作出这样的公开声明:“这个观点是我永远无法接受的,”(6)因为他自己所倡导的证伪主义,与证实主义一样, 在逻辑上同样需要观察作为基础。没有这个观察基础,证伪主义纲领也是根本无法贯彻的。因此,他又深刻地认识到:“用观察反驳理论的可能性乃是一切经验检验的基础,”(7)由此看来, 波普尔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理论的来源问题和基础问题并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
二
如果理论的观察基础在科学上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为了保证观察事实作为理论的基础的可靠性,在哲学上,就必然需要探讨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观察与理论是否可以有严格的区分?有没有独立于理论的所谓“中性观察”?
逻辑实证主义既然把观察看作是科学理论的可靠的逻辑基础,很自然地就相信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可以作出严格的区分。卡尔纳普在《理论概念的方法论性质》中最先把科学语言划分为所谓的“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然后,借助于所谓的“对应规则”,就可以将“理论语言”还原为“观察语言”。这样,在卡尔纳普看来,科学理论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布雷恩韦特,艾耶尔和内格尔等逻辑实证主义者都持有与卡尔纳普相似的观点(8)。
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观察/理论的绝对的“二分法”的致命打击来自于历史主义者汉森。汉森在其《发现的模式》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9)他认为, 科学观察不单纯是视觉意义上的看。对于同一对象,不同的观察者往往作出不同的观察,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并不是由于视觉图象本身的不同,而是由于观察者对看到的东西进行了不同的组织。这种组织的方式是受着经验和理论的影响的,也就是说,观察者看到的东西,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视网膜上的映象,而且也依赖于他原来的经验和知识。其次,观察之所以渗透理论还在于整个观察过程都要运用语言,图象进入大脑,立刻就与相应的语言符号联系起来,原来的知识是以语言的形式保存在大脑中的,当对视觉图象进行组织时,它就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观察结果的陈述以及交流也都要用语言形式表达。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一提出来,就很快为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人所接受,并借此展开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面批判。
库恩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对大量科学史料的分析,积极支持和阐发了“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他认为不存在什么“中性观察”,科学观察总是受到世界观、理论、经验、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社会环境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因范式的改变会引起视觉转换。
费耶阿本德的观点甚至更为偏激。他认为,仅仅指出观察渗透理论还是很不够的,观察与理论之间根本就无法加以区分,它们总是相互影响的,观察不仅渗透了理论,而且充满了理论。观察结果也不是只由简单的观察事实所组成的,它是按照某种理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因此观察的结果必然被理论所“污染”,不仅受到观察者所接受的理论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污染,也受到他本人的认识论偏见的污染。
由于历史主义者的这些分析和批判,现在,在科学哲学界再也没有人能够接受逻辑主义的观察/理论的绝对的“二分法”了,甚至连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自己后来也不再坚持这种绝对主义的观点。确实,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的科学活动都无可怀疑地表明了:所谓的“中性观察”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观察不仅不自觉地渗透了理论,而且,科学的观察正是要求自觉地受到理论的指导:科学观察不仅要求事先带着一定的理论上的目的,而且要求借助于一定的科学仪器和设备,而观察者也必须受到必要的科学教育和训练。很难想象:一个科学上的门外汉能够作出卓有成效的科学观察。因此,那种摆脱了理论的观察(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至少不是实际的科学活动中的观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逻辑主义的静态的逻辑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科学是经过逻辑重建后的科学,而不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科学,而这种经过逻辑重建后的科学与实际科学是有相当距离的。历史主义学派正是看到了逻辑主义所忽视了的主要因素而取而代之的。
不过,我们又要认识到,在现实中,任何一种分类法都是相对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分类法。因此,虽然在观察与理论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线,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两者之间作出相对的区分,这种相对的“二分法”不仅不是无意义的,而且对于实际的科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科学存在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科学之成为科学,就在于它的实证性。否定科学的实证性就违背了基本的科学精神。任何一种科学哲学都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背离这一点的科学哲学在基本方向上是与科学的实际状况背道而驰的,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可取的科学哲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逻辑主义是走在正道上的,虽然跌了一个跟头,而历史主义却走上了歧途。
现在,一般地说,人们并不怀疑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可以作出相对的区分。但是,许多人却认为,要作出这种相对区分,就必须相对地排除观察中的理论负荷,而这是能够做到的,只要将理论分为背景理论和待检理论就行了。因为虽然背景理论无论如何都无法从观察中排除出去,但待检理论却是可以排除的。
事实上,这还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在实际的科学观察中,无论是背景理论还是待检理论,实际上都不可能从观察中排除出去。考察科学史上的观察实验,我们就可以发现:按照观察是先于理论的,还是后于理论的,我们可以把观察分为先行观察和后检观察两类。先行观察是在新理论发明以前就已经作出的,或者虽然新理论已经发明了,但这个观察是在不知道新理论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当然没有受到新理论的污染。而后检观察则恰恰是依据新理论设计的,自觉地受到新理论的引导,而且观察者本身必须熟悉并理解了这个新理论,不管是接受还是反对,他的头脑都已经受到新理论的“污染”了。出乎哲学家的意料之外,科学家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观察恰恰是为了检验新理论。因此,任何企图排除观察中的“理论负荷”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实际上,“观察渗透理论”这个结果并不直接影响观察/理论的相对的“二分法”(当然使绝对的“二分法”归于破产),而仅仅直接导致对观察证据在理论检验中的逻辑合理性的怀疑。历史主义者之所以竭力反对这种“二分法”,只是因为这是他们否定观察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前提。另一方面,“观察渗透理论”这个命题本身就要以观察/理论的相对的“二分法”为基础,如果观察与理论根本就不可分,两者是混然一体,那么谈论“观察渗透理论”不就失去了意义吗?因此,要在观察与理论之间作出相对的区分并不以排除观察中的“理论负荷”为其前提条件。
三
既然不存在独立于理论的“中性观察”,那么,“观察事实作为理论的裁判官是否合法”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既然相信观察/理论的绝对的“二分法”,这个问题在他们那里当然是不存在的。但他们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即使在逻辑上,他们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归纳法可以在观察事实与理论之间架起一座逻辑的桥梁,而没有看到归纳法所作出的结论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前提的范围。因此归纳法并不是一条完美无缺的逻辑链条,在从前提到结论的这条逻辑链条的断裂处,归纳法作了一个逻辑学本身无法说明的非逻辑的跳跃。这一点正是波普尔反归纳主义的现实基础。因此,当我们用观察事实去检验科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完全逻辑的。
后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利用概率论和现代数理逻辑的成果,建立起了概率的归纳逻辑,从而将绝对的证实主义弱化为具有一定概率的确认主义。但是,波普尔的工作表明:高概率根本不是科学的目标,因为逻辑概率是与理论的经验内容成反比的。而且,从数学的观点来看,过去的观察事实总是有限的,而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数与无限数之比总是为零,因此,任何理论的逻辑概率只能是零。由于波普尔的这些反驳以及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例如从未有人能够真正计算出一个理论的逻辑概率),因此,概率的归纳逻辑也远非是一个成功的理论。
波普尔虽然接受“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但是他还是相信:虽然理论不能被观察事实证实,却可以被证伪,当然,从逻辑上讲,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证伪是演绎逻辑的一种形式。因此,在波普尔看来,观察事实作为理论的裁判官的合法性也是无可怀疑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波普尔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没有越出逻辑主义的雷池,难怪与逻辑实证主义一样地受到历史主义学派的激烈批判。
在历史主义者看来,观察事实作为理论的裁判官的合法性是很成问题的,费耶阿本德甚至根本否定观察事实可以作为理论的裁判官。他指出,既然观察报告或者含有理论假设,或者由于其被使用的方式而预设了这些假设。因此,根据这样的事实陈述去证实或反驳我们的理论,就是根据隐含的未经检验的假设去检验这个理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他甚至认为,我们要把试图用观察来反驳这个理论的论证倒转过来,用这个理论去发现那个引起矛盾的隐藏在观察报告中的自然解释,然后用新的自然解释去代替这个不合适的解释。
虽然历史主义者们认识到科学的发展决不可能严格地局限在理性规律或逻辑规律所预定的轨道之内,是非常中肯的,而其中的许多论述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个极端对于实际科学是更加有害的:不恰当地强调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完全否定观察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新历史主义学派都力图缩小和弱化历史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在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虽然都接受老历史主义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但仍然坚持观察的相对确定性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历史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夏佩尔以太阳中微子实验为例,一方面强调了背景知识在科学观察中的重要作用,另方面又批判了由此导致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他指出,哲学通常使用的“观察”术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知觉方面,二是认识方面,而在科学中这两个方面最后被分开了。因为科学毕竟关心的是作为证据的观察作用,而人的感知则并不完全可靠。因此,科学观察,尤其是现代科学的观察,越来越依赖于背景知识的作用,而削弱“观察”的知觉方面,以保持观察的科学性。他认为:说一切背景信息“不确定”,在于强调我们的全部信念是“可怀疑的”,但是仅仅是怀疑的可能性,并不构成不能依赖这些信念的理由。事实上,被科学用作背景信息的,都是它可利用的最可靠的信息,迄今为止,这种信息已被证明在过去是非常成功的,关于它不存在任何具体的令人信服的怀疑理由(10)。
不仅背景知识在科学观察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我看来,接受检验的新理论在检验该理论的观察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在上面已经将观察分为先行观察和后检观察,这种分类法使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科学领域,先行观察证据不足以使科学家们完全接受新理论,而只有后检观察证据才能使新理论最终在科学上站稳脚跟。确实,就理论的检验而言,新理论对先行观察只不过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因为这个新理论的发明多少是为了解释或适应这个观察事实的,而新理论在后检观察中则扮演着真正的诸葛亮的角色。因此,这种预言式的后检观察证据要比仅仅是解释性的先行观察证据使我们给理论以更高的置信度,从而在科学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可以在科学史上找到许多这样的例证而无一例外,使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最后站稳脚跟的不是它能够解释苹果落地的现象,而是海王星的发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不仅仅是因为它解释了水星近日点的过剩进动,而是因为成功地预言了光在引力场中的偏转现象和引力红移现象;发现中子而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不是约里奥——居里,而是查德威克,虽然他们两人都作过同样的观察,而且前者要比后者早。正是由于受到卢瑟福的新理论的“污染”,使查德威克作出了不同的观察结论,从而证实了卢瑟福的中子理论。
但是,在哲学领域,哲学家的想法却与科学家的根本不同。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不对受到理论污染的后检观察证据在检验该理论中的合理性表示怀疑的。当然,从纯逻辑的角度而言,这种怀疑确实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在论证中包含有要论证的成份在逻辑上是绝对不允许的。由此看来,在埋头苦干的科学家与高谈阔论的哲学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导致这种对立的原因在于:当哲学家们讨论“观察事实作为理论的裁判官是否合法”的问题时,他们是从纯逻辑的角度出发的(尽管历史主义表面上是反逻辑主义的),他们所谓“合法性”实指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实际状况却是:我们用观察事实去检验理论的行为本来就不是一种纯逻辑或纯理性的行为。因此,在历史主义对逻辑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自相矛盾,他们在批判逻辑主义的时候,恰恰应用了严格的逻辑标准。正是这种严格的逻辑标准,导致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用受到理论污染的观察证据去检验理论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所以观察证据根本就不能用来检验理论。而逻辑主义的错误只在于:相信这种检验(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还是确认)都有其充足的逻辑根据,而没有看到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非逻辑的因素。
通过以上对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无论如何,我们人类并不是完全逻辑的,正象牛顿物理学把机械运动理想化了一样,逻辑学也把人的思维运动理想化了。而任何理想化都只是对现实的近似描述。因此,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象牛顿物理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但是,历史主义者完全抛弃掉逻辑主义,企图在科学哲学上另辟蹊径,由于他们的非理性主义与基本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历史主义在反方向上甚至比逻辑主义更远离了真理。虽然新历史主义比老历史主义要理性得多,但仍然停留在历史主义的框架内。我认为,正象现代物理学不能完全抛弃牛顿物理学一样,未来的科学哲学也必须在继承逻辑主义的基础上,同时又吸收历史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而发展。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坚持科学的理性主义,同时又要充分地认识到科学中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科学哲学称为历史的逻辑主义。
注释:
(1)转引自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 第165 —166页。
(2)(3)(6)(7)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4)(8)参见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6页。
(5)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4年,第11页。
(9)汉森:《发现的模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
(10)夏佩尔:《科学和哲学中的观察概念》, 《哲学译丛》,198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