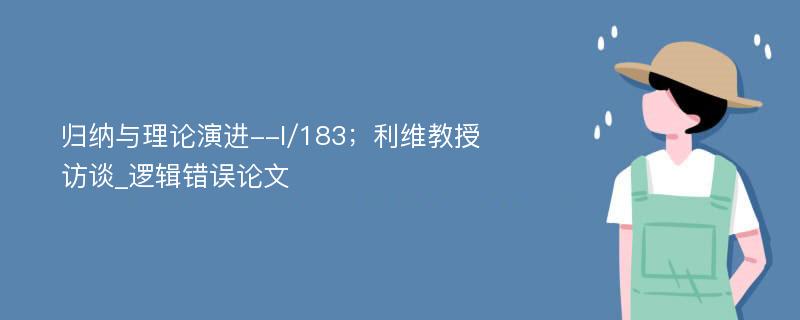
归纳与理论进化——I#183;莱维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纳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莱维(I.Levi)教授是访问学者鞠实儿在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访问时的合作导师。莱维曾任哥大哲学系主任,他集毕生精力研究归纳逻辑学及其认知基础,是归纳逻辑的认知效用学派和信念修正理论的创始人,被西方学术界誉为逻辑学和认识论领域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访问期间,鞠实儿就归纳逻辑及其哲学基础等方面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专题采访,现将采访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鞠:当代的归纳逻辑在决策论乃至智能计算机等新兴科学研究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但自波普以来,科学哲学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中具有明确的反归纳主义倾向。希望您能够就反归纳主义、归纳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发展动态等问题发表看法。首先,请您谈谈对波普证伪主义的看法。
莱维:我认为,波普的反归纳主义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着可精确描述的证伪程序,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在波普看来,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东西,没有东西可被视为可靠的。波普通常以一种与怀疑主义更相似的方式说话。他主张我们能够证伪受到质疑的信念。全称命题不能证实,但能证伪,信念正是这样的全称命题,甚至科学的数据本身是由约定而不是由观察提供的。这些数据取自约定,因此,我们实际上所享有的是这些报告与理论之间在逻辑学意义上的不相容。然而,逻辑并不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任何东西,因此,波普最终似乎陷入了某种形式的怀疑论。我的观点是:我们确实不仅具有信念,同时具有确定的饱和信念(full belief)。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免于信念变化和修正。在相关的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中,我们赞成的方案是这样的:当我们试图对科学和日常生活作出种种看法的条件作出说明时,我们有理由通过确信或放弃一个假说来改变我们的看法,而确信或怀疑某一假说的条件正是我所要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能够对科学探究作出一个合理的说明。该说明基于信念辩护和信念变化的条件,这些信念中既包括当前确定的信念,同时也包括概率判断乃至价值判断。上述观点起源于J.皮尔士和J.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它们甚至可被拓广到政治学领域。
鞠:在您看来波普证伪主义的主要困难是:(1)没有能够说明理论究竟是如何变化的;(2)将一个科学方法论问题还原为演绎逻辑的问题。困难(2)是致命的。根据波普的理论变化模型,理论的变化涉及到理论的选择。理论具有一般性,它断定了迄今为止尚未经验到的事件。除非选择是任意的,否则它必遵循某种规则。如果你根据这种规则选择了某一理论,那么你就根据这种规则对迄今为止尚未经验到的事件作出某种断定,从而超越了当前经验。这显然是一种归纳推理。您是否能从选择规则出发进一步说明困难(1)?
莱维:的确,就波普而言,理论或假说的变化究竟是何种类型的变化,这一问题是不清楚的。正如我先前所说,他将整个问题转变为一个关于一致性的逻辑问题。费耶阿本德同样不承认归纳法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他将理论或假说的变化视为研究者的概念框架的变化。作为一个归纳主义者,我要申辩的是:人们经常要完成的工作是以非演绎的方式将新的信息加入到已接受的信念中去。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我要强调:对这种信念变化的辩护是与我们从事的特殊研究的目标相联系的。这似乎类似于波普的观点,其实它们完全不同。粗略地说,存在着两类我们感兴趣的价值,它们促使我们进行信念修正。其一,如同C.皮耳士所说,减轻我们的怀疑,用更技术化的语言说,也就是获取新的信息。其二,关心错误的风险。正因为我们关心避免错误,才引发真理问题。然而,当我们试图避免错误时,相对于在这一时刻被断定为确定地真和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我们估计错误的风险。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一般性理论,它解释归纳如何以波普所否认的方式起作用。在这方面,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拉卡托斯似乎都忽略了担忧错误风险的这一事实。他们否认如下观点:为了决定我们将采纳哪一个猜想,并将它视为一个确定的信念,我们能够采取一个中性的立场去判断当前所考虑的猜想的错误风险。因此,前两者都不考虑错误风险问题;而拉卡托斯与他们有所不同。我想我与他之间至少会有一个相近之处。当我说人们关心错误风险的目的是为了错误风险最小化,他们必须有理由冒风险,这涉及到你希望寻求的信息类型。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概念在理解上述信念类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研究纲领并不完全控制理论变化过程,你必须同时关注错误风险问题。事实上,我们心目中的研究纲领并不是一个信念集合,而是一组价值目标,它要求我们寻找某类信息。因而,如何改变研究纲领的问题也就成为如何改变我们的价值的问题,后者从属于一般的价值问题。我的观点是:尽管拉卡托斯及其支持者在这一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它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和未被触动的领域。我认为,对信息的需求和错误风险两者相互作用的确定的见解解决了如下问题:人们何时可能对在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结论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如何说明实验中控制的作用,数据的种类和解释力的关系等问题拉卡托斯的观点与上述想法相接近。
鞠:按照通常所采用的定义,归纳推理(或论证)是放大性推理。该定义并未规定控制归纳推理的具体规则。您在决策论框架中描述归纳推理,给出了一种基于决策的归纳推理方法。您的方法是简单而明确的:一个背景知识集B,一个穷竭的竞争假设H,在H上定义若干个依赖于B的概率分布Q和一个价值函数V;当新的证据E出现时,根据Bayes公式和Q可得到H上的条件概率分布Q[,E];于是,从期望效用公式出发,便可从H中选出具有最大期望效用值的成员;最后,依据该成员与B的逻辑关系,B被修正。由此,在归纳的基础上理论变化得到说明。虽然我本人对您的方法略有保留,但是我认为您确实回答了一个波普、拉卡托斯、库恩以及基于非单调推理的信念修正方法的爱好者所难以回答的问题。那就是:如果通过某一过程得到改变了的理论面临着进一步改变的可能,那么凭什么理由将当前的理论作为真的来处理问题,或作为推理的前提?因此,在考虑理论变化时必须同时考虑风险!另一方面,从B到B的修订本可以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但是,波普称之为归纳主义者的卡尔纳普及其学派似乎不考虑这类问题。作为归纳主义者,您的理论与卡尔纳普的理论的区别何在?
莱维:当然有区别。存在着另一个不同于波普的反归纳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不能确信任何事情,人们所作的不过是赋予假说某个概率。卡尔纳普和R·杰弗里便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作为波普反归纳主义的反对者,我所关注的不是证伪的概率,而是在无人确信任何事件的条件下概率的变化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将那些自称在归纳领域工作的概率主义者列为反归纳主义者的原由。我想说:当今大多数科学哲学研究者在基本立场上不同于我所说的反归纳主义者。波普和卡尔纳普这一类哲学家之所以归属于反归纳主义,更深层的理由是:正像那些为了避免错误风险而将自己局限在某种逻辑保护伞下的人那样,他们对某些事情采取一种纯客观的立场。的确,波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作出了与众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并不理解对什么是错误风险。事实上,不但对于日常生活,而且对于科学研究,错误风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起重要作用的推理就是放大性推理,这种推理的结论超越了证据的逻辑蕴涵。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唯一开发利用的就是根据价值重要性对潜在结论作出评价。当波普和拉卡托斯从事这种评介时,他们所做的只是C·皮耳士所称的溯因、假设或猜测,并未占有任何方法去选取某个猜测以便作为背景证据的一部分用于后继研究。我本人对此一直持有异议,并致力于用一种简洁的归纳理论取代它们。该理论不仅给出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允许人们由于不可预见的差异而运用归纳增加新信息;而且,它还说明人们如何放弃某些观点,尽管它们在此之前曾被认为是最好的。放弃某些观点而不是增加信息构成归纳的逆(an inverse of induction),对它的研究是我工作的另一部分。但是,归纳及其逆两者都是重要的,它们的结合将对科学方法论作出一个普遍的说明。当然,如果我们考虑特殊学科的具体方法,特殊学科的方法论则常常基于该学科在某一时刻所预设的基础理论。不过,如同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那样,我所关心的是最一般的研究形态。但是,坦率地说,我不欣赏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社会学化及历史学化倾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费耶阿本德倾向于成为一个伽利略主义者时,在此范围内他具有许多非历史化观点。在他看来,思考这些问题时他的转变并不是局部的。或许,他所强调的同时也是人们所未强调的最重要的思想,即我们应当确信那些就其本身而言不应当确信的东西。我们总是处于怀疑和确信构成的胶着状态,这也许可称之为辩证法。在此谨借用C·皮尔士的看法:在怀疑和确信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
鞠:我想生活本身对归纳的合理性提供了另一种说明。事实上,在一个对于未来生活充满着机会和不确定性的社会里,选择是必须的。过去和现在是不可选择的。因此,作出一种选择意味着固定一种对未来的看法。但是,未来是尚未经验到的。从彻底的经验主义者的立场看,我们确信了那些就其本身而言不应当确信的东西。这无疑是一个矛盾。但是,这就是生活,归纳法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归纳不仅存在,而且对于人类生活是必不可少的。您是否能简略地介绍您本人在归纳逻辑方面的主要贡献和当前的工作。
莱维:首先,我提出了第一个认知效用的一般模型,该模型说明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归纳推理是如何进行的。在"Gambling with Truth"一书中,我提出了该模型的原型。在"Information and Inference"一文中,该原型得到了细致的改进。其次,在"Enterprise of Knowledge"一书中,我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建立了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般理论;该书技术方面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不确定概率基础上的效用判断和概率判断作出了说明。其三,我希望能够以一种方式描述各种基于不确定概率的理论之间的差别。根据这种描述,我给出了一个能容纳争论的结构;在此结构中,我本人的理论只是争论的一方。这一结构不仅对科学哲学有意义,对社会政治选择理论、决策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同样有意义。事实上,在"Hard Choices"一书中它被推广至个体决策和社会选择理论。最后,我在"Gambling with Truth"一书以及后继研究中,依据我的归纳理论对沙克尔的潜在惊奇理论作出了解释。在此之前,无论是沙克尔本人还是其他我能了解的学者都未提出过这样的解释。"Enterprise of Knowledge"一书中以非形式的方式给出的关于修正、扩充、收缩和替代的理论,已引起了日益增长的兴趣。在我的新著中,我讨论了同一主题的不同应用领域。
鞠:根据欧美逻辑学界的正统观念:逻辑学分为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就归纳逻辑学在当今的发展而言,它可大致分为:基于Pascalian概率的归纳逻辑和基于非Pascaliang的归纳逻辑。沙克尔测度属于后者。归纳推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概率判断和效用判断的形成,更体现在信念修正过程中。因此,归纳逻辑学家在构造归纳逻辑系统时常常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如果追求系统的合理性,那么系统将变得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容纳在一个简洁而优美的形式系统中;如果或多或少地放弃合理性要求,那么或许会有一个简洁而优美的形式系统,不过该系统可能是不合理的。请问您是如何处理上述两难问题?
莱维:当我使用诸如积分等数学工具时,我关注的只是数学的应用。在此,我特别强调应用的重要性。不论从事形式逻辑和演绎逻辑研究,还是用数学研究哲学问题,许多人如此沉醉于形式结构,以至于忽略了形式结构的应用对象和常识的作用。相对于形式的优美,我宁愿选择尽可能精确地描述应用对象。的确,归纳既不是演绎也不是数学。但是,如果你打算运用概率论研究归纳,你应当考虑和尊重概率论的结构。我所采纳的一个更为严肃的观点是:归纳是决策论的基础,形式系统的作用是对决策者的态度而不是对语言学的或纯形式的结构施加约束。因此,在我看来,逻辑自身应被视为规范学科,它关注的是融贯一致的思考所应采取的方式。规范问题是根本问题。
鞠:您曾对沙克尔测度作过重要的研究工作。我认为,沙克尔工作的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事先列举某一行动的所有可能后果是不可能的,并据此对经典概率论在处理决策问题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进而建立了一种非Pascalian概率,即您所说的沙克尔测度。而我则在沙克尔的启发下,考虑定义在不完备可能世界集合即开放世界上的命题的逻辑结构。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对知识的不完备性或无知的思考。在我看来,没有一种合理的逻辑作为元方法,很难解决不完备样本空间上的不确定性度量问题;或许,这种逻辑本身也会有它的独特的价值。我很想知道您的看法。
莱维:我必须强调:无知和怀疑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我倾向于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开放性与无知的表达问题相联系。这使我们进入了一个重要而充满争论的领域。从某种角度看,就不同的意见争论不休并不意味着研究的深入展开。我们可以将不同点从形式上暂时悬置起来,在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合理结论。在我看来,上述想法同样适用于科学研究。
最后,如何正确处理开放或怀疑与确信的关系,什么是人们应该具有的信念,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改变信念,这些也就是我本人在哲学领域中不变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