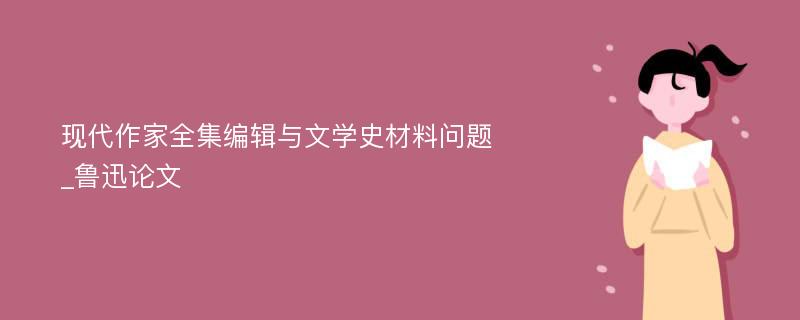
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与文学史料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全集论文,作家论文,编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代作家作品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和依据。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重新审读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包括作家的全部文学创作。所以,搜集和编辑作家全集就是整个研究工作中的一项非常重要和很有价值的工作。
新时期以来,我们出版了不少单个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前者如《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徐志摩全集》、《艾青全集》、《沈从文全集》、《冯至全集》、《李何林全集》等等;后者如《老舍文集》、《巴金文集》、《王统照文集》、《郁达夫文集》、《蒋光慈文集》等等。在已出版的“全集”中,大多基本上是“全”的,“不全”的是少数。“文集”中不全者居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作家的亲属为亲人讳。据作家“全集”或“文集”的编辑者反映:作家亲属主动协助编辑者尽可能“全”地辑录作家所有文稿者有之,但只占少数。多数是不同意收录作家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所写的批判他人的文字。这里的关键是对“为贤者讳”的态度问题。首先,某人是否为“贤者”,并不由编辑者或其亲属确定,而是由所有史料来确定。其次,更重要的是,有些所谓的“为贤者讳”只不过是“掩耳盗铃”。须知,任何一位认真的研究者必然尽可能全面和详尽地搜集、阅读有关作家的资料,既是公开发表过的资料,就难以逃过研究者的眼光。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剩下的只是发现时间的迟早问题。所以,“为贤者讳”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对于这一既不利人又利己的古已有之的观念,实有彻底抛弃的必要。因为这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中的主要阻力之一。应当说明是,我这里所说的并不包括未公开发表而又牵扯到作家个人隐私的文字。关于个人隐私问题,国家的法律已有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违反。有些关系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如某人系我派出负有特殊任务者,则应作处理后付印(处理方法,最好是空出若干字,处理后无人能猜出原文)。
第二种原因是资料搜集方面的困难造成的,或是由于战乱,或是由于自然灾害,或是由于报刊保存方面的问题,也有作家笔名过多而造成的搜寻困难,等等。总之,这种在作家作品搜求方面的困难有时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委托吴宏聪先生、胡从经先生和我主编《徐志摩全集补编》,我们连同助手近十人花费几年的功夫,搜集到徐志摩佚诗、佚文四卷约八十万言。且不说未查到的佚文,有的如《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已辑录到下半篇,也知道上半篇发表的报刊及日期,就是找不到这一天的报纸。唯有阙如。
“全集”或“文集”的编法多种多样,从中可以体现出编辑者的才学和智慧。我以为,作家“全集”的编辑者至少应当注意两点:(一)名实相符,尽可能地收进作家的全部著作。假如《鲁迅全集》不收鲁迅的译文,就不是“鲁迅全集”。鲁迅的译文很多,对研究鲁迅,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少了它,就缺了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单个作家作品,如果要编“全”,也很难。《鲁迅全集》仅1981年版,就花了大量人力、财力,投入人力(脱产、全力投入约3—5年)约百人,经费数百万,结果仍有遗漏。我想,编辑者顾名思义,只有“编”的自由,并无“取”“舍”和删改的权力。我们的法律对此似无明确规定,其实是应该予以界定的。(二)为读者着想。一切服从于便于读者查阅。例如:“集外文章”,最好集中在一卷或两卷里,免得读者查过许多卷之后才能查到。有些不能一下就判断的(如学术著作与“随笔”、“散文”、“杂论”,有些难以区分),就更难断定。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全集”这儿编得不好,那儿编得不妙,你可否能提出一个最佳方案呢?必须指出:由于各个作家的情况不同,已出版集子的状况各异,很难提出一个能适合所有作家的方案来。大略而言,“全集”有两种编法;对作家自己编成集子较多的作家,如鲁迅,生前将自己的著作、书信、翻译、辑录、校勘等数十种专集出版;也有别人(如杨霁云)为之编辑的《集外集》面世。无论为新编《鲁迅全集》质量计,抑或为新编者省力计,为方便读者计,都以原专著基础上编“全集”为好。如今相当多的“全集”都采取这种编法。为便于读者查找,集外文字宜于集中编在一起。另外一种编法是,重新以创作或发表的年、月、日为序排列。这样编辑的难处很多,因为作家并未说明,这篇作品写于何年、何月、何日,有的既无写作的年、月、日,甚至也未提示最初刊发作品的报刊和卷数、期数,有些刊物更是很难查到,这就更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难度。有些难以确定写作年份的作品,只有附在年度之后。写作月、日仿此或干脆不署月、日。
现代作家全集编辑得好坏,除了编辑思想、辑佚的工夫外,对作品校勘和考订是否认真负责,也是关系到全集质量高低的重要方面。这里面牵涉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和文献学的功底,其中,也有编辑者粗心所造成的问题,比如,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2月30日初版的《徐志摩诗文补遗》“第三辑·文集”第111页就有多处错误:
(1)“……在这个大圈子里面。在事实上光的速度总算极快,但是光只能在圈子内行动:”原文则是这样的:“……在这个大圈子里面。圈子外面这句话又是没有意义了。假使在这个大圈子里,有一个物件永远直线进行,结果还是在圈子里面。在事实上光的速度总算极快,但是光只能在圈子内行动:”
这一处就漏掉了四十五个字。这一页中掉字或错字的地方还有:
(2)第四行第九字与第十字之间,漏掉一个“圈”字。
(3)第五行英文最末一字母原为" r" ,却被改为" e" 。
(4)第八行,“有一定的容积又没有缘边的呢?”
应为“有一定的容积又没有边际的呢?”
(5)第十二行倒数第五字“是一个走量。”
应为“是一个定量。”
(6)最末一行原为“有了面扩”
改为“有了面积”,改得对,但未注明。
(7)同上段,“原来只有长度”。
改为“元来只有长度”。
古“原”、“元”通用,可不改。改了也应注明。
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有类似错误,而且错误何止百处。这样的书籍,何人敢用?
对于古籍或虽系白话文但距今时间较久者,编辑者一要具备必要的文字工夫,二要慎重。闻一多先生的某些诗文,就必须如此。例如,群言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了一本《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在该书的第一页、第二页有这样的文字:
(一)因念他(它)们实能代表当时的一番精力
(二)保存起来,到(倒)一则可以供摩挲
(三)《夜坐,风雨雷电交至,凛(懔)然赋此》
(四)《从崑(昆)山午发》
整理者的意思,括弧内的字是正确的,括弧前一字应改为括弧内的字。其实,第一条中的“他”、“它”在“五四”时期无区别,不像今天,“他”是指“人”,“它”是指事、物。第二条中的“到”“倒”,整理者理解错了,原件无误。第三条,查《康熙字典》“凛”:《说文》:寒也。《玉篇》:凛寒也。《韵会》:凄清也。《辞海》:“凛”,冷,严冷可畏貌。通“懔”,懔栗:敬畏。凛冽,刺骨的寒冷。凛秋:寒冷的秋天。凛然:严厉貌:形容令人敬畏的神态。联系整个题名,以不动为妙。第四条是简体字与繁体字之别,更不用动它。整理者所加的注全属多余。
从史料学的角度说,“全集”对原件的错讹,负有改正的责任。当然,这种改正必须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如无确凿证据,则宁肯不动。如《鲁迅全集》中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说:
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 Pong Pong Pong" 铅字逐渐大了起来……。
" Pong" 与原诗对照,多了一个字母" g" ,音也就多了个“其”字,这错误是应该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但1981年版《鲁迅全集》和所有注释本均未查出并指出。其中,编者也有难言之隐,因为王独清的诗集《Ⅱ Dec》(《十二月十一日》)在国内似系孤本。
对于各种版本,“全集”宜将情况全盘托出。记得在《沫若文集》的编辑过程中,朱正同志同一位出版社的总编有过一次对话(大意):
朱:你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好像《女神》、《文艺论集》后来没有修改过一样。
××:这是不由我决定,我也没办法。
朱:那你出一卷,我就出版一本《汇校本》。
1983年8月、1984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和黄淳浩的《〈文艺论集〉汇校本》,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全集”所收作品,编者不能禁止作家改动,但一定要将改动情况注明。“全集”也许只出一次,也许几十年、几百年才出版一次,改动情况现在加以说明较为容易,几十年后乃至几百年后,就困难得多了。
有人说,做史料工作不算学问。我不想为史料工作者辩护。只想说两个事实:一、我的这则短文,如果无史料作基础,就无法完成;二、我撰《中国新诗史》,史料工作占时近80%,撰写著作本身仅花时间20%而已。最后,我想着重指出的是,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的发展,因为资料的缺陷,会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在现代作家的全集中,缺失和错漏以及辨别上的失误,都会对研究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