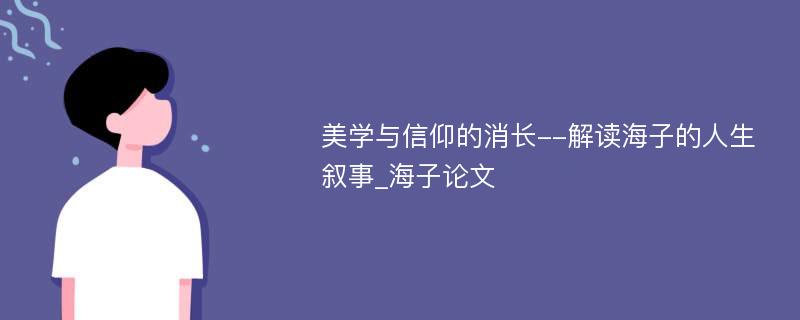
审美与信仰的消长——对海子“生命叙事”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子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论及雪莱时说,雪莱短暂的一生“即悲剧之实现”,“亦即无韵之诗”,其实这也正是所有早逝的精神天才的写照!我不认为那样的毁灭是美好的,但我认为它别具殉道色彩。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出“生命叙事”这一说法的(主要是为叙述方便)。我把那种把生命投注进去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名为“生命叙事”。1989年3月26日,中国诗人海子借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写就了一次这样的生命叙事。本文拟围绕诗人的生命叙事进行精神现象学考察。我感兴趣的问题是:诗人究竟为什么选择了诗?选择了诗在诗人生存层面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审美与信仰两种精神母质是怎样内在于诗人心灵中的?它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消长和互动关系?并且,怎样一步步牵引出创作主体与创作活动之间的悲剧性关系?
一 审美与信仰的消长及诗性劳作的内在危险
诗人究竟为什么选择诗呢?对这个问题的庸俗社会学性的回答恐怕于事无补,因为大多诗人选择诗作为自己的事业与功利意识似乎无涉,甚至在衣食住行方面对自身格外残酷。我相信,只要走进创作主体的内心,甚至某种程度上只要走进我们自己的内心,就已经能够悟得这个问题的朦胧答案:创作是主体处于精神困境中时内心的一种审美诉求和某种自我表达的愿望。这种独特的选择发轫于主体的痛苦、迷惘和压抑以及对于艺术的本能般的爱和信赖。这个诉求的过程能奇妙地减轻主体所感到的压抑,美化其迷惘,缓解其沉浸其中的痛苦。当一个事件或一种情绪——一旦我们把之诉诸艺术——使我们进入一种美化的境界,进入一种新的感知或理解的境界,我们就会通过这种诉求而感受到某种超越感。这个过程对精神天才们来说起初无疑是有着极大的魅力的。海子在1987年11月14日的日记里回忆道:“少年时代他迷恋超越和辞句,迷恋一切又打碎一切,但又总是那么透明,那么一往情深,犹如清晨带露的花朵和战士手中带露的枪支。”这里面无不透出一个浪漫少年被艺术所感动的神秘。其《半截的诗》则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艺术珍爱的某种感受,尤其是当面对自己所创造的艺术青果的时候:“你是我的/半截的诗/半截用心爱着/半截用肉体埋着/你是我的/半截的诗/不许别人更改一个字”。[1]
然而,对于诗人来说,审美诉求的进程中隐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因为精神性的掘进越往深处走,主体就会触及到越来越尖锐的生命存在本身的问题,并且要求艺术创作担当自身难以承担的形而上意义上的任务。这正是审美诉求最终的恐怖之处。
许许多多沿着这条艺术创作之路走下去的天才结局都很不幸,甚至发疯或自杀。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如果艺术之神既让诗人和艺术家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同时又能保全他们的生命该多好!——看来她也无力扼死这个艺术创造过程本身的悖论。也许,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正因为它们最强地折射出人类存在本身的悲剧性,而创作主体则由于长期背负了这悲剧性的难以估量的精神重荷而不得不过早倒毙。
这难以估量的重荷不但来自与生俱来的痛苦,更来自某种绝望,来自自我意识深度觉醒后的创作主体纯粹审美的生命立场的不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人往往具有浓重的终极关怀意识,对生命无比虔诚的他们,渴望人的完整的真实和存在的真理。随着他们的审美诉求由开始的相对中和逐渐转向激越,他们在精神性掘进中迟早要陷进与人的终极实在相关联的事物及思想的包围,进而与意义问题遭遇。也就是说,随着审美诉求的扩张,他们会越来越感到来自形而上的压迫——事物或者观念——观念有时候比经验对人的精神影响更甚,他们的天性事实上根本无法使他们与形而上的需要诀别,诚如尼采所说:“一位自由思想家即使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艺术的最高效果仍然很容易在他心灵上拨响那根久已失调、甚至已经断裂的形而上之弦。”[2](p.158)这时,精神追求永恒的要求将与感性肉身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主体将不免会为自身的局限性而感到绝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诉求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的创作与其说是一部部艺术品(当然首先也是艺术品),不如说更像是为思想和信仰效劳的一种工具——尽管抒发情志,但他们在不断行进中还是在某个时候不自觉地冷落了艺术所由产生的创造的主观性的生动感性,而去拥抱了智性——而这个“智性”则由于其对“世界诗”的暴力解构,从而使主体不期然离开了审美本身。这种离开是危险的。因为绝望情绪开始在他们心中萌发并越来越茂盛,因为艺术难以对意义问题作出最后的答复。
二 超越性创作与主体的精神困境
超越性的创作(有着终极意向的创作)活动常常会给创作主体带来巨大的精神困境,使他们的生活及其覆盖层(人的意识、精神、心理等)发生极大的变形,致使他们无意之中远离常人的生活。例如海子在1987年11月14日的日记里就曾写道:“因为全身心沉浸在诗歌创作里,任何别的创作或活动都简直被我自己认为是浪费时间”,而“对于生活是什么?生活的现象又包孕着什么意义,人类又该怎样地生活?我确实也是茫然而混沌”。即便超越性创作不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仍会有一些生活事物不停地溢出,但那溢出的也只会是一些生活的碎片,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完整生存。从事超越性创作常常迫使主体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经常会使主体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最终由于在遥远的事物里沉浸得过深过久——生命肉身俨然成了一派精神氛围——而出现精神分裂、心理透支、幻听幻视以至于最后的崩溃。“世界变成了梦,梦变成了世界”——德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谈到诗人最终的解体的这句话,对崩溃前的海子来说也算是实现了。海子在遗书里说过他出现了思维混乱、头痛、幻听、耳鸣的征兆。可以说,那样的精神生态长期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此在的全部可疑性会突然闪现出来,主体的理解认知力面对这种可疑性就如同面对最后的无法洞穿的存在之谜,他原以为生存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它面前都将彻底瓦解。这种状态对生命个体时刻都潜伏着一种危险、一种杀机。
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使诗人不可能停留于审美的表层,他有过这个阶段,但会或快或慢地被他自己跨越过去。写到了一定程度不能罢手么?不能。他心中也许蕴含着一种时代赋予的“天职”(对真理的追忆、朗显、固守或预识)。由于时代浅表文化的污染,这个“天职”本身似乎已返回世界的深处。能怀揣虔诚“在黑暗中走遍大地”,并坚持在心灵的基点说出透明、洁净的灵魂话语的人,只有在远离尘嚣的自我氛围中,才能做到。所以,主体一旦发觉自己被钉在了这个十字架上,他实际的返回就将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主体在这种精神劳作中也会感到一种别样的狂喜与满足,一种灵魂被施洗般的狂喜。可反过来说,主体在那种氛围里精神的享受越深,他返回现实时就会对具体的生活越失望。由此,主体与文本相互强化的氛围开始为他指路,并迫使他继续走下去。下面我们就通过译解海子诗歌文本的信息考量一下其心灵轨迹,看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自己命运的深渊的。
综观海子的诗作,从麦地抒情短诗,《传说》、《河流》、《但是水、水》到鸿篇巨制太阳七部书,麦地—太阳形成他辗转漂泊的精神脉索。这条飘渺宏濛的意象带在文化心理上体现为东方回归自然的“桃源”情结与西方终极关怀的宗教情结两条人类精神之轴的反向延伸与汇合。麦子是海子前期诗作的中心意象,诗人与麦子的相遇不是偶然的,这决定于诗人的乡土情结。乡土情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理特征之一,是一种幽深的历史积淀。海子出生于乡村,同乡土有着天然的多重的文化心理关联。诗人的麦地劳作似也在努力造一座自己的“桃源”。如:“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麦地》);“风吹在村庄的风上/有一阵新鲜有一阵久远”(《两座村庄》)。[1]诗人“打一支火走到船外去看山头被雨淋湿的麦地”颇有点儿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况味。在《思念前生》里,诗人甚至追思到:“也许庄子是我。”但是,诗人的麦地意象总让人感到诗人之于麦地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士”对自然物象的玩味,也并非意味着主体借此就逃遁到了田园牧歌情调里去,而是寄寓着诗人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预示了主体苦难意识的醒觉。如:“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答复》)[1]。海子由此从对土地的触摸转向对生命本质的感悟与沉思。
希腊古哲阿那克西曼德有一句也许是西方思想的最古老之箴言:“万物生于何处,也将按照必然性复归何处。”表面上看,人来自泥土,也将回归泥土,人在本质上属于自然,自然力在其生命肉身注入不可抗拒的一切,但人类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被大自然所埋葬的无意识的存在”(黑格尔语)。肉体是短暂易逝的,人类也许只有设想精神是永恒的,才会感到自己置身于万物之中时的真正尊严之所在。超越的诉求确也是古老的人类之梦,正如海子所说“智慧与血不能在泥土里混杂合冶”(《土地》第四章)[1]。海子的《土地》、《但是水、水》等著名长诗对“作为自然的人”与“精神的人”彼此撕咬的双重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表达。
《土地》可以被看作是一出关于人类及世界万物存在仪式的“叙事”。这部诗作依大自然每年十二个月份的季节轮回和万物兴衰荣枯的自然律动对应于人的生命的生死转化,及内在于生命自我的各种精神冲突,把人类命运和自然现象完全交织在一起,诗与思的双重运作直抵生命力的根基和人类生命体验的至深处,赋予了生命此在以某种永恒的意蕴。另外,《土地》的结构还暗藏着一种永恒复归的古老神话意蕴。自然、宇宙永恒重复、循环的思想本是古代智慧的核心思想之一,古老的宗教仪式中有很多都是通过模仿自然万物产生、死亡、再生的基本范式来参与存在,以求得生命的永恒。但也有一些古代智者(比如古代印度智者)则认为,对自然、宇宙的永恒复归意味着生命所遭受苦难和奴役的无限延长。他们恰恰在时间永无止境的循环和自我重复中感到了绝望,认为最后的解脱应是对自然、宇宙范式的超越。诗人似乎认同这后一种思想(尽管其超越方式是独属于“诗歌烈士”的):“土地的死亡力迫害我形成我的诗歌”,“土地对我的迫害已深入内心”(《土地》第二章)[1]。诗人于是从大地上发出形而上的太息:“黑夜从大地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黑夜的献诗》)[1]。从这样的诗里我们不难感觉出,在诗人与土地之间还寄托着终极关怀和宗教精神。
海子感性最为丰沛的早期长诗《河流》、《但是水、水》是抵达实体的伟大诗篇。在这里,诗人像一位誓将自己委身于大地的赤子,以“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黑乎乎的实体照亮”,并洞穿东方民族的心灵深处,目击了它“古老的沉积着流水和暗红色血块的心脏”,感受到了“河流的含沙量和冲击力”(《〈河流原序》)[1],并最终凸显出人类古老的终极关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我们是谁?”(《〈河流〉代后记》)[1]这种根本的觉醒是决定性的,使他由此开始转向宗教(一种内在宗教)。在长诗《传说》中,诗人只身探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根部,以自我之灯照亮东方人类古老的生存,仿佛一个灵魂哑默的民族突然攫住他,让他为其生存作证,那叙述不尽的一切自诗人的良心中滔滔涌出。然而,诗人的道说最终还是从根部点明了东方文化空洞的本质:“对着这块千百年来始终沉默的天空,我们不回答,只生活。”诗人接着说道:“亲人啊,你们是怎么过来的,甚至甘愿陪着你们一起陷入深深的沉默。但现在我不能。为你们的生存作证,是他的义务,是诗的良心。时光与日子各各不同,而诗则提供一个瞬间,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民间主题》)[1]。于是诗人决计要从实用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出:“用我们横陈于地的骸骨在沙滩上写下:青春。/然后背起衰老的父亲。”可是,“时日漫长,方向中断”(《秋》),诗人背起“衰老的父亲”将走向何方?走出传统文化,走离“桃源”,又没有一座更好的精神栖息地接纳诗人,诗人的精神世界一片荒凉:“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1]。
东方的“桃源”远去了,在诗人的心灵视野里也许只剩下西式的天堂(海子曾从印度史诗中汲取了很多精神资源,构成了他“一次性诗歌行动”的一个因素,但他最终没有安歇于印度思想(注:典型的印度思想都是从一个原初论点——苦难——出发,通过修行解救人脱离苦海。是出世的。它不否认苦难作为一种宇宙事实而存在,但它要通过人类自我精神的绝对自由超越之,以挣脱自我只是被虚幻地拖入其中的宇宙范式。于是,苦难虽然继续存在,但对人却失去了其意义,这种对苦难的超越并非经验的(包括自杀),因为经验的解决本身就是某种因果关系作用于人而引起的结果,印度的立场是要超越所有的人格关联,让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在自我意识里化为空无。参阅室利·阿罗频多:《神圣人生论》,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而西式天堂也已长久破败失修。在以基督之爱为精神支柱的西方世界,“上帝之死”使现代人的灵魂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精神状态。不堪忍受价值的普遍虚无,诗人们也正当这世界之夜的夜半纷纷离去(自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社会自杀或发疯的诗人不下百位)。诗人的世界眼光提醒他,在现代西方世界,人们也正在“上帝死了”之后的精神荒原演绎着荒诞的“当下即是”的疯狂表演,求诸西方的意义模式像求诸本族传统的价值体系一样虚妄。双重的失落,使诗人一样跌入了现代人文精神的黑暗中心,甚至跌得还更深。
那么,怎样安抚自己受难的心灵呢?被信仰抓住的诗人最初也许只能通过语言艺术向着自我意识的深层掘进,从自己的生命中唤醒所有沉睡的力量来将养自己受伤的心灵。他在精神的大空虚中粗暴地撕去精神充实的假面,从而他不仅拒绝接受古老东方文化的空洞的诱惑,与现代理性反目又不愿也不能在人类的过去所留存的令人遗憾的宗教残迹中觅得心灵的居所,最终达至精神之翅独自止憩于自我之内的疯狂目的。一种血淋淋的目的八面撞击,抽打大地的文化和价值之墟,让这世界之夜的精神苍凉在意识的冷光中在苍茫的时空中无限上升,上升:“让我离开你们独自走上我的赤道我的道/我在地上的道/让三只悲伤的胃燃烧起来/(耶稣 佛陀 穆罕默德)”(《太阳·诗剧》),“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祖国》)。[1]海子后期的大诗,以“太阳”为中心集结了许多邈远的燃烧意象。诗人对有限生命选择了燃烧的方式,生命不计后果地在精神的白热时空吹息放射:“我处于狂乱与风暴的中心,不希求任何安慰和岛屿,我旋转犹如疯狂的日”(见1987年11月14日日记)。在一种精神迷狂中,在垂直燃烧穿透自然和人文诸事物中诗人感到一丝超越的狂喜同时也感到痛苦的更剧烈煎迫,这种煎迫又会逼使他燃烧得更炽,最终竟“被智性的净火烧成焦炭”。
三 超越性创作的至深处是伟大而单一的主题
超越性创作的至深处是伟大而单一的主题,即对人的终极实在的聚焦。与之相随的主体精神生态则是形而上的迷狂。是一种内在的宗教激情,一种对皈依的极度渴求,一种对生命的大爱与弃绝,同时也是一种从灵魂深处刮起的精神风暴,一种人类智性最后的狂妄与绝望。在这个层面上,主体往往进入了其一生创作的巅峰期,而其实他消费巨量话语道说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仿佛一切都已说尽了之后仍在无休无止地说——当然,这之后可能是永恒的沉默——和无言的永恒躺在了一起。这时那滔滔而出的东西把创作主体“交付给了一种断言”,对此,“他毫无权威可言,这种断言本身也无稳定性,他事实上不肯定任何东西,它不是安息”[3](p.7)。他为什么要发疯般地创作呢?是为作品本身么?是为某种荣誉么?根本不是。他创作好像是在完成冥冥之中赋予他的某种使命(也许只是自己赋予自己的一种解释世界的冲动,这种冲动的释放往往是宏篇巨制的诞生),尽管这种使命他永远难以完成。(注:当诗性活动到了较深的程度,创作主体就开始进入一个相对较长的酝酿期,这往往孕育着一个试图通过自己的文本解释世界的超大当量的创作(生命之作)。主体被这种冲动所宰制时,其心力有可能纯粹升华为一种十分危险的激情,这次创作的完成有时也便意味着创作主体生命的完成,仿佛一切被掏空之后的终结。我为这种现象所感动的同时,又总是会萌生一种无言的悲哀,因为一场文学的虚妄可能就此穷尽他们的生命甚至杀死他们的生命。每当读到精神天才们的生命之作,我都会感到难以言喻的震撼,但是我这时丝毫也高兴不起来,更不会为人类中竟有这样了不起的个体而豪情万丈,相反总是因其所承受的苦难而来的一种无声的眼泪和悲悯,或者是对人类存在本身的悲剧性的低首默认。)
海德格尔曾这样说过:“每个伟大的诗人作诗都出自于唯一的一首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在于,这位诗人对这唯一的一首诗是否足够信赖,以至于它能够将它的诗意纯粹地保持在这首诗的范围之内。”[4]我不敢说每个伟大的诗人其一生作诗是否都出于“唯一的一首诗”,只是感觉到那些具宗教情怀的诗人走向创作的至深处时其精神诉求有某种惊人的契合,并且主题甚至他们所寄寓的物象都表现出某种固执的单一。
海子的巅峰之作应该是太阳七部书。也正是太阳七部书的创作透支了他的生命,并导致他最后的炸裂。他之写作太阳全书,如他在《太阳·断头篇》中所说:“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我不知道行家们对太阳七部书都怎么看,我个人的观点是:与其说它是史诗,毋宁说那只是海子绝望的激情一次大喷发。海子在他的诗剧里把多种原始力拟人化,只是他在多个形象里都融入了自我,象喻着自我矛盾冲突的各个方面,在诗剧里真正占主角的其实还是诗人的自我。在这个自我的周围,则蕴蓄着诗人另一个巨大而空虚的报复:解释世界。而在这股解释世界的冲动中,诗人则始终是深陷在精神绝望中的。
其实太阳七部书的主题相当单一:强烈的形上诉求加暴烈的自我献祭。这是一个“黑暗而空虚的王”最后炸裂前的灵魂自白书:
《太阳·断头篇》以大爆炸的当代科学与人文的宇宙背景作为诗歌布景,涂抹上一个“断头战士”与天空和大地、天堂和地狱、生和死的对质。海子曾经表示自己的这首长诗是一篇失败之作(也许是写得太白了,受到了“艺术”的警告),其实海子正是从这里真正开始投入了他那“一次性诗歌行动”,开始了他反抗宿命的宿命历程,开始了他的“行动哲学”,直到1989年那一次生命叙事结束:“除了死亡/还能收获什么/除了死得惨烈/还能怎样辉煌”(《太阳·断头篇》第一幕第二场)、“大地将毁灭/或更加结实/更加美好地存在。行动第一”(第三幕第一场)。[1]《太阳·土地》主要表达了对人的属地宿命(“土地固有的欲望和死亡”)的反抗(前面已论述)。《但是水、水》则唱出了灵魂的干渴。可以说这首长诗首先是献给母亲、母性、大地和生命的深沉颂歌。诗人的诗与思在这里可谓深入了人类原始经验和体验的内核。海子这首诗把整体背景置入作为生命的墓地和摇篮的民间,置入大地深处,以“水”为中心象征,唤起并润育了一大批于生生大化息息相关的意象,如日月、河流、土地、雨雪、根、火苗、田野、井、陶、鱼、肚脐、乳房、血液等等,这里,“土地是一种总体关系,魔力四溢,相互唤起,草木人兽并同苦难,无不深情,无不美丽”(《寂静》)。诗人本意是想通过这首长诗“唱唱反调”,“对男子精神的追求唱唱反调”,但他并没有在这里作过多停留。
《太阳·弑》是一出仪式剧。“那是一个血红而黑暗的恐怖空间”,“人物全部有如幻觉,与命运而不只是相互格斗,最后无一例外地死去或迷狂。”在借具象的事物表现一种可怕的精神空虚上,鲁迅先生的《墓碣文》堪称“经典”。海子在这方面丝毫也不“逊色”。我们单揣量一下《太阳·弑》的背景设置就可以感领得到:舞台氛围不是黑暗就是血红,背景音乐则时常是沉闷的鼓声、撕人心脏的佛号或呜咽的喇叭。可以说,死亡一直是海子诗歌的根本主题,在他的二百多首短诗里,有着死亡意象或死亡意识的有三分之一居多。太阳七部书更是一部关于时空、生命和死亡的大书,并且,在“麦地抒情短诗”中笼罩着死亡的那一层柔美的氛围也不见了,只剩下钢铁般的死亡。《太阳·诗剧》一开篇就说:“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如果说《诗剧》的徐徐行歌还勉强可以被认为是安详、恬静的死之宣言的话,那么《太阳·断头篇》、《太阳·弑》则纯粹成了自我暴力的诗性渲染。这里,语言绕着死亡主题火一样旋转,死亡像茫茫世界的虚无中唯一的实体无比尖利地刺入生命时空。这里,诗人开始了“一个也不能原谅”的最后的精神复仇,这复仇越过实体直指本体。
诗人在巨大的空虚与绝望中竟没有忘记他那个“解释世界”的抱负。在《太阳·弥赛亚》这首诗人自称“用尽了天空和海水”、“用尽了生命和世界”的长诗中,这位以激情突入为主要方式的诗人竟好像慢慢穿越了激情,主观地抵达了“一种明澈的客观”,以维特根斯坦式罗列命题的话语方式作结,给出了一种关于世界起源及在世界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自然宗教图式。但这首长诗只是一部残篇。也许是诗人这时彻底从骨子里意识到文本的虚构本质;也许是诗人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创造终究属于虚无主义视域,最终无法摆脱宗教;也许是太阳全书创作到这里诗人已经身心俱疲,身心俱焚,达到了诗性活动的临界点——匆匆留下这个残篇,而后自我杀戮。在这部残篇的最后,这位“诗歌烈士”竟“出人意料”地暗示了一种非自然宗教性的希望和救赎:“天堂的大雪一直降到盲人的眼里/充满了光明/充满了诞生的光明”。这个结尾似乎暗示了一种面向救主的拯救诉求,也许这是人类智性用尽后的一种回归,有一种“物极必反”的味道。
四 精神性掘进遥指临界点
过于执着的诗人多是些“短命天才”。短命的发生方式大致有这样几种:癫狂、自杀、病逝(所谓病逝,在他们那里无异于慢性自杀,因为这病起因于长期的精神危机,或者说至少是由精神危机有害地刺激而引发的,并且这病比肉体上的创痛更容易伤身心,几乎无药可治)。这是一种十分令人感叹的现象。我们在光天化日下那突然而至的黑暗中,“抱住一位宝贵的诗人痛哭失声”(《黎明与黄昏》)[1],却永远无法更改他的命运。循着一种内省的思路,我被导向了如下判断: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的持续创作抵达并强行越过了一个临界点。现在我们就围绕这一思路来进行考察与寻索。
一个切近根源的问题:在其滔滔话语所营构的艺术氛围里获得超越感的创作主体为什么会走向自绝?凭直觉就能得出的答案是:主体在其自我话语氛围里并不能获得存在性具足,单纯的审美诉求在一定的界面上终将显现其苍白。在一定精神的层面上,艺术就会逼使诗人“奉献”自己的生命。(注:当代思想大师福柯在《作者是什么?》这篇文章里,雄辩地指出了写作与死亡之间的不解之缘,认为写作是“生命本身的牺牲”,作者通过离开“生命”来撰写“生命”,他说,“以往作为防止死亡的说或写的叙事概念,已经被我们的文化改变。……凡是作品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这个说法有些朦胧,不过以此来看那些宗教型诗人和艺术家,似乎是恰切的。福柯:《作者是什么》,见《最新西方文论选》,第447页,王逢振等编,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透视那些终极关怀意识很强的诗人的精神真相,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推测:当诗人的精神掘进达到一定深度(即达到某一临界条件)时,就非常需要宗教出场救助,否则,那种超过这一临界的以艺术为载体的精神性掘进便难以继续。当且仅当达到这个生命的临界点,诗人极可能不得不在不远处结束自己的艺术活动,并通过以下三种出路中的一种完成自我:疯癫、自杀或皈依(皈依是“正道”,自杀是弃绝,疯癫也能算是解救之道,是处于临界点的主体作为救命的最后手段之一)。当然,我们说有这样一个临界点,并不意味着它就像数学那样一定会准确地出现在诗人命运曲线的某个点上,它是一道模糊的精神分水岭,遥看冥蒙近却无,但它确是诗人精神发生质变的开始。
海子早在1986年好像就已切近了那个临界点。他在1986年11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一直就预感到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一生中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我差一点自杀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情绪体验,也许有些许个人情感的因素,但我坚信那远非事情的根本原因。我们能够感觉出,在这之前海子的诗作就已经透出一种大密度的生死主题,而且太阳七部书中的《太阳·断头篇》也完成在此前。可以认为,海子其实早已拥有了无以消解的痛苦和绝望感。并且,他的诗作一直或隐或显地包蕴着某种神性体验,这种体验对海子来说却始终伴随着内在的空虚与黑暗。1986年的那个关头看来之后被他突破了,他继续前进了,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此后的劳作并没有使他在心灵层位获得新的有效提升,这样的继续使他最终彻底抵达并越过了那个临界点。越过那个关口之后,也就是1987年以后,他放弃了前期诗歌中的母性质素,竟进而跃向一种父性、“一个也不原谅”的精神复仇,不消说这加速了海子向死亡的最后冲刺。这时,诗人当然有可能产生返回的愿望,但是,昔日为诗人所感动的事物却已经也都对他翻脸不认。后面失真,前面用尽,诗性活动至此,它所承受的真空的力量——“我吞噬真空/是真空里的煤矿”——致使诗人产生速速烧尽自我的“恶念”,这个烈性诗人除了坠入自我的地狱外别无选择。
最后,我简单讨论一下诗人与宗教信仰的悖论关系。诗人深刻的苦难意识和神性体验使他们内在地“从精神走向宗教”,但他们却没有由此获得丝毫的“宗教快感”。(注:宗教快感,又称宗教幸福感。大致有如下一些含义:(1)指信教者出于对上帝、耶稣、天国的信仰而带来的精神上的宁静、满足、充实的感觉。当基督徒到教堂做礼拜,当穆斯林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麦加朝圣,当佛教徒长年累月在深山修行时,都获得一种有所寄托、有所实现的幸福感。(2)指信教者通过宗教信仰摆脱痛苦。人生有各种痛苦,而宗教徒通过宗教得到精神寄托,使痛苦被祛除。受苦的人幻想来世,于是处之泰然。总之,宗教快感是指宗教徒在信仰中确实产生的幸福、实现、心静等快感。这个术语最早由苏联的一些哲学家提出,后在不少宗教学方面的著作中都可以见到。)我敢断言诗人这时所走向的宗教是一种“理性宗教”(或可称为“自然宗教”),一方面认为存在超自然的精神(或者叫作神)存在,一方面又认为人对这种存在无法认知,并且人类的所作所为与它永远无关。这种“理性宗教”是主体经过纯粹理性演绎而得出的一种意识形式(注意!只是一种意识形式,而不是建基于心灵感性基础上的宗教信仰),诗人把这种由理性推出的宗教经过自己的情绪加工使之感性化,化为想象力的作品。但这是一种危险的状态。因为宗教信仰归根结底是与理性相抵牾的。理性(包括价值理性)的出发点有时可能是想为宗教辩护,但是辩护到后来,由于自身绕不开人类智性注定要遇到的悖论,结果反而是扮演了为宗教拆台的角色。正如存在主义思想大师克尔恺郭尔所言,在现代科学理性的背景下,不顾理性去信仰是痛苦的,但一顾及理性,信仰就好像摇摇欲坠。现代诗人自我意识的深度觉醒及理性的内在在场,总使他不期然地去追问甚至质疑绝对者。他们一方面在骨子里是不可知主义者,一方面又近乎迷狂地对绝对者进行漫长的空洞静悟式的体验和认知;一方面有着强烈的还乡意识和拯救诉求,一方面又因救主的缺席而深感绝望。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诗人对世界的神性体验不是使他的个体生命由此得到安顿,而是反使他处于一种内在撕裂中。他有强烈的信仰渴求,但信仰什么他自己并没有成见。信仰上帝?可上帝缺席;信仰虚无?他又决不甘心!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经常使他感到内在的大空虚和大黑暗。“一只羔羊在天空下站立/他就是受难的你”(《土地》第二章),海子尽管如是吟唱,但他终究看到了“牧羊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