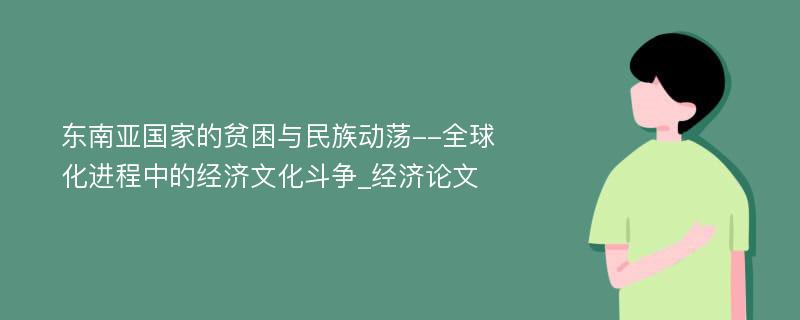
贫困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动乱——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文化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乱论文,贫困论文,东南亚国家论文,进程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东南亚国家中,为什么由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有时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有时则以民族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与东南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有无关联?如果将全球化视为源于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则二战后初期东南亚仍处于被动式现代化阶段,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指向乃是继政治独立之后的经济独立,此间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农民—地主”这种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几乎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重叠,民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转而为地方或族群所利用,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少数族裔—主体民族”这种民族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民族主义之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是贫困问题与民族斗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民族运动取代了阶级斗争而居于世界舞台的前列。① 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贫困,而且是文化(广义的文化)贫困,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贫困。在这种双重贫困的境况下,以地区、宗教、民族、语言等为基础的各种亚群体及其分别发起的群体性运动遍及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逐渐与组成国家的主要社会阶层(阶级)一争高下,且与民族国家相抗衡。② 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一般基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而与文化无直接关系,然而在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国际资本等因素的运作可能损害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而且文化均质化的倾向亦可能危及这些亚群体的文化根基。
一、“经济—文化双重结构”的提出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的释义,来阐述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民族动乱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经济”和“文化”概念除了其一般的含义之外,还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经济”是经过整合了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而“文化”则是多民族国家中单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经济”层面,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已无法分割;而在“文化”层面,各民族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整合则尚未完成。这就出现了二者的错位或不同步,由此产生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就民族国家的整合而言,国家的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是相互促进和彼此制约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对其经济劣势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经济容忍度”)往往大于对其文化从属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文化容忍度”),因为文化的消亡才真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最终消亡;而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包容度也常常大于对其文化的包容度,因为对主体民族来说,本民族的文化通常是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能是被整合的对象。
就一般意义来说,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尚未达到极限而其文化容忍度已达到极限时,或者说二者的叠加使文化层面上的容忍遮蔽了经济层面的容忍时,反叛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倘若将贫困(狭义的贫困)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它就不会必然导致少数民族的反叛,因为在经济贫困下其生存安全的范围是较有弹性的。倘若综合考虑贫困(广义的贫困)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因素,它与反叛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大大增强,这是民族文化的敏感性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动乱或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时,对抗才不可避免。换言之,从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物质上的匮乏并不一定触及精神层面的安全感,但从超越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并考虑到精神受物质刺激且反作用于物质的必然性,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二、文化是“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主要的矛盾方面
就上述意义而言,何者是“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过去,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构成了抗议的基础,今天经济问题占了主导地位,边缘性共同体声称,由中心或关键性族裔控制的政府,剥削了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忽视了他们的地区或使该地区边缘化”。③ 换言之,经济是主要的矛盾方面。然而,此说无法解释如下现象:泰国北部山区的经济比泰国南部(以下简称“泰南”)四府更为落后,泰北山民的抗争却远不如泰南穆斯林来得激烈;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经济也落后于南部穆斯林地区,而前者亦未发生如后者那样的激烈抗争;印尼亚齐地方经济的衰退虽非全印尼之最,然而亚齐的分离主义倾向却是最突出的,等等。笔者认为,文化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这一观点,上述现象或许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文化之所以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首先是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纵观二战后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发展的重点先是从政治自由转移到经济增长,继而转移到社会平等,最终转移到文化自主”。④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政治独立之后的内部变革,最主要的是经济变革。然而,这一变革除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之外,其过程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不平等。而统治集团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二:一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对于分配公正的考虑挤到一边”;一是“忽视特质文化的要求及其争取自主的自我表现”。⑤ 二者的要害都是否定文化的中心作用,因为分配公正与文化自主都是经济发展本身所无法提供的,它们乃根植于相应的社会道德、文化之中。“如果以蛮横的态度对待文化,文化会做出暴烈的反应,为发展而进行的许多努力可能因此毁于一旦”。⑥ 因此,对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不可能弃文化以求发展,因为文化有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已经走到舞台中央,影响着发展的过程及其成果的分配”。⑦
其次是政治文化的急剧变迁造成的。民族认同是人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认同之一,它不会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更改,它是由文明的特质、各文明间的差异决定的。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新认同政治(the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对传统政治和阶级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归附于亚团体或者重归个人”。⑧ 换言之,“种族认同、地方认同、性别认同等正在冲击和替代着传统的阶级认同、政党认同”。⑨ 这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的变化造成了身份界限的模糊”,使人们“加强了对身份归属的紧迫要求”。⑩ 而传统的阶级认同无法解决文化归属问题,只有文明“是确立身份和意义的有效源泉”。(11) 这样,民族或种族的认同便取代阶级认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认同取向。这一认同取向无疑凸显了文化的作用,进而也决定了在“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
三、反贫困斗争的物质与道义性质:以森林开发利用为例
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反贫困的斗争不仅具有捍卫生存环境的物质上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具有捍卫民族文化的道义上的性质。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围绕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斗争,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从自然资源开发史的角度来看,越是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其森林资源的保存越完好。然而,这是就经济开发尚未全面展开的时代而言的。在全球化时代,这些边远、偏僻之地已被纳入开发的范围。在印尼,97%的森林分布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西伊里安等的外岛上,(12) 那里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既是山地民族的聚居区,也是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是全国林木资源贮存量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这些地区的森林无一例外地被大量砍伐,世代居住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抗争活动也随之频频发生。民族动乱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具有生存环境和文化象征双重意义的森林资源的被破坏,无疑是使少数民族陷入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印尼外岛,由森林问题导致的冲突已经爆发,这是因为天然热带森林不断被砍伐,乡村居民不断被驱赶。(13) 在泰国,土著山民部落在反贫困斗争中是这样表达其观点的:“土著民族珍惜森林与自然,珍惜这个世界的生态。他们生活在森林中……森林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社区、他们的生命。国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部落民族珍惜森林,并以一种平衡的、恰如其分的方式与之共处。”从他们的宣示中,透露出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贪得无厌和具有破坏性的”(14) 这一残酷现实。这对视自然与人为浑然一体的土著民族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在菲律宾棉兰老,“跨国公司——多尔大菠萝公司——已经获得了对该岛低地的占有权,该公司正在毁坏土壤并将农民赶到高地上。在高地所有者与低地所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土著人——‘部落群’——为保护他们文化的完整和‘祖产’而战”。对原本和谐的自然—人文环境的破坏和侵蚀,“是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活动而导致的结果”,其殃及地区“包括穆斯林棉兰老岛自治区以及卡加延—德奥罗—伊利甘增长走廊”。(15) 森林不仅承载着土著民族的自然生命,而且融入了他们的人文意识,所以森林被破坏所导致的贫困绝非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
对于东南亚的少数民族或土著民族来说,外力介入森林资源的开发剥夺了他们的“似乎属于自然权利的东西”。换言之,居住于林地、利用森林产品是土著民族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从前一直像空气一样免费的、现在仍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资源,突然间不允许他们沾边了”,(16) 这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打击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国家为何能如此恣意妄为?“在东南亚,土地控制作为国家或国家机构合法化的基础,大体上源于殖民主义”。(17) 但在殖民地时期,以土地控制为基础的森林开发主要限于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远离政府所在地的森林中心地带——那里常常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尚未被触及。当现代化与全球化潮流相继涌来时,对土地与森林的攫取已是无所不至,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不能幸免,而他们的经济—文化抗争也就势在必然了。
四、发生民族动乱的决定性因素:对不同贫困类型的分析
“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因应于一定的条件而发生转化。当少数民族尚未将经济上的贫困与政治—文化权利的丧失联系起来时,该矛盾统一体的结构会呈现相对稳定状态,但这也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当少数民族明确地意识到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文化地位密不可分时,这种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长期积累的问题就会以突变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会在其“暴烈的反应”中凸显。
那么,少数民族的贫困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会与其他因素共同导致动乱或反叛呢?对此难以一概而论,因为这要视具体的民族地区属于哪一种贫困类型而定。东南亚的贫困状况虽然复杂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类型,即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前一种类型是指融入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不仅未能得益于发展,反而陷入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印尼亚齐、菲律宾棉兰老为例;后一种类型是指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了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在欠发展中陷入一种近似绝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泰国北部山民、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例。
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省,自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以来,迅速发展成一个能源大规模开发的省份。从1980年开始,亚齐平均每年为印尼带来20亿—30亿美元的出口收益。1985年,亚齐是印尼第三大出口创汇省份,仅次于廖内和东加里曼丹。(18) 尽管亚齐从本地油气收入中所得的份额一开始就很小,但当时的亚齐并不是印尼最贫困的地区。从印尼各省的贫困率来看,1980年亚齐的贫困率仅为8.8%,而同期其他省份的贫困率多在10%—20%,有些省份甚至在50%以上。(19)
从长远来看,亚齐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及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亚齐的资源开发被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获益者乃是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而不是亚齐人民。不过,从亚齐发展的起步阶段来看,这一恶果尚未显露出来。然而恰恰在亚齐开发初始且贫困问题尚不突出时,延续了本地区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并提出“独立”诉求的“自由亚齐运动”兴起了。这说明,属于“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一定要坠入贫困的深渊时才会有民族动乱或反叛发生,而是只要当地精英人物意识到本民族政治—文化自主权有所丧失,就可能出现动乱与反叛。这是由于长期反抗外敌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积淀极易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等外来因素的刺激,所以当经济剥削尚未超出可容忍的范围时,文化上的被剥夺感就已超出了可以忍耐的限度。
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从自然与矿物资源的拥有来说它是菲律宾最富裕的地区——(政府)一开始的努力就是为菲律宾北部的工业搜括资源……独立后,许多跨国公司来到棉兰老置业……棉兰老成了菲律宾赚取外汇收入的主要地区”。(20) 从这一点来看,它与亚齐是非常相似的。但棉兰老岛的情况也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它输出的主要是热带经济作物产品及木材,而不是能源产品;其次穆斯林在其聚居的13个省当中,只在4个省占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来自北方的天主教徒移民反而成了多数。这两点都使棉兰老岛土著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其民族文化受侵蚀的程度比亚齐严重;后一点则使棉兰老岛的贫困问题较为复杂。因为来自北方的移民也有许多是贫苦农民,所以难于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等同于穆斯林。棉兰老岛的大规模开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反抗运动也正是兴起于这一时期。能否以此断定经济原因即是当地民族反叛的主要原因甚至惟一的原因呢?该阵线在宣言中将土地被掠夺与伊斯兰教受到威胁并列为起义的两大原因。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并不能单独起作用,民族文化受到歧视是一重要原因,“当普通的菲律宾穆斯林民众无法面对继续存在的歧视、无从改进自身的生活条件时,大都会倾向于支持武装的分离主义组织”。(21) 因此,与亚齐属同一种贫困类型的棉兰老岛,在贫困与动乱的关系上也是类似的。
如果说发展中的贫困是后发式的,那么欠发展中的贫困则是原发式的。另外,作为贫困的主体,前者是一元同质的,后者则是多元异质的。泰国北部山地民族(山民)的贫困,即是后一种类型的贫困。泰北山民由20多个民族组成,他们在历史上长期的迁徙、流转过程中,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他们共约有70万人、10万户(1990年),分散居住在泰国北部的近3500个村寨中。(22) 泰北山民的贫困是一种“三合一”式的贫困,亦即由原始的农业经济、封闭割裂的社会、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同构成三个互相黏结又互为因果的贫困。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部分泰北山民非永久性地流入城市,现代政治意识也开始渗透到各山民部落中。那么,在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巨大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泰北山民为何没有像泰南穆斯林那样进行抗争?其原因不是泰北不如泰南贫困(实际上其贫困程度乃全国之最),而主要是异质文化无法对各山民部落产生凝聚作用。尽管历史上泰北有的地方如东北部,也曾因是“反对曼谷政权的中心地区”而具有“反叛传统”,(23) 但当代的情况却是,即使抗争,也是采取合法、半合法的形式,有时还须借助于外力的推动,如“在非政府组织与学术界的鼓励与帮助下,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农民网络在泰国北部地方社区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了。该网络为其会员的资源权利与社会公正而斗争,那些作为会员的社区有许多是少数族群(‘山民部落’),比如克伦人”。(24)
这说明,属于欠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是其贫困程度不足以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而是由于其文化的异质性、居住的分散性、思想的保守性以及精英缺失等,使得有组织的、强有力的反抗终难形成。
菲律宾有60多个山地少数民族,分布在自北到南的全国各个地区,其文化的异质性与居住的分散性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在拥有庞大贫困人口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处于贫困者的最底层,欠发展的印记在他们身上更为深刻。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些菲律宾山地民族如阿埃塔人还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但是,现代化的浪潮使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其中,他们原有的经济—文化模式惨遭破坏,如阿埃塔人转而在贫瘠的山坡上从事游耕,在与外界接触后其原始信仰也遭到腐蚀,从而变成“濒危”民族。(25)
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们也和泰国山民一样,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民族运动,而只能要求实践宪法规定的民族自决权。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边缘化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因为他们不是相对集中于一个区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缘化是一种以空间上的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26) 他们极为分散的居住地像是主体民族汪洋大海里的一个个孤岛,他们最终有可能完全消失于强势的主流文化中。尽管他们也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但要想阻止贫困化与边缘化的趋势,他们的抗争却显得软弱无力。总之,与泰国北部山民属于同一种贫困类型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在贫困与抗争的关系上也是相类似的。
将贫困与抗争的关系置于“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主意识,以及使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才是动乱或反叛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贫困的程度则是文化自主意识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之一。
五、对不同视角下的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探讨
在前文所述的“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经济”与“文化”的特定含义是为了立论分析时兼顾反贫困斗争中对立的双方而给予的限定。实际上,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都会从自身的角度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经济的整合乃是客观的、不可逆转的事实;国家文化的整合虽尚未完成,但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被整合的对象是必然的,即从长远来看,少数民族文化不可能“单独存在”。从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具有分离倾向的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经济的整合是可逆的,本民族地区的经济可以自成一体而不依赖于现有国家;本民族的文化更是可以长期单独存在,并且完全拒绝同化式的文化整合。
那么,是否有必要将国家与少数民族不同视角下的“经济”与“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做一综合性的探讨呢?为了全方位地厘清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民族动乱的关系,显然有此必要。这里将以泰国南部为例来进行探讨。做此选择的理由是,泰南的贫困是介于“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之间的类型;泰南的民族动乱既非连续式的亦非间歇式的动乱,而是一种由长期因素与突发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起伏不定式的动乱。选择这样一种中间类型,既可以较为均衡地展示国家与少数民族双方在贫困和动乱中的立场、观点及斗争策略,又可以将前述两种主要贫困类型联系到一起,就斗争双方的种种表现做一横向比较,并找出其共同点。
在泰国政府看来,随着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不断进入泰南,以及该地区资源的不断开发,泰南是国家整体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地穆斯林的看法却与其相反。他们认为,无论是移民还是开发,都是以牺牲当地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他们要求与泰国分离。泰国官方对此的反应则耐人寻味。曾任泰国副首相的巴拉帕特(Prapat)说过:“(泰南)马来人可以离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土地必须留在泰国。”(27) 可以想见,在泰南穆斯林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情况下,该族群陷于贫困便势属必然。从区域经济差距来看,泰南较之发达的泰国中部要贫穷许多,但比之于泰北则不算贫穷。从开发程度来看,泰南介于发展与欠发展之间,故其贫困属发展中之贫困,亦即属于尚未定型之贫困。倘若不对泰南穆斯林的经济结构加以改变,其贫困可能深化并定型。目前,泰南四府的马来穆斯林人口大约有72%生活于农村,他们主要是自耕农。(28) 这种从业结构对其摆脱贫困是不利的。
泰国政府与泰南少数民族在经济整合观上尖锐对立,二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看法更是格格不入。自20世纪30年代大泰族主义兴起至80年代泰国政府开始正视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前,泰国官方一直否认境内存在少数民族,自然谈不上承认其文化上的独特性与自主权。泰国政府在经济上对泰南穆斯林还不时予以让步和扶持,但在对待其文化上则是以打压为主。围绕着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的学校“旁多克”(Pondok)的开办与封闭,泰南穆斯林与泰国政府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由于认识到“旁多克”在泰南穆斯林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泰国政府于1961年颁布了“教育改进计划”,欲以政府控制下的私立伊斯兰学校取代穆斯林社区领袖开办的“旁多克”。以北大年为中心的“旁多克”教育系统,长期以来是马来半岛穆斯林精神力量的源泉。因此,泰国的这一教育改革计划遭到了泰南穆斯林的反对。“保守的伊斯兰教士和乡村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笔者)认为,政府的这一政策是对马来人伊斯兰认同的一个打击,是对其文化、社会与宗教价值观的打击。这种感觉导致了分离主义组织反叛活动的扩展”。(29)
如果说泰南穆斯林对经济的贫困尚能容忍,那么他们对文化的贫困乃至衰微则无容忍之余地。泰国政府欲以釜底抽薪的办法销蚀穆斯林的精神支柱,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了少数民族反叛的蔓延。
很显然,无论从哪种视角赋予“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的“经济”与“文化”以何种含义,都不会影响到“文化”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在贫困与动乱的因果链中,文化是潜藏其中的深层关联因素。泰南如此,亚齐、菲南亦如此。亚齐的间歇式反叛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起落及虔诚穆斯林意识的反弹同步,菲南穆斯林的连续式抗争亦与天主教强势文化的不断侵蚀相关。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导致这三个地区反叛的直接原因,但文化才是贫困衍化为动乱的终极推力。
六、余论
对历史和现实的纵向考察,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境内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抗争之发展脉络。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在前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的东南亚,使用国家空间和非国家空间概念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他引用埃德曼德·李奇的话说:“我们事实上应该将相对人口密集、在首都范围内的种植水稻地区看成‘王国’(即国家空间——笔者注),而将其他地区,尽管可能距离首都也很近,看成是‘非国家空间’。”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的发展计划,不论是在东南亚或其他地方,都要创造出国家空间,从而使政府可以改造那些‘被发展’的社会和经济。现代的发展主义民族国家将边疆的非国家空间转变为国家空间是普遍发生的,并且对于这些空间的居民往往是痛苦的。”而“在实际反叛的背景下,人们创造和清楚区分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努力的逻辑结果才会显现出来”。(30)
笔者认为,现代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乃是历史上国家空间对非国家空间的挤压之现代版,而非国家空间的居民之痛苦,更突出地表现为文化自主权被剥夺的痛苦,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更多的是有别于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如果说经济上的贫困是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显性特征和民族动乱的表层原因,那么文化自主权的丧失则是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本质特征和民族动乱的深层原因。因此,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的贫困与反叛的关联,便主要表现为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
本文已经指出,东南亚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尚未完成,并且从国家与少数民族的不同视角来看待文化整合,仍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倘若从全球历史中民族国家的整合这一大视角来考察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欧洲,“这种整合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平衡、不彻底的。其间充满了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压迫、歧视、强制同化和社会文化的边缘化”,更遑论东南亚这样的发展中地区了。因此,“这种结构上的非均衡性与文化上的非均质性,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特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使“人们对保持民族文化权利、使民族文化特性不至于泯灭在一体化过程中等问题,变得非常敏感”。包括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在内的种种冲突,“既反映了具有强烈的历史民族认同意识的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主体民族文化霸权的不满和抗议,也反映了全球化、一体化过程中人们对共同体外延和内涵的重新界定,以及对最大限度的文化自主性的追求”。(31) 全球化时代的“贫困”是指广义的贫困,亦即由经济与文化共同构成的多层次的贫困,其中文化上的贫困更具有本质的意义,它决定了这一时代的贫困之性质,从而又决定了由贫困推动并促成的民族动乱之性质,那就是捍卫民族文化自主权、重振民族精神,以求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待遇。在不跨越国家所能容忍的底线——不破坏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完整——之前提下,应该说其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以便使少数民族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注释:
① 参见[法]阿兰·图雷纳著、程云平译:《现代性与文化特殊性》,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② 参见[美]尼尔·J·斯梅尔塞著、黄语生译:《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43—44页。
③ [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等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④ [印]S·C·杜布著、何素兰译:《发展的文化维度》,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217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214、217—218页。
⑧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⑨ 同上,第95页。
⑩ 同上,第38、82—83页。
(11) 同上,第83页。
(12) 参见Nancy Lee Peluso,Rich Forests,Poor People: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5。
(13) 参见Nancy Lee Peluso,Rich Forests,Poor People: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p.5。
(14) Bruce Missingham,“Forging Solidarity and Identity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oor:From Local Struggles to a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in Thailand”,in Asian Studies Review,vol.27,No.3,September 2003,p.332.
(15) [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23、233页。
(16)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17) Nancy Lee Peluso,Rich Forests,Poor People: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p.17.
(18) 参见Dayan Dawood & Sjafrizal,“Aceh:The LNG Boom and Enclave Development”,in Hal Hill(ed.),Unity and Diversity: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since 197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07。
(19) 参见[印尼]J·S·乌帕尔、布迪奥诺·斯里·汉多科著,谧谷译:《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间收入不均》,载《南洋资料译丛》,1988年第3期,第62页。
(20) Syed Serajul Islam,“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in Asian Survey,vol.38,No.5,May 1998,p.452.
(21) Rizal G.Buendia,“The GRA-MILF Peace Talks:Quo Vadis?”,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2004,p.215.
(22) 参见申旭:《泰国山民问题及政府对策》,载《东南亚》,1993年第2期,第37页。
(23) 参见[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第254页。
(24) Bruce Missingham,“Forging Solidarity and Identity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oor:From Local Struggles to A 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in Thailand”,in Asian Studies Review,p.324.
(25) 参见包茂宏:《论菲律宾的民族问题》,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第31页。
(26) 参见[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著、刘得手译:《全球化综合征》,第289页。
(27) Moshe Yegar,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Southern Thailand,and Western Burma/Myanmar,Lexington Books,U.S.,2002,p.127.
(28) 参见Moshe Yegar,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Southern Thailand,and Western Burma/Myanmar,p.126。
(29) Moshe Yegar,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Southern Thailand,and Western Burma/Myanmar,p.135.
(30)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47—250页。
(31) 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40、241、239页。
标签:经济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泰国历史论文; 穆斯林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