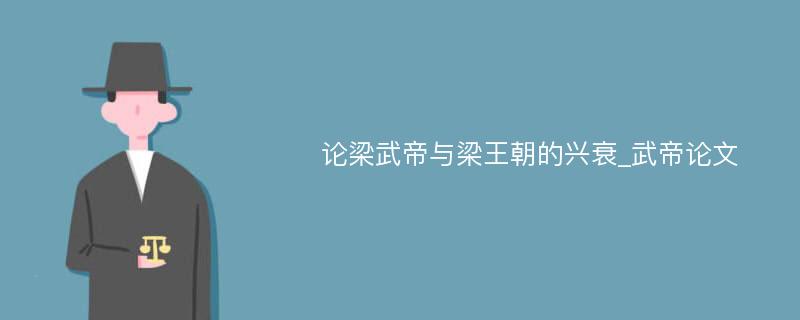
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亡论文,梁武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1-0045-010
一
梁代的兴起和败亡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梁武帝个人的作用。但综观他的一生,从一个丁忧的“诸府参军”,遭际齐武帝临终时的政变投向齐明帝,为他出谋划策,迅速地由一个七品小官一跃而成位居四品并掌管着南朝精兵汇集之地的雍州刺史。不久,又以雍州为基地出兵东下,夺取了南齐的皇位,前后不足九年时间。在他执政之初,确也曾使南朝政局出现过一个“洽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武帝纪》“史官”语),并且据说当时“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环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五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同上)。然而“及乎耄年,委事群佞”以后,“政以贿成”,“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同上),终于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梁朝亦随之很快灭亡。我们试看侯景之乱的前夕,东魏杜弼所作的《檄梁文》中数说梁政之腐朽云:“彼梁主操行无闻,轻险有素,工用其短,以少为多,反覆山渊,颠倒冠屦,射爵论功,荡舟称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礼崩乐坏。改换朝章,变易官品,虽世异汉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舍乖方,立废失所。矫情动众,饰智惊愚,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净。内恣鸱靡,外逞残贼,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灾异降于上,怨讟兴于下。履霜有渐,坚冰且至。恃浮躁之风俗,任轻薄之子孙。朋党路开,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难起腹心。”这段话虽属敌国声斥之辞,但大抵符合当时实况,尤其是后面几句话,当时虽尚未完全显露,也被后来事变的进程所证实。可见梁武帝的一生已由早年的“奸雄”或颇具才略的政治家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昏聩颟顸的亡国之君。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追究这变化的原因。像这种变化,显然不能单纯地用年龄等自然因素来加以解释。在这里,笔者想就个人所见提一个初步看法,请大家指正。
二
梁陈的易代并非单纯地是一个家族代替另一个家族称帝,如齐之代宋、梁之代齐,而是意味着南朝的政权从原来由北方南迁的某些集团手中转到了一些南方土豪之手。在这个转变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使南朝的疆土大为缩小,已经形成了北强南弱之势,决定了南北对峙之局已难长久维持下去。像这样重大的历史转折,自然不能完全由梁武帝个人及其意志来解释,而必须进一步深究其社会根源。我们知道,南北对峙的局面是在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形成的。东晋皇朝的建立实际上是由于琅邪王氏等几个由中原南渡的高门士族对晋元帝司马睿的支持,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晋书·王敦传》)。但东晋皇朝建立后,这几个士族高门之间的争权斗争始终没有停止,有一些家族在斗争中被消灭或削弱,使这个政权的基础发生了危机。所以王导晚年力主息事宁人,以求取得各种力量的支持来维持东晋的统治。王导死后,继起者也大抵继承着他的这个方针。然而,随着当时政局的变化,东晋朝廷不能不建立一支足以外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内镇压叛乱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终于产生了,它就是寓居于以今江苏镇江、常州为中心的,以原来鲁南苏北一带移民中的平民和低等士族为主干的“北府兵”。这支军队在抗击苻坚入侵的“淝水战役”和镇压孙恩、卢循的战役中都曾建立殊勋。从此以后,东晋政权中一些重臣在争权斗争中都要借重“北府兵”的力量,“北府兵”的向背往往决定着这些大臣的成败。在这种情况下,“北府兵”的首领自然产生了夺取皇位的野心。刘宋皇朝的建立者刘裕就是“北府兵”出身的政治家,后来南齐的建立者萧道成和梁代的梁武帝也都是这个集团出身。但“北府兵”内部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势力,宋、齐两代的许多内部战争,大抵是在几个“北府兵”将领之间进行的。由于这种互相残杀,大大地消弱了“北府兵”本身的力量。再由于从魏晋以来士族中盛行着重文轻武的风气,大抵一员将领在建立功勋,得到高官之后,其子弟就转而弃武从文。这在刘、萧等族及吴兴沈氏、彭城到氏等家族中都有所表现。这种情况大大地削弱了“北府兵”的战斗力,以至到宋中叶以后,迄于齐梁,南朝武装中力量最精锐的部队已经不是“北府兵”,而是聚居于今湖北襄阳一带以晋陕等地移民为主的雍州兵。所以早在宋末齐初,执政者对雍州刺史的人选已特别留意,不敢轻易授人。“北府兵”的削弱,也是出身“北府兵”将领的刘、萧等从北方迁来的那部分人在社会上的势力趋于削弱。正在此时,发生了“侯景之乱”这个强烈的外因,使原来统治南方达二百余年的北来诸集团受到致命打击。当时南方政权如果遇上像北魏盛时那种北朝政权,那么是否尚能维持三十多年之久,本很成问题,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对立,客观上使南朝得以苟延残喘,而在这时候,以陈霸先为代表的南方士豪正是在这个条件下建立了陈朝。但陈代的统治基础远较宋、齐、梁为薄弱,各派割据势力时叛时服,朝廷又不得不团结一部分地方武装去镇压另一部分地方武装。这就决定了南朝政权早晚要被北朝所灭,因此,梁代之亡,正是南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叫梁武帝一人独尸其咎。
至于南朝士族的趋于没落,亦非一朝一夕的情况。从中原南渡的高门大族,多数人本来就缺乏大志,只图在南方苟安。《抱朴子》中《疾谬》、《讥惑》两篇所记中原南渡士人们的种种行为,有些虽似轻视礼法,有些却也反映了灵魂的空虚。这些南渡的士人虽对中原的沦陷不无伤感,但“新亭对泣”的事例,却也说明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些中原人来到南方,大都满足于暂时的安乐。《世说新语·识鉴》:“周伯仁母冬至举酒赐三子曰:‘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顗之母还算是有识鉴的妇女,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当时南北士族中具有政事才能的人确很少。《世说新语·规箴》注引《陆玩别传》载,王导、庾亮等人死后,晋朝以陆玩为司空,陆玩对友人说:“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无人矣!”据云,“时人以为知言”,可见他说的是真实情况。造成士族中人才稀少的原因就是养尊处优。《颜氏家训·涉务》云:“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馀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正如《抱朴子·刺骄》所说:“生乎世贵之门,居乎热烈之势,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样的人,哪能办得政事。更荒唐的像同篇所载:“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为败,及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仇恨之。”像这样的人竟被派去带兵打仗,焉得不败!所以到宋齐以后的统治者,多已看出士大夫之无能,认为他们办事还不如一些寒门人物。《南史·恩倖·刘係宗传》:“係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齐)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係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梁武帝也有这种看法,《颜氏家训·涉务》说到“举世怨梁武帝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也是从这情况出发的。
不过士族的日趋腐朽,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东晋不少士人,虽有“迂诞浮华”之习,却非人人如此,还出过王导、谢安、谢玄等政治家。其他的人虽无政治才能,至少还不至于连自己走路也要人扶的地步。但到了梁代的士大夫,连这样的能力也往往很缺乏。《颜氏家训·涉务》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腹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梁朝政权基本上以这些士大夫为基础,这个阶层既已腐朽至此,其败亡自不可免。当然,从晋至梁,统治者的成分是有过变化的,宋、齐、梁三代的统治者出身“北府兵”将领,其先世自不致像王谢大族那样“迂诞浮华”,但当他们一旦致身高位以后,处处模仿当年高门,而且变本加厉。这种腐化的过程,决非任何个人意志所造成的,而且在梁亡以后,其风尚未停止。到了陈代,为了优待功臣,对侯安都这样的武将,也要“给扶”。举朝上下以此为荣,说明这种蜕化的过程,有一定的社会根源,不能完全归结为梁武帝的过错。不过梁武帝的许多政治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过程。
三
梁代的灭亡虽不能把全部原因归结为梁武帝个人的过失,但他的行为也促使梁代及南朝政权走向灭亡。梁武帝在施政上的失误无疑是很多的,在这里不想一一列举。笔者所要探讨的,倒是他从一个“奸雄”蜕变为昏君的思想原因。梁武帝的这种变化,显然有其思想根源。他所以后期会有这种变化,这和他前期的种种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不把他前期的行为作一简略的剖析,就很难解释他后期思想的变化。要弄清梁武帝其人早年的所作所为,还必须对他的出身和教养作一些探讨。因为他早期的某些行为如果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实在是大逆不道,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许不一定要深责。例如他的取代南齐,就是这样。我们不妨把梁武帝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他的出身和教养来推想他对自己的某些行为可能会有的评价。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梁武帝出身于兰陵萧氏这个“北府兵”将领的家庭。这个家族在东晋时代已有人出任官吏,如《晋书·荀崧附荀羡传》,就提到穆帝永和年间青州刺史荀羡有位参军叫萧辖,曾奉命领兵守泰山,抵御前燕慕容俊。萧辖就是梁武帝的高祖,据《梁书·武帝纪上》载,他后来官至济阳太守。可见这个家族虽称不上高门,却也不失为士族,再加上经宋迄齐,“北府兵”得势以后,他们的子弟都会接受较好的教育。因此梁武帝早年出入齐竟陵王西邸之时,即以文学之士的身份,和沈约、谢朓、王融、范云、任昉等为伍。这说明他从小就受过较深的儒家思想熏陶。另外,兰陵萧氏这一家本来就笃信道教,梁武帝本人早年就是个道教徒。在他的《舍道归佛》中,曾声称“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他作此文时间为天监三年(504),他年已41岁,所受道教影响当亦不浅。我们知道,儒家讲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而道教的道德观,亦与儒家类似,如《太平经》云:“今天地开阔,淳风稍远,皇平气隐,灾厉横流。上皇之后,三五以来,兵疫水火,更互竟兴,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肆凶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长少,贵贱乱离。”(《太平经全校》卷一至十七《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辅历纪岁次平气去来兆候贤圣行种民定法本起》)此外,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是一个佛教气氛极浓的地方,梁武帝早年出入西邸,至此行将20年(注:西邸之开设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大致不离永明二至五年间(484~487),而梁武帝离开西邸赴荆州则为永明八年(490)。至天鉴三年至少十七八年时间。),显然也会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对儒、道二教的伦理道德虽强调得较少,但其宣扬的“因果报应”及地狱等说,显然也和梁武帝早年的行为大有径庭。可见梁武帝早年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完全有悖于当时统治着中国思想界的三种主要思想体系的。
梁武帝既深受儒、道二家影响,当时亦已初步接受了佛教思想,而在永明末至天鉴初这十年时间内,他的许多行为却与这三派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这个原因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作为一个军阀和政客的梁武帝,在当时激烈的政治冲突中,为了追求现实的利益,他必然会背弃那些虚无渺茫的宗教教义和道德信念。这种情况对古今中外一些政治上的奸雄概莫能外。否则历史上许多罪恶和暴行,就未必能发生了。然而,当这些“奸雄”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道德准则而仍然付诸行动时,其内心也常常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例如:东晋的王敦在下兵石头威逼朝廷时,曾对谢鲲说:“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世说新语·规箴》);另一个权臣桓温,也曾自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晋书·桓温传》);连杀害宋文帝的刘劭,也深知自己弑父是“天地所不覆载”(《宋书·二凶传》),所以当他们做出了那些暴行以后,也常常害怕天神的责罚和鬼魂的报仇。因为关于鬼魂索命的传说,几乎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曾流行,而中国尤其盛行。翻开许多古籍,常有这种内容。如:《左传》庄公九年记齐国公子彭生向齐襄公索命故事;成公十年记赵氏祖先为厉鬼向晋景公为子孙索命;《昭公七年》记郑国伯有死后现形向杀他的人索命故事。《墨子·明鬼》下和《论衡·死伪》所记周宣王杀杜伯后杜伯鬼魂索命故事等。尤其著名的是《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魏其侯窦婴和灌夫的鬼魂向田蚡索命的故事。可见这种传说,在古代的深入人心。尤其梁武帝这样深受儒道佛三家影响的人,不可能对此全无信仰。当他因现实的利害而置封建道德于不顾,做出一些暴行或策划某些阴谋之后,内心往往存在恐惧,期望鬼神的宽恕或想依靠皈依佛门的手段,来求免去罪孽。这大约是许多“奸雄”所常有的现象,甚至民国初年那些杀人放火的北洋军阀在晚年也会吃素念佛。梁武帝的佞佛显然也属这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儒、道二家虽然也讲“报应”,讲鬼神索命,但还没有谈到免罪的问题,而佛教则公开宣扬信佛可以免去一切罪孽的问题。如《太平广记》卷一百零九引《幽冥录》中《赵泰》故事,记赵泰游地狱时问主管者:“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甚过得除否?”答云:“皆除。”这自然最符合梁武帝的心意,他晚年的竭力佞佛,盖由于此。历来有一些人认为梁武帝的佞佛是梁亡的主要原因(如唐韩愈的《佛骨表》),这当然未必正确,不过梁武帝的政治失策,往往和他早年一些行为造成的心病有关,而这些心病正是他所以要佞佛的重要因素。
四
梁武帝前期的一些行为造成他的“心病”以致影响他后来思想的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南齐高帝(萧道成)和武帝(萧赜)的众多子孙被齐明帝萧鸾所杀,他实在有重大的责任。关于这个问题,作为南齐皇室后裔的萧子显在作《南齐书》时,由于存在顾忌,所以讳莫如深,但唐李延寿的《南史》,却吐露了事情的真相。《南史·文学·吴均传》:“先是,均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梁)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这里说到吴均称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梁武帝“恶其实录”,说明他所讲的都是真话,后来梁武帝叫刘之遴加以诘问,他自然有所顾忌,不敢再说实话,以免杀身之祸,决非真的“支离无对”。吴均说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的事,在这里自然不必详说,不过事情还是比较清楚的。梁武帝早年,只是南齐巴陵王萧子伦和王俭幕下的一个小官,仅仅依靠文学才能得以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并为受到萧子良器重的王融赏识。后来出任齐荆州刺史随郡王萧子隆的谘议参军,仍不过是个七品小官。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病重将死时,竟陵王萧子良一直在旁侍候,当时王融想发动政变,拥立萧子良为帝而拒绝“太孙”萧昭业继位。王融这一行动显然不是自作主张,而是出于齐武帝和萧子良的授意。试看《南齐书·王融传》记载事情失败以后,王融对自己罪状的辩护辞,说明他在事先的准备工作是由“司徒宣敕”才进行的。司徒即萧子良,他的为人据《文选》任f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说:“进思必告之道,退无苟利之专”,像这些招募军队的大事,他自然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奉了齐武帝之命行事。再看齐武帝病重之际,并不叫萧昭业和明帝萧鸾留在自己身边,而只要萧子良一人,其用意本极明白。显然,齐武帝死前,已经看到萧鸾存在着野心(注:其实萧鸾的野心,齐文惠太子萧长懋早已看出,并对萧子良说过(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不过齐武帝当时对长懋不满,萧长懋可能来不及对他说,或说了之后,齐武帝还没听信。),怕年轻的萧昭业不是他的对手,而想让萧子良继位以杜绝觊觎。然而萧子良是一个懦怯而缺乏政治才能的人,他在长期里官居高位,却对军队毫无指挥能力,因此在这场事变中,他所依靠的都不过是一些文人。据《南史·梁本纪上》载,当时萧子良所任命的“帐内军主”有梁武帝及其兄萧懿,此外还有王融、刘绘、王思远、顾暠之、范云等。这些人除了梁武帝兄弟外,都是些白面书生,根本不会作战。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梁武帝兄弟当时正在为父亲萧顺之服丧期间,按照当时的礼制是不能出来做官和参预政治活动的。萧子良所以要破例任用他们,就因为他明知那些文人无济于事,只能主要依靠梁武帝兄弟。但梁武帝兄弟打的却是另一种算盘。他们看到萧子良的政敌正是萧鸾,而萧鸾官为尚书左仆射,兼领右卫将军,手中有一定的兵权,他又有拥护萧昭业的招牌,因为萧昭业的“太孙”名义并未废黜,有一定号召力。至于萧子良让王融所召募的兵力人数甚少,不足以对付萧鸾。于是他们就临阵倒戈,转而支持萧鸾。他这一行动使萧鸾不战而胜,旋即杀害王融,使萧子良忧惧而死,接着废杀了萧昭业及其弟昭文,公然屠杀了齐高帝、齐武帝的许多子孙,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完全夺取了齐高帝、武帝子孙的天下。在这方面,梁武帝是为齐明帝立了大功的。因此当萧鸾得势以后,就很快把梁武帝从七品的诸王谘议参军提升为四品的宁朔将军。如果说梁武帝的临阵倒戈,是因为力不足以制齐明帝而想保全自己的话,那么他后来的一系列行事则远远不能说明是为了保全自己,如《南史·梁本纪上》云:
初,皇考(萧顺之)之薨,不得志,事见《齐鱼复侯传》。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时齐明将追随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帝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惟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此并惟利是与,若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止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宝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亦吾意也。”即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游击将军,并至。续召随王至都,赐自尽。
随王萧子隆即梁武帝早年所事的南齐藩王,在齐武帝诸子中,“最以才貌见博”,所以最先被害。萧子隆之死,在海陵王延兴元年(494)九月,从此以后,齐明帝就放心大肆屠杀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子孙。这次屠杀,主凶虽为齐明帝,而出谋划策者则为梁武帝。梁武帝所以要做齐明帝的帮凶,据说是因为和萧顺之晚年曾奉齐武帝命于永明八年(490)去荆州镇压齐武帝第四子鱼复侯子响之乱。萧顺之临走时,据《南史·齐武帝诸子·鱼复侯子响传》载,接到太子萧长懋的密令,叫他在当地杀死子响,萧顺之照他的命令做了。事成后还都,过了一段时间,齐武帝因为萧子响毕竟是自己儿子,颇为后悔,有时思念流泪。据说萧顺之见到后十分忧惧,因此得病而死。关于萧顺之之死和萧子响事件的关系,大致就是这样,史籍并无更详尽的记载。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萧顺之并未受到追究与处分。即使他得病与此有关,也不能归咎于齐武帝,所以说梁武帝帮齐明帝杀害齐武帝子孙,很难用“雪心耻”来解释。再说,即使其父得病由于齐武帝,但齐武帝的兄弟和子孙,对此又有什么干系?梁武帝所以要为齐明帝出谋划策,把他们杀个干净,显然主要不在“雪心耻”,而是为了讨齐明帝的欢心,以求爬上高位,为将来夺取皇位作准备。后来梁武帝也自知此论说不通,因此即位后对自己帮齐明帝夺取皇位的事掩盖唯恐不及。《梁书·萧子恪传》载,梁武帝登上皇位后,为了拉拢萧子恪(齐武帝弟豫章王嶷之子)兄弟,还自称夺取齐明帝子宝卷的天下“非惟自雪门耻(指为萧懿复仇),亦是为卿兄弟报仇”。这种话岂非与“雪心耻”之说矛盾?不论梁武帝怎样寻找借口,但他对自己的行为是如何违背封建伦理和起码的道德标准显然很清楚。正如他的大臣沈约在临死时会想到自己劝梁武帝杀害齐明帝子孙的事受到报应一样,梁武帝自然也惧怕这些行为的报应和鬼魂索命。
如果说齐高帝、齐武帝子孙之死,梁武帝还只是一个帮凶的话,那么对齐明帝的儿子萧宝卷(东昏侯)和萧宝融之死,其主要责任就全在梁武帝身上了。关于萧宝卷,据史籍记载都说他是一个昏暴之主。这或许和梁武帝得势后过分夸大他的过恶有关。不过,像萧宝卷这样的人既为昏暴之主,杀他也许不算大过。至于萧宝融,情况就不同了。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荆州当刺史,政权实际操于他的长史萧颖胄之手。萧颖胄因害怕梁武帝手下襄阳兵之强,同意和梁武帝一起出兵反对萧宝卷。于是梁武帝就把宝融推出来做傀儡皇帝。他无权无势,更谈不上作恶,只是由于梁武帝攻克都城建康以后,急于称帝,萧宝融这傀儡已对他不复有用,反而有妨碍,所以就只能处死。可是萧宝融死后,梁武帝也构成了心病。据《南史·齐本纪下》载,梁武帝登上帝位后,曾考虑把萧宝融封于南海郡(今广州一带),保全其性命。这显然不是出于“仁慈”,而是萧宝融这孩子并不足危害自己的统治。但沈约却力主杀害,梁武帝最后听了他的话。沈约临死时,据《梁书·沈约传》载,曾“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这当然是沈约的心理反应,但当时人却信以为鬼魂索命。据云:“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梁武帝知道后,大怒,屡次派人谴责。其实萧宝融之死,沈约只是帮凶,梁武帝才是主犯,他听说鬼魂向沈约索命,显然不能不怕。这显然也是梁武帝后来佞佛的一个原因。
当然,梁武帝作为一个帝王,他的佞佛自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南朝宋以来,统治者已经重视佛教对巩固其统治的作用。据何尚之对宋文帝说:“窃谓此说,有契理奥。何者?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治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万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全宋文》28)何尚之这种想法,梁武帝也同样会有。不过,在他大事宣扬佛教的同时,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接受其某些教义。作为一个皇帝而信仰佛教,其用作用可以有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佛教有“戒杀”的教义,因此梁武帝后期也深信“报应”之说,在他的《断洒肉文》(一)中,他强调宰杀动物以供食用,会受到“报应”:“若使啖食众生父,众生亦报啖食其父。若啖食众生母,众生亦报啖食其母。若啖食众生子,众生亦报啖食其子。如是怨对报相啖食,历劫长夜,无存穷已。”如果说杀动物以供食用。尚且会受“报应”,那么杀害人的罪孽自然更大,报应自然更重。因此梁武帝称帝后,杀戮确实较宋齐两代为少,试看宋齐两代的大臣和文学之士,往往被帝王所杀,而且有的似乎还没有什么当杀的理由。至于梁武帝这方面要宽容些,大臣如王亮,梁武帝对他不满,也不过疏远而不加重用而已;沈约的道士上章,自称齐梁易代不干自己的事,梁武帝只是谴责,没有杀他。至于对不喜的文人如刘峻、吴均,也只是不加提拔而已。这些人如果在宋齐朝代就难保不被处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在梁武帝身上也未始不起一些积极作用。其次,由于梁武帝信佛以后,在生活方面较宋齐以来的君主来得节俭。《梁书·贺琛传》载贺琛因上书触怒梁武帝,受到“口敕”的斥责,在这里梁武帝大肆宣扬自己的生活节俭及不好女色。历来论者大抵认为这些细枝末节的长处,无救于政治的腐败,这自然是对的。不过,他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贪图享受,势必又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所以他的信佛,不能说一无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他身为帝王如果不能严明法制,往往因不愿对某些恶人加刑,反而造成成千上万善良百姓的痛苦和死亡。《南史·梁宗室传上》载,他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的暴行就令人难以容忍。我们知道萧正德曾经叛降北魏,后来又和侯景同谋,这些先不说它,就讲他劫掳百姓之罪就令人发指。据云:“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剥掠……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梁武帝也完全知道他的不法行为,曾斥责他道:“更于吴郡杀戮无辜,却盗财物,雅然无畏。及还京师,专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头断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闭晏开。又夺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横尸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诱为妾媵。”像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梁武帝竟然不加惩处,仅仅“免官削爵”,而且不久又恢复封爵加以任用。这种对罪犯的宽纵,实则是对百姓的残忍。这种政策,势必造成吏治的极端腐败。以致像杜弼说的“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梁武帝因畏惧“报应”而实行的“妇人之仁”,还不如某些严刑峻法、果于杀戮的帝王。因为他的“仁慈”,仅仅施诸于自己的家族和某些大臣,至于老百姓丝毫未受到好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曾指斥梁武帝在天鉴十四年(515)命康绚筑堰堵塞淮河,士兵饥冻而死的很多,后来堤堰溃决,冲了夹淮几百里见方的土地,军民死者更不可胜数。梁武帝却在哪里讲什么“戒杀放生”以充“仁慈”,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如果说对待南齐的“高武子孙”和明帝后裔方面,梁武帝早年的行为对他构成“心病”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亲人们也有严重负心之处。这主要是对他哥哥萧懿和发妻郗氏的问题。萧懿在萧顺之诸子中,其政治和军事才能很高,曾有人认为他有可能成为皇位的争夺人之一。据《南史·梁本记》云:
初,齐高帝梦屐而登殿,顾见武、明二帝后一人手张天地图而不识,问之,答曰:“顺子后。”及崔慧景之逼,长沙宣武王(萧懿)入授,至越城梦乘马飞半天而坠,帝所驭化为赤龙,腾虚独上。时台内有宿卫士为觋,常见太极殿有六龙各守一柱,末忽见失其二,后见在宣武王宅。时宣武在益州,觋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觋还都,乃见六龙俱在帝所寝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谓同侣曰:“萧雍州(梁武帝)必作天子。”
这种荒唐无稽的神话本身,自不足信,但它反映了当时人心目中,萧懿和梁武帝都是有可能登上皇位的。但事势的发展却决定了萧懿不可能成为帝王。原来萧懿在东昏侯萧宝卷初年是南齐的“梁、南秦二州刺史”,治地在今四川一带。这个地方在南朝并非军事要地,历来很少驻扎重兵,对都城建康的影响也较小,南朝以来很少叫宗室或心腹大臣出镇此地。这比起当时天下精兵汇聚的雍州(襄阳)就逊色很多。萧懿后来又被调为卫尉卿。永元二年(500)齐豫州刺史裴叔业反,萧宝卷派萧懿为刺史去讨伐,梁武帝就派典签赵景悦去劝萧懿乘机兴兵杀死萧宝卷身边的人。这其实是一个冒险的建议,因为萧宝卷当时还有实力,后来崔慧景曾以同样方式举兵,结果迅速溃灭。在崔慧景起兵时,萧懿率兵三千人入援,很快击溃了崔慧景。当时萧懿手上只有三千兵力,如果举事,可能还不如崔,而建康附近支持萧宝卷的将领还不在少数。这时梁武帝又派虞安福劝说萧懿举兵废黜萧宝卷。萧懿不从,最后被萧宝卷赐死。据《南史·梁宗室传上》载,在萧宝卷打算杀害萧懿时,有人劝他逃到雍州去,萧懿不听,说:“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对于这句话,宋代的叶适在《习学纪言》中曾从封建道德出发,对此大加称赞(见卷三十二)。其实萧懿未必是忠于南齐。当时他的实力不足以举事,而逃奔雍州又因路途遥远,所经皆萧宝卷的势力范围,所以只能坐以待毙。其实萧懿在建康,势孤力单,萧宝卷当时,早已对梁武帝有戒心,对萧懿亦有猜忌,梁武帝一再派人到建康去劝说萧懿造反,客观上是促使萧宝卷下手。不管梁武帝主观意图如何,实际上萧懿之死,和他不能说没有关系。这一点梁武帝心里十分明白。《南史·梁宗室传上》云:
懿名望功业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监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见褒崇。戊辰,乃始赠第二兄敷,第四第畅、第五第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号,迁神主于太庙。帝不亲奉,命临川王宏待从。七月,帝临轩,遣兼太尉、散骑常待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献皇后及德皇后尊号。既先卑后尊,又临轩命策,识者颇致辞讥议焉。
这一情况并非梁武帝对萧懿的感情超过了父母,而是他内心里对萧懿存在着深度的内疚。正因为在兄弟关系上,梁武帝有着“心病”,所以很影响他以后对宗室的政策。例如其弟临川王萧宏据《南史·梁宗室传上》所载,实在是罪在不赦,却屡蒙宽免。叶适在《习学纪言》中责备梁武帝对萧宏在洛口的战败“不以为意”,却又认为“至宏不反逆,而帝能容之,不失兄弟之恩,盖人情所难”,其实这纯属迂腐之见。萧宏在前线弃军逃归,使有利的战局毁于一旦,梁代的军力亦大为削弱,仅此一点,就完全应予严惩。但事情远不止此,他还派人伏于骠骑航,想刺杀梁武帝,又与梁武帝女永兴公主私通,再一次派人行刺,两次阴谋都已败露,却未受任何处分。萧宏其人不光谋害梁武帝,还到处搜刮财物,在建康横行不法,残害百姓,《南史·梁宗室传》有大量记载。可以说,梁武帝这种“不失兄弟之恩”的宽容态度,实际上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根本不值得肯定。梁武帝早年也曾屡次下诏要制止贪官“忘公殉私,侵渔是务”,“大政侵小,豪门陵贱”,但犯到他兄弟或子侄身上,却一切不问。这种厚于骨肉而薄于广大民众的行为,和早年在萧懿问题上的心病有极深的关系。应该指出,这种思想,也导致了梁武帝最终的失败。我们知道,南朝自宋以来,帝王常用兄弟子侄为各州刺史。这政策流弊甚大,在宋代就不断出现南郡王刘义宣、桂阳王刘休范、竟陵王刘诞等叛乱。南齐吸收了这教训,把诸王权力移交给朝廷任命的典签,形成了“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的局面。齐明帝杀诸王亦多用典签之力。梁武帝夺取政权后,各州刺史,全用其弟或子侄,却不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典签已同虚设。到“侯景之乱”时,上游诸镇不能并力救援都城,甚至像萧绎还阻挠别人出兵。这不能不说是梁武帝全盘否定了典签制度、放弃了对诸王的控制之故。其思想根源却正在萧懿事件使他过于重视了“骨肉之情”。
关于梁武帝的发妻郗氏之死,《梁书·后妃传》也全取隐讳不言的态度。《南史》则语焉不详,仅云:“后酷妒忌,及终,化为龙入于后宫井,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为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此文充满迷信色彩,且人死能“化龙入井”,更使人难于理解。关于这问题,倒是《建康实录》卷十的注文使我们了解部分疑问:
按《东京记》:皇城西南洛水北,有分谷渠,北,隋朝有龙天王祠。俗传梁武帝郗氏妒忌,武帝初立,未册命,因忿怼,乃投殿庭井中。众赴井救之,已化为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乃册为龙天王……
这段话虽亦有神话色彩,却说明了她乃投井而死。不过,这里有个疏漏,即说她死时“武帝初立”。其实她死于永元元年(499)八月,《梁书·后妃传》有明文。我们再看《梁书·后妃·丁贵嫔传》,丁贵嫔被梁武帝纳为妾时“年十四”。丁贵嫔死于普通七年(526),以此推算,她做梁武帝的妾正是永元元年。这说明郗氏之死因,正由于梁武帝纳妾,才忿恨投井而死。郗氏本中原高门,又是梁武帝的结发妻子,梁武帝对她不会毫无感情,所以终身不立皇后,实由此故。对此,我们还可联系《南史·梁宗室传上》记永兴公主与萧宏通奸并合谋杀害梁武帝的事。永兴公主乃郗氏所生的女儿,本不可能谋害生身之父。如果联系到郗氏的死因,这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郗氏之死,对梁武帝晚年思想,也会有影响。他称帝之初,虽仍是个好色之徒,如《梁书·范云传》所记,他抢了萧宝卷的妃子余氏;《豫章王综传》记萧综母吴氏,本萧宝卷的妃子。但到晚年奉佛后,追忆郗氏之死,不免后悔,因此他在斥责贺琛时自称“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恐亦有实情,而其原因亦与此有关。这虽主要表现在生活方面,却对政治亦有影响。例如他既立萧统为太子,却不“母以子贵”,立丁贵嫔为后,也多少给诸子侄争位提供借口,以致一度被他收养的萧正德竟向北魏自称“被废太子”(《南史·梁宗室传》)。所以郗氏之死,在梁武帝晚年也是一种“心病”,并影响到他的政治措施。
当然,梁武帝后来的走向灭亡,从他主观思想方面说,也不能完全归结为这些“心病”所造成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他的过分自信而认为没有人能与自己相比。这也是由他的时代及经历决定的。南朝初年的政坛上,尚有较多的人才,如宋武帝刘裕初起是与刘毅、诸葛长民等合作,后来其中一些人就成了和他争天下的对手,刘裕必须一一消灭他们,才能登帝位。萧道成之代宋,也有刘秉、袁粲、沈攸之等人与之为敌。他们的得天下是艰苦备尝。但梁武帝以一个小小的七品官,九年中登上帝位,可谓毫不费力。他打败萧宝卷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他登上帝位时,又逢北魏衰乱,“六镇”叛乱,对南朝不再构成威胁,所以梁武帝未免自以为天下无人能及。试看他直到侯景作乱时,还在那里自我吹嘘,说什么“是何能为,吾以折箠笞之”(《南史·贼臣·侯景传》)。但他的估计显然完全错误,竟把抵抗侯景的事务交给了屡次背叛,且与侯景早有勾结的萧正德,再加上梁代军政久已废弛,诸军与侯景作战时一触即溃,上游援军又为萧绎所阻,使侯景初起时仅有兵千人,而不到三个月,当他攻至建康城下时,竟达十万人之众。这和梁武帝平时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目空一切,显然有密切关系。即使在对待像萧宏、萧正德的问题上,其表现也是如此。《南史·梁宗室传上》载,梁武帝曾对萧宏说:“我人才胜汝百倍。”不错,比起萧宏这蠢才,梁武帝的确要高明得多,但蜂虿有毒,对不如自己的人,也未可疏于防备。其实萧宏之子正德,其才亦不胜乃父,但最终却开门揖盗,把侯景引进建康,毁灭了梁武帝的统治。可见过于自信,目空一切,亦为梁武帝失败的重要主观原因。
收稿日期:2000-08-28
标签:武帝论文; 北府兵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南朝论文; 萧子良论文; 萧顺之论文; 萧昭业论文; 萧宝融论文; 佛教论文; 鲜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