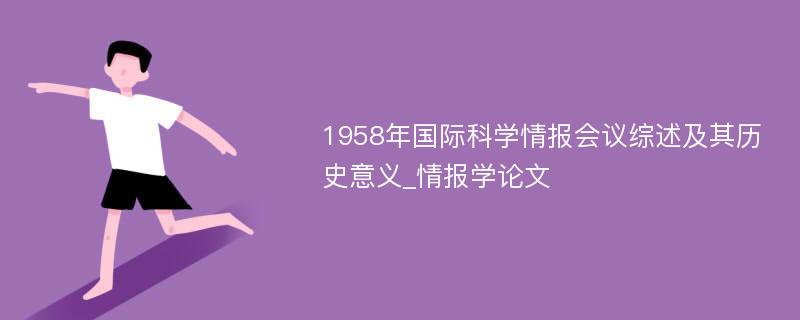
1958年国际科学情报会议综述及其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意义论文,情报论文,会议论文,科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11月16日至21日,国际科学情报会议(根据对information翻译的不同,该会议在国内也往往称为“国际科学信息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该会议由三个组织支持赞助,即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美国文献学会(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它聚集了当时情报学、图书馆学及相关领域最顶尖的专家学者,不仅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末情报学的整体面貌,更对科学界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以往国内对该会议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介绍层次,浅尝辄止。本文从会议背景、主要议题和内容及历史意义等角度,回顾并分析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1 会议的召集及其召开的原因与背景
1.1 阿尔佩托·汤普逊其人与1958年会议的筹备
阿尔佩托·汤普逊(Alberto F.Thompson,1907.12.1-1957.6.18)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在哈佛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中,作为曼哈顿区工程师兵团的陆军少校参与了原子弹的研究,随后成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技术信息服务部门(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的主管。1955年11月,他被任命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技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主管,掌管一系列研究计划以促进科技情报的发展[1]。
从1956年起,他开始担任1958年国际科学情报会议的执行秘书,筹备这个最初由米尔顿(Milton O.Lee)提出的大型会议。在他的领导和精心筹备下,会议几乎涵盖了当时与情报学相关的所有研究领域,从存储系统到回溯检索,从技术方法到理论探讨。在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机器翻译专家吉尔伯特·金(Gilbert King)看来,是汤普逊将会议从空想变为现实,他投入了许多甚至过多的热情在会议的筹备之中[2]。
虽然汤普逊在会议开始前就已经去世,但他的工作赋予了本次会议独有的特征。首先,在详尽的规划和筹备中,会议的基调、内容和方向早已被确定下来;其次,他以政府机关主管的角色组织会议,沟通连接科学领域和政治领域,使得会议具有一定程度的战略色彩。无论如何,汤普逊对1958年会议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认真筹划奠定了会议的巨大影响。
1.2 会议召开的背景与原因
首先,美苏争霸是会议召开的政治背景。早有学者提出,该会议一直暗中关注苏联科学技术情报机构和信息处理,这和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密切相关[3]。但当今看来,依然会颇为惊讶,为什么在冷战的背景中,能顺利召开如此大型的国际科学交流活动?美苏此时处于冷战的缓和阶段,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二战后科技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及对科技信息的重视——这是第二个时代背景。正如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所回忆的,“即便冷战中最糟糕的时期,科学信息的交流也没有被禁止”[4]。科学发展提出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强烈,甚至超出了国界,科学信息的重要意义也因此为社会所认识。赞助机构认为,在这一时候,组织和传播科技信息是极为关键的,而对信息的储存和检索方面的探索又是重中之重。
最后,科技信息的大量增加也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此时的情报学需要一些总结性与前瞻性并举的会议来完善其学科体系与知识系统,引领发展方向。早在1948年6月到1950年9月间,4个情报学的国际会议就曾将全世界的领先科学家、图书馆员和在书目、文摘、索引等领域的专家聚集一堂,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成果。这4个会议即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的首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及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三次相关会议[5]。它们的许多议题在1958年的会议中被继承并深入。
2 会议的主要议题和内容综述
2.1 会议的基调和形式
诚如上文所言,阿尔佩托·汤普逊的个人理想深刻地左右着会议的基调。在管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时,他就希望做到:在美国境内,无论科学家来自哪个图书馆或机构,他们都能够快速锁定并获取想要的文献;科学家不需要付出过多的时间和金钱,就能获得其他语种文献的译本;还应该通过文摘、索引、综述等出版物和专门的情报中心,保证他们能够获得研究领域内最新的成果[1]。因而,1958年的会议中,科学家的现实需求被放在首位——无论是来自小型图书馆的个人研究者,还是那些可以利用大型信息检索中心的学者[6]。
从后来者的角度看,阿尔佩托·汤普逊的个人理想与当时科技情报领域的目标几乎是一致的,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诱发了前者,已经无从考察。但他的某些主张显然有先见性,例如他曾提出,整个世界最终都将通过机器来检索和利用科技信息。
会议的形式主要是讨论、交流。从1956年春开始,非正式的初步规划委员会就以接近每周1次的频率,不断讨论和修改会议的计划和范围;11月11日,近50位业界专家齐聚一堂,拟定会议发表论文的种种要求[7]。没有新的文章在会议上发表,这些论文早在会议前两个月就已经打印出来,使得与会者不需要当场浏览,而是在讨论前就已经胸有成竹。相关的论文被分成7个主题,会议上所有的讨论都被限制在这些领域[8]。7个分会场均预定持续一个上午或下午,它们的时间并不重叠,因而与会者可以参与到所有主题的讨论中。每一个分会场大约有2/3的时间安排给本专业小组的人员内部谈论,剩下的时间里,任何人均可参与到对话之中[9]。下文将从这7个会场的主题着手,对会议进行全面的综述。
2.2 会议的主要议题和内容
2.2.1 科学家的文献和参考需求
二战以后,科技信息爆发性地增长,科学家需要通过更多、更有效的途径来获取有用的信息,但问题是如何入手?第一会场的主题即通过调查问卷、访谈、日志、个案调查等方式,调研了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家的文献和参考需求。尤具代表性的是艾莉·特努德(Elin Tornudd)的研究,她通过大约70个文献和图书馆服务的应用案例,总结斯堪的纳维亚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的信息模式[10]。类似的文章包括贝尔纳(J.D.Bernal)的《科技信息传播的用户分析》,菲兴登(R.M.Fishenden)的《研究人员发现信息的方法》,索罗·赫纳(Saul Herner)和玛丽·赫纳(Mary Herner)的《原子能信息的参考需求》等,它们揭示了不同科学家之间的信息需求和信息习惯。实证调查的结果颠覆了许多理所当然的想象。例如,面对面沟通的方式被发现是科学家之间进行学术信息搜集和交流最重要的手段,某些时候,对化学家而言,与其他学者沟通甚至比待在实验室更为重要,也占用了更多的时间[11]。
事实证明,所有科学家都会用到传统的摘要、专题论文或者综述等工具,但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专业背景、服务层次和语言等方面能力的不同,个体之间会显示出对这些工具的不同程度偏好。论文和讨论的成果使得情报学界的工作和研究对象变得明确起来。
2.2.2 文摘和索引服务的功能和效用
第二个主题是全面解析文摘和索引系统的效用。会议一致同意,速度、效率和覆盖范围等,是判断让人满意的文献服务的基本维度。在讨论环节,埃尔默·哈奇森(Elmer Hutchisson)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文摘系统:这个系统应该覆盖所有本学科和边缘学科的论文,在确保摘要明确性和索引可用性的基础上,将所有论文浓缩到极短的长度,保证所有科学家能够以任何语言阅读,并能够免费提供服务[12]。
这样一个模型仅仅是理想的目标,现实必须做出妥协。苏联著名情报学家米哈伊洛夫(A.И.Mikhailov)介绍的全苏科技情报研究所的服务,可以视为这个“理想模型”的注脚,探讨它在当时所能实现的程度;尤金·加菲尔德提出的包含所有科学领域、所有文献的跨学科索引(可看为SCI的前身),则勾画了这个模型未来的实现方案。
2.2.3 科技专论、汇编和专门中心的效用
第三个主题评价了科技专论、汇编和专门情报中心,他们在科技情报的使用和传播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某些时候甚至有着独一无二的功用。但本会场提交的5篇文章中;2篇关于综述和述评的功用,3篇是讲述不同国家的科技文献情况,并没有专门的文章论及科技专论、汇编和专门中心。因而会场主持者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在讨论开始前就阐明,这些文章是讨论的起点,但不限于此。
综述类文献的数量正在下降,而重要性却越来越强。针对这个问题,讨论后认为,如果能够形成中心化的文献服务将能有效补足对综述类文献的需求。当然,这样的服务需要配备专家和设备,并保证通畅的通讯网络。
会议中,对科技专论的定义,汇编对化学等学科的重要性及其编制的资源要求,苏联、日本等国家科技情报服务中心的相关情况等分主题都做了全面的探讨。与会者基本达成的共识是:本主题涉及的文献工具其建设的过程应当放在工业化、国家化的层面考虑,因为它们的编制和运营都将耗费大量的资源,而带来的效用也是巨大的[13]。
2.2.4 以存储和搜索为目的的信息组织
1958年会议的第四、五、六个主题都是在“以存储和搜索为目的的信息组织”的大命题下细分而成的,其中第四会场主要探讨现有系统的对比,第五会场讨论与新系统相关的设备和问题,第六会场则论及为系统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的可能性。这三部分占据整个会议近一半的时间,从过去到未来,从实践到理论,多层次探索了信息组织及系统建设的方方面面。
系统的对比推动了系统评估的研究,包括手工文献系统、基于IBM702计算机的系统等,都被列为考察的对象[14]。该部分最后的三太结论是:(1)进行更多的实验是绝对必要的。还应该以此为基础了解不同条件下系统的表现情况,有计划地提高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各项标准。(2)某些已经规划好却没有着手的实验应当在会后实施,并借鉴会议中得到的经验教训。(3)对知识分类等奠定系统运作基础的内容,要给予更多的关注[15]。
第五会场介绍了系统的新发展。更进一步来讲,探讨了许多关于系统涉及相关的议题,包括系统功能设计、分类和索引、如何充分应用已有的设备条件、自然语言检索乃至于通过用户反馈帮助提升系统的可用性等[16],识别特定的信息单元和各单元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系统建设中的主要挑战。在第六会场,关于系统设计的讨论更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如加尔文·莫尔斯(Calvin Mooers)的《检索中语言符号的数学理论》、维克里(B.C.Vickery)的《信息检索系统的结构》等。必须注意的是,当时的“系统”虽然常常指向机械化的工作,但社会化的“系统”也并未被会议忽略,例如罗伯特·法诺(Robert M.Fano)畅谈了他的“法诺之梦”,提出了利用电视终端在家中远程获取图书馆服务等大胆的想法[17]。
2.2.5 政府、专业学会、大学和企业促进情报服务的责任
第七会场讨论各种组织在情报服务方面的责任和他们的可为之事。如果要推动情报服务方面一些重要的进展,各种机构包括个人、专业学会、大学、基金会、工业组织和政府等都需要承担责任。该会场深入分析了某些国际合作的案例,例如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并针对一些实际问题,如财政支撑等进行了规划和思考。虽然现场研究了许多合作的设想,但当时并没有达成实际的协议。
各种机构承担信息服务责任的基本条件是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因而关于人力的讨论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乔治·波恩(George Bonn)对英国、荷兰、丹麦等许多国家的培训情况(包括目的、机构、设备、方法等)进行了介绍[18];而埃文斯(Agard Evans)和法拉丹(J.Farradane)甚至提出了有别于图书馆员的新型信息处理者概念——“科技情报主管”,更对其培训方式做出了研究[19]。
3 会议的历史意义
3.1 开创了情报学诸多崭新的领域
1958年会议在总结之前几乎所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很多从未触及的方向开始了新的思考。因而在实际上,它成为当今众多情报学研究领域的起点。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用户研究”的主题。国内有学者认为,本次会议“用户是整个情报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对其理解不够深入,对用户培训重视不够,情报学理论研究薄弱”[20];又有学者截然相反地提出“在1958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科学信息会议涌现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对科学家的信息使用是当时信息行为研究的主要议题”[21]。这两种看似完全背反的提法其实是归一的,诚如威尔逊(T.D.Wilson)所言,第一个分会场中13篇关于科学家信息需求的研究,在当今看来,正是第一份正式关于信息用户研究的资料汇编[22]。因为是起点,所以研究尚显薄弱,但也正因为是起点,所以它们拥有重要的意义。信息检索、存储等领域不少主题也是具有开创性的,例如相关性的研究,维克利(B.C.Vickery)的《信息检索的主题分析》等文章引发了对相关性概念的最初探讨,并成为日后相关性研究争论和探索中不可跨过的一页[23-24]。这些新领域的出现及其后的成长,塑造着我们当今所熟知的情报学、图书馆学的研究体系。
3.2 推动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的分离
信息科学产生于图书馆学,早在1948年英国首次国家科学信息会议上,“一个新型的情报(信息)收集、加工和服务行业”就已经开始形成,“这些活动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工作和文献资料服务工作”[25]。到了1958年会议前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离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有很多的实例可以证明这样一种趋势,最著名的无疑是1958年英国情报科学家学会(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s)的成立,这是第一个以情报学命名的机构[26]。
虽然会议对图书馆及其服务依然保持了相当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主要在于案例的采集和获取,更多的精力被放在情报检索和存储的研究和实现上。对相关性、索引理论、内容分析等方面的开创,客观上促进了情报学学科体系的真正成型。
然而,两者的独立和分离也只是相对的。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谢拉等的推动下,国外图书馆学在包括课程体系、研究兴趣和学术期刊等方面都开始大量吸收新兴的情报学的内容,促成两者新一轮的融合,逐渐形成了当今熟知的LI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学科[27]。
3.3 奠定了情报服务及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的基础
一些会议被历史所铭记,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往往是因为它们达成了促进人类共同合作的协议。然而,1958年会议虽然在技术、理论等方面突破良多,却并没有在协作方面取得任何实质上的进展。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源于美苏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分歧和阻碍;其次在于准备阶段并未重视国际合作的需求;最后则是出于技术与时代发展的桎梏,与会者虽然认识到国际协作是必然的,但在当时,全球性的携手并不现实,唯有从地区级或国家级的合作做起,循序渐进[28]。
即便如此,该会议,尤其是其第七个议题,让与会者对国际合作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多成果奠定其后数十年信息科学及相关领域国际协作、国际支援的基础。例如保罗·博凯(Paul Boquet)创立科技情报国际中心的建议,后来成为启发联合国科技信息系统(United N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原点[29]。
4 借鉴与启发
1958年会议是情报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研究价值。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来,很多具体研究内容早已是过眼云烟。会议对于今日的实践意义,也许更在于其组织形式及随之产生的影响力。
当前中国的情报学由于种种原因,深陷“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种情报观的窠臼,情报学研究的内容基本与信息科学的研究范畴重叠,不少学者提倡应当“将Intelligence Studies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引入目前的情报工作中,将Intelligence Studies和Information Science结合起来”,改变研究的方向[30]。这种倡议随着近年来对竞争情报等方面的重视,逐渐成为现实。但事实是,情报学的未来走向依然迷茫,如果不能通过具有影响力的事件对已有的学科体系进行改造,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还要持续较为漫长的一段时间。在这种时势下,是否能够借鉴1958年会议的形式,通过组织类似的大型学术活动,将“Intelligence Studies”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梳理并整合到现有的情报学研究体系之中呢?至少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值得考虑的。对历史的回顾和重视,也许将给学界以启发,帮助我们解决一直以来都在求索的问题:如何引领新时代情报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