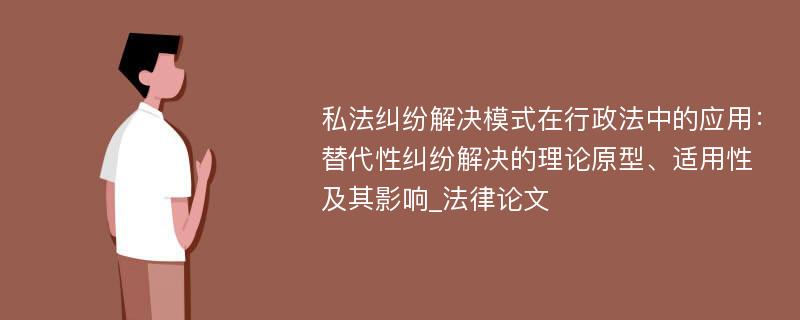
私法纠纷解决模式在行政法上的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之理论原型、妥当性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纠纷论文,私法论文,在行论文,妥当论文,原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替代性纠纷解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的广泛适用,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近数十年来最重要的法律发展之一。①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诉讼爆炸”的社会现象,然而,司法诉讼程序的高成本、低效率、过于专业化形式化、容易与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逻辑产生隔阂,以及容易被律师所操纵等缺陷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暴露无遗。②美国司法部法律政策办公室在一份意见书中指出“我们不能过于依赖法院解决纠纷,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许更为有效,它们比司法诉讼程序成本低、效率高,它们不是通过强制的途径解决纠纷,而是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更为敏感,更加能够回应潜在的问题”。③这种认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社会,传统的“司法崇拜”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人们试图以正式司法制度外的纠纷处理方式来代替法院的处理。以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模式为理论原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应运而生,并在西方各国的民事争议、劳动争议、消费者争议、医疗争议和交通事故争议等领域广泛使用。④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行政程序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将ADR引入行政过程,并取得重大成功。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行政争议解决法》(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和《协商立法法》(Negotiated Rule-making ACT),这两部法律的目的旨在授权和鼓励联邦行政机关适用调解、协商、仲裁或其他非正式程序,迅速处理行政纠纷以及制定行政规章。⑤其他西方国家如澳大利亚、英国等也在行政程序领域推行ADR。⑥ADR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
然而,按照西方法社会学主流的纠纷解决理论,ADR被认为是主要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纠纷解决机制,纠纷双方当事者地位的平等性及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能力是ADR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将ADR适用于行政法领域、用以解决公法纠纷,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本文的旨趣在于,梳理、介绍ADR在法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论原型,西方国家将ADR适用于行政法领域的妥当性,以及ADR在西方国家行政法上的适用范围和技术装置,进而关注ADR对西方现代行政法产生的影响。
一、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模式:ADR之理论原型
在法社会学的意义上,所谓纠纷是指伴随着特定秩序的违反或与特定秩序相关联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纠纷与秩序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和谐、均衡的静态秩序观不同,法社会学意义上的秩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纠纷的发生和解决,秩序的和谐与均衡历经着不断地被打破、生成的循环过程;纠纷并不仅仅是指明显或公开的冲突,纠纷也可能表现为某种潜在的状态。在纠纷发生的不同阶段解决纠纷,可将纠纷解决的模式分单方解决机制、双方解决机制和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三方解决机制)。⑦
第三者对纠纷的介入可能因当事人的要求,也可能出于第三者的主动。这意味着纠纷对周围或社会的影响达到了相当程度,从而导致纠纷被置于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之中。第三者是指区别于纠纷当事人却又介入了该纠纷过程,并能够从中立的立场给纠纷带来解决或终结的主体。根据纠纷是通过合意解决还是裁决解决这一标准,第三者对纠纷的处理又可分为“调解”(Mediation)和“审判”(Adjudication)两大类型。
作为“调解者”(Mediator)的第三者在介入纠纷或使纠纷终结时都必须得到双方当事者的同意,因而,这种方式又被称为“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⑧调解型第三者在处理纠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般来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调整双方对情况认识的差异,为合意的形成创造条件;二是对各方当事人的主张作出判断并提出解决方案;三是动员或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给当事人施加压力或影响促使当事者接受解决。⑨在审判型的第三者纠纷处理机制中,作为判定者(Adjudicator)的第三者经一方当事者的请求就可以强制性地介入并能够以裁决强行地终结纠纷,其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按照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的观点,源于西方法律传统的现代司法审判制度就是这种纠纷解决机制规范性程度的最高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法的决定过程”。⑩
上述两种第三者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社会最具稳定性和正当性的解纷机制。审判型纠纷解决的正当化机制集中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之中;而调解型纠纷解决机制的正当性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自我决定权。自立宪以来,随着司法独立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以法院司法权为核心的审判型纠纷解决机制一直是西方社会维系整个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支点,发挥着秩序正统性的再生产功能。调解型纠纷解决机制的兴起是在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法院系统在解纷过程中显露的种种弊端而采用的替代性方案,因而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一般认为,司法诉讼程序具有高成本、低效率、过于专业化形式化、容易与当事人的日常生活逻辑产生隔阂,以及容易被律师所操纵等缺陷,而ADR则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缺陷。ADR的重心装置在于调解,调解是指在第三方的推动和促进下,在保证当事人最大程度参与的基础上形成一致意见的灵活、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纠纷解决过程。对ADR的研究和认识,往往是在与司法诉讼程序的比较和对照过程中展开的。人们普遍认为,以合意解决为基础的ADR形式与以裁决解决为核心的诉讼形式在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实际发挥功能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
1.诉讼强调程序的正式性(Formal)、正当性(Due Process)和强行性(Coercive),ADR则倾向于程序的非正式性(Informal)、参与性(Participatory)和当事人的意见一致性(Consensual);
2.诉讼强调规范的适用(Norm Enforcing)和法规中心主义(Act Centred),ADR侧重于规范的生成(Norm Creating)和当事人中心主义(Person Centred):
3.诉讼以事实为导向(Fact Oriented)、在平等适用规则的前提下主张案件处理的一致性(Consistency),并具有高度的专业化色彩,而ADR则以当事人的关系为导向(Relationship Oriented),对纠纷进行个别化(Individualized)处理;
4.诉讼程序必须有公开的记录,而ADR则趋向于保密;
5.通过诉讼的纠纷处理结果往往与日常生活逻辑不契合,而ADR对纠纷的解决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修复和治愈(Therapeutic)。(11)
二、ADR适用于行政纠纷解决的妥当性
在西方国家,ADR主要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纠纷解决,如商法、劳动法和家庭法等;也适用于某些因轻罪行为而导致的纠纷解决。ADR在这些领域的适用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一种富有参与性、创造性、节省时间和金钱,并且有利于长期维护和调整人际关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般认为,ADR发挥有效功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纠纷当事人具备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是对话、交涉并寻求合意的前提;二是当事人对纠纷所涉的权利义务具有处分权,这是相互妥协、达成合意的保障。但行政纠纷似乎并不具有这两个特征,因此,将ADR适用于行政纠纷的解决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反对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疑问:(12)
首先,行政纠纷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个人相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无论是在资源、技能、获得信息方面,还是在对纠纷解决迟延的忍耐能力方面均处于劣势。
其次,许多行政纠纷涉及的利益之争超越了当事人本身的利益,而是关乎公共福利、国家利益或者公共政策,尤其在那些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行政纠纷中,如果适用ADR来解决纠纷,就存在着行政机关被掌握丰富资源的利益集团“俘获”的风险,从而危及公共利益。
第三,行政裁量权是现代行政国家履行职能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为了限制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裁量权,行政法律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公开地行使权力,但是ADR程序的保密性却允许行政机关可以“关起门来”与行政相对人讨价还价,这为行政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空间。
第四,许多行政纠纷涉及基本人权与自由的争议,在宪法的意义上,个人对这些基本人权与自由并没有处分权,因此无法在ADR程序中以妥协的方式解决纠纷,这些争议必须由司法机关依循先例作出裁判;另外,行政机关对其拥有的法定职权也不具有处分权,这也使得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失去了基础。
针对上述反对意见,支持将ADR适用于行政纠纷解决过程的一方作出了有力的辩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支持方的意见逐渐占据上风,并很快成为压倒性的主流观点,最终促成了《行政争议解决法》的通过。支持意见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ADR适用于行政纠纷解决的妥当性。
第一,ADR只是提供了一种通过合意解决纠纷的途径,不可能完全取代各种正式的行政程序。正如一位学者所言,“ADR不准备、也永远不可能取代法治。法治是我们社会的基础,而且其价值将会继续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模式。”(13)ADR至多只能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补充。因此,尽管行政纠纷当事人的地位具有事实上的不平等性,但是如果个人在ADR程序中受到行政机关的压制和强迫,则可以通过正式的行政程序寻求救济,ADR程序并没有堵死法律的救济之门。其实,在一般的私法纠纷中,当事人由于在财力、信息掌握以及社会关系等资源方面的差距,他们的地位是很难平等的,但只要有正式司法救济程序的存在,通过ADR解决的私法纠纷并没有出现“恃强凌弱”的局面。另外,正式行政程序作为ADR的“后备”救济方式的存在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行政机关被利益集团俘获、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出现。
第二,由于行政过程中广泛的裁量权的存在与行使,表明行政过程中协商妥协的可能性无处不在,与其让行政机关单方面地行使这种权力,还不如让其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获得合意以便合理地行使这种权力。(14)
第三,ADR程序中的信息保密是解决纠纷的关键机制。只有在信息保密的前提下,纠纷各方当事人才可能放心地将自己的需求和谈判底线告诉中立的第三方调解者,这使得第三方有机会获得关键性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促成合意的形成。
三、ADR在行政法上的适用范围和技术装置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ADR不仅适用于解决个案争议的行政裁决过程中,而且也适用于行政规则、公共政策、管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适用ADR的最引人注目的领域包括能源管制、环境保护等行政过程。但随着ADR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绝大多数行政领域,都存在着适用ADR作为正式裁决替代品的空间和条件。因为ADR是一个开放的、包容性的、弹性的概念,它排除任何精确定义的可能性,是一个对形形色色领域的限缩称谓。随着行政实践的发展,它所包容的不仅仅是协商、仲裁和调解,还蕴含了许多正在生长的创新和混合的机制。(15)正如ADR本身词义所隐含的意义,只要某个技术或者装置可以作为替代正式诉讼的解决纠纷的手段,就可以纳入ADR的范围之中。可以说,ADR已经成为行政法的一部分,而且其适用的领域仍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以下就西方国家ADR实践中一些比较成熟、常见的技术和装置加以讨论,尽管以下的陈述并不全面,没有也不可能穷尽ADR所有的技术和装置,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ADR过程的基本的、典型的特征。
1. 非正式的协商(Negotiation)与和解(Settlement)
通过非正式的协商、和解,最终达成协商协定(Negotiated Agreements)从来就是、而且可能永远是ADR过程中最常见的技术,90%甚至更多的行政纠纷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它的核心机制是当事人之间对纠纷的自行解决,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私了”,而是一种在“规则指导下的交易”(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Law)。因为这种装置往往是正式行政程序的一个前置阶段,在不违反公共利益的条件下,正式的行政程序往往允许当事人在行政决定作出以前自行和解。和解协议并不一定被行政机关所接收,但方案一旦被接收就成为一个行政决定自行案件。同其他类型的调解者和中立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主持正式行政程序的行政法官可以作为“和解法官”(Settlement Judge)在特定案件中被指派从事调解型的活动,但他们不对案件作任何判断和评价。Settlement Judge被称为是“一个精巧的装置”。(16)其精巧之处在于,法官既积极介入调解过程,同时又避免了法官过于积极地介入谈判调处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另外,“和解法官”对于纠纷的解决还具有以下优势:(1)避免行政程序法的一些约束,例如禁止事先接触等;(17)(2)由于他们特殊的行政法官身份,比一般的调解型第三者更加具有权威性;(3)由于他们本来是主持行政裁决的法官,因此对于待解决的案件比较熟悉,更加有利于促成当事人合意的形成;(4)作为调停者,他们在技巧和策略上具有灵活性。(18)在美国,使用“和解法官”的机关包括联邦劳工关系机构(FLRA)、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和卫生审查委员会(OSHRC),以及联邦通讯委员会(FCC)。(19)
2. 调解(Mediation)
调解是最为典型的ADR程序,如同“和解法官”一样,调解者(Mediator)完全是以一个中立的第三人的身份,对案件保持超脱的立场,以帮助当事人就其分歧达成合意。简言之,调解者(Mediator)是一个中立的调停者(Neutral go-between)和“诚实的经纪人”(Honest Broker)。调解者没有权力以强制的方式结束一个争端,也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某个观点或意见,调解者的一系列职业行为标准规定,“当事人的自我决定是调解的最基本原则。它要求调解过程依赖于当事人达成自愿的、非强制的协定。”调解者一般不受任何既定的程序、证据规则、议程的拘束。调解与正式的裁决程序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调解方式的固有灵活性。在不违反调解程序的强制性规定的限度内,调解者可以以非常灵活的方式满足各方当事人的要求,或者及时调整调解的技术和策略。调解者在调解争议时,可以在当事人双方之间进行往复穿梭外交,讨价还价,就各方意愿进行沟通;或者让他们坐在一起进行正式的真诚的沟通。无论采取怎样的程序和策略,调解者的目标都是要帮助当事人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定。
3. 安抚(Conciliation)和促进(Facilitating)
在一些较为激烈、复杂或者多变的冲突中,当事人往往很难、不愿意坐到桌前,就其分歧进行谈判,或者缺乏进行谈判的心理准备。此时,调解型第三者须采用安抚技术,试图去减少紧张和促进当事人沟通。在很多场合,调解和安抚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但至少一个区别是明确的,安抚的作用在于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促成沟通。而促进的作用与安抚类似,两者的区别在于,促进所指称的似乎是程序化的介入(例如举行会议,协调讨论),使用程序装置来让当事人坐到一起,促使他们进行谈判和和解,但并不积极地介入当事人的立场或观点的实质部分。
4. 中立的评估(Neutral Evaluation)或者早期中立的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和事实发现(Factfinding)
中立的评估或者早期中立的评估是指调解型第三者作为一个中立的事实发现者,以其拥有的所需要的实体技术,来对当事人案件的是非曲直加以评判,这类程序通常运用于争议早期。第三者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告诉当事人有关他们纠纷的感受,并对相关的实体问题作出评价,以促成当事人调整自己的立场和策略向有利于谈判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评判通常是书面的,没有拘束力的。而事实发现更为强调第三者的技术专长,第三者往往是有着相应技术专长的一个中立人或者一个中立小组。由他们对所争议事项的事实认定作出建议。他们通常会将事实认定结论以非正式的方式告诉各方当事人。之后当事人之间可以继续进行谈判。当争议是围绕着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或者其他专业领域的问题展开时,中立专家的事实认定结果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Rule706条款已经允许联邦法院主动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申请使用专家证人,以促成案件的和解。
5. 微型审判(Mini-trial)
“微型审判”一词可能多少会招致误解,从字面上看,它更像一个正式的裁决程序,但实际上仍然属于ADR的一种程序装置,其特点在于将已经进入正式行政程序乃至法院的争议转移到当事人自己手中。这种程序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争议各方都非常了解对方的立场、依据以及自己的弱点。这种相互了解的达成有时需要通过听证会背景下各方的陈述。各方当事人是在高级官员面前作陈述,官员被授权听取陈述。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前置的、结构化的处理过程。当各方当事人就有关纠纷的认识达成一致时,就将案情的一个高度简缩版本交给高级官员(有时有中立者辅助),官员能够较为全面地审时度势,对各方的立场和地位作出判断,以便提供一个更为现实的谈判基础,然后由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协商过程秘密进行,不作案卷记录。(20)微型审判是一种十分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美国,适用这种程序的机构主要包括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公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内务部、能源部、联邦原子能委员会等,主要用于解决政府采购契约和环境争议。
6. 协商会(Conference)
协商会是非常容易被人们遗忘的ADR技术,但它却是一种经常使用的老技术。在举行听证前或者是其他会议前,由行政法官(或者其他主持听证官员)召集协商会,寻求探讨和解的可能性。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授权召开协商会来解决或者简化问题。各个行政机关的程序规则一般都以一成不变的语言,授权行政法官和其他听证官员为了解决或简化问题而召开协商会。此外还有几个机关对调处协商会作了明确规定。
7. 仲裁(Arbitration)
仲裁者的地位类似于法官,但却是由当事人自己选择的私人裁决者,他们往往是与争议事项有关的专家。仲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高度司法化的仲裁,另一种是非正式的协商或讨论的仲裁。前者大多是强制性的、有约束力的;后者往往是建议性的、自愿的。对于有约束力的仲裁,当事人可以放弃司法审查、限定审查范围或者保留完整的司法审查权利。(21)严格地说,高度司法化的仲裁已经不属于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的范围,而是属于裁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但在客观上它仍然发挥了对法院司法裁决的替代作用,所以一般意义上人们还是将其归入ADR的范围。
从上述ADR的各种技术装置可以看出,它的整个过程覆盖了实质性的纠纷产生以前的各种预防、缓和、安抚机制。这是一种专注于纠纷的实质解决的机制。而在诉讼的解决纠纷机制中,裁判一经作出即认为纠纷在法律意义上得到了解决,但法律上纠纷的解决并不能等同于纠纷的实质解决。
四、ADR与“回应型”的公共行政体系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特把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法律现象分为三种类型:“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22)这三种类型的法与其说是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毋宁说是按照理想型(Ideal-Type)方法建立起来的用以分析和判断同一社会的不同法律现象的工具性框架。按照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法学传统之上的现代西方法治具有典型的“自治型法”的特征:建立了包括司法独立、正当程序以及法律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的法治制度;通过设置一套专业化、相对自治的法律制度把决定的大权限制在一定的职能范围之内,其中公正而合理的程序是法的核心;整个社会的秩序以普遍性的规则为准绳,政治和法律、立法与司法之间泾渭分明,在司法独立原则下,法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自治型法”过于强调法律自身的价值而主张法律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变革只能通过既定的政治渠道,不能运用执法机关裁量的方式。这种类型的法把过多的能量消耗在维持法制的纯洁性、追求形式正义方面,而牺牲了诸如实质正义等其他目标的实现。具有“自治型法”特征的行政法无论在形式或是内容上都比较单一,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这种类型的行政法表现为两种形态(Modality):
第一,行政权力以命令的方式运行。与行政权力的这种运行方式相对应的制度设置是各类政府机构(包括地方政府机构、公共部门),权力的运作过程具体表现为政府的立法过程、政策制定过程和次级规则制定过程以及裁量行政,权力运行具有强制性、决定性、单方性以及追求效用性的特征。(23)这就是大陆法系行政法上所谓的“高权行政”方式。它亦可能在“威权政体”下发挥作用,并且是“压制型”法中行政权力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作用方式。在“自治型法”中,“高权行政”也是行政权运作所不可缺少的形式,但它的运行是“在法律之下的”、缓和的,尤其是行政权的强制功能,只在某些迫不得已的、势在必行的情势下发挥作用。
第二,个人权利、合法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实现。澳大利亚学者Laurence Boulle认为,行政法这项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行政法上的“装置”的运行——通过某些公共机构的权衡或审查,以实现那些可与行政权力对抗的个人权利或者个人的合法期待,这些从事权衡或者审查行政权力的公共机构可能是裁判所、保护权利的机关,也可能是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法院。它还应该包括民间的裁决机构、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权利保护机构、权利法案、调查委员会和裁判所等制度设置。其运作过程则包括裁判、事实认定、规则适用、质询和调查。这个过程具有决定性、强制性、二元对抗性和形式主义、法律教义主义以及可直接执行和公众性等特征。司法独立的存在是其中关键性的制度保障。(24)
“自治型法”下的行政法之重心在于:用司法审查禁锢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要求行政权的运行遵守各种法律程序,而法律程序的目的则在于促进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的准确性、合理性和可审查性,行政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合法期待集中于自由和财产方面的利益,(25)具有鲜明的形式主义“硬性法治”特征。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变——社会的信仰危机、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犯罪激增、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导致了国家正统性的削弱,于是出现了用“软性法治”取代“硬性法治”的呼声。“回应型法”的提出,恰恰是对这种社会变革呼声理论上的回应,它试图为社会变革提供一种规范性的模式。这种模型的基本思路在于:使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统合于制度之内,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在维护普遍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26)“回应型法”的一大特征是:在维系法的整体性的前提下,使法律制度具有开放性和弹性,从而促进法制的改革与变化,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准则和价值。这种法制能够回应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并成为社会调整和社会变化的能动性的工具。
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社会的ADR运动正是以“回应型法”为理论原型的“软性法治”改革的具体表现。ADR实践试图削减法院在纠纷解决中所起的作用,不受法律形式主义的羁绊,扩大当事人的参与权和自我决定权,以追求纠纷解决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实质正义。通过ADR实现的正义乃是“共存的正义”(Co-existential Justice),区别于通过诉讼实现的“争吵的正义”(Contentious Justice)。(27)这种比诉讼制度更具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诉讼的功能,成为另一种缓解社会压力的机制,(28)并被认为在未来的数十年将对法院的司法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29)而ADR在行政法领域的适用则被认为有可能引起行政法的结构性转变(Structural Change)。迈向“回应型法”、“软性法治”的行政法律制度必须构建一个能够支持公平原则、理性原则、平等原则、适当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公共行政制度。这个制度提供的责任和控制机制、审查和监督机制、开放和磋商机制能够促进上述原则的实现,并导致行政样态的多元化。而以ADR这种特殊制度解决与政府之间的纠纷,使人们更容易得到官方信息,而在行政程序方面则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也促使行政机关运用各种信息的、财政的、程序的方法以实现实质正义。总的来说,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具有“回应型法”、“软性法治”特征的行政法意味着一个回应型的、可靠的、负责的公共行政体系的存在。而这个公共行政体系的完整构型与ADR运动的兴起是无法分开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ADR实践的发展使得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向“回应型法”发展的趋势,并发展出两种新的行政法的运作形态,即“回应型”的公共行政体系体现为四种典型的形态。
首先,传统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高权行政”形态在“回应型”行政法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已处于次要的、退居二线的地位,行政权力主要以其它的非强制命令的方式发挥作用。以实现个人权利、合法期待为终极目的,以司法审查制度为核心的法律“装置”仍然是整合法律秩序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它们发挥的功能和作用被削弱。ADR的目的在于实质性地解决纠纷,它的整个过程覆盖了实质性的纠纷产生以前的各种预防、缓和、安抚机制,这就必然引起整个行政过程中行政权作用方式的“柔性化”、“弹性化”。ADR在行政法上的广泛运用也必将弱化司法审查在整体纠纷解决方面的功能和作用。(30)
其次,以利益为基础的问题解决机制。(31)这是“回应型”公共行政体系中行政法的一种新的形态,即为了克服传统的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ADR)。ADR技术在委任立法、政策制定、具体纠纷解决等行政领域的广泛适用已经使得它成为西方行政法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ADR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强调由卷入纠纷的行政机关和私方当事人通过合作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协商以解决纠纷,它的关键性机制在于当事人的高度参与和非对抗性,以及他们之间以未来为导向的,激励性的、协调关系为中心的建设性的交往和商谈。ADR技术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以一致性意见为基础、折衷性、规范的生成和参与者中心主义等特征使得现代行政法能够积极地、能动地回应新的社会问题和需求,在处理纠纷、社会危机方面也更为有效。同时,ADR技术的开放性也为在实践中探求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准则和价值提供了契机,并赋予行政法以自我修正的能力。
第三,预防性介入形态。(32)这也是“回应型”公共行政体系区别与传统行政法制度的新的表现形态。在回应型公共行政体系下,预防性介入不仅是指行政机关的预防性管制活动,更为注重的是,行政机关为了提升行政决策的满意度、防止政府管理中出现不当或者不负责任的现象,作为一个公共的、咨询性的、开放的机构,常规性地开展向公众听取意见、提供指导和帮助、进行舆论测评、接受和处理民众的投诉和抱怨等活动。这是一种行政权的“柔性介入”,旨在构建一些与公众进行常规性的交流、广泛地提供参与机会的机制,并且通过这种机制获取信息,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避免公共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冲突、混乱或者危险。它具有预警性、授权性、诊断性、教育性和共同选择性等特征。公共行政体系中预防性介入形态的产生是ADR在行政法上推广的结果,如果在社会整体层次上将ADR视为解决行政纠纷、整合秩序的基本理念,而不仅仅是处理具体行政纠纷的技术,那么,预防性介入形态的产生对于整个行政法秩序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这也赋予了现代公共行政体系更高的回应性和能动性。
注释:
①L.Ray,Emerging Options in Dispute Resolution,75 A.B.A. JOURNAL 66 (June,1989).
②See:Laurence Boulle,ADR Applic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aw,Acta Juridical,1993.
③Office of Legal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Path to Justice:Major Public Policy Issues of Dispute Resolution(1984).
④Philip J.Harter,Dispute Resol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The History,Need and Future of a Complex Relationship,29vill.L.Rew 1984.
⑤参见王锡锌:《规制、合意与治理——行政过程中ADR适用的可能性与妥当性研究》,载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
⑥See:Valerie A.Sanchez,Towards a History of ADR:The Dispute Processing Continuum in Anglo-Saxon England and Today,11 Ohio St.J.on Disp.Resol.2 1996.;Laurence Boulle,ADR Applic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aw,Acta Juridical,1993.
⑦有关“纠纷三阶段”理论参见Nader,L.,&Todd,H.F.,ed.,Introduction,The Disputing Process:Law in Ten Societies.N.Y.Columbia Univ.Press.1978,14-15.王亚新教授对这一理论作了非常准确的中文介绍,参见王亚新:《纠纷,秩序,法治——探寻研究纠纷处理与规范形成的理论框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参见[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⑨同注⑧,第85-99页。
⑩同注⑧,第14-17页
(11)同注②。
(12)Fiss,Against Settlement,93 Yale Law Journal,pp.1073-1075.
(13)Meyerson,Bruce E.,&Cooper,Corinne ed.,A Drafter's Guide To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p4.,America Bar Association.
(14)同注⑤。
(15)同注①。
(16)Joseph & Gilbert,Breaking the Settlement Ice:The Use of Settlement Judges i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3 ADMIN.L.J.571,573 (1989-90).
(17)同注(16),582-584(1989-90)。
(18)Joseph & Gilbert,Supra Note at 585-86.
(19)See:Erin Parkin Huss,Note:Response to the Experimental Role of Settlement Judges in Unfair Labor Practice Proceedings,37 ARIZ.L.REV.895 (1995).
(20)See:Davis and Omlie,Mini-trial:The Courtroom in the Boardroom,21 Willamette Law Review,pp.531-532(1985).
(21)See:Alfred C.Aman and William T.Mayton,Administrative Law,West Group(1992),P.292.
(22)See:P Nonet &P Selznik Law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Towards Responsive Law(1978).
(23)同注②。
(24)同注②。
(25)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页。
(26)参见季卫东:《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的法》(诺内特 塞尔兹尼克著,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代译序”。
(27)“共存的正义”(Co-existential Justice)、“争吵的正义”(Contentious Justice) 这一用语,参见M Cappelletti,Access to Justice a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w and a Practical Program for Reform,(1992)109 SALJ34.
(28)See:R Imbrogno,Using ADR to Address Issues of Public Concern:Can ADR Become an Instrument for Social Oppression? 14 Ohio St.J.on Disp.Resol.1998-1999.
(29)See:Robert.A.Baruch,Alternative Futures:Imagining How ADR May Affect the Court System in Coming Decades,15Rev.Litig .1995-1996.
(30)同注②。
(31)同注②。
(32)同注②。
标签:法律论文; 行政法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司法调解论文; 行政处理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行政诉讼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