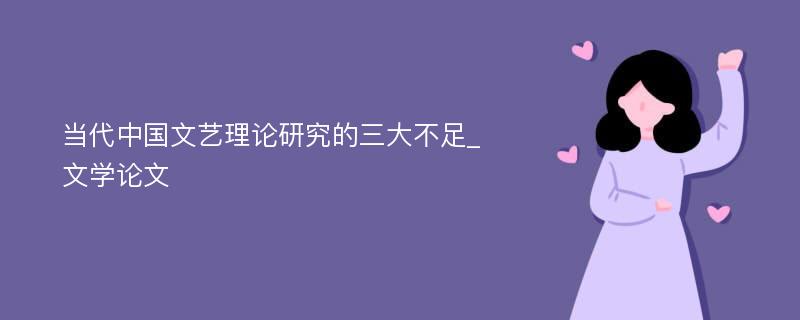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三个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缺失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否定主义文艺学的视野中,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不仅存在着从概念命题到思维方式依附西方的问题,使得不少中国文艺理论家停留在“中西拼凑”的低程度创新水平而无焦虑感和警醒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对理论的基本理解和运用上,很多研究者不仅深受中国传统“博学”、“笃学”观念的制约造成理论的“知识性沉迷”,进而因“中国问题意识”的匮乏,在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思维方式上,也很难有中国式的推进。本文所列的三个缺失,便是其中隐而不察的被遮蔽问题。
缺失一:理论作为“知识”遮蔽了“理论是一种能力”
近年来,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时,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的话题除了跟着时代的变化做“西方文论的知识性转换”、“西方问题的现代转换”外,也不会提出独特的、能切中我们文学要害的问题。于是,马列文论研究会议从“劳动异化”转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异化”的介绍和讨论,文艺理论会议从“主体论”转化为“主体间性”、从“文学中心”转化为“艺术生活化”,就成为中国文论会议的“生存性质”;最多的是“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论现代化、民族化”这些命题的会议,很多学者也不能突破“融会”、“互动”等既定思维的制约,致使其结论要么大而无当、要么就难以触及“怎么融会”、“融会成什么”、“大而全的融会究竟能解决什么中国文学问题”这些人人心中所有的疑问。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师学者只能向学生传授各种理论知识,介绍他们读各种“必读书”,却不能教会学生进行理论性思维的能力,所以,这些本科生、研究生走向工作岗位后,不是很快遗忘了所学的理论知识,就是组成了这样的不会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的理论界之后备军。如果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比如王朔),这些现成的理论知识可能都是没什么用的,大家就会不是谴责其“不学无术”,就是越发产生对现有知识的依赖。
所以我想说的是,理论的这种“知识性异化”,就把理论在根本上是一种“能力培养和训练”的性质遮蔽了。这种能力作为一种“过程”,我以为至少包含这样三个阶段:
一是真正的理论家,应该能够提出让现有的理论尴尬的“问题”,而不是依据现成理论知识去“看问题”。无论是爱因斯坦暴露牛顿“绝对时空观”的局限,还是阿多诺发现“概念同一”的虚假性,作为尚未理论化的“潜在的、独特的问题意识”,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理论家必须独创性地提问题,而不是把前人、他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由于前人提的问题多半已经有了知识性的回答,我们就很容易连这种回答也接受下来。比如“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必然伴随“人是理性的动物”等多种知识性回答,从而不需要我们再对此进行质疑,这样,“他人的问题”在本质上就仍然是知识。所以,当西方文论家怀疑理性、怀疑本质思维、怀疑概念和结构的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尊重、学习”这些理论,但却不能作为我们理论建设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代文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现代性的文学本质观,建立起由这样的本质派生的与传统文论关系的“理性”,所以我们要反的那种西方的理性,在中国只是名存实亡的存在——中国传统文论,用的也不是西方式的本质思维。特别是:中国当代文论家,也不能以古人的视角、立场、观念来“提理论问题”。比如依据“重义轻利”来说今天社会“欲望横流”,依据“文以载道”来说今天的“文学身体化、自娱化”的轻飘……这样的“问题”,只能导向对现有理论知识的“捍卫”,而不可能导向理论知识的“原创”。如果我们不会提出让现有理论均感到“尴尬”的问题,自然就不可能有理论上的重大创造。
二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只能用自己所提的问题,来暴露和发现现有理论知识的局限,即分析现有的理论为什么不能解答“我的如此问题”——海德格尔正是通过他对“在”的独特理解和体验,暴露出西方认识论知识系统遗忘他所理解的“在”之局限的。所以理论作为“能力”,是批判现有知识面对新问题“为什么无力、无力在哪里”的能力,而不是以“颠覆”、“告别”既定理论为目的。然而,在批判问题上,中国文论界除了做“正确”、“错误”、“偏激或不全面”、“辩证或不辩证”、“保守”、“先锋”等判断外,就很少见到中国文论家对西方文论做有深度的批判性分析。因为用“激进”、“保守”、“正确”这些词,根本无法说爱因斯坦和阿多诺,也无法说福柯与哈贝马斯,甚至无法说孔子和老子。另外,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思潮的演变看,无论是当年的“Pass刘再复”,还是“晚生代”的“断裂写作”,抑或是今天不少学者所谈的“告别艺术中心化”,依我看均与这种“非理论性批判”的“大批判”文化有关。“大批判”是以一种现成的观点去“颠覆”另一种现成的观点,“颠覆者”只是在做“观念取舍”,而不需要自己去发现“新的理论问题”。在此点上,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演变,同样是不具备“理论批判”意义的。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理论采取的“局限”分析的态度,强化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科学技术的欺骗性,与马克思的理论构成彼此尊重的存在,是为我们塑造了真正的理论批判的典范的——哈贝马斯并没有“告别”和“颠覆”马克思的理论。
三是理论批判作为能力,最后必须以建立自己的理论命题、范畴或思想内涵为目的,否则也不是真正的理论批判。这意思是说,理论作为能力,最后必须通过理论思辨与理论批判,生产新的观念和思想,而不是沿袭、承传和捍卫既定理论观念。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论,不是沿袭“实践”、“劳动”、“意识形态”、“活动”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论范畴,就是只能依附“结构”、“解构”、“形式”、“自由”、“陌生化”、“对话”这些西方现代文论范畴。也有学者受马克思“美学的—历史的”统一学说的影响,以融会思路提出“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等命题,显示出中国学者在理论创造上可贵的努力。然而,概念之间的冲突隐含的问题,很可能使这样的努力难以介入实践。比如,在我的理解中,“审美”是以其个体创造对“反映”和“意识形态”的“穿越”、“突破”,并使优秀的作品难以被“反映”和“意识形态”说明,我们如何说这种创造也是一种“反映”和“意识形态”呢?这样说又能解决怎样的“文学问题”呢?如果“反映”和“意识形态”被等同于“文化”这样的大概念,也就失去了自身的规定性。当然,能力作为提高的过程,开始要求理论家必须建立自己的概念范畴,可能不一定现实。但如果我们能对既定的概念作赋予自己独特的理解的努力,这同样可以视为理论能力的初始显现。十余年前,当我对“否定”和“存在”这两个概念分别作“本体性否定”和“个体化理解”① 的界定时,也正是这样努力的开始。今天,像学者赵汀阳对“天下”② 这个概念划分的三个层次,也同样是这样的努力。我感觉遗憾的是,文艺理论界这样的努力尚不多见。
缺失二:“文学是什么”遮蔽了“文学性程度”研究
由于上述理论能力的贫困,这就造成中国当代文论在文艺理论基本理论的研究上,过于局限于中西方文论已有的文论命题,而一旦这样的命题没有什么作用,不少学者就很容易回避基本理论的研究。如果说,艺术的形式本体论、解构论和艺术的非中心化,等等,是西方文论家根据其时代变化提出的新的文学命题,那么,中国当代文论除了跟着西方文论命题进行转换,其“文学是什么”的研究则始终如一。或者,就是通过放弃文艺理论研究来放弃这个命题——但“放弃”决不等于“改变命题”,如果回到文艺理论研究上来,大家就还是会回到老命题上来。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文艺理论研究“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从西方“摹仿”到“表现”再到“形式”、“解构”,我们在一般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西方文论家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解答,自然中国的“言志”、“载道”、“缘情”、“人学”、“劳动”、“活动”等也如此。只要存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文学是什么”、“文学不是什么”这些命题就永远不会过时。然而,我之所以说“文学是什么”遮蔽了“文学性程度”,是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一直没有关注我们的文学为什么在“政治”与“市场”、“中心”与“边缘”之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没有思考为什么我们各种文学观都倡导过,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程度依然很低这一问题,更与我们对“文学性”与“文学”这两个概念的混淆有关。长此以往,我们在文论建设上,当然就很难找到可以面对“自己的问题”的理论突破口。
首先,我认为,文学是为政治服务还是应该脱离政治、文学是顺应市场要求还是应该保持清高、文学是中心化好还是应该甘于边缘,这些之所以是文学理论中的“假问题”,是因为关心政治、写政治内容、尊重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学,有好的文学,也有差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或尊重政治要求,其实并不是产生优秀文学的真正障碍。真正的障碍在于我们能否以新的文学性思维“穿越政治”。换句话说,“脱离政治”、只写自己的个人感受、日常生活,同样也不见得就会创作出好作品,所以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与《木子美日记》就文学价值差异很大,因为文学创作比的不是“胆量”。同样,文学中心化,文学再被重视,也很有可能出现的是“大跃进民歌”那样的文学现象。而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哪怕时代将文学大军淘汰得只剩下几个作家,那里面照样可以出“村上春树”这样优秀的作家。所以文学受不受重视、作家多不多,基本上也与文学自身的问题无关。而当昆德拉、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在中国产生热门效应的时候,当全国有一亿多人晚上10点都在看韩剧《大长今》的时刻——那一刻,文学艺术是中心的呢还是边缘的呢?很可惜,“文学是顺应政治还是脱离政治”、“文学是写大叙事还是日常琐事”、“文学是关心底层还是不关心底层”这样的命题,几乎接触不到这样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就可以解决中国文学受政治、市场、重视程度下降带来的困惑,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任何生存环境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良好感觉——这显然是一个“很中国、很当代”的文学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弥补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问题脱离的“弊病”。
其次,文学是模仿、表现、形式、解构、载道、缘情、人学这些“文学观”,只是不同文化、时代、时期文学应对文化要求的“结果”,但无论是西方文论还是东方文论,均把在这些文学观念下生存的文学实现自身的程度,作为文论研究的盲点,这就产生如下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引进过西方各种文学观,作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观的准备,这种理论资源当然不可或缺。然而,20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学在走向现代化,为什么文学精品、文学大家不仅与明清“四大名著”相比很难乐观,而且与近一百年的西方文学相比,也同样不很自信呢?我以为,任何外在因素都不是我们写不出好作品的主要原因,而是优秀作家突破各种文学观制约和外在约束、实现自身的“文学性程度”问题,没有在文论视角下引起重视——这一缺陷,必然与中国当代文论、文学批评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满足在“知识”和“方法”上引进西方的“原创力”贫困相关,也必然造成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脱节,文学理论越来越成为一种“经院化的知识”。这一缺陷,如果在一直强调创造性和个体性的西方文学中,还不是很重要的话(尽管西方的后现代越来越暴露“批量复制”的问题),那么,中国文论就应该认真对待。比如,像“文学是人学”,通过强调文学写人性、人情,来突破“左”的工具性文学观对文学的扭曲,以恢复文学“以情感人”的功效,也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而,文学是通过形象思维打动人的,只是文学区别非文学的“基本标志”,如果在“感人”后面有“教化”和“启迪”之别,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就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很多学者却容易满足“以情感人”而忽略这样的研究。这种忽略,使得中国当代作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昆德拉、村上春树这样作家差距的原因,成为我们文艺理论说不清的东西,必然会纵容中国文论家与文学家依附中西方现成的世界观、文学观而不自觉,长此以往,也必然会制约我们的文论、文学产生重大的突破。
再次,我之所以提“文学性程度”而不提笼统的“文学性”概念,是因为近年开始被重视的“文学性”研究,一直是在与“文学是什么”、“文学特性是什么”混淆状态下的研究,而没有把“文学”与“文学性”区别开来。无论是西方的乔纳森·卡勒把“文学性”理解为一种“文学属性”(即我们为什么把一种东西界定为文学)③ 还是特雷·伊格尔顿说文学无法定义④,或是中国学者依附他们理论对“文学性”的解释⑤,在我看来均存在这种局限。即:一方面很多学者依据文学观的不断变化而认为“文学性”无法定义,却忽略了与经典作品关联起来做这样的追问:我们是依据什么把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说成经典的?我们又是因为什么认为经典应该是有很强生命力的?甚至永恒的?这样的追问,可以把“文学性”与使经典成为经典的“稳定性”关联起来。即“文学观”可以不稳定,但“文学性”则是一种稳定的评价。很可惜,也许是我寡闻,进行这样区别的研究尚不多见。另一方面,很多学者习惯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中谈“文学性”,将“文学性”与“形式”、“形象”、“生动性”等概念等同起来,从而忽略了“文学”与“好文学”的张力关系,是“文学性”更为重要的显现场所。即从“非文学”到“文学”再到“好文学”,“文学性”应该是一个“程度”概念,因为我们说一部作品“文学性强”,多半是说这是一部“好作品”。关注“文学性”问题,不仅仅是解决“文学特性”,而且还应该解决“好文学的特性”,并搞清楚其间的“张力关系”。我想,如果“文学性”不落实到这样的问题上来,谈“文学性”就会最后落入谈“文学是什么”的结局。这样,就不能通过我们对“文学性贫困”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原创性建设找到突破口。
缺失三:“二元对立思维”遮蔽了“二元对等思维”
在中国当代文论中,若从思维方式着眼,多数学者使用的均是由“一元论”支配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以“冲突”、“克服”、“消长”的否定观,形成二元之间不对等的关系,从而以一方支配另一方构成“对立”的不平等张力,故曰根本上是一元论。诸如“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本质与现象”、“个人与群体”,等等,而“新与旧”、“善与恶”、“美与丑”等,也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我想说的是,上述所有思维,均不是文学自身的思维,而是我们习惯了“文化支配文学”的历史积淀后,逐渐以此来思考文学问题所造成的。尽管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来说,理解这样思维的合理性是必要的——刘勰倡导的“宗经”思维就是其文化渊源——但我仍想说,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个命题下,如果我们的文学的思维方式依然还是以文化性思维来支配文学思维,以这样的思维来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这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具有创造性品格的。
这也就是说,“文学本质主义”、“文学中心主义”的思维,在根本上也不是文学走向自身的思维,而是文学长期作为“工具性存在”或“对抗性逆反”的结果——前者是文学假文化之虎威的结果(如阶级斗争文学),后者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抗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性形象(如法兰克福学派崇尚的非理性文学)——其功能,依然是文化性、现实性的。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以非理性艺术来“对抗”理性文化,其功效就不是唤起我们对艺术的艺术魅力的欣赏,而是产生批判、改变理性文化现实的冲动,而当我们又不能完成改变理性文化现实时(改变理性文化必须设计出新的文化模式而且具有可行性),这种冲动就转化为破坏性的颠覆。一旦艺术产生的是如此效果,文学就再一次充当了“感性生命的文化”的“工具”。虽然“感性”在马尔库塞这里有“充分调动形式和质料的潜能”这样特定的内容⑥,但在中国语境下,还是很容易与中国传统就有的“缘情说”合谋。这种合谋,很有可能会阻碍我们对“情与理”命题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
因此,我提出建立文学自身的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学独立”,就不是使“文学中心化”,也不是使“文学对抗化”,而是形成文学与文化“不同而对等”的关系,即通过建立新的二元论,来改变既定的二元论——这是文学能建立自己的思维方式的前提。所谓“对等”,是以文学的“性质”和“功能”均区别于文化为前提的。这种区别是指:文学属于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既然如此,这个世界就不应该参与现实世界的改造和发展等工作,而是通过打动尤其是启示人而给“不得不”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以“心灵依托”,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人生的平衡感”。为什么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只能“平衡”而不能“对立”和“冲突”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性质的事物均有利有弊,以自己的“利”来统摄对方的“弊”,是达不到统摄效果的。如以文化的现实性来轻视艺术的软弱性,就是如此——因为艺术就是以其现实的软弱为其生存性质的。反之,艺术也不具备现实教化的功能——越是优秀的艺术,“教化”功能越弱就是一个说明。所以,艺术性的“启示”是给人以心灵依托的,而不能用来进行现实性的实践,因此,《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不能参与现实性的反封建实践,一旦参与,他就是一个无能儿。所以越是好的作品,其现实功能就越弱,而心灵启示的功能就越强。
在现有“对立”的二元思维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必然产生“文学中心”还是“文化中心”的思维与话题。在“不平衡”的二元关系中,文学常常被文化“越界”作为工具服务其目的,“艺术魅力”是作为“手段”看待的。即二元对立思维也讲艺术魅力,但这魅力常常是被作为达到更好的“教化”效果来对待的。反之,文学也常常“越界”参与现实性的文化改造活动,并因触动和改变了现实以为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这就是像“抗战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中的一些作品(如《屈原》、《伤痕》、《乔厂长上任记》)被推重的理由。所以,“文学中心化”是以文化力量显示自身的,而不是以文学打动和启示为生存目的的,因为以“打动”和“启迪”为性质的事物,在功利的现实中,是不可能“中心化”的,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的,甚至很难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以“消、长”、“有、无”进行运思的二元对立思维,我以为不能用来处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更不能用来处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和谐”关系。由于我对“天人合一”的“和谐”已做了“不同而并立之平衡”的现代改造⑦,所以,不同、并立、平衡,就成为我对“文学与现实”、“艺术与文化”关系的现代性理解和设计——我把这种理解和设计,称之为“二元对等”思维。
以此思维为基础,文学就可以在“尊重文化”的前提下,开始自己建立另一种世界的穿越性努力。“尊重文化”是作为区别“依附文化”、“对抗文化”、“脱离文化”等传统思维提出来的。否定主义文艺学认为,只有“尊重”才能建立“平等”关系,而只有“平等”,才能保证自身的独立品格。在传统文化中,“依附”和“对抗”都是“不平等”所致,而“脱离”则是害怕“依附”和“对抗”的结果——一旦与文化、现实政治打交道,“脱离者”还是很容易选择“依附”或“对抗”。在我看来,文学一旦“尊重文化”,就可以平静地将所有的文化现象作为自己创作的“材料”,从而为自己世界的“丰厚性”提供了保障;而文学如果“依附”或“对抗”文化,便只能取“一种文化”来拒绝“另一种文化”,这正是儒、道、释在中国循环的道理,也是我们走不出“中体西用”怪圈的道理。在“尊重文化”的思维下,所有中西方的文化都只是材料,作家只能以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作为自己的价值依托,用各种“既定材料”来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这样一个过程,我理解为是文学对文化的“穿越”。“穿越”在我的理论中,是作为区别于中国传统的“超脱现实和文化”与西方“超越现实和文化”⑧ 的思维提出来的。 其基本含义是: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所有被过去二元对立思维所划分的内容,本来其实都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划分,因为它们都是等待作家的创造性的想象、体验来“改变”的“材料”。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或成功的文学艺术创作,就是使读者很难用上述二元对立思维去进行把握。如果我们用“大叙事”优于“小叙事”的“不对等”思维,又怎么能解释仅仅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儿女琐事的曹雪芹与张爱玲呢?
结语
我想,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所以在文学价值高低和文学独立性问题上多经验性的、似是而非的讨论而难有共识,原因可能就在于上述三个缺失的相互关联。如果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难以突破,文学理论在今天转为文化研究也好,还是今后再回到文艺理论研究上来,文艺学是建立知识体系还是放弃知识体系,很可能我们还是会在原地转圈。
言下之意,如果我们首先从中国文学创作的“文学性问题”出发,以此审视中西方文论面对这些问题可能存在的局限,文艺理论就可以直面中国现实凸显出它挑战既定理论的批判与创造结合的品格。中西方现有的文论知识,就会成为这种批判张力中的“材料”而不再是理论。那样一来,中国的当代文艺理论就可以成为一种“生长性”的东西,进而摆脱我们现在只能“融会、拼凑、在现有中西文论概念间‘褒彼抑此’”的尴尬状况。关键是,由这种直面创作的“文学性问题”的态度,还可以导致恢复中国文论是从创作中提取理论命题的文化性传统。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始终难以突破西方式的各种观念,或者就是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命题和范畴中寻求概念上的“转换”而成效甚微,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从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中提取新的理论内容的努力。那样一来,我们就既说不清象苏轼、曹雪芹、当代画家黄永玉这样的作家与西方作家的区别在哪里,也说不清他们与其他有个性风格的中国作家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因为这些作家,同样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宗经思维”、“风格风骨”、“意境神韵”等也难以很好解释的。
所以,否定主义文艺学认为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既尊重现实又不受现实束缚”的“穿越现实”的品格,是西方文论无法概括的,也是中国古代文论难以准确概括的。这种难以概括的品格应该成为中国当代文论形成自己独立命题和思维方式的基石。不仅如此,这种“穿越现实”的品格,还可以一方面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尊重他人与世界”的精神打通,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文化上为中国现代化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提供积极的方法论话语,并最终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温和的、智慧的、有力的、启示性”的独特的作家形象和文化形象。
我认为,只有当这种形象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说“这是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这句话的时候,才可能会胸有成竹起来。
注释:
①⑦ 参见吴炫:《否定主义美学》(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见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④ 参见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⑤ 参见郑国庆:《文学性》辞条,载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参见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7页。
⑧ 参见吴炫:《论文学对现实的穿越》,《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思维障碍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读书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