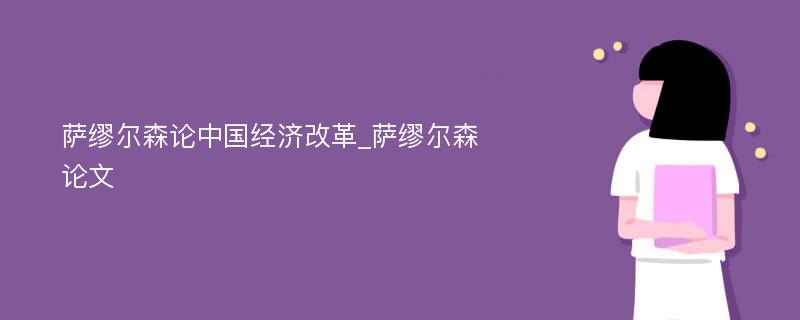
萨缪尔森谈中国经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萨缪尔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我们同意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但中国正在向更侧重于市场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萨缪尔森:我们先看看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你们听说过智利的“芝加哥小子”吗?他们是一批在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受过训练的保守的智利经济学家。以阿伦德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当政期间做过许多事情,其中包括许多蠢事——头一两年看起来很不错,然后就开始变糟了。随后军方介入,皮诺切特将军成了独裁者,通常,如果一个独裁者上台,就会出现像阿根廷那样的裙带资本主义。统治者在瑞士银行存有巨款,像菲律宾的马科斯等人。由于历史的偶然,智利军方把一切大权都差不多移交给了一个“宗教”团体,我指的不是天主教团体,而是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小子们完全将他们所学的付诸实践,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供求关系,分析私有产权,等等。这一招还挺灵,与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和巴西相比,智利的经济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内很不错。
这样一来在我的教材的后面几版中,我不得不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别:原来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后来我又加上了法西斯资本主义。政治上是专制制度,但经济上基本依靠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价格机制。这种制度也不是说完全不行,至少它能运作一段时间,但你不知道它能否持续下去。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种模式是苏联模式。中国曾经总是想学苏联。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岁数比你们大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来到麻省剑桥,来到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他们问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他们总是问:“斯大林的制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吗?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当然,大部分美国人对卡尔·马克思并不知道多少。
事实是,斯大林之后的制度行不通——苏联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它在军事上能够做出很多绝妙的事,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物理学家,但与此同时,苏联的保健制度却不那么好,他们甚至不能完成医院体温计的生产指标。在苏联,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的寿命在缩短,这在任何社会都很难出现。战后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女人53岁,男人50岁;现在他们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美国,女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在古巴这样落后的经济中,如果你能用科学方法控制住传播疟疾的蚊子的肆虐,你就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再看看中国,二战之前的上海,如果某一年诞生了1000个婴儿,大概只有500个能活到年底, 这主要是由于排污系统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大概在70岁以上——你们国家仍然是个穷国,但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均寿命可以大大延长。我的意思是,在苏联连平均寿命都在下降,可见它的制度已经失灵到了什么程度。
当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他们开始变得挑剔起来,他们开始在乎鞋子的大小、衣服的颜色,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难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要。苏联打仗打得很好,但经济上不行。如果你看看两次大战之间的捷克,它一战后从奥匈帝国中独立出来,经济上有所进步,从此之后便停滞不前。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即使在残酷的沙皇统治之下也取得了某些进步,然后,斯大林做了一些容易做的事情,诸如发展钢铁工业,修筑大坝等等,使经济得以发展。而捷克则完全是停滞不前。你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有些国家就像在相同条件下做对比试验,比如东德和西德,朝鲜和韩国。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计划制度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有追寻利益的政客,有谋求私利的大众。做得最好的可能也只有瑞典模式,在实行平均主义的同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进步。
但看起来中国的作法颇有不同:你们大踏步地走向了市场,尤其是中国从小规模工业和农业着手,而不是去搞1.5万人的大工厂。 从某种程度来讲,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我在麻省贝尔蒙特有个邻居——贝尔蒙特是剑桥郊外的第一个镇子——他开了个技术公司。我当时在遛狗,然后和他聊开了。
他说:“我在中国有一个工厂。”
我说:“你是说在香港?”
他说:“不,是在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地区。”
我问:“工厂怎么样?”
他回答:“特别好,不交税,工资也很低。”
我说:“再告诉我一点详情吧。”
他说:“你得在香港找对人,然后他们会把你介绍给中国内地合适的人。然后你就干起来了。”
这是12年或15年之前的事了。
这种合资企业在培养劳动力方面很有好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就会有能力自己单干了。但我觉得,你们在试图得到资本主义的高效率的同时,必须警惕许多资本主义的副产品。
在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实行的是阿尔·卡彭——芝加哥黑帮式的资本主义——阿尔·卡彭是芝加哥的黑社会头目,有名的芝加哥歹徒!他最后被关了起来,他曾经持着机枪横行四周,杀人越货——现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都是这样,你必须得有保镖,这是一种罪恶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罪恶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都很自私,在拼命为自己牟利。但是,赚取利润是资本主义运转的原动力,而且在竞争机制下,来自他人的竞争是一个人所能获取利润的惟一限制。微软的领导人比尔·盖茨是当今世界上最富的人,就像1910年时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一样,而激烈的竞争会对一个企业的垄断程度有所限制。
最后一个模式与亚洲危机有关,因为亚洲国家一直都模仿二战后的日本。日本战败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实际上实行了一种独裁统治:美国人坚持改变一些法律,京都的艺妓以前是12到14岁,麦克阿瑟说,她们必须至少16岁;许多条款还被要求列入新宪法,比如说妇女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利。自1853年佩里将军打开日本的国门以来,日本人开始派他们最聪明的人去学一门十分难学的语言(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学英语好像比中国人学英语要难一些)。他们只要在西方看到好东西,比如如何修建现代公路,就会回来照葫芦画瓢。
因此,他们出现了发展方面的奇迹——这个奇迹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的第一天。这时,房地产泡沫突然破灭了,股市泡沫破灭了,外国人不愿意搞合资企业了,因为日本已经不景气了,天空乌云密布。泰国1997年出现了同样的情形:1997年,所有的评级公司,包括标准普尔、穆迪等等,都说泰国的信用等级很高;危机发生的前一年泰国的增长率是6%,前五年平均增长率是8%——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新兴市场成了投资热门,所有的美国股票经纪人都在给像我这样的傻教授打电话,说“快点快点,买新兴市场上的股票”。谁也不知道泡沫什么时候会破灭。当泡沫破灭时,资金不滚滚流入,而开始流出,突然之间,泰国大街上的招工广告都不见了踪影。
韩国也是如此,韩国人向日本学习。日本有庞大的家族集团,三井、三菱,还有一些在战前并不富裕的家族,如索尼和丰田。韩国学习了日本公司之间互相持股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个公司都有一个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做最后的决定;它的银行会拥有这些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也会拥有该银行的股票,银行的不同的客户之间也会互相持股。尽管日本的经济规模只是世界经济的10%,而美国是22%,但如果你看看日本陷入危机之前最大的全球20家银行排名,日本银行占大概14到15家——其实这并不能代表日本的经济实力,正如当年日本被炒上天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没有什么意义一样。
80年代后期,日本一改二战以来对西方的崇拜态度,开始对西方的商业模式嗤之以鼻。他们对自己的以下几点颇为自得:(一)在日本公司里,决策是集体一致做出的;(二)他们更注意长期的增长,而不像美国公司一样把注意力放在股票价格的波动上:(三)他们愿意花钱做长期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像当年希特勒的德国认为美国腐朽堕落一样,日本人认为他们的产品是世界上最棒的,生产工艺是世界上最好的。1989年以后,随着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人为自己的傲慢和自负付出了代价——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体系,这个社会陷入了一场价值危机当中。政治和经济上的过分保守使得日本陷入了持续10年的停滞当中, 而与此同时, 在克林顿和格林斯潘的带领下, 美国很快摆脱了1991年海湾战争带来的短暂衰退,全力冲入了一个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全新的无通胀发展时期。
然而,亚洲国家大都遵循了日本模式。1997年,当资本开始流出泰国等新兴国家时,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工业企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地跨掉,只有新加坡、香港和远在天边的巴西没有受到严重波及。到1999年,那些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紧缩政策的国家开始走出危机,而求助于资本控制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未来还不明朗。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但都未能获得经济史的有力支持。那些宣扬“亚洲价值”不同于西方的论调的人也是一样,至今未能得到历史的证明。
你们在斯隆学院应该学到的是,当你作出新的投资时,应当考虑未来的回报。在建一座横跨查尔斯河的收费桥梁时,你必须做工程预算来预计有多少车辆会使用这座桥,他们会交多少钱,你需要为投资支付多少利息,维修费要多少。然后,你必须在文件材料上显示这是一个合算的投资,可以偿还银行的贷款。
日本模式的支持者们说:“这根本不对,你应当考虑长远的将来,你不应当担心明天你的股票的价格。”他们不懂得麻省理工斯隆学院和其他商学院发明的商业分析工具是无可替代的。如果你所有的钱都投入了合理的项目,并且都有材料证实它的合理性,那么在危机出现,资本突然停止流入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人来投资;日本所有的银行记录都不公开,人们无法得知他们投资的回报率如何,我觉得中国的企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在资本流入减少时显现出来。国际收支盈余带给了中国大量外汇储备,但所有国家都有陷入危机的可能,不管它有多强大,美国也不例外。
问:也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它们必须注意基础性的管理手段。
萨缪尔森:对。如果一个穷人走进一家赌场,说:“我走投无路了,我需要赢一大笔钱来养家糊口。”这不是成功的养家糊口的办法,它违反了所有的概率原则。马来西亚的总理和日本大藏省一位要人一直喋喋不休地宣称亚洲有一种不同的文化。我认为,在商业领域内,这是个危险的幻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罗伯特·默顿、约翰·考克斯等人发明的投资管理工具。
(本文节选自中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就读MBA 学位的三位留学生廖理、汪韧、陈璐合著的新著《探索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