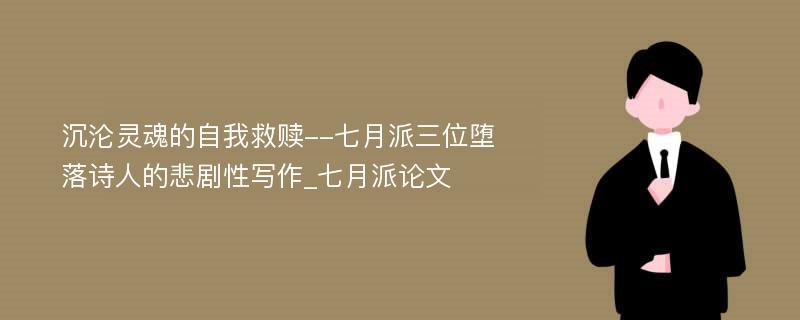
沉沦灵魂的自我救赎——“七月派”三位落难诗人的悲怆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怆论文,诗人论文,灵魂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力量的年代里,一批又一批诗人不仅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甚至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长时间里,他们沉落于社会的底层,忍受着被抛弃的煎熬,也因此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味到人生的不幸,看清了社会的变态。苦难加深了他们对历史人生体验的深度,在沉沦中以诗歌作为唯一的精神救赎方式时,对社会历史的感知也就融入了个人生命形态,于是向社会发出诉求便无不以自我的存在为出发点,它表达的是有着独特遭遇的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满怀疑惑的印象以及无辜获罪的愤懑,而诗歌写作运用的象征手法又使抒情形象超越了具体所指而具有普遍性因而成为对一代人生存困厄的写照和对一个昏昧时代的抗议与批判。
绿原、牛汉、曾卓这三位“七月派”的重要诗人,在“胡风事件”中落难,到“文革”“又一次沉沦,/沉沦,/沉沦到了人生的底层”(绿原诗句)。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在一个苦难的年代开始写诗,又为写诗进一步蒙受苦难”,诗和苦难是他们共同的忠实伴侣(注: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16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这几位长期身处“炼狱”的诗人,即使是在最荒诞最绝望的年月,“迫于一种生活的激情”,他们也没有从生活中放逐诗,相反,对苦难的深刻体验,使思想凝成的诗歌更有深度和震撼力。绿原在20世纪80年代分正集和续编出版的收有他几十年诗作的选集《人之诗》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写于受难的日子里的那几首诗,如《又一个哥伦布》(1959)、《重读<圣经>》(1970)等。20世纪的这个哥伦布(受难诗人的自况),“形销骨立,蓬首垢面”,他的“圣玛利娅”不是一只船,而是监狱的四堵苍黄的墙壁;他的“发现一个新大陆”的坚贞信念,不过是等待着“时间老人”的“公正”判决。而时间加给人类的永恒局限比空间带来的神秘更难以突破,说明历史时间虽推移既久,但是人这一自觉个体在追求和获取自由的道路上遭遇的却是比庞大自然更可怕的人类社会自身的茫昧。这个智识被囚禁的怪诞事实也告诉我们:历史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倒退!
同样是在中西对比中来批判时代的逆行,《重读<圣经>》公布了诗人在“牛棚”里为排遣愁绪,于夜深人静时在倍感凄清中读《圣经》,对当今世道人情的发现。进入《圣经》,诗人发觉:“论世道,和我们今天几乎相仿,/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正是感受到当下生存环境中人格普遍下降乃至沦丧,作者才不仅敬重为人民立法的摩西、推倒圣殿的沙逊、充满人性的大卫、聪明的所罗门,不仅热爱有颗赤子之心的赤脚的拿撒勒人和心比钻石坚贞的马丽娅·马格黛莲,他甚至佩服那嘲笑“真理几文钱一个”和杀害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甚至同情出卖耶稣的犹大,因为彼拉多敢于宣布耶稣无罪,犹大面对十字架勇于“悄悄自缢以谢天下”。诗人痛感今日正义感和良知的严重匮乏,不由写下: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马丽娅·马格黛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太决不会想到自尽。
只有无辜蒙难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中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到这种可怕的世情,诗歌冷峻地揭示出一个时代灵魂之柱的坍塌,在历史的对照中,这严重的现实更引人深思。
由思想艺术个性所决定,苦难在曾卓的诗里起的是另一种作用。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诗人被囚禁,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煎熬着善良的诗人的,是被抛弃的孤独。早在1957年,曾卓写过一首诗《我期待,我寻求……》,披沥的就是一个被集体抛弃的孤独者的痛苦挣扎和近乎绝望的祈求。渴望在群体事业中实现自己,而偏偏被“神圣的集体,伟大的事业”所抛弃,孤独感是那样刻骨铭心:
我的身外是永远的春天,
河流解冻,田野闪射着彩色的光芒。
到处是欢乐的人们,和他们的
欢乐的歌声。
而我的心有时干渴得像沙漠,
没有一滴雨露来灌浇。
我将嘴唇咬得出血,挣扎着前进,
为了不被孤独的风暴压倒。
诗歌提供了50年代人民大众一片欢腾,而被宣布为对立面的少数知识者却在被“遗弃”的孤独中煎熬的象征性情境,真切地记录了时代的“畸零者”的被忽略的内心风暴。表现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孤独感的诗,50年代还有何其芳、穆旦等人写过(注:何其芳在1952年发表了用三年时间写成的《回答》一诗,回答人们对他的沉默提出的“新的生活开始了,诗人为什么不歌唱?”的疑问。让等待者失望的是,诗里表现的不是对新生活的毫不迟疑的认同,而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心境。诗的开头就这么写:“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轻一点吹呵,让我在我的河流里,/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穆旦写于1957年的《葬歌》也坦陈了一个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的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旧世界观,与旧我诀别的真诚却又曲折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但是曾卓把这一主题持续到了70年代。1970年创作的《悬岩边的树》,以诗的象征获得了高度的概括力,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不利处境及灵魂姿势。在前一诗里,“我”还抱有希望,因而现身出来,向集体发出“不要遗弃我啊”的恳求,结果是历史的风暴无情地拒绝了个体的请求。现在,“我”既无名也无言,犹如一棵远离群体、处于危境的树: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注:又是“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岩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这肯定不是一棵普通的树。不然“奇异的风”不会把厄运施加于它。“一棵树”和“森林”,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当然喻指了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即前诗中“我”与“集体”)的关系。在以阶级论为理论基础的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属性(注: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里,有一个提法就是“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不难理解“深谷”的含意,也不难理解“风”将“树”置于“临近深谷的悬岩上”用意的可怕。像艾青《鱼化石》中的“鱼”一样,“树”的生命被不可抗拒的灾难“固置”在悲剧的形态。渴望归附于一个集体,却被逐离成为“零余者”。然而,“树”终是在厄运中证明了自己。一旦被抛逐到边缘位置反而能冷静地审视和对待对它来说只能是灾难的环境,它懂得了真实的可贵(“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并选择了(“倾听”)它作为精神的支柱。“树”改变不了狂暴的外力对它的左右,但外力也无法改变它所代表的类的生存愿望与生命意志。内在的坚毅与精神腾越已经改写了“风”肆意扭曲的结果,“寂寞而又倔强”、“像是要展翅飞翔”,说明“风”的意图最终落空。《悬岩边的树》是受难的一代的命运写照,也是曾卓用苦难生涯和象征艺术锻铸成的一座不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雕塑。
在“七月派”诗人里,甚至在新时期“归来”的众多诗人中,能够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仍保持创作活力且在艺术上又有新的拓展的,牛汉是相当突出的一位。牛汉也是苦难磨砺出来的诗人。外在的打击使心灵更丰富,生命受重创而灵魂愈挺倔,这是诗人牛汉给我们的印象。牛汉在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一度被囚系。“文革”中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系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仍不知疲倦的寻找、发现和捕捉诗。“复出”于诗坛后,他首先发表的就是写于“文革”期间的作品。它们“大都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面貌”(注:绿原为牛汉诗集《温泉》写的序:《活的歌》。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在不允许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的背景下,这些诗,大都借助自然界的物象,且多是被摧伤、遭残损的形象,来寄托他的性情和感慨。牛汉说在“古云梦泽”劳动的五年(注:指1969年9月到1974年12月。咸宁属古云梦地区。),“大自然的创伤和痛苦触动了我的心灵”。但如一位文学史家所说,这可以看作:“他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创伤和痛苦,在创伤的‘大自然’中寻找到构形和表达的方式。”(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牛汉在落难时期写的这些诗,有着咏物诗的传统表现方式,而又富于现代感性,抒情主体带着饱受打击和屈辱而强化着内在抗争性的精神特性,投射出来后往往在残损中看出内在的生命力,《华南虎》、《半棵树》最为典型。写于1973年的《华南虎》,具有如《悬岩边的树》一般的受难者的精神自传的特性,而又有着更强的鞭击灵魂的艺术震撼力。在这里,孤立的树与森林的关系已经变成了羁于笼中的老虎和围观的人群的关系。传统的伦理关系在这儿被切断,庸众的人性中的怯懦与残忍在对比中凸现了出来。老虎这威猛的生灵,被囚于动物园的铁笼中,“胆怯而绝望的观众”或用石块砸它,或向它厉声呵斥,或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当诗人试图用受过伤的心灵去接近它时,顿然有了震惊人的发现:“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这些是残害的证据和对拘禁自由进行不屈反抗的痕迹!这种发现使诗人终于明白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虎用自由不羁的灵魂笞击、唤醒了人类:
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
恍惚之中听见一声
石破天惊的咆哮,
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掠过我的头顶
腾空而去,
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
火焰似的眼睛,
还有巨大而破碎的
滴血的趾爪!
这一首虎的颂歌从屈辱而悲愤的心灵中发出,对一个时代里驯服、苟安、乐于当看客的国民性,不失为一道醒目的指证。驯服、苟安、乐于当看客的的国民,正是造成虎一般的强者也会遭受羁缚、凌辱与戏弄的由众数所形成的力量。有过无辜罹难、饱受凌辱的诗人,在深刻体验着的悲剧性的社会人生情境中,感知到了国民性与强者的悲剧之间的关系。不难想见有过被囚系的经历的牛汉,面对笼中的老虎,产生的愤懑而痛苦的情感。只有有着相类似的遭遇的人,才关注并有可能进入虎的精神世界:“哦,老虎,笼中的老虎,/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还是想用尾巴鞭击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你的趾爪/是被人活活地铰掉的吗?/还是由于悲愤/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听说你的牙齿是被钢锯锯掉的)/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与其说是对不幸落入异质环境的老虎的屈辱与悲愤的心情的理解,不如说人从老虎身上联想到自己的不幸,激起难以抑制的悲怆之情。与老虎为自由而不屈抗争的行为相比,作者为他这一代受难者的只是无言地接受社会的打击而感到羞愧。而被虐害者的反省,反衬的是作为多数的观众充当帮凶性质的看客却浑然不觉:这一对比更引人深思,诗的象征因而获得了更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
《半棵树》写于1972年,地点仍是咸宁。在社会的政治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浑身创伤无法复原的生命,于大自然中看到了另一受了巨创的生命: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树”因为直因为高而被“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可见天庭的权威忌恨地面苍生中的出类拔萃者,实际上不容许这些生命有自己的生存意志和发展的自由与权利。然而生命的自由意志(还有生存智慧)又是无法摧毁的。树的外部形体的残损与内在精神的完整,对天庭的暴虐是一种控诉也是一种反讽。令人悲怆的是,暴虐而阴险的雷电不允许它的权威受到挑战,已身受重创的树,随时还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树的“倔强”程度,与遭受打击的程度,几乎是成正比的,“半棵树”比“悬岩边的树”更富有性格和命运的悲剧性,它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映象,它的遭遇触击到当代社会冲突的一个深隐的层面,也就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命途多舛的真正原因。
也许三位落难诗人的隐匿写作告诉我们,即使在“文革”那样的时期,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文化批判与思想抵抗的责任。政治打击与社会迫害,逼使“五四”精神在无声的中国悄然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