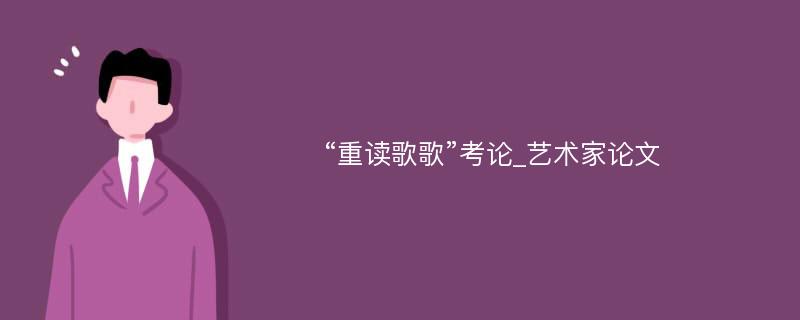
“Пошлостъ”考辨——重读果戈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果戈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被介绍到我国后,“媚俗”一词立即流行起来,成为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之一。关于“媚俗”的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俄语中“пошлостъ”一词与西方学者们所探讨的德语词“kitsh”的某些突出特征极为相近,但其内涵要丰富得多,它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早已是俄罗斯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仅在一篇论文里是无法详尽地考察“пошлостъ”一词的内涵与历史流变的,本文仅聚焦果戈理笔下双重性的пошлостъ,揭示它总是作为人类一种境况的真实面孔,剖析果戈理在虚幻的低俗现象中显露崇高的特性。
虽然“пошлостъ”一词与西方学者们所探讨的德语词“kitsh”的某些突出特征极为相近,但它毕竟是一个地道的俄语词。它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其它语言,即使有一系列的词可以作为它的同义词①,但要确切地表达它的涵义,终难摆脱以偏概全之嫌的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一直被作为贬义词使用。然而,在我们看来,在果戈理笔下“пошлостъ”的概念是双重性的②。正如Ю.В.Манн所说,它“不仅仅指低俗的和不体面的现象,而且也指普通的、寻常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包括我们的生活。”这里涉及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正反同体的现象,为了阐释的方便,我们暂且分别而论。
Ап.格里高利耶夫曾谈到果戈理将自己的作家身份定位为“人类‘пошлостъ’的分析家”[1](78)。果戈理受到普希金特别的青睐,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擅长展示生活里形形色色的“пошлостъ”。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的文学批评里,果戈理笔下的“пошлостъ”多被从社会学角度加以揭露和批判,更为甚者,在意识形态化的批评里,被简化为对“寄生虫”、“贵族老爷”的庸俗生活等进行贴标签式的社会批判。不过,也有例外。其中的佼佼者就是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经常提到“пошлостъ”这个词,他认为,在俄语中借助于这一个词就可以表现广为流传的弊病。由于此词词义复杂,他在转译成英语的时候,使用了自己生造的一个词“poshlust”。纳博科夫的研究受到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高度评价。他指出:“纳博科夫论果戈理的文章中涉及到poshlust的十来页,在迄今为止所有以媚俗艺术为主题的探讨,以及所有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德语词‘kitsh’的某些突出特征非常相近似的探讨中,当属最诙谐、最睿智之列——尽管它根本没提到过那个德语词。”[2](251)
在《媚俗之人与媚俗》一文中,纳博科夫对与“пошлостъ”相关的一些俄语词加以了辨析。譬如,他认为,庸人(обывателъ)和小市民(мещанин)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词。但是,可以将庸人称之为“彬彬有礼的”(“благовоспитанный”)“布尔乔亚的”(“буржуазный”)。彬彬有礼是以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庸俗为前提的,它比朴直的粗俗更糟。这里“布尔乔亚的”一词借用的是福楼拜的概念,③而不是马克思的概念。他强调:“布尔乔亚”——是自满自负的小市民,高傲的庸人(Буржуа-это самодоволъный мещанин,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обывателъ)。小市民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庸人——则是世界性现象。在一切阶级和民族国家里都能见到。他指出,应当承认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会落入媚俗、陈词滥调的窠臼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庸人。“高傲的媚俗之人”是“彻头彻尾的职业的装腔作势的人”、“体面的布尔乔亚”、“平庸和因循守旧的世界性产物”。“伪理想、伪同情、伪智慧是他固有的特性。欺骗——是真正的庸人的忠实同盟者。诸如美、爱、大自然等崇高的字眼出现在他们的嘴里是虚伪的,出于自私的目的。”[2](385)在纳博科夫的眼里,《死魂灵》中的乞乞科夫,就是这种人。
本文中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果戈理笔下的艺术家和媚俗艺术。果戈理对它们的刻画,真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部中谈到两类作家,其中一类就是典型的媚俗作家。“他从奔腾不息的生活涡流中选取为数不多的例外,从不变更自己的高雅的创作格调。他高高在上,不愿屈尊去接近那些贫穷微末的弟兄们,不愿接近生活的底层,而热衷于描写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人物。他的好运气更是令人羡慕:他置身于那些高贵的人物之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写起他们来得心应手,与此同时,他便蜚声文坛,名声日隆。他用令人陶醉的烟雾迷惑读者的眼睛,巧妙地讨好他们,隐瞒生活中的阴暗面,只向他们展现完美的人。人们为他欢呼,为他喝彩,跟在他的华丽的马车后面奔跑,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把他捧上了天,说他高于世界上所有的天才,就像雄鹰翱翔于一切飞鸟之上,热情奔放的年轻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就激动不已,热泪盈眶——他的力量是无尽的,任何人都不能与之相比拟。他就是上帝!”[3](153)不言而喻,这活脱一幅媚俗作家写真!
果戈理在彼得堡故事里刻画了艺术家的众生相。在《涅瓦大街》中,像孩子一样天真纯洁的梦想家画家庇斯卡廖夫与庇罗果夫中尉们庸俗踌躇满志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画家对艺术的献身,对善和美的追求,最终却以痛苦的绝望,心碎而死;而自满自足、厚颜无耻的庇罗果夫中尉却洋洋得意。别林斯基指出:“这种对照包含着多么深长的意义啊!……并且,这种对照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庇斯卡廖夫和庇罗果夫,一个黄土长埋,另外一个志得意满……是的,先生们,这世上真是沉闷啊……!”[4](201)
正如В.Д.杰尼索夫所指出的那样,“通常人们将彼得堡故事描绘成他的‘欧洲主义’(以及欧洲弊病)”[5](56)。“在贫瘠、荒野的北方”出现的彼得堡“是与大自然和社会规律相矛盾的”。在官方,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被描绘成启蒙的“发祥地”;在俄罗斯传播科学、艺术、手艺的集散地;洋溢着欧洲文化的城市;北方的帕尔米拉;圣彼得的城市;东正教的中心;靠近天堂的地方。然而,在民间,这却是反基督的神秘的北方王国、接近于“世界的尽头”,极为有害的“Питембурх”,全是“德国人”(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即“非俄罗斯人”)……[5](56)宏伟的城市及其令人惊讶的命运令无数艺术家挥笔疾书,倾注毕生心血。果戈理笔下的彼得堡是既非俄罗斯的,又非外国的,恶魔式的城市。它是现代文明的缩影。这里“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样子不同!”(《涅瓦大街》)
中篇小说《肖像》在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通过对艺术变成出卖的对象,为有钱人奇思遐想服务的媚俗现象的揭露,提出了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命运问题,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画家恰尔特科夫为了致富不惜毁灭自己的才能,沦为一个匠人。实际上,这里展现的是一部媚俗艺术家的精神堕落史。面对求画者,“他知道,只要能按照此刻自然向他显示的样子完美地画出来,就会画成一幅杰作。”可是求画者贵妇人却认为这简直就是败笔。起初,对求画者形形色色的要求他还挺为难,真弄得他汗流浃背。“最后,他懂得了诀窍,就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为难了。只要听上两三句话,就知道对方希望把自己画成什么样子。谁要喜欢马尔斯,就给他脸上装个马尔斯进去,谁要想做拜伦,就给他拜伦的姿势和神态。太太们无论想做柯林娜也好,温季娜也好,亚斯巴希雅也好,他都满口答应下来,再凭自己的想象给每个人加上端庄美丽的风采??求画的人们,当然,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称他是旷世奇才。”[6](207)恰尔特科夫成了一位十足的时髦画家,金钱彻底征服了恰尔特科夫:“……他所有的感情和冲动都转向金钱。金钱变成了他的热情、理想、恐惧、享乐、目标。”精神的堕落,不仅剥夺了他的创造力和灵感,而且也使作为一个人的他走向毁灭。
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说:“所有形式的媚俗艺术都意味着重复、陈腐、老套”[7](243)。恰尔特科夫的肖像画已毫无艺术,毫无创造而言。在这里,果戈理不仅描写了媚俗艺术、媚俗艺术家的遭遇,也揭露了上流社会的“伪奢侈”。在马泰·卡林内斯库看来,“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美学上,媚俗艺术都是现代性的典型产品之一”。[7](242)缘由在于,一是它源于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描述的现代的基本冲动之一——“伪奢侈”:“在所有阶层的杂然共处中,每个人都表现得像他本身不属于的阶层,并以巨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艺术家的产品日见其多,每一件产品的价值却在降低。艺术不再能飞升到伟大艺术的境域,他们就精雕细琢于小巧优美之物;外表比实质更受重视。”由于消费美的主要是些富豪和暴发户,“他们所喜爱的艺术,主要是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被创造和购买的”。[7](244)二是“媚俗艺术的热爱者也许追求名望,或是令人愉快的名望幻觉,但他们的快乐不至于此。构成媚俗艺术本质的也许是它的无限不确定性,它的模糊的‘致幻’力量,它的虚无缥缈的梦境,以及它的轻松‘净化’的承诺。”[7](245)无论怎么说,“媚俗艺术的整个概念显然都围绕着模仿、伪造、假冒以及我们所说的欺骗与自我欺骗美学一类的问题”。所以,“可以很方便地把媚俗艺术定义为说谎的特定美学形式。如此一来,它就显然与美可以买卖这样一种现代幻觉关系甚密。”[7](246)
В.Д.杰尼索夫高度评价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他写道:“如果说在俄罗斯浪漫主义中篇小说里(包括Н.波列沃伊、А.季莫菲耶夫、B.卡尔戈夫等人的小说在内)主人公以自己的艺术与庸俗的世界相对立,那么,果戈理笔下人物与之间的关系要丰富得多。”“他们每个人都有由其性格和‘时代’决定的观点、与世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其全部的变化多样性、宗教-历史内幕、与民族的和普遍的生活、还有人身上及其艺术中‘神性因素与恶魔因素的斗争’(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о ‘б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с ‘дъволъским’ в самом человеке и его искусстве)、被描写事物矛盾的、辨证的复杂性”[5](74)充分展现了作者的立场。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谈到,孩提时代他对上帝产生过一种困惑:当他看到插图本《旧约全书》中的上帝高居云端,是一个拖着长长的白胡须的老人,他想:既然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他吃东西,那么他必然会有肠子,而肠子是生物消化器官的一部分。于是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感到琢磨上帝是否有肠子实在是亵渎神明。而上帝与粪便不能掺和在一起这一事实,使作为孩子的昆德拉对基督教人类学关于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基本论点满腹狐疑。要是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那么上帝就有肠子。言下之意即粪便不应是令其耻辱和羞于启齿之物。昆德拉进而提出了他著名的“媚俗”概念:“媚俗就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8](295)。因此,“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之为kitsh”[8](295)。从词源上来看,kitsh这个德语词产生于伤感的19世纪中期,随后传到各种语言中。但是该词的频繁使用已经抹去了它原来的形而上学的价值。因此,“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讲,媚俗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8](296)在昆德拉看来,上帝与粪便、天使与苍蝇、崇高与卑贱之间绝非互不相关,但丑恶本身并不是媚俗,媚俗是企图用完美和完善的基本信念进行伪饰,以达到取悦世俗社会和迎合公众趣味的目的。[8](292)
在果戈理笔下有一类作品里描绘的“пошлостъ”,并非贬义上的凡夫俗子的生活,纯属普通的、寻常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如人类生活中的吃、喝,爱情、吵架、死亡。譬如《旧式地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等。他写的是“那些细小的、庸庸碌碌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如此的渺小,以致参与其中的人看起来并不比苍蝇来得大”。[9](334)不过,与昆德拉一样,苍蝇与天使、卑贱与崇高之间绝非互不相关,如果对这些视而不见,伪饰崇高,图解这一类作品,这就是批评的媚俗。
别林斯基不仅在批评界对果戈理的围攻中保护他,而且称之为“现实生活的诗人”,把他与普希金相提并论。在别林斯基看来,果戈理小说的显著特色是“朴素的构思、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4](176)
果戈理在《旧式地主》中对老夫妇的描绘令别林斯基感叹不已:“啊,这些描绘,这些特征,是如此可贵的诗的珍珠,相形之下,我们土产的巴尔扎克们的华丽词藻简直成了豌豆!……这一切都不是虚构的,不是得自道听途说,或从现实抄袭的,而是在诗的启示的瞬间用感情揣摩到的!”。[4](189-190)别林斯基指出:《旧式地主》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这两篇小说比《夜话》较少“抒情的狂热”,“但更多生活描写的深度和正确”。《旧式地主》中善良的老夫妇相互间感人的爱情虽然是建立在习惯上面,“但习惯总还是一种人类感情,任何爱情,任何依恋,不管建立在什么上面,总是值得同情的,因而,为什么可怜这两个老人,还是可以理解的。”别林斯基感叹道,阅读果戈理的作品“为什么会那么悲痛地微笑,那么忧郁地叹息呢?这里便是诗歌的秘密!这里便是艺术的魔力!你看见的是生活,看见了生活,就不得不叹息!”[4](194)“因为作者在这庸俗而愚蠢的生活里面也找到了诗,找到了推动并鼓舞他的主人公们的感情:这感情就是习惯。”在果戈理看来,这种习惯感情甚至比那种所谓崇高的热情“更有力、更深刻、更持久”。对于平凡的人,普通人“它是真正的至福,真正的神意的禀赋,他的欢乐和人类的欢乐的唯一的源泉!”别林斯基赞叹:“我们卓越的行为,优美的感情的原动力,往往就隐藏在这些地方!不过,别林斯基又哀叹道:“啊,不幸的人类!可怜的生活!然而,你无论如何还是会可怜亚芳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尔赫里雅·伊凡诺夫娜的!你会为他们哭泣,他们只是吃、喝,然后就死掉!”[4](186)这里同时包含着讽刺和同情。
巴赫金独具慧眼,他看到果戈理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来源于同家乡土壤上民间节庆形式的关系”。[10](7,第四卷)他认为果戈理是“民众意识的天才表现者”[10](14,第四卷)。他将《旧式地主》归入爱情田园诗之列。他在《小说中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探讨了小说中田园诗的时空体问题。他认为田园诗有多种类型,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时间空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1)地点的统一;2)内容严格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基本生活事实:爱情、诞生、死亡、结婚、劳动、饮食、年岁等;3)人的生活与自然界的生活的统一。[10](424-436,第三卷)
虽然“这个不大的空间世界,受到局限而能自足,同其余地方、其余世界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世界里,世代相传的局限性的生活却是无限的绵长。”在爱情田园诗中“与个人日常生活假定的社会性、复杂性、分裂性相对立,这里则是大自然怀抱中生活的同样完全假定的单纯性。这种生活只归结为完全升华了的爱情。在这一生活各种假定性、隐喻性和风格模仿等因素的背后,总还隐约地可以感受出民间文学那种完全统一的时间,还有古代的各种毗邻关系。”[10](426,第三卷)《旧式地主》中古代的各种毗邻关系一应俱全,如老年、爱情、饮食、死亡等等。饮食在这儿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为纯粹的日常生活。[10](428,第三卷)
巴赫金既充分肯定了田园诗中人本身的深刻的人道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田园诗生活的整体性,它同大自然的有机联系;物品没有脱离自身的劳动,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系等特点,同时也指出了田园诗小世界的狭窄性和封闭性的局限性。尤为可贵的是,巴赫金还探讨了诸如田园诗的毁灭、田园诗般家庭关系的破灭、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道德支柱的崩溃、人道主义关系的瓦解等问题。巴赫金发现,“田园诗世界的正面人物,这时变成了可笑可悲、多余无用的人;他要么毁灭,要么改造成凶恶的利己主义者。”[10](435,第三卷)深入研究“(在金钱的作用下)如爱情、家庭、友谊关系的瓦解、学者艺术家创作劳动的蜕化”等问题在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C.A.尼柯尔斯基和В.П.菲力莫诺夫在新近合写出版的《俄罗斯世界观。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祖国文学与哲学中的俄罗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一书的《果戈理作品中的人民与俄罗斯之路》一章中分析了果戈理的艺术构思,他们指出:“《密尔格拉得》中的‘旧式地主们’的庄园的田园生活方式是《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继续,与《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民间节庆相呼应。”[11](163)“无疑,在果戈理之前(甚至在他之后相当长时间)文学上未曾有过在集体节庆形象中表现出来如此富有表现力的民众团结。”[11](162)同时,他们还认为,果戈理的价值在于,“他最先探索到斯拉夫人思维方式里的核心,这一核心后来激励冈察洛夫创造出了令人惊讶的奥勃洛莫夫卡田庄世界,作为祖国世界观的某种内在支柱,这种世界观使得奥勃洛莫夫身穿著名的睡袍,躺在沙发上,无论如何也不干预实业界的和靠近实业界的彼得堡的忙乱。”[11](164)除此之外,他还首次在俄罗斯的“文学和社会思想中以如此富有表现力的形式展示了整个集体的农民村社解体的因素,面对生活其成员心理上被存在主义的恐惧所摧毁。这一恐惧并不说明农民对生活的普遍态度。在他们十分熟悉的大自然整体的范围内,在村社生活的道德准则范围内(确切地说,是小俄罗斯村社的生活),他们是感到有信心和平静的。一旦离开熟悉的大自然整体或者村社,他们马上就会感到恐惧袭来”[11](162-163)两位学者的分析是独到而深刻的,不过,笔者认为,虽然,这里的情节发生在乌克兰,但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是小俄罗斯村社的生活”。因为果戈理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作家,他的作品的价值是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
果戈理的性格是错综复杂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初就指出“他的许多特征直到现在还是殊待猜测的。可是他的天性的突出的品质是毅力、力量、热情,这却是一眼就可以了然的;他是一个不知道有中庸的天生的热狂家;不是沉沉酣睡,就是生命沸腾,不是沉醉于生命的欢乐感,就是去受苦受难,如果二者都没有,就会感到沉重的苦闷。”[12](148-149)时至今日,尽管关于果戈理的研究材料汗牛充栋,但对果戈理的性格之谜的解析远未穷尽。
赫尔岑也发现,“……在他的灵魂里好像流着两条溪流。当他逗留在科长、省长和地主们的房间里的时候,当他的主人公们至少佩戴着圣安娜勋章或者有八等文官的官衔的时候,他是忧郁的,难于和解的,充满着有时使人笑得抽搐,有时又引起接近于憎恨的蔑视的讥讽。可是相反地,当他跟小俄罗斯的赶车人打交道的时候,当他走进乌克兰的哥萨克人或酒店里跳舞作乐的小伙子们的世界里的时候,当他给我们描写一个为外套被窃而痛不欲生的年老的穷录事的时候,果戈理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才能是照旧,他却变得柔和、人性、充满着爱情;他的讥刺不再伤害和毒杀人;这是一个悲壮的、诗情的、感情外溢的灵魂。直等到他偶然在路上碰见了市长、推事、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为止,——那时候,一切就都变了;他剥掉他们的假面具,用粗野而辛辣的笑使他们遭受到公众鄙弃的拷问。[13](112)
描写生活中“猥琐的与庸俗的事物”与“伟大的与美好的事物”这二者的统一,使果戈理跻身于世界大文豪之列。
如前所述,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部中谈到两类作家,其中一类媚俗作家我们已经提及。然而还有另一类作家,“他敢于揭示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但冷漠的眼睛却看不到的一切,敢于揭示那些阻碍我们的生活前进的令人震惊的可怕的生活琐事,敢于揭示那些麇集于我们的土地上,在有时是痛苦而乏味的人生道路是随处可见的冷酷、平庸并且受过伤害的人物的灵魂,并且以无情的笔触鲜明生动地将他们刻画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作家的命运和遭遇就完全不同啦!既没有人向他喝彩,没有人为他洒一滴感激的泪水,没有人为他兴奋和激动,更没有十六岁的少女为他神魂颠倒,像迷恋英雄一样投入他的怀抱。他不可能孤芳自赏,陶醉于自己演奏出的优美的音乐之中;他最终逃避不了伪善而又麻木的当代批评家的评判。他所珍爱的作品被称为猥琐庸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视为亵渎人类的作家,落到一个屈辱的地位。那些评论家会把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品格与他本人等同起来,会摧垮他的心灵,熄灭他的天才的圣火。当代评论家们不承认,可以反射阳光的玻璃和可以显示微生物蠕动的玻璃同样珍奇。他们不承认,取材于社会底层的画面只要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就能光彩夺目,成为艺术珍品。他们不承认,高尚的愉快的笑,并不逊色于高尚的抒情,它和江湖艺人的忸怩逗笑有天渊之别!当代评论家们非但不承认这一切,而且指责和辱骂这个得不到承认的作家。于是他无人理睬,得不到同情,像一个没有家室的单身旅人,孤苦伶仃地站在驿道上。他的前景是阴暗的,他感到凄苦,孤独。”[3](152)这俨然果戈理本人的自画像。
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中写道:“我的主人公根本不是恶棍;只要我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添上美好的一笔,读者就会容忍他们所有人的。但加在一起的庸俗令读者感到害怕,令他们可怕的是,我的主人公们一个比一个庸俗,没有任何可以感到慰藉的征候,可怜的读者甚至没有地方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或者喘口气,读完全书让人觉得确似从某个令人窒息的地窖来到天上。要是我展示的是张牙舞爪的恶魔,人们倒会原谅我;但不会原谅我展示庸俗。”[14](97-98)他为这种“惧怕”而振奋:“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惧怕!谁的内心强烈地憎恶卑微,想必他心中具有与卑微相反的所有一切”。[14](98)
然而,停留在令读者感到惧怕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果戈理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通向崇高之物的觉察不出的阶梯”,“含有一种虔诚的思考,充满温柔暖人的光芒,让读者感到不同寻常的安慰”。他坚信,在艺术的感召下,“俄罗斯本性在每个人身上都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让心灵“突然从可耻的睡梦中苏醒,……唾弃自己的肮脏和卑鄙无耻的缺点,变成一个行善的斗士”。
对于果戈理而言,大自然里没有低微的事物。艺术家创造者即使描写低微的事物,也像描写伟大的事物一样地伟大;在他看来,可鄙的事物已经不是可鄙的了,因为通过它,这创造它的人的美丽的灵魂无形中就透露了出来,可鄙的事物获得了崇高的表现,因为它滤过了他灵魂的炼狱。
在果戈理看来,艺术家从事艺术活动“不是出于某种想象,而是因为在自己内心感到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因此艺术家得到了比其他人“对问题看得更远、更广、更深的智慧”。为了不辱使命,首先作家要完成自我的心灵提升,因为他的写作是“心灵真实”的写照,谈到《死魂灵》中的人物时,他深有感慨地说:在“自己没有变得哪怕有点像他们”,心灵中没有装进善良的品德时,“无论你的笔写出什么,都是僵死的东西,就像大地远离苍天一样,与真理相距甚远。”他还写道:“……往往有这样的时候,当你不能描写出社会或整个一代人的真正卑鄙龌龊的整个深度时,你就不能以另一种方式使社会或整个一代人去追求美好的事物;往往有这样的时候,在不能立即为每个人像白天一样清楚地指出通向崇高的和美好事物的道路和途径时,你甚至根本不应去谈到它们。”[14](103-104-98)
在《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中,果戈理指出:“对象越普通,诗人的心灵就越要高尚,才能从普通中发现不凡”;在《1936年的彼得堡笔记》中他主张从“那些每日每时包围我们的东西,同我们形影不离的东西,平常的东西”中挖掘戏剧情节,他认为这样的戏剧才是“镜子”,才会成为“讲坛”。显然,这里不仅仅是在谈戏剧,而且是在谈作家的创作观。他还强调“唯有深刻、伟大、不平凡的天才才能觉察出”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中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在平凡中发掘不平凡,发掘否定现象的全部深度的同时就是正确地表现崇高理想。”[15](191)这些是果戈理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
应当看到,果戈理是将俄罗斯精神复兴寄希望于贵族身上的。他认为:俄罗斯“民族的精华是贵族阶层,而不是某个外来的外国阶层”[14](177)。贵族应该具有一种“高尚气度”,因为“贵族阶层像是一根血管,里面蕴含着这种道德的高尚气度,为了让所有别的阶层的人明白,为何这个上流阶层被称作民族的精华,这种高尚气度应当传遍整个俄罗斯大地。”[14](178-179)
从词源学上来看,“пошлостъ”一词的变化是基于古俄语里它本身蕴含的“старинный”、“обычный”[16]的词义。在12-18(17)世纪的古俄罗斯文本中,形容词“пошлый”具有中性的、正面的内涵。④在18世纪,这一词几乎不用,但从18世纪末开始,文化涵义开始偏移且多用于贬义。从19世纪40年代起“пошлостъ”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多指从精神层面对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生活的意义等问题的思考。可以说在不同的时代这一概念的具体词义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原初的涵义渐渐被人们淡忘。不过,也有不少文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曾对此从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等各个层面探讨过。因此,考察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历史流变,深入研究其引发的诸多问题,可以管窥俄罗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思潮的变迁及其内在原因。
我们重申,从果戈理的创作来看,“пошлостъ”的概念是双重性的,正反同体的。这一词汇不仅古风犹存,而且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果戈理旨在强调“пошлостъ”的普世性质(всеобщий характер)。人是复杂的综合体,具有多面的本性,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既有崇高的追求,也有凡俗的权利。对日常生活中пошлостъ的宽容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低俗平庸的现象的一概接受,我们反对的是将低俗引为时髦。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理解甚至喜欢果戈理笔下两位老人那样的旧式地主,但我们内心也深深地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毕竟不代表人性更高级的层面。那种活在当下的简单的幸福概念还有提升的空间。
这就是价值观深刻的悖论。
果戈理的创作是高度的综合。果戈理笔下诸如妖魔化的城市/田园诗般的庄园、文明/自然、小市民/贵族、崇高/低俗等一系列虚幻的二元对立中,蕴含着作家的立场。
重读果戈理,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呼唤美的救赎。由于文学承载了“内容”即道德评判的重负,这在传统观念中显得重要,文学知识分子通常把文学作品当作进行社会和文化诊断的文本。而在当今,社会诊断多于美学批评这种以社会政治学为基础的美学观念注定会走向自我解构。应当警醒的是,当主体的人成为意义和价值的来源时,美是不确定的,崇高也可能导致伪崇高。
重读果戈理,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呼唤自我救赎。一个人、一个民族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能单靠面包活着。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媚俗、不迷失个性,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换言之,一切真正民族的、个性的东西都不是媚俗的。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剖析“пошлостъ”,但必须反思我们的思维方式(定势),而当代的价值观也应当蕴含于其中。
注释:
①网上找到的俄语同义词达37个之多。
②амбивалентна又译为“正反同体的”。
③在福楼拜写作的时期,“布尔乔亚”指的是中产阶级,即那些没有独立财富和贵族祖先,但其职业又不需要他们投入过多的体力劳动来供养自己的生活的人。他们是华而不实的实利主义者。他们不加区别尽其所能地享受。
④意指“исконный”,“давний”,“настоящи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