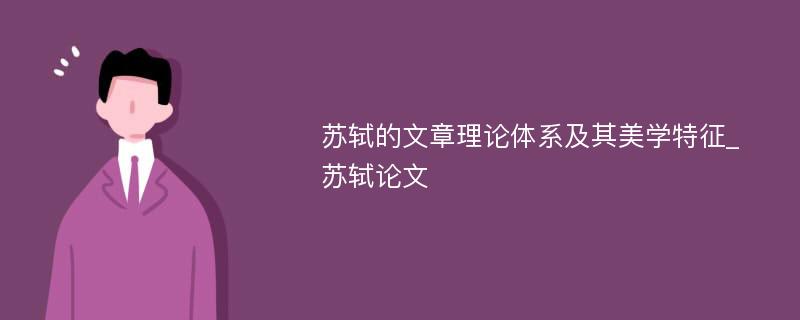
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特质论文,苏轼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轼在欧阳修的奖擢下跃入文坛,正是北宋古文运动将要取得实绩之时,而这个实绩之主要体现应该说就是苏轼的文章写作和文章理论批评,正是苏轼为北宋古文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时代已经是古文的时代,骈文的违反辞达,仅剩下一点未殄之余风,而古文的违反辞达,则有“求深”、“务奇”两种弊端,成为新的“时文”,可称之为“古体时文”。所以,革除这一新的文弊,便成为当时文章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苏轼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他的文章写作和理论批评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针对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倡导古文者在观念主张和写作实践上所存在的种种违反“辞达”之弊,苏轼提出了自己的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理论见解,并且付诸创作实践,从而对唐、宋古文运动及其理论作出了重大的发展突破,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的文章创作理论系统主要由“立意”、“辞达”、“自然”三说构成,涉及到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条件、言意关系、风格美学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而苏轼的创作天才、感悟能力、开放心态又使得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确乎超越流辈之上。
一
在苏轼看来,文章的第一要义是先需“立意”。据《韵语阳秋》卷三所记,苏轼曾对向他讨教作文之法的葛延之说: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对苏轼此议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尤袤《梁溪漫志》卷四、王构《修辞鉴衡》卷二都有记载,仅文字略有出入,可见其影响之广。又据《清波杂志》所记,苏轼认为:
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总之,认为“立意”为“作文之要”,文章写作必须遵循“以意为主”这一美学原则。
问题在于如何解读苏轼所谓之“意”,许多研究苏轼文论思想的论著都认为“立意”即强调文章的思想内容,“意”即文章之主旨,这种意见差不多已成定论。我们认为,苏轼的“立意”说,其着眼点并非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方面,而是在强调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兼有弘扬创作主体之个性特点和拓展文章表现的时、空境界之意。其深刻的含义是认为要摆脱拘束,自由地表现包括审美感觉在内的主体精神;要敢于突破现成的思想模式,充分传达投射于主体心灵的“自然之理”。这实际上是针对在他之前北宋古文家之刻板与迂顽,为当时的文章抑或整个文学创作指出一条发展的通途,其美学精神的核心是要求增强文学的主体创造力。
苏轼重“立意”的创作思想,是循他年轻时代的“有意而言”的作文主张发展而来的。他曾在《策论一》中说:“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此处之“意”,指作者的思想情感而言,与“立意”说之“意”在义脉上一脉相承。苏轼认为文章之用在于述意表情,只要是真实、自由地表达了作者意绪之作,即可为“至言”。这实际上是对传统“载道”说的一种“解构”。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些鼓吹者极端强调“道统”、“文统”,“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成为柳开、石介等人关于文章写作的不二法则,而他们所要“载”、“贯”之“道”,又只能是统领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先儒之“道”,实际上为文章的思想、情感传达划定了一个严格的范围。至于程、朱等理学家则更偏狭,干脆认为“作文害道”,鄙视文的价值。而苏轼之“意”,不同于“道”的关键之外,就在于其是个性化、情感化、审美化了的作者之思想境界,并受制于作者当下之境遇、精神状态,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非如“道”那样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思想范式。所以,所谓“有意而言”、“意尽而止”,实际上就是把文章创作看成是一个充分展示主体内在精神风貌的过程,这自然是对古文家、理学家之“道统”、“文统”的一个超越。在这一点上,苏轼遭到了理学家的攻讦,如朱熹即批评:“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王介甫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又是一样议论。”及“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朱子语类》卷一三○)朱熹此番评说并非完全厚诬东坡,苏轼确实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如朱熹所讥讽的“两截底议论”。如对待韩愈,苏轼有时批评韩愈“拒杨、墨、佛、老甚严”,有时又非常推崇他的卫道辟佛。又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赞成以诗赋取士,反对以经义取士,然而在《谢秋赋试官启》中却又以为“文章诚可以制治”,而“声律不可以入官”。然而,对于朱熹来讲,其所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恐怕还是苏轼在文章写作中所坚持的自由提取各家思想学说,因时因地自由地表情达意这一点。由于苏轼敢于突破“道”这一古文家和理学家为文章所设定的思想规范,因此在朱熹看来自然是散漫失“统”了。朱熹不明白东坡议论之前后不同,在于其彼时彼地感受之不同,在于其不胶柱于一种思想资源。较之于刻板的古文家和理学家,苏轼确实具有一种自由、开放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视域,这便决定了他之“意”与古文家、理学家之“道”在思想资源和文化意蕴方面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苏轼所强调之“意”实际上是主体精神和个性气质的一种体现,较之于古文家和理学家之“道”,其无疑更贴近于人生、更贴近于独特的审美体验。
苏轼所重之“意”,从内涵上来讲,是一种基于厚博的文化修养基础之上的对于宇宙、历史、现实人生本质的独到而深沉的感受。他在《上曾丞相书》中云:
凡学之难,难于无私。无私之难,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虽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悦于世也。故其言语文章未尝辄至于公相之门。这里之“无私”,可理解为是一种非功利的以及无“门户”之见的文化心态,而“幽居默处”则代表着一种虚静型的主体智慧精神,它们均得之于“观万物之变”、“通万物之理”。坚持“无私”,观照“自然之理”并顺应之,既不依傍“贤人之说”,亦不惮“不悦于世”,一切皆“断之于中”,这可以说是苏轼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趣向之主要特点,而他的“立意”说正是在这种主体精神中孕育而成的。所以,苏轼所强调之“意”,实际上往往指主体在观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审美意趣。《超然台记》中写道: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所谓“寓意”云者,指一种纯粹的审美性观照,如此“以意摄物”,自然能充分调动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臻入自由创作境界。对此,我们只要通过苏轼的《赤壁赋》、《石钟山记》、《超然台记》等文章,即可以体悟到他所谓的“立意”、“达意”为何等之美学境界追求了。
苏轼的“立意”说与“载道”说有如此思想文化分野之不同,其与极端追求“用”的王安石、司马光等一派政论家的论文主旨亦有区别。就强调文章须“有补于世”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有一致之处。但是,王安石等却以“用”为唯一标准,以“用”排斥“文”,要求一切皆须验之于当下,一切皆须“同”。而苏轼之重“意”,在坚持“有为而作”、“有补于世”的同时,更要求文章表达作者的个性特征,所以他批评王安石“欲以其学问同天下”。
“意”作为由现实感发而得来之思想境界与审美感受,其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是引发和增强表现能力,使这一过程充溢思想与艺术的生机。于此,苏轼曾云:“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据何璩《春渚纪闻》卷六引)“意之所到”之“意”,应该理解为是在心物感发基础上形成之情感激流及其张力,而文章表现过程中的“笔力曲折”、曲尽人意,无不得之于此种主体内在力量。所以,苏轼曾赞许王庠“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者”(《答王庠书》),又批评李方叔的文章“读之终篇,莫如所谓意者”,并指出其原因在于“未甚得于中而张其外”(《与李方叔书》)。由“立意”而达“笔力曲折”,终臻“无不尽意”,可见苏轼之“意”有时又兼指作家的主体性外化于作品中所形成的审美价值。对此,我们仍可以从苏轼的《赤壁赋》中得到印证。在《赤壁赋》中,作者惨淡凄凉而又不失乐观放达的心情,以及对宇宙自然之理和人生之旅的冥悟和感受,是所要表达之“意”,而这一切又与赤壁月夜的山水清境融而为一,从而形成了文中描写、抒情、议论三者结合而造意深刻曲折的艺术妙境,正所谓“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苏轼的“立意”说是他创作经验的理论升华,无论在当时或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中评曰:“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明代焦竑则在《刻苏长公外集序》中说:“唐宋以来,如韩、欧、曾之于法,至矣,而中靡独见,是非议论或依傍别人。子厚、习之、子由乃有窥焉,于言有所郁勃而未畅。独长公洞览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应手,落笔千言,坌然溢出……”(《淡园续集》卷一),重“意”的创作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源远流长,《淮南子》在论艺术创作主体性时曾有“愤中应外”、“有充于中而成像于外”的说法,其后范晔、杜牧等主张“以意为主”,书画理论中则讲求“意在笔先”。苏轼的“立意”说发展深化了前人的见解,使其内容更加充实,而将其提炼成一个光辉的美学命题。
二
“立意”说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条件提出了要求,但是,文章作为一种传达或表现,如何提高其表意的功能,即如何达或述所创之“意”,便涉及到了创作过程中的心与手、文与意关系,确乎关系到文本的成败与否。于此,苏轼又提出了“辞达”说。
苏轼在论文名篇《答谢民师推官书》中云: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于手者乎?是者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又《答虔卒俞括奉议书》云: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故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与手。
又《答王庠书》曰:
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辞达而已矣”出之于《论语·卫灵公》,为孔门弟子所录孔子之言。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体现了孔子主张先质后文、质文两备的主张。但是,对于孔子的这两句话,一般认为第一句是重质轻文,第二句因与第一句看似矛盾,加之出于《左传》,故疑非真出于孔子,或者根据需要不同,分别加以引用,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苏轼在这里借用了孔子的思想资料,从自己的美学思想出发做了新的解释和发挥,改变了其理论出发点,就是超出了孔子原来谈内容与形式即质、文关系的范围,而主要是探讨文学表现过程中的思维机制、表现原则等美学问题,从而为古老的“辞达”说熔铸进了新的美学意涵。就方法论而言,这是一种舍本意的借用。
仅仅把苏轼的“辞达”说视为是对历来对孔子原话之解的一种校正,是远远不够的。苏轼的“辞达”说的基本命题是“辞”以“达意”,但是此“达意”又不同于司马光的“通意斯止”,也不同于王安石之单纯的“书诸笔而传之人”。从苏轼的一些议论来看,他对于作文如何作到“达”,在思维机制、表现原则与技巧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大体有主客体融会贯通问题、作者气力与表现传达关系问题、审美直觉与意象持纵问题、心手器关系问题,等等。所以,他的“辞达”说的主要理论内涵是创建文学创作表现过程的美学原则,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辞”的功用发表意见之上。
“辞达”说与“立意”说、“自然”说彼此之间相互关联、映照,属于同一创作理论系列。“立意”说的主旨是创建一种新的文学主体精神,“自然”说的主旨是在标立一种新的风格美学,而“辞达”说的主旨则是意在阐明传达过程中的美学原则以及文本身的独立价值。苏轼认为,首先,作者必须善于“求物之妙”,对表现对象“了然于心”。苏轼把“物之妙”在另处又表述为“物固有是理”之“理”,于是了然“物之妙”于心即为知“物理”。一些论著将此处之“理”解释为事物内部的本质或规律,进而又认为“求物之妙”即把握事物的本质或规律,这是以认识论取代审美论,由此遂抛弃了其固有的丰富内涵。其实,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所谓“物理”、“自然之理”从来也不是单纯指事物本身的本质或规律方面之“理”,更大程度上蕴涵着感觉主体在对自然、宇宙精神的体验过程中对人生现象和生命律动的情感化的窥视、把握。具体于文学创作表现,就是在情感化的景物描写中直指人生底蕴,或曰航渡至“天人合一”之妙境。在此,“自然”成为连接作家与世界、文学与宇宙时空的津梁。所以,苏轼此处之“求物之妙”、“知物理”实际上就是指创作过程中的心物、主客互相感发、融会的过程,一个“妙”字正代表了这种物、我之间的契合。这样,“了然于心”就指“情瞳瞳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陆机语)的审美意象生成浮现,而“系风捕影”云者,则喻指对一瞬即逝的“感兴”、“意象”的捕捉。“系风捕影”一词原出《汉书·郊祀志第五下》,为谷永向成帝辟神怪时所用之语,苏轼在此加以借用,言临文之顷对藏如景灭、行犹响起之意象“拾得”之不易。这对作者来讲,当然是一个考验,因为这里所从事的表现不是把现成的“道”安放在文字语言组织之中,不是做礼教政治的功利诠释,亦不是简单地描述事物的外观形貌,而是进行一种游心于天地自然之间的精神体验与创造。其次,苏轼认为,做到“了然于心”是重要的,但仅此又是不够的,就表现传达的能力技巧而言,还必须做到“了然于口与手”。关于创作表现中的心、手、器关系问题,《庄子》、《淮南子》、《文赋》、《文心雕龙》等中均有精辟的见解,苏轼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亦非常强调心手合谐一致、密而无际的高超技艺,如言:“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与可之教予如此,余不能然,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心向往之的是在对法度、规矩熟练掌握的基础上直觉运用之,进入超越自由的创造境界。所以,苏轼提出的“系风捕影”之功“求物之妙”达到“了然于心”,并且了然于口与手”,实际上正是对创作中心、手器关系的揭示,而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所记文与可之语:“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则正好是对此之具体说明。
但是,苏轼的“辞达”说又并非仅仅是对批评史上的重质与重文两派观念的调合,更深的意义在于他吸收道家美学思想,将“辞达”说改造成为一个创作论概念。心手无碍的互感互应与“气”密切有关,意识状态与表现方式之间不可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讲,得心应手即为气贯心手,为道艺合一,这正是道家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苏轼认为,只要作者有内在风力,以“气”为文,就可以做到“能道意所欲言者”,做到“辞达”,如此,自然就会写出“不可以有加焉”的至文。把“辞达”问题与“气”说互相沟通,视气为达到“辞达”之关键,认为由气可进乎了然于心并了然于口与手之境界,这是苏轼的一个创新,如此“辞达”问题就超越了文质关系之范围而演变成为一个地道的创作美学概念。
在北宋时,孔子的“辞达”说被许多人加以借用,来表现自己的文质观,如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中云:“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王安石在《上人书》中则云:“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均解孔子“辞达”之说为重质轻文,同于孔安国“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何晏《论语集解》)之解。他们的解释一定程度上都与孔子先质后文、质文两备之原意有距离,实际上是把孔子的言论纳入了他们自己的重功利轻辞章的文学观念系统,只是政论家之于文辞不特如道学家那样鄙弃之甚也。司马光之文质说主要是针对苏轼父子而发的,而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甚大,这说明苏轼所理解的“辞达”与他们有实质性的不同。道学家和经学家的所谓“辞达”,是排斥文之“达”,或曰是只期适于功利之用的“达”,而苏轼则要确定文的价值,他所谓“不可以有加”云者,指文达到高妙的艺术境界,所谓“不可胜用”云者,则包括文的审美之用。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程朱的差异是文学与理学、政论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苏轼与欧阳修亦有差别,欧阳修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似乎无需在辞上下功夫,更不讲临文之顷的兴到神会、滤发性灵,有道即可。而苏轼却讲“系风捕影”、“求物之妙”,讲内外一致、心手相应,在理论上无疑高欧阳修一筹。所以,苏轼的“辞达”说被人誉为“论文之妙”。如程洵《尊德性斋小集·钟山先生行状》引李缯语云:“尝曰:‘文者,所以载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而世儒或以文不足学,非也。顾其言于道何如耳。’每为学者诵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理而已矣。’以为此最论文之妙。”关于创作过程中的心物关系和心手关系问题,苏轼在一些书论、画论中也多有阐发,其美学精神与“辞达”说是一致的。苏轼的“辞达”说受到了其父苏洵的影响,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所讲的作文经验与苏轼的“辞达”说比较接近。
三
与“立意”说、“辞达”说紧密关联,或曰由此二说发展而来,苏轼又创建了他的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自然”说,代表了他在风格问题上的审美理想,一系列精辟的议论蕴涵着极其深厚的美学思想。
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云: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尝行于的当行,尝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又《自评文》云: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不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尝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父子喜欢以水喻文,这是因为他们由水在流动中变化不居的特点而感悟到文章在风格上应有之美学追求。如苏轼曾讲到;“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以及“世有以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斫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苏氏易传》卷三)苏轼论文,贵天才变化,贵以“意”摄之,独辟蹊径,总之是重“活”与“变”二字,而水之无“常”无“定”的自然特征正好能为此提供一个具象性的说明,故经常取而喻之。可以看出,苏轼无论是赞扬别人的文章能做到有意而言,意尽辄止,在风格上犹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舒展而变化迭出,还是不无自信地描述自己当汪洋恣肆之文思汹涌来之时,不假雕琢,任情思自由抒发,而笔力曲折,无不尽其妙的情形,都以水之属性反衬文之姿态,体现出他对于文章风格的一个基本的美学追求,即摆脱束缚,不受任何固定之格式的拘限,达到自由的表现或表现的自由境地,概而言之,曰“自然”。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受老、庄影响而形成的“自然”这一范畴,就审美主体而言,主要是强调一种扫除知性负赘,融合主客而齐物的自由兴发;就文本风格而言,是要求作品以自然现象本身呈现之运化成形的方式去表现、去结构自然,此种观念统合了自然和艺术之间的主客两极对峙,缓解了自然的兴现与艺术的刻意二者之间的张力。所以,在“自然”一词的评语之下,往往意味着肯定艺术品的重造自然的审美品格,以及艺术家的犹如自然之运动的“自然”兴发的表现力,诸如自然、自发、天机、天放、气韵生动、神逸等等,都是用来描述艺术作品妙臻自然本身情状之境的批评术语。苏轼亦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批评观念,在他看来,风格的实现在于把表现方式调整到最接近自然的程度,应如自然的律动(如水之流、云之行等)那般自由地云表现,使文之气、即文之内在脉搏与自然的律动合拍,与自然物象涌现时的气韵气象迹近,如此即可做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所谓“文理”云者,正指文气、文的内在韵致。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司空图和苏轼都是老庄所创宗的推崇自然和直觉方式的美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完成者。惟需可以说明的是他们所提倡的这种类于庄子的不知其然而然的直觉表现方法,是建立在对事物的体察达到了然于心之境界的基础之上的,即是在“求物之妙”与“立意”已完成的基础之上放任精神去自由表现其有异于西方艺术理论所说的那种完全非理性、无节制的生理与激情冲动的直觉。中国艺术直觉的心理基础是“虚静”,西方艺术直觉的心理基础是“狂迷”,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甚大。
苏轼认为,要做到自然,必要的前提就是不得有“作文之意”。《南行前集叙》云:
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乏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一命题是深刻的,其含义是:创作应该是出于“不能自已”的有感而发,而不是为作文而作文,为写物而写物。只有在直观体察中逐渐于胸中构成意象,做到“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才能在表现过程中做到文思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心使笔驰,法为我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一气而呵成,则无不自然而能工。相反,在“作文之意”的干扰下,则易使创作成为模写的过程。主体如果束缚于法度与物态之中,则成为文的奴隶,不是我使法,而是法使我,我累于物,物累于笔,笔累于意,意累于气;意之不足则气之不张,结果便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气韵不周,空阵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
可以看出,苏轼的“自然”说实质上是强调一种天才洋溢、自得天成的创作个性,而反对模仿步逐、刻镂组绡,以迂怪艰僻饰生气之贫。对语言文辞的风格要求,苏轼主张于平易、通达中显出丰富、多样,而反对尚奇猎险,如云:“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与鲁直书》)“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答谢民师书》)苏轼的这一主张还体现在他对唐宋古文运动中出现的片面尚奇弄险而走向艰涩生僻之歧途的批判之中。除此而外,苏轼又认为文章在讲究“体气高妙”的同时,还应努力做到“词理准确”,如言:“子由之文,词理准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书子由超然台赋后》)在风格上,苏轼力主多样化,他在《答张文潜书》中讥刺王安石“好使人同己”,并说:“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体现了他在风格问题上和王安石的分歧。苏轼的这些意见均由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而来,对于当时的种种文弊,无不具有针砭作用。
苏轼以水喻文,强调“自然”的美学风格,具体受影响于田锡和苏洵。田锡在《贻宋小著书》中云:“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生气也,不亦宜哉!……使物象不能桎梏我性,文彩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咸平集》卷二)田锡为蜀人,苏轼曾为其《咸平集》作序,他们在强调创作个性方面以及对文学的功用的认识上,有一致之处。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云:“故曰‘风行水土,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故乎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惟水与风而已。”(《嘉佑集》十四)这里,以风水相遭成极观衬“无营而文生”,追求一种不知其迹之所存而自然自得的境界,以此为文章的极致。“自少闻家君论文”的苏轼,自然对此默会于心。
苏轼的“自然”说,在金、元、明、清均不乏知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赵秉文、王若虚、李贽、叶燮、刘熙载等均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加以借用、发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明代公安三袁的影响。东坡之“自然”说实际上已蕴涵了“性灵”“趣”等因素,只是由于价值思想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差异,苏轼不特如三袁那样将“性灵”、“趣”与“嗜好情欲”互相沟通而已。苏轼的“自然”风格美学理想,并非仅仅限于文章方面,在诗歌方面体现为“天工”与“清新”之论,在绘画方面则有“随物赋形”之说,可视为是他对艺术创作的基本美学规律之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