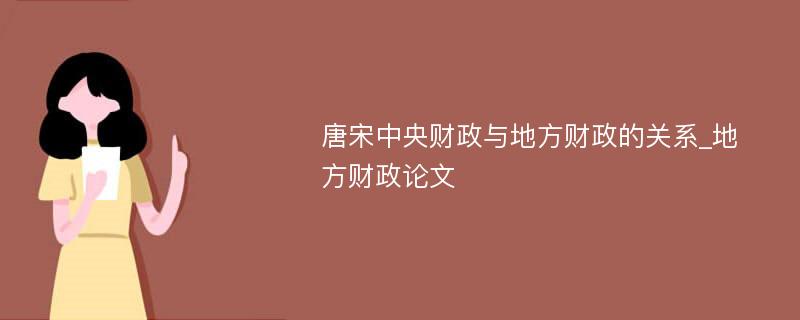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地方财政论文,时期论文,中央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K244;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5-0095-06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提到的唐宋时期,主要是指实行两税法以后的唐代后期及北宋时期。这主要是基于唐前期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国家税收由中央统购统支,地方政府只有如期完税,纲典上供,转运输纳的义务、却无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而南宋政权由于建立于兵荒马乱之中,实行的是战时经济体制,故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本文旨在从唐宋时期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配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管理等方面进行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学者。
一、唐宋时期的两税三分制
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占据河北诸州的节度使,大者跨州郡,小者兼数城,拥有节旄,专制一方,“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1](卷六四,《方镇表序》)。受连年战乱的影响,均田制迅速崩溃。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本是唐前期国家税收的支柱,因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中央的财政收入骤然减少,唐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支离破碎。此后数十年间“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2](卷一一八,《杨炎传》)。节度使的侵夺财权,对中央政府长期执行的税收统购统支体制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唐玄宗就在向成都逃亡的路上,颁令赋予地方节度使各种权力,在财政方面,即是“应须士马、甲杖、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3](卷一八,至德元年七月)。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中央朝廷鉴于地方政权尾大不掉,难于驾驭,於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正式颁布了“两税法”,将国家的全部税收分成中央直接受益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两大类,原属于中央财政的部分税收和部分财权划归地方。这一法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唐前期以租庸调为支柱的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和唐后期以两税法为核心的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
“两税”泛指夏税和秋税,包含的主要是地税和户税。两税法制定之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4](卷八三,《租税上》),故应包括在内,另外,“两税”中还包括向商人征收的资产税。两税是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共享的主要税目,“自国家制两税以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为人,定额以给资”[5](卷六五一,《钱货议状》)。则明确了对两税收入的三级划分。上供自然是指地方供输朝廷的财赋,留使是相对地方藩镇而言,如相对州而言,则称为“送使”;留州指留在本州。唐武宗曾发布敕文说:“州府两税钱物斛斗,每年各有定额,征科之日,皆申省司。除上供之外,留后(即留使)、留州任於额内方圆给用,纵有余羡,亦许州、使留备水旱。”[5](卷七八,《加尊号敕文》)这说明,在完成上供朝廷的定额之外,藩镇和州可以自由支配属于留州和留使额的地方财赋。
宋朝沿袭了唐朝的两税三分制的财政政策,其中上供指直接运送至京师的财赋,包括以“谷、帛”为基本内容的夏、秋二税、榷货、金银课利,以及熙宁、元丰年间新增加的兔役、常平、坊场钱等。地方财赋除上供部分外,另有军资库钱(即留州)、公使库钱(即送使)。宋代军资库、公使库的钱物属于“系省”,即实际留在地方的财赋,在名义上属于中央,原则上支用权归属朝廷,地方不得随意支用。宋初通过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政权的措施,地方行政单位——州县已不能成为一级财政单位;作为地方财赋存储的军资库虽然遍设于各州,但州县长官并无实际的支配权。只有中央派驻的路转运使作为地方财政的主管,拥有实际的地方财政支配权,送使也成为上缴直属中央的路转运使,唐代后期的藩镇屯兵自养,擅自截留上供租税的现象和自由支配留使、留州的地方财赋的权力,随着宋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已经不复存在,送使和留州的内涵与唐代相比已迥然不同。
二、中央对榷利的征收和管理
唐后期中央的直接受益税目有盐税、茶税、酒税、矿产税,以及关税和市税等。在唐代,茶、盐、酒和矿产等皆由国家实行控制,一般由国家专营买卖,称为榷盐、榷茶等。史书中对榷利的收入不乏记载。如代宗大历末年,“通计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4](卷八七,《盐铁转运总叙》)。德宗建中三年(782)“禁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军费”[6](卷一一)。德宗时还下令“天下山泽之利,当归王者,宜总榷盐铁使”[2](卷四九,《食货志》)等等。征榷之利自唐代实行两税三分法以后,始终是由中央朝廷控制,作为国库的大宗收入。这点与后来的北宋初年相比,是非常突出的。
宋代立国之初,榷利实际上是由中央和地方共享的。各项专卖收入均是由地方管理,路转运使掌握,以完成上供和地方开支。如前所述,宋承唐制,地方财赋包括上供、军资库钱(即留州)、公使库钱(即送使)三大部分。其中军资库者,主要用于地方的驻军和行政开支,“旧制每道有计度转运使,岁中则会入诸邑之出入,盈者取之,亏者补之”[7](卷二四,《国用二》)。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7](卷二四,《国用二》),主要是封建统治者为减轻地方上因支付往来使臣厨传费用不堪重负而设置的,但朝廷所给十分有限,“而著令许收遗利”[7](卷二四,《国用二》),即商税、茶盐课、酒榷、坊场钱等。北宋前期对地方财政“未尝立拘辖钩管之制”[7](卷二四,《国用二》),“至于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是以未尝立为定额”[7](卷一九,《征榷六》)。根据史料记载,宋初财政收入的大宗盐、酒、茶等榷利,有相当一部分归州县支配,如“国初盐荚只听州县给卖”[7](卷一九,《征榷六》);“东南酒课之入,自祖宗时悉以留州”[8](卷一四,《东南酒课》);“凡茶之利,一则卖以实州县,一则沿边入中粮草算清,以省馈运,一则榷入纳金银铁帛算请,以赡京师”[7](卷一八,《征榷五》)。至于酒课,在庆历以前大都是“藏之府县而已”。史料中就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曾令诸州以茶盐酒课利送军资库的记载。
这种主要由地方掌握榷利的状况一直延续到真宗朝方有所改变。神宗朝以后,朝廷开始逐步通过改变专卖形式等措施,使榷利由地方转归中央直接管理和支配。如茶利,“至蔡京始复榷法,于是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7](卷一八,《征榷五》)。盐利在徽宗朝以前始终是“东南盐岁自钞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9](卷一一),蔡京扩大钞法,将盐利集中于榷货务,聚于京师,使得这一地方财源完全转归中央所有。这种茶盐榷利归属的变化正如宋人李纲所言“夫茶盐者,天下之经费也。异时官运收息,郡县之用所以足者,以茶盐之利在郡县也,比年走商贾实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盐之利在朝廷也”[10](卷一四四,《理财论中》)。除此而外,“自熙宁以来,坊场河渡、白地房廊、坑冶、市舶、农田水利各置提举,而利权不在州县矣”[11](续集,卷五四);又“熙宁以前,买扑之利归于大户,酬奖之利归于役人,州县坐取其盈以佐经费,以其剩数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宁悉罢买扑酬奖之法,官自召买,实封投状,其价最高者得之,其旧章废也”[7](卷一九,《征榷六》)。大致在神宗朝以后,宋代前期那种茶盐榷利由地方掌管,中央与地方共享的局面逐渐不复存在,征榷之利最终与唐代相仿,成为了宋代中央直接掌握的大宗财政收入。
三、对地方政府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
唐后期地方政府对两税的管理权限可以概括为:州县长官(特别是刺史)拥有相当大的两税制税权,藩镇长官拥有部分两税放免权。在唐后期,两税收支定额基本以州为单位,各州的两税预算收入总额有黜陟使、观察使及刺史共同制定,其中由黜陟使代表中央行主管之责,观察使行刺史上司的监督之则,具体承办本州的配税,派税工作的则是州刺史。唐宪宗曾言,“两税之法,悉委郡国。”[5](卷六○,《直两税使诏》)除此而外,作为基层的官员、两税纳税户的“衣食父母官”的县令,也拥有一定的制税权限。藩镇长官通常不参与制税,但对其支州两税收入定额的完成负有督促之责。较之州县长官,藩镇长官的两税管理职权主要在于拥有部分两税放免权。例如唐宪宗平定西川叛乱后,颁令“留州、留使钱委观察使量事矜减”[12](卷九一,《邦计部·蠲复三》);德宗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允许“列州互除租,凡三年一复”[1](卷一五八,《韦皋传》)等。
唐代后期中央对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是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来实现的。各州两税预算的定额指标有四项:即预算收入总额、留成额、上供额以及藩镇的留成额。两税预算定额管理有利于保障唐中央朝廷对两税上供部分的获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两税收支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比部勾覆制度和御史弹劾制度而进行。比部在每年年终都要对地方的财物账目进行审计,其对象主要是刺史,文宗大和四年(830)比部明确规定了刺史可以合法支用留州额结余的五种财务范围,获得了文宗的批准。对于藩镇两税收支的监督则主要是通过御史弹劾制度来执行。如宪宗时期,监察御史元稹弹劾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于两税定额外加税钱、米、草[13](卷三七,《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文宗时期,天平军节度使殷侑“不由制旨,增监军俸入”,受到御史大夫温造的弹劾,殷侑因此被调职[2](卷一六五,《殷侑传》)。当然,对唐代中央监督藩镇两税收支的效果不能估计过高,盖因其中央集权的强弱变化而变化,如在宪宗朝成效较为显著,武宗以后则逐渐形同虚设。
宋代各地的上供岁额由国家制定,地方长官并无制税权。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具体的上供岁额方面,各路分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国家根本,仰给东南”[14](卷三七七)。江南六路是宋代的经济中心所在,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向以上供岁额最重而著称,而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因“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不仅岁赋基本全部留用,朝廷还不时拨出巨额经费以助军用,从而造成了各地方机构的上供与留用、乃至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体制内部的不平衡现象。
宋代对地方赋税的征收主要由以转运使为核心的路转运司负责。转运使一职始置於唐玄宗年间,主要为转输江淮财赋以供京城。赵宋立国后,“惩五季之乱,藩镇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7](卷六一,《职官十五》)。转运使隶属于三司,作为朝廷派驻路级地方的主要长官,凡一路租赋、漕运、和买、坑冶、茶盐酒榷及朝廷封桩于地方的财物,全都负有督管之责,故称作“漕司”。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六十一《职官十五》中总其职能为“催科征赋,出纳金谷,应办上供,漕辇纲运”,简言之,“经度一路财赋”。两宋的赋税征收,主要是在路转运使的督责下,由州县完成的。据《宋史·食货志上二》》载:“诸州税籍,录事参军按视,判官振举。形势户立别籍,通判专掌督之。……岁起纳二税,前期令县各造税籍,具一县户数、夏秋税、苗亩、桑功及缘科物为帐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长吏厅,县籍亦用州印,给付令佐。”征收完毕的粮帛等由转运使依据定额转输京师和经度一路的费用。与唐后期的藩镇不同,宋代的路转运使并无两税的放免权。如遇天灾年景,地方拖欠岁额而又无法补足时,路转运使只能奏请“特赐依阁”而不得擅自行事,根据实际情况酌减田赋的决定权掌握在朝廷手中。如哲宗元符三年(1100),两浙路奏请特赐依阁拖欠朝省钱三百五十万石,哲宗批准分十五年拨还,自第二年起,“每年许管还一分,逐年终”[15](《食货》四九之二四)。宋代前期中央通过设置路转运使一职“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有效地对州县地方财政进行调控和管理,从而保证了京师和地方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
“天下支用悉出三司”乃宋朝廷的基本法度,地方经费也要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7](卷二三,《国用一》)。即规定了系省钱物不得随意支用。宋朝在州一级推行“记账”法,即预决算制度。《文献通考》卷二十三《国用一》载:“诸州应系,(省)钱物,合供文帐,并于逐色都下具元管年代,合系本州支用申省。候到省,或有不系本州支用及数目浩大,本州约度年多支用不尽时,下转运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据在京要用金银钱帛诸般物色,即除式样遍下诸州府,具金银钱帛粮草收、支、见在三项单数(其见在项内开坐约支年月)。省司即据少数数目下诸路转运司移易支遣,即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约度不足之处,许以收至逐色课利,计置封桩。”这段史料说明了州级地方官虽然不需要逐一开列收支细目,却需要每年开列该年度的收支总数,年终汇总申报一次,并且预计下一年度支用总数,称为“年计”或“岁计”。宋太宗时期还健全了应在司,“居无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7](卷二三,《国用一》),用以负责地方的岁终上计工作。另外,宋初还设置了三司都磨勘司“掌覆勾三部帐籍,以验出入之数”[14](卷一六二,《职官二》)。通过对地方财赋中上供部分的限期、限额征收,预留部分的岁终上计及勾稽磨勘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北宋朝廷强化了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彻底铲除了唐中叶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经济基础。
四、中央削减地方财政的主要措施
唐代后期,以藩镇节度使为代表的地方分权势力既争夺两税上供额,又争夺中央直接受益税,无疑从财政上威胁着唐中央政权。因此唐中央朝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地方财政进行限制和削弱。除三令五申地要求各地藩镇遵守两税预算定额管理制度,禁止藩镇擅自减少上供额等外,主要措施一是改变两税送使与上供的程序和数量关系,变相地减少地方的两税提成。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度支奏论重编两税预算计划曰:“……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指藩镇会府州),合送上都税钱(指两税上供额),即须差纲发遣,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须重迭。其诸道留使钱,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指会府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亢,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指藩镇支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4](卷八三,《租税上》)这反映出唐中央力图削弱藩镇与其支州的财政联系,加强中央对州级两税收入直接控制的意图。经过几次修订两税预算计划,取得的效果是除会府州外,藩镇支州的送使钱比从前有所减少,而上供额有所增加[16](pp.233~235)。二是推行朝廷对“中外给用钱”的常额“抽贯”与额外“量抽”的“除陌”法,变相减少地方财政收入。“除陌”主要是从留使、留州的地方钱中抽取巨额税钱。穆宗于长庆元年(821)诏令曰;“诸道除上供外,留州、留使钱内每贯割二百文,以助军用,贼平后仍旧。”[2](卷一六,《穆宗纪》)中央“除陌”所得应不在少数。另外在德宗和宪宗朝,通过鼓励各地藩镇向皇帝进奉财物,唐中央也向藩镇夺取了一定的财力。宋人范祖禹解释德宗热衷进奉的原因是:“德宗欲刬灭藩镇,故聚天下之财。”[17](卷七,《德宗》)而对藩镇来说,其进奉的财源既有“割留常赋,减刻吏禄,贩鬻疏果”,又有“增敛百姓”,从中受益最大的还是他们自己。
根据史料记载,北宋初期的地方财政是比较宽裕的。宋人陈傅良曾说:“国家肇造之初,虽创方镇专赋之弊,以天下留州钱物尽名系省,然非尽取之矣。当是时,输送毋过上供,而上供未尝立额,郡置通判,以其支收之数上计司,谓之应在,而朝廷初无封桩起发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应在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以七千八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可谓富藏天下矣。”[18](卷一九,《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这段话道出了宋初地方财政的充裕状况。真宗景德四年(1007),朝廷开始订立诸路漕运米数;大中祥符元年(1008)始立银纲,逐渐加强了对地方财政的管理,意在保证中央财政的充足。自真宗朝开始“四十年间理财之令数下”[7](卷二三,《国用一》)。宋神宗年间启用王安石变法,主要的目的是为削减地方财政,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陈傅良紧接着言道:“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诺路岁额,熙宁新政,增额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一路增至十数倍,至今为额。其他杂敛皆起熙宁,于是有免役钱、常平宽剩钱,至于元丰,则以坊场税钱、盐酒增价钱、香矾铜锡斗秤批判之类凡十数色,合而为无额上供,至今为额。至于宣和则以赡学钱、籴本钱,应奉司诸色无名之敛凡十数色,合而为经制,至今为额。”[7](卷二三,《国用一》)其中所说名目繁多的无额上供,到了宋徽宗年间,则进一步改为了立额上供。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地方财政来源被压缩,转运使的权力被削弱,“凡赋税、常贡、征榷之利方归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榷货户绝没纳之财悉归朝廷,其立法与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禁军缺额地利之资皆号朝廷封桩,又有岁课上供之数,尽运入京师别创库以贮之,三司不预焉”[11](后集,卷五四)。王安石变法时期,在诸路设提举常平司,直接管理新法所开辟的财源。熙宁九年明确规定:“常平、钱谷、庄产、户绝田土、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渠委提举司专管勾。”[19](卷二七九)时“天下利源所在,皆归常平使者,转运司岁入之计,惟田赋与酒税而已”[20](卷七,《应诏论四事状》)。提举常平司隶属于司农寺,不属于地方财政系统,三司亦无权过问。宋初的“天下财用悉出三司”至此转而为与司农寺共同理财的局面取而代之。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国库收入,随着边衅屡开,连年用兵,朝廷对地方的上供额度在逐渐加重。至南宋半壁江山,国用日蹙,朝廷新增加了经总制钱、月桩钱等名目,向州县增派岁赋,“所以倚办责成于州县者,以其原有桩留之赋”[9](卷二四,《国用二》),即是说已经将州县原有的财赋几乎剥夺殆尽。而州县也因此擅自加重对民间的科敛,如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都省言:“南渡以来,诸路上供数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数虽减,而州县犹以大数拘催,害及百姓。”[14](卷一七九,《食货下一》)最终是加重了民间的负担。
综上所述,唐代在安史之乱后,鉴于藩镇专擅财税与财权的现实,建立了两税三分制,将国家税收划分为中央直接税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两大部分,之后为保障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反复地争夺。唐代是从中央高度的财政集权过渡到中央和地方既有各自的财政收入,又有双方共同分享的税收的财政体制。北宋立国后恢复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然而在财政税收方面,一方面承袭了唐代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同时初期对地方财政“未尝立拘辖勾管之制”,上供无有定额,对于’朝廷留在州郡的系省钱物,“长吏得以擅收支之权柄”,颇为宽松。真宗以后朝廷逐渐加强了对地方财源的挤压,至王安石变法,中央始将地方收入剥夺大半,直至北宋末年才正式完成了事实上的一切财权收归朝廷的进程。
收稿日期:2003-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