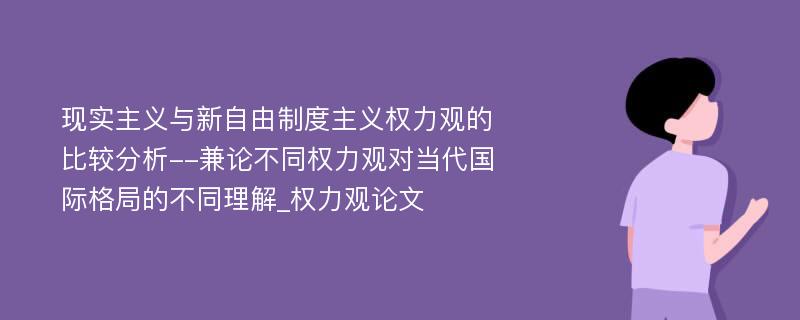
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权力观之比较分析——兼谈不同权力观对当代国际格局的不同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格局论文,观之论文,当代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力(power,或翻译为“强权”、“实力”、“力量”等)这一概念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广泛使用。在现实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权力更是无所不在的焦点,是构成和决定冲突与合作的根本原因。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无论它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什么不同,都不得不关注、重视乃至追求权力,因为尽管全球化的深化导致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的作用日益突出,但是国家却依然处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之中,而权力也依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并且还是影响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变量。然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历来就对权力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有学者甚至发现了至少17种不同的关于权力的定义。① 无怪乎,罗伯特·吉尔平认为:“有关权力的定义如此之多,这是令政治学家们感到尴尬的事情”。②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不同的学术流派对权力解说和分析也是不同的,而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分歧,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权力观是完全对立的。本文拟着重对此做一些比较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两种不同的权力观对当代国际格局的不同理解,以期引起国内国际关系学术界同行的进一步讨论。③
一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流派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最为引人注目,不仅仅因为其悠久的历史,更因为其简洁明了地描述了国际关系的现实。
国际政治学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鼻祖汉斯·摩根索将权力定义为“人对他人的心灵和行动的控制”④。他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其行为的本原在于追逐权力、保持权力和炫耀权力。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则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出发,进一步指出大国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对象,它们为了生存和安全而需要拥有权力。近年来产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有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⑤ 同时由于“国际事务在本质上都是冲突的”、“国家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国家必然自助,政治事务的最后仲裁者就是权力”,⑥ 因此不论何种流派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都认定: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或曰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
在对权力的内容或基础的论述中,摩根索清楚地列出了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等九方面,并将其分为相对稳定的要素和不断变化的要素,⑦ 其中他认为武力是最经常的方式,而“在有助于国家强权的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外交的素质,不管它是多么的不稳定”。⑧ 沃尔兹认为,权力应该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即不仅包括军事力量还要重视经济力量。他认为,“由于国家处于一个自助系统中,所以必须使用自己的综合力量以促进自身利益。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其他能力不能被割裂开来分别加以衡量。”⑨ 米尔斯海默则指出“权力以国家拥有的某种物质能力为基础……权力不过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⑩ 由此可见,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者们对于权力的认识即便强调综合国力,但是却主要集中于其物质性的一面,并且强调军事经济实力在权力构成中的基础地位。
现实主义者赋予权力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权力或者是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或者是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关系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摩根索明确指出:“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搜寻国际政治领域内通道的主要路标是用权力来定义利益的概念”(11),即国家执行政策的依据是由权力所决定的国家利益。沃尔兹则认为国际政治结构除了无政府状态这一原则以外,国家间权力的分布及其变化也会影响到结构的变化。米尔斯海默更是极其崇尚权力,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安全的稀缺性,必然导致各国追求权力最大化和希冀成为体系内的霸主。
总之,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大都认为民族—国家尤其是大国是国际政治中权力的主要载体,国际政治就是大国间的权力政治或干脆就是强权政治。现实主义在定义权力基础时认为,物质性力量,如经济、军事实力才是最为重要的,其中尤其是军事实力是决定国际政治行为的决定性变量。
二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派别之一,它是在继承自由主义的传统基础之上,融合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合理假设,采纳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凭借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与国际组织作用日益增强的国际社会的深入研究而形成的一种机制理论。它的理论核心在于,以国家间相互依赖为前提,重新认知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利益,提出国家在国际政治的自助体系内更加关注绝对利益的获取,同时运用制度经济学有关交易成本、信息费用和不确定性等研究方法,提出国际社会中应该是合作大于冲突。此外新自由制度主义还强调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惯例等制度能够保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对国际制度的强调,而且还在于它有一套独特的关于权力的看法,其中尤其是它的权力观与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有鉴于此,我们将就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权力的定义、权力的来源、权力资源的转化和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等四个方面做比较系统的考察,并由此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观与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进行全面的比较。
首先,在权力的定义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力,即某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其代价为前者可以接受)。但是,权力还可以视为对结果进行控制的能力。”(12) 很明显,新制度主义的这种定义与现实主义的观点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相互联系在于,都确认权力是一种能力,它能使拥有者(大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让他者(小国)做原本并不一定愿意做的事情。而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是从手段上定义的,即强调实力强大的国家对于他国的一种直接的强制能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规则是从结果上定义,强调权力行使对象对于权力的接受程度以及行为体对结果模式的实际影响。其二,现实主义的权力定义缺乏对权力施予者与被施予者之间互动的考虑,仅强调权力主体单向度的行使权力;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定义则是双向的,包含了权力行为主体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次,在权力的来源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的主要来源除了物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应该包括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状态。当我们说非对称相互依赖可以是权力的来源时,权力被视为对资源的控制或对结果的潜在影响。在某种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拥有较强的权力资源。(13) 此外,国际制度、网络信息等由于也能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相互交往所产生的结果具有实际影响,因此也都应该被视为权力的来源。由此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具有很强的情境性特点,即认为权力应该还来源于一定的情境之中,如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等。另一方面,由于权力还在于对结果的实际影响,因此那些能够对结果实施控制的机构、网络、制度和信息等等都应该成为权力的来源。
再次,在权力是否需要通过一定的中间体得以转化的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持否定的态度。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权力是国家独有之物,国家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就拥有更多的权力,其间没有什么需要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权力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使存在权力资源向权力的转化问题也是国家内部处理的问题,与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无关。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因其权力观强调情境性和对结果的影响,则认为拥有权力资源只是拥有权力的一个基础条件,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参与,没有合适的转化渠道,权力很难得以实现。一般而言,政治谈判是将潜力转化为影响的手段。(14) 同时,国际机制也是一个合适的转化渠道,因为“一般的说,机制的原则确定了其成员期望追求的目标”。(15) 国际机制由此通过确定国家追求的目标来引导国家行为,而权力资源对结果的影响就在国际制度中得到了实现。
最后,在如何看待权力的地位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像现实主义那样简单明了。现实主义不是将权力视为国家追求的目标(经典现实主义),就是将它视为保证国家生存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结构现实主义),而无论如何,权力都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权力虽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其地位却取决于不同的解释模式,在决定哪种解释模式适用于某类情况或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清楚现实主义或复合相互依赖与该现状相符的程度。(16) 不同条件下应该适用不同的解释模式,因此不同解释模式中的权力的地位也就必然不同。另一方面,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伴随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增加、国际政治本身渐渐超越国家间政治的范围,于是,权力也必然会受到制度、信息、相互依赖等等条件的竞争、制约和影响,其地位相比之下也就明显有所下降。
此外,新自由制度主义更为强调说服性权力(persuasive power)或软权力(soft power)的作用,而现实主义则更强调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或硬权力(hard power)的作用。强制性权力或硬权力主要指依靠诸如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等强迫他人服从自己,从而达成自身目的的能力,而说服性权力或软权力指的是利用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力量,产生对他人的吸引,进而影响或说服他人自愿地服从自己,从而也达到自身目标的能力。与硬权力的运用不同,软权力的运用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达到自己预设的目标。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应该包括下述三个方面: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17) 在2004年3月所作的题为《软权力:在国际政治中赢得胜利的手段》的演讲中,奈指出:“在反恐战争中军事力量对取得胜利而言并不是不必要的,阿富汗战争就是实例和证明,但是光有军事力量并不够。我所担心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过于强调我们的军事力量而忘记了我们需要结合运用软权力。因此我们需要从冷战中吸取经验,作为一个聪敏的大国你必须有能力将硬权力和软权力相结合。当前我们没有正确地使用这一公式。好消息是在过去我们曾经这样做过,而在原则上,我们在未来也能再一次这样做。”(18) 由此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软权力的作用是丝毫不能忽视的。
三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观与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差异呢?具体原因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新自由制度主义有着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时代观。我们知道,按照现实主义的基本理念,直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时代,也就是一个权力政治(强权政治)的时代。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体系的大国强权政治特征在21世纪初并没有变化,世界仍是由在无政府状态下生活的国家所组成。(19) 罗伯特·吉尔平甚至声称,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际政治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仍可以理解当今的世界。(20) 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强调,任何国际政治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总体环境,而时代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指出:“国际制度正朝着这样一个后威斯特法利亚时代的方向发生演变。”(21) 而国际体系的具体变化就在于目前的国际政治图景已经开始从现实主义的三个假设——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武力是支配性的手段;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向“复合式的相互依赖”的三个假设转变:(1)国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跨国行为体也是重要的角色;(2)武力不是唯一重要的手段——经济控制和利用国际制度也是支配性的手段;(3)安全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福利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22) 既然时代发生了变化,或至少正在开始发生变化,那么权力的本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不仅对权力的定义要有新的改变,而且还需要用新的视角探索权力的来源,同时又必须注重权力资源的转化并注意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变化。总之,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主义原则开始逐步失效,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包括其中最主要的行为体——主权国家需要更多地强调依法行使权力和合法拥有利益。从1945年发表的《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56条要求成员国承担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集体责任,就可以看到国家权力的本质在发生变化。(23)
第二,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球化是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的推动下,世界经济通过世界贸易、跨国投资、国际金融的作用,不断实现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市场不断地在更深和更广的层面上整合,生产要素和产品跨国界流动的速度和数量不断加快和加大,整个世界因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导致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强,而时间和空间也产生巨大的压缩,同时全球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深受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而同样显示出一体化的倾向。(24) 毋庸讳言,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信息革命对于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正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促使全球高度网络化,时空紧缩化,跨国参与不断强化,经济边界加速退化,政治疆界逐渐淡化。所有这一切都实质性地促使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相互依赖。
正是在全球化环境中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客观条件下,决定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权力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开始发生变化。新自由制度主义正是抓住这种变化提出了与现实主义大异其趣的权力观,其中特别是通过分析相互依赖的特点来说明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际体系中的相互依赖状态本身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根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分析,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拥有较强的权力资源,该行为体有能力触动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而一旦该关系发生变化,则相比较而言,该行为体方付出的代价小于他方。”(25) 此外,相互依赖还可以区分为“敏感性”和“脆弱性”两种,前者产生于政策框架内的互动,指政策框架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各行为体对同样事件做出反应的程度;后者产生于政策框架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指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付出的代价。在向行为体提供权力资源方面,脆弱性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大于敏感性相互依赖。(26)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环境中,正确地操控相互依赖也能够影响到各个国家权力的变化。依赖性较小、对资源控制更有利的一方,往往并不比那些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行为体更弱。
第三,国际制度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国际制度的深入研究,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新权力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罗伯特·基欧汉的观点,国际制度是指“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持久的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27),并且还包括“帮助实现这些规则的组织”。(28) 也就是说,国际制度既包括为约束国际关系某一领域的行为体而设立的原则、规范和程序,同时还包括为执行、监督和修改国际制度而设置的国际组织。因为国际组织是国际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国际制度的载体和现实表现形式。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包括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29)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制度迅速发展,以致今天在各个不同的国际关系领域一般都有自己的国际制度,像国际安全制度、国际人权制度、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环境保护制度等等。这一系列国际制度的共性在于它们具有相当的法理型权威特征,因为它们具有在不同的程度上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并且能够得到国际体系中行为者,尤其是迄今为止最为主要的行为者——国家的赞同。
国际制度的作用在于改变了国家的决策环境:国家从有限理性出发,经过成本—收益的分析,形成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和对他国行为的合理预期,预设了国家决策的范围和后果,因此国家会自觉遵守国际制度,形成合作共赢,国际制度也就成为保证国家合理行为的原动力。国际制度赋予国家以权力,而不是束缚政府的行动。(30) 由此可见,在国际制度的作用下,权力可以被制度化,对权力资源的控制在相当多的场合需要通过制度来发挥其对结果进行影响的能力。虽然国际制度本身依然具有很大的合法性缺陷,但是国际制度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如果没有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的参与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尽管它们并不能取代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然而,正是因为国际制度的现实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国家提出国际议题、创设国际制度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伴随着国家发展程度而不断变动的,因此具有很大的动态特征和可操作性。国际制度这种对权力的强烈影响,自然给予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以新的理论来分析权力的依据。
四
也正是由于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在权力观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两者对后冷战时期即两极国际格局之后的国际格局的演变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这样的不同看法,不论对我们如何认识今天的国际局势,还是对我们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国际格局的理念产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国际体系结构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比如罗斯格罗斯、卡普兰以及霍夫曼乃至基辛格等都对国际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格局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直到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问世,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分析才臻于完善。沃尔兹认为:“在系统理论中,结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产生了系统的结构”。(31) 沃尔兹这里所说的“系统的结构”,实际就是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格局。沃尔兹进一步认为:“对于国际政治这个系统,需要全神贯注于影响最大的国家。有关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必然是以大国为基础的。”(32) 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下述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国际政治的体系,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重视自身利益的单元的共同行动而形成的。国际结构,是根据一个时代的基本政治单元来界定的,不论这些单元是城邦国家、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结构产生于国家的共存局面。”(33) 而正是国家的共存局面使得国际格局的秩序始终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之下。其二,“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系统的单元,不是根据它们所担当的功能不同而加以正式划分的。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之间的关系是同等关系。”(34) 这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中构成国际格局的单元——国家的性质、功能、类别都是一致的。其三,“(国际)结构的不同,不是由于单元在特征和功能上的差别,而只是由于它们之间能力的不同而引起的。”(35) 沃尔兹这里所说的单元的能力就是指国家的权力,而国际政治格局则是由拥有强大权力的大国所决定的。由此“研究国际政治的人,只根据大国的数量对国际政治系统进行划分。”(36)
根据沃尔兹的分析,决定国际格局本质的三个重要原则——单元排列的秩序、单元的功能和单元的能力分配——之中,只有第三项是可变的因素,因此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也就自然非国家的权力,而且是非大国的权力分配莫属。于是,从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大国就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单元,而拥有强大的物质权力——“军事、经济和其他能力”的大国就构成了国际体系中的“极”——国际格局中的权力中心。由此,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就是随着大国权力的此消彼长而形成“多极的”(由三个以上大国统治的)、“两极的”(由两个大国统治的)或“单极的”(由一个超强大国统治的)国际格局。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者们对于权力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其物质性的一面,并且强调军事经济实力在权力构成中的基础地位,因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的国际格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宣告终结之后,西方绝大多数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者,都根据冷战后大国间的权力分配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因为“今天的美国的突出实力在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大国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及政治势力方面曾经有过如此绝对的优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它有任何真正的竞争者”。(37)
然而,虽然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承认国际体系结构的无政府性,但是由于他们的权力观与现实主义有很大差异,即认为权力的主要来源除了物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应该包括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状态,同时他们还强调权力行使对象对于权力的接受程度以及行为体对结果模式的实际影响,关注权力行为主体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们对当代国际格局的演变也就有着与结构现实主义者们十分不同的看法。约瑟夫·奈指出:“一些人把苏联解体后的世纪称作单极世界,还有一些人称作多极世界。双方都对,双方又都不对,因为双方都只强调了力量(权力)的一个侧面,而这里所说的力量现在已不能够被仅仅看作军事优势。单极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夸大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能够随心所欲的程度;多极化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它的意思是有一些力量大致相等的国家。”(38)
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今天权力在国家间的分配,类似一盘复杂的三度空间的国际象棋。其中第一度即军事力量这一维度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但是第二度也就是经济力量这一维度则是多极的,而第三度作为国际格局大棋盘的底部更是无法用“单极、多极或霸权加以描述”(39),因为在这一维度上包括形形色色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权力在这一维度上并不集中于国家这一传统的行为体手上,而是分散在各种不同的行为体,甚至包括国际恐怖组织这样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之中,不仅如此,权力在这里并不以传统的军事乃至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还更强调其情境性和对结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国际格局的这一基础层面,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参与,没有合适的转化渠道,权力很难得以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将第一和第二度的空间联系起来看,那么就会得到“一些观察家称之为单极—多极杂交世界”。(40) 但是,如果将三度空间统合在一起观察,眼前的世界就很难用“极”的概念来做界定了。虽然约瑟夫·奈似乎并没有对这样的国际格局下明确的定义,不过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却明确地指出:“我认为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既非多极亦非单极。”(41)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是在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们在对时代发展的新认识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权力观的一种革新,因此通过其新的权力观而对当代国际格局的分析似乎显得更加贴近实际。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权力观并没有彻底否定传统的现实主义权力观,这不仅是因为现实主义毕竟反映了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的实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世界体系还没有完全转换为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国际格局也依然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这也就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因传统的权力政治的客观存在而仍有其解释的力度,因而从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出发,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视为美国霸权下的单极格局或正在走向多个力量中心并存的多极化,也就依然有其“市场”。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目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着千百年来的大变革,当代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已开始导致世界大变局的产生。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大国的权力虽然依旧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其性质、地位却在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变量已经不再仅仅为大国的权力。在一个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如欧盟、东盟等,乃至正在引起所谓“全球结社革命”的无以计数的国际、国内和地方的非政府组织,都在运用它们的权力(主要为说服性权力或目前通常所谓的软权力,但是更确切一点的说法似乎应该为“市民或公民权力”)来影响全球事务。(42) 然而,很明显,这些国际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本身及它们的权力与国家及国家的权力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当它们在全球化世界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传统的国际体系结构也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以大国权力为基础的“极”的国际格局将不可避免地要被以不同性质、不同功能和不同类别的行为体共同作用的“元”的国际格局所取代。(43) 这就意味着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大国在今天的世界中仅仅只是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一种单元,而与之性质、功能、类别不同的,拥有新型权力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其他类型的单元,也在同时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影响。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因此是在这一系列性质不同的单元的互动中展开的,由此,现实的国际格局也就逐步超越沃尔兹及其他现实主义学者所分析和推演出的单极、两极或多极结构的范围,向着网状的“多元”结构方向发展演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格局超越“极”的结构而向“元”的结构发展是一个复杂且持久的过程,其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尤其是大国依然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大国的权力也依然在国际格局的演变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在特定条件下还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2003年美国就是运用其超强的国家权力、绕开联合国实行对伊拉克的入侵,从而使得整个国际格局显示出一超独霸的单极时刻,虽然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日益加剧,这样的单极时刻似乎如过眼烟云,但是只要大国的权力依然在今天的国际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格局的单极、两极或多极的发展也就仍然成为某种可能,或者至少被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者们认为可能,由此可见,超越“极化”的“多元化”国际格局虽然已经开始显示出其客观发展势头,但是这种新型的国际格局的完全确立依然任重而道远,这或许就是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辩证法。
本文为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前国际格局走向与和谐世界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06BGJ004)前期成果。
注释:
① Dennis Sullivan,“The Perceptions of National Powe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4 September 1970.
② 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p.24.
③ 迄今国内学术界讨论现实主义权力观的文章不少,如:张西虎:《现实主义学派及其权力理论述评》,《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李南移:《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概念解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崔海宁:《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比较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讨论新自由制度主义权力观以及将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权力观进行比较的却不多见。
④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⑤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⑥ [美]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⑦ 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第151页。
⑧ 同上,第190页。
⑨ [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⑩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79页。
(11) 本句原文为:“The main signpost that helps political realism to find its way through the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the concept of interest defined in terms of power”(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p.4.)。国内学者对之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本文作者在卢明华等人的译文基础上对这句摩根索的名言做了新的翻译。
(12)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3) 同上。
(14)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2页。
(15)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6)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25页。
(17) 参见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20—36页。
(18) Joseph S.Nye,Jr.,“Soft Power and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Remarks at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May 10,2004,http://www.fpa.org/topics_info2414/topics_info_show.htm?doc_id=225504.
(19)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09页。
(20)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21) [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2) [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23) 同上,第338页。
(24) 不同的专家学者对全球化的解释和定义各有不同,本文对全球化的解释是一种综合性的描述,有关全球化的缘起、含义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作用和影响的具体讨论,可参阅叶江:《大变局——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
(25)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2页。
(26)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2—16页。
(27)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3.
(28) [美]罗伯特·基欧汉:《国际制度:相互依赖有效吗?》,门洪华编译,《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第77页。
(29) 关于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界定,可参见:叶江、谈谭:《试论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及其缺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2期;陈晓进:《“国际制度”概念辨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苏长和:《重新定义国际制度》,《欧洲》1999年第6期。
(30)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第13页。
(31)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4页。
(32) 同上,第84—85页。
(33) 同上,第107—108页。
(34) 同上,第110页。
(35)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6页。
(36) 同上,第115页。
(37) [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8)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治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2页。
(39) 同上,第42页。
(40) 同上。
(41) 参见《文汇报》2003年12月16日,第4版。
(42) 有关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当代国际格局影响的具体分析,请参阅:叶江、甘锋:《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当代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58—64页。
(43) 根据沃尔兹的理论,国际体系中的“极”作为一种单元其性质、功能、类别是相同的,它就是构成权力中心的大国,而本文所言的国际体系中的“元”则是性质、功能和类别各不相同的单元,它们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既可以是政府间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
标签:权力观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格局论文; 资源依赖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全球化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