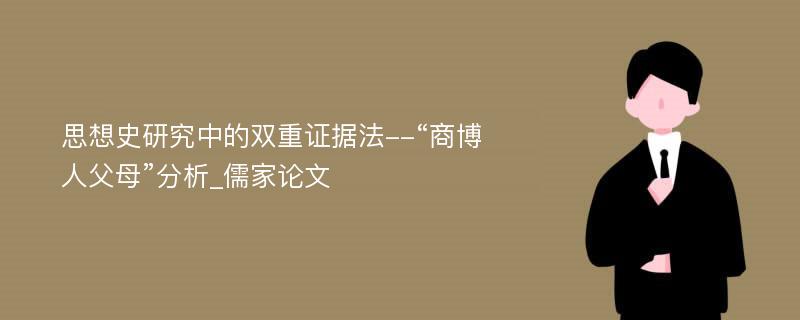
二重证据法研究思想史之一例——上博简《民之父母》篇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例论文,思想史论文,父母论文,证据法论文,篇论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博简《民之父母》(马承源2002:149-180,以下称简本),在诸篇中保存情况最好(注:据整理者濮茅左介绍,本篇凡14简,397字,重3,合6,现状良好,且这14简完全可以连续编联。(马承源2002:151)),其内容又见于传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所以它的发现为研究后者提供了极好的对勘材料。综合运用地下材料(竹书)与地上材料(传世文献)这二重证据,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孔子有关“民之父母”的思想,进入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堂奥。
简本与传本文字有异,因此,需要将诸本进行比勘,发现其差异,考量孰为合理,然后进一步分析其思想意义。由于篇幅限制,对照文字略去,径论其内容。综观诸本,皆含四个相同的关键词,分别是“民之父母”、“五至”、“三无”、“五起”。以下,我们循此一一考察。
一、民之父母
有关“民之父母”,诸本大同,小异可不议。子夏在孔门以文学名,尤擅于《诗》。全篇由论《诗》起。“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见《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冋酌》。关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诗·毛传》认为:“乐以强教之,易以说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四库本《毛诗注疏》,下引不注版本,24:82b)(注:然孔《疏》指出:“《传正义》曰‘乐以至之亲’者,皆《孔子闲居》之文也。彼引此诗以为此言以释之,故《传》依用焉”(同上书,24:83b),则毛《传》所据原为《礼记》。)。而王肃注《孔子家语》,径将“豈”和“弟”释为“乐”与“易”:“恺,乐;悌,易也”(《孔子家语·弟子行第三十二》)。“乐”与“易”又作何解?孔颖达《疏》认为:“乐者,人之所爱,当自疆以救之。易谓性之和悦,当以安民,故云悦安之。”(《毛诗注疏》,24:83b)。
不妨说,“豈”与“弟”所达到的效果分别有如待父之尊与待母之亲。人君具此两者,即可称民之父母。《礼记·表记》正是这样论述的:
《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
要言之,即是以礼乐两手教化人民。
作为一个单独的词语,“民之父母”亦见《诗经》他处,如“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南山有台》)。(注:《诗序》称:“《南山有台》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郑玄《笺》曰:“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贤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礼乐乐之,则能为国家之本,得寿考之福。”(《毛诗注疏》,17:5a)据此而言,人君若能任贤尊贤,即可称为民之父母。这里所说的“乐”意谓“喜爱”(like),它属于情感上的好恶。把“民之父母”与“乐”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引入了情感之维。这一趋向在《礼记·大学》中有更明确的表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即是强调民之父母与民有共同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感(同好同恶)。)
不过,在《民之父母》篇中,子夏所关心的,不是“凯弟君子”何解,也不是“凯弟君子”何以为“民之父母”,毋宁是“民之父母”的含义。孔子的回答也集中于此,且此一论述构成全篇纲领。在孔子看来,所谓民之父母,“必达于礼乐之原(注:“原”,《家语》作“源”,两字通。),以致五至,以(注:“以”,《礼记》、《家语》均作“而”,义同而字异。)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何为礼乐之原?如何可谓“达于礼乐之原”?子夏未问,孔子亦未言。子夏与孔子接着详细讨论的,是五至与三无。
这种言谈及其所反映的致思路向颇堪玩味。这个路向用现代哲学语言表达即是:“达于礼乐之原”是指在实际中做出了可以称得上“达于礼乐之原”的行为,这当然也是一种“知”(Knowledge),但这种“知”主要不是“知道什么”(Knowing What),而是“知道如何”(Knowing HOW)(注:有关“知道什么”(knowing what)与“知道怎样”(knowing how)的区分,参见赖尔(Gilbert Ryle):《心的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所论。),因此知道礼乐之原的定义(“何谓礼乐之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在实际行动中如何去做而可达于礼乐之原,而“致五至”、“行三无”即是通晓达到礼乐之原的根据或手段(“以”)。
有关“民之父母”的讨论,实际上是探究如何做一个好的统治者。从孔子的回答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特点。首先,“民之父母”这种提法本身就带有比较明显的宗法性(Patriarchal),认为国君与他所统治的人民之间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国是一个大家,而国君就是最高的家长。由此不难看出,在儒家政治哲学对国家所做的描画中,并无公共社会(Public Society)的一席之地。与此相连,只有父子兄弟夫妇,而没有类似古代希腊城邦中的那种“公民”(Citizen),围绕“公民”概念所产生的一系列法权观念,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中西政治生活的分野由此已见端倪。其次,按孔子的理解,要成为民之父母,关键在于懂得制礼作乐的根本精神(亦即所谓“达于礼乐之原”)。通常礼乐总是表现为一系列复杂的规则,事无巨细,大小靡遗。孔子在这里提出“达于礼乐之原”的要求,就不无甩开细节而直奔本质的意味,它在理论上包含了对具体仪式做出损益变革的可能,这种变通诚然是基于当时礼乐体系紊乱的现实而采取的一种简明立场。
要弄清孔子所提倡的礼乐之教的具体内容,则应了解作为“达于礼乐之原”手段的“五至”与“三无”。
二、五至
诸本都提到志、诗、礼、乐、哀五至(注:有学者认为,简本所说的五至应是物、志、礼、乐、哀,传本作志、诗、礼、乐、哀,实误(季旭昇:2003)。按:季文对简本过于信从,而对传本则怀疑过甚;其不从传本志、诗之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五至关系解释的困难。),所谓五至,当即指此。五至被设置为一个层进关系,即:从志至到诗至,再到礼至、乐至,最后到哀至,环环相扣、陈陈相因。何以从志至能到哀至?后面出现的“诗礼相成,哀乐相生”,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诗与礼、哀与乐之间关系的一个说明。顺便指出,简本有“哀乐相生”句,而无“诗礼相成”句,应是简本在抄写时遗漏所至,当据《孔子家语》添上此句为是。
在“此之谓五至”后有数语。此数语,简本与传本颇不相同,两传本之间亦小异,其中,《孔子家语》比《礼记》多出一句。对照后文可知,传本这几句出现在简本论“三无”的段落中。显然,简本与传本肯定有一个发生了错简。那么,究竟是哪一本发生了错简?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克于四海”(注:此数句,《礼记》与《孔子家语》小异,较其文意,以《孔子家语》为全,故从之。)这几句,究竟是放在论五至段还是放在论三无段比较合适。
首先,让我们从表达形式入手。“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说的是无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说的是无闻,这与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在遣词上近似。又,与“塞于天地”、“克于四海”类似的话,在简本论五至段亦有发现:“无声之乐,塞于四方”,“无体之礼,塞于四海”。据此不难看出,“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克于四海”这样的话与三无关系更大。
接下来,让我们从义理层面分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君子所行,虽不形诸见闻,但并不妨碍它有良好的效果。换言之,君子正是通过这些看不到、听不到的方式施展其影响,这个意思与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正好相通。相比之下,“明目而视之”与上述论五至这些话,不仅在遣词造句上相去甚远,在意思上也看不出有多大关联。
总之,无论是从表达形式还是从表达内容来看,“明目而视之”这几句话放在论三无段应该比放在论五至段更为合适。因此可以推定,是传本发生了错简。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段论述五至的话,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此五至与前述民之父母是何关系?与后述三无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是这五至而不是别的?五至之间的因果递进关系有什么根据?这个提法是否可以得到同一语境中其他文本的支持?如果它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在思想史上又有什么意义?以下我们试着逐一解答。
五至与民之父母有何联系,这个问题可以从前述“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论述得到提示:五至、三无似乎都是民之父母所当采取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达于礼乐之原的一种表现。
五至与三无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有关三无的理解,留到下面讨论三无时再议。先考察五至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以及说话者对五至的描述在思想史上有什么意义。
必须承认,志、诗、礼、乐、哀之间这种递进式的因果关系,的确是理解上的一个难点。对此,前人的一些注疏已经显示(注:其中,比较有力的质疑是清人姚际恒做出的,姚氏云:“《书》曰:诗言志。故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则志即在诗内,不得分为二至。且章首是言民之父母,则五至皆谓至于民也。至志于诗,何与于民?其不得以志为第一至,审矣!郑氏以其不可通,故曰:凡言至者,至于民也。志谓恩意也。言君恩意至于民,则其诗亦至也。以志为恩意,曲解显然,即作者之意,亦岂尝如是?或乐亦至焉之乐,音岳;乐之所至之乐,音洛,欲取哀至之义,忽以乐(阅)字脱换作乐(洛)字,甚奇!(注与疏以三乐字皆音洛,则礼乐不相接。陈氏《集说》上二乐字皆音岳,则乐哀又不相接也。)《诗》、《礼》、《乐》属经,哀属人情,又何得并《诗》、《礼》、《乐》为一至乎?至于哀乐相生,又别一义,竟与《民之父母》章全不照顾矣!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本《老子》希夷之说;志气塞乎天地,袭《孟子》其为气也则塞乎天地之间,然气可言塞,志不可塞也!”(杭世骏1992:4868-4869))。由于这种困难,有人干脆认为五至之说是汉儒杜撰(注:清人陆奎勋言:“五至、三无、五起,以数命名,此系汉儒积习,疑非孔子本文。”(杭世骏1992:4869))。需要对这些关系作出认真分析。
可以看到,孔子对诗礼、哀乐关系作了明言:诗礼相成、哀乐相生,而对志诗、礼乐关系则未明言。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对话者子夏与孔子之间,志与诗、礼与乐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换言之,诗由志生、乐随礼至的观念在他们当属于共同知识。那么,验之史籍,诗志相从、礼乐相随是否确是孔子乃至先秦时代的共同知识呢?
如所周知,在先秦典籍中,“诗言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思想(注:如《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告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中说:“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诗序》云:“《诗》,志之所之也”。详请参见朱自清1996。)。而新出土文献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些佐证,如郭店楚简《语丛一》云:“《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注:研究论文参见饶宗颐2002。),上博简《孔子诗论》篇则有:“诗无泯志,乐无泯情,文无泯意”。因此,将“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视为孔子乃至先秦时代的共同知识应无问题。
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诗由志生,展露出儒家政治学对于文学的特殊关切。诗歌在此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成为民意的一种载体,成为反映政治支持率的一种指数。在某种意义上亦可以说,文学被政治化了。作诗与传诗,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艺术活动,它用以表达政治立场、报告社会现状。与此相关,收集诗歌、倾听或阅读诗歌也就主要不是一种艺术欣赏,而同样是一种政治行为,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民意调查。重视采集民间诗歌并及时调整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政治。“诗言志”的志,既表示民意(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即中国古人所说的人心向背;又表示民情(社会现状、政治形势),即中国古人所说的民间疾苦。要成为民之父母,对此道理当然不能不知。
关于礼与乐的关系,在先秦礼乐通常并举,传说周公制礼作乐,而《礼记·乐记》则云:“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从《礼记·乐记》的论述来看,礼与乐是一种互补关系,它们各自强调两个不同的方面,合起来实现完整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强调秩序原则,而乐强调和谐原则,综合运用两者才能造成和谐有序的社会,所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散。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礼,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合矣”。另一方面,礼用来处理外部矛盾,而乐则用来调节内部平衡,综合运用此两者才能达到内外皆治的效果,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由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志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来说,和谐原则是对差异原则的一种纠正,从原始的无差异状态(人兽混居、你我不分)到区分贵贱、上下有别,再到上下相亲、和睦互爱,相当于哲学上的正—反—合命题。因此,礼治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引进乐治。古人对此认识得也非常清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即有“乐,礼之深泽也”(注:关于郭店楚简中的儒家礼乐思想,研究论著甚多,本文主要参考了龚建平2002。)。由于乐是在礼充分发展之后有见于礼之不足而出现的,因此,通晓乐义的人从道理上说不可能不知道礼,这就是郭店楚简《尊德义》篇所说的“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的意思。据此而言,“礼之所至,乐亦至焉”所反映的思想,原是《礼记》等先秦儒家文献中的基本观念。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乐随礼至、以乐辅礼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与管理艺术(注:陈来认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是以乐辅礼,此是中国文化自上古以来即有的一种辩证智慧的体现。见陈来1996:275-278。)。“五四”以来,现代学者对儒家的礼教批评甚烈,以为礼教强调森严的等级秩序,维护权威主义,压抑人性、禁锢自由。这里有必要指出,原始儒家所说的礼并非如此,以周代文化为代表的周礼包含了“乐”在其中。周礼省称为“礼”,其实质则是礼乐文化整体。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礼胜则离”,看到了等级制度过于森严会带来人际关系疏远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的危险。因此,古人自觉地要求化解等级制度的内在紧张,培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亲和力,而乐教被认为是培养这种亲和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前已述及,在中国古人那里,礼所代表的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乐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调适。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普遍的道德法则对具体的人而言,总是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强制,通常它以律令(Law)的形式要求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是被动的服从者,人经过理性的考虑决定去服从某个道德法则,这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但不能说是主体的一种自愿。要使道德行为成为主体的一种自愿,那就需要它同时也能满足主体的情感要求。只有同时满足了主体的情感需要,德行才会化为德性。而一旦普遍的道德法则成为人的一种德性,人在实施道德行为时就不再感到有任何强制,而纯粹是发乎自然。单靠理性的自觉并不能保证道德行为始终如一会实现;自觉加上自愿,则为道德行为建立了坚实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礼至之后也应当乐至的思想,实际上是注意到伦理学上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这无疑是深有所见的。
以上讨论了孔子所未明言的诗志相从、礼乐相随这些观念。以下对孔子明确提出的诗礼相成、哀乐相生这些说法,再作几点说明。
从诗到礼,表面看来似乎并无逻辑可言,然而在孔子那里,诗、礼乃至乐,是一整套教化措施。《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果说诗主要是情感的一种抒发或现实的一种描述,那么,礼主要是一种经过理性考虑之后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情感的抒发,诗多表现为一种感性认识,需要上升到一种理性化的认识;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描述,诗基本上还停留在言的层次,需要进而表现为行。要求诗至而礼亦至,实际上是要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言落实到行,这是符合思维发展要求的。
有人认为,礼乐的乐与哀乐的乐读音与意思都不相同,从礼乐到哀乐,概念已发生转换,意不相属。实际上,这种说法只看到乐(音“阅”)与乐(音“洛”)的不同,而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古人看来,好的音乐(即所谓德音)能给人带来愉快的心情,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有以音乐来使人愉悦的做法(即所谓“以乐(音“阅”)乐(音“洛”)之”),《礼记·礼器》有“乐(音“阅”)也者,乐(音“洛”)其所自成”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古人并没有将乐(音“阅”)与乐(音“洛”)理解为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古人还认为,作为与心情有关的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悲,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即有:“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的论述。礼乐相随、哀乐相生的思想在郭店楚简《尊德义》篇中也有反映:“由礼知乐,由乐知哀”。可见,由礼乐到哀乐在理路上并不突然。
三、三无
简本与传本有关差异甚巨。首先,简本“君子以此皇于天下”句为传本所无,这句与第一段中的“以皇于天下”重复。从文理上看,这句显得突兀,删之并不影响文意,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此为简本抄写错乱所致。其次,在传本中处于论五至段落中的“奚(系)耳而圣(听)之”数句在简本此段出现。前文已指出,从义理、文气上看,此数句放在论三无段中比放在论五至段中更为合适。易言之,在对此数句的安排上,简本比传本合理。另外,简本所引诗与传世本小异,就“城(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又(宥)密”句而论,简本所引较传世本完整,而从后面所引诗皆为两句的情况来看,当以简本为是,传世本当从简本补上前句“成王不敢康”。
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而得气塞于四海,可以认为是说三无的神奇功效,但三无的政治学涵义尚未凸显。而下面以诗说三无的内容无疑值得我们重视,这种引诗作解的方式正是孔子与子夏谈话的风格,会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三无提供更多的线索。
让我们来看与三无意思相近的这几句诗。孔子引“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解无声之乐。原诗见《周颂·清廟之什·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诗经》卷八)依注疏,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整句诗合起来意思是:谨慎从事,取信于民,待民以宽,使民安宁。这种做法重在以身作则,要求君王以行而不是以言来安民。在此,孔子明白地告诉子夏,三无之一的无声之乐,应该结合《诗经》中的“夙夜基命宥密”句来理解。经过孔子这样引诗说明,无声之乐的政治学意蕴已晓然无疑,无声之乐能成为民之父母必行的三无之一,也就毫不奇怪。
孔子又引“威仪逮逮,不可选也”解无体之礼。原诗见《国风·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诗经》卷二)依注疏,棣棣,雍容娴雅貌;选,屈挠退让貌。整句诗合起来意思是:雍容娴雅,不可屈服。再联系前面“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几句诗,“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所强调的,似乎是内心意志坚定,表现于外貌则是大义凛然状(注:按,关于此诗作者及动机,《列女传》卷四《贞顺传·卫寡夫人》有说可参:“(夫人)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孔子认为与无体之礼相近的诗句是“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即无体之礼特征就是内心坚定而外貌凛然,不怒而威,自有一种庄严,而这种威仪不是借助服饰、仪仗等外在之物达到的,而是从主体内在的意志品格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东西。民之父母应当通晓这种无体之礼的妙处,在和颜悦色之中能使百姓领略到其内在的威严而不敢轻视。显然,欲达到此种效果,为君者就要做到意志坚定、品格贞毅,即是要加强内在修养,而不是把注意力投到外表的修饰以及各种繁文缛节的设立上去。
最后,孔子引“凡民有丧,匍匐求之”来解无服之丧。原诗见《国风·邶风·谷风》:“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求之”(《诗经》卷二)。匍匐,爬行状。匍匐救之,极言救之心切。整句诗的意思是,君王将老百姓的安危时刻挂在心上,一旦老百姓有难,救之惟恐不及。这是一种与民同体、天下一家的政治情怀。经过这样解释,无服之丧的含义及其与民之父母的关联就变得非常清晰。本来按照丧礼的规定,遇丧者、吊丧者都要穿特定的服装,以示哀悼并区别亲疏。无服之丧,则是内心持哀而不形于服饰,类似于古人所服的心丧。将此列为民之父母所行的三无之一,所强调的无非是为君者当以黎民百姓为念,忧其所忧,急其所急。
综上所述,作为民之父母当行之事,三无实际上对君主提出了如下要求:首先,他要谨慎持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百姓安宁;其次,他要坚忍不拔,使百姓倾倒于自己的沉毅风度;最后,他要急民所急、忧民所忧,内心充满对百姓殷殷关切之情。
从孔子引诗对三无所作的这些解释不难看出,孔子期望的民之父母,是小心翼翼、老成持重、视民如亲的有道君子。相比于仪式化的礼乐制度,君主个人的涵养更为孔子所重视。三无的这些要求与孔子一贯主张的道德主义政治观是相一致的。孔子理想的政治境界是人们基于道德的天然吸引力而形成一种关系密切的共同体,这就是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种政治实践就其目标而言,乃是不要政治,以道德代替政治。
由于孔子的这种政治主张冠上了“无”的名义,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道家思想。传世本尤其是《孔丛子》曾因此被怀疑为伪书。简本出土后,有人遂认为此论出于孔子决无可疑,并进而提出,应当据此重新考虑先秦时期儒道哲学关系(注:参见庞朴2003a、2003b。)。先秦时期儒道哲学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系统的讨论显然非本文力所能及,在此只想就三无这段材料发表一点看法。显然,我们不能单凭用了“无”这样的字眼就断定其为道家。我们认为,儒、道的思想分歧不在于它们是否使用“无”这个概念或者是否推崇某种“无”的境界,而在于他们对“无”的不同理解,或者说他们所要“无”(取消)的内容具体是什么。事实上,儒家并不讳言“无”,在《论语》等儒家典籍中不难找到有关“无”的论述,此段有关三无的论述亦是一例。在政治哲学上,儒、道的一个重大分歧是: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即所谓以德治国;而众所周知,道家认为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是次一级的东西,所谓“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主张一仍自然。孔子在此举三无为民之父母之当为,他的意思是强调君主当以自身的德行感化人民,是谨慎勤恳,以德服人,是行无言之教,修无刑之政。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三无毋宁说是一种道德之治、仁义之政,它与老子所讲的无为之治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四、五起
简本至此,全篇结束(注:简本此段末尾刻有√号,以示全篇结束。),而传本此后尚有关于三无私之论,据此可推,简本似为摘要。
五起何解?从简本以及传世本《礼记》所列的五组排比句来看,似乎是说实行三无后所收到的五种效果。相比之下,传本《孔子家语》只列了两组排比,当有所遗。因此,下面我们主要根据简本与传本《礼记》来研究五起的含义。
简本与《礼记》本关于五起的说法大同小异。两者所述第一、四、五起,文字全同;所述第二起,文字小异,其中简本作“无声之乐,塞于四方”,而《礼记》本作“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意思相近。差别最大的,是关于第三起的论述,两者文字几乎完全不同。简本作:“无圣(声)之乐,它(施)及孙子;无体之礼,塞于四海;无备(服)之丧,为民父母”;《礼记》本作:“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从所述一、四、五起开头都有“无声之乐,气志既X”的形式来看,第三起的开头作“无声之乐,气志既起”当更合理。易言之,此处当从《礼记》本。“施及孙子”句,简本置“无声之乐”后,而《礼记》本置“无服之丧”后,用字则小异,“及”作“于”,从第四起所述“无服之丧,施及四海”观之,此处宜作“无服之丧,施及孙子”,即,句序当从《礼记》本,而用字则从简本。至于所论“无体之礼”,《礼记》本作“施及四海”,而简本作“塞于四海”,既然后面论“无服之丧”为“施及孙子”,为免重复,当以“塞于四海”句为佳,即此处应从简本。综此数点,原本所述第三起,当如下述: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塞于四海;无服之丧,施及孙子。
文字既经疏通,以下当观义理。不难看出,有关五起的论述句式整齐,朗朗上口,以韵文形式出现,颇近于《诗》。这种诗式文字反复吟咏,予人深刻印象,所以虽号称五起,而五段排比所表之意其实相近。其对三无作了多方面的描述,三无又各有所重:关于无声之乐,重其对气志兴起之功;关于无体之礼,重其所表威仪及其使四海认同之用;关于无服之丧,重其与内在德性关联及此德性造福天下之效。
无声之乐比有声之乐更高一级,它既保留了乐的功能,即对人心的调谐和对情感的宣泄,同时又摆脱了有声之乐的物质形式(如钟鼓);无体之礼比有体之礼更高一级,主要指由于内在意志的坚定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自然的威严,它既起到礼的功能(即使上下有序有条不紊),同时又摆脱了礼的具体仪式(如玉帛);无服之丧比有服之丧更高一级,主要是指内心一直保持着一种仁爱、一种虔敬,这种内在德性可以对人发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使万邦归顺、天下太平。
无声之乐所强调的依旧是统治手段中乐的运用,无体之礼强调的也依旧是统治手段中礼的运用,而无服之丧所强调的则是统治者的修德以服人的层面。礼所代表的秩序原则、乐所代表的和谐原则以及作为实施两者的主体所具备的德行因素,所有这些有机地构成了孔子所理解的民之父母的政治意涵,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儒家政治学的经典表述,而在以后的思想史进程中不断被回溯。
标签:儒家论文; 礼记论文; 孔子论文; 毛诗注疏论文; 孔子家语论文; 父母关系论文; 思想史论文; 诗经论文; 国学论文; 二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