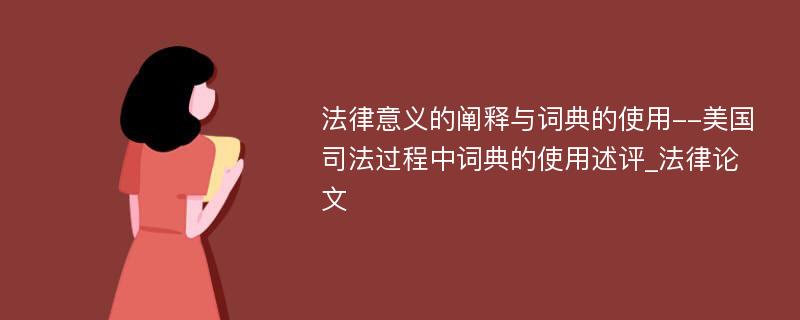
法律的文义解释与词典的使用——对美国司法过程中词典使用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典论文,述评论文,美国论文,过程中论文,司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成文法律的解释,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有三种相近的说法,这就是成文法的文义(含义)、意义、意蕴。这三种说法虽很接近,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区别。“文义”一词一般来说是指该用语或词在一般语言习惯上被了解的含义,即强调法典词条的原来含义;“意义”一词强调该用语或词在特定环境中与其它事物发生关系而产生的影响;“意蕴”则是在文本与理解者对话过程中所衍生的第三者。以“法”字为例,它的古代文义从表面上看应是平之如水,从水而去。从其深层来看法即惩罚;从现代意义上看,它则是统治者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这便是法字的文义(或含义)。但如果我们分析法字的意义,恐怕主要是指法对社会发生影响的体现,重点强调法的作用。至于法的意蕴,我们已经看到了由法而衍生的各种争论:从法价值角度出发,法的重心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从法运行的角度看,法到底是规范还是行为;从法文化角度看,法到底是观念还是制度等等。法的意蕴突出了文本与主体之间的理解,并强调这种理解是介于文本与主体间的第三者,既不属于原意说明,也不是任意的解释。
法律的文义解释,虽然不可能完全是文本原来的含义,但它的显著特征在于强调严格按字面进行解释,它属于法律解释中的语法解释,有时也把它称为字面解释、语义解释等。梁慧星教授认为,语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条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以阐释法律意义内容。”〔1〕文义解释在法律教育和适用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大陆法系,由于成文法律是其最主要形式,所以要了解成文法的含义,须首先了解法律条文所使用的词(字)的含义。台湾法学家王泽鉴先生讲:“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开始,但也是法律解释终点。易言之,即法律解释始于文义,不能超过可能文义。否则就超越法律解释之范畴,进入又一阶段之造法活动。解释法律应尊重文字,始能维持法律之尊严及其适用之安定性。”〔2 〕王先生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讲法律文义解释的特征和功能,这就是说文义解释只能是由文字本身而来,不能溢出文字本身的含义,否则,就不能称为文义解释。在功能上,如解释法律不尊重其文义,就等于不尊重成文法,就会破坏成文法律的稳定性,使人的行为失去统一的标准,法律的规范作用就会下降,成文法代替个别判决的优越性便会被抹熬。台湾法学家黄茂荣先生说过:“文字因素亦即可能的文义在这里显示出它的范围性功能。它划出了法律解释活动之可能的最大回旋余地。”“因此,着手解释法律的时候,首先须去确定文义涵盖的范围。”〔3〕但我们怎样去确定文义呢? 这是法律解释的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系人们的行为规范,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设立的,故必须以文本中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法律文本中作出特别解释的除外),〔4〕像民事法律行为、法人、恶意、 推定、时效等。但“除了像数字这些极端的例子外,每一个用语都有解释的余地,‘认定某一个用语是单义的’或‘认定某一个规定是例外的’这本身已是解释的结果。所以,那种‘在法律的文字有疑义时,才有解释法律的必要’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5〕因此, 许多法律条文中的字词是需要确定其通常含义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所谓通常的含义,“通常”的解释究竟蕴藏在什么地方,这种通常的含义是大众的共识,还是法律工作者的认定。杨仁寿先生讲,欲确定法律的含义,“必须先了解其用词遣字,确定字句的意义,始能究其功。”〔6 〕但问题是怎样理解成文法中的“用词遣字”。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确定标准会出现许多问题,较为典型的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妄说义理。这种错误是指那些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曲解法条中的词义,然后加以引伸。像刑法规定的缓刑,没有经过法学训练的人,就可能把它曲解为缓期执行。二是过度强调义以载道,对某些词语进行词义以外的政治等观念的说教。虽然在解释法律文义时,立法目的应加以重视,但这种载道不能脱离语言本身来进行。如果这样做,就会破坏法律条文语言的科学性,使法律成为少数人任意玩弄的工具。三是拆拼为单,把本为同义复合或本为连绵的字分析成单音词解释的现象。四是任意扩大范围。文义解释只能就释词索义,不能像训诂学那样任意扩大释义范围,否则就超出了文义解释的范围。在这些戒律的背后,我们究竟怎样认识法律条文中的文义呢?
在美国,各级法院很早就使用了词(字)典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对法律进行文义解释。“最高法院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岁月中,已经参考了各种词典处理了不下600宗案件,……近年来, 最高法院对词典的依赖已渐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7〕在过去的10年中, 借助词典确立各种纷争的观点已急剧增加。从1958年到1983年的25年中,最局法院引证词典仅仅25次(年均5次)。但1987到1992年, 最高法院引用词典一年不少于15次,尤其是1992年引用词典达到32次,在其中的几个案件中,词典的定义成了最终结果的决定因素。词典在法律的文义解释中运用的增加成了普遍趋势,所解释的对象涉及到宪法和普通法律,最高法院参考的词典达27种之多。按照美国的传统理解,词典是为了让法官们在对法律某些条文的字句的理解发生争执时,由法官选择的一种方法。亨利·哈特(Herry.Hart)和阿尔伯特·塞克思(Albert.Sacks)在他们具有创意性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的法制程序》中,把词(字)典解释法律称为“很好”的,确定人们可以接受含义的方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一般学者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对词典日益增长的依赖是与法律和文义解释方法(即逐字逐句的解释)的广泛被接受分不开的。在过去的10年期间,联邦法院已经接受了法律文义解释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应接受法律条文字词的普通含义,因此不能过分注重立法史或别的不太重要的材料,而应重视逐字逐句的解释方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非法律专业的读者也能识别法律语言的应有含义。这种方法被安托尼·斯卡利亚(Antonin.Scalla)法官称为“朴实含义”的解释方法。美国的很多法学家认为使用词典数量的增加不可能完全是巧合,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严格法制的产物,因为:第一,如果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任意解释法律,法律便会失去其稳定性,人们也会失去对法律行为安全性的依赖;第二,对抗式的审判方式使某些词的争辩达到难以使法官选择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字典被当成了法律的高级法源;第三,词典词条本身的概括性和成文法律规范的概括性一致,也为法官使用词典提供了方便条件。
以斯卡利亚法官为代表的法律文义解释主张之所以坚持用“朴实含义”的方法解释法律,是因为他们相信文义的解释方法是说明法律语言含义的最常用方法,旨在反对司法权侵蚀立法权。他们认为,多数人依据立法史等资料解释法律会蹈入法官更多的主观性因素,他们已经预料到词典是对法律朴实理解的最有用工具。斯卡利亚法官在遇到各种纷争时,总是抓住各种词组的普通含义去反击对手。在他经办的几个案件中,他积极利用词典阐明诸如“代表”、“雇佣”、“使用”、“审判”这些词汇,试图使词典成为法律解释的最基本工具。
但是,早在50年前,罗尼德·韩特(Larued.Hand )就说过:“不以词典为准绳才是成熟法理学的标志。”〔8〕循着这一思路, 现代美国的许多学者呼吁最高法院停顿下来思忖一下在解释法律时使用词典的利弊,探讨解释法律时词典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对一些最高法院的陪审团成员来说,词典已成为一种显示成文法欠缺的源泉,各种词典决不象“朴实含义”的解释者认为的那样公正客观,也不是法律术语(或法律条款)“朴实含义”的贮藏库。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词典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因为现实的问题是,词典提供词汇的含义并不是单一的,并且词典也不止一种。我们该怎样确定词典的某一含义是法律条款中的应有之意,我们选择哪一种词典作为我们解释的工具,这实际上就严肃地提出了词典的操作性问题。像有些学者抓住了法条含义原意苛求者的虚拟假设一样,他们认为运用词典解释法律也是主观性的选择。以词典作为工具也不能完全避开主观性问题,并且可能加强这方面的因素。从表面上看,各种词典似乎掩饰了主观任意的决断,但实际上只不过使法官的主观性选择更加复杂罢了。客观世界不断地变化,但词典的修订有限,法官到底选择哪些词典来迎合时代的发展呢?他们举例说,斯卡利亚法官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处理了四宗参照1950年《新国际大词典》第二版和其它版本的国际大词典。不同时期和不同版本的大词典有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定义,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有很大不同。所以,美国部分法学家认为最高法院应设法规范词典使用的无序状态。他们说,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使用词典前后不一致的行为,以及不能证明自己把词典运用到个别案件是正当合理的,免不了公众对利用词典确定法律语言的朴实含义表示怀疑。法官利用词典完全能够主观随意地使宪法和法律条款具体化,从而使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受到侵犯。事实上,许多善于引用词典的人都是些政治倾向性鲜明的法官,而这些法官正是利用各种词典用语的模糊性和表面上的客观性,为政治上操纵法律打开了方便之门。
词典不仅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法官解释的工具,而且给我们展示了语言自身的各种内涵。因此,选择法律含义的过程必然会涉及到揭示语言涵义的各种规律。各种词典作为解释工具所具备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从它们所反映的语言的复杂性去判定。法院在使用词典时有时难以确定所要使用语言的含义,这实际上是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词典在这时的负载已超出了它所能解释的范围。它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各种词典的定义、解释与法律的上下文之间不具有完美的联系。在缺乏上下文联系的情况下,词语的内涵在法律中不可能得到充分详实的描述。没有哪一本词典能完全地描述一个法律术语的历史框架和原文结构,各种词典仅仅回答了如在有上下文的保证的情况下一个特定含义能被人们接受的问题。词典仅仅是解释存在疑问的法律的起点,如果在没有上下文联系并作范围保证的情况下肯定会导致解释的错误。如果脱离法律的原则和技术,纯粹运用词典解释法律,那就会对法制造成危害。因为在特定的法律意境中,词典中的含义与法律语言本身的固有内容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在美国的多数词典中,通常把蕃茄定义为一种水果,但按人们的习惯,蕃茄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蔬菜。法官是接受植物学的分类,还是按习惯的认识来判明种属就是一个复杂的论辩过程。法官必须使自己对特定的法律环境及立法目的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另外,利用词典的困难还在于语言领域自身的问题,这就是把成文法条所使用的词语本身的复杂性呈简单化倾向。按语言自身的规律,越是常用的词汇本身也就越具有较多的含义,但法律条文本身的明确性要求它须是固定的甚至是单一的。如果我们将法律条文中的词汇单独抽出来放到语言领域,其含义可能是模糊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一种专门的词典,这种词典一方面能给一般读者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能使法律专家依照法律本身的范畴给字词以确切的法律解释。另外,法院也须为理解运用各种词典提供一套程序和原则,以避免词典解释走向歧途。
应该说,使用词典去识别法律条文中部分词汇的作法,如果考虑到词汇的原文、结构、历史演变以及该词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的话,那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困难在于词典所提供含义的标准如何确定,词典各种含义的界限如何把握。词典为人们解释法律的文义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但在使用词典解释文义时,必须从开始处理案件的时候进行,而不是在案件的某一阶段或结束时使用,并且所使用词典的含义应当同多数高质量的词典的含义一致。总之,我们必须承认,词典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在解释法律时是可以被运用的。但像任何方法的使用一样,我们既不能僵化,也不应拒绝。如果法学本身的原理已不能解释有关词汇,我们就可以进行词典解释的尝试。
注释:
〔1〕梁慧星:《论法律解释方法》,《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47页。
〔2〕王泽鉴:《民法判例研习丛书·基础理论》, 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3年版,第130页。
〔3〕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3年版,第307~309页。
〔4〕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23~124页。
〔5〕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3年版,第308页。
〔6〕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25页。
〔7〕《 Looking it Up:Dictionaries and
StatutoryInterpretation》《哈佛法律评论》,Vol.107 No.6 1994,P.1437.
〔8〕《 Looking it Up:Dictionaries and
StatutoryInterpretation》《哈佛法律评论》,Vol.107 No.6 1994,P.1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