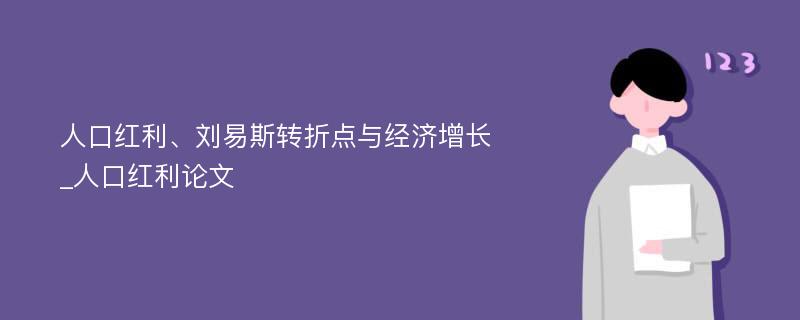
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转折点论文,刘易斯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的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气势令世人瞩目。各种探究原因的研究著作、论文汗牛充栋,体制改革、资本积累、技术模仿、威权主义等等解释不一而足。不过,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人们似乎发现了一个新的富矿,“人口红利”概念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1](p.205)“劳动力短缺终将成为现实”[2],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人口红利推动的吗?经济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瓶颈究竟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现代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体两面
近代以来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一直与人口转变过程相伴随。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一体两面。人口过程包括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分布的变动过程。经济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虽然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人口变动也有波动性,但是社会一直朝着潜在生产能力增加的方向演进,而人口也是朝着低生育率方向演进。凡是进入经济发达状态的国家,人口都已经完成了转变,而尚未进入发达状态的国家,人口转变仍未完成。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人口转变已经完成。
现代经济增长到现在只不过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在此之前,或者是国富民贫,或者是国贫民贫,人口和经济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中,绝大多数人口处于勉强温饱的生存状态。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并迅速带动了欧美各国的现代经济增长车轮。Angus Maddison的计量经济史研究发现,1000-182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四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只增长50%,而1820年至1990年代,世界人口增长了五倍,人均收入增长了八倍。[3](p.3)
前现代人口和经济历史为马尔萨斯“人口法则”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材料。然而,现代经济增长的轨迹则打破了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革命引起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农业剩余”的增加是支撑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赵冈特别强调中国近代以前的农业社会中,余粮率是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农村的余粮率,即农民自我消耗后所剩余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一来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城市化的上限,二来可以决定城市人口的分布,也就是集中或分散的情况”。[4](p.8)现代经济增长引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城市工业化提供的就业岗位增加,导致了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迅速膨胀。
近代以来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进行和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引起了学者们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关于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悲观派、乐观派和中间派。悲观派认为人口增长将会限制经济发展,代表人物和作品包括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年)、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1968年)、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具有分母效应,使人均食物、人均资源、人均资本数量下降,从而使人均福利水平降低。乐观派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代表人物和作品包括Julian Simon的《人口增长经济学》(1977年)、《最终的资源》(1981年)。中间派认为人口增长是中性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是Ronald D.Lee和D.Gale Johnson主持的美国科学院的报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由于各方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人口增长的后果持一种中性的立场。
David Bloom等人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过去这些研究都只关注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率,而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变量。[5]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年龄人口的行为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少儿人口是需要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密集投资的人口,成年人口是提供市场劳动并储蓄的人口,老年人口是在健康和生活方面需要照料和供养的人口。在相等的人口变动规模下,由于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相对比例不同,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强度也会不同。由于不同年龄组的人口行为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人口转变过程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David Bloom等人力图证明,造成东亚崛起的奇迹的部分原因是在1965年至1990年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受供养人口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6]随着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当该国大部分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时候,这个额外增加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人口红利”[7]。当然人口红利并非不可避免,David Bloom等人承认,东亚崛起能够利用人口红利,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和政策允许这些国家充分发挥由人口转变所创造的潜能。他们所有研究文章和报告中都把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作为创造和实现“人口红利”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王峰(音译)和Mason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的研究只是把Bloom等人结论放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进行验证,试图证明中国的人口转变促进了经济更快增长。但是他们也承认“人口转变只是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前提是“政策环境的支持”。[8]
二、什么因素推动经济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源泉的研究和争论,一直是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何增加一国的财富?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种理论。
1.分工扩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然而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
16-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者都主张通过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便增加国家的金银货币,这是民族国家富裕的根本手段。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追求,使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国大力推进殖民主义,在全球追逐利润。以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重商主义只会对财富生产造成破坏。只有每个人自由追求自我利益时,公共利益才能增进,国民财富才能增加,这就是著名的斯密“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教义。在斯密的理论中,产出增长直接依赖资本和劳动的增长及其利用方式,依赖分工的扩展。劳动的地位是消极的,劳动力的使用完全取决于资本积累以及人均固定资本量。[9]斯密特别强调分工对于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性,但他又认为分工的扩展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Stigler第一次详细阐述了斯密的“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原理,即“斯密定理”[10]。
杨小凯把分工演进的过程进行模型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不是人口的增长,或是交易、生产或偏好参数的外生变化。毋宁说,增长是因分工演进而产生的”。[11](p.184)很大的人口数量并不足以让分工的统一网络从均衡中出现。当交易效率改进,或者当分工自发地演进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时,很多相互隔离的地区会并入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市场网络中,因而产生了内生增长和相关的发展现象,这可以在没有人口增长或其他规模效应时发生。中国和美国市场大,实际上是指它们的交易条件很好,而不是它们的人口数量大。同样的人口规模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市场大小。台湾只有2000多万人口,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时却拥有大大超过大陆的国内交易量和国际交易量。[12](p.424)
2.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国人们生活水平相差巨大?为什么生活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
二战以后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希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个问题吸引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去研究,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奠基之作。这个理论提出的前提是继承了从斯密到马克思的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把劳动力看成是在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无限供给的。[13]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人口和经济结构,意味着其经济是资本短缺型经济,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决定了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政策含义非常明显,加快资本积累,大力推进:正业化,是改变二元人口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条件。
3.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
D.C.North和R.P.Thowmas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承认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人们努力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或者至少要有一部分人渴望经济增长、渴望改善生活。然而,即使人们希望去从事经济活动以获得更多的享受,在没有制度激励的条件下,人们也没有去从事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的动力,整个社会依然会处于停滞状态。他们证明了这样的观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14](pp.5-6)
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表现最为明显,以1978年为分水岭, 1978年以前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高度集中,国家能够调控国内生产总值在资本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割,长期以低工资、低福利的方式增加资本积累。1953-1977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3%。1978年以后是改革开放时期,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开始显现出来,1978-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
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储蓄很重要,没有储蓄率的增加就无法为快速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罗斯托认为,只要储蓄率能达到12%以上就算进入了“起飞”阶段。[15](p.17)然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率的提高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它只改变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以及任意时点上的人均产出水平,但是它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没有影响。只有改变技术进步率才有增长效应,其他因素的变化都只有水平效应。[16](pp.18-19)内生增长理论的目的,则是理解技术知识与各种经济和社会结构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导致经济增长。这表明,技术与经济生活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而后者又推动了技术进步。[17](p.2)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近200多年来世界各国陆续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起点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制度不同等,都可能造成经济增长过程的巨大差异。企图用简单的一两种因素来解释各种经济增长模式,总是片面的和可疑的。熊彼特曾经在评论“人口决定论”的思想时这样写道:“认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变化虽然是片面的看法,但比起任何其他出于偏见的历史理论,亦即相信总会有一个推动社会或经济前进的单一的、主要的因素——例如技术、宗教、种族、阶级斗争、资本形成等等——至少是同样有道理的。”[18](pp.378-379)
三、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还是结果?
在Bloom等学者提出人口红利概念以后,国内学者很快把“人口红利”概念引入,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蔡昉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19]
从蔡昉的研究可以明显看出,虽然他论证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了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人口比例升高的现象,但是他始终没有论证,到底是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收获了人口红利?
既然人口红利只是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那么这意味着由人口转变引起的劳动力比例升高仅仅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随时可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说明所谓的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与马克思论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没有太大的差别,人口转变带来的充裕劳动力供给只是经济周期性增长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要素而已。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实际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利用了中国快速人口转变所引起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人口红利”。
蔡昉在他的著名文章中,给出了不同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在1978-1998年期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为21%,未解释的部分为3%。[19]这里的增长核算虽然指出了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就像随着经济发展,离婚率提高,但我们无法用离婚率来解释经济增长。就业的增长是由于经济增长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等学者对上海、武汉等五个城市的调查,2002年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3.2%。[19]这再次说明,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实际上是“劳动蓄水池”。高失业与高经济增长并存,这是中国人口过剩与快速工业化并存的产物。
对于人口转变所引起的人口红利,另一个理由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能够使储蓄率上升,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二者的紧密关系并没有得到证明,蔡昉的理论论证是有缺陷的。按照他的理解,人口转变引起储蓄率提高的时候,经济就达到一个更高增长速度的稳态,并由此判定这就是“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这显然是对索罗模型的误读,索罗增长模型实际上表明储蓄率的显著变化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产量水平只有较小的影响。假设一国的资本收入所占份额大约为1/3,那么在长期内,产出的储蓄弹性大约为1/2。当储蓄率增加50%时,均衡产出水平仅增加25%。[16](p.23)
根据王德文、蔡昉的研究,中国的储蓄率从1980年代的平均30%左右上升到1990年代平均40%左右,储蓄率增长率约为30%,因此长期人均收入比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大约上升 15%。[20]不仅如此,要提高到15%的长期水平,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渐进收敛过程,Romer在合理假定下经过计算,要经过18年的时间才走完平均增长路径值一半的距离。这意味着我们如果奢求人口红利的储蓄效应发挥作用,要“等到花儿也谢了”。
同时我们实际看到,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人均收入增长,即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也增加了许多倍。即使储蓄率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而提高,其对人均长期收入的影响也十分有限。真正影响长期收入增长的是技术进步率,是技术进步速度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的长期平衡路径上的增长速度。
把中国的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进行对比,是最容易引起人误解的。所谓“四小龙”是指新加坡、韩国、香港、中国台湾,这些地区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1980年新加坡的人口为240万、韩国人口为3800万、香港人口500万、中国台湾人口约1787万。[21]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口还不足北京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台湾人口比北京市人口略多,韩国人口不到广东省人口的一半。把这么小的区域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是没有说服力的。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地区都是自发的人口转变,没有任何政府的强制性干预。与其说是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是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
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详细总结的亚洲奇迹的因素,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良好教育与高识字率)、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收入不公平程度较低、出口的促进、成功的工业化、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相关实用技术转让。有学者提出“雁形假说”,工业化在亚洲引发地区内的溢出效应。日本对本地区各国或地区的直接投资,以及日本的产业转移为其他地区发展创造了市场机会。[22](pp.42-45)
从日本的抚养比和经济增长率比较来看,1960-197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 9.4%,抚养比平均值为49.1%;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4.5%,抚养比平均值为47.1%;1990-200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5%,抚养比平均值为49.0%。这里我们看不到日本的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红利推动的迹象。[20]1970年代的抚养比略低于1960年代的抚养比,但是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1990年代的抚养比与1960年代相当,但是经济却陷于停滞。由此可以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或停滞与人口红利没有显著关系。
四、刘易斯转折点对中国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
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的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时,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时;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与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23](pp.111-112)刘易斯特别强调“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因为正是从这里,我们超过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
按照国内学者的定义:“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24]
可见国内学者与刘易斯提出的“转折点”并不一致,至多只能算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甚至在目前中国的非农产业到底有没有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更不用说要达到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的阶段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刘易斯的用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来说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差别,并非把二者等同于非农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刘易斯的成名之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年)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根本无关紧要,只要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就是无限的”。更确切地说,“劳动力的短缺不是创立新就业源泉的限制”。[13](p.4)这些潜在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包括“农民、临时工、小商人和门客”,还包括三个阶层: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有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引起的人口增长、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后备军”。这里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是指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
可以看出,即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谋生,也并不表明劳动力脱离了无限供给的状态,劳动力短缺对于现代部门的扩展不会形成阻力。至于说熟练劳动力的短缺,这跟刘易斯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刘易斯认为只要非熟练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那么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仅仅是有一个时滞而已。
目前理论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有肯定也有否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要谨慎断言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与“四小龙”或日本等发达地区进行人口红利期比较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明显事实。无论是用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还是抚养比来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完成自发人口转变时已经建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却在只有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半强制性地完成了人口转变。
第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城乡二元人口老龄化,农村老年人口增加与城市老年人口增长的后果完全不同。城市老年人口大部分是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人口,直接影响财政支出;而农村老年人口则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对财政支出基本没有压力。如果说笼统地说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储蓄率,就会掩盖城乡二元人口老龄化的区别。实际上,大量农村年轻人口流入城市以后使城市人口老龄化大大减轻甚至年轻化,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和经济快速增长。
第三,在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的情况下,断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劳动力短缺时代的到来,是非常不准确和危言耸听的判断。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还不足45%(其中包括了流动人口),未来中国城镇现代部门的扩张,仍然有农村新增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即使按照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000万~1200万左右,再过30年,中国农村人口依然还存在4亿~4.6亿,城市人口才达到68%~70%的水平。可见中国人口城市化依然任重道远。日本在1970年时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71%[25](p.41)。当时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由此对比,中国人口城市化在未来几十年依然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四,中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瓶颈在于国内城市扩容和国际市场扩张的速度和程度。城市扩容需要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国内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1998年中国原煤产量是12.5亿吨,到2005年增长到21.9亿吨。1998年钢材产量1.07亿吨,2005年增长到 3.97亿吨。可见经济快速增长是支撑中国人口快速城市化的基础。这种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是高度依赖的,以2005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额占33.8%。从GDP核算的角度,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消费仅有38.2%,比2000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占43.4%,比2000年增加7个百分点。[26](pp.136、169、34)这些指标反映出国内民间消费严重不足,对出口和投资的严重依赖。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就业增长、城市人口增加,这种发展模式将面临严重困境。国际压力已经越来越显示出来。
五、结论
通过前面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是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不确定的。从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等方面可以发现人口与经济之间的正向、反向、中性的关系。Bloom等学者发现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加密切的关系,提出人口红利的理论,但是依然强调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制度和政策等因素是更深层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第二,经济增长是很复杂的历史现象,对增长源泉的研究特别突出的是人们对增长的追求、分工的演进、资本的积累、制度的改良等方面。
第三,所谓人口红利,并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过去不是,未来也不是。人口转变所引起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升高,既不是提高中国储蓄率的原因,也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毋宁说,是快速经济增长减缓了人口转变引起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中国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拖经济增长的后腿。因此人口红利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第四,国内对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与刘易斯本人的定义并不一致。目前国内学者讨论的刘易斯转折点很大程度上是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然而只有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才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目前离第二个转折点还有很远的距离,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的影响至少还要到几十年以后才会开始显现。我们目前应该重点关注的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性问题包括:城乡二元人口结构长期存在、城乡二元人口老龄化、国内资源和环境对城市扩容的制约、国际市场空间的制约。
标签:人口红利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经济论文; 刘易斯论文; 刘易斯模型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人口增长模式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储蓄率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