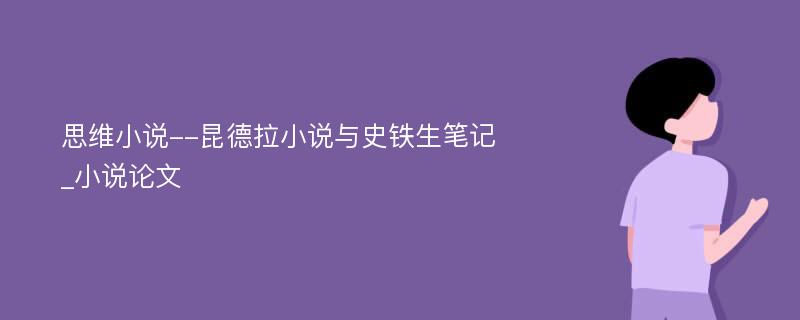
思索的小说——昆德拉的小说学与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昆德拉论文,笔记论文,史铁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106.4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8019(2000)03-0025-06
1
读完《务虚笔记》,我想到了“思索的小说”这个概念。经由这一概念,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学与史铁生的创作在我的思考中相遇了。
昆德拉把小说分为三种:叙事的小说(巴尔扎克、大小仲马)、描绘的小说(福楼拜)、思索的小说。他把自己的小说定位在第三种[1 ](P.434~446)。昆德拉曾设问:“小说通过自己内在的专有的逻辑达到自己的尽头了吗?它还没有开发出它所有的可能性、认识和形式吗?”他的回答当然是没有。于是,他列举出小说在今天的四种可能性。他将之称为“四个召唤”,即“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和“时间的召唤”[2](P.14~15)。 由“思想的召唤”而来的思索的小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是小说合并哲学的可能性。
昆德拉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果说欧洲哲学没有善于思索人的生活,思索它的‘具体的形而上学’,那么,命中注定最终要去占领这块空旷土地的便是小说。在那里它是不可替代的(这已被有关存在的哲学以一个相反的证明所确认;因为对存在的分析不能成为体系;存在是不可能被体系化的,而海德格尔,诗的爱好者,犯了对小说历史无动于衷的错误,正是在小说的历史中有着存在的智慧的最大的宝藏)”[3]。 的确,在勘探存在方面,以扭转欧洲思想史上“存在的被遗忘”为己任的思想巨人海德格尔所倾心的哲学和诗,各有自己的局限。哲学的手段是概念和逻辑,但由概念和逻辑所构造的体系套不住活的存在;诗的手段是感觉和意象,但意象的零星碎片难以映显完整的存在。而小说则可以通过设计出一些基本情境和情境的组合,将哲学的体悟和诗的感觉包容进去,贯通起来,“还原”为完整的活生生的存在,从而实现其在勘探存在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约在1985年左右,那时昆德拉还未被介绍到中国来,史铁生的创作便开始呈现出以小说合并存在哲学的倾向。后来有人问他,何以不直接作哲学表述而要采用小说的方式呢?史铁生从自己的创作体会方面回答说:“一种意义,你感到了,但你要把它表达为一种简洁的哲学逻辑……它已经近于枯萎了,有时,甚至你根本就无法作这样的表达,你必须把它‘还原’到生活中去,让它活在它产生的地方,它才能发出它的全部消息。很多消息是存在于哲学和逻辑之外的,这种‘还原’就接近文学了。”[4] 这番回答虽然没有昆德拉的那番话充满大气磅礴的自觉的历史使命感,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且从实践者的经验方面将昆德拉的令人振奋的思想平实地具体化了。
这里有一个疑问应该提出来加以讨论,这就是昆德拉在那番富有使命感的雄心勃勃的话中指责海德格尔“犯了对小说历史无动于衷的错误”,那么萨特呢?昆德拉是否忽略了萨特的哲学小说的存在呢?的确,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萨特不仅将小说与哲学进行了结合,而且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萨特的结合方式有所不同。他是用小说这一文体形式来表达他的“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即人的自由”、“他人是存在的地狱”等先在的哲理,而不是通过小说的方式思考、追问和揭示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可能性。用昆德拉的话说,萨特的哲学小说“不过是哲学的附属,哲学观念的小说图释而已”,而不是以小说“去占领直到那时仍为哲学占据的领地”[5]。昆德拉还说:“在《恶心》中, 存在主义哲学穿上了小说的可笑服装(仿佛一位教授,为了给打瞌睡的学生们开心,决心用小说的形式给他们上一课)。”并说“《恶心》使哲学与小说的新婚之夜在相互烦恼中渡过[3]”。 昆德拉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说称作“思索的小说”而不称为“哲学小说”,为的就是同这种以一些论点、框框、某些论证为前提,并以某些抽象的哲学结论和证明为最终目的的哲学小说相区别。
由此看来,小说与哲学的结合,存在着两条路径,一条是小说合并哲学,另一条是哲学合并小说。从哲理寓言到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再到萨特的哲学小说,是欧洲文学史中哲学合并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以小说合并哲学,即思索的小说,昆德拉为它勾画的发展线索是从本世纪中欧的穆齐尔、布洛赫到昆德拉。思索的小说在中国的杰出作品无疑应推史铁生的《务虚笔记》。
史铁生从21岁开始便身处人生的困境,这使他产生了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发现某些值得活下去的意义的强烈的感情需要,这便促进了他对生命的意义、对存在的不断发问。这种发问构成了他写作的发源和方向,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具有自发的哲学气质的小说家。在他这里,小说对哲学的合并,既不是来自于文学史的召唤,也不是来自于哲学史的召唤,而是从他苦难的命运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是他苦难的命运成就于他的一种冥思生命的角度和方式。从他较早的小说《命若琴弦》、《宿命》开始,到他这部集中地表达了他多年来对于生命存在之意义的穷根究底的追问与思考的《务虚笔记》,都是他“知命运的力量之强大,而与之对话,领悟它的深意”[4]的笔记。 他的这种小说方式的哲学思考,使他在化解现实苦难、超越残疾局限,迎向健朗生存的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着顽强地思索着自己的命运,思索着人的存在的强大的灵魂。
2
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2](P.42 )这段话表现了思索的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不同旨趣。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关注的是“现实”的范畴,它的基本方式是反映;思索的小说关注的是“可能”的范畴,它的基本方式是揭示。而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揭示,在昆德拉的小说中演化为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对人和人的世界进行设置与追问,进行实验与研究的过程;在史铁生的小说中,则主要演化成为对人的命运的可能性的揭示,体现为对人的困境的设置与研究。
《务虚笔记》以“写作之夜”里“我”的一个回忆开头:我在一座古园里与两个孩子相遇,便把这两个孩子写进了书中。那么在这部书里,这两个孩子又是谁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一个男孩儿”[6](P.575),所以,他们便是《务虚笔记》这部书中所有的人。就是说,作者将人世间形形色色的人的命运的可能性都还原到了这两个孩子身上。
然后,作者以自己童年的印象为基础,使这种可能性在其初始状态显现为“童年之门”——那是小巷深处一座美丽而出人意料的房子,家住灰暗老屋的9岁男孩(童年中的“我”)对这座房子无比憧憬, 在一个午后怀抱着梦想到这房子里去找一个同龄女孩。他走进这房子里几乎迷失于那些门中。这童年的幻觉和记忆中的无数的门意指的便是人生的诸多可能性。
就像那个绝妙的游戏,O说, 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怎么不一样?O说:不,没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会是什么, 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6] (P.47)可能性就这样在偶然推开的这个门而不是那个门中走向现实人生。那两个小孩就这样被通往不同世界的门所分化,成为人世间形形色色命运各异的人物。因而作者便经由这“童年之门”引出这部书中的诸多人物:如果那个9岁的男孩在离开这如幻似梦的房子时, 因为回身去捡从衣袋里掉落的一件东西,在同样的经历中稍稍慢了一步,他从那门里听见了女孩母亲的话:“她怎么把那些野孩子……那个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告诉她,以后不准再带他们到家里来……”[6](P.52 )那男孩的梦想因此便被碰到了另一个方向上,成为日后的画家Z ——一个被人世间的不平等所刺伤而心生怨恨,通过艺术来抒发他的雪耻欲望的人;如果他没有听见女孩母亲的声音,或者他听见了,但没有来得及认为这声音很要紧,他正一心与那女孩儿话别,一心盼望着还要再来看她,那么,他便是日后的诗人L——一个不断追寻爱的梦想, 既是好色之徒又是真诚恋人的人。而那梦幻般的房子里的女孩,如果因为在那梦幻般的房子里长大,便始终沉溺在美丽的梦境里,最终因为不能接受梦境的破灭而自杀了,那她就是未来的女教师O; 如果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毅、豁达的品格,而能沉勇地面对身世沉浮,并终于事业有成,那她就是未来的女导演N。而“当O 和N在我的盛夏的情绪中一时牵连、重叠,无从分离无从独立之时”[6](P.165),诗人L 狂热的初恋则使她成了模糊的少女形象T, 这个形象后来在一个为了出国而嫁人的姑娘身上清晰起来。正如昆德拉一再强调他的作品的“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2](P.32 )一样,《务虚笔记》以如此的方式引导出它的人物来,这人物当然也就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了,它是基于作者关于命运之于人的理解之上的一种想象。在史铁生这里,一个人终于成了自己而不是他人,那是他独特的命运使然。因此,命运即人。他的人物:Z、L、O、N、C、F、WR……都是命运的符码。
那么,命运是怎样决定一个人独特的存在的呢?从其初始状态看来,那不过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它们有时候看似微不足道,却在不知不觉中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方式,造就了不同的人间角色。比如画家Z在这部作品中的人生之路, 就是被他童年的那个下午偶然听到的那几句话所决定的。史铁生将这偶然的一刻名之为人物的“生日”。并为作品中的人物查找出他们的“生日”,不同的“生日”,意味着人物从不同的门进入世界。
“生日”的不同,既取决于客观遭遇的不同,也取决于对遭遇的不同反映。画家Z后来再没有到那座美丽的房子里去找那个女孩, 未见得全是因为那儿的主人把他看做“野孩子”,当然这是主要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如果他能够相信他有理由不被他们看作‘野孩子’,那么,深深的走廊里流动的那一缕声音也许就会很快地消散。如果他有理由相信他的位置只是贫穷但并不平庸并不丑陋,那一缕声音就不会埋进他的记忆,成年累月地雕刻着他的心了。如果母亲没有改嫁,没有因此把他带进了一种龌龊的生活……”[6](P.350)但是所有这些“如果”,在作者看来,最终都不是个人能够支配的,所以Z 最终还是被他的那个生日降生为Z了。
这样的“生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常常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比如作品中C这个人物已经成为一个青年而即将进入爱情了, 就在这时,他的一个真正致命的生日才降临到他的身上,使他成为残疾人C。 于是他不再与WR相混,“他不再是别人,别人仅仅是别人……无比真实,不可否认也无以抗拒这就是你今后的路途,C ——你的路途……你只是你,只是自己”[6](P.407)。无以防备的命运的震惊强行地将人从群体中剥离出来,难以预料的创伤经验促进自我意识的增长,使孤独的灵魂降生人间,这就是命运即人的含义。
这种终于走上了自己的命途“不再是别人”,“你只是你”的人,并非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个性化的人物。作为这部思索的小说的人物,残疾人C即使自杀了,那么这世上某个不死的残疾人仍然是C。小说写道:“写作之夜,C是一个活着的残疾人,还是一个活着的残疾人是C,那都一样。”[6](P.423)这大约就是这部作品必须以字母取代姓名的原故吗。因为姓名是一个专名。专名指称独一无二的对象,那是不可通约、不可归类、不可还原的非同一性的差异存在。而这部作品中的人物意指的则是人的种种可能的命运,并非某一个体专属的命运。残疾人C 在狭义上意指双腿瘫痪的人的命运;在广义上,残疾是人的困境的隐喻,它揭示的是身处困境的人的基本的存在境况。在这种情况下,专名是会对作者的命运之思、存在之思造成限制的,所以史铁生要取消专名。
取消人物专名,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也是存在的。例如他的长篇小说《生活在别处》,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红头发的姑娘”、“拍片姑娘”、“画家”、“看门人的儿子”等等称谓。两位主人公:诗人雅罗米尔和他的母亲玛曼似乎有名。但“雅罗米尔”在捷克语中意谓“他爱春天”,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姓名,不是一个专名;“玛曼”是“妈妈”的同音指代,都不过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代表着任何时代的任何抒情诗人和他的母亲。作者这样做,是因为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所思考和揭示的不是某一个体,而是人身上最黑暗最深刻的激情,以及这种激情可能导致的浪漫主义悲剧——毫无价值却又深刻的悲剧。这种激情突出地表现在各个时代的抒情诗人和像诗人一样的知识分子身上,故雅罗米尔实际上乃是这些人的激情及其悲剧的可能性的写照。在这里,专名以及与专名相伴随的个性化刻画不仅是多余的,而且造成妨碍。基于同样的道理,在昆德拉为思索的小说所追溯的源头布洛赫那里,在他的《有罪的人》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也是以字母A来指代的。是否可以认为, 这是思索的小说在人物形态上的一个带规律性的趋向呢?如果说在叙事的小说和描绘的小说里,包括描写人物心理的小说,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没有姓名的人物是令人不能想到的,那么,不以摹仿现实为旨趣,而以研究存在,以揭示人的种种可能性为目的的思索的小说,反抗人物专名的局限,反抗个性化的美学原则,也就在道理之中了。
3
作为一部思索的小说,《务虚笔记》的故事被思索的逻辑与结构所切割,分散在书的各个部分。如果将它归纳起来,主要是这么几组故事:女教师O与从政者WR、画家Z的故事;残疾人C与恋人X的故事; 医生F与女导演N的故事;诗人L和他的恋人的故事;Z 的叔叔和成为叛徒的女人的故事。比较次要的故事还有Z(或者WR)的母亲与亡夫的故事; HJ(Z的同母异父弟弟)与T的故事;T(或N)的父母的故事,以及“写作之夜”里“我”的自叙与独白等等。
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残疾人C与恋人X的故事虽然在篇幅上只占全书十四分之一左右,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将它理解为那几个主要故事的逻辑起点。在这个故事中,残疾的命运使C 的恋爱权利成了问题:你爱谁你最好是远远地离开谁,放了她吧,那样你就像是一个好人了,否则,你将做一个被指责的“自私鬼”。这看法来自四面八方并内化为当事人内心的道德律令。这道德律令显现为一个悖论:“你爱她,你就不应该爱她”,“她爱你,你就更不应该爱她”[6](P.416)。在这个悖论中,将“她”置换为“他”,对于残疾人的恋人X同样成立。于是“C的心没有停止过哭号。命定的残疾,C知道,那是不可删改的, 可爱欲也是不可删改的”。因为“命运在删改C的肉体时, 忘记了删改他的心魂”[6](P.414)。
那么,以此为逻辑起点,可以伸展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和什么样的故事呢?
第一,如果C屈服或者不屈服于以上那个悖论,那结果会怎样呢? 医生F与女导演N的故事便是从这一问题中伸展出来。F与N由青梅竹马而成为恋人,但当N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西北后,F不敢违抗年老双亲的意志。在他们分手的那个晚上,N向F执拗地发问:“如果爱是真的爱就不可能错,如果那是假的那根本就不是爱……”;“要是我们并没有错,我为什么要放弃,我们凭什么要分离……”;“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遍,N说, 你曾经告诉我的(你说你爱我——引者按),是不是真的?N说,请你告诉我,是不是出身可以使爱成为错误?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爱成为错误?……我不是指现实我是指逻辑,现实随它去吧……”;“我只想证实这个世界上除了现实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什么是真的……我不要求它是现实但我想知道它可不可以也是真的,我求你无论如何开开口好吗?”……而F除了以泪洗面,无言以对, 一夜间黑发变成了白发。如果C反抗那个悖论,坚持于自己的渴望,那么,C 就走进了N的角色,而X则处于F的位置了;如果C屈服于这个悖论,放弃爱情, 则C就走进了F的处境,而恋人X又可能处于N的位置。故F与N的故事在可能性维度延展了C与X的故事。
第二,让C接受那样的道德律令, 也就是让一个人为自己所不能支配的命运去承担道德责任,这公道吗?Z的叔叔与叛徒女人的故事, 便是在这一方向上所进行的思考。这女人当年凭借爱的激情,把敌人的追捕引向自己,使她的恋人——Z的叔叔——得以脱险。 她在敌人的枪声中无所畏惧。“要是敌人的子弹射中了她,她便可大义凛然地去死”,成为英雄,“但是那机会错过了”[6](P.312)。在被捕后敌人无休止的折磨下,她成了叛徒。这是个既可以在爱的激情中成为英雄,也可以在酷刑下成为叛徒的女子,但命运的安排偏偏是放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这使她此后的岁月在一个荒诞的悖论下受到了永世的道德惩罚。这悖论是:“你被杀了,你就是一个应该活着的好人;你活下来了,你就是一个应该被杀的坏蛋。”[6](P.417)小说通过晚年Z 的叔叔重返故地去寻找被他所遗弃的恋人,对这种不公正的道德进行了富有思想穿透力的剖析。
第三,C的爱情权利问题, 在根本上反映的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现实维度,人之间的平等是否可能的问题。女教师O与从政者WR、画家Z的故事便是在这一方向上伸展出来的。WR试图以政治的手段来消除人间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为了获取政治权柄, 他抛弃了自己所爱的初恋情人O,娶了一位要员的女儿。但他在日后的仕途上也遇上了一个无法解脱的悖论:“如果你被贬谪,你就无法推行你的政见;你若放弃你的政见呢,你要那升迁又有什么用处?”[6](P.555)这悖论宣告了“他的宏伟目标永远不过是动听的梦话”[6](P.511),他实际能做和他实际所做的不过是使自己成为拯救者,成为救星,从而成为人上人。画家Z 则坚信不平等是人间永恒的法则。他向以不平等给他以耻辱的社会的雪耻,是用自己的天才和勤奋使“你的崇拜要变成崇拜你”[6](P.501),“要在这人间注定的差别中居于强端”[6](P.520)。而始终守护着平等之爱的梦想的O,一经遇上画家Z,便离开了自己的前夫, 与她崇拜的Z结婚了。于是她掉进了一个无力自拔的问题之中:爱的选择基于差别,爱又要求平等,如何统一?她无法在现实层面达到统一,便自杀了。
第四,何以“命运在删改C的肉体时,忘记了删改他的心魂”, 那爱欲便是不可删改的呢?这问题其实也就是人何以需要爱情,爱情是什么。诗人L和他的恋人的故事,便是在这一问题上展开的思索。 其实这部小说中所有的故事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探讨。它们在思索的逻辑上从C的故事发源,走向问题的东南西北,但无论走了多元, 又都在爱情问题上彼此渗透,互文见义。那么,人为什么需要爱情,爱情又是什么呢?当这一问题由诗人L提出来时,医生F回答说是“孤独”。孤独又是缘何而来呢?这一问,便将这部小说的爱情之思与命运之思内在地关联起来了。因为孤独源于命运,源于人的生命历程中那一个一个“生日”的降临。虽然“生日”因人而异,因时而不同,但每一个“生日”都是一次难以预料的创伤经验,从而令人体会到人间的差别、歧视、羞耻、隔离、恐惧和伤害,致使自我意识在其增长的过程中,独立的自我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即个体从世界中分化出来,即心魂在降生人间之时,便不得不走进戒备、防范与隔膜,不得不走进孤独。而走进孤独的心魂必定生出一个渴望,那就是:走出孤独,回归乐园。这乐园便是爱情。所以人需要爱情,从根本上说就是命定的孤魂需要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是这部小说从命运的角度为爱情给出的一个解释。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将上述从命运视角为爱情给出的解释独特地表述为“残疾与爱情”,并认为这是“生命本身的密码”[6](P.13),即命运与梦想的密码。由此, 小说将有形的“残疾”泛化为无形的“残疾”,将它提升到存在的界面,成为对一切人可能的存在境况的揭示了。与此相应,上述那些相对独立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被思索的内在逻辑组织成为一种昆德拉式的复调结构,形成同时展开的不同声部,随着作者对命运、爱情、存在的冥思不断推进,回旋般地展开,在展开中不同声部间形成互文,其互文性使意义获得相互的训释与提升。你感到它们在小说思索的回旋推进中,都具有一种由个别的具体升腾到普遍的具体的意味。为了制造或强化这种效果,作者还使这些故事中的人物经常相互混淆,使他们在一些细节上,在一些情景中,在不同的故事里相互重叠。我们的阅读行进到这种重叠、混淆的地带,时常感到似乎有一种力量要把我的思索托浮起来,从那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情景之中上升,上升到一种对于存在的领悟之境中去。这是这部小说揭示存在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运思特征。
4
思索的小说因其思索性成为小说的核心与灵魂,故某种相对来说更为直接的思想形式插入到小说中来,便是这一小说形态的一个易见的特征了。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这种相对直接的思想形式的最常见的也是最别致的样式是对“基本词”的不断定义。昆德拉宣称:“一部小说首先是以某些基本的词为基础的”[7](P.70); “我不仅要以极端的准确性来选择这几个词,而且还要给它们定义和再定义”[2](P.122)。例如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长篇小说中所选的基本词是:重、轻、灵魂、肉体、大进军、大粪、媚俗、同情、晕眩、力量、软弱等。昆德拉将特丽莎的依恋、恐惧、自卑等种种情态给出一个基本词“晕眩”。她感到晕眩,什么是晕眩?昆德拉最初寻找到的定义是“一个使人头昏的不可克服的下跌的欲望”;然后,又更深入明确地定义为:“……晕眩,就是沉醉在自己的软弱中。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但又不想反抗它,而是任其下去。人因自己的软弱而沉迷,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所有人的面前瘫倒在大街上,希望脚踏在地上,在比地还低的地方。”昆德拉就这样通过关于特丽莎的基本词——晕眩——的定义,使“我们知道这种晕眩,至少知道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可能,一种存在的可能[2](P.29)”。昆德拉的这种方式既与小说的情景融合得比较好, 又给作品注入了一种直接的思想穿透力,强化了作品对存在的研究性与揭示性。
在《务虚笔记》中,这种相对直接的思想形式突出地表现为其中大量的思想对话。可以说,这部小说中的那些故事、情节和景物,都是写得十分精彩的,但其中写得最精彩的,则是那些对话,那些思想的对话。那些精粹的故事和情节,那些诗意的场景与景物所铺垫、所孕育的那所有的痛苦,那不尽的迷茫,那寻找出路的情绪,那飘忽不定的感悟,都要在这对话中释放出来,澄明起来,撞击与质询、穷根与究底,以获得自己确切的意义。阅读这些思想的对话,有时像看技艺精湛的体操表演,那敏捷到位的高难度翻转,恰似这对话中的逻辑运转。某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在这对话中崭露出了它发人深省的层面,某些为我们忽略或回避的角落被这对话挖掘出了震撼心扉的真相。读着这些思想的对话,你也许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你读小说,读中国当代小说,却生活在真正的思想之中。
我采用“相对直接的思想形式”这一说法,这在昆德拉那里是极力回避的。他把思索的小说中的这种思想形式称为“小说的深思”[2] (P.75),或者统称为“小说式的思考”,以区别于非小说性的哲学思想或其它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形式。他曾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本几十年中作为反专制主义专业人员的长期参考书”的小说,斥为“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读物。[3]据此, 我们也应该将刘心武新时期之初所写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小说中的那些大段议论排斥在小说式的思考之外。因为这些议论并不是真正从小说中那些故事和人物中孕育和生长出来的,这些议论非但没有将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所包含的那些意味上升到它所能够达到的澄明之境,而是无情地将它缩减到其纯时政方面了。由于这些议论是以思考的名义加害于小说的,其影响之恶劣,以至于我们一谈起小说中相对直接的思想形式,就不免心存疑虑。所以“小说式的思考”的提法是绝对必要的。
作为“小说式的思考”的思想对话,在《务虚笔记》中若依对话者的变化,可以分为若干类型。其中就对话形式而言,最有特色的,是由“写作之夜”的“我”所参与的那些对话和众声对话等形式。
在这部小说中,“写作之夜”的“我”具有双重身份。首先,他是这部作品中所有人物在名义上的创作者,因此,“我”可以像上帝一样知晓这些人物内心的困惑迷茫所思所想,可以自由地不经任何桥梁与过渡而来到他们的身旁,进出他们的心灵。其次,“我”还是一个参与到书中故事与人物中来的人物。在书中他人的故事中夹杂着“我”的故事和“我”与他们共同的故事。这样“我”作为书中人物的一员,又与其他人物具有平等关系,这就使“我”与他们的对话成为可能。“我”的这种双重身份使这成为可能的对话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灵便自由:无论书中的人物是孤身远行在外,抑或正与恋人幽会,只要需有一个他者意识参与进来启动和促进思考之时,“我”皆可突然幽灵附体一般与其人物展开心灵的对话。
例如小说第16章,Z的叔叔晚年重返故地去寻找那个叛徒女人, 在他独行于葵花林间时,“我”与他拉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内心对话。这对话追问剖析咄咄逼人,它锋利无比地揭穿了人间对叛徒的道德义愤,其实来源于害怕落入叛徒曾面临的那种可怕的处境:疼痛、死亡、屈辱、殃及无辜的亲人,被扯碎的血肉和心魂……。正因人们深知这处境的可怕,才创造出更为可怕的惩罚——叛徒,来警告已经掉进那可怕处境的人,警告他不要殃及我们,不要把我们也带进那处境。“叛徒”一词就是这样,“作为一种警告,作为一种惩罚,作为被殃及时的报复,作为预防被殃及而发出的威胁,作为‘英雄’们的一条既能躲避痛苦又能推卸责任的活路,被创造出来了”[6](P.383)。而一当“叛徒”一词被创造出来,我们就更加害怕被殃及,因为“我们也可能经受不住敌人的折磨,我们也可能成为叛徒,遭受永生不完的惩罚”[6](P.384)。这结果是,我们为了预防被殃及而发出威胁,而威胁也威胁着我们。这样,我们便制造了人的更为可怕的处境。这时,人的唯一指望只能是:不要被敌人抓住,不要被叛徒殃及。这就导致我们更加憎恨叛徒。
当对话追击到这种滑稽的恶性循环之时,那深深隐匿着的叛徒之耻辱的真相便豁然地呈现出来:“一个叛徒的耻辱,不过是众多叛徒的替身,不过是众多‘英雄’自保的计谋。”[6](P.387)在“写作之夜”的“我”与Z的叔叔的这一长串的对话中,鞭辟入里的追审拷问, 将步步退守的辩护直逼得无路可逃,把一个在别人眼中,在自己心里与叛徒处于对立价值之两极的革命英雄高尚的灵魂深处的卑污无情地逼供出来,从而拷问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问题上自以为是的道德感中的不道德。它同时,还以令人感动的人道精神深情地揭开了“叛徒”这个耻辱的词语覆盖下的作为一个人的不应被忽视的求生欲望,作为一个人的不应被忽视的价值,并进而从Z的叔叔那灵魂深处的卑污与不道德中, 挖掘出他那历经几十年岁月而不能忘怀的沉默的爱来。作者将这种爱作为一种希望,寄托在这个因人类自身的弱点而来的惩罚引起惩罚,惩罚造就惩罚的世界上,希望通过这种爱使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应有的珍视,使每一个人的价值得到应有的尊重。
读着这段对话,我想到了鲁迅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的话。看来,在这方面,史铁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并不逊色的。
众声对话,是这部小说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思想对话类型。在小说第21章中,围绕第3章“死亡序幕”中O的自杀展开了一场各抒己见的众声对话。这部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人物,如诗人L、女导演N、医生F、 从政者WR、Z的弟弟HJ和弟媳T、残疾人C等, 他们带着他们独特的意识与视野,在这一章里畅所欲言地表达了他们由对O自杀原因的不同的推论、 分析所伸展开来的有关差异与平等、有关爱与性的思想,从而使思考面对同一个问题从四面八方多维立体地走来,形成思想之众声交流对话的狂欢节。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场众声对话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所有这些参与对话的人物,他们在这部小说中并非处于同一故事中,有些人物在作品可能的故事中并不具有谋面的可能。如果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法则,他们是无法这般聚合起来进入对话的;如果硬要将他们聚会在某一客厅之内,则势必要为此而煞费苦心地敷衍出一些节外生枝的情节来。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由于所有的人物都来自“我”的写作之夜,因此,无论他们在各自的故事中可否相遇聚会,他们都在“我”的“写作之夜”。于是,这不可能发生在故事中的众声对话,却可以发生在“写作之夜”。因此,这场众声对话实际上是从“写作之夜”里传来的。在“写作之夜”,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针对作品中的一个章节的情节内容,高谈阔论,而“我”则对他们的分析、推论、思辨,或质疑问难,或点头称是。这一对话形式其实是一种元小说的形式,只不过它不像通常的元小说那样,由叙述人谈论小说,揭示小说的叙述性;而是由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会聚于“作者”的工作室,对小说的某一章节内容开研讨会。这一对话形式极具巴赫金所述的狂欢节性,它将这部小说的思想对话推向了高潮。
此外,这部小说比较特殊的思想对话形式还有人物与不明身份的声音对话,不明身份的两种声音之间的对话。在“写作之夜”的“我”所参与的对话中,除了上述的直接与人物对话外,还有拟想式人物对话和代叙式人物对话。同时,这部小说还存在着人物与人物之间、故事与故事之间的非直接对话的对话性关系。
在一部小说中采用或创造出如此多样的对话形式,对作者史铁生来说,无非是为了更充分、更自由灵活、更简捷有力地实现思想的对话,实现他对于存在的小说式思考。设若这部小说只采用传统的人物对话形式,我想那不仅会导致篇幅的成倍增长,而且,其思想的对话也绝不可能在一部小说中达到如此的广度、密度、深度和明快透辟。这便是《务虚笔记》在对话形式上的创造与探索之于思索的小说的意义。
《务虚笔记》自1996年发表以来,在有关它的不算热烈的反应中,一个较普遍的看法是,它不像小说。但从昆德拉的小说学来看,它乃是一部奋力走在以小说合并哲学的道路上,且已经走了很远的小说。以昆德拉的小说学的视点来研究这部作品,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也有利于总结和发展“思索的小说”的理论。
收稿日期:2000—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