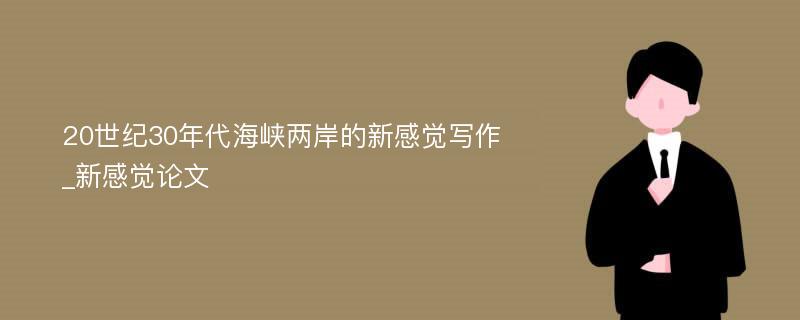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海峡两岸的新感觉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峡两岸论文,新感觉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1-0081-07
大陆学界关于新感觉派① 的研究,近年来颇为热络,但研究者更多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和上海的新感觉派倾注热力,相比之下,台湾新感觉书写② 则是一个未被充分展开探讨的领域。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推行最力者刘呐鸥③ 就出身台南世家。稍后,留学日本的翁闹④、巫永福⑤、王白渊⑥、郭水潭⑦、吴天赏和郭秋生⑧ 等人直接汲取日本新感觉派的营养,创作了一些新感觉味颇浓的小说。这里,我们将回顾同时发生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新感觉书写的流脉,力求揭示都市是以何种映像出现在新感觉书写的文本中,这些作家做过何种语言实验和叙事实验?如何倾向精神分析的人性解剖和交感式的感觉描写?这些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一、海峡两岸新感觉书写
回顾海峡两岸文坛的新感觉书写之始,恐怕必须回溯到1927年台湾人林华光和杨浩然在上海暨南大学参与组织成立的“秋野社”,其同仁刊物《秋野》月刊可能是最早介绍日本新感觉派的刊物,杨浩然还翻译过片冈铁兵的《新结婚二重奏》,但知者寥寥。倒是经过刘呐鸥之手,带起了一股新感觉派小说的热潮,从而构筑起跨越上海、东京和台湾三地的炫异多姿的新感觉文学版图。
(一)摩登上海:海峡两岸作家的上海制造
刘呐鸥留日期间即对日本新感觉派抱有极大的兴趣,1927年,他由日本赴上海震旦大学就读,不久,即出资并协同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创办了“第一线书店”,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被看作是上海新感觉派的滥觞。同年,刘呐鸥翻译出版的《色情文化》⑨ 花了相当大的气力来介绍日本新感觉派文学。1930年刘呐鸥具有新感觉实验意味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出版。1932年5月,《现代》杂志的创刊,标志这些作家作为一个流派已经集结在一起。台湾学者评价说: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刘呐鸥,透过个人的“新感觉式”的小说创作与“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翻译,以实际写作、出版,结合文艺同仁制造“新感觉热”⑩。如其所言,新感觉派的其他作家的确是通过刘呐鸥才了解日本新感觉派的,施蛰存曾回忆说:“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的文艺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和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论著和报道……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11) 这些文艺书籍对施蛰存和穆时英等人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刘呐鸥对上海新感觉派的出现在资本支持和文本示范上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上海新感觉派可以看成是由海峡两岸作家携手打造的。遗憾的是,大陆学者多年来一直忽略了刘呐鸥的身份背景。
此后新感觉书写在中国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消失不见。倒是台湾作家翁闹、巫永福、王白渊、郭水潭、吴天赏和郭秋生因留学日本而承继了更多的日本新感觉派的文学真传,其新感觉书写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彰显,他们在大陆都市文学的断裂处,接续了新感觉书写这一脉络。
(二)怪兽东京与回眸乡村:台湾文学“本格化”建设中的新感觉书写
如果说上海新感觉派的擎旗者是刘呐鸥,那么台湾文坛上新感觉书写的号召者则是郭秋生,1934年7月,他批评了台湾文坛的前期创作中出现的“感觉的世界是从所不曾顾及的”(12) 的倾向,指出未来的创作方向应充分探究感觉的分野及人们内部的心理世界。他本人还创作了以揭示人物内心为要务的小说《王都乡》。在此前后,直接沐浴于日本新感觉派余韵之下的巫永福、翁闹、王白渊、郭水潭和吴天赏也无意识地暗合了这一方向,并成为主要的实践者。这些作品主题多是反映市镇生活,表现出一定的“新眼光”、“新态度”和“新感觉”。巫永福自言在明治大学文艺科时,“影响我甚深的文豪有山本有三、横光利一、评论家小林秀雄先生。”(13) 翁闹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过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但其小说中可以寻到很多酷似的话语,并且,他和巫永福都曾是日本留学生台湾艺术研究会的成员,二人曾是过从甚密的朋友(14),至于在新感觉书写这一问题上有过何种切磋现在不得而知。此外尚有王白渊的《唐璜与加彭尼》、翁闹的好友吴天赏的《龙》、《蕾》(1933年)、《野云雁》(1935年)、郭水潭《某个男人的手记》(1935年)等作品,也带有由于殖民地台湾早熟的、颓废的物质意识而带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游离与脆弱。
在日本,横光利一等人并不完全以书写都市作为新感觉派文学的唯一要务(15),他们视都市为“恶之华”。此点正合乎了台湾留日学生的根深蒂固的乡土倾向。他们虽生活在日本都市,但皆来自台湾乡村,笃信以乡土道德来衡量都市,流露出对都市生活的厌恶感和恐惧感,展现了都市与乡村文化价值的冲突,此时台湾与东京的现代化程度有很大的差距,这对于更多受农业文明影响的台湾人来说,打破了原有的地理归属感,无疑会演变成心灵的灾难,让东京变成了不断膨胀的都市怪兽。也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更多感受到的是都市的吞噬本能,让进入都市的陌生人,无法融入,最后只能悲惨死去,如用野兽来喻指日本的《首与体》、仇视都市现代文明的《天亮前的恋爱故事》、刻画都市对生命力戕害的《可怜的阿蕊婆》、恋爱至上主义者最终回归乡村的《某个男人的手记》、对资本主义道德进行批判的《唐璜与加彭尼》等等一系列作品。纵观台湾新感觉书写的文本呈现出一个相似点就是他们都心仪日本新感觉派小说中所具有的乡土气息和诗化色彩,保持了浓重的乡土味和草根性,与刘呐鸥、穆时英等人流连于华砖丽瓦之间的都市书写相比,他们笔下的都市书写是充满了消极感觉,没有向往,更多的是不适和逃离,从而成为30年代相对于上海新感觉派的另类叙事。
阅读海峡两岸的新感觉书写,如果说刘呐鸥和穆时英更多是在摩登上海中徜徉,施蛰存以现代人的意绪重铸历史人物,王白渊和郭秋生是以社会主义思想解读历史人物的心理感受,翁闹和巫永福是对心理距离非常遥远的东京的审视,海峡两岸作家的新感觉书写所描绘的城市与人文,构筑出跨越上海、东京和台北的都市风景线。在不同时段中,此类都市书写都呈现出反传统秩序的艺术形式和思想主题的试练,我们由此得以揣测海峡两岸新感觉书写的文学论述场域中浮现的乡村与都市的诸种文化选择。
二、凸显感觉的语言实验
谢六逸在谈到日本新感觉派的文字修辞技巧比以往小说推陈出新之处在于:“新感觉派注重‘感觉’的装置和‘表现’的技巧”(16),从而抓住了形式技巧的关键。30年代的上海新感觉派是从形式主义文学的角度来模仿日本新感觉派的,他们注意到日本新感觉派从主观感觉出发去表现客观,从而改革表现方式,直至语言词藻。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一出版,其新奇的艺术实验,就成为介绍的重点:“文学的新手法,话术的新形式,新调子,陆离曲折的句法,中国文字趣味的改革,风俗研究的更新”(17),此后的新感觉书写也非常重视小说形式的革新。从艺术实验的角度,可以看出海峡两岸作家的创作都具有高度类似的语言实验。
新感觉书写追求瞬间感觉的细腻直达,将主观感觉印象融于客体之中,强调内向性,因而在反映外部事物时,不是客观地再现本来面目,而是从自我的主观意识、情感和知觉出发去描述、感受和评价。上海新感觉派刻意追求新奇的主观感觉印象,展现人的拟物化和物的拟人化,审美视角内转,将主体感觉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于是外在事物和场景经过主体感觉的过滤,便具有了浓重的新感觉的意味,各色气味、色彩与感觉的混乱交织的世界。在刘呐鸥的笔下,跑马场里有“流着光闪闪汗珠”的白云,看台上的观众“滚成蚁巢般”,天空因为异物充斥而变得“郁悴”起来,连英国旗都显得“太得意”(《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在穆时英的感觉世界里,笑声都变得非常淘气,“骑在绯色的灯光上从窗帘的缝里逃出来”,卖报的小孩子因为霓虹灯的映照而“张着蓝嘴”叫卖,舞娘太夸张的“嘴唇上的胭脂”“透过衬衫直印到我的皮肤里”,此类感觉书写在他们的文本中随处可见,那些无生命的外界景物活转过来,显示一个非常态的意念中的现实世界,表现出具有交感意味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并呈的独特意象。但是上海新感觉派致力于心理感觉的强化,并一味制造文字上的标新立异,却又掉进了形式主义的泥淖。
陈大悲曾以欣赏的笔调指出新感觉派的语言实验是“一字一句,一句一段。或断断续续地想象,不拘于修辞的修辞,现成的文法的摆脱,一连串的名词,一连串的形容词。错综的,突兀的,生硬的,老练的,短而有劲的,构成了新的风格,新的情调。”(18) 更得日本新感觉派语言衣钵的应是翁闹和巫永福。翁闹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不突出,但他力图雕镂某种生活感受,却颇得新感觉的精髓。《憨伯仔》中有这样的语句:“他们都感觉到,一如一天容易过去,长久的岁月也成了一块飞逝而去。看来,过去就如呆板的铅灰色旷野。”这种比喻像极了横光利一那句被奉为新感觉经典的语句,“白天,特别快车满载着乘客全速前进,沿线的小站像一块块石头被抹杀了。”(《头与腹》)这里同样是结合视觉经验的联想,将岁月/沿线小站比喻成一块一块迅速流逝的灰色旷野/石头,暗示了生命反复、回绕的机械化过程,真实地揭露出无奈的空虚感。至于巫永福在描写自然时,常采用拟人的手法,赋予万物适当的生命,同时作者的主观思想跃入描写对象中,让客观对象活跃起来。
但我们更要看到,海峡两岸作家的新感觉书写语言实验的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30年代的上海,国语的文学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早期创作中的过分白话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上海新感觉派高度重视语言实验恰好是对文学语言的过分口语化这一倾向的反拨。然而这些语言实验在当时并未被看好,如刘呐鸥在小说创作中,书面语和外来语占了大部分(19),因而让人觉得洋腔洋调,别扭生硬。至于台湾作家的日语文学受到横光利一等人大量使用文语体的影响,存在着语言高度凝练和转换过快的问题,让读者颇不适应,如翁闹的小说当时就有身为“台湾文艺联盟”执行委员的徐琼二批评说:“因为句子极短,对文章全体有令人觉得未尽然的感觉……宛如火车疾驶的铁轨一般,因为各段铁轨的衔接,使火车摇晃震动,更不舒服的是使读者饱尝车内不断‘喀顿、喀顿’噪音的干扰似的。”(20) 海峡两岸的新感觉书写都力图以语言的陌生化来更新读者的阅读经验,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读者的不适。但不能否认的是,新感觉书写一直试图重建语言体系,对语言的长度、节奏、组接进行刻意经营,剔除口语,重视书面语言,开辟崭新感觉空间。从凸显感觉的角度来探讨新感觉书写的语言思想和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实践,可以说,新感觉派小说的语言特色不仅是其小说各方面特色的载体,更是其作为独树一帜的新感觉书写美学的显著标志。
三、意识流叙事倾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新感觉派实际上是把日本这个流派起先提倡的新感觉主义与后来提倡的新心理主义两个阶段结合起来了。其中刘呐鸥、穆时英的作品如果说具有较多新感觉主义特点的话,那么施蛰存的作品主要是新心理主义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心理分析派的作品。”(21)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海峡两岸的新感觉书写皆以情绪理论作为主调,它非常强调内心世界和外界景物的关系,景物所呈现的色彩往往是主体心理的投射和映照。最初尝试意识流书写的恐怕要先推举刘呐鸥和穆时英,刘呐鸥的《残留》初步生硬地展现了一个刚死去丈夫的年轻少妇的内心欲望;穆时英的《上海的弧步舞》在工人因事故致死的描写中,以断续感觉、意识流连缀起来,对人物弥留之际的意识流动进行了恰切的展现,与刘呐鸥比起来,略显高出一筹,其书写显得更加自然、贴切和真实。同期的施蛰存意识流书写更为圆润,更为熟捻,他是“情绪理论”的倡导者也是最重要的实践者,他摒弃了刘呐鸥等以快速的节奏反映生活的方法,而用朦胧的舒缓的笔调来分析人性深处的颤栗。《魔道》、《巴黎大戏院》和《春阳》中,出现过非常地道的意识流。上海新感觉派在描写与发掘人物的意识、潜意识、微妙的心理变化以至变态心理方面,其跳跃般动感的“印象”、“新感觉”就有文学“意识流”表征之影子。从而构筑了一个个充满弹性与张力的心理空间,带动了心理型小说的流行用语,成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台湾的新感觉书写更多受日本新心理主义小说的影响,对人物微妙心理的细腻把握非常出色,这又胜出上海新感觉派略显矫情的情绪描写。翁闹和巫永福的部分作品如《音乐钟》、《残雪》和《首与体》描写了少年男女间“发乎情、止乎礼”的交往,轻染着感伤情调的风格,带有精神审美的神韵。但在另一些作品中对都市情欲意识展现则带有更多颓废主义的成分,如翁闹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天亮前的恋爱故事》将情欲书写推展到疯狂的极致,具有精神病理学意义,其叙事明显受到意识流小说的影响,短短的情绪化句式,几乎通篇的“内心独白”,将人物的精神分裂流(即精神上的不一致或者反常)展现出来,关注的是人物的精神世界万象杂处的境况。这里有作者的夫子自道:“在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偏执狂,我是疯疯癫癫的。”曾有论者认为这篇之后“可能他真的疯狂了,或可能他已走上自我毁灭之途了”,(22) 纵观其作品,其笔下人物也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如经常陷入意识流般的自言自语,翁闹个人的命运罹难却使他的癫狂的内心书写因祸得福,其小说因为“充满了现代主义的敏锐感觉、心理分析和象征手法”,而被高度评价为“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可说到了翁闹的手上,才有独树一帜的表现,才开启了另一文学艺术的崭新领域”,(23) 至于巫永福的《首与体》则呈现了局部的意识流,整篇小说都徘徊在“为了摆脱那些紧紧盘旋在脑海里的意念”(指反复出现的狮子头和羊头的意象)的情绪之中,这里频繁出现的与小说情节发展无关联的意识独白,目的是想要制造出小说的复调世界,其中的虚拟“独白”,正是巫永福有意识地营造光怪陆离的人物内心世界。他的《黑龙》和《阿煌和父亲》中以小孩子的心理刻画为主,意识流动更快,跳跃更大,更加符合孩子的认知特点。王白渊的《唐璜与加彭尼》与施蛰存致力于古典人物的现代意识挖掘极为相似,作者跨时空地在小说中创设了欧洲历史上的情圣唐璜和30年代的美国黑手党领袖加彭尼的对话,有些对话就是独语,更接近意识流的色彩,主人公是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背叛者而出现,幻想着苏联模式是解救资本主义最好的选择。值得指出的是,与上海新感觉派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描绘大上海男女醉生梦死、腐朽堕落的生活不同,台湾作家常借意识流书写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善于从偶然的小事中挖掘其象征意义。这里,新感觉书写的意识流叙事摈弃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倾向于对人的潜意识和二重人格的挖掘,从而扭转了传统叙事文学中人物性格扁平的流弊,此种试练表明作家的人格意识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以上简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海峡两岸作家的新感觉书写在文学“意识流”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他们最初都是通过日本新感觉派而吸纳了当时外来的各种新进的先锋文艺思潮,不过因为作家的实际运作水平不同,个人主体的倾向性不同,而使文本呈现出复杂性:刘呐鸥、穆时英强调描写主观的感觉印象,反对理性的加工和提炼;施蛰存倾向于弗洛伊德和霭里斯;翁闹、巫永福和王白渊等人吸取了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于新心理主义……总体看来,无论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乃至台湾文坛上的一系列新感觉书写均与文学“意识流”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与西方意识流小说零散杂处不同的是,新感觉书写的意识流只是作为一种手法,穿插运用。虽然有现代派的基本特性,又没有全盘转入歧途。整个叙事是依循人物情感的表达而进行,依循的是心理的逻辑,而不是外在时空的逻辑。
综上所述,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以新奇的艺术实验,提示了另类文学的存在,台湾新感觉书写心仪日本新感觉派的语言实验,甚至创作出颇具日本风的语句,其语言技巧娴熟,感觉描写与意识流表现得更为自然贴切,摆脱了刘呐鸥看似还稍嫌硬涩的语言困境,灌注了现代主义文学传达的两项最重要的讯息——运动感和变化感,也是新感觉派书写区别于他类书写的显著标志。新感觉书写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但他们所致力的形式实验,却影响至今。
四、殖民处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尴尬
对照阅读海峡两岸的新感觉书写,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会生长出相似的文学“恶之华”,新感觉书写的文本中所潜藏的对话动机是什么,思考20世纪两岸新感觉书写的变异文字策略,我们会从不同时段的文本中依次发现,所谓与现实无涉的新感觉实验,实际上承载了因租界和殖民的真实存在而带来的文化认同的尴尬。
上海、台湾和东京三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产生于斯的新感觉书写往往又牵涉到整个大时代,此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都是小说在感受都市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庚子之后,留日学生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类似“弱国子民”的屈辱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笔下表现过。新感觉派作家却以叙事立场的模糊和消解展现了令后来的一些批评家诟病的主体意识的大转变。在传统文学中,作家会对笔下的人事强加以是非判断。新感觉派小说销匿了作家的叙事立场,不再交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价值期待,而是并列地呈现自我的观察,将价值判断的任务交给了读者。刘呐鸥、穆时英等人虽饱读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新兴文学作品,但在小说文本多流于日常生活的描写,缺乏义正词严的国族认同的立场,似乎无法达到中国现代小说主流论述中对于“感时忧国”主题的高度关怀;与左翼立场的分歧,也是上海新感觉派备受质疑的原因之一。而此后刘呐鸥和穆时英的死于暗杀(24),也使二人如何面对国家分裂与国族模糊的困境,成为难以探寻的敏感话题,最终成为文学史上的悬案。至于刘呐鸥的台湾人身份,又游走于台湾、东京和上海等地,他个人的国族意识究竟如何,是日本的二等臣民?是中国人?其复杂性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但事实上,从其文本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他力求以现代主义的手法来探讨无产阶级文学关心的劳动、机械等问题。与刘呐鸥成功地从殖民宗族国日本脱身相对照,身处日本的台湾作家始终摆脱不了殖民时代的国族认同问题和殖民现代性问题的困惑。因而一些知识分子更多地走向个性化的自我世界,充满了殖民地的过客意识,翁闹是典型的代表,“以30年代中期而言,他(翁闹)所走的纯文学新感觉派的路线,与杨逵所走的无产阶级的普罗文学路线,正是两个极端。”(25) 但我们也要看到,翁闹的挣扎,如《残雪》中的林春生挣扎于纯朴而落后的台湾与现代而摩登的日本之间,其实就是翁闹本人的真实写照,至于更鲜明地表现翁闹的左右为难的情境的则是1936年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举办的“台湾文学当前诸问题”上,在乡土文学和殖民地文学的问题上,翁闹主张:“形式上与日本文学相同,内容上属于台湾”,文字表现则应“寻求日语和台湾话的折中”(26)。事实上,这种折中的困境带给他更多的困惑,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翁闹必将面对的是解决不了的国族认同的困境。至于巫永福笔下的留学生S不也是一直烦恼着的“首与体”的问题。而这烦恼也不啻是台湾人的苦恼,日据下台湾人的头是“日本”,其体“台湾”抗争着头,并试图摆脱头的驾驭。与翁闹不同的是,巫永福鲜明地表达过自己的国族之情,诗歌《遗忘语言的鸟》、《祖国》表述了对“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祖国的热切呼唤,其内心的祖国就是中国,这种感情在异民族的统治下更加强烈。就在台湾岛内作家不得不接受殖民统治的严苛束律之下,身处日本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揭露知识分子艰难的处境,不论在台湾在东京同样都是觅寻幸福而不可得,这就是殖民地情境下知识分子宿命的命运。整体看来,在三地的文学场域处于高度组织化与民族意识高涨之际,新感觉作家各有各的困惑:刘呐鸥的复杂国籍与文化认同,穆时英的暧昧政治立场,施蛰存的政治回避主义,巫永福和翁闹等人国族认同上的困惑……海峡两岸的作家正是面对种种文化认同的困惑,从而带来了文本中消解宏大叙事,缺乏明确的政治导向,不特设鲜明的批判客体和意识形态,缺少淑世的理想主义倾向,埋头致力于文字技巧的试炼,遁入感觉的世界里,却带来了文学转型的契机,不仅给小说带来表现手法上的革命,也带来了主题的拓展,将读者“带进都市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同时深入人类异化的心灵世界”。(27) 但这种逃遁并未带来这些作家的身心安适,反而在小说文本中随处都露出苦恼的痕迹,那些华洋杂处、文化交错或是以文化立场变换的处境之尴尬其实质都暗示了这群知识精英的文化认同尴尬。
思考20世纪30年代跨越三地的变异文字策略,新感觉书写实际上在文本中镶嵌了知识分子灾难重重的心理现实,其虽脆弱,但比起同期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文学作品往往富含更丰富的能指。尤其是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翁闹、巫永福、郭秋生、吴天赏和郭水潭等人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他们的文学实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各自的文化场域中殖民话语和类型化文本进行文字搏斗的结果。
注释:
①新感觉派是日本评论家千叶龟雄针对1924年间围绕在《文艺时代》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和片冈铁兵等人的称呼,后来这一名称被活跃在上海的刘呐鸥等人原样套用,由于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加盟,引起文学界的侧目,遂被称为上海新感觉派。
②所谓新感觉书写是指以悟性活动调动起触觉、嗅觉、视觉、听觉等各感官的机能,以比喻、象征、自由联想等手法来突出主观体验的文学创作,常倾向于表现超验的感觉、变形变态的幻觉、错觉以及联觉,其与象征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有着密切关系。海峡两岸的新感觉书写不具备一般文学流派所具有的固定组织和架构,具有跨地域、跨时段的书写特性,但其审美感觉方式、思想内涵和写作模式上都极为相似,因此笔者以新感觉书写概括称之。因篇幅所限,所论体裁多限小说,对其他体裁稍加忽略。值得指出的是台湾诗人杨炽昌曾经接受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岩藤雪夫与龙胆寺雄的影响,推动了台湾超现实主义诗风,其意义正如戴望舒之于上海新感觉派,只因体裁的差异而被隔绝于流派之外。
③刘呐鸥(1905—1940),本名刘灿波,出生于台南柳营第一世家,毕业于日本应庆大学,1928年将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作家保尔·穆杭的都市文学引进上海,推出文学半月刊《无轨列车》,译有大量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品、理论主张,1940年遇刺身亡。
④翁闹(1908—1940年),台湾彰化社头人,毕业于台中师范,1934年,前往东京发展,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兼有文学评论和新诗,小说有《音乐钟》、《戆伯仔》、《残雪》、《罗汉脚》、《天亮前的恋爱故事》和中篇小说《有港口的街市》等。参阅张羽:《试论日据时期台湾文坛的“幻影之人”翁闹》,载《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⑤巫永福(1913年—)台湾埔里人,日本明治大学文艺科毕业,从事过小说、诗歌、戏曲、论文、俳句、短歌的创作。曾经发表过《首与体》、《黑龙》、《山茶花》、《河边的太太们》、《欲》等作品,这些小说深受日本新感觉派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
⑥王白渊(1902—1965年)台湾彰化人,东京美术科系研读,1932年曾与东京留学生在发起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创刊《福尔摩沙》杂志。主要作品《唐璜与加彭尼》、《荆棘之道》等。
⑦郭水潭(1907年—)曾攻读日本古典文艺,后转入新诗创作,曾入台湾文艺联盟,其诗歌多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其小说《某个男人的手记》记述了一个恋爱主义者逃离乡村最终又返归乡村的情绪体验,多少带有个体的感觉色彩,曾获1935年的大阪每日新闻社佳作奖,曾领导“盐分地带”。
⑧郭秋生(1904—1980年)台湾台北人,1933年与廖汉臣等人组织了台湾文艺协会,任干事长,1934年协会创刊《先发部队》,给予刊物精神上物质上的大力支持,主要小说有《死么?》、《鬼》、《跳加冠》、《王都乡》等。
⑨1929年,刘呐鸥翻译的《色情文化》既选有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的作品,也有普罗作家林房雄、小川未明的作品,这本译著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新感觉派不满于当时社会的停滞状态,试图从新感觉派小说探寻出路,也为刘呐鸥等人打破上海文坛的沉寂局面提供了借镜。
⑩许秦蓁:《文学史的一张缺页——新感觉派是台湾人的上海“制造”》,载《刘呐鸥全集·影像集》,台南县文化局编印,2001年,第16页。
(11)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12)郭秋生:《解消发生期的观念行动的本格化建设化》,《先发部队》1934年7月,东方文化书局复刻本第18页。
(13)《巫永福全集》小说卷Ⅱ,传神福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页。
(14)1933年7月,台湾艺术研究会发行机关志《福尔摩沙》,翁闹曾是《福尔摩沙》的投稿作家,与张文环、吴坤煌、刘捷、巫永福等人都有“过从甚密”(许俊雅语)的交谊,但翁闹与巫永福的文学友谊到底有多深,二者在受到日本新感觉派影响之时,是否有过文艺思想上的交流,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有一说翁闹平日结交的多是日本文人,而对在日本的台湾作家则无法维持长久不渝的交情,加之翁闹为人狷介,又参证了巫永福和翁闹二人之间可能只是君子之交。
(15)日本新感觉派不完全是都市文学之中,如横光利一的《苍蝇》、《日轮》、《拿破仑与顽癣》、《头与腹》、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春天的景色》、十一谷义三郎的《青草》多是以乡村小镇为背景的非都市小说。由此可以看出刘呐鸥等人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接受,明显有误读的成分,其混淆了法国的保尔·穆杭和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品之间的区别,保尔·穆杭的代表作《敞开的夜》和《关闭的夜》是典型的都市小说,刘呐鸥等人过分强调了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书写特质,相比较而言,翁闹、巫永福等人的书写更具有日本新感觉的本质特色,即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区位的描写。
(16)谢六逸《新感觉派———在复旦大学的讲演》,原载《现代文学评论》1卷第1期,1931年。
(17)署名壮一,为刘呐鸥,载于《新文艺》杂志的目录页的背面,1930年第2卷第1期
(18)陈大悲:《新感觉派表现法举例》,原载《黄钟》第1卷第29期,1933年。
(19)《刘呐鸥全集·日记集》上 康来新 许秦蓁载《刘呐鸥全集·影像集》,台南县文化局编印,2001年,第38、34页。1927年,刘呐鸥的日记大量使用中日文,还夹带英法文,语言使用的驳杂至少暗示刘呐鸥写作语言的混杂性,日记中曾说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小,也许是福建话的单语少,每每不能设想出适当的话来表达心里所想的”(1月5日),以及提到自己在学习国音会话(1月3日)都说明了他本人汉语写作存在一定的问题,其汉语写作的弱势能力直接带进了这些翻译作品和创作中。
(20)徐琼二:《〈台新〉读后》,原载《新文学月报》第二号,1936年3月2日发行。
(21)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09页。
(22)张良泽:《关于翁闹》《台湾文艺》95期1985年7月15日。
(23)张恒豪:《幻影之人——翁闹集序》,《台湾作家全集·翁闹·王昶雄·巫永福合集》台北市:前卫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24)刘呐鸥担任过汪精卫伪政府所主持的《国民新闻》,1940年秋,刘呐鸥之死的真正原因,或被解释成孤岛战乱时期的和平运动殉难,或被认为是沦落为日本侵韩时期卖国求荣的汉奸,如今成为难以解释的谜团。至于被指斥为“卖身投靠,认贼作父”的穆时英,据司马长风观点:他是受国民党中统的派遣,出任新闻宣传处处长的。他在担任国民新闻社社长期间遭暗杀,系国民党军统特务所为。两人的政治身份模糊成为立场判断难下的重要原因,从而也成为上海新感觉派作家的政治话语难以深入进行解读的原因。
(25)张恒豪:《幻影之人——翁闹集序》,《台湾作家全集·翁闹·王昶雄·巫永福合集》台北市:前卫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26)翁闹在1936年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举办的“台湾文学当前诸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台湾文艺》第三卷第七、八号合刊(1936年8月)座谈会记录《台湾文学当面の诸问题》,翁闹在《乡土文学、报告文学、殖民地文学》《关于小说的趣味》等部分的发言。
(27)郑明娳、林燿德:《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与新感觉派大师施蛰存先生对谈》,《联合文学》第六卷第九期,199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