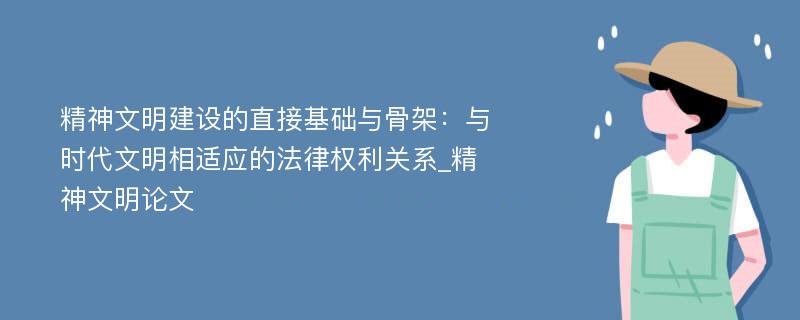
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基础与骨架:合乎时代文明的法权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权论文,骨架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关系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恩格斯的判断,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某个很早的阶段”就产生了立法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历史昭明,为习惯法和成文法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就是“法权关系”;迄今,人类文明发展的所有阶段,这种关系都不失为文明的保障与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孪生姊妹,为社会各界所重视;然而,法权关系及其与两个文明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法权关系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决定作用,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法权关系是社会文明的主要纽带与保证
人类社会之所以异于动物者繁多,归根到底是因为人类具有不同于动物的智能型生产劳动能力。因此,人类结成了不同于动物的广泛社会关系。文明社会,尤其是近现代社会,更是一张纵横交织、上下重叠、繁杂无比的关系网。例如,以两性结合为造端的血亲关系,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化关系,以公共权力为杠杆的政治关系,以占有方式为分野的阶级关系,……以及人们熟悉的地缘乡土关系,业缘行业关系,宗教信仰关系,家庭邻里关系,学朋友好关系,乃至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形成起来的许多新的社会关系,覆盖着整个社会躯体。这些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陆续出现,大都同人类生产劳动条件的开拓、成果的形成及其占有形式同步发生和发展。社会进化过程表明,没有生产劳动的存在与发展,便没有这些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没有这些关系的存在与发展,便没有社会的发展与两个文明的升华。这些关系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些关系无论是作为静态的历史现象而存在,还是作为动态的历史过程而运作,都同一定时代的文明规范相联系,例如,思想道德规范,行政管理规范,法律制度规范等。易言之,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来看,这些关系是靠更高的关系范畴来维持和推动的。这些关系范畴或者形成于社会自发的传统习惯力量,或者形成于国家与法权的强制性力量。二者虽然都具有传统性与持续性,在推动文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但是,后者因为是国家主权管理的表现,所以包括主权管理的主体(统治者)与客体(被统治者)二者的关系及其变化本身,都属于法权行为及法权关系。马克思在谈到争取人权和公民权时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法定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是统治阶级或国家的意志表现,既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又渗透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的一切人和事都不可自外于法权关系,即使在专制统治下权贵能够以言代法,也是由于他们居于法权关系网的宝塔之尖。社会没有法权关系,就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其他各种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都可能遭受破坏,文明秩序将荡然无存。
二、法权关系是精神文明的直接基础与骨架
国家与法权是人类从原始民主进入阶级专政之后,社会统治(或管理)制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没有作为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工具的国家机器,就没有作为这种统治与管理的法权关系;反之亦然。所以,作为上层建筑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与法权现象,虽然同精神文明一样,其发展与升华必然历史地存在于文明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之上,受不同的种族、民族、信仰、社会历史传统乃至物质生活条件和自然条件所制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一切社会文明,都要存在于一定形态国家与法权规范的基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乃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架构之中。在有国家存在的历史阶段,超国家与法权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是不存在的。
法权关系是统治阶级意志规范化并系统化的表现。迄今,已定型的表现形式历经了如下三个阶段的演变:一是奴隶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可以当作牲畜来使用和宰杀的生产者奴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奴隶主阶级的君主专制或贵族共和的奴隶制形态;二是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农奴、依附农和佃农,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及官僚制的封建制形态。这两个阶段法权关系的文化表现的核心是亲亲尊尊的宗法制观念和以君臣、父子、夫妇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三是资本家和工人在法律上各自有了“独立平等”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以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为旗帜的民主共和制统治关系。这种新的法权关系,摒弃了世卿世禄和宗法官僚的人为特权,只承认经济活动中的金钱力量,并且在文化领域内以“民主个人主义”为中心一以贯之。同上述三种法权关系相适应的三种精神文明,显然以其法权关系为中介,并且随着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发展,直接靠法律来保护,作为社会存在的法权关系成为精神文明的直接基础乃至基本标志。
三、当代中国法权关系面临十分复杂的挑战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随着剩余劳动被少数人占有的私有制形态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矛盾的发展,私有制将被否定,社会将自觉地摒弃“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旧的法权关系,建立起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法权关系。同这种变革相适应,在上层建筑中要建立起为广大劳动者充分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在思想文化领域实现“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化。但是,由于迄今出现过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它们的法权关系都未出现马克思曾设想的那种典型性质,而是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法权关系——资产阶级法权乃至封建特权和社会主义法权的矛盾混合体。旧中国工业少有发展,封建小农经济汪洋大海,通过革命手段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的新的法权关系,当然不可能超越这种混合体。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私有经济得到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以及政治体制中已经进行的某些调整与改革,改变了以往法权中那种僵化的、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的成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变化、思想观点乃至价值观念的变化。但是,由于改革不仅是在混合法权关系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改革本身又具有复杂性;所以,改革开放越是向深广发展,就越使人们感到现存的法权关系具有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所有制形式多元并存的相互矛盾及公有制主体地位弱化;二是劳资双方在法理上并重及实际上劳动者地位相对弱化;三是分配原则多元化及按劳分配原则被模糊;四是决策的民主理性规范及实际决策的非程序表现;五是为人民服务原则与公仆宗旨淡化及以权谋私的现象蔓延;六是超经济手段造成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及社会主义的合理占有原则失去制约作用;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权在社会基层未形成规范体系及封建的乃至黑社会的非法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的应有法权关系;八是教育权劳动权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出现缺失及由此而加剧相对贫困;九是经济活动中的短期行为破坏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法律遭受践踏;十是法权定位的三大环节——立法、守法、执法出现脱节现象,金钱与权法交易在某些地方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现行法权关系面临的这种复杂挑战,使当代中国法权文明至少在实践中处于非清晰状态,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直接的和明显的消极制约作用。
勿庸赘述,精神文明与法权关系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不同范畴,既不可划等号,又不存在相互影响上的机械比例关系。但是,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科学与法律两翼之上的新型文明,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理顺社会主义的法权关系为基本要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